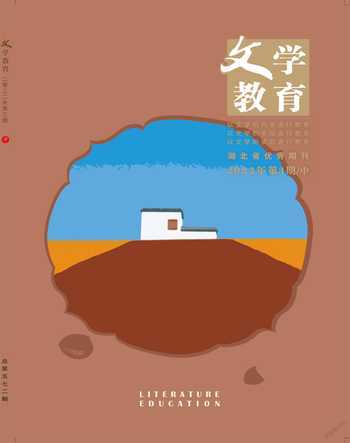李商隐诗的个性特征及其成因
丰晓流 王宏玮
内容摘要:李商隐的诗歌由于意象迷离、广纳比兴、典故纵横等而导致了极具审美意义的“乱辞无绪”之现象,其成因不出人生际遇、审美个性及时代折射等。
关键词:李商隐 诗歌 人生际遇 时代 审美 折射
王国维在谈及南宋词人姜夔的词作时,曾经不无遗憾地说:“虽格调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1]其实“雾里看花”未尝不美,真正巧妙的“隔”不是坏事,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郝库利斯石”,它“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象磁石那样,能吸引其它铁环。”[2]如此环环相吸,自然能引起读者浮想联翩和敏锐感应,“隔”从何来?可见,只要朦胧得法,也可以成为好诗。李商隐的诗即是如此。
表面看来,李诗“瞻万物而思纷”[3],擅长将富于变幻的意象错错落落地组织成“百宝流苏”[4]:或步步纡回,或层层重迭,或来之无端,或去之无迹,蝶梦迷离,鹃声悲切,孤鸿欲问,蓬山万重……亦或处处设典,句句比兴,问杨柳“如何肯到清秋日”,叹莺啼“有泪为湿最高花”。如此等等,其幻象之凄迷,变化之多端,乱辞之无绪,实乃如秦观之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令人难以捉摸,在感知中遭遇“隔膜”。然透过依稀影象的楼台津渡,却可以使得人们更敏锐地想象到记忆中印象最真切、兴趣最浓郁的楼台和渡口。鉴赏者可以把真感情渗透到“雾”和“月”中,展开幻想,创造出为自己所眷念、神往的楼台、渡口,从而“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二月二日初》)。正如清代诗论大家叶燮所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5]李商隐之诗即是如此,诗人凭借其极具幻象的“乱辞无绪”,在黄昏凄艳的晚唐王朝中雕塑出了自己独特的“绿暗红稀”之美。那么这种极具审美意义的“乱辞无绪”缘何而生,是诗人“有心插花”还是“无意为柳”,笔者试图作出以下之分析。
一.根源于诗人生平的悲剧遭遇
《锦瑟》一诗,古来聚讼纷纭,有人说是爱情诗、咏怀诗,也有人说是咏物诗、游仙诗,更有甚者,说是爱情、咏物、、咏怀、游仙兼而有之。试想,古代传说中的蝴蝶已经扑朔迷离,却又偏偏出入于诗人的凌晨残梦之中;一个古代帝王的失国,恰恰是托为暮春杜宇的悲啼;苍茫大海之上,明月照着珠光和泪影;深埋着蓝田玉的泥土中,又冉冉升腾起无从掩抑的光彩,如此等等。这里的韵味、状貌、神采不仅相得益彰,竭尽变化,而且又深深地应和着诗人心灵的节奏起伏,一个凄怨、美丽、富于诗意的古乐器承载了如此多的“絮果兰因”、神话传说与悲欢离合,难怪后人仰其项背而仍不得其要旨。笔者认为,诗人“中路因循”和“才命两妨”(《有感》诗: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是此类诗歌“破茧而出”的主要原因。
处于牛李党争夹缝中的李商隐,终其一生四十几年,几乎可以说与两派争斗相始终。再加上甘露事变后宦官势力愈益猖狂,朝官互为倾轧,有增无减。在一场大屠杀和翻云覆雨的政治漩涡中,卢仝惨死了,白居易变得胆小怕事,李德裕远窜到红棉花开、鹧鸪飞舞的南荒了……黑白不分,直言遭祸。诗人早年写《有感二首》和《重有感》時那种少年气盛、无所顾忌的气概,不能不随着世故的增长和“腐鼠”势力对自己折磨的增加,多少有所收敛,至少是他不能不重新选择一条寄托遥深的道路了。于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回避现实的矛盾,两者之间,不能不要求他抉择。尽管在他心中,王屋山上的“白道青松”还分明留下记忆,可是自己毕竟是“爱君忧国”的,所以有“我欲乘风归去”的苦衷。这是他在《偶成转韵》中曾经自我表白的,也可以说是他毕生的艰难心事。就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他一方面固然要用清新的目光去批判现实,但却又不得不和晚唐的某些诗人一样,用他们精心构成的艺术羽纱编造出一个美妙的精神避难所和艺术的七宝楼台,作为苦闷象征和心灵浸润,也作为理想的寄托。李商隐在政治上遭受到一连串的排挤、打击,被卷入党争的漩涡深处,不都是和缔婚王氏有关么?他的“华年”之忆,不正是既寓家国之伤、也抒身世之愤么?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仕途原来如此紧密。清人赵执信曾推崇吴乔的“诗之中须有人在”的话并加以发挥:“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6]”斯言极是也。
二.固化于诗人的性格、气质。
李商隐十岁丧父,在就学时代便挑起抚养家庭的重担。生活煎熬和人情冷暖把一个孤贫无依的孩子培养得多愁善感,世故人情更是早熟,使得他更需要家族亲人的温暖。特别是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当他母亲去世丁忧后一段时期中,他先后为亲人营谋葬事达五起之多,连一个小侄女寄寄的死,都为她写下了一往情深的祭文。这就更可以看出诗人在那个世情淡薄的社会中,特别需要得到“宗绪衰微”的家族的慰藉。他对于这些镌印着辛酸、惆怅的少年往事,一方面诚然感到凄凉,但另一方面却又偏要深深地沉浸其中,经过精细入微的体验,铸造出一些既与严峻现实有间隔而又隐约地透露出对当前自我心影沉潜观照的朦胧意境。
纵观李商隐时代,正是中唐诗歌向晚唐诗歌过渡的时代。时代的苦闷导致了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倾心于内心体验和艺术技巧的锤炼,斯时,“为时而著”的新乐府高潮早已趋于沉寂,连“鲁殿灵光”的白居易都心安理得地在洛阳府邸“安营扎寨”,唱出“知足乐天”的闲适与恬淡。年轻一辈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们虽“书生意气”但又有何良方“挥斥方遒”?虽然也共通于“感时花贱泪,恨别鸟惊心”的伤痕,但三人折射时代、社会,共鸣人生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杜牧把“作赋论兵”和“听歌纵酒”集于一身,怀着跌荡坦率的豪情唱出“十里春风”的“扬州绮梦”;温庭筠则选择了“歌台舞榭”或“荒村茅店”通晓音律地吟诵,留给时人亦或后人“风尘仆仆”的身影与“颓唐”的情调;而李商隐却是那么执着而惆怅地留恋着“乐游原上的夕阳”,绵邈而深沉的弹奏着那象征着华年如水的“锦瑟”。显然,这是三人创作道路和感情气质并不相同使然,三种不同的个性特征使相同的“时代光感”产生了三种迥然不同的折射,亦或可以说三种不同的个人气质选择了不同的时代“线条”、“意象”、“色彩”浅斟低唱。清初钱谦益如是说:“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若喑而欲言也,若魇而求语也,不得不纡曲其指,诞慢其辞……此亦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7]。此乃正是对李商隐个性特征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委婉”、“曲折”之投影。
三.“成像”于晚唐时代的“群体感伤”
1.“成像”的“背景”条件
德国美学家里普斯总结过“堵塞性”产生的悲剧性法则——灾难加强了价值感。晚唐的诗人们大都醉心于唐王朝开元、天宝前的光荣史,希望它永远“荡荡乾坤大,瞳瞳日月明”(杜牧《感怀诗》),然越是醉心于唐王朝昔日的辉煌,人们的向往便越是受到遏制、障碍、隔断,从而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堵塞。正是这种堵塞,又自然不自然引发人们对“堵塞”前的怀念,而随着堵塞的加深,怀念的痛苦更为加深。隐居在山西老家的司空图给自己庄园的亭子题名为“休休”,这二字背后的“怀念”冷嗖嗖直逼人眼,甚至连贵为节度使的风雅诗人高骈都直言不讳地供认“将军醉罢无余事,乱把花枝折赠人”(《广陵宴次戏赠幕宾》)。
由此可见,越是土崩瓦解,越是歌管纷纷。对如梦如烟的开元、天宝元年盛事的回溯,几乎成为晚唐诗歌的普遍题材。这应该可以说就是诗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缺陷与怅惘所产生的背景(《乐游原》)了,只不过李商隐所目击的“夕阳”已经不比李白登宣州谢朓楼时的“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也不比李贺的“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了。即使同诗人自己的《行次西郊》相比也不再有“此地忌黄昏”的满腔愤慨。显而易见,除诗人内心深处不可排遣的凄惋外,此“夕阳”还饱含了李商隐对唐王朝盛世的缅想,恰恰是一位晚唐初期文人的缅想。虽说夕阳西斜,但毕竟还没有到司空图用“休休”一词作为他园亭题名的时代。天际斜阳,终于留下了几分“可怜的鲜艳”色彩。鲜艳,驱使他们醉心于镂金错彩;可怜,说明那些金彩透露了黄昏晚照。“狂来笔力如牛弩”(《偶然转韵》),这是诗人长期沉浸在绵邈意境中陡然爆发的惊呼,然而这惊呼却转眼为严酷现实所压垮。诗人有时简直是消沉得不想歌唱了,因为他感到“徒劳恨费声”歌唱只是白费。
显然,这不是李商隐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它是文人在夕阳犹好而终近黄昏时分的普遍苦闷,也是在夕阳的回光返照中对虚弱美、病态美的追求。
2.“成像”的“光感”条件
如果仅仅只有晚唐时期的“群体感伤”,或者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仅仅只限于感伤而没有形成“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时代氛围,那么也不可能孤立地产生李商隐诗歌极具审美意义的“错辞无绪”;如果没有晚唐整个诗坛在诗歌创作、诗歌评价上的系列艰苦探索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不可能有李商隐绵邈朦胧的“标新立异二月花”。对诗歌艺术规律探索的热衷,促使当时一些诗人耽于苦吟。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寄柳舍人宗元》),李频的“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转引《北梦琐言》),李贺的“呕出心始已”,杜牧的“苦心为诗,惟求高绝”(《献诗启》),都可以说明把诗歌当做生命或刻意写诗,已经成为当时的风气。
唐人的诗歌理论原来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的:一条是从陈子昂、白居易到皮日休的道路,侧重于诗歌的现实内容与社会意义;另一条则是从皎然到司空图的道路,对诗歌的艺术性进行苦心探讨,并结合佛家的“境界”学说,提出了意境的理论。苦吟风气无疑是和侧重艺术一派相通的。皎然曾经对“不要苦思”說进行过反驳,认为“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至于那种“有似等闲,不思而得”的作品,只是另一种“高手”的事。由此可见,取境的生面别开和富于锤炼,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晚唐诗歌艺术有走进象牙塔的某些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中国美学传统之一的意境理论,促使中晚唐诗歌创作积累了一些比较自学的实践经验。否则,晚唐末期司空图的《诗品》要概括二十四种意境和风格,是不可能的。
李商隐显然是属于侧重艺术的一派。但从他的诗歌看来,却又绝对不同于苦吟者的推敲。他之所以可贵,是把体验自己情感和外在事物的精切,同“韵外之致”结合起来,把刻镂深细的形貌和意在言外的韵味结合起来。刻镂深细反映了晚唐诗歌艺术的精致,但刻貌取神却更远溯于殷璠所倡导的“比兴”之说,有异于“轻艳”之词。难怪李的爱情诗突出精神美,而很少象一些香奁体的庸俗琐屑的描头绘足了。由于李走的是“兴象”一路并和“意境”携手,这就很自然地形成绵邈和精细相结合的特征。用司空图的话来说,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巴山夜雨,涨满秋池,这不是眼前历历可见的景物么?然而轻轻一转,同一巴山夜雨,却又经过时间推移,成为陈迹,成为来日缅想中闲话的内容。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假想,一种盼望,通过“适当”的摇曳生姿而体现了空灵的境界。
这是李商隐渊源屈原和经过长期流莺“巧啭”的辛勤探索而形成的艺术特征,但也反映了中唐诗人围绕诗境说而探讨的艺术理论在晚唐初期的宝贵实践。
3.“成像”的“聚焦”条件
倘若只有晚唐时期的“群体感伤”与晚唐诗人的“群体探索”,而没有晚唐时期城市经济的相当繁荣,没有这种相当繁荣的城市经济所带来的旖旎风光,那么也就不会涌现晚唐进士阶层“裘马轻狂”的“诗歌原型”;也就不会产生奢靡、精致、光怪陆离的“诗歌意象”。自然,李商隐“离奇的幻想、大胆的比兴、凄迷的编织”等也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现摘录张籍之弟张肖远的《观灯》一诗作为此种繁华之极的见证: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处处见红光。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
星宿别从天畔出,莲花不尚水中芳。宝钗骤马多遗落,依旧明朝在路旁。
京都长安的早春又是怎样的呢?——想得芳园十余日,万家身在画屏中。[8]
东都洛阳又是:九陌鼓初动,万车轮已行。[9]
第一商业都市扬州的繁华随手拈来,便有张祜的诗: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还有王建的名作: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以上罗列,均为中唐以后社会繁华的“艺术纪录”,它显然不同于过去以金粉驰名的南朝绮罗的留影,那时,南朝的繁华还缺少中晚唐夯实于城市经济基础之上的通都大邑的绚烂色彩,因而“鲍照、沈约”们的审美感受也就不可能象中晚唐诗人那样丰富,他们不可能渲染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整幅画面,从而形成更高级的人化了的自然[10]。
晚唐诗人却做到了。李商隐正是在这样一个“日下繁香不自持”(《曲池》)的特定时代,孕育了他的“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楚宫》)的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的。李商隐显然将这种时代折光拌和着自己的创作个性,从而编织出串串重重叠叠、大大小小的“珠链儿”。
综上所述,李商隐诗所呈现出的极具审美意义的“乱辞之无绪”,实乃诗人人生际遇、审美个性、时代风情所自然折射,鉴赏者若能知其人,论其世,析其时,那么就会练就自己文学鉴赏中的“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的审美敏感度,从而达到文学鉴赏中的最佳境界。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9.
[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7.
[3]陆机.文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
[4]敖陶孙.诗评[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7.
[5]叶燮.原诗内篇[M].济南:齐鲁书社,2001,5.
[6]赵执信.谈艺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9.
[7]钱谦益.注李义山诗集序卷十五[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9.
[8]施肩吾.长安早春[J].全唐书卷五一七.
[9]于武陵.过洛阳城[J].全唐书卷五九五.
[10]吴调公.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J].文学遗产,2009,(1).
(作者单位: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省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