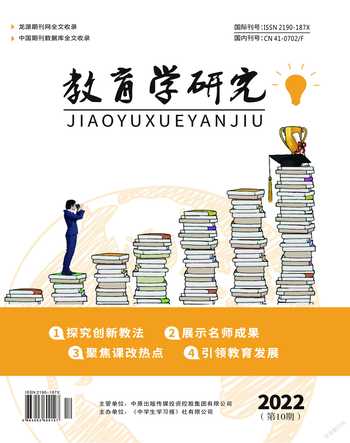迷人的想象,悲哀的现实:论唐亚平《黑色睡裙》中的戏剧性
摘要:《黑色睡裙》一诗因其鲜明的叙事特征而获得了戏剧性的艺术效果,成为唐亚平《黑色沙漠》组诗中独一无二的一个现象。本文通过对诗歌中戏剧性情境、戏剧性动作、戏剧性语言、戏剧性结构和戏剧性冲突的分析,从中探究诗人如何通过这些表现手段来抒发情感,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揭示,对现代化转型语境下的都市文明进行艺术化解构,笔者希望本文能为诗歌评论拓展话语空间,也为当代诗歌创作中多种文体的有机融合提供一些可能的启示。
关键词:叙事;戏剧性;表现手段;现代化转型;隐喻
《黑色睡裙》是唐亚平《黑色沙漠》组诗中的一首。这组创作于1985年的诗歌使诗人成功跻身中国第三代女诗人之列,形成了当代女性诗人对“黑夜意识”的预感[1]。与组诗中其余十来首诗一样,《黑色睡裙》题目中引人注目的“黑色”既代表了诗人彼时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也表达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普遍情绪。由诗人的女性身份而产生的女性诗学已成为学界自然且惯常的批评视角,这一视角将女性的身体写作、女性的生命体验、女性的灵魂自白、女性的价值立场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释。
新批评理论家伯克 (Kenneth Burke)认为文学作品是有关人生障碍的表现和对其象征性的解决,因而所有文学作品形式必定含有戏剧的成分[2]。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进一步提出“诗的结论是各种张力的结果——統一的取得是经过戏剧性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逻辑性的过程”,主张把诗中所有成分都看成戏剧台词[2]。如果说伯克和布鲁克斯是从较为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去强调人类所有文学作品的戏剧性,那么《黑色睡裙》一诗则集中体现了诗歌这一文体中的戏剧性特质:它虽以抒情为鹄的,但文本肌理却整体显现出叙事的特点,因为叙事者“我”以自己所处的内视角叙述了一个简短而完整的故事,使诗歌具备完整的情节,包含叙事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而通常来讲,叙事诗中往往具有戏剧成分,这是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情节是戏剧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遗憾的是,除了陈剑澜在其文章中提到《黑色睡裙》是《黑色沙漠》里唯一一首叙事诗之外[3],评论界至今鲜有论者从戏剧性角度对这首诗进行过研究。基于此种现状,本文试图结合戏剧的基本要素对这首诗进行分析,旨在探讨诗人唐亚平运用了哪些戏剧性表现手法使诗歌获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希望能为诗歌评论拓展话语空间,也为诗歌创作提供一些可能的启示。
根据通常的戏剧理论观点来看,戏剧性主要体现在戏剧动作、戏剧语言、戏剧冲突、戏剧情境、戏剧悬念、戏剧场面和戏剧结构等几个方面。本文将根据《黑色睡裙》这个诗歌文本中所实际表现出的戏剧特性进行分析。
一、戏剧性的情境
兰色姆对诗歌戏剧性之一的戏剧情境有过这样的描述:“要理解诗歌,‘戏剧情境’差不多是第一门径。诚如理恰兹所言,许多诗歌如没有它几乎乏善可陈。如果失去戏剧情境的吸引力,勃朗宁的戏剧独白一定十分单薄,因为它根本缺乏我们希望在诗歌中看到的那种总体肌质”[4]。而所谓的戏剧情境,在我国戏剧理论家谭霈生看来,是指促使戏剧冲突爆发、发展的契机,是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条件[5],具体体现在两个关系最紧密的要素之上:一是事件、一是人物关系[5]。
在诗歌的开端部分,叙事者“我”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我”的处境,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诗歌中事件发生、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我在深不可测的瓶子里灌满洗脚水/下雨的夜晚最有意味/约一个男人来吹牛[6]
第一诗句中的叙述借助“瓶子”这一容器隐喻来形象说明,“我”的身体空空荡荡,需要借助外物来填充,从后文得知,空虚的感觉主要来自情欲之火的灼烧,所以即使用洗脚水也难以将其填补,如果说第一诗句所形成的困境主要是缘于主体的身体原因,那么第二诗句中外界寂寥而喧闹的雨声则烘托了“我”的心灵困境,因为雨的存在阻隔了“我”与外界的联系,从而陷入身心双重困境,让“我”无比孤单寂寞。在这种处境下,第三诗句中“约一个男人”来家里便成为解除困境的一个最佳办法。其中,数量词“一个”说明将要到场的男人只不过是万千世界中很随机的一个符号,其年龄、身份和性格都是不确定的,充其量只是满足特定情境下“我”的需要的一个工具人,而“我”和他也显然是陌生人的关系。但我无法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所以“来吹牛”便成了一个可以被替换为“制造意义”的自欺欺人的蹩脚理由。显然,明明“我”内心的动机是解除身心困境,但口中的理由是吹牛,这就为后来诗歌中事件的发展既设置了悬念又埋下了伏笔。这样一来,充满未知数的戏剧性情境就成为人物行动的特殊实验室,在这里上演的行动将最终检测出人物的真假、善恶与美丑。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后文中诗歌的戏剧性事件在不断发展变化,但这一情境依然是人物一系列行动的起点,在继续为行动提供缘由。
二、戏剧性的动作
动作作为戏剧的基本表现手段,向来在戏剧艺术中非常关键。戏剧动作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外在动作和内在动作。外在动作是可观看的动作;内在动作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现。黑格尔说:“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5]。 同时,需要进一步指出,戏剧的主要因素不是实际的动作情节,而是揭示引起这种动作的内在精神[7]。
由于这首诗中的人物只有叙事者“我”和“一个男人”,所以诗歌中的动作表现为两个人互动的结果。由前文得知,因为是“我”主动约请别人到我家中,所以“我”等待客人到来的一系列动作便自然而然首先出现在读者眼前:
我放下紫色的窗帘开一盏发红的壁灯/黑裙子在屋里荡了一圈[6]
由“放下紫色的窗帘”、“开一盏发红的壁灯”、“穿黑裙”、“在屋里荡了一圈”等动作可以看出,叙事者“我”是一个喜欢浪漫且性格奔放的女人,虽然自称是叫人来吹牛,但“我”的一系列肢体动作说明,为了让心向往之的约会能够成功,“我”在用心营造温馨迷人的氛围,幻想着浪漫的二人世界,并预演着释放本我的激情之夜。
而接下来,在“我”打开房门之后,眼中来客的动作却是这样的:
他进门的时候带着一把黑伞/撑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6]
来客“带着一把黑伞”的动作说明,即使在这样一个密雨如织的夜晚,他也害怕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行动,所以才用黑色雨伞来进行遮掩。这样的动作不禁让人推测到,来者要么是一个有妇之夫,要么就是对此次约会心存戒备。而他将雨伞“撑在屋子中间地板上”的细节动作一方面暗示出他没想和眼前穿着黑色睡裙的女人共舞,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一个见机行事,随时准备逃离现场的胆小鬼。
在看到这幅情景时,“我”不再对约会抱有希望,但由于是自己主动邀请对方前来“吹牛”,所以这时候,将见面模式由“约会”切换为“吹牛”便成为无奈中的权宜之计:
我们开始喝浓茶/高贵的阿谀自来水一样哗哗流淌/甜蜜的谎言星星一样的动人/我渐渐随意地靠着沙发/以学者的冷漠讲述老处女的故事/在我们之间上帝开始潜逃/捂着耳朵掉了一只拖鞋[6]
用浓茶来招待客人,说明“我”切换回了自己的主人身份,开始努力将两人的关系保持在一个非常客套的距离之内,并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智,使自己不至于因为心灵空虚和身体饥渴而沦陷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但由于两人之间的谈话空洞无物,华而不实,所以“我”的坐姿也渐渐慵懒随意,不再故作庄重,“我”给对方讲述老处女的故事,既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嘲讽,也是对对方的戏谑和鄙视。
所以,虽然整首诗歌中的戏剧性动作是外在的,但这些动作却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中最深刻方面的精彩折射,它们将人物内心的深层动机和心理变化通过形象的外部动作显现出来,实现了戏剧性动作的内在和外在统一。
三、戏剧性的语言
颇有意味的是,在这首叙事性极强的诗歌中,除了叙事者“我”和来客的动作描述之外,人物之间没有具体的对话内容,而是自始至终通过“我”的独白式语言来展开故事的全部情节。同时,叙事者使用的语言又是滑稽讽刺的,它们除了揭示人物的心理现实外,还富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比如,在客人到来之前,对于“我”的一系列精心准备,叙事者的自述是“他到来之前我什么也没有想”,“门已被敲响三次”“我”才去打开。这与她预演浪漫、充满期待的真实心理形成了极大的悖论。这些自述至少说明,一方面,“我”是一个想要以强大姿态示人的女人,如果坦率表露自己对约会的满怀期待,可能就无法为自己接下来的失望和尴尬留下余地;另一方面,对于都市男女雨夜约会这样的事情,“我”在潜意识里并不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只能故作淡定矜持,心口不一。
在故事的转折部分,在“我”渐渐识破来者伪君子的真实面目之后,诗歌的语言表现出更大的反讽意味:诗人用“高贵”修饰“阿谀”,并将后者比喻为自来水,说明“我们”之间的谈话索然无味,缺少实质性的内容;用“甜蜜”形容“谎言”,还说它像星星一样动人,是对两个成年人之间廉价的逢场作戏的辛辣讽刺。
就这样,男女主人公仿佛是当众表演的演员,在观众面前上演着一出滑稽讽刺的现代喜剧,将人生无意义的东西撕裂开来丢在人们面前。本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上帝,但哲学专业出身的唐亚平长于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并能够运用语言这一媒介将现实和想象巧妙裁剪拼贴,形成了极具张力的艺术表现空间。于是,鉴于主人公的滑稽表演,诗人便引入上帝这样一个代表西方世界里信仰、真理和本质的重要形象出场,让他作为全知全能型的观众和裁判,注视两位演員的表演并做出道德审判。但在亲眼目睹了现代人的可鄙可悲面貌之后,就连上帝也是如坐针毡,最后竟然狼狈潜逃。“潜逃”一词在此发挥了画龙点睛的功效:它既说明了上帝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掌握所造之物灵魂和行为的能力,为自己不能仲裁现代人的灵魂纠纷而深感汗颜难堪,更重要的是对上帝神圣形象进行消解,使他也沦落为一个在读者眼前落荒而逃且掉了拖鞋的小丑,从而实现对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都市文明的解构。借助这样的戏剧性语言,读者起初会对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动作忍俊不禁,但在笑过之后,难免会思考黑色幽默叙事背后的荒诞现实。
在诗歌最后,叙事者再次将场景切换到雨夜:
在夜晚吹牛有种浑然的效果/在讲故事的时候/夜色越浓越好/雨越下越大越好
如果说开端时的雨景更多烘托了“我”孤单寂寞的心绪,那么结尾处诗人再次动用黑夜和雨景则不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简单重复。它的出现不但强化了抒情主人公内心的悲哀,也使得诗歌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与尤金·奥尼尔在《琼斯皇》一剧中鼓声的表现主义手法相似,它们将“我”内心的绝望、无力和悲哀用具体可感的颜色和声音得以外化,实现了内外交融,情景合一的艺术功效。
四、戏剧性的结构
完整性和统一性是任何样式的文艺作品都必须注意的问题,是艺术标准之一。而实现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是结构的课题[5]。通常来讲,对于戏剧作品而言,动作是最主要、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因为它能够将戏剧的冲突、情节、场面等串联起来。所以戏剧结构的基本任务就是选择不同人物的动作并将它们组织在一起,使它达到完整性和统一性。《黑色睡裙》一诗在结构上的特色也是使其富有戏剧性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这首篇幅不算太长的诗歌中,故事发生在雨夜里一对男女身上,如果按照动作单元构成情节的观点来看,那么诗歌的戏剧性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环形反讽特征:
(1)动作的开端——希望约会:雨夜里“我”由于身心的空虚寂寞,想找一个男人来约会;
(2)动作的发展——准备约会:“我”制造浪漫气氛,预演激情之夜;
(3)动作的高潮——“约会”的过程:两个人在交流过程中一个故作矜持、欲擒故纵,一个畏首畏尾、虚情假意,所以约会最终降为虚伪、无聊、滑稽、廉价的过场戏;
(4)动作的落潮——对“约会”的失望:“我”渐渐识破对方的伪君子面目,约会希望破灭,故而索性拿“老处女的故事”来亵渎游戏对方;
(5)动作的结尾——雨夜中的绝望:夜色和雨景加重了我的哀伤,孤独的阴影面积比之前更为扩大。
可以看出,从诗歌开始时“我”对约会的热烈希望,到最终互动后的绝望,诗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反讽式结构;从开始到结尾一直伴有雨景,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但前后两个雨景因为“我”心境和情绪的巨大反差说明了生活不但停滞不前,反而在无聊的重复中增加了哀伤失望,愈加显出现实的灰暗残酷。
五、戏剧性的冲突
“冲突”作为戏剧艺术特性和本质之一,具有广泛而牢固的理论基础。在谈及戏剧冲突时,黑格尔说过:“人类情感或活动的本质意蕴如果要成为戏剧性的,就必须分化成一些不同的对立的目的,这样,某一个别人物的动作就会从其他发出动作的个别人物方面受到阻力,因而就要碰到纠纷和矛盾,矛盾的各方面就要互相斗争,要求实现自己的目的”[7]。
诗歌虽然是以叙事者“我”的人称来讲述,但真正牵动意志之线的显然是诗人本人。作为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中國诗坛的女诗人,唐亚平以其深邃而敏锐的艺术眼光洞察到了由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变迁。表现在这首诗歌中,女人是在家发出邀约的主人,而男子是被动赴约的客人;女人是宁愿坚守老处女身份的强女人,而男人则是唯唯诺诺、软弱顺从,缺乏男性气质的胆小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阴抱阳式的两性和谐相比,现代男女的角色在此发生了结构性的颠倒错位,所以即使是万能的上帝也只能潜逃,宣告约会失败。
可见,虽然诗歌中的人物没有明显的外在冲突,却因为双方内心深处的较量而使冲突变得复杂尖锐。由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男女角色和地位的深刻变化成为诗歌内在戏剧性冲突的深层原因:女性在与男性的激烈竞争中逐渐挤进社会舞台中央,但在心灵深处又希望从男性那里获得回应,有所依靠;男性愿意出演女性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但又无法接受女性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在男女们为自己争取舞台话语之时,双方内心深处的焦灼和撕扯便使得他们不愿表现真实自我而是互相较量。于是,两性虽然同台演出,却按照各自拟定的剧本自说自话,身体虽近在咫尺,而心灵却有如万水千山之隔,由努力控制社会话语权力的一个极端不幸滑向了生物性别异化的另一个极端。所以,黑色睡裙成为这场冲突的一个道具,其出场时的华丽迷人和落幕时的灰暗哀伤正深刻隐喻了发生在现代社会男女两性之间和谐的破坏和难以和解的震荡性危机。
六、结语
著名戏剧人类学理论家巴尔巴(Eugenio Barba)认为那种被现代人遗失的戏剧是一种社会行为方式:“什么是戏剧,如果试图减少这个词到某种明确的东西,我发现是男人和女人,人类相遇在一起。戏剧是在一种被选取的环境中的一种特殊关系——一种文化意义上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戏剧概念,那便是人类的相遇、交流,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8]。戏剧作为与时俱进的人类艺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致力于对人类危机境遇的揭示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也许,正是诗人唐亚平洞察到了戏剧的本质精神,发现了戏剧精神对于文学乃至整个人类的重大意义,所以她在诗歌创作中便运用了戏剧性的表现手段,而这些手段不仅让《黑色睡裙》在她的“黑色姊妹”中独具一格,而且将现代人在生存的残酷自然法则和社会通则中须臾不能离弃的叙事本领提高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引发读者的深沉思考。
参考文献:
[1]汪剑钊.女性自白诗歌:“黑夜意识”的预感[J].诗探索,1995:80.
[2]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72.
[3]陈剑澜.谁的80年代?——重读唐亚平《黑色沙漠》[J].南方文坛,2017(3):131.
[4]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M].王腊宝,张哲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06:41.
[5]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98;102;11;209.
[6]岑晨钰.唐亚平组诗《黑色沙漠》.2016.10.7.<http://www.douban.com.>
[7]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248;257.
[8]陈世雄,周宁,郑尚宪.西方戏剧理论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1119.
作者简介:吴生艳(1984- ),女,宁夏盐池人。 宁夏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