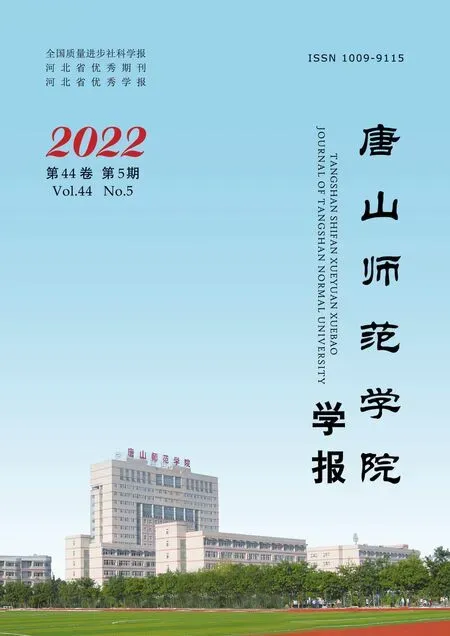生命的诗意,自由的联兆—— 评王蒙长篇新作《笑的风》
李旭斌
生命的诗意,自由的联兆—— 评王蒙长篇新作《笑的风》
李旭斌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笑的风》以广阔性的视角展现了新中国60余年的时空变迁,通过知识分子傅大成的两段情感经历,记录了时代变化给一代人的思想、情感、记忆带来的震荡。小说自始至终的诗意建构是王蒙在其作品中对生命和人性的经验性表达,而纯净感伤的爱情空间则试图超越主客体关系追求一个丰富多姿的自由世界。《笑的风》印证了作者不仅注重外在的“形似”,更深入到内在的生命哲思,提醒人们在有限的生命活动中洞察自由的超越性。
王蒙;《笑的风》;生命;自由
2019年12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王蒙的中篇小说《笑的风》,卷首语却指出这是“一部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小说发表后,作者自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是其创作历程中“前所未有”的“把我自己迷上了,抓住了”[1]1的一部小说,于是又在庚子新春将其“扩容”为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
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到还是高中生的傅大成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听到了风中传来的女子的笑声,萌动了青春的情愫而写下了一首小诗——《笑的风》。由此展开了傅大成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和婚姻波折,折射出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情感涟漪。“笑的风”就是隐喻个体生命最原初最柔弱的状态:笑是人类最不容易矫揉造作的情感宣泄,风则是自然界无影无踪的力量,二者统一于自由的形式。
人们总是被与生俱来的悲情牢牢地束缚着,生命中充满了无尽的欲求和忧患,能够真正快乐的时候少之又少。小说的结尾已是2019年末,经历了无数坎坷后的傅大成逐渐洞察了生命中自由的超越性,再回顾过去时,幸福也罢、不幸也罢,都可以在把握必然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因此,大成用五笔字型打“悲从心来”时,显示的才是“春情”。《笑的风》则是对生命诗意的情感体验的一种自由呈现。
一、自由的权利——行为的超越
王蒙的小说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意识,从开始创作起,作家创造的人物不仅要反映其个体所在的天然背景,还可以有效传达出其所处环境的历史性文化氛围和时代观念。进一步说,则是一个相当范围内的群体的人们共有的情感模式、道德想象和行为习惯。人固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超出工具性价值去关注人的目的性价值时,其本质更应该是自由的。
20世纪50年代,贫农出身的傅大成获得了重新上学的机会。那从风中传来的笑声,激起了大成潜意识中朦胧的爱意。人本身就应该是自主的,顺应人性本然本质的。然而,一个生命的存在方式总是由社会的现实环境决定的,因此,书写个体生命的存在就不得不展现社会的存在。大成没有经历任何震撼人心的自由恋爱,就由父母做主,以封建包办的方式娶了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白甜美。
人是情感优先的动物,也必然生存于情感之中。与白甜美的结合,虽然让大成感觉到“自己可能缺少了点什么”[1]12,但家庭的温馨和亲情的温存也暂时遮蔽了大成生命活动中根本需要的满足。大成一家在Z城定居后的生活,增添了小说的诗意美,而这背后则是对当时狂热的政治生活的一种行为的超越。
王蒙是一位文体意识强烈的作家,十分注重追求语言的诗意,这就使得小说创作“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和写意化”[2]。《笑的风》的语言充溢着模糊的精确,这种诗性语言其实来自诗性思维,也就是隐喻思维。傅大成在特殊时代里的行为超越即是这种隐喻性结构所展现的一个典型性场域,小说三、四章的叙事在隐喻思维的主导下构建成有机的艺术整体,这个有机体也就是读者看到的“文革”中令人羡慕的大成一家,形成了一个自由的时空体,也有学人将其称为开放的时空语境,而“开放时空中的时代变迁决定了人物命运的浮沉变幻”[3]。《笑的风》这种自由的时空体中大成一家平安与幸福的生活与动荡的政治生活相遇时,表现出Z城日常生活的脱序,也是时代变革的无奈和文化氛围的撕裂。时间在自由时空体中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成为文学艺术中直接的显现;空间则不断扩大而消融了紧张的时代气氛,让现实和未来的选择拥有了无限可能。在自由的时空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4]275。傅大成在此中的行为的超越,自然构成了自由时空体中的生存境遇原型。
作家构建的这个自由时空体,实现了从先验世界的隐喻向生命隐喻的过渡。动荡年代的Z城生活在自由时空体中既是凡俗的日常生活,又是宏大的革命政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有力的又是微弱的,既有外在世界的荒诞、变形又凸显世态人情的本真状态。因此,这种自由时空体既是形式的范畴,又是隐喻的所指,作为“喻体”,它可以映射到除了傅大成一家之外的不同场域,从而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超越和回归。傅大成虽然是生活在自由时空体中的一个审美符号,但他是以生命的方式存在而不是充当哲学构思的道具。傅大成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了异样的方式超越生命的现存状态,也让这种生命的隐喻呈现出不同的层次。
首先是对生命本体的隐喻,这种对自身的隐喻指向了探究生命存在的真实维度。傅大成被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切断了青春最大的好奇与美妙——尝试爱情,他也一度远离家乡,企图逃避本不该归属于他的责任;即使在多年之后,他真的与白甜美离婚,但心里却始终无法完全释怀过去这段虽不甚自由却十分幸福的回忆,他的一生似乎都陷在“超越——回归”的经历中,并用自己的实际体验印证了在个体生命的不同形式、不同阶段、不同侧面中一直存在着逻辑的悖论:自由绝对不是简单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某种状态的隐喻。在这里,读者似乎又能感受到王蒙小说中隐含的“作者声音”,那就是不论生活欺骗了你,还是你欺骗了生活,都不该忘记时时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
其次是对生命存在的隐喻,在傅大成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能够“活着”并不就是懂得“生活”,就像卢梭所说的,呼吸不等于生活。活着只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简单方式,而不是生命存在的全部归宿,傅大成因此一直思考着如何活着才能更完整地完成生命的存在。在追求这种完整性的过程中,大成超越了包办婚姻后的不自在,从白甜美那里获得了有限性的满足;但大成的作家身份与边疆小城那种简单易得的安定生活之间又重新构成了一种张力,他不得不选择从之前的自由时空体中进一步超越,他的超越正是空间的时间化,将未来或理想之维代入现实之境,因此,这个短暂存在的自由时空体只是迈向生命隐喻的桥梁。重新显现的张力和矛盾让大成陷入了更为痛苦的身份焦虑和人性分裂,这也就是萨特所说的“非实在”,这些非实在就是生命存在中一些无法选择的痛苦和灾难,它们的存在并不是每个个体活着的必然,却指向了人类存在的实然。傅大成不会耽于日常生活的享受,而是选择填补自由恋爱和精神世界的空缺,就是在把握了生命存在必然的基础上的自我超越,这种行为超越的权利并不是社会和道德赋予的而是王蒙笔下的人物对自由超越性的洞察。
再次是对生命社会存在的隐喻,书写个体生命的存在无法不触及对社会存在的书写,而王蒙小说的隐喻,也就成为了“时代的象征”[5]。生命存在固然需要生命个体来完成,但并不能依靠个体的独立作用,而必须借助现实的生存世界或者理想的生存世界。傅大成的生命存在,主要是通过两个女性形象及其代表的不同社会存在来完成的。《笑的风》中的白甜美,在某种程度上与王蒙“季节”系列中钱文的妻子叶东菊有形象塑造上的重合或者再现。叶东菊教会了钱文克制自己容易感动的情绪,她的生命存在准则就是做一个“最最普通的人”[6];同样,白甜美的一生始终相信:“每个人只是他或她唯一的自己,这就叫安分。”[1]29安分让大成在没有自由恋爱的婚姻生活中也体会到了别样的快乐。与白甜美不同的是,“后发制人”的杜小娟也有一段无爱的经历,她与大成一样接受了现代教育,她对爱情世界的理想与追求是白氏无法想象的;杜小娟的出现填补了傅大成理想世界的精神需要,傅大成接受杜小娟就是接受新时期的新变化,也就是接受现代性的挑战。王蒙并没有引导读者批判傅大成的“负心”或者妄想,而是让人们坦然接受生命中自在状态的改变,这似乎是一个单向而无法悖逆的过程。王蒙通过结合现实和理想的生存世界,隐喻个体生命社会存在的真实性问题。
二、自由的意志——人格的超越
王蒙为傅大成一家在Z城构建的自由时空体作为小说的隐喻性叙事结构,既隐喻了在那个“狂欢的季节”中人们的失态与踌躇、时代的变革与阵痛,又喻示了那个时代里个体人格结构的分裂和矛盾。也就是说,在傅大成的人格深处,他不会安于这种生活,因此,新时期刚刚开始,他就找回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在Z城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诗歌和小说,还被邀请到北京去参加座谈会。
如果说自由的权利来自个体生命在社会环境中的选择,而自由时空体中行为的超越则为这种选择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生存方式,也为“本我”避开非实在的痛苦提供了可能;自由的意志则来自个体人格结构的“自我”,而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意志是很难协调统一的,《笑的风》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生命悖论的小说”[7]。在西方,宗教信仰能够置身于两者之间,让个体生命在实现行为的超越后能够获得信仰的救赎从而弥补人格结构的分裂;但在中国,由于宗教信仰的缺失,知识分子人格的超越就需要借助“生命的完美”或者“诗意的人生”:用爱和精神满足达到的审美救赎来将行为超越后得到的现实人生提升到人格统一、人性和谐的审美世界。
《笑的风》不仅用婚恋关系来探讨现代性的问题,而且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助佐西马长老之口说出人格结构深处的隐秘:用爱去获得世界。弗洛姆说过:“爱,真的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唯一合理、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那么,任何相对的排斥爱之发展的社会,从长远的观点看,都必将腐烂、枯萎,最后毁灭于对人类本性的基本要求的否定。”[8]5傅大成在Z城的生活不可谓不幸福,但他依然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生命的缺憾和人格结构分裂的问题,说明人身上最强烈的情感激发并不依靠本能需要的满足,而是源于大成在读高中时听到的“笑的风”——人类生存特殊性的东西。这个特质就是弗洛姆所说的“爱”。
新时期再次开始创作的傅大成,也乘着时代改革的春风寻找刚刚逝去的青春,同样也是缅怀人性中纯真自然的瞬间。他在北京的一场诗歌分享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杜小娟的声音。在一个重新充满爱和希望的社会环境中,大成似乎又感受到了20多年前的笑的风,这是爱情的呼唤,也是现代性的呼唤。杜小娟的出现似乎激起了傅大成守护“爱”这种自由存在并进而追问这种存在意义的活动,爱情在这里也成为生命活动而不是认识活动。大成在北京的这次短暂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无法从白甜美那里获得的愉悦感,这种主观的普遍必然性是基于文学交流会这种审美活动而产生的审美愉悦。傅大成与杜小娟初次相遇就互相吸引,也不在于实现爱情的自由,而是自由地体验自由,这在大成之前的“本我”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动乱时期的Z城生活虽然安逸,却也单调乏味;大成感到自己在北京之行后变了,“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了”[1]54。这种改变重又触动了人格结构的隐秘。
在文学的世界里,大成放下了自由恋爱的缺憾,开启了全新的理想境界,但这一境界又不时触动个体人格结构的矛盾,让大成不得不对包办婚姻的生活更加感到惶惑。尽管白甜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敏于行而讷于言”,来到Z城的她,变得能言善语;待人接物,能够迎往送来。新时期以后更是拥有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即使这样,从文学世界回归家庭生活时,傅大成虽然能找到自我,却又迷失了自我。当傅大成的心灵痛苦无处诉求时,在北京偶遇的杜小娟再次出现了,二人交流了文学创作、人生理想。傅大成关于文学的种种在杜小娟这里有了回响,她是唯一能够理解大成的人格痛苦、真正欣赏他的性格魅力的女性。大成也深深地陶醉于她多层次的心灵构造和充满活力的精神空间。
《笑的风》从第八章到第十五章,介绍了傅大成和杜小娟的生命存在中蕴含的相似历程,其实是他们对自己灵魂呼声的响应和追求。二人分别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知己”,从人格结构的完整性来看,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前的“自己”,也就是拉康所说的“一种互为镜像的想象性关系”[9],也就是爱的双方身处位置的隐喻化。他们重复对方的脚步,置换双方的位置,不仅是对自我心灵自由的坚守,更能超越自我去爱;他们因相似而相知,对另一方的呼唤和追寻,就是对当前充满张力的人格的超越。在王蒙看来,二人只有走到一起,才不是精神和灵魂的孤独者,才能在空洞的世界中寻找到心灵的慰藉。
马斯洛发现:“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10]傅大成在诗意的生命存在中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的魅力和生命的完整,与之相对应的是把精神从肉体中超脱出来,与人的自由意志的绝对权利、绝对追求、绝对责任相平衡的人格结构。人的自由意识不是被规定的,但也不是毫无准则的,这种规则是一种普遍法则的准则,是生命个体自身对自由意志的促发——人格超越。这种人格的超越是从窒息人性的“铁屋”中破壁而出,唯有在这种审美情感中,自由才可以直接得到呈现。
但王蒙却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的进程是要付出代价的,白甜美就在自己的丈夫实现人格的超越与生命完整性追求的过程中承受了痛苦。作者也不忘提醒读者,婚姻与爱情并不是一场还不清的道德欠债,爱情就像笑声一样,没有那么多刻意与伪饰;爱情又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是人性自由的隐喻。当人们有勇气正视这种人性时,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笑的风》不是道德的审判庭,而是能够洞悉自由的超越性和生命真实存在的探寻地——揭示生命存在的真相与可能。因此,作者没有也不希望读者在白甜美和杜小娟二人中做一选择,也不会对傅大成进行道德批判。相反,傅大成的自由意志能把世界看作“自我”,用自我超越“世界”,使生命存在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生生不已的自由境界。
这种生命自由的境界,是对于形而上追求的表达。从傅大成将世界作为“为我之物”而言,则是审美世界在先,客观世界在后;是生命意义之所在而非物质所在。借助于它,才能打开精神世界的无限之维,获得人为之人的终极根据,而“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8]98。傅大成与杜小娟恋爱的情感核心是体验,是人格超越的隐喻表达,而他们追求的生命境界的核心则是自由;如果生命的真实存在意味着超越,那么爱情就是在人格超越过程中的体验,而最终的境界则是人格超越中爱情体验的自由呈现。因此,“人格——超越”“爱情——体验”“境界——自由”这三种原本并没有关联的组合就在自由的意志中得到了统一。
三、自由的感觉——心态的超越
傅大成在自由时空体中的行为超越为生命的存在形式提供了各种可能,而他极力化解的人格矛盾也在审美活动中得到了救赎。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意志成为他最终体会到自由感觉的前提,也就是说,大成已然认识到了自由的基础来自社会,自由的手段则依靠本我世界的超越。可是,这种对于必然的把握是否指向了大成自由生活的目的?大成与白氏离婚后,在与小娟建构的世界里终于体会到了相知相契、同心同趣的滋味。然而“趣”走到了头,则是“无”。大成发现,小娟可能并没有理想世界那么完美,反而还是一个充满管制力的人,这其实是二人婚后生活不自由的表征。大成一直对白氏心存愧疚,小娟也无法完全进入大成的世界,二人的感情自然会稳中走低,最后的结果也会不言自明。生活与命运终于落实了那句话:我只在我,我必报应。
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已发现,“报应”一词在《笑的风》中出现了不止一次。早在杜小娟给傅大成寄去的那首署名“鸢橙”的《只不过是想念你》里,小诗就提到过“我只在我,我必报应”[1]108。在这首诗中,杜小娟用时间的明晰性和模糊性构成了想念、相思、相爱的事体情理,从而达到了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和共通性。确定的时间将历史的虚无和人生的感叹交融起来,模糊的时间则带来了诗歌空间的立体化:小诗似乎预告了爱情和生命的结局就像随风飘去的断线风筝,预告显然是未来时的;然而,杜小娟却同样看出了“我只在我,我必报应”这样的故事完成时;最后,诗歌展现的情境和抒发的情感显然指向了现实空间。就这样,预告的未来时、故事的完成时和情境的现在时交错在一起,这样的写作手法既可以让个体生命在感受当下的景与情之时,又能提供形而上的依据,从而真正完成生命存在的“觉”,也就是达到真正的自由境界。
看到这首诗的大成也惊异于“报应”的预判,他想极力掩饰自己与杜小娟的书信往来,可诗稿早被女儿阿凤偷走。大成的一双儿女自然是十分抵制自己的父亲与别的女人精神出轨。可后来,阿凤居然是凭着演唱杜小娟的诗改编而成的《未了想念情》而走红,这种戏剧性的情节也是一种“报应”,但更有一种反讽的意味。“报应”其实是历史情景的循环性描写:白甜美被向往自由恋爱的傅大成抛弃了,而多年之后,当杜小娟的儿子立德出现时,傅大成的二次婚姻也走向了终结,他独自守在空荡的家中,仿佛也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这些相似的情景,将不同时间的空间连缀起来,实现了历史空间的时间化。因此,与其说这些“报应”是对生命个体的反讽倒不如认为是一种隐喻,它隐喻的仍然是一种自由的发展状态:自由发展到极致,反而会陷入一种不自由甚至是“无自由”。可以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往的价值,而是在否定这些价值之后自己出面去解决生命存在的困惑。作者并没有直接透露这种解决的方式,而是通过小说叙事话语的多层维度去启发读者进行思考。
接到杜小娟的小诗后,惶恐之余的大成写信向女儿解释,但阿凤的思考方式确是大成始料不及的;她看待杜小娟寄来的这首诗和诗中的内容,是超越了单向性、有限性的话语所指而试图构建为一个全面性、超功利性的意义世界。这背后实际上暗含了阿凤对待爱情与婚姻问题的超越心态,这在后文中也得到了证明。大成与女儿的通信让小说的独白性话语转变为对话性话语,使叙事话语的所指分裂为表层含义与深层意蕴两个方面,让读者从小说的话语、人物、故事等角度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复杂性和含混性。
《笑的风》中另一处相似的对话性话语发生在傅大成与杜小娟之间,二人结婚多年之后,却在什么是爱情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大成认为爱情是奋斗而来的“成果”,因此要精心呵护,坚持到底,让它永不改变;而小娟却把爱情看作一种审美享受,是幸福的感觉。既然爱情是美感而不是“物质”,那么爱情满足的就不是实用性、功利性和合目的性这些低层次的需求,“爱”应该是以“爱”为目的而非手段,爱情的活动能力也不会是单向或者唯一的,而是可以不断转化和不断感受的。杜小娟的爱情态度反映了她活在当下的生命心态。活在当下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妥协,对处境的苟且,而是在把握必然的基础上完成的自我超越。在与杜小娟的争论中,傅大成似乎还没有理解这种心态上的超越,这与离婚后的白氏不肯再嫁有些许的相似;但在这一问题上,大成的女儿阿凤却与杜小娟站在了一起:阿凤劝自己的母亲不必执着于永远的幸福,幸福一段总是强过永远的不幸。
当读者阅读这些对话性话语时,看似是特定情境中的“人物——人物”的对话,其实是“作者——人物”和“作者——读者”之间的交流。正如巴赫金所说:“小说应是杂语的小宇宙。”[4]202杂语将读者代入到作者创造的“众声喧哗”的故事中,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扩展,这种杂语打破了故事与意义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解放了每一个故事作为小说构成要素的价值空间。作者、读者与人物争辩着、谈论着,从而超越了主客体间的双向对话关系,彼此深入到灵魂的深处。晚年的大成,看似又成了一个灵魂的孤独者、爱情的失败者,他开始反思和回顾自己过往的行为和人格超越是否带来了自由的感觉。一直追求自由精神境界的心态和人生观,在有限的生命活动中不正是所谓的“北极光”吗?人的自由感觉其实只能诉诸于人的心灵,自由应当是自我的生命体验。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认为爱应该是:“在感觉的倾向之中,在行动的原理之中,在温存的同情之中。”[11]傅大成回顾自己的一生,爱不应该是被要求和规定的准则,也不是一种义务;对于这种“爱”来说它本身就是目的,而非追求自由的手段;爱是生命的诗意,它不受外物驱使而生发;爱是自由感觉的作用,并因为爱而使自由的感觉得以延续。经过对眼前现实的否定之否定,傅大成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支点,他接受了所有的后果,把一次次“欺骗”了自己的生活看作宝贵的记忆和人性的财富;生活不光欺骗了你,也在同时恩惠了你,安慰了你,充实了你。
四、结语
《笑的风》和稍早创作的《生死恋》,再次印证了王蒙相信爱情的人文立场,但作者又不忘提醒读者,不要将爱情定义成一种“义务”,爱情的生发不能以“应当”为基础,爱情的建立和延续也不能建构在“愿意”之上。爱情的目的应该是爱本身,是爱者的自由感觉为自己立法,也就是说,对于必然的把握只能成为自由的前提,而对必然的最终超越才是自由为之自由的根本。
[1] 王蒙.笑的风[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2] 李萌羽,温奉桥.一个人的舞蹈——王蒙小说创作的一个维度[J].南方文坛,2019,33(3):159-163.
[3] 郭宝亮.浅谈王蒙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新探索[J].当代作家评论,2020,37(5):100-108.
[4]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5] 马凯丽.王蒙小说的现代性[D].汉中:陕西理工大学,2019: 38.
[6] 王蒙.踌躇的季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9.
[7] 李萌羽,温奉桥.正典传统,空间美学与史诗品格——论王蒙《笑的风》等小说近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 43(4):197-208.
[8] 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9]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83.
[10]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68.
[11] 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06.
The Poetry of Life and the Signs of Freedom: A Comment on Wang Meng's New Novel
LI Xu-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Through the two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Fu Dacheng, an intellectual, the novel records the shocks brought by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o the thoughts, emotions and memories of a generation. The poetic construction of the novel from beginning to end is Wang Meng’s empirical expression of life and humanity in his work, while the pure and sentimental space of love attempts to transcend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n pursuit of a rich and colorful world of freedom.proves that the author not only focuses on external “likeness”, but also delves into the inner philosophy of life, reminding people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transcendence of freedom in the limited activities of life.
Wang Meng;; life; freedom
I206.7
A
1009-9115(2022)05-0054-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2.05.010
2021-08-29
2022-07-15
李旭斌(1997-),男,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