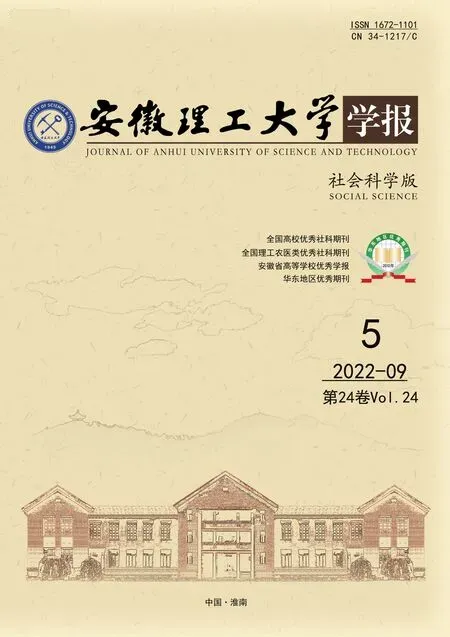论译者林徽因及译本《夜莺与玫瑰》
丁大琴,丁立福,2
(1.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淮南师范学院 翻译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 232038)
一、林徽因研究的系列拐点
2021年10月10日在中国知网以“林徽因”为篇名进行精确搜索,得文献753篇,包括学术期刊论文402篇、硕士学位论文43篇、会议文章2篇、报纸文章38篇、学术辑刊10篇、特色期刊258篇。其中,402篇学术期刊论文所涉学科排在前4名的是中国文学、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人物传记和建筑科学与工程,分别有相关论文244篇、76篇、24篇和24篇,这大致也就是相关林徽因研究所涵盖的主要领域了。
在建筑科学与工程方面,林徽因曾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撰写了许多有着独特贡献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且成就很是显著。如,她为梁思成清代建筑研究专著《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绪论》“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1]序,她与梁思成合编的《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演化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她在建筑科学与工程方面令人最为赞叹的成就是:参与了国徽及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改造了传统工艺景泰蓝。
人物传记和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关系较为密切,通常情况是先有语言文字版的人物传记,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再次艺术创作乃至搬上影屏,随后影屏收视又会反哺影视创作和人物传记,并促进相关研究兴盛起来,故而将其合一处加以阐述。一是林徽因人物传记有关研究。此方面研究文献1999年之前仅有7篇,其中最早的1篇是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在《读书》1983年第2期刊发的一篇纪念性文章《建筑家的眼睛 诗人的心灵——忆林徽因教授》,有3篇是相关“林徽因年表”的。可以说新世纪之前,林徽因人物传记类相关研究仅止于其生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主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如《一代才女林徽因》(林彬,1993)、《梁思成与林徽因》(费慰梅,1997)、《林徽因传》(林彬,1999)、《梁思成与林徽因》(黄杨,1999)。拐点正是在1999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原本展现诗人徐志摩与原配夫人张幼仪、心仪对象林徽因及最后伴侣陆小曼之间的感情生活,可能是剧本名取自林徽因代表诗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从而让林徽因凸显出来,成为家喻户晓式的人物,由此引发林徽因人物传记类相关研究。二是有关林徽因的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研究。在这方面最早的一篇文献是《影像中的情感塑造——纪录片〈梁思成 林徽因〉的创作背后》,尔后的23篇相关文献主要涉及纪录片《梁思成 林徽因》、中篇评弹《林徽因》、歌剧《林徽因》、歌剧《再别康桥》、锡剧《林徽因的抗战》等。相应拐点应是2010年首播纪录片《梁思成 林徽因》,该片先后获得第二十二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纪录片大奖、“第七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最佳导演奖及十大纪录片奖等荣誉,并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列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系列十佳作品,可以说影响较大,也由此促发了有关林徽因的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研究,并迅速飙升至前三甲。综合以上两个拐点及相关研究文献,可得到以下几点启发:一是相关著作类的传记继续走高,二是相关学术论文开始大量涌现,三是由传记走向影屏的影视作品有效地催生了相关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类研究文献,并迅速兴盛起来。
在林徽因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以文学为业余爱好的她生前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集。尽管早在1937年,“冯至、卞之琳、梁宗岱等主编的《新诗》月刊第六期上已预告即将出版林徽因诗集的消息。随着抗日战火的蔓延,诗集也就灰飞烟灭了。”[1]79林氏生前文学作品大都散见于《新月》《诗刊》《北斗》《学文》《晨报副刊》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报刊,因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关注和研究。1982年,福建师范大学的陈钟英和陈宇开始搜集和整理林徽因诗作,历经3年艰辛,编辑而成首部林徽因文学作品专集《林徽因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欲出版林徽因文集之前,著名作家萧乾先生曾发文《一代才女林徽因》(详见《读书》1984年第10期)回忆、介绍了林徽因一生的文学创作情况。以这两件事件为拐点,林徽因研究迅速拓展到诗歌领域,这也是有关林徽因文学研究的起始点。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选编出版第一部林徽因小说集《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除集中收录了林氏创作的所有6部短篇小说,即《窘》《九十九度中》《钟绿》《吉公》《文珍》《绣绣》之外,小说集还收录了林译的童话小说《夜莺与玫瑰》,附录了诸如《窗子以外》《彼此》《一片阳光》《蛛丝与梅花》等13篇散文。由此构成另一拐点,林徽因研究领域在新世纪迅速拓宽至小说研究、散文研究、翻译研究以及文学综合性研究;进而在将林氏列为建筑学家和诗人之后,又有人开始呼其为小说家、散文家、文学家乃至翻译家。本文拟就林徽因译者身份及《夜莺与玫瑰》译本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二、译者林徽因
在论述林徽因是否是译家前,先需辟谣。《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在简介完林徽因生平后,附有林氏翻译书目《古代的人》(历史散文,房龙,1930)和《钱魔》(小说,辛克莱,1934);林彬在其传记《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将林徽因如何为克服丧父之痛而译《古代的人》的过程描述得维妙逼真,可惜至今未有人见得林徽因译本。相反,上世纪80年代迮卫和靳翠微合译房龙著作《宽容》时,在附录“关于房龙和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郁达夫在林微音译本《古代的人》的序言中分析了房龙的写作艺术,认为他的方法……”[2]402-403;无独有偶的是,上世纪90年代常绍民在领衔翻译房龙另一著作《与世界伟人谈心》时,在“中译者序”部分亦明确指出,“郁达夫曾在林徽音译本《上古人》所作序言中这样评价房龙的写作艺术……”[3]3。似可断定翻译《古代的人》的并非林徽因,而是林微音——上世纪30年代中国海派作家中的文学青年——又常被误写为林徽音,进而被误认为林徽因了。另,中译本《古代的人》在郁达夫所作的序文及其译者序中均提及译者失业一事,但1927年8月郁达夫为该书作序前林徽因还在美国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求学,而且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林徽因亦不存在失业潦倒从而靠译书赚钱生活的问题;再者,林徽因与郁达夫互不往来,似不太可能邀郁氏为其作序,而林微音在文学创作上则较为推崇郁达夫,曾是“达夫赏饭”的出席者。以上探讨,可侧面佐证郁达夫作序的《古代的人》译本应为林微音所译。事实上,近年来的多种书目汇编也一再证实辛克莱的《钱魔》亦由林微音所译。
那么林徽因到底有没有译过作品呢?答案是肯定的。为了给刚成立的新中国在建筑方面有所借鉴,1951年8月,林徽因就曾和丈夫梁思成合译了窝罗宁教授的著作《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约5万字),译作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于1952年5月出版。
有学者指出“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作为《林徽因诗集》的编选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林徽因的另一位终身好友美国人费慰梅(1)Wilma Fairbank: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夫人。回忆称梁思成曾告诉过她,林徽因在 1923 年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便是她翻译的《夜莺与玫瑰》”[4]90。需要指正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林徽因诗集》的编选者并非梁从诫先生,而是福建师范大学的陈钟英和陈宇两位老师;梁从诫仅为诗集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并对原刊于《读书》1983年第2期的回忆性作品《建筑家的眼睛 诗人的心灵——忆林徽因教授》稍作修改,后代作该诗集的序言。笔者查阅《林徽因诗集》,也未见梁先生提及费慰梅所忆之事。倒是费慰梅1994年在著作《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提到,林徽因投身于新月社是其“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据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发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它们是新月社成员早期的重要园地”[5]21。费氏作品出版于1994年,1997年由曲莹璞、关超等译成中文出版。在寻找、发掘林徽因译作《夜莺与玫瑰》的过程中,原南通大学文学院陈学勇教授作出了卓越贡献。陈学勇教授亦是当代林徽因研究权威,1991年就考证过林徽因确曾用笔名“尺棰”和“灰因”发表过诗文[6]230-232,229。不过“尺棰”为林氏笔名早已不是新鲜事。1931年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时就曾选录林徽因的诗作《仍然》,《仍然》即是林徽因以“尺棰”为笔名1931年4月刊于《诗刊》第2期的诗作。令人欣喜的是,陈学勇以笔名“尺棰”为线索,竟然发现“北京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即有她译的《夜莺与玫瑰》”[7]35,于是早在1999年选编出版《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时就将林译《夜莺与玫瑰》收录其中,2005年在主编《林徽因文存》时又再度将这首译诗收录。而就在陈学勇将这首林译诗首度收录出版时,另一林徽因研究专家曹汛在国家图书馆搜寻到了刊有“尺棰译《夜莺与玫瑰——奥司克魏尔德神话》”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出版),再次证实林氏确实译过《夜莺与玫瑰》。
随着“尺棰”所译《夜莺与玫瑰》重见天日,林徽因研究便又拓展至翻译研究领域,进而有人将林氏列于“翻译家”行列[8]113-114,119[9]161-162,186。然而,在汉语言文化传统中,“家”一般是指“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10]620,如雕刻家、画家与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等。某个人要想被称为“某某家”,仅“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是不够的,还应“从事某种专门活动”并取得较好成就。林徽因专研建筑学,同时在诗歌、小说领域掌握了相关专门学识,从事创作并颇有建树,是故可以称之为建筑家、诗人、小说家,也可将诗人和小说家合称为文学家或作家。然而就翻译而言,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林译作品只有上文提及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和《夜莺与玫瑰》。其中,前者不属于文学译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者是林徽因的处女作,林徽因翻译发表时还是稚气未脱的19岁中学生,且篇幅也就4千字左右,其意义有待评估。由此可见,林氏并非专职于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尤其是缺乏能够称其为“翻译家”的成就来证实她本人所掌握的“专门学识”,故本文认为宜称其为“译家”。当然,林氏的英语水平不容置疑:少年时代全家迁往北京后就一直在英国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至1920年随父游历欧洲,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即与徐志摩一起担任全程翻译,随后又赴美留学4年,30年代受聘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为外语专业学生主讲《英国文学》——这些使得人们在仰慕之余不禁浮想联翩,林氏在译完《夜莺与玫瑰》后“倘若继续翻译……完全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7]35-36。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假设的余地。林徽因在译完《夜莺与玫瑰》后再也没有涉足文学翻译,与梁氏合译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也无甚影响和学术意义。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称呼林徽因为“译者”,因为汉语言文化中“者”通常“用在形容词、动词或形容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后面,表示有此属性或做此事的人或事物”[10]1649,“某某者”名称的内涵没有成就上的特定要求,如评论者、作者、讲解者、阅卷者等。再如笔者,译过并发表数十篇译作,而且写过近20篇翻译方面的学术论文,但终没有“译家”的感觉,但自称“译者”应该不会遭致争议。
三、译本《夜莺与玫瑰》
确切地说,重见天日的“尺棰译《夜莺与玫瑰——奥司克魏尔德神话》”在眼下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林徽因翻译热潮,具体表现为对林徽因译作的争相出版和对林徽因译作研究的持续投入,当然,热潮都集中于林氏的文学译作《夜莺与玫瑰》上。
《林徽因文存》中收录的林译《夜莺与玫瑰》,译文有明显的文言遗痕,细腻的情感表述表明译自女性之手。2011年某出版社出版了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该书腰封处标注着“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首次出版”。此书出版不久,即有著名林徽因研究专家指出,其是一本打着林徽因招牌的伪书,引起学界一段时期哗然之后,不了了之(2)详见https://news.ifeng.com/c/7fbdzkHR9BU与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6857344/discussion/44153739/。。笔者网购该书之后即发现:某社译(3)引文源自王尔德著《夜莺与玫瑰》(某出版社2011年出版),译著虽标为林徽因译,实非林氏所译,真正译者姓名也不得而知,为与林徽因译文相区别,行文中一律暂称为“某社译”。的第一句译文“她说只要我为她采得一朵红玫瑰,便与我跳舞,”青年学生哭着说,“但我的花园里何曾有一朵红玫瑰?”[11]4读来毫无语言上的“阻碍”乃至距离感,不免让人疑窦丛生。经查,林译(4)本文所引的所有林徽因译文均源自陈学勇著《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为表述方便起见,行文中一律称为“林译”。第一句实为:“她说我若为她采得红玫瑰,便与我跳舞。”青年学生哭着说,“但我全园里何曾有一朵红玫瑰。”[12]153通过认真地对比研读,笔者提出3点疑惑。
(一)某社译可能并非林译
某社译可能并非林译,这很容易例证。如,某社译“这才是真正的有情人,”夜莺叹道,“以前我虽然不曾与他交流,但我却夜夜为他歌唱,夜夜将他的一切故事告诉星辰。如今我见着他了,他的头发黑如风信子花,嘴唇犹如他想要的玫瑰一样艳红,但是感情的折磨使他的脸色苍白如象牙,忧伤的痕迹也已悄悄爬上他的眉梢。”[11]4-6而林译却是“夜莺叹道,‘真情人竟在这里。以前我虽不曾认识,我却夜夜的歌唱他:我夜夜将他的一桩桩事告诉星辰,如今我见着他了。他的头发黑如风信子花,嘴唇红比他所切盼的玫瑰,但是挚情已使他脸色憔悴,烦恼已在他眉端印着痕迹。’”[12]153相较而言,某社译多用双音节词,句式较为通顺,除个别语句外多是流畅的现代汉语;而林译则多用单音节词,句式安排追求修辞效果,留有明显的文言痕迹。
(二)某社译可能亦非译自王尔德原文
这似不好妄下论断,因为若原文本不同,译文本自然有异。好在某社译提供了王尔德的原文,想来这就是某社译者所“依据”的原文本了,否则译者及其出版社岂不是在自找麻烦?仍以某社译第一句为例:“她说只要我为她采得一朵红玫瑰,便与我跳舞,”青年学生哭着说,“但我的花园里何曾有一朵红玫瑰?”[11]4某社译本所附原文第一句是:“She said that she would dance with me if I brought her red roses,” cried the young Student, “but in all my garden there is no red rose.”[11]167这一句翻译起来基本没有什么难度,但某社译前后两处统一使用“一朵红玫瑰”,定是译者没有仔细阅读原文“red roses”和“red rose”之故。其实王尔德这么措辞是有一定用意的,“red roses”侧重于属性,似在表明红玫瑰有许多(种),不管是哪(种)只要是“红玫瑰”即可,而“(no)red rose”侧重于数量,意在表明园中一朵都没有,以突出青年学生寻得红玫瑰的难度之大。另外,原文中“all”也是一个能够烘托文意的语词,理应在译文中凸显,但某社译却忽略不译。其实,不深究此处也可,译者只需忠实地译出原文即可。90年前年仅19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即使是初次翻译实践也能正确译出原文本意,某社译者为何如此“粗心”?若要究问原因,恐怕只能推断是某社译可能并非译自王尔德原文了。
(三)某社译部分改编自林译
要说某社译和林译一点关系没有,似亦不当。如林译:“青年说,‘乐师们将在乐坛上弹弄丝竹,我那爱人也将按着弦琴的音节舞蹈。她舞得那么翩翩,莲步都不着地,华服的少年们就会艳羡的围着她。但她不同我跳舞,因为我没有为她采到红玫瑰。’于是他卧倒在草里,两手掩着脸哭泣。”[12]153而某社译则是:“青年学生说‘乐师将在舞会上弹弄丝竹,我那爱人也将随着弦琴的音乐声翩翩起舞,神采飞扬,风华绝代,莲步都不曾着地似的。穿着华服的少年公子都艳羡地围着她,但她不跟我跳舞,因为我没有为她采得红玫瑰。’他扑倒在草地里,双手掩着脸哭泣。”[11]6两个译文显然不是出自同一译者。首先,林译中的所有核心词汇绝大多数都在某社译中得到体现,尤其是“丝竹”“弦琴”“莲步”“华服”“艳羡”等带有文言遗痕的独特词汇,这怎能不让人生疑?其次,两译文中的“两手”与“双手”、“草里”到“草丛里”等有明显的编改痕迹。再次,林译本中绝大多数复杂、难以改写的词句某社译本都有保留。如原文有3处同样的句子“…and I will sing you my sweetest song.”,林氏先后译为“……我为你唱我最婉转的歌”“……我为你唱最醉人的歌”和“……我为你唱最甜美的歌”[12]154,某社译则完全一致[11]7-8——若非部分改编自林译,岂有如此程度的“默契”?
综合上述3处疑点分析,本文认为某出版社出版的童话集《夜莺与玫瑰》中的单篇童话《夜莺与玫瑰》并非林徽因所译,整个童话集也非译自“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之手。童话集《夜莺与玫瑰》收录了王尔德第一部童话集TheHappyPrinceandOtherTales中的所有5篇童话(《夜莺与玫瑰》仅是其中一篇),还收录了王氏第二部童话集TheHouseofPomegranates(1892)所有4篇童话中的2篇,即《少年王》(TheYoungKing)和《星孩儿》(TheStar-child),将童话集书名定为《夜莺与玫瑰》,亦无可厚非。问题是童话集《夜莺与玫瑰》在封面、版权页以及扉页上均醒目地标明“[英]王尔德著 林徽因译”,童话集《夜莺与玫瑰》为王尔德著是“真”,为林徽因译则是“伪”。确切地说,林徽因只译了王氏童话集中的一篇“TheNightingaleandtheRose”,但此篇《夜莺与玫瑰》(林译童话)非彼篇《夜莺与玫瑰》(童话集收录的《夜莺与玫瑰》)。关于此书为林徽因译本的真伪,有记者曾向策划出版方咨询过,相关负责人的回应是“这可能是大家考据不同造成的。”至于童话集《夜莺与玫瑰》里的其余6篇童话译文,译者是谁,抑或摘编自它处,答复亦是无可奉告。因此,这里恳请出版方能够给以准确回复。
四、结语:竭泽而渔几时休
某社译本童话集《夜莺与玫瑰》版权页上虽没有印数记录,但“得益于”其腰封上“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首次出版”等似乎言过其实的宣传言辞,该书从2011年9月出版第1版,到 2012年12月已经开始第3次印刷,其火爆程度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某社译本童话集《夜莺与玫瑰》在图书市场上迅速蹿红之后,竟引得众多书商和出版社纷纷效仿,迅速推出了类似的“偷梁换柱”译本,更糟糕的是,之后有关林徽因译作《夜莺与玫瑰》的研究多是基于某社译本童话集《夜莺与玫瑰》而来的,如韩宇著“From the Theory of Dynamic Equivalence to Analyse the Translation ofTheNightinggaleandtheRoseby Lin Huiyin”(2013)、余小梅著《〈夜莺与玫瑰〉:林译本与巴译本的比较研究》(2013)、赵鹏著《〈夜莺与玫瑰〉汉译本语言特色对比研究》(2014)和苏孝明著《重读林徽因汉译〈夜莺与玫瑰〉》(2014)等。难以想象,倘若本文推测正确,后人在研究林译《夜莺与玫瑰》时引用了上述所涉基于某社译本童话集《夜莺与玫瑰》所作的学术论文,后人的后人再复之……待到“假作真时真亦假”时,林译《夜莺与玫瑰》研究到头来不仅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会严重贻害我们的子子孙孙。
若本文推测正确,那么,尽管此次所谓“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夜莺与玫瑰》短期内在图书市场上取得了巨大销售业绩,但从长远来看,此举显然是竭泽而渔,其危害于著(译)者是毫无尊重,于图书市场是扰乱秩序,于出版界是得不偿失,于所承载文化是诋毁污蔑,于读者是坑蒙拐骗、混淆视听和全面伤害,金钱上的、热情上的、兴趣上的、知识上的……另外,图书译著属流通品,流通一次其危害便增多一次,而且流通一次可能会附带产生许多相关流通品;而当这些相关流通品带着言而不实的“劣根性”再次流通时,其危害便成倍增长。于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便有可能出现,反过来必然会给人们所守望的精神家园带来沉重打击。模仿林升“西湖歌舞几时休”诗句而来的标题“竭泽而渔几时休”,其用意一是想突出问题的严重性,二是期望各界联手采取措施,迅即有效地治理相关乱象,担当起传承、发展文化之大任——这已超出本文研究范围,涉及到另一富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这里姑且作为一个引子吧。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