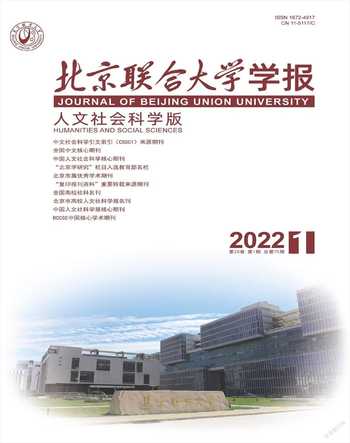莱昂内尔•罗宾斯文化经济学思想述评
[摘 要] 按照露丝·陶斯的文化经济史观,在威廉·鲍莫尔正式创立文化经济学之前,还有一段史前史,而其中凯恩斯和罗宾斯,不仅涉猎文化经济问题,而且担任英国“艺术管家”,无论是在文化经济管理还是理论方面都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是文化经济学这段历史的重要奠基者。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全面描述罗宾斯与艺术交往的历史,解读其文化经济学名篇——《艺术与政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其如何利用艺术拓展经济学疆域,以及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艺术问题,以期系统总结其文化经济学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 莱昂内尔·罗宾斯;奠基者;文化经济学;艺术与政府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F091.32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2)01-0082-07
罗宾斯曾经的学生,国际知名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斯比,在梳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时认为,“如果说当代文化经济学学科有一个起始点的话,威廉·鲍莫尔与威廉·鲍温于1966年出版的《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无疑就是这个起点”,然而,如果论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则这方面的学术努力起步更早,如“1960年加尔布雷斯在《自由时间》发表的讲话”,而在与之隔海相望的英国,“罗宾斯则是英国第一个分析政府在支持艺术与资助公共博物馆与画廊等事务中的经济角色的英国经济学家”,这篇名作就是罗宾斯于1963年出版的《政府与艺术》。[1]而另外一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国际知名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也认为,“文化经济学已经吸引很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鲍莫尔、布劳格、皮考克、杨潘(Jan Pen)、加尔布雷斯、西托夫斯基,而在他们之前,凯恩斯和罗宾斯不仅在艺术经济问题上有所涉猎,而且在英国的艺术管理中贡献巨大”。[2]而事实确实如此,在经济学家当中,罗宾斯与凯恩斯一样,无疑是介入艺术领域广度与深度最为突出的,自然也是研究经济学家如何介入艺术领域,或者说,经济学如何在艺术领域实现疆域拓展的最好例证。[3]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全面描述罗宾斯与艺术交往的历史,深度解读其文化经济学名篇——《艺术与政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其如何利用艺术拓展经济学疆域,以及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艺术问题,以期系统总结其文化经济学的学术思想。
一、英国“艺术管家”
虽然,罗宾斯轻而易举地成为经济学家——他30岁就当上世界最知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也是当年英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可是,他的理想并不是经济学家,“我的主要的,事实上是唯一的真正野心,就是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诗人”。[4]29身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精神层面面临着严重的分裂与秩序的重建:一方面,人们虽然在形式层面还如爱德华时代恪守教规,例如按时参加宗教的仪式,并只接触教义容许的有节制的艺术形式,但是,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由于技术革命与科学进步而受到极大冲击,甚至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人们通过艺术等方式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并借助艺术重建心灵的新秩序。早年的罗宾斯对宗教的热情不高,而是将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艺术当中。他的两位挚友埃德温·罗斯(Edwin Rose)与克莱夫·加德納(Clive Gardiner)让其艺术鉴赏水平大增,罗宾斯在其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表述道,“由于我早就学会欣赏音乐,而且是以音乐之媒介所传达的方式,而不是我主观投射式地聆听音乐,这样一旦我学会如何欣赏绘画艺术,按照我自己的语言,绘画就向我呈现了一个崭新体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像其他所有伟大的审美成就一样,都遵循这样一种收益递增法则——知道得愈多,你就愈加享受”。[4]243在罗宾斯那里,艺术已经取代了宗教:一方面,它为罗宾斯在宗教之外提供了精神家园,而且这个家园中,罗宾斯不仅完美地安顿了灵魂,更赋予其人生更多的色彩与意义;另一方面,他浸沉艺术的独特经验,不仅为其日后的“艺术管家”的身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支撑,甚至对其突破经济学“物质主义”的束缚,重新界定经济学的疆域,并将艺术纳入经济学的视野有着直接的贡献。
年轻的罗宾斯对艺术的执着及其在这个领域丰富的经验似乎注定他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做点什么,然而,这个过程似乎来得有点晚,他首次以“艺术管家”的身份出现是在1936年,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罗宾斯毛遂自荐,成为考陶尔德画廊(Courtauld Gallery)理事会的成员,并在考陶尔德去世(1947)后被选为理事长。按照罗宾斯自己的说法,“事情之间环环相扣,当你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时,后面一系列事件就接踵而来”:1952年,他受邀担任国家美术馆的理事,并在一年之后成为泰德美术馆的理事,而两年之后他又被选举为国家美术馆理事会的理事长,直到1974年才卸任;1954年,他接受委托担任主席就是否重建皇后宫提供咨询建议,1956年担任皇家歌剧院的理事,并担任其中芭蕾和财务委员会的主席,直至1980年才卸任;其间他还参与艺术品出口审查委员会(Reviewing Committee on the Export of Works of Art)的委员,当然,还有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后者相关的报告(也称罗宾斯报告,1963年)直接导致了英国文化行政部门(1964年)的成立。作为艺术鉴赏大师,罗宾斯丰富的审美经验无疑对他履行这些职责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让他在履职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如在绘画上倾向于收藏印象派的作品,为此他也遭受不少非议,甚至《标准晚报》称其为“艺术独裁者(art dictator)”。当然,这些都不是本文的重心所在,本文重点要梳理与总结的是,他作为艺术管家的实践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经济学思想。由于罗宾斯作为艺术管家的实践主要集中在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管理方面,以下我们就此展开分析。
在罗宾斯结束第一段国家美术馆理事生涯之际(1959年),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件中这样评价道,“此次卸任对我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许这不是最重要的,却无疑是我生命中最富有回报,也是最快乐的职位”[5]760。当然,这种回报是双向的,由于罗宾斯的介入及其卓越的管理智慧,英国国家美术馆不仅规模扩大、拨款增加,而且找准定位,逐步走向规范管理,并成为国家美术馆管理的典范。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罗宾斯担任国家美术馆理事长的重要任务就是解决财务问题,这不仅包括博物馆重建的费用,而且包括博物馆良性运营所需之费用,以下分别予以分析。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国家美术馆大量馆舍受损,美术馆西翼被迫关闭,大量藏品寄存在爱尔兰,建筑重建所需资金是理事会面临的首要难关。作为曾经的政府雇员,罗宾斯深谙向政府部门申请拨款的奥秘。在他看来,这些公务人员,不管他们如何爱好艺术,当他们认为艺术之类的事项并无政治上的紧迫性时,他们是不肯轻易拨款的。因此,他建议理事会可以派代表前往劳工部与财政部进行游说,游说的技巧就是“概述我们所需之物,而不是我们想象政府部门可能给予之物”。而他自己亲赴财政部,获得了财政部“极富同情的接待(sympathetic reception)”,其结果诚如罗宾斯所期,财政部给了“我们所需之物”,同意拨款重建甚至是扩建国家美术馆。 [5]768 解决了重建资金之后,罗宾斯又面临日常运营的资金压力,而且在他看来,美术馆要想良性发展,理事会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可自行支配的资金。当时,国家美术馆每年的财政拨款只有区区1.25万英镑,罗宾斯在分析这种窘境的原因时认为:其一,自爱德华和乔治时代以来,英国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都很势利,它们只愿意投入物质的领域,如投入4 000万资助国内的猪肉生产,而在艺术之类等非物质领域的投入往往少得可怜;其二,与隔海相望的美国比较,英国也缺乏刺激民间艺术捐赠的公共财政政策,如美国就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刺激社会资金投入艺术领域,这为博物馆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支持。[4]254作为理事长,罗宾斯对症下药,谋求国家美术馆发展的稳定的财务保障:首先,他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财政部门游说,增加财政的公共投入,并最终在1959年就将年度财政拨款额度从1.05万提升至10万英镑,极大地缓解了美术馆的经费难题;其次,他也试图效法美国,如通过设立“博物馆之友”来吸引大众捐赠,减免税收以鼓励社会捐助,以及减免遗产税来鼓励艺术品捐赠等方式扩大美术馆的收入来源。作为理事长,罗宾斯在解决国家美术馆财务危机的成绩有目共睹,以至于与他共事的馆长——菲利普·亨迪(Philip Hendy)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罗宾斯与行政事务以及政府部门有着十分特别的关系。国家美术馆预算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5]760。
当然,作为国家美术馆的理事长,罗宾斯除了面临财务的问题之外,还要面临诸如美术馆经营与管理问题,其中美术馆是否免费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经济学家的身份让其解决这个问题更加得心应手。罗宾斯首先承认,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博物馆免费并非惯例,如伦敦塔、汉普顿宫就收费参观,而且,它们的经验表明,国家美术馆的参观人次也不会因为收费而出现断崖式地下滑,所以,国家美术馆收费也是可行的。即便事实如此,罗宾斯个人还是倾向于免费开放,最起码是那些经常性藏品应该免费开放。不过,罗宾斯还是面临其他观点的挑战,如其他公共产品,像老维克(Old Vic)剧院和考文垂花园(Covent Garden)剧院,就向观众收费。罗宾斯斩钉截铁地认为,这两类产品本身就没有可比性,这是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一种情况需要收费,而另一种情形则无需收费,是否征收的关键在于其容量相当于需求而言是否足够” [6]。也就是说,虽然博物馆与剧院一样,都受制于空间因素,但是,剧院的消费者相对于容量而言,易于产生拥挤性问题,如一个剧院的容量最多也只有千余座位,而其消费者数量常常超出这个数量;相反,美术馆每日可容纳的人流量则可以高达数万人次,因此,通常情形下不会产生拥挤问题,就没有必要收费。当然,对于常规展览之外的特展,由于它不仅会产生拥挤问题,而且还会产生诸如安保之类的额外费用,所以,这类特展收费是理所当然的。如今,这已经成为英国国家美术馆,甚至是所有公共美术馆的通行做法——常规展览免费,而非常规的特展则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罗宾斯无疑是第一个利用公共产品之拥挤理论,阐述与倡导这种做法的学者,其首创功不可没。
作为“艺术管家”,罗宾斯的作为远不止这些:他推动国家美术馆出版第一份年度报告,并亲自撰写序言阐述美术馆的使命与目标,建立美术馆与社会沟通的良性机制;他主持设立美术馆之友,拓展美术馆的捐赠渠道的同时,也优化美术馆的服务功能,如今已是美术馆运作的惯例性做法;他推动设立审查委员会,不仅为国家美术馆的艺术收藏把关,甚至参与民族艺术品的保护,这种近似“国家收藏”做法也为国家美术馆明确了自身的定位。总而言之,在罗宾斯这位“艺术管家”的精心治理之下,英国国家美术馆进入其发展的最好时期,不仅规模大幅扩展,服务更广泛的民众,并赢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管理日趋规范,并成为全球国家美术馆管理的典范。
二、经济学向艺术的领域扩张
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斯比,在描述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时,这样表述道,“虽然文化学者多年来在剖析文化和文化实践的社会意义中注意到某些经济学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也有意无意地探究經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艺术的经济学问题时,我的很多同事还是将‘文化经济学’仅仅作为业余爱好而已,它注定被排斥在正统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 [7]而作为大卫·索斯比的老师,罗宾斯所处的时代,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则更为疏远:虽然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城邦的围墙尚未搭建,经济学范围尚存争议,但是,即便如此,文化由于其“非物质性”而彻底地被经济学排除在外。其实,在这两个不同时代,经济学对文化排斥的原因各有不同:在索斯比所处的时代,经济学排斥文化的主要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假设经常不能为文化活动提供量身定做的衡量架构”,而且“文化由于其易变性与松散性特征,不太容易接受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的入侵”[8];而在罗宾斯那个时代,经济学对文化排斥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学的领地主要在物质福利,而文化由于其非物质性特征而被排斥之外。而罗宾斯则是将经济学疆域从物质领域拓展至非物质领域,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拟定经济学的范围与意义的第一人,自此以后,文化以及其他非物质的内容也被纳入经济学的疆域之内,这无疑是文化经济学大厦的重要地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罗宾斯及其《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的努力,恐怕也不可能有其大洋彼岸的学生威廉·鲍莫尔的《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9]——这被视为文化经济学的起源,文化经济学学科的诞生之日恐怕要无限期的推迟。以下我们结合罗宾斯的经济学名著——《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论述罗宾斯如何通过自身的学术努力,将经济学的范围扩展至艺术领域及其对文化经济学的影响。
“饶有趣味的是,当我们猜测罗宾斯对于艺术的热衷,是否也是他排斥基于财富的经济学定义的重要原因。如果考虑到他对艺术的倾情投入远远早于其方法论的形成,上述猜测恐怕是成立的” [10]。对比自传中有关艺术经历的描述与《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分析方法,我个人十分认同学术界这种看法,即艺术是罗宾斯拓展经济学疆域的重要契机。不过,在那个时代,罗宾斯要想实现这些却非易事,他首先要面临传统经济学,或者罗宾斯所谓的经济学物质主义的挑战。按照传统的看法,经济学常常被描述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马歇尔);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解释人类物质福利赖以存在的一般原因” (坎南);“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人类物质福利的科学,这样定义太宽泛”,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相互合作来满足其物质需要。” (贝弗里奇)。[11]8在检视这些经济学大师对于经济学的界定之后,罗宾斯认为,这些界定有着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即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圈定在物质福利,而将自己所钟爱的艺术置于经济学的围墙之外。对此,罗宾斯深感不满,认为“该定义完全未能展示所有最重要法则的范围或意义”,于是,他就从其最为熟悉的艺术领域入手,突破经济学“物质主义”的堡垒,并在拓宽艺术疆域的同时,重新界定经济学的范围与意义。
罗宾斯是以工资作为突破口,来攻破经济学“物质主义”的堡垒的,在他看来,传统的工资理论并不能为“非物质”支出作出解释,这是“不可容忍的”。他举例说,掏粪工的工资是一种劳动所得,它有助于增进物质福利,但是,他接着以其所熟悉的艺术领域举例道,“比如管弦乐队成员的工资,则是付给与物质福利毫不沾边的工作的,这种服务与另一种服务一样,可索取价格,进入交换领域。工资理论既适用于解释后者,也适用于解释前者。它并不是只能解释增进人类‘物质’福利的工作的工资”。[11]11-12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在消费领域也是如此——人们的工资并不只是用于物质消费,“工资挣取者可以用其收入购买面包,但也可以购买戏票”。也就是说,由于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经济学长久以来跛足而行,因为经济学另外一种支撑——非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游离在外,这种局面必须得到纠正。纠正这种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界定经济学,即“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 [11]19在这个界定中,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物质与非物质得到了统一,例如,“厨师的服务和歌剧舞蹈者的服务相对于需求而言是有限的,而且可加以选择使用”,也就是说,无论是物质福利,还是非物质福利,它们都面临稀缺手段的配置问题。以歌剧舞蹈者为例,其服务相对于需求而言是有限的,因而存在稀缺性,而且舞蹈者作为劳动力资源是可以另作他用,比如说改行做厨师,所以其中就面临选择问题,这正是经济学职责所在。
正如其前辈约翰·穆勒所言,“正像修建城墙那样,通常不是把它做一个容器,用来容納以后可能建造的大厦,而是用它把已经盖好的全部建筑物围起来”[12]。当罗宾斯给经济学确立这样的定义之后,经济学终于修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城墙,而非物质的内容,当然也包括艺术,理所当然也是经济学城墙之内的大厦。20世纪40年代以后,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新定义被萨缪尔森所采用,并广泛传播,最终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定义。按照这个经济学的标准定义,罗宾斯1971年发表了《关于艺术政治经济学之未决问题》[13],该文真实地演示了经济学该如何应用于艺术领域:在那篇文章的开头,作者抛出三个问题,即“为什么纳税人要为艺术买单?为什么艺术不交由消费者需求决定?如果人们需要艺术的话,他们自会购买,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么生产何为?”接下来,罗宾斯严格按照《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所确立的经济学方法条分缕析:首先,在作者看来,这些问题都涉及目的,或者终极价值的问题,而价值问题不是经济学所能,因此,经济学对此爱莫能助,而只能交给政治科学来回答;其次,当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入决策阶段,经济学就能有所作为,因为经济学能够解答“稀缺手段的配置”问题,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实用的方法。就此而言,由其爱徒威廉·鲍莫尔所开拓的文化经济学,正是在罗宾斯所划定的经济学疆域之内,按照其所拟定的经济科学性质来讨论文化问题,即文化领域“稀缺手段的配置”问题,如表演艺术的成本病、艺术的公共资助等,因此,罗宾斯无疑是文化经济学学科大厦地基的构筑者,这是文化经济学学术史应该谨记的历史事实。
三、艺术与政府的关系
大卫·索斯比在梳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时认为,“罗宾斯是现代英国第一位论述政府在扶持艺术以及资助博物馆与美术馆中的角色的经济学家” [1],这篇作品就是《艺术与政府》[14]。其实,这篇文章最早只是1958年罗宾斯接受伯明翰城市博物馆与艺术画廊主管的邀请,给同行做的一个关于“艺术作品经济问题”的演讲,后来他将其做了些修订后收入其名为《政治与经济: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63年)之中。由于该文的目标受众是博物馆与画廊的管理者,所以有关艺术的内容也多集中在视觉艺术方面,但是,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则不仅限于视觉艺术,而是要回答当时社会——广大公众以及政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门,有关政府为什么要资助艺术的问题。就此而言,作为其长辈的凯恩斯早在1936年发表了一篇同名文章《艺术与政府》来阐述政府为什么要资助艺术的问题,可惜的是,无论是罗宾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文化经济学研究者似乎很少提及这篇名作,其中缘由耐人寻味,不过它倒是这篇文章不错的一个参照系。[15]在那篇文章中,凯恩斯不仅论述了艺术与政府的历史以及英国的现状,而且分析了艺术之于政府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将其经济学思想嵌入其中,系统论述了政府“干预”艺术的原则、对象与手段。与凯恩斯从历史出发论证艺术与政府之间的积极关联不同,罗宾斯的论述则直接从艺术与政府关系所涉及问题入手,“促进艺术是否是政治机构的恰当的功能?此种促进行为是否与政府职责的自由理念相符?”[14]。
对于这个问题,凯恩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其艺术领域政府干预的核心思想主要如下:其一,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虽然政府本身有着诸多局限性,也就是说,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政府干预只能是补充性手段;其二,政府干预的目标与手段要寻找一种“中间道路”,特别是在手段上不能太集权化,以保证政策的软着陆。[16]就其结论而言,罗宾斯与凯恩斯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就是“政府如果是在一种全然自由的氛围——如同人们根据自己意愿从事艺术——中提供鼓励与支持,那么,这种支持就不会与自由社会的原则相冲突,而与其浑然一体”。[14]从其表述来看,两者均强调政府应该支持艺术,不过要注重方式,不能过于集权,而要注重氛围的营造。只不过,罗宾斯的论证逻辑有所不同,他首先要面对的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观念,特别是那些堪称其精神导师的艺术家的概念,其中尤以布鲁姆斯布里朋友圈之重要成员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与 罗杰·弗莱(Roger Fry)为代表。克莱夫·贝尔对政府在艺术中的作用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社会能对艺术家做的唯一好事就是置之不顾”,[17]在这些信奉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艺术家眼中,政府的干预——不管是什么形式与力度,均面目可憎,只能造成艺术自由的限制,并最终导致艺术的衰败。在罗宾斯看来,自由放任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如同倒掉洗澡水也将孩子一同倒掉一样,既缺乏实用的价值,也缺乏历史与理论的支撑。就历史的视角而言,罗宾斯举希腊伯里克利统治时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为例,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就不可能成就这些伟大时代的伟大艺术。罗宾斯本人既不是艺术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因此这方面的论证只止于此,其重心还是从经济学角度给予政府资助艺术以理论支撑。与历史的论证相同,罗宾斯在理论论证部分所面临的挑战也来自自由放任主义,即“为什么纳税人要为艺术买单?为什么艺术行业不交由消费者需求来决定?如果人们需要艺术的话,他尽可自行购买;如果不需要的话,艺术便无需生产?”[13]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罗宾斯深知艺术,当它作为私人产品时,市场则是配置资源的“看不见的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艺术不仅仅具有私人属性,还具有公共属性,而罗宾斯的论证也就由此展开。罗宾斯这样表述道,“只有我们能够证明教育的这种形式(艺术)不存在无差别的益处,我们关于花费纳税人的钱财资助艺术的论证才站得住脚。”也就是说,在艺术领域的自由主义思想如果行得通,就必须证明艺术是一种纯粹的私人产品,而艺术恰恰具有公共属性,或者说,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产品——“艺术的收益不仅仅是无差别的,而且培育、学习与保护艺术的积极影响并不仅限于那些直接支付费用的消费者,而是扩散至更广的人群,就如同公共卫生机构或者精心规划的城市景观那样”。[14]基于此,我们也许就可以顺理成章作出如下推导,既然艺术与教育具有公共性,那么艺术就应该与教育一样享有来自政府的资助。这样的推导的确简单,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罗宾斯深知经济学乃是研究“稀缺手段的配置”,既然原本可作他用的财政资源,比如说公共卫生,如今则被用于艺术,那么这样的配置方式有什么样的额外收益呢?罗宾斯分析认为,对于满足那些能够明确区分的需求而言,市场机制确实无与伦比。但是,如果认为市场机制也能满足善良社会(good society)所有必要条件的话,这就太过简单化,也会冒着败坏善良社会基本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信誉之风险。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公共经济学分析逻辑: 由于文化产品具有高度的正外部性,往往存在供给不足和效率不高的缺陷,这就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乃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原本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当我们的社会是“善良社会”的话,这种市场失灵则并不可取,因为这会导致社会效益的损失,而影响“善良社会”的构建,因此,为了使社会效益的损失最小化,政府一般会实施干预,比如说提供财政资助,以便社会效益最大化,从而构建“善良社会”。众所周知,公共经济学的这种论证逻辑其实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范式,而涉及政治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罗宾斯这样表述道,“如今,我们十分清晰地知道,这个问题并不能借助经济科学来回答。这其实是一个终极价值问题,是有关你认为什么是政府作为社会威权的目标与功能,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因此,作为这个星球上的政治目标,我个人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认为,艺术的养成与较高的学习水平是我心目中政府应尽之义务”[13]。质言之,艺术领域的政府资助是一个“善良社会”之政府应尽的义务,而且,这种资助有利于提升公民的艺术素养,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并最终构建“善良社会”。
这种观念在他的得意门生、文化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鲍莫尔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一旦出现这种情形(公共产品提供的市场失灵),政府也未能提供资助,就会导致十分糟糕的经济状况——集体资源的错配,以及公共意愿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的投入并不意味着无益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是对社会大众需求的一种回应。[9]385-386罗宾斯的这种理论在其身后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文化经济学界论证艺术资助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国家论证艺术领域公共政策的重要学术支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悼念罗宾斯的讣告中这样表述道,“莱昂内尔拥有多重身份:事实上,我早就听说他被人尊称为‘伟大的文艺复兴巨匠’。年轻时,他作为一名士兵奔赴战场;中年时,他则扮演着类似艺术之王室资助者的角色,同时,也是大学的创建者;他通晓英国文学;他创作——而且,当他以朗诵的方式演讲时——丰富、圆浑的韵文;他在国家事务中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且在壮年担任立法院(legislative senate)委员;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伟大的教师”[18]。正是这种多重身份让罗宾斯在文化经济学领域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贡献: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身份及其经济学思想,不仅让文化首次进入经济学的疆域,而且使很多文化现象与政策有了经济学的解读,从而逐步走向国家政策的舞台;他作为艺术鉴赏家的身份,使他对艺术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免于教条主义,这为文化经济学走向独立与自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作为艺术管家的身份,则不仅让他在文化领域的经济学思考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且在博物馆定位、功能乃至运营等诸多领域有着很多创新之举,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 Throsby, Davi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Arts: A View of Cultu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32 (March),pp.1-29.
[2] Ruth Towse: “Editorial”,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994, 18, p.1.
[3] ML Balisciano, SG Medema: “Positive Science, Normative Man Lionel Robbi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January 1999, 31(Supplement), pp.256-284.
[4] Lord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algrave Macmillan,1971.
[5] Susan Howson: Lionel Robbi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Lord Robbins:“Unsettled Question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rt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Vol.18, No.1,(1994), pp. 67-77.
[7] David Throsby: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8] Gillian Doyle: “Why culture attracts and resists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10) 34, pp.245-259.
[9] Baumol, w. J., Bowen, W. G.: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6.
[10] M.L. Balisciano and S.G. Medema: “Positive Science, Normative Man: Lionel Robbi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31(supplement), pp.256-284.
[11] [英]萊昂内尔·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2] 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引自[英]莱昂内尔·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页。
[13] Lionel Robbins: “Unsettled Question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rts”, The Three Banks Review, September 1971, pp. 3-19,Reprinted in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Vol.18, No.1 (1994), pp.67-77.
[14] Lionel Robbins: Art and the State, cited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an,1963, pp.53-72.
[15]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艺术与政府》,《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志忠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2—420页。
[16] 周正兵:《凯恩斯文化经济学思想述评》,《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7] Clive Bell: Art, p.252, Cited in Lionel Robbins: Art and the State, cited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an,1963, pp.53-72.
[18] James Mead:“Obituary: Lionel Robbins”, Economica, 1985, 52, pp.1-7.
A Review of Lionel Robbins’ Thoughts of Cultural Economics
ZHOU Zheng-bi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Ruth Towse’s view on 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there is a period of prehistor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cultural economics by William Baumol. During the prehistory period, Keynes and Robbin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for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economics, not only because they addressed cultural economic issues, but also for their art Butler role in Great Britain.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thesis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s Robbins experience as art butler, thoroughly interprets one of classical masterpiece of cultural economics——Art and State, then tries to figure out how he widened the territory of economics with the aid of his knowledge on art, and how he applied economics theory into the field of arts. By all these efforts, this thesis wants to summarize the Robins’ thought on cultural economics, and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Lionel Robbins; founder; cultural economics; Art and State
(責任编辑 编辑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