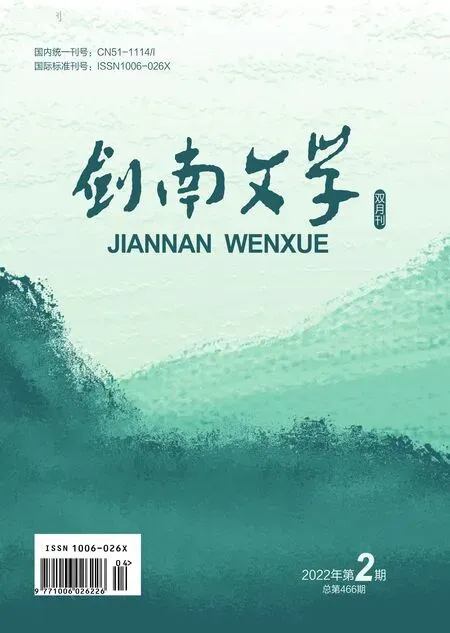攀枝花记
□杨献平
走或者坐在某处,暴烈的日光下,三角梅开得热烈,水流沿着谷底,在时间中衔沙吞石,浩浩荡荡。尤其晚上,天空狭小而窄长,星星似乎是从天庭逃匿的仙子,于额头之上的晴空,颗颗闪烁。很难想到,七十年多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处空谷,只有几户人家在这里生息,彼时的荒草和岩石铺满山谷,尽管偶尔有牛羊在其中散漫,但当时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一道偏远而又荒芜的裂谷,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众人的聚集之地,甚至由此而成为一座与世界和人类文明发展同步的现代化城市。
这个地方,叫攀枝花。
站在保安营机场边缘俯瞰,一座城市在峡谷中赫然陈列。一栋栋的楼宇,虽然不够紧凑,但也起伏有致,且设施和样貌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丝毫没有区别。四周是莽苍连绵、纵横勾连的群山,攀西裂谷以上的天空蓝如汪洋,阔大无际,且纯粹透亮,浓郁的阳光似乎色彩明丽而又黏稠。满城的花卉以各种颜色点缀其中,红的似乎像燃烧的炉火,白的像是洁白的卵石,粉色、黄色、蓝色也跻身其中,使得这座崎岖不平的城市,像是一艘造型极为奇特的巨型船舶,横在峡谷底部。若不是川流不息的车辆,以及各种各样的矿产设施,散漫各处缓慢移动的人群,整个攀枝花市区,就像是一张横卧于天地之间的自然巨画。
而在这幅巨画衔接的山谷之间,有两条蔚蓝色的锦带,在高山峡谷中蜿蜒,如静静飘逸的丝绸,以优美的动感,自由的延展,浩然于苍茫远方,奔纵于城市一侧。那种姿势,像极了亲近的注入,也像极了鼓动的双翼。她们的名字,一个叫金沙江,是川藏之间的又一条伟大的河流,其又名绳水、淹水、泸水,发源于遥远青海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或者与之相距不远的唐古拉山脉东段北支5054 米无名山地东北处。起初成为通天河,至玉树直门达更名为金沙江。其状如游龙,于万山之间,流经川、藏、滇三省区,途中,又有雅砻江强势汇入,奔流到四川宜宾,再纳岷江,便就是浩浩荡荡、千里连贯的长江了。另一条便是名闻遐迩的雅砻江,作为金沙江的最大支流,这条河又名若水、打冲江、小金沙江,在藏语当中称为尼雅曲(多鱼之水)。
雅砻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系尼彦纳克山与冬拉冈岭之间,她的孕体也是洁白的积雪,高孤之处的神灵般的密集存在。其行至四川甘孜州石渠县之时,便被唤作雅砻江。其身全长1500 公里,多数时间在奇崛山谷中奔腾咆哮,向南穿过龙县、雅江县的箭杆山,再到蜀山之王贡嘎山,尔后转道木里县,在锦屏山甩了一个一百多度的大急弯,因而形成了一道堪称奇观的大河湾,然后从容流经冕宁县,越过锦屏山和牦牛山共同挤压而成的峡谷,进而直奔阳光之城攀枝花。
两河交汇,使得攀枝花在攀西高原的高山峡谷之中有了柔性的特质,也具备了人居和城市的根本动力。当然,金沙江和雅砻江的忽然结合,也使得整个攀西地区有了灵性的内蕴和血脉上的沟通。
攀西裂谷隶属于世界上最年轻的横断山脉,这是中国境内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唯一的兼有太平洋和印度洋水系,横亘于青藏高原东南部,贯通四川、云南和西藏东部。
在华力西晚期 ( 405 ±5—250Ma,包括泥盆纪至二叠纪),岩浆活动频繁,进而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攀枝花带、昔格达带、金归塘带和三堆子带四个近南北走向的岩浆岩组合带。所谓的裂谷,是地壳伸展构造作用的产物,它使岩石圈减薄和破裂,地壳完全断离,有时新生的洋壳就会在其间产生,因此它代表了大陆裂解、洋盆产生的初期过程。而形成裂谷的根本驱动力,则来源于热构造的应力和浮力作用。在海西晚期 (270Ma-200Ma),攀西地区曾经历过一次强烈的构造-岩浆热事件。这次构造-岩浆热事件以海西晚期岩石圈张裂、地幔熔融开始,和超基性-基性岩浆的大规模侵入和强烈喷溢为特征,此后裂谷发展进入沉降裂陷阶段,形成宝顶断陷盆地、红坭断陷盆地。当岩石圈底面的热穹窿只有一个穹窿顶时,便形成一个裂谷;当热作用不均匀时,在热穹窿的顶部便又形成某些相对低温的区域,对应裂谷中央的窿起区。当穹窿顶的低温区不断扩大和加宽之后,就形成了两个穹窿顶,即两个构造岩浆带。因此,攀枝花-西昌带具有 “双裂谷” 的特点。
遥远的地壳运动雄奇而壮观,但目击这一奇绝运动的动植物,则无一例外地成为了灰烬或者化石。地球或自然的伟大性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种彻底的改天换地的自然运动,在地球的早期历史上频繁上演而使得当时的生物灾难重重。生物们的消失,以及地球样貌的改换,使得人们在不断的科学研究中,一点点地追忆和验证到了我们所在地球的坚韧和无常,仁慈与残酷。
庆幸的是,直到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依旧安之若素,如此之多的人和其他生命同处同生,在风雨和云霓,日月星辰、山川江河、村庄城市、沙漠大海之间,人们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装上了穿透性的眼睛,并且有心灵始终与天地保持着一种相互依存、谛听与领悟的关系,用智慧和科学,一点点地了解它的过去,并且试图洞彻它的未来。人,以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个星球的组成部分。
这就像我所了解的攀枝花的前世今生,起初,它只是地球的一部分,剧烈的岩浆运动之后,逐渐成型,并且很快随着人类的诞生和不断的迁徙,进而成为了与世界、与每一个人同气连枝、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据科学家考证,在史前时期,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足迹。其中的元谋人、蝴蝶人和回龙洞人,都在这里留下了生活的踪迹。可惜的是,地球自身的变迁乃至人类多舛的命运,以及气候的作用,总是令一些人来到,尔后又归于无声。地球和时间的利剑快刀,总是在屠戮被其掌控的万物。
没有人知道,在距今一万或者两万年前,有多少人在这里生活,又有多少人和其他生物由此迁徙,去向远方,或者融合。至上古时期,在这里产生的神话令后人猜想不已,据司马迁 《史记·黄帝本纪》记载,黄帝,这位传说中雄武大帝之次子昌意便被分封或者被派遣到若水 (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 居住,并且统御一方。在这里,昌意生下了后来成为 “五帝” 之一的颛顼。不管这个记载真伪如何,至少可以证实,无论是多么早的历史,无论多么纷繁的传说,古中国始终是一体的,而不是割裂的,也不是狭小的某一个专属地域。关于这一点,《禹贡》 上说,“禹分天下为九州”,“华阳黑水唯梁州”。这里所谓的梁州,就包括了现今的攀枝花和西昌地区。
斯时,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先后有髳人、微人和濮人,这些人现在是难以描述和确认的,但 《尚书·周书·牧誓》 当中,俨然有这些人或者部族参与武王伐纣的记载。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在早期中国历史上,苍茫的大地上不仅住满了各种各样的族群,这些族群还是相互联系的,可以说是同族同源的。也可以说,我们的先祖从来不是分裂的,也不是互不造访、迥然隔绝的,而始终保持着一种形式不同、目的有别,但相依共存的社会或者部落联盟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始终紧密。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单独的个体。个体只有容身于集体之中,才能找到基本的安全感。这种情况从宇宙洪荒之日起,延展到现在,仍旧没有很大的改变。就像攀枝花苏铁。那么多距今二亿八千万年前的铁树,在巴关河西岸的丰家梁子上,依旧葳蕤,且年年开花。相对于植物,攀枝花的地域和政治属性,则一再更迭。在西汉前期,这里一度成为 “化外之地”,直到汉武帝时期,这个有雄才大略而又将西汉王朝折腾得家底贫瘠进而显露出淋漓败相的有为之君,派出司马相如带队前往该地区招抚 “嶲夷”,并于公元前111 年,在现在的西昌设立越嶲郡,置馆衙及驻军,对攀西地区的民众进行统领。至王莽时期,这里又被改称集嶲。随着西汉王朝的崩溃,中央帝国不复存在,攀西地区也和其他边远之地一样,与所谓的中央帝国失去了联系。
这也说明,中央帝国的强盛与否,一直是左右边地乃至下属之地的主要杠杆。尽管东汉一度恢复了对越嶲郡的管辖。但盛衰自古有序,只是众生不察。到蜀汉时期,诸葛亮远征,孟获,这个具有传奇性的彝族首领,他的疆域包括了今之攀西、云南昭通、贵州毕节等广大地区。因此,在这些地域上,均留下了诸葛亮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及令人不疑的传奇故事 “七擒孟获”。
王应樑在 《诸葛亮与云南西部边民》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 (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11 月第一版) 中说:“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在现时云南全省各地区中,是被一致崇拜敬仰着的一位古人——或者可以说是一位神灵,武侯祠是在任何城市村镇中可以常看到的,孔明之名,虽村妇孺子,也多知之。这原因,当然为着这位历史上的伟人,在距今1700 百年前,曾经身统大军,五月渡泸,来到这南蛮之区,七擒孟获,使犷悍成性的南蛮,也居然能心悦诚服的俯伏于地曰: ‘南人不复反矣!’ 神威厚德,广被南中,一千余年来,受南中人民的馨香敬仰,自不是偶然的事了。”
古来的文人名士,将相大臣,都在大地上、人群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和传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句民间俗语端的是至理名言。像诸葛武侯这样的忠义孤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不二之士,百般计谋、所为一事的孤绝之人,纵然有违世之执拗、弃时宜而不顾的种种偏执和失败,但其所为及所留,特别是个人品行上的自觉高拔、思想和入世之后的独善与兼济,想来也是独一无二、令人敬佩的。关于他的故事,至今在百姓口中、西南大地上久久不散,处处皆有。然而,无论哪一种人生,都是短暂的,王朝也是。三国之后的攀枝花地区,随着中央王权的频繁更迭,再次落入隔绝。至北魏,再称严州。隋朝因循之,唐时又改为嶲州,设置都督府。强文弱宋无力顾及,元朝击灭大理国后,随手将攀西地区纳入其版图。后来的明清,则一直对攀西地区行使管辖权。其在近代史上逐渐明了的时期则是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 开始的,期间,虽有多次更名,州府易地,但始终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衔接。而吊诡的是,攀西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却一直是沉睡的,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迁徙的无数人们根本意想不到,就在这旷寂的高山峡谷之间,居然蕴藏了堪与他们的生存、发展和迁徙史相提并论的丰富而“卓越” 的矿藏。
攀枝花当地朋友说,诸葛亮率军在此擒放孟获。现在的攀枝花机场所在地保安营就是其当年驻军地之一,此外,还有万宝营。保安营是攀枝花市区的制高点,万宝营也是。前者以开阔的山头和雄奇的身姿,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后者则以其幽秘纵深而又超拔深藏成为松露及其他野生珍稀动植物们的家园。攀枝花的朋友还说,当年,诸葛亮及其军队至此,还得到了著名的七星砚台,即攀枝花仁和区之独有的“苴却砚”。
苴却砚是最能体现攀枝花古来文化气息与文化内涵的,这一种名砚,以其色彩丰富而亮丽,独步于四大名砚中,其有石眼、青花、金星、冰纹、绿膘、黄膘、火捺、眉子、金线、鱼脑冻、蕉叶白、庙前青、玉带、紫砂、鸡血等等,品种多达百种,尤以碧翠神溢、如珠似宝的石眼著称,此一特点,唯独端砚和苴却砚所有,一般由带核心的绿色,呈极规则的椭圆形团块分布于砚石当中,顺着圆心的水平单面剥开中心,可以看到或红或紫或带金星的瞳眼 (眼心),有心为活,无心为死或盲眼。其周围或带晕、或有数圆环。其型有龙眼、猫眼、龙眼、象眼、鹤眼、鹰眼诸多种。
按照人类新的对地球的研究和测量方法,在时间之中穿越无数晨昏的攀枝花,具体位置为东经101°08′至102°15′,北纬26°05′至27°21′。在来自高寒之地,澎湃激越的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之地,东边是著名的古城会理,北边则为德昌和盐源县,西边与现在隶属于云南的宁蒗、华坪、永仁临界。如此的一方地域,既有仿佛神灵的大水源源而入,又有苍苍生灵于其间扎根、挪移和更迭。时间行至20 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正在经历又一场浩劫——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无数人在其中丧生,即使偏安一隅者,内心也充满了末日般的惶恐。在东方战场,日本侵略者攻势猛烈,奋起的中国人民与之进行着殊死较量。
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先后相距不远的两次世界大战肯定是空前的,无论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也无论战争对自然乃至人类的摧毁力度。尽管,攀枝花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并不是主阵地,但一国之灾难,任谁也无法幸免。当时对这方土地和人民具备统领权利的,是孙中山之后的中华民国。当时的政府所在地依旧设在西昌,称之为 “西昌行辕”。这个名字,显然带有文白夹杂的意味,其中也隐隐透露着古老的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时代转身的艰难意蕴。
这个西昌行辕颇有意思,虽然地处西南,又适逢国难,但其配备一样不少,可谓五脏俱全。其中的地质专员就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职位,另外的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也令人闻有所思。今天的人们,不妨作如此猜想,即: 中华民国虽然没能蜕尽明清之皮囊,但从国家机构乃至其倡导的科学、文明角度来看,它又是与世界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具有同步或者趋同性质的。因而,对于彼时甚至今天的攀枝花来说,也从中受益匪浅。而这个 “益”,一方面源于地球自身运动的玄妙与神奇,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现代科学对于地质的全新认知和科学探测。
这里隆重出场的人分别名叫常隆庆,还有刘湘、刘文辉、卢作孚、刘之祥、汤克成、赵亚曾、殷学忠。都是在攀西裂谷留下隆重痕迹的重要人物。历史总是在不期然之间,格外垂青某些人和某些有灵之物。但在此之前,一场6.4 级的地震席卷了马边和雷波县地,主震区在马边县的玛瑙乡 (今民主乡)和雷波县马湖北。
从1935 年12 月15 日到1936年5 月16 日,这一带先后发生了3次强烈的地震,最大的为6.4 级,最小的6 级。这三次地震,使得攀西地区以及宜宾、重庆、楚雄等地都有强烈的震感。这三次地震,均对攀西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当时缺乏必要的预测和抗震能力与技术,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数很大。但这一历史事件,除了在专业的学科期刊和书籍上有所记载之外,后来很少被人提及。地球母亲在时间中的暴怒及其决绝的剧烈动作,带给众多生命的伤害,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人类是善于忘记的,也善于从灾难中站起来。人类生存与繁衍的顽强能力,绝对可以与天地之恒久相提并论。
攀枝花处于亚热带地区,日光充足,气候宜人,直到现在,仍旧是四川乃至其他地区人们过冬的最好去处之一。然而,在1936 年,这里还一片荒寒。整个峡谷中,只有上坝和下坝两个自然村。除此之外,莽苍峡谷,多数的山是光秃的,没有一丝生机。只有少部分山野,草木茂盛,野花众多。在此交汇的雅砻江和金沙江寂寞奔淌,没有任何自然的节制和人为的影响。这一年冬天,重庆雾锁大江,日渐寒冷。作为地质所所长的常隆庆带着助手殷学忠,跋山涉水,前往“宁属七县”,调查发生在马边和盐源县的三场地震,他们在马边和盐源的主震区实地查看并做了调查之后,发现当地的灾情不怎么严重,遂把主要的任务转化成为对攀枝花地区矿产的探测和研究上。
这是1935 年12 月。此前,现在属于凉山州的会理县也发生了强烈地震。当时通信不够发达,关于地震灾情,流传的说法不尽相同。有的说,这次地震震幅很大,造成了大面积的山体坍塌,从而阻断了金沙江。在此背景下,时为四川省建设厅长的卢作孚就派常隆庆前往勘察。常隆庆便和助手殷学忠一起,从重庆出发,到会理进行实地勘察。
从重庆到会理,何其遥远?斯时,并没有公路,即使现在,从成都乘坐火车到攀枝花市,也要9 个小时左右。当年,交通落后不说,沿途的一些情况也比较复杂。当常隆庆和殷学忠到达会理的时候,已经是又一年的春天了。
照实说,这种漫游在大地上的崎岖行程,不管是旅行还是公务,其过程肯定是相当艰苦的。等常隆庆他们走到会理已经是1936 年了。此时,春天已经到来,本来就温润的会理一带春花竞放,万山葱翠。气候显然与重庆和成都有着天壤之别。经过调查,常隆庆和殷学忠发现,这次地震,对会理乃至金沙江的影响并不像传说的那样严重。遂写好报告,转而把自己的任务重点转向了探测和发现会理周边的矿产资源上来。
常隆庆自1921 年开始,就痴迷于地质学,北大学成后,又跟随翁文灏先生,地质学造诣深厚且敏锐。在调查过程中,常隆庆等人强烈意识到,宁属七县之地理地质条件,极有利于金属成矿。所谓的宁属七县,便是今天的攀枝花-西昌地区。因为当时隶属于宁州 (今德昌) 之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边、盐源、宁南七个县。从重庆至宁属七县,路途遥远且艰苦,与其匆匆返回,不如就地做一些地质考察。这也是当时四川省建设厅长的卢作孚先生的意见,或者说交给他们的另一个任务。常隆庆决定与殷学忠一起,以调查矿产资源为目的,把重点放在宁属七县。他在后来发表的 《宁属七县地质矿产》 绪言中说: “此次调查,纯出于四川建设厅长卢作孚先生之计划。” 说明他们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卢作孚建设抗战大后方的战略思想是相一致的。
宁属七县地域面积广,地质构造特点独具,是川滇交界之地极富有特色的地方,境内有彝苗蒙回等多个民族,历来为王朝所重视。常隆庆和殷学忠迈开脚步,以双脚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漫游和勘察。他们先是从会理步行到盐边东南、金沙江左岸的三堆子,又渡过雅砻江到达倮果,然后沿着江边的崎岖山路继续西行。
这是一条没有任何道路的山地,途中的崎岖、艰险可想而知。在奔流的雅砻江畔,两个地质学者,一边艰难跋涉,一边细心踏勘。见到特殊的岩石和地形,都要爬上去仔细搜索和勘验。每到一处,他们都采集标本,一块一块地放在口袋里。若非带有两匹老马,可以代为负重,仅凭常隆庆及殷学忠二人之力,如此漫长旅途,恐怕很难带回那么多的标本。
许多天后,他们到达密地、倒马坎江边,常隆庆和殷学忠发现,这一带有很多的铁矿石,以后说不定可以找出一个大矿来。他在山头上、大江边上盘桓许久,仔细查看,并采集了一些典型的标本,带回去化验,然后又在地图上做了标注,与殷学忠继续前行,到走马颈子、烂泥田、弄弄坪、巴关河、棉花地等处,再翻过冷水箐,到达盐边县城之后,稍微休息了几天,整理了资料之后,又去往盐源、西昌,然后到达雅安。
这一次行程,常隆庆和殷学忠走了近7 个月,走破了七八双鞋子,衣服褴褛不堪。斯时的成昆路上,高山峡谷,河流浸漫,想想也是一场苦行僧般的旅程。1936 年9月中旬,常隆庆到了位于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这一次勘察,可谓收获多多。正如常隆庆在其《宁属七县地质调查》 一书中所说:“费时半年,周历七县,在勘矿区50 余处。” 这一次,常隆庆和殷学忠采集了数百块化石和矿物标本,并用地图的方式,把自己所到之处,进行了详细的标注,做了大量的考察笔记。
常隆庆和殷学忠的这一次勘察,大致是中国科学家对攀西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他们之前,似乎没有人系统地考察过这片土地上的矿产资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黎明教授在 《常隆庆: 攀枝花之父与攀枝花磁铁矿的发现》 (载《攀枝花学报》 第33卷第三期) 中说: “攀枝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地处金沙江、雅砻江汇合处,攀西大裂谷中南段。早在《后汉书·郡国志》 中便对台登 (今泸沽)、会无(会理) 出铁的事实做了明确无误的记载。而在清朝,会理小关河一带的冶铁业已经十分鼎盛,小土炉达百座之多。”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利用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开始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他们的别有用心且肆无忌惮的侵略势力,他们以经商、传教、考察为名,深入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各种勘测和科考活动。从1872 年到20 世纪初,在川滇一带的羊肠小道上,出现了诸多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先后进入攀西地区,对矿产资源进行了初步勘探。据资料记载,这些西方地质科考人员当中有法国的莱克勒,德国的李希霍芬、乐尚德,奥匈帝国的劳策,瑞士的汉威等,他们皆是当时科学巨擘。其中,1901 年由法国派出的矿产工程师勒克莱编写的 《东川附近省份地质和矿产研究》 获得出版,里面记述 “纳拉青北部滨江台地 (今攀枝花东区肉联厂一带) 第四纪含金岩层与马尚 (今攀枝花矿务局技工学校东南) 附近瑞提斯煤层” 等地质矿产情况。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攀枝花乃至往昔的 “宁属七县” 范围内,人们早就发现了储量较多的铁矿。只不过,限于当时的技术能力,人们只能小规模地开采和冶炼。但对于攀枝花的巨大矿产资源,尽管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涉足,并且企图在这里发现惊喜,进而作为一种个人乃至国家民族的荣耀,但他们对攀西地区总体上还是轻忽的。
可以说,20 世纪初期,是西方对东方大发现的高峰时期,那么多人来到古老的东方帝国境内探险,寻找他们足以光耀当世影响后代的宝藏,尽管其中有许多人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不同地区发现了一些震惊世界的 “文明” 遗迹与 “证据”,可是,中国的内在的文明还是无法被真正发现和套取。因为,在泱泱数千年的历史当中,中国一直是世界先进文明的创造者和延续者,直到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的普及,才导致了这个老大帝国于近代的积贫积弱,再加顽固与愚昧,才遭受到了残酷的几近于灭顶的灾难。
然而,在中国,始终有睁眼看世界的高瞻之士,也始终有着不折不挠献身于家国民族的仁人志士,更有着怀着热血之心,激荡青春理想,用知识和科学,为家国奉献生命和智慧的人。
攀枝花矿最初的发现者,后来的开创者,都是如此。其中有一些名字不该被忘记,如卢作孚、刘之祥、常隆庆、汤克成、徐学勤等实业家和科学家。当然,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亲自到攀枝花指导,确定了攀钢的建设地址。应当说,每一座城市的形成,都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甚至是他们的血肉和骨殖。攀枝花也是如此。由于攀枝花钢铁集团和攀枝花市的发展建设,今天的攀枝花,已经是花果遍地、芳香弥散的阳光之城了。
在攀枝花,有一种极其古老的植物,完全可以与攀枝花矿产资源的存在时间相提并论,且有过之无不及。它们长在攀枝花一面山坡上,名字叫苏铁。在攀枝花西区和仁和区所共有的这面山坡上,生长有38.6 万株成年苏铁,幼苗14.5 万株。这一古老的生命,延伸到了今天,俨然是一道令人思接千载、精骛八极的关于生命和灵魂的风景。
苏铁最早出现在距今两亿多年前的古生代二叠纪,中生代晚三叠纪至早白垩纪为其繁盛时期,苏铁是当时植物中最喜欢结群者,术语称之为 “建群”,它们的身影遍布白垩纪。仿佛在那个遥远年代,它们才是地球表面上堪为最高统治者的植物之王。可是,自宇宙诞生之日起,盛衰就成为了整个自然界的整体命运。这多么像是我们人类,乃至逐渐在地球上销声匿迹的动植物们?进入新生代又经第三纪造山运动及第四纪冰期气温下降之时,苏铁开始了它们的衰败历程。强者生,弱者死,这种地球表面上的演化从来没有停止过。苏铁也是,强大的留了下来,弱小的归于大地。当地球来到今天,苏铁也渐渐稀少,目前,仅间断性地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攀枝花苏铁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布德镇巴关河西侧海拔1140至2000 米之间一面比较陡峭的山坡上。苏铁看起来有着无限扩张力的茎叶,尽管有些锋利和粗硬,但它们却毫无杀意,完全是一种虚张声势的 “自卫性” 的肢体语言表达。想来,在远古时期,苏铁也如同这般,在大地上丛丛生长,四散开来,以这种柔和的硬度,来保卫自己。
谁能想到,如此的一种植物,它们见证的,经历的,显然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类的想象范畴。植物的灵性体现在它们对于大地自然的顺从性上,什么样的环境生长什么样的植物,也潜藏什么样的动物。适者生存不仅体现在动植物的生存能动性上,更体现在它们高度自我的选择性上。攀枝花苏铁胚株无毛,与分布在日本、波利尼西亚、马达加斯加等地的同类不太相同。其大孢子叶片为篦齿状,雄花球刚硬直,一如青春期的男性之生殖器……雌花球内部凹陷,如女性之生殖器。天地造化,自古就是男女平衡,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中国古老的阴阳学说,是大地上所有生命的共有特性。
我拨开茎叶,仔细观看,只见雄花球果真刚直,雌花球则微微下陷。有一些蜜蜂潜入其中,不停地挪动,扇着翅膀,寻找苏铁当中的甜蜜部分。再去看其他的苏铁,大致也如是。在这片保护区,苏铁和柏科、壳斗科、杨柳科、桑科、荨麻科、莲叶桐科、石竹科即五味子科、十字花魁、蔷薇科、景天科、豆科、大戟科、使君子科、仙人掌科、桃金娘科等数十万株植物同生并存,有交叉但没有战斗,有覆盖但没有强行的压制。如此森然之貌,生存之地,体现的是大自然的宽容与丰饶之美,也体现着万物秩序之精妙。
在其间,还有长吻鼹、穿山甲、豹猫、高山姬鼠、西南绒鼠、大绒鼠等地面性的动物出没,天空上,有白腹锦鸡、红腹角锥、大鵟、黑鸢、雀鹰、苍蝇、燕隼、斑头鸺鹠、棕胸竹鸡、中华鹧鸪、红隼等鸟类飞跃。可以说,攀枝花苏铁保护区,乃是一个美不胜收的自然之地,因为有苏铁,众多的动植物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在峡谷以上的山坡,日日眺望着高楼林立的攀枝花市区,也守望着日月星辰,以及沧桑的岁月。
从山上朝下看,整个攀枝花市区尽入眼底,攀钢在最远处矗立。而城市,则呈间隔性在峡谷之中参差不齐,一片片的楼房建在山坡上,给人的感觉清爽而又明亮。走在街道上,无论是哪里,都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还有很多北方的吃食。说攀枝花是三线建设带动的城市,不如说攀枝花是不同地区的劳动者,乃至散落在这片地域上发热的各个民族共同塑造了攀枝花的混血性,尤其是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这些年来,对于巴蜀乃至西南各地,我最喜欢的,大致就是攀枝花了。这座城市虽然没有成都大,但他的宽和度却是足够的,又毗邻云南,到处都是阳光,无论是原始森林,还是荒废的滩涂,无论是城市楼宇,还是乡野四合院,那种别致、细微而又庞大的照耀,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冬天,在攀枝花生活,其惬意的程度,与日光的温度简直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