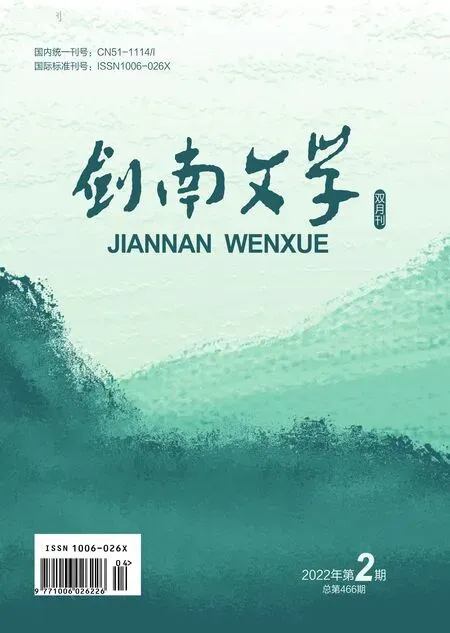文化记忆、民间智慧与现代性反思
——阿来《蘑菇圈》再解读
□达则果果(彝族)
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初刊于《收获》2015 年第3 期,后与《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一起收入“山珍三部”系列,因其“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而于2018 年获得鲁迅文学奖。《蘑菇圈》以阿妈斯炯的生命历程为时间线索,围绕消费主义浪潮下被狂热追逐的松茸展开叙事,建构了阿妈斯炯与蘑菇圈之间惺惺相惜的诗意关联,道出机村人朴素的生存经验与文化记忆。同时,呈现了藏地同胞对待自然的态度由敬畏到占有的心态历程,以此折射出人性变迁与复杂的人生韵味。作者对消费社会中人性的贪婪欲望进行了无情批判,展露出对不断消解的原生态文化的哀婉叹息与深沉思考。
“机村”是阿来的文学故乡,阿来向来通过描写机村的地域风貌、风俗习惯、人情世故来建构其浓郁的乡土情结与文化记忆。在物质贫乏的饥荒年代,机村人靠着强烈的生存欲望与朴素的生存经验渡过生命之劫,斯炯靠着养蘑菇帮助家人躲过饥饿带来的恶梦,机村所有人也都无不得到蘑菇圈的恩惠,阿来平稳沉着的叙述口吻背后是对人与自然互依互靠的生态关联的肯定。而工作组的到来带给机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也消解了其原有的诗意家园与原生态文化,阿来借此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深沉思考。另外,作者以蘑菇圈这样的奇珍物产来观察当地人群在消费主义浪潮下对金钱与名利的渴望和追逐,道出机村人世界观变化的实质是机村原生态文化变迁与解构的真相。人性的贪婪与虚荣是作者所唏嘘的,但如阿来在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里谈到:“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阿来的笔调始终向人性的真善美倾斜,在温情叙述中引导读者完成理性的反省与思考。
一、文化记忆:对诗意家园的眷恋
在对过往的认知和未来的建构方面,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扬·阿斯曼说:“记忆不是对以往事实的简单的储存,而是对这些事实富有想象力的重构,每个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他先前获得的知识带入眼前的文本之中,这个已有的知识相当于背景知识。”机村作为阿来记忆的“场域”,是藏地文明的一个缩影,夹带了作家个体的文化记忆。阿来以文学作为记忆的媒介和载体记录了机村日常生活,对机村诗意家园与原生态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不断消解表现出沉重的叹息与眷恋。
在阿来的记忆中,机村有着朴素的原生态文化,人对自然万物充满怜惜与敬畏,遵循着自然的节奏与规律,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比万物生灵优越,当布谷鸟鸣叫时人们会停下脚步抬头望望天,聆听大自然里传来的“音乐”。朴实的藏族同胞并不从形式或理论上去强调自然生态观念,也不是出于友善相处以维护自身安宁的现实功利主义目的,他们对自然的怜惜是出自本能地对环境和谐、平衡的维护,对万物的敬畏,达到了与自然万物心灵的融洽与相通。斯炯对一切生灵都心生怜悯,见了啄蘑菇圈的小鸟时,她会说:“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只是来看看。”小鸟、人与蘑菇是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态共同体,他们的相处是融洽而默契的,正如拉慢·塞尔登说:“我们的人生是要实现我们自身与周围充满生机的宇宙之间的纯洁关系而存在的。”不论是机村人对工作组“物尽其用”思想的惊讶,还是法海和尚寻思自己死后是否会转世成蘑菇的生命轮回观,皆映照了藏地淳朴的文化观念下人与自然纯洁关系的存在。阿来将藏地植物与小说叙事相融合,通过叙述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从而抒发对天然朴实的诗意生态家园的眷恋。那些吃野菜蘑菇,与小鸟泉水做伴的记忆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记忆,也是机村人的集体行为,是一个群体认知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想象。
工作组的到来改变了机村原有的伦理文化观念。法海和尚叫胆巴是因为在机村的文化记忆中很多人都叫胆巴,而非外人所猜测的那样这个名字效仿了元朝帝师的名字,刘元宣等人对“胆巴”这个称呼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猜测,法海的一句村里还有几个人也叫这个名字使得他们哑口无言。斯炯与女组长之间对话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女组长对胆巴的身世刨根问底,甚至猜测斯炯有很多男人。女组长的话语是站在道德与政治高点的审问,而斯炯觉得这个世界不该容不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藏地的包容是一种原始的大爱思维与人文关怀的映现,阿来以此凸显对外界的实用目的与功利情感的讽刺。另外,随着政治权利的涌入,政府把原来八百人的寺庙精简到只有五十人,和尚被要求还俗回家从事生产。寺庙的精简实际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村原生态文化的侵蚀。政治与权力话语使机村原有的思想观念和宗教形态都受到了冲击,从而将当地居民最初的自然意识纳入进国家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机村这样的自然村庄在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消解了其原生态样貌,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皆得到解构。但是,阿来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对外来观念的入侵充满愤怒和无奈,文中不止一次提到遭遇饥荒时工作组教会了当地百姓识别野菜,教会他们蘑菇的多种吃法,外界传入的饮食文化机村人是乐于接受,并感恩于心的。阿来所哀悼的仅仅是那些破坏生态平衡的所谓开发自然资源的新思想,他在文中痛心疾首地写到:“基于这种新思想,满山的树木不予砍伐,用去建构社会主义大厦,也是一种无心的罪过。后来,机村的原始森林在十年间几乎被森林工业局建立的伐木场砍伐殆尽。”树木砍尽的后果是机村陷入前所未有的旱灾,山林葱郁的神性世界遭到破坏,随之而起的将是人文生态的坍塌。
阿来不以高高在上、置身事外的姿态书写机村,他不盲目推崇原生态的愚昧落后部分,也不凭着感性情怀批判改变机村的外来力量。他是在理智的心态下饱含着深情去描摹人性的淳朴、善意,缅怀充满诗意与神性的自然家园。对遭遇话语破坏的原生态文化与自然吐露着深沉的哀叹与惋惜,试图通过重组文化记忆来启示人类谨慎、辩证地对待现代文明和权利话语的思想武器。
二、民间智慧:朴素的生存经验与人情关怀
阿来的小说里处处渗透着藏地特有的地域文化景观,但其视野是开阔的,如刘青说的那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不会拘泥于某种文化,而是去开掘正史没有概括的‘智慧’——而当作家发现了民间智慧,智慧的多义性,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阿来写宗教风俗、生死景象、婚丧嫁娶等人文风情,但不局限于民族志那样客观的文化记载,而是在藏地景观书写中渗透人们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样态,呈现一种地地道道的根植于民众的民间智慧,那是一种与现代人和现代文明全然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生产方式。这些智慧包含着人类集体经验的传承与发挥,包含着人性的浑浊与复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最接近底层世态的“民间”现实。
“人定胜天”的大跃进之风的涌入将机村推进颗粒无收、饥饿困苦的境地。在饥荒年代,人们发挥出朴素的生存经验,以勤劳、顽强的民间智慧应对现实生存困境。机村人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他们用牛奶烹煮蘑菇,但从不追求所谓感官文化的迷恋,只感叹与感激自然之神的赏赐。男人放牧或打猎,女人寻野菜是他们世代积累的生存法则。而工作组却对机村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进行了重新定义:“旧”的是落后的,“新”的是先进的。工作组认为粮食产量翻一番的方法就是多上肥料,上足了肥料的麦苗拼命生长却始终不熟黄。斯炯只好悄悄背水上山喂养蘑菇存活并成长,她与蘑菇之间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相互依赖,也是精神上的相互依靠,她对蘑菇悉心照料让其生命得以延续,蘑菇回报她以战胜饥饿的希望。不同于莫言、阎连科等作家笔下的饥饿书写,偷、抢、藏,甚至人吃人的人性之荒诞与丑恶暴露无遗,阿来笔下的藏地在面对饥荒时是充满温情的。在食物极度稀缺的困境下,斯炯带着儿子挨家挨户将蘑菇悄悄放置于同村人门口,而机村人得知蘑菇来自斯炯后,将打猎得来的肉偷偷放置于斯炯家门口。如此,整个机村所有的生命体都存在于一种互相依赖和联系的关系网络结构中,而机村则是整个大自然界关系的缩影。在这复杂的关系中,各生命体之间最密切的关系便是相互依靠和帮助。机村人面对饥饿没有形成饮食的狂欢或畸变,而是于饥荒的隐忍与坚韧中相互扶助以共渡难关。
小说中吴掌柜以他悲剧的人生遭际观照了故事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轨迹。面对生存危机,相较于机村人的坚韧与智慧,吴掌柜的内心是绝望与恐惧的。他为了在死前吃顿肉而偷了生产队的羊。王光东先生在《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 中指出:“当人的生存成了根本性问题时, 人所关心的就是如何活着, 至于在常态下的伦理规范、美丑、善恶、真伪等对他们而言已不是重要的问题。”面对生存困境,机村人关心如何活下去,且依然坚守天然的真、善、美的可贵品质,而吴掌柜则表现出了遗憾中的决绝,越过了伦理规范。面对吴掌柜的偷盗行为,机村人不仅不责怪,反而用无限的悲悯对吴掌柜的行为予以理解和关怀。不同于社会伦理法规冰冷的道德评判,斯炯等人始终对吴掌柜充满善意与同情,在自身难保的时候给他食物和盐。通过饥饿,他们更加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与意义,坚定了生存的意志。在他们朴素的世界观中,一切生灵皆可敬,如尼采所说的那样,即便在最艰难最异样的问题上也要肯定生命。在机村人眼里,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他们以坚硬而朴实的生命质地发出对慈爱、宽容和悲悯的人情复归之渴望。阿来通过书写小人物生存的黯淡与艰难,对比机村人与外来人吴掌柜对待饥饿困境的不同行为态度,凸显了边缘藏族人对生命的敬畏和温情的执着坚守,影射出他们顽强坚韧的民间生存策略。
三、现代性反思:消费主义浪潮下的“机村”变迁
消费主义浪潮下物质至上的金钱名利观念在中国的涌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消费主义这一概念萌生于20 世纪初期的美国,是消费形式的异化在消费社会里表现出来的一种消费景观,主要表现为人们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并将高档甚至奢靡的消费作为人生追求和生存价值的心理观念。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过度追求物质、虚荣好胜、攀比、无节制消费、猎奇心理行为等代替了物质仅作生存之需的一般实用传统,边地世代延续的任性之美在现代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日渐异化。阿来通过对物质狂欢图景的刻画,对“现代性”所蕴含的现代化对本土精神文化所造成的侵蚀进行了理智的批评与反思。
《蘑菇圈》被纳入阿来“山珍三部曲”之列,既是山珍,定会成为消费主义盛行时代的特别物产,也注定要成为一种带有符号效应的超出其自然属性与实用价值的奇珍异产。早先,机村人把一切菌类都称作蘑菇,后来人们开始把没有毒的蘑菇进行分门别类,羊肚菌成了机村人知道准确命名的蘑菇。学会分门别类对蘑菇命名是实用理性观念的开始。但那时的机村人还没有明码标价的买卖观念,蘑菇大值钱,人们为蘑菇疯狂的时代是毫无预兆地来临的。阿来写道:“不是所有蘑菇都值钱了。而是阿妈斯炯蘑菇圈里长出的那种蘑菇。它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茸。”原来五毛钱一公斤的松茸突然涨到三四十块,那是因为叫松茸的蘑菇比其他蘑菇口感更好或更有营养价值吗?显然不是,是因为消费者赋予了它“松茸”这个被标签化和符号化的名字,如唐小祥在《阿来〈蘑菇圈〉的三重象征意蕴》 说的:“阿妈斯炯的蘑菇圈被建构成了一个差异性符号,使它处于在消费者看来更高的等级序列,而消费者购买这种处于更高等级序列的松茸,也就确证了自身比其他消费者处于更高的阶层和等级。”消费本是人维持生存、延续生命和自我实现的生活需求,松茸涨价却是因为消费者对他者或边缘生活、文化、饮食的猎奇心态所致。西藏绝不是一个形容词。相反,边缘、藏地、少数民族等概念在消费世界中是位于一般日常生活之外的奇观异景,是被想象,被形容为某种标签与代码的虚无,从而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它本来的模样。机村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被发掘出来的。收购松茸的商人一批批涌进来,他们等不及斯炯的蘑菇在雨后长出来,商人告诉斯炯要赶到省城最早的飞机飞到北京,再转飞日本,一天的时间里这些蘑菇就将出现在东京考究的餐桌上。改革开放信息交流通畅了,交通建设发达了,机村人也开始像商人那样对松茸趋之若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和人性的变化也随之而来。
斯炯不心疼钱被别人赚完,只担忧山上的蘑菇将要灭绝。为防止被同村人跟踪,斯炯只敢在天黑后上山看蘑菇圈。人人都在觊觎他人的财富,人人都渴望得到更多的金钱。当斯炯用蘑菇圈换钱时,机村人嫉妒、酸腐、仇视的病态心理就立刻暴露无遗。本该脱俗豁达、一心向佛的和尚也打起了发财致富的主意,他们借用胆巴的权势为寺庙生财,以封山育林的名义将寺庙周围的松茸占为己有,直言没有生财的办法和生财的办法太少都不行。佛教的神圣性在金钱面前世俗化和物质化,事实上那是人类信仰与敬畏之心崩塌的征兆。丹雅的到来更是毁灭了机村最后的神秘,她狡黠地盯上了符码化的市场消费模式,不择手段地在斯炯身上安装了GPS,偷窥到蘑菇圈的位置,且理直气壮地说那样做是为了很多很多的钱。她想投机取巧地将自己的蘑菇包装成阿妈斯炯的野生松茸,从而去各地城市捞取大钱。无论是机村人的觊觎和跟踪,还是丹雅输出虚假商品的行为都表明个人主义和金钱主义至上的名利观念破坏了和谐、淳朴的机村民风,人对自然与道德的认知在利益驱动下渐趋浮躁和肤浅。
斯炯试图在临死前把儿子胆巴介绍给蘑菇,胆巴说:“我不会用耙子去把那些还没有长成的蘑菇都耙出来。以至把菌丝都弄破了坏了……我也不会去山上盗伐森林,让蘑菇圈失去阴凉,让雨水冲走了蘑菇成长的肥沃黑土。”但机村不再是那个依靠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组成的乡土社会,胆巴不再像祖祖辈辈那样在山里与花草为邻,他的官越做越大,离蘑菇圈和原始家园越来越远,胆巴的女儿更是从小立志要去国外念书。蘑菇圈的守护人的断代是机村原生态文化断层的象征,亦是人性变异、家园变迁的隐喻。现代性观念给机村注入了新的生活观念,也改变了机村人的发展轨迹,但是阿来却发出了灵魂拷问:“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阿来对现代性的态度是谨慎的,他从小处着手反映时代变迁下现代物质文明腐蚀人性的弊端,通过书写斯炯对自然家园与善良的坚守来呼唤真善美,试图救赎被物欲覆盖了的人性和破败不堪的文明家园,实现对现代理性实用思维的反思与反叛。
《蘑菇圈》展露了作者对逐渐衰落的诗意自然与文化生态的眷恋,面对不断被解构的自然诗性,作者试图通过重构文化记忆来呼唤人们谨慎对待权力话语思想武器。不过,阿来没有凭着感性情怀批判改变机村的外来力量,而是在冷静而理智的心态下饱含着深情去描摹人性的淳朴、善意,缅怀充满神性的自然家园。其次,《蘑菇圈》赞扬了机村人顽强的生存经验与朴实的生命观念,在饥荒年代,机村人以坚韧的生存欲望和温情互助共渡生存浩劫,呈现出一种艰难但不乏诗意的民间智慧与生存哲学。最后,阿来借“蘑菇圈”进行机村变迁的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所蕴含的物质富有、个人主义等观念改变了人性的真善美,人们在利益驱动下相互觊觎、嫉妒和猜忌,人对自然与道德的认知渐趋浮躁和肤浅,面对消费主义浪潮对人性的侵蚀,阿来表达出深沉的忧虑。同时,他在引导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在经济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里既可以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同时又能保持家园的完整和精神的富足?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