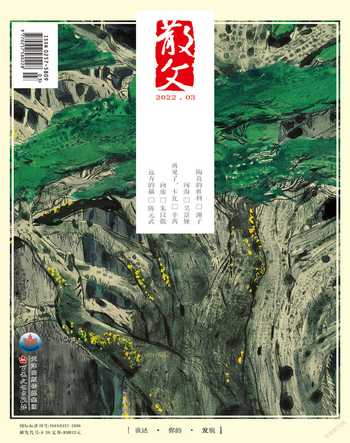再见了,卡瓦
辛茜
卡瓦死了,他的死来得太过突然。
卡瓦是一位藏族青年,生活在青海湖南岸江西沟乡大仓村。走出家门,穿过村人简陋的房舍,沿着冬天黄草夏天绿茵的小路向北,就来到了青海湖边。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湖水,和大海一样宽广明亮的天空,听渔鸥、鸬鹚、斑头雁不停鸣叫。
金色的马先蒿在阳光下闪烁,夏季的傍晚如此亲切,卡瓦的心脏宛如湖水在轻轻颤动。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正摆动着翅膀,在金色的光线下飞舞。他钟情于这片湖水,忘不了夏日晴空下,湖水的娇艳明朗带给他的兴奋与欢乐,也忘不了冬天银灰的、迷雾一样的湖面,让他感到的寂寞与孤独。
卡瓦原名娘吉本,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少语系。他喜欢写诗、写散文、写童话,喜欢作家托尔斯泰、黑塞、加缪、毛姆、马尔克斯、王尔德,喜欢留言博客,渴望每一种擦肩而过的缘分,更期待爱情降临。卡瓦这个笔名是他给自己起的,藏语意为“雪”。因为他出生的那天,山沟里下了一场大雪。
卡瓦的诗《我不是罪人》获得过第二届“岗尖梅朵杯”全国藏族大学生新创诗歌大奖。卡瓦的散文《假如我死去了》《我的憧憬》《回乡笔记》,文字优美而悲伤。2014年,卡瓦与朋友拍摄完成了微型纪录片《雅砻江边的孩子》。同年,又出版了童话绘本《飞蛾》。他心地善良,敏感易伤悲。他相信,爱会改变一切。
他曾梦见一个春天,黄昏的太阳刚要落山,他牵着爱人的手,在大西洋最西边的海岸奔跑。他的幸福,如海浪般拍打着海岸线。他曾梦见有一个冬天,白雪飘落,村子里的人早已沉沉入睡,他不出一丝声音地哭泣,然后静静离去。
可是,卡瓦真的死了,死得悄无声息。那一天,青海湖的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没有拍打着云朵的边襟,也没有流淌出金汁般的酥油。那场景历历在目,叫人心碎。人们簇拥在他早已冰凉的遗体旁,惆怅,无助,悲伤……
土地是这样的沉重,青海湖的美艳、沉寂、荒凉,让他学会了独自承受。他留恋大地上诗意栖居的人们,也向往那些离开家乡、四处流浪的人。为了父母的期待,他曾离家追逐远方。可最终,他还是回来了。伴着秋日的黎明,无尽的憧憬、忧伤与乡愁,他与村民一起收割,一起喝青稞酒,一起唱老掉牙的牧歌。
除了放牧、写作、画画,卡瓦还是一位保护青海湖裸鲤的志愿者。他读过七百年前一位女作家的书,那本书里写满了青海湖,写满了女作家对青海湖的一片深情。他觉得自己是青海湖人,从小在青海湖边长大,保护青海湖是分内的事,所谓“分内”,就是他应该做的。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骨子里有着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性。
当然,他也很喜欢放牧。如果可以,他宁愿选择和父母一样的游牧生活,在草原上娶妻,生子,慢慢老去。
夜深了,卡瓦还在写诗。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在漆黑的夜的脸颊上,写在寒冷的风的翅膀上:
心的翅膀伸展到天空尽头,
天边的暴风却猛烈地刮着,
在岸边形只影单地站立着,
手高高地举起示意着分别,
有一天我不再回来的时候,
在此岸边永远地沉沉睡去,
让血与肉化作天然的肥料,
献于花朵草木滋生的养分。
8月的一个周末,我来到青海湖畔大仓村。多杰扎西帮我找到了卡瓦的家,他们是远亲,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卡瓦的父亲和母亲都在,这不免让我有些紧张,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对失去儿子的老人。
落座后,多杰与卡瓦的父亲在轻声交谈,我观察着屋内的陈设。这是一个普通的藏人之家,没有过多的装饰。温柔的奶香中,阳光洒满连着灶台的大炕,灶膛里跳动着火焰。雾气蒸腾,我看见穿着红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卡瓦,悄无声息地穿过长长的阳台,走进屋子,面对墙柜里擦得亮闪闪的碗盏,舒舒服服地坐在我端坐的这张沙发上,与父母交谈。
卡瓦的父亲知道我为卡瓦而来。他目光凝重,没有我想象中的悲切神情。他用藏语平静地诉说着八岁开始上学,聪慧、善良、腼腆的儿子;假期里揣着一包青稞炒面、一壶热水,把羊群赶到湖边,一边照看,一边趴在草滩上写作业的儿子;长大后,成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的儿子。以及再后来,共和县政府对他们家每年一次的探望。除此,他再无多言。
卡瓦的母亲是勤劳的女人,身着紫色藏装,体态健硕,长发浓密,黑红的圆脸饱经风霜。她为我们烧好奶茶、端上馍馍,不动声色地打量我。我很希望她能坐下来和我聊聊,可她却一刻不停地忙活,来来回回走动。不一会儿,她一声不响地端来一碗饺子。先给了我,接着又端来一碗给了多杰扎西。最后,依然十分恭敬地用双手端给了卡瓦的父亲。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打破沉寂。我们一边安静地吃,一边想着各自的心事。一位中等个头、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是卡瓦的哥哥,会说汉话,却也沉默着。我端详着他,情不自禁地对他说,卡瓦和你长得很像,不过他比你长得高,好像比你更加强壮。他听了一怔,露出一丝微笑。过了一会儿,一个眉眼十分俊俏、眼睛又黑又亮的小伙子走进来,看了看我,又出去了。他是卡瓦姐姐的儿子,身后跟着一个调皮的男孩,也是卡瓦姐姐的儿子。卡瓦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家中老四。
饭后,我提出为卡瓦的父母亲拍照。卡瓦的母亲颔首答应,快步走进卧室,拿出来两顶礼帽。一顶给了卡瓦的父亲,一顶端端正正地戴在自己头上。随后,我被邀请到卡瓦住过的屋子。屋子里的陈设原封未动,如卡瓦生前一样,电视柜上有他的兩张照片。一张是在雪山下,另一张在青海湖边。照片上的卡瓦,凝目注视,心无旁骛。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他的毕业证书、获奖证书、诗集、童话绘本《飞蛾》。原来,在我吃饺子的时候,卡瓦的母亲和哥哥,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
有人说,青海湖是大地上的一滴眼泪。有人说,青海湖的水下是鱼,风上是鹰。鹰是另一个世界的居民,灵魂部落的首领;鱼是湖中精灵,主宰着环湖流域芸芸众生的命运。而卡瓦,是草原的天使,牧人的英雄,父母心头的肉,哥哥姐姐永远的遗恨和伤痛。
一群群斑头雁掠过青海湖上空,一匹又一匹赤红色的马像流浪的歌手,在草原上徘徊,相互问候。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青海湖唯一的水生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青海湖裸鲤,民间称作湟鱼的,原来竟也是有鳞的,只因青海湖流域海拔越来越高,湖水越来越咸,营养越来越少,它们有鳞的身体无法适应严酷的生存条件,才忍痛褪鳞,以增厚皮下脂肪,抵御寒冷。它们在湖水中艰难觅食,与清洁的滩地、瘦弱的芦苇、低矮密集的苔草、成千上万的候鸟,构成纯粹简单、强大又无比脆弱的生态链,维系着雄居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巨大湖泊水体的高原湿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捕鱼者在青海湖畔扎下的帐篷白茫茫一片。疯狂的捕捞,让裸鲤数量由1958年总量三十二万吨,下降到两千七百多吨,那鱼翔浅底、万鸟沸腾的景象不复重见。之后,政府虽连续四十年封湖育鱼、严厉打击、禁止捕捞,但因低温干燥,营养贫乏,加之裸鲤本就生长缓慢,青海湖裸鲤资源恢复缓慢。
2015年6月26日晚上七点半,两名鱼贩子正在大仓村湖岸偷捕青海湖裸鲤。卡瓦和村里的四個年轻人闻讯迅速赶到湖边。看到他们匆匆赶来,狡猾的鱼贩子急忙把夜里布下的渔网投入湖中,面对卡瓦的指责劝诫,拒不承认。卡瓦又气又急,为了当面取证,更为了阻止他们再次偷捕,毫不犹豫地独自向湖中走去,准备拆卸渔网。
卡瓦下了水,岸上的其他几个人顿觉心神不安,刚要劝他赶快上来。没想到,话还没说出口,往湖里走了不到二十米的卡瓦就陷入了湖水。
同去的四个年轻人和两名鱼贩立即下水施救。可是谁都不会游泳,他们找不到他。从卡瓦下水到陷入湖中,整个过程仅一分钟,没有挣扎,没有声响,施了魔法般的湖水,就这样让一个活生生的,只有二十六岁,还来不及与心上人见面的年轻人消失了。
夜深了,6月的青海湖气温骤降,冰冷的空气无奈地咀嚼着苦涩的湖水。只有受惊的几只普氏原羚窃窃私语,忧郁的音调格外凄凉。
许多人赶来,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捧着松香。为卡瓦年轻的生命点燃酥油灯,祭献食品,诵经超度……
如果生命有颜色,卡瓦应该是蓝色的。他为湖水而生,又消融于湖水。像凡高的《星空》,深邃,绚丽。如果生命是音乐,卡瓦应该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激越,灿烂,闪耀着浪漫与激情。
一年又一年过去,大仓村的村民可能已经忘记,往年这会儿,卡瓦正站在湖岸,面对湖水凝神静思,让欢悦的情绪溢满心房。相邻的莫热村是卡瓦母亲的娘家,我赶到莫热村去见卡瓦的舅舅,村里正举行仪式,祭拜藏族人的水神。山坡上桑烟袅袅,岩石上挂满水神雕像,清泉自山间涌出,两边开满了花。
卡瓦的舅舅沉浸在神秘的气氛中,似乎淡忘了这个曾经给予家族荣誉的亲外甥,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想不起来。
午后的草原寂静无声,宽阔的原野在白云下凝固不动,卡瓦的父亲和哥哥带着我来到他遇难的地方。
湖水上涨,卡瓦下水的地方离湖岸又远了二十多米。我默默肃立,心中怅然。古老的湖水与8月的蓝天一样缥缈不定,不可逆料。湖水在风中激荡,勾起了我压抑的悲伤。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莫名的恐惧,恰似心叶颤动,危立于悬崖。卡瓦是一个最接近自然的人,也是最坚强的人,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融入了一场几乎没有人看见的巅峰决战,令盗猎者望而生畏。
草原静谧,静谧得令人窒息,又无所依傍。我踮起脚尖,和卡瓦的哥哥一起,把我带来的哈达举过头顶,系在石碑上。那石碑素朴简约,只镌刻着一行字:
您无畏的精神永存于我们心中
浪花层出不穷地涌现,湖水在天边曼舞,我一步一回头。卡瓦的呼吸就荡漾在湖水里。微风中,蒿草弯腰俯视苍莽大地,起起伏伏。阳光不再灼热,远望中,金色的马先蒿、紫色的野葱排列成行,头戴金冠,身披如意,将一座石碑、一个草垛般的白塔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安放在看得见湖水、听得见涛声、嗅得到湖水气息的沙地上。
再见了,卡瓦。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