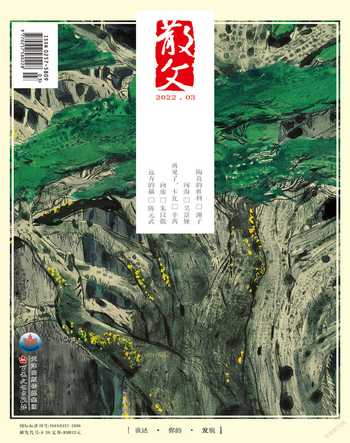时光回响
杜阳林
记忆与钩沉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宗璞在九十岁生日到来前,为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画上了最后的句号。此时,距离她开笔书写这部小说,已过去了三十二年。
在小说最后一卷《北归记》的后记中,宗璞借用父亲冯友兰的一句话,对她所经历与书写的年代,还有伴随她多年的书中人物作了告别: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从1985年开始写作第一卷《南渡记》以后,宗璞先后经历了丧父、丧夫,还有几场大病的打击。视网膜数次脱落,更使她双目几近失明,但她还是坚持写作,即便只能口述,也坚持将小说完成。
宗璞执拗地溯源往昔,是因为她不愿遗忘和背弃历史。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九岁的宗璞还是一个跟在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父亲身后的小女孩。整部小说正是从她童年记忆中的北平开始,此后的南渡、东藏、西征、北归,贯穿整个全面抗战的叙述,是关于那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经历与思考。
西南联大是“学术抗战”的一座丰碑,在四川成都,美丽宁静的华西坝,被誉为抗战期间中国大后方的又一所“西南联大”。顺着水流的方向,粼粼波纹,还有一些文化精英与高校师生,在长江边城留下了深深的足印。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生命因水而兴,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明发祥地,都离不开江河的孕养。宜宾,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热闹而繁荣,在历史上极负盛名。
古往今来,因为一江横贯,水陆通达,宜宾持有开放包容的特质。中原先进的文化与技术,随着人员和经济的交流,沿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在与僰文化的融合中,产生了独具特色的“长江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苏辙到了宜宾,亦是十分感慨:“江流日益深,民语渐已变。岸阔山尽平,连峰远非汉。”江帆远影、码头会馆、民族融合、道佛合一等等繁荣的人文景象,在这方舞台上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军肆虐,铁蹄凶残,大好河山遭受重创,无辜百姓流离失所,四下迁徙。在逃难的人流中,有学界精英,有高校师生,他们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只为寻找一块能放下平静书桌的净土。最终,他们来到宜宾李庄和江安县,在这里教学育人,钻研学术,勤奋创作,演出话剧,将中华民族的一线文脉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历史选择了长江边城,长江边城也创造了历史。地处大西南一隅,在连天战火中,为保存中华文化,边城远镇的江畔民众,做出了令人惊叹的巨大努力。
这是一场时间与空间的伟大相遇,如同彗星與木星交会的刹那,出现璀璨景象,在其后的岁月中,依然不断释放着独特的光芒。距离抗战已过数十年,走上这片土地,仍能见到当初痕迹。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屋、桌椅、学生作业、大师批阅……勤勉的先辈,伏身于一盏灯火摇曳的油灯前,书写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与依恋。斗转星移,时间如水,当我们来到同一个地方,共享同一个空间,隔着时间的距离,依然能感受这份激荡的历史回响。
中国文化精英与长江边城的相遇,是抗战那段血色斑驳的日子中一抹温暖的亮色。如今,走上多情的川南大地,那些过往的人文记忆历历在目,依旧激动人心。
人们需要认真回首与凝望历史,虽然那些早已湮没于岁月风烟的旧迹已然孱弱,但不晓过往,哪知今夕之福来之不易?倘若一个人不知自己的来处,一个国家被生生切断了历史,面对的只是空白与迷雾,就失去了伫立天地的根基。我们需要一次次叩问灵魂,叩访历史的记忆,去阅读和聆听,去了解和察知。
江安国立剧专因种种原因,百分之九十的建筑都被拆除,目前保留的仅仅是当年的门庭。2017年,江安通过了恢复国立剧专的决议,目前,旧址修复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随着国立剧专旧址恢复,它将被打造为中国戏剧艺术博物馆,人们也会从中找回更多失落的记忆,知晓风云突变的岁月中,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留下了多少深刻的精神印迹。
可喜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他们或在物质世界修复旧物,或在精神领域书写传承,复兴话剧的因子。这也许是面对历史风云最深的领悟与慈悲。未来可期,不同的笔触、不同的声音,一次次回望与驻足,必将孕育更多书写的可能。
那些学界精英顺江来到宜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特定事件,为宜宾留下了文化脉络。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交织,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无论是宗璞的《野葫芦引》,还是汪曾祺的散文《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都以“西南联大”为记忆入口,书写了荡气回肠的“那时故事”。与之相比,同时期发生的宜宾抗战历史,也具有探究和钻研的重要价值。
沉睡与唤醒
即便风化成沙,往昔历历,也是抹不去岁月的记忆,却有人持了骄狂的妄念,以为凭借霸道和王权,可以让历史臣服。公元前213年和212年,史无前例的始皇帝做了一件荒唐事:焚书坑儒。嬴政以为焚毁了书籍,坑杀了儒生,就能堵住悠悠之口,令天下臣服。
文化与知识,像是冻土中的种子,即使被掩埋、遭践踏,亦只是暂时的,只待春风吹拂,一个小小的契机,就能复苏记忆,破土发芽。无论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连天炮火,还是秦始皇的如山铁令,都没能将文化赶尽杀绝,文化所蕴含的格外强大的力量,形成了让人无法忽视的文明记忆,影响着社会和人类的进程。
炎黄子孙的历史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明灭起伏,打下了鲜明的“东方印记”。中国人在心理层面形成的时间体验,主要是将自然的时序变化作为人情感情绪的表征。《诗经·采薇》“昔我往矣”之叹,《麦秀》《黍离》之悲,无论涉及个体还是家国,均是将原本自然性的时间内化成了感性的心理时间。
明末清初的张岱写《西湖梦寻》,对杭州一带重要的山水景色、佛教寺院、先贤祭祠等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把杭州的古今展现在读者面前。为何他要频频回望,在文字中编织出一重虚拟的空间?也许,张岱是在明王朝行将毁灭之际,黯然离开心爱的杭州入山隐居,然而隐居只能让肉身安顿,无法令精神休歇,他无休无止地怀念着昔日吟风弄月、徜徉山水的生活,而这些目下已成为再也无法触及的幸福体验。可恨此生漫漫,他还要经受人世的风霜和挫磨,苦挨接下来的日月。如果没有写作来作为慰藉,他该如何直面人生巨大的空洞?
是对故梦的寻找,映照了现实的残败,过去与当下交织,在一次次朝着西湖方向的深情张望中,渐渐催生出了张岱记忆的激越。
《西湖梦寻》是一首千回百转的曲子,它的每个音符都跳跃着轻快,但听懂的人却不由得泪流满面;是闪闪烁烁的西湖碧波,阳光折射出点点光亮,鱼儿遨游,水草繁茂,记忆逆着水流,也逆着时间,来到了最初的光阴,最想让时间停留不动的从前。就像闻一多所说,时间为经,空间是纬,织锦织缎,文字营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张岱一次次溯游,一次次回眸,让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在此处歇息休憩,平定从容。
当张岱醉在西湖的旧梦中,“只愿长睡不愿醒”时,另一个清人沈复,大概余生都会凭借对“沧浪亭边的芸娘”的思念,才能抵挡人世汹涌的潮汐,残酷的浪涛,让遗憾和孤单,在对往事的不断回眸中,化育出一丝丝可回味的甜。
昔日种种,那些支离琐碎的生活细节,如今竟如梦似幻,即便平凡庸常,也都饱蘸着深情与眷恋。烟火人生之美,如露如电,瞬息破灭,幸好沈复还能从记忆中翻检出那些明明灭灭。
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倒金樽,浇洲渚千年芳草。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沈复的悲叹,是时间无法逆流成河的憾恨,憾恨深切,历数百年依旧动人心弦。
为什么沈复丧妻的痛楚,能引发后人大面积的共鸣呢?因为人生从来就有七情六欲,无论性别、种族、年龄,情绪都是共通的,欢喜时大笑,悲伤时落泪,即使并不具备“丧妻”的经历,读者也能从沈复的文字中,触摸到这一份真实的凄楚哀伤。以绵绵柔情,书写往昔沧浪亭边点滴的沈复,在他与芸娘的往事中沉浮辗转,靠着文字回溯温暖往昔,由此才打动了大家的心。
时间能造就历史,也是人们书之不尽的文学母题。毕竟没有谁,能逃过时间的恩赐与诅咒。在它面前,贫贱也好,富贵也罢,一切都能被抹平等差,也能被长久收藏。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