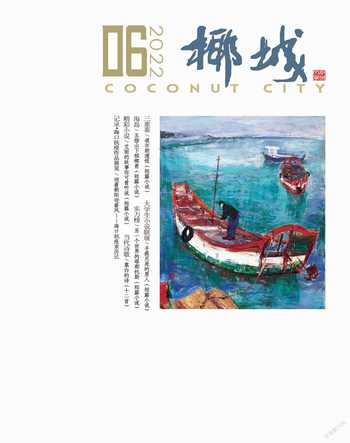道尔朗遗恨(短篇小说)
李洋洋
清晨的露水从草尖滑落,滴在安吉的眉眼之上,将她唤醒。焦灼的太阳匆忙地上班,穿衣服的工夫,便从东山爬到了当空。已经有人来公园晨练了,他们一圈一圈地绕着安吉奔走,时而投来疑惑的眼神,时而两两密谈,猜度着昨夜这里的境况。
他妈的,把老娘一个人丢在这里。龟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安吉骂了一句。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精致的南方小镇,只有安吉对草木如此亲切。她可以在蓝天白云下抚草放声歌唱,也可以月黑风高时抱木酣畅而眠,睡在床上反而是不舒服的,劣质的木板一翻身便咯吱作响,舍友的手机里矫揉造作的男明星整夜发嗲地吟唱,还有床底的湿气、空气中的霉味,这一切都让她不习惯。
八点整,辅导员就打来了电话,催她交学费。
去你的,一分钟都等不了吗?
安吉同学啊,你不能这么说话的,这一学年都快要结束了,整个学院就你一个人没有交学费了。
你教我啥了我给你交学费?你是教我骑马了还是教我挤奶了啊!
辅导员默不作声,电话里传来办公室嘈杂的声音,知识分子大多受不了如此粗糙的话,但其实做着比这更恶心的事儿。
反正老娘已经把学费花了,有本事你们就开了我吧,安吉把电话挂了。
她知道不论自己做出多么出格的事情,学校都做不到把她开了。她没什么事则罢了,但凡有什么事,上头自有人出来护着她,家里上面有老熟人,这是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留给她最后的庇佑,也是她心灵深处的一方黑洞。
安吉扎了一头小辫儿,将眼睛画得乌黑,牛仔裤上的洞是自己掏的,独一无二的式样,皮鞋上面的泥和尘土,似乎与利落的着装不太搭。没有关系,不会有人敢对安吉的皮鞋指指点点,即便有,她也不在乎。如此收拾一番,倒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像她这样的人,每天不就是瞎游逛吗?
走在校园的马路上,一排排的梧桐树伫立两旁,为这所校园添了一份庄严。青砖白瓦的古建筑,是学校历史的见证者,歷史是不会骗人的。学生或背着书包,或提着袋子,形色匆匆地往教室赶,往图书馆赶,他们都在为明天的光亮而努力,成功有人分享,失败有人鼓励。可是安吉没有,所以安吉也不必顺着人潮的方向攒动。
安吉的身世,就像祁连山的一处秘境。母亲去世后,这处秘境变得更加地鲜为人知。有人说是因为妈妈进山放牧时被人性侵,但她妈妈不承认。又有人说是和草原游客发生了一夜情,终究也没有实际证据。说是有人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人说,草原上的裕固族儿女终究不像城市乡村的人那样爱嚼舌根,人人潇洒放牧,过的大多是离群索居的生活。
小时候,安吉家的帐篷坐落在一条小河的尽头,小河从天而来,融化了祁连山无数个冬天的积雪,清凉甘冽,哺育了小安吉。小河和繁茂的野草野花,成群的牛羊马匹,陪伴了安吉的整个童年。那个时候,她尚不知道人的意义。但听妈妈说,与人在一起,不如与成群的牛羊在一起,与潺潺小溪在一起,与野草野花在一起。所以安吉的玩伴,除了母亲安祁,就是家里的那匹鬃马,她们给它取名叫做毛毛。
盛夏的骄阳透过山顶的积雪,将更耀眼的阳光投射在安吉家的帐篷上,母女俩坐在河边,翻找着青青小草下面湿润的泥土,安吉堆砌城堡,妈妈捏小人和骏马,这就是安吉关于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妈妈说,那两个泥人,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安吉,马自然而然便是毛毛了。
妈妈妈妈,你把安吉捏得跟你一样高了,安吉是有小辫儿的,为什么你捏的安吉没有小辫儿呢,你快点给安吉捏一个小辫儿嘛。城堡游戏每一次都会在这里画上句号,妈妈便起身给牛挤奶去了。
一座座城堡在安吉和妈妈的手里完工,而后又被河水冲走,在城堡毁灭的每一个瞬间,安吉的童年便消磨了。妈妈带她下山,在草原的边际租了一家小店,迎宾送客,供安吉上学。
安吉从学校超市拿了一瓶饮料,习惯性地不付账走了出去。售货员的眼睛一个劲地随着安吉的脚步往外瞪,鼻孔被愤怒的血管撑大,直到安吉消失在她的视线尽头,才将整张脸收了回来。真是想不通,这学生怎么这样,父母知道她在外面干些什么事嘛,真给家里人丢脸……
夕阳刚下,还有余光将天空点亮,周边的居民都来学校跑步、打球,或者遛狗。安吉不齿,狗有什么好遛的,有本事骑马遛几圈。城里的人们总是温文尔雅的,连运动都带着自欺欺人的性质。一只足球从天而降,落在安吉的脚下,安吉向后撤了一步,一脚将球踢到了学校院墙外面,院墙外的马路上有人无故受到痛击,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安吉听到了,那人骂她有病,但她不生气,破坏的行为让她感到舒心,这种很轻易就引起别人愤怒的能力,让她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高粱熟来红满天啊,九儿我送你去远方,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安吉扯着嗓子吼了几声,做出策马的姿势,离开了。
去你妈的,做完了就做完了,出去吃什么饭,你当老娘真拿你当个玩意儿啊!昨夜一起狂欢的小伙子,不知道怎么搞到了安吉的电话,约她出去吃饭,被安吉凶了几句。
在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里,安吉变得随意和放荡。对于与她发生过关系的一些男人,她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记不清具体的样貌,只能在倏忽之间,想起那些刺鼻的香水味或者口臭,总之男人都是臭的。她不喜欢男人,从骨子里,她厌恶每一个男人,当她对人和性有了初步感知的时候,她就明白了,如果不是有一个男人的出现,她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她憎恶那个让她出世的男人,她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她隐隐约约地预料到,这个男人现在就在她的身边,正在为她现在所做的一切感到丢脸、愤恨。不然呢,妈妈怎么可能在三千里外的陌生城市认识一个有权有势的“上面”的人呢?除非这个人过去与她发生过点什么,并且这份交情足以驱使他躲在一旁默默地保护安吉,五脏六腑同时涌现出一个词语——父亲。这让安吉感到恶心,她自言自语地我呸、我呸、我呸,呸了无数声,才消了心中的恶气。
要怎么找出这个人呢?妈妈说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现在看来已经没有意义了。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真善美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一个有良心的犯罪者来说,受害者过得越好,他心里的罪恶感便越轻,久而久之,他便可以在心灵深处偏安一隅,达到自我原谅。这不是安吉想要的,她断定这个人还存有良心,否则妈妈不会让他护着自己,他一定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掌握着一切,当某一天,心灵的遮羞布被扯下,他便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F13AC511-EA07-4312-A0D6-A7B2566905FF
祁连山的夏天是繁茂的,每一株小草都在用力地生长,叶子连接着叶子,枝丫拥抱着枝丫,簇成一团,不给黄土留下一丝缝隙。山花烂漫,挣扎在严丝合缝的绿网中,艰难地绽放。山顶的积雪仍然残留,蒸发时水汽氤氲,和流云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天上人间、腾云驾雾的感觉。
远道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有自驾来的,有飞机火车载来的,不远万里,都是为了一睹祁连山巍峨的风光和裕固族独特的风土人情。行进和离开的时候,安祁酒馆都是他们小憩的最佳场所。
安祁每天为游客们服务,简单的餐食地道且美味,有时候是手抓羊肉、红烧驴肉,有时候就是一碗蘑菇汤面片……有限的厨艺一次次受到客人的赞扬,再加上自制的酸奶和米酒,怎么说都是一番自然的饕餮盛宴。
安吉在皇城镇的小学上学,每天背着书包,紧追慢赶地来去。好几次竟然不听劝阻,将毛毛骑到了学校,一路上的水泥地坪,磨穿了好幾副马掌。小安吉是非常听话和能干的,妈妈经常这么夸她。从九岁开始,她就负责将妈妈做好的饭菜端到客人的面前,有时候盘子比整个人都大,头重脚轻的她摇摇晃晃地走到前厅,引得客人忍俊不禁。有时客人会与小安吉开玩笑,小姑娘,会唱裕固族的民歌吗?小安吉总是不答对方,张口就来《裕固族的姑娘就是我》,嗓音未落,热烈的掌声便在梁上波波回旋。
夜深人静的时候,安吉与妈妈一起坐在屋外的楼梯上,夜空中星光点点,激起安祁心中的涟漪。安吉啊,妈妈的一辈子怕是就只能这样了,作为一个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好女孩,而不要像妈妈一样……你要珍惜时间,要洁身自爱,要知错就改,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否则便要赔上一生的光阴去改正……安吉半懂不懂,妈妈拨动着安吉的发丝,在额头上轻轻地吻一下。晚风拂拂而来,夹杂着青草的芬芳,从安祁的每一条皱纹中掠过,摇曳了那些令人神伤的往事。
安吉在一次家长会上的作为,让她第一次对父亲这个名词有了概念。酒馆里的客人进进出出,安祁一时无法抽身,迟迟没有到学校。班主任等得焦急,就把安吉叫到了门外,安吉,你妈妈呢,怎么还不来?安吉不语,沉默了半晌才说可能是因为店里人多。那你爸呢,你爸怎么不来?安吉急了,她硕大的眼睛像一匹受惊的野马,恶狠狠地盯着班主任,我不知道,我没有爸爸,你为什么要提我爸爸……愤怒的安吉飞奔回家,拉着毛毛的缰绳冲进了草原。
她急切地拍打着毛毛,不间断地喊着“驾、驾”,鞭子抽打着无辜的草原和土地,在成片的青草上划出一道道裂痕,青汁浸湿了马鞭,抽打的声音变得愈发壮烈。牛羊马群从安吉的身边走过,她看到羊群中一公一母的追赶,又看到小溪边上,牛妈妈正在用舌头舔着刚出生的牛犊,原来创造一个生命也可以如此简单。安吉一直往深山骑去,似乎是去验证某一些传说,看看深山里究竟有没有牧羊人,看看她是不是来自这里。安吉一遍遍对着山谷呼喊,爸爸,我有爸爸吗?你要是我的爸爸你就给我出来……回音在整个山间荡漾,声音由大变小,却始终只回荡着问题,并没有答案。灵性的毛毛停住了脚步,天已黑,草原上燃起了一团团篝火,像是绿色天际里的点点星光,帐篷外,人们在歌唱,牛马在嚎叫。
安祁站在路口,漫无方向地张望。你干什么去了,你是要急死妈妈吗?
安吉不语,沉默地拉着毛毛向前走去。妈妈从小跟你怎么说的,尊敬师长尊敬师长,你随意顶撞老师,老师还怎么教你……安祁絮絮叨叨地说着,沉默的安吉紧闭双耳,只有毛毛霎时的嗷叫打破深夜的寂静。
安吉不紧不慢,将毛毛拴在了棚下的柱子上,抱着一捆干草扔到了马槽里,用手拨弄着、挥洒着,双手在马嘴间来回,扰了毛毛吃草的兴致方才作罢。
我为什么没有爸爸,我爸呢?
安祁沉默了,冷风呼呼而来,她干裂的皮肤在黑夜里炸出一个口子,血管里流动着回忆的痛楚。两行清泪缓缓而下,她席地而坐,挣扎着,纠结着,撕裂着,痛苦着,是否要在这个黑夜将一切和盘托出。安吉依偎在跟前,等待着有关于她身世的光亮。远方的篝火星星点点,有新燃起的,有刚熄灭的,小草在晚风中徐徐摇动,带动了整个草原,带动了整个山坡。芳草的气息交杂着牛羊的腥气,一阵一阵地吹拂到马棚,在天地间的一阵阵摆动中,很快,黎明来临了。母亲在心底将过往尽数一遍,嘴上却只字未提。
安祁起来了,双手拍打着裤子,将沾染的尘土和干草清理干净。安吉,你没有爸爸,以后不要再提了,是妈妈对不起你。揉了揉眼睛,离开了。
安吉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在这个问题上,她却很识相地戛然而止。她曾在学校与嘲笑她没有爸爸的男生打架,被人扯了头发,她抓了对方的脸。也曾在数个放学后的傍晚,在草原流浪,观看每一个牧羊人的面庞,企图找出些与自己相似的因素。但在妈妈面前,她只字不提。
安吉平平淡淡的日子是在一节英语课上结束的。
老师喊她与另一位同学做关于人生规划的对话,当对方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抛来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时,安吉却在课堂上不急不缓地说出了两个字:渣女。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女生窃窃私语,男生吹起了口哨。
英语老师站在讲台上一动不动,气急败坏地摘下了眼镜,然后又无奈地戴了上去,空洞的眼睛透过反光的眼镜片流露出瘆人的愤怒,死死地盯着安吉看了看,拎着包走出了教室。
正午的斜阳从敞开的教室门里洒了进来,将安吉的半个身子照亮,安吉对着老师远去的背影做了一个鬼脸,舌头裸露在阳光底下,赤红赤红的,很是可怕。
第三天,安吉就收到了学校老师谈话的通知。据说那天英语老师甩门而去之后,就直接冲到了院长办公室,直言这样的学生没办法教了,要求院长开除安吉。全院老师以及保安、保洁,都趴在院长门口,听到门缝里传出一声声渣女。自那以后,安吉就成了全院师生人尽皆知的“理想渣女”。
安吉同学你好,请问你为什么要在英语课堂上顶撞老师?
你说你想当渣女,是发自内心的吗?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F13AC511-EA07-4312-A0D6-A7B2566905FF
安吉也不知道,学校竟然弄了这样大的阵仗,还请了个心理老师。心理老师一张纸一支笔,洋洋洒洒地记着些什么,嘴里吧唧吧唧地说个不停。
是啊,我是发自内心地想成为渣女啊!
你不想吗?
你们都不想吗?
在座的老师们左顾右盼,沉默不语。只见院长一只手转着钢笔,一只手攥成空拳,捂在嘴上咳嗽了几声清嗓子,正襟危坐地准备发言了:安吉同学啊,我院时常开展德育课、心理辅导课,你都没有参加吗?
没用的课我为什么要参加?
院长被怼了个猝不及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许是因为从未见过此等学生的缘故。
我院每学期都会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辅导员会为每一名学生量身定做职业方案,你也没有参加吗?
我不需要别人为我规划,安吉瞪着院长,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本色。
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份职业的呢?作为一名大学生,你要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渣女没有价值吗,你不喜欢吗,没见过吗?老师们使劲地压抑着自己的笑声,但有几位女老师还是没忍住,上面没出来的笑竟然从下面放了个屁。
院长无法抑制心中的怒气,恶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刚准备继续往下说,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教室里先是陷入了一片寂静,而后随着院长迟迟不进来,老师们便开始窃窃私语。安吉依稀闻到空气中高雅的香水味,混着他们的口气,促成一股特殊的人味,令人厌烦。他们说要将她开除,心理老师说这样的学生还留着干吗,简直没救了。
你才没救了,安吉冲心理老师嚷着,刚要站起来,院长便推开门进来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安吉同学啊,你回去吧,知错能改就是好学生,老师们期待你的改正。
安吉起初和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不解,但是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那个人出现了——父亲。安吉跳起来握拳,向桌子砸了下去,一边走一边踢着教室的桌椅,她恨自己,为什么又在心中默念了这个名字。
安吉是在大一11月份接到母亲的病危通知的。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安吉正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在好好学习,在努力地成为一个好学生、好女孩,图书馆里寂静无声,安吉失控地哭了。泪水浸湿了刚刚写满的纸张,浸透了笔迹,在字的周围、符号的周围,延伸出一条条小小的道路,像蚂蚁一样,像河流一样,像祁连山的山丘一样。安吉没有想到,癌细胞却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在母亲的身体里打了一场歼灭战,母亲用生命中最后的顽强等到了安吉的回归。
病房里白色的墙壁和白色的床铺一起,将房间营造出了一层恐怖的气息,只见母亲的全身都插满了管子,绑满了袋子,一个个袋子里盛放的,是从母亲身体里流出来的最后的液体,黄色的尿、红色的血,还有一袋透明的,是它维持着妈妈的最后一缕气息。
安吉跪在床头,轻轻地抚摸着妈妈干枯的手臂,趴在妈妈的肚子上,小声的哭泣,惊醒了沉睡的安祁。
安祁用无力的双手拥抱着安吉,摸了摸安吉的头、安吉的脖子、安吉的手、安吉的屁股,眼前亭亭玉立的少女正是她的女儿。曾经,她也以这样强劲又虚弱的身体迎接她的到来,也曾在这样单调死寂的床铺上将她降生,安吉小時候的一幕幕在她的脑海里放映,十个月走路,一岁说话,她的女儿真的聪明可爱,可是现在……她的手想继续滑落,她想用这样的节奏继续抚摸,她想用最后的力量尽情感知,她不小心掐了安吉一下,几乎是最后的心力,在生与死的边缘,她纠结,是否要带着这个秘密死去。若此,今后安吉将在世上举目无亲,安吉将成为一个孤儿,对,一个十八岁的孤儿,两滴眼泪从眼角挤了出来,浇灌了干涸已久的肌肤,风干后,落成两道白色的印痕,与眉骨相连,与鼻梁交叉,仿佛一道十字架疤痕。是的,这是她的一道疤痕,安吉是她这一生最大的疤痕,她不愿意再去撕扯一边,让干枯的伤痕流出新的鲜血。同时,她不确定安吉的态度怎么办,当安吉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怎么办,又有谁来帮她的女儿抚慰那些心酸的情绪……想到这里,双手便停驻在了安吉的大腿处,然后顺着安吉坚硬粗糙的牛仔裤垂垂而下了,天光在她的眼中逐渐模糊,世界的喧闹霎时化为乌有,安祁用此生最后的余光注视着她的女儿,直到黑夜在她的大脑中降临,直到全世界在她的生命中黯淡下来,她带走了秘密,却不能带走那道疤痕的产出物。
沉寂了,静默了,全世界都凋零了,安吉呐喊着、嘶吼着,不要用被子盖上妈妈的头,她不喜欢蒙着头睡觉……不要用白色的被子盖着她,她不喜欢白色,她不喜欢白色……她的大腿瞬间失去了力量,跪在了病房光滑的地板上,妈妈抚摸过的地方麻木了,每一根神经都艰难地跳动着。她多希望刚刚的疼痛再来一遍,妈妈温暖的手再掐她一遍,眼前一片恍惚,一个声音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旋,安吉,我的小安吉。她想去拉住妈妈的手,却被左邻右床的人拦住了,护士把妈妈推走,一片沉寂的白顿时变得冷漠无情。看着妈妈远去的躯体,安吉隐隐约约地知道,从此,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在流水潺潺的小溪边,甚至在人山人海的世界里,她,安吉,举目无亲。
……
安祁的葬礼很简陋,安吉将妈妈的骨灰埋在了西山处的荒原,那里到处是散墓,接二连三的土堆紧接着,是另一番落寞又热闹的景象。睡在那里,抬头便可看见祁连山山顶的皑皑白雪,向远处瞻望,青青草原上的牛羊也尽收眼底,龙卷风吹来,卷起四周的黄土和干树枝,将它们一起卷向天际,像是灵魂的蜉蝣,又像是人神的别离。
安吉在坟前久跪不起,这是第一次,她跪在这里仰望祁连山,仰望天际。原来人在世间是如此渺小,权富亲情不由己,生命来去也不由己,妈妈已经离去,在这个世间,将再无与她血脉相连的人。不,或许还有一个,安吉瞬间清醒,还有一个,应该还有一个,否则,她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呢?
回到宿舍的安吉像一个独行的探秘者,秘境之下的水帘洞就在眼前:若拨不开,他们两人或许近在咫尺;拨开了,便必须远隔千里。急切的求知欲和假设的恐惧令她心慌,她恨,这么多年来,她忍受的白眼和流言蜚语此刻在她的耳边嗡嗡作响,这个让她来到世界上的男人为何十八年以来对她不闻不问,又为何在此刻出现在她的生命中。不应该的,不应该的,安吉一遍遍地重复着,她狂暴地揉扯着自己的头发,锤击着床板、墙壁,杂乱的响声让她恢复了片刻的宁静,转而又陷入更加焦躁的一团火焰之中。F13AC511-EA07-4312-A0D6-A7B2566905FF
她翻了个身,从床上跳下来,给鞋带绑了一个死结,跑了出去。风声如雷贯耳,雨滴像针尖一样穿越她单薄的衣裳,针针戳心。妈妈的面容在她的眼前摇晃,站在积水面前,安吉的面庞倒映在水中。是的,她与妈妈几乎不像,在基因的表现力度上,从未见过的那个男人却占了一半多,安吉踢裂了水中的自己,从水面上跨越过去,冲向了秘境之门。
朱老师,我来交学费。安吉站在辅导员面前,双手背在身后,向左微微跨了一步。
辅导员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像一坨独立的肥猪肉。他先是用低弱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来了,先坐。然后又操作了一会儿电脑,片刻,方才抬头。
安吉啊,你来交学费了?最近有钱了吗?辅导员一边扶着眼镜,一边盯着安吉看,你坐吧,别紧张。
安吉方才坐在沙发上,虽然安吉来过这间办公室无数次,但今天的空气明显不一样,和善、恬淡。
辅导员从脚下的柜子里拿出来一个纸杯,接了一半冷水一半热水,递给了安吉。你怎么想到今天过来交学费了啊,辅导员翘起了二郎腿,正对着安吉,期末考试的成绩下来了吗,你考得怎么样?
安吉不语,也不看他,若无其事地看着天花板,看着窗外的鸟雀和蝴蝶在草坪里追逐。
你能主动过来交学费,就说明你还是一个好孩子,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过去的事情都可以既往不咎,我们老师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
安吉打断了他的自言自语,学费多少钱?
这个啊,你不知道吗?你的学费有人帮你交过了,所以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哈!
安吉沉默了半晌,秘境的真相逐渐地浮出了水面。安吉喝了一口水,故作镇定地说道:你帮我谢谢他,谢谢你啊朱老师。然后便要起身离开。
辅导员将安吉送到门外,等一下安吉,你与黄校长是什么关系啊,我们这个工作没做好,都没有调查清楚……
安吉回头瞪了辅导员一眼,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一路上,安吉默念着这个名字,黄校长、黄校长、黄校长……
一直以来,安吉认为正对着南门的那一栋楼,是学校最美的地方。两排梧桐徐徐而迎,像守卫边疆的战士,又像盛大节日里红毯两边的奏乐者。楼不高,是只有五层的俄式建筑,人字形的斜角很锋利,没有一点多余的雕饰,暗红色的楼顶斜面,乌青色的墙壁,伫立在烟雨蒙蒙的小城,诉说着多情温柔的江南气质。安吉曾无数次在这里驻足,看红霞斜阳铺陈在墙角,藤蔓有条不紊地向上爬去,与流云野鸟倾心攀谈。树枝上悬挂着的雨滴粒粒分明,随着微风摇曳而下,落在安吉的眼角,冰凉又清冽。安吉揉了揉眼睛,向楼上走去。
每走几步,声控灯便将前路照亮,安吉从没有走过如此光明的道路,她渐渐地将脚步放轻,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攀登,沉稳又有力。脑海中浮现出草原安吉的画面,她拿着马鞭驯服着不知名的野马,用树枝敲打着落伍的山羊,双手握着犄角骑在牛背上,捡起一块石头敲向小白兔的脑门,用弹弓射击来去的飞鸟,一刀砍向公鸡的脖子,与班里的男生在河边打架,暴击他的胸口,拳打脚踢地不饶人,将他的头按在冒热气的牛粪上,再揪着他的耳朵将他放进水里……野马、山羊、老牛,驯服这些笨重的家伙她毫不吃力;兔子、鳥、公鸡,杀死这些小巧的东西她也无一失手。与人对战,她也毫不怯懦。到了,“校长办公室”五个大字展现在安吉的面前。
安吉站在门口,习惯性地跺了跺脚,深吸了一口气,将双手插在裤兜,用脚踹门,一个个脚印在暗红色的门板上展现,脚印向后移动的那一刻,瞬间光亮闪眼,安吉的心跳一下跃到了脸庞之上。
我妈是安祁,安吉盯着眼前这个体面的校长,比对着与自己的相似之处。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乌黑的头顶在阳光下挑现出几根白发,眉毛粗短又稀疏,厚厚的眼镜片遮挡了他眼睛的余光,鼻骨高悬,颧骨凹陷,在脸面上呈现出左右对称的陌生弧度,嘴唇泛紫且干裂,不知进行了多少次仁义道德的说教。
他站了起来,双手麻木地垂放着,眼神呆滞却哑口无言。
祁连山下的安祁,你认识吗?
裕固族的安祁,你知道吗?
他向后撤了两步,将一只手扶在月光稀薄的窗台上,从头颅之上冒出了一点声音,是你吗,你就是?
安吉在沙发上坐下,双手从裤兜换到了衣兜,用冷峻的眼神审讯着屋子里的一切,桌椅、书籍、烟灰缸、茶杯,审讯着他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日子。妈妈去世时的脸庞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窗台后面,她听到妈妈的声音,听到妈妈呼喊着她的名字……关于我,我想听你说一说。
他顺直蹲了下来,将整个身子靠在墙面上,眼球一动不动的。安吉隐隐约约地看到,有几滴水珠在他的眼角打转,映出了自己的模样。他空咽了几口唾液,秘境之上的那一块幕布霎时融化。
安吉听过,道尔朗是裕固族历史上的一种婚俗,女子十五岁到十七岁时可以独住一顶帐篷,与任意男子约会皆不算婚约。
我做的专题便是裕固族婚俗的科考,你妈妈赶着羊群经过,她太美好了,她的两条辫子像是山峦之上的彩带,笑容像云开月明一样让人舒心。她很开朗,主动与我们聊草原生活,道尔朗的故事是我讲给她的,我没有想到,她会回过头来跟我说,我也有自己的帐篷哦!
他捂着双眼哭了出来,泣不成声。我更没有想到,短短一个月,竟然孕育了你。我是真的不知道,科考结束后,我便离开了,我不知道她一个人撑了一辈子……
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吗?安吉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单脚踩在红木茶几上,妈妈的脸庞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明朗,她看到了妈妈的两条麻花辫,她热情洋溢的笑容,在风中策马奔腾……安吉从桌子上跳了下去,一霎那,便将手掌落在了那张丑陋刺眼的老脸上。安吉并不看他,她盯着窗户,盯着红木茶几,盯着夜空中若隐若现的星光,一脚踹了过去,她听到他疼痛的声音,但只是几声叹息,并不嚎叫,也不说话。安吉感到自己的心里一阵抽搐,她的眼光再也捕捉不到妈妈的面庞了,转而闻到外面熟悉的青草香,安吉朝他的下体蹬了一脚,离开了。
今夜星光明亮,安吉长舒了一口气。
我从别人口中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已经不姓黄了,只是偶尔在同学老师那儿听说,关于昨天某人在某医院碰到前校长看前列腺的消息。F13AC511-EA07-4312-A0D6-A7B2566905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