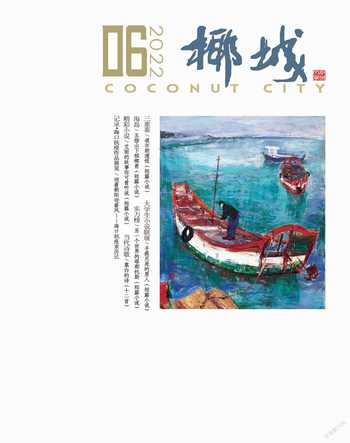另一个世界的塔那托斯(短篇小说)

作者简介:小乙,本名钟志勇,四川洛带客家人。2015年开始文学创作,科幻及现实主义小说散见于《椰城》《湘江文艺》《作品》《青年作家》《小说月报》(原创版)等刊物。
1
大巴车亭很安静,让我想起停止拂动的风。我坐在排椅最边上的位置,就像坐在梦的前面。梦里是暮色深处,夕阳罩着我的视野,迷糊了我的意识。梅子,偏巧在我意识之帘的外面。她隔我两个椅位,拘谨地并拢双腿,望着远处的三峨山。脸庞小而细腻,淡熏妆的眼睛。
梅子的邻居痘痘姐骑着三轮车卖豆花,路过这里,她爱怜地说,梅子,早点回家休息呀。然后将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带出些许警惕。
我如老僧入定,任凭心脏发出金属般的跳动声。持续几天的兴奋,不吃不闭眼,身体充满危机;接下来嗜睡,醒后低迷,焦虑过渡到冷漠。是的,我彻底和拼搏的岁月告别。拼搏就是困于远离性别的车间,守候在注塑机前,执着地聆听狮吼般的啸声。月光在我脚下流淌。拼搏就是西装革履地踩着积雪,推销老板代理的哈希产品。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工地、酒厂、书店,都曾为我开出微薄的工资条。在You+公寓过着群居生活,我们带着自制的柠檬水,观看即将下映的打折影片。荷尔蒙在封闭的空间碰撞。
站亭旁有绿篱。诗是我的盾牌,诗是我的长矛。我像被上帝驱逐的使者,深沉地打量梅子,打量绿篱间的海棠花。荒漠里有诗句,那是我的绿洲。
2
落日渐渐往地平线隐退。暗色里的光,把每扇门染成幽蓝色。嘎吱——所有的门打开。脖子辣辣地痛。每個人都卡我脖子,拎我衣领,把我这只毒蜥蜴扔出去。耳际边不断传过压迫鼓膜的深深沉寂。
昨日的黄昏,梅子同样坐在这张排椅上,望着远方。远方是令人心动的词语。远方,是浪花遇见奔腾,落叶遇见风,或者孤独承受寂静。最后一班大巴停留了半分钟,梅子没上车。我在站亭外站了一会儿,悄然离去。回头,梅子朝我投来一瞥。她眼里的光带着冬的悸动,烙在我的脑海里。继续前行,再次转身,梅子已然消失。
夕阳斜照,在亭子前映出一汪阴影。
现在,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我脸上保持着不可战胜的笑意,决不让灾难有得意的机会。梅子侧过头,定定地注视我。顺着她的目光,我摸一摸脖子,手上有黏湿感,是半干的血迹。请不要卡我脖子。她眨一眨眼,迷人的睫毛闪动。瞳孔里的漩涡,可以融化掉云团状的岩石。梅子收回了目光。
我说,对不起,这不是蜥蜴的血。我是说,你喜欢诗吗?
梅子抿嘴一笑,笑得很克制。她说,大巴车早收班了,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不会打扰你的。我说。我听到自己朗诵的声音:走吧,落叶吹进深谷……(记忆突然混乱,神经错杂)呃,冰上的月光……我们没有失去记忆……路啊路,飘满红罂粟。
好深奥。梅子打断道,你真是有趣。
有些决绝吧。我说,要不换一首《生活的空白》,怎么样?
空白?好颓废。梅子摆摆手,做了个堵耳朵的动作。
我自嘲地笑道,诗在乎的是情感饱满。
梅子没有给予肯定或否定。时间沿着各自的思绪流逝。梅子从肩上滑下提包,放在膝盖上。她从包里掏出纸巾说,记住,不要在女人面前露出你的伤口,哪怕你有无数伤口。
我接过纸巾,拭了拭脖子。
柔软的纸巾,像河面吹来的暖风,摇曳着我意识底部沉睡已久的东西。我应道,不,男人真正的伤口,藏在心里。
好深奥,跟你聊天我挺有压力,但我们骨子里好像有相同的地方。梅子埋下头,我想,我们都不应该坐在这里……对不起,我想静一静,你走吧。
我把翘起的二郎腿互换两下,然后迅速站立,朝街对面走去。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我永远在路上,行色匆匆。告别职业学院的日子,从此分秒必争。在秋天成熟之前,我摘下果实,青色的汁液,在我手心里沸腾,在路人的脸上刻下岁月的深沟。刚走两步,又转身。梅子用眼瞟我说,别扭扭捏捏,是男人,说走就走。
我脖子僵硬,快步走到岔路口。闪进巷道,我躲在拐角的屋檐下。敛气屏息,探出我影子的头,窥望车亭。
十秒钟、半分钟、一分钟、两分钟……梅子左右张望,挎上提包,朝上场口走去。浑浊的街灯笼罩着小镇,梅子向朦胧的迷雾深处走去。
现实从何处开始,梦幻在哪里结束?暗色流动,她的身姿像风浪中的船,来回晃荡,执拗又倔强。我觉出哪里不对劲,脚不听使唤地尾随。死亡是我坚强的证明,死亡让我怯步。几丈开外,我怔住了。
没错,梅子的左腿是瘸的。
我读出她瘸得如此自卑,如此不甘心。世界装了消音器,惆怅在弥漫。我对命运充满愧疚和恨意,多么矛盾的心情啊!
3
古镇的静,静得时光戛然而止。沿街的瓦屋顶是涌动的海浪,闪动着石膏般的光芒。梅子迈着小鹿般的步伐。我如同折翅的麻雀,在假想的电线上折踅。我没有目标地走,如同风没有方向地胡乱吹。
返至北干大道,回到站亭,亭灯把我照成梦境。倦意在俘虏我,黑暗具有了现实性的重量。恍惚中,我看见有人影从街灯下走来。小鹿的步伐声在回响。我像蜷腿的昆虫,闭目合眼,纯然的黑暗倏忽笼罩下来。
竞岗、效率、业绩、考核、训斥。跟时代的比特流竞跑,喘息声在耳畔作响,游移在神经末梢的诗句,吞掉噬人的蚂蚁。没有一个早晨我不期待太阳升起。KTV包厢,迷醉的酒吧。音乐节奏强烈,称兄道弟地呼喊,声音支离破碎。精神的雪山在坍塌、崩溃。甲基苯丙胺点燃虚幻的快乐。摇头、龇牙,卖力拱肩、扭臀。我是被流火击中的枯木,熊熊燃烧,肾上腺激素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我所向披靡,我迷恋快乐,死亡使我怯步。救救我!
强制戒毒中心有白色的房间、白色的墙,白色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我硬着头皮,冲向白光照射下的白墙。我听到绝望在破裂。教官将我提在床板上。压抑、疲惫、拘泥、缓慢、刻板。死亡在寂静地等待。空白,带着我辗转。空白是我的心跳,时间都退到窗外……127C867D-384F-4170-A0EB-028539BCF1A0
跨出白墙,阳光卷土重来。可所有人都视我为有毒的蜥蜴,所有目光都是来福枪,瞄向我荒芜的坟墓。嘎吱——门打开。走吧走吧,每一扇门都装不下你的欲望;走吧走吧,留在这里,谁都没法清静。
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
现在,寂静再次笼罩,意识里是浓得化不开的黑。小鹿的步伐继续迈进,沉默横于其间。有什么在蠢蠢欲动?没有戒断的体瘾反应,心瘾却随时存在,周期无规律,环境和言语一触即发。焦躁、恍惚、激动。我的舌头被秘密之火灼烧,我的神经绷得比钨丝细。
我嚯地弹开眼,撑起身子。
咦,你还在?原来是痘痘姐,她对我说。
一股暖流淌过。对不起,认错人了,我以为……是梅子。
对呀,你们俩怎么一个在这里,一个跑到山边?天不早了,快回家吧。
亭边的海棠花在暗色里模糊了轮廓,我闻到令人不安的芬芳。
4
景观灯把三峨山口映照成空洞的句号。梅子坐在不远处的山坡边,犹如幽暗中的兔子,在静静谛听大自然的声音。接近梅子时,她转头说,不会一直偷偷黏着我吧?我说,没有啊,是你邻居痘痘姐告诉我的。心里像有什么欠着,我就忍不住来了。
梅子支颐下颌,回道,你和我的确有相似的地方。她将自己放倒在杂草丛中,双手垫在后脑,仰视苍穹。略带疑问的侧脸,俨然奇妙的符号。
不会讨厌我待在这里吧?我问。
没有应答,问号轻飘飘的,连同夜风,一点儿一点儿地被吸入大自然。挨次坐下,我眼皮沉重如鉛。时间聚成黏湿透明的冰块,裹住了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一无所有,我开始在无形的深渊挣扎、挣扎、挣扎,罂粟花悄然怒放!莫名焦躁情绪灰暗,极度疲倦极度厌世。蚊蚁振翅萦绕,嗡嗡声不绝于耳,由小变大升级为巨大的轰鸣声。眼中的景象晃荡、扭曲。激动恐慌,渴望肾上腺激素增强获得的冲动和快感……铅一样的沉重把我往下拽,疲惫形成吞噬一切的漩涡……
强光忽地朝我压来。睁开眼,我居然紧贴着梅子,右手搭在她胸前。那对美丽的乳房,在月光下颤动。我的唾液在分泌。枝叶的细碎响声。讨厌,不准看我,不准看我!梅子猛然起身,慌乱地向另一个方向挪动。小鹿般优美的步伐。
我抓住带齿的蕨草说,你走吧,我是蜥蜴,我要消亡了,与你无关。电闪雷鸣,头晕目眩,我听到身后凌乱的步伐。小鹿般优美的步伐,蝴蝶落在你的角头扇动着翅膀。我感受到了你的呼吸,你周身都在放电,电荷使罂粟花环绕,身体蓄势待发,我的细胞由此充满暴力。
嗨,你不是想读诗吗?你读吧,读诗呀!是梅子的声音。
你走,别管我。
你读呀,你读我才走。
我的意识在抱团打架,像诗的缠绕。欲望的冰在燃烧,我远离自己和一切。消亡,构成我的命运……梅子,离我远一点,不然你会有危险……水流着流着就染红了我的梦,鸟叫着叫着开始凄切和沙哑,在玻璃上划出痕迹……
大声读!把你心里的诗全部读出来,统统读出来!
我悲伤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我坚强一个男人被迫选择的坚强,我堕落别人不会的堕落……
不要停,不要停!小鹿的脚步在后退,踩出一串涟渏。她继续冲我说,像小鸟一样唱出来。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加油!像雄狮一样怒吼出来,这样可以帮助你释放!她的声音渐渐离我远去。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我歇斯底里,梅子,梅子,还在吗?
没有应答。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梅子,梅子?
时间化作梦的碎片,像鱼群在浮动。消失的小鹿,连同她的步伐。我继续制造混乱的字句。不知过了多久,一双柔软冰凉的手探进我欲望的深渊,慢慢地游移起来。我的身心的确需要释放,我是不可救药的患者,是横行施虐令人齿寒的瘟疫。我被永恒地贴上了标签,它是更毒的罂粟花。我拿脐带寻找生活,时刻找地方接上去。站亭里的梅子昂着头,微微上翘的鼻子随时迎接挑战。
我的小宇宙变得炽热、坚硬。意识模糊,心脏发出旷远持久的跳动声。云朵般的手抚过我的欲望和躁动。小鹿在心里踱步。月色隐退,几丝乳白色的云晕在战栗。现实与梦境之间失去界限。
浑身无力,但我逃离了一次厄运,战胜了罂粟花的诱惑。
5
晨曦的光从林间泻下,在三叶草丛间映出阴翳。搜索记忆,梅子像精灵一般钻入我的梦境,走进我的荒野。昨夜的战栗到底发生在哪里?一切似是而非,令人极端不可信赖,恰如现在,离我而去的梅子正躺在我身边。她目光顺着高大笔直的桉树,投向天空的一隅。
是你吗?我试音般地唤道。
半晌,梅子欠起身,捋一捋刘海说,昨晚你念了好多诗,真的好让人意外。我不太懂诗,但隔着老远,我都能从那些诗句里听出你的……你的坚持和勇气。她扶住身边的树丫,缓缓站起来,左脚尖踮一踮,又坐回去说,心里有诗的男人一定不坏。
抱歉,昨晚失态了。不过,现在真的好安静,我很久没有这样安静过了。梅子将手插入发间,梳理几下,似乎在寻找另一个话题的开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她说,我也曾经拥有过平静的日子。一份待遇不高但对未来充满期待的职业,每天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体体面面。周末骑游、登山,睡觉前翻翻畅销小说、人物立志传、心灵鸡汤,甚至包括初级哲学一类的书。毕竟人一辈子要接触各行各业、各种档次的人,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嘛。那个时候,读到“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说服力,因为时间无需通知就可以改变一切”之类的句子,虽然不能理解它的含义,但就是无端地喜欢。停顿良久,梅子又说,可就是这句话成了我的厄运。有一天,我的腿出问题了,不能正常走路了。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子抛弃了我,曾经被我最看重的海誓山盟也背叛了我。那以后,我每天都要对着镜子,看自己走路,越看越害怕,越害怕越忍不住看。上天太不公平了,我即使接受命运,也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生活。127C867D-384F-4170-A0EB-028539BCF1A0
我咽了咽口水,嗓子被粗粗拉拉的东西卡住。
晨风拂过。梅子眉头微蹙,像小小的波澜。她接着道,如果你是我,怎么办?
我垂下头,把目光藏起来。
无解,是吧?我好想逃离。可每次大巴车来了,我就像中了魔咒,怎么也动不了。
九又四分之三站。逃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我问。哈利波特从麻瓜世界通往魔法学校的一堵墙。
生活?想起一句话:我们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在或悲或喜的体验里,形成各自的人生。不好意思,在诗人面前说这些挺班门弄斧的。以前,我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人生中没有能难倒我的事……梅子略微激动,我喜欢挑战、挑战,冲刺、冲刺。登山曾经是我最大的爱好。峨眉、青城、剑门、西岭雪山……我都征服过。我甚至想去攀爬珠峰,不图啥儿,就是想挑战极限。但现在,我的生活里只有死亡的阴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挑战死亡。
我意识的坚冰在分崩离析。
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有点儿累,不过很开心,很开心认识你。不早了,你该回到属于你自己的生活里了。
你呢,继续待在这里?
你走吧。
我站起来,愣在原地。
走呀,走呀,你好讨厌,不准回头。
是男人,说走就走。我踌躇着往山下走,半步、一步、两步、三步……鸟鸣不时传来,短促尖细。阳光穿过云隙间,越来越多地洒向大地。路过几丛凤尾竹,一抹竹影横在面前,让我生出碾碎它的快意。我忽地转身说,现在轮到我提问,如果我就是死亡的阴影,正站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办?
梅子缩一缩腿说,你不是,生活从来就没有如果。
过来。我稍稍后退,把自己罩在竹影里,没有如果,生活就永远不会改变。就像如果没有遇到你,就不会有昨夜的事。
梅子嘴唇碰了两下,没出声。
不要怕!我开张双臂。梅子静静地望着我,眼里有光闪动。我再次大声道,我就是九又四分之三站,好吗?许久,她刷地站起来,紧抿嘴唇,左脚移了移,大腿裤管晃了两下。她缩回脚,再次慢慢地迈出去,左脚尖跟探路似的,小心翼翼地着地,脚跟随之轻轻落下。或许,我从一开始就看见一座错误的灯塔。我和她在某个错误的交叉口相遇。
往山下走,我一旦故意落在后面,她马上止步,直到我保持比她快半步的距离。好几回想转身牵梅子的手。她心有所觉,略微避开。她走得很慢,老想抓住山道边的扶梯,手臂抬起,又缩回。
行至山口边,我问,还去大巴站亭吗?
梅子望着远方,目光从犹豫过渡到坚定。片刻,她说,会的。我还要听你念诗呢,到时我们一块念。
我在心里重复着她的回答,目光越过城市的高处,所有的一切,融在天边化成一缕明净的烟。我说,梅子,你的声音是穿越生与死的力量。一言为定哦。
好啦,现在我们回到各自应该回去的地方吧。梅子说。阳光斜照在她身上,闪动着细碎的光芒。
我点头。思绪的洞穴,遥望着时光尽头的银河。
6
梅子隐身的时光,我的心魔在呐喊,火束是隐喻,塔那托斯在舞蹈,命运的角落,时光残喘不息。精神的雪山再次坍塌、崩溃。嘎吱——我推开那扇唯一可以通向虚幻世界的大门。甲基苯丙胺点燃幽灵的裙裾。我迷恋惊艳和快乐,死亡又使我怯步。救救我!我无法与之抗衡。
每天傍晚,我依旧坐在站亭里,时而碰见痘痘姐,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渐渐省去寒暄。我被卡在九又四分三站里,与现实分离。大巴车来来回回,海棠抽出嫩芽。带刺的春天,让人无法靠近。无望地等待。我是蜥蜴,无声地来无声地去。
再次碰见痘痘姐,她居然主动唤住我,梅子的情况,你知道吗?
我低头。小鹿的步伐声在回响。任沉默恣肆流淌。
哎,看来你真不知道。痘痘姐脸色切过短暂的白,接着说,她去年患上了骨癌。刚开始还去医院看病,后来,除开吃镇痛药,什么治疗方式都不肯接受。她是想通过自己的意志挑战病魔吧。好倔强的孩子,就這样走了。
晴天霹雳!
梅子的腿疼厉害了,她老爱唠叨说,你一定会阳光地去找她。痘痘姐打量着我,目光深切。我报以回视,身姿凝固成冬天——我从痘痘姐的眼里看到了梅子的目光。我分明地感受到,是梅子通过痘痘姐的眸子传达对我的盼念。那一瞬间,有关梅子的记忆,在思绪的沸水里翻滚。稀疏的行人像时间的幽灵在踱步。不早了,你该走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脖子的痛感依然存在,我是这个世界的蜥蜴。
我起身,痘痘姐又唤我,等等,梅子留了一样东西给你。
银灰的手机,银灰的世界,闪动着银灰的斑点。我接过来,不明所以。痘痘姐离去。站亭阒无声息,像闭幕的舞台。
寂静的夜晚,风依旧静止不动。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那是银灰手机里的一段音频。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梅子在朗朗诵念,乐观、倔强。我能等到你,等你阳光地来找我。不,我们在异口同声: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声音来自苍穹,来自大地,来自深海,来自远方。疼痛但坚韧。
夏日的阳光照耀每一个清晨,我寻找着另一个自己,如同梦在寻找春天。相遇,只是为了用记忆带走各自的影子。一遍又一遍地听,一天又一天地一块朗读。九又四分之三站豁然洞开!所有的纷杂和喧嚣退避三舍,只留下冥冥之中奇妙的感知。我拉紧神经的弦,小心翼翼地越过那道以为不可逾越的厚墙,从麻瓜世界走到魔法学校——社区戒毒康复中心。与黄马甲们相互拥抱,微笑握手;坐回少年才有的课堂,两个月、四个月、半年……瘾痛的塔那托斯,让我饱受电流般的袭击;一次又一次的尿检,迎接它的挑战;灯光,朗诵,温暖,寻找超我的力量。我被监控的级别从红过渡到暖橙,切换至鹅黄。美丽的渐变,是我生命的礼物。
再次回到站亭,只有我的世界。
我续写我的第一首诗,从最初改到现在,原来,中间只下了一场雪,如同我没有完结的句子,至今都纷纷扬扬。梅子的声音已然如刺青,烙在我记忆的纹路深处,那里面的力量深深地嵌在我的身体里。
我短暂地陷入自制的小巧玲珑的短暂空白,直到大巴出现。你能等到我,等我阳光地来找你。嘎吱——车门打开。我迈出小鹿般的步伐。嘎吱——门关上。我朝车厢里挪一挪身体。走吧,路啊路,我要将罂粟花抛至荒野,我要将自己带到有阳光的远方。
车轮滚滚,碾压着路面,碾压着时间,也碾压着塔那托斯。127C867D-384F-4170-A0EB-028539BCF1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