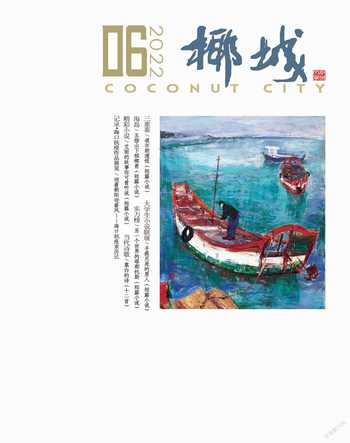艾丽的故事你可曾听说(短篇小说)

作者简介:张香琳,甘肃省作协会员,庆阳市西峰区作协主席。曾在《飞天》《绿洲》《黄河文学》《湘江文艺》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千万别出声》、长篇小说《凤城传奇》。
夏末的时候,卫伟租下套带家具的房子,在海南。然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找到了新的工作,叫我忘掉曾经的不愉快,搬去与他同住。他说他已戒赌,希望我过去监督他。我相信他这次是真的。他毕业于浙江金融学院,曾经是操盘手,来钱不是很困难。后来,他用赚来的钱搞网络赌博,又悔恨地割腕。我原谅了他,但好景不长。
这次,我决定离开。和他分开半年,我换了手机号,去了很多我认为值得去的地方,花光了所有的钱。储蓄已完全没必要。不过,我又想起件事,联系了他。我们曾经一起买过一份保险,到了交费时间。他很高兴,大约他发现我恢复了他的微信权限,再次发语音过来说,仁顺,礁石、海鸥、沙滩椅,还有游泳的我们,不好吗?我举着手机反复听,脑补场景。他的声音仍旧很有磁性。我说我会考虑考虑。之后,我真的想了想。几天后,他又打来电话问我,你来吗?我说我还在考虑。他说,我们可以再办次婚礼。我说,这不可能。那边没了声音。我想,这说明他思考了。我再次告诉他,我无法去。为什么?如果要个孩子我们会更好,他拖着很重的鼻音说,我会是个好爸爸。我也这么认为。但我建议他开启新生活。
佳佳的电话跟着打进来,她语速极快,讲了十分钟,归结起来就是:姥姥的寿诞我必须参加,无论如何。我答应了。此时,我正在云南闲逛,一整天也没什么胃口。我不记得这些天我都吃过些什么。我在地铁口用心看一个女人,她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面前有块红布,上面写着儿子得了亡父遗传病治疗的经过。没人扔几个小钱。女人两条油腻的辫子里夹杂着行道树落下的槐花瓣,脸上有种麻木冷峻的悲壮。这期间,女人把塑料勺子探进儿子嘴里,给他喂水。又扯儿子明显短了半截的裤管,遮住他泛黄的皮肤。网上说,这都是骗子的伎俩。我不打算分辨真伪。我塞给她一张红色的钱。女人的回应得体又亲切,这让我多少有了回家的动力。我背着包,乘坐京广线列车,十八小时加四小时再加一小时,从版图的鸡肚到鸡心,回到家乡。
佳佳发位置给我,还是那个古建酒店。她没提我爸爸近况。当然,我也不想问。好几年了,他不知道我结婚。现在,我也不打算告诉他我离异的事。虽已脚踏故乡土,但我仍然觉得这不过是场敷衍。
我居然提前了一小时,也好,可以整理一下。眼线笔、腮红可真是个好东西,BB霜也不错。它们让我看起来状态没那么糟,至少黑眼圈和黄皮肤有所隐藏。
酒店临湖,打开窗户,外面睡莲一小片一小片,柳丝斜扬,送来几缕粉红的风。我们6年没见。我和我爸爸,也从未视频过。今天会怎样?他还会像最后那次扭着我的胳膊,搞得我像搁浅的鱼一样在地板上翻腾吗?哈,这次肯定不会。如果真那样,我会毫不犹豫地拨打110。他顶多会阴郁着他那张国字脸,佯装轻看我。他会走上来拥抱我吗?啊,不,不,这很可笑。即使这样想想,也令我不舒服。或者他会当着那个富态女人的面对我客气微笑,像这6年根本不存在一样拍拍我的肩膀?可能还会说,路上好吗?然后我会说——说些什么?我真不知道自己会说些什么。要不谈谈我妈妈?
我有一头密如瀑布的头发,这无疑遗传自我妈妈。她有张梨形脸,眼睛水汪汪。我从看图识字起就看她。直到有一天我把她扣在桌子上,再也不想看。所有人都说她是个了不起的硬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生我这件事。我的周围常会响起些莫名议论的含混声,在我警惕想听的时候又水花般消失。事实上,哪怕我真的是在看电视,眼睛的余光和耳朵还是比雷达更灵敏。没什么事能骗得了我。
小姨经常到我家来,带着女儿佳佳。佳佳和我同天生日,却老爱摆出一副老大的模样。我给她饼干,她用食指纏着羊角辫脑袋晃来晃去说,都给你留着。我不明白。分享才快乐呀!她尖着嗓子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没妈妈,我应该让着你。我生气极了,把饼干揉成细渣扔到她脸上,还捶她一老拳。她哇哇大哭,返身砸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的头发散了,裙子扯破。小姨以为我们抢饼干,下次来,买几大包,又唬着脸给我们讲道理,薄嘴唇一张一合,像水箱的鱼缺了氧。这让我更加不喜欢小姨。我爱吃小笼包。爸爸说,你妈妈也爱吃。去姥姥家,姥姥端出好几笼。小姨也一样,买了送家里来。我逐渐讨厌那肉馅里的葱味,太浓郁。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认定我会一直喜欢它。
照片里的妈妈披着弯曲的长发,戴一幅眼镜,笑得露出八颗牙。爸爸挨着她的肩,表情羞涩而不自信。我从爸爸藏着的影集里翻出妈妈生病时的照片。她穿蓝色病号服,身上搭些乱糟糟的红黄绳索,床头柜放台大屁股仪器。她闭着眼,脸庞浮肿黄亮,不知道在想什么,小腹隆起老高。那里面肯定是我。没错,就是我。那时候我肯定在和她互动,用手和脚在里面全力撑着她的肚皮,让她感受到我的蠕动。我需要在透明的羊水里游泳,还需要做做体操。或许就是我这些可人的小动作使得妈妈下不了决心。她倒是对自己狠得可以。
实质上8岁以前的事我记得不多,去诊所算是最真切的。
真勇敢,不疼吧?爸爸背我去诊所扎针。嗯嗯,我只管点头,眼睛盯着张阿姨的脸。她温热的手臂压在我屁股上,有种说不出的奇妙。我喜欢这份触感,还喜欢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气息。为了多接触她,我赖在诊所床上不走,说,消毒水的味道真好闻。爸爸看穿我的诡计。不过,他也留意到张阿姨相当俏丽的脸蛋。小学老师布置了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长项。我笔下的妈妈当然有黄鹂般好听的声音,会做赏心悦目的美食,还有张阿姨那样光荣的职业。老师夸我写得好,把我的作文拿到校广播站播放,于是我理想中的妈妈就萦绕在天上啦,真实得像我头顶上的云彩。放学铃响,同学们撒腿跑向校门口。他们的妈妈声音真甜蜜,呼唤着他们的小名。我被打回原形。借你们妈妈的手,让我牵一下。我追赶着要好的同学,想说这话,跑到跟前,又慢下脚步。如果这样,她们肯定会嘲笑我在作文里吹牛。可我不吹牛,难道要告诉她们我是个没妈的孩子?嗯,佳佳说得对,他们都比我富有,他们有我没有的。而我,再也不能把属于我的东西分给任何人。127C867D-384F-4170-A0EB-028539BCF1A0
倒霉的开端还是从我和佳佳过14岁生日时说起吧。那天,佳佳穿上了泡泡袖新裙子,孔雀开屏般在我面前跳来蹦去。当年最流行的百褶裙衬得她脸上红霞溢彩,白雪公主也美不过她。而爸爸正忙乎,他又一次从只带灰尘的大皮箱里翻出件新衣服。不,确切地说,应该是放了十几年的新衣服。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述。妈妈一共为我准备了18套裙子。每套裙子比上一件长两寸。按照她和我爸爸的计划,我每年生日穿一套。还有一叠信,每年读一封。那信足有二尺高。爸爸仔细熨烫那套黄色的碎花布裙,把它套在我身上。真令人窒息,我又一次像被裹在被套里。这裙摆,也太宽大了吧。镜子里的我如同根干芦柴棒,黑不溜秋陷在一片黄花地中,瘦,眼晴奇大。
“爸,我不穿这个!”
“挑食,挑衣。”爸爸说,“快,他们在等!”
“穿别的不行吗?”我想着舅舅和小姨的面孔,说,“土。”
“必须穿,你懂的!”
我不懂。去年就是这样,爸爸逼我穿裙子,拖着我去古建酒店。据说,妈妈考上大学在这酒店庆贺。爸爸抱得美人归,他俩结婚也是在那儿。
桌上的生日蛋糕有水果和卡通两种。唱完生日歌,到了吹蜡烛环节,我和佳佳一起伸长脖子。我穿着套海魂衫裙,它白条蓝方领,是早就没人穿的老式样。而佳佳,当然是和我完全不一样。“越长越像!”“如果艾丽在就好了!”果啤咝咝的气泡声夹杂着压低的声音。没错,他们在透过我看一个人,大概那人的灵魂裹在我裙子上。姨父夹菜给佳佳,也给我。爸爸坐在我身边,他没这样做。他盯着眼前那盘小笼包,颊骨高耸,没一句话。大家让他喝酒他就喝,你说多少就多少。喝,喝!后来,大家不让他喝他也喝,拽都拽不住。他趴在桌沿边,眼睛红巴巴的,伸着脖子咳。
现在,我14岁了,我拒绝被他再拎去酒店,木偶一样。
“为什么?”爸爸在客厅来回走,声音震得窗玻璃嗡嗡响,“穿一会儿都不行吗?”
“我讨厌这一切!”
“看看你妈妈给你写的信,别辜负她。”
“那些信,除了让我流泪,改变不了任何。”我脱下裙子尖叫,“你根本不懂我需要什么!”
“你,想要个妈妈?”爸爸瞪大眼珠子。
“也许,不。”
“你可以穿我的,我穿你的。”佳佳说,帮我抹眼泪。她总是有办法、有理由让着我。
家里很意外来了客人。她坐在沙发上,看到我放学回家,脸上堆起笑。是我喜欢的张阿姨。我赶紧帮爸爸准备油焖虾和大闸蟹招呼她。我很高兴家里有了新变化。
“你煮的饭真可口。”张阿姨对爸爸说。她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还有浓密黑长的睫毛。不过,她颧骨高,眼窝处有明显的皱纹,即使不笑的时候,也隐约看得到。她陪我去逛街,给我买新衣服。其实,后来更多的时候是她和爸爸出去。他俩去丽江,我去姥姥家过暑假。
“雍,来帮我呀!”旅游回来的張阿姨声音越发甜腻。爸爸扔下手里的活计去给张阿姨戴项链。24K金,爸爸送她的。他们当然也送我礼物,一条巴掌大黄丝巾,装在一个皱巴巴的纸盒中,上面印着心形的图案。我把它扔到一边去,看着实在不顺眼,再踩两脚。
“不久,他们就会给你生个小弟弟。当姐姐的好处就是永远有个奶瓶需要你去涮。”佳佳用她有限的经验对我说,表情神秘。
张阿姨波浪发垂在脑后,蓬勃如秋天的金色草。爸爸的手动辄就搭在那草上,抚摸个不停。这还不够,她又用根蓝布带把头发从额头前束起来,嘴巴用玫瑰色口红涂得发亮。看起来,她完全是芭比娃娃的装扮,和爸爸依偎在一起看电视(起初,是在我做作业时)。有时,她还会换身藕色的旗袍,古典风,粉色细跟鞋,身上的香水味浓郁到我根本无法靠近她。上学,吃饭,睡觉。她对我来说,像当年给我打针一样,没一句废话地干脆。有一天,我透过卧室的梳妆镜发现她在阳台上栽花。中午光线明亮,打在她泛着光泽的粉色绸缎睡衣上。爸爸从身后抱住她的腰。她笑得断了气似的咯咯咯。爸爸继续用大胡须扎她。俩人嬉闹,如同森林里的两只猩猩,完全忘记人类的存在。我蹦出卧室,拿出妈妈的照片摆在客厅。念妈妈留给我的信,最大声地读出来:“亲爱的雍,你为我们的仁顺吃了不少苦……我们彼此相爱,来世,我们一定团聚,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把我们分离,仁顺替我……”
妈妈在信中幻想了我们的生活。包括爸爸给我做饭、给我洗脚、给我辅导作业的场景。包括爸爸老了,我照顾他起居的事情。但绝对没有爸爸和另一个女人生活的设想。
阳台上的人安静下来。静得出奇。不大一会儿,传来花盆粉碎的声音。一个,又一个,再一个。
我把这事告诉佳佳。她从姥姥家偷出小姨当年录制的碟片给我。我自然要把它经常播放在客厅,尤其是在周末。谁也不能阻止我对妈妈的思念:碟片里呈现的场面混乱不堪,有个男人,声音像头受伤的黄牛。我都不好意思看。他对妈妈发誓永不再娶。妈妈安详地躺在那里,表情恬淡而满足。碟片经过后期制作,配的背景音乐诗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小姨干的。哦,我真想吐。当年,妈妈的勇敢在县城无人不晓。她在怀我6个半月的时候,被确认为肝病重症,医院给出两种方案:保大人,立刻做终止妊娠手术,进行肿瘤切除;保小孩,肿瘤一旦扩散会危及母体……
“真没一点别的办法了吗?”爸爸哀求医生。
“即使顺利生产,母体也将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医生反复看CT片,说,“无法保证母子健康,还是建议保大人。”
“我的孩子胎动很正常,”妈妈把那堆化验单扔得雪片一样张扬,“想让我引产?除非我从这楼上跳下去!”
“艾丽,你的病必须治!”
“我们的孩子,是爱的结晶,丁雍。”妈妈用手抚摸着小肚子抽泣,“即使我有意外,她也会替我陪着你。”
妈妈在生下我九个月后去世了。留下的衣服、信和视频每年都在严肃提醒我——无论她去了哪里,在火星土星水星在任何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她都是爱我的。她当然不知道她走后那个和她谈恋爱时敢于烫爆炸头、穿阔腿牛仔裤的时尚男人也和她一起消失了,只有“晦气”两个字贴在他的额头。他了不起的妻子为了给他延续后代拼死生产,这样的选择、这样的爱情不是最感动人心的么?多家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他俩的故事。那些日子,他觉得他行,一定行。他需要低下头,需要含辛茹苦,需要像个捍卫爱情的圣徒一样高尚地活着。127C867D-384F-4170-A0EB-028539BCF1A0
现在,我同样需要。如果爸爸不和张阿姨分手,我就整宵不回家。我和新认识的朋友待在遍布城区的网吧里,狡兔不止三窟。呵呵,让我那个几近疯癫的爸爸遍寻姥姥家、舅舅家、小姨小姑家吧!让他们把他数落成一只被拔了毛的丑公鸡吧!不过,爸爸法力无边,他和那个伪善的女人一起把我拽回家。好吧,那就把妈妈留给我的东西全部烧掉吧!留着它还有什么用?什么天长,什么地久?全部都是恶心、做作!我把那些花瓣一样的粉色信件扔进火盆,当着爸爸的面。还有他和妈妈抱着我的照片。
“是你们,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为一个话题性的人!”
“是你们,让我的出生带着原罪,让我的存在成为包袱!”
“你,愚蠢的家伙!”爸爸扑向那张三人照,想用手去拍灭。我来回躲闪,不能任由他去抢回那些。灼烧的疼痛。但显然爸爸比我有力气多了,螳臂当车这词形容的就是我。眼泪淹没我密林般的睫毛,我用手背甩走它。是的,我远没有妈妈想象的那样乖巧、聪明,一年一个变化,向上的台阶,继承着她超高的智商和优秀。我,梁仁顺,笨得出奇,丑得出奇,糟糕透了。当然,爸爸也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让那个女人走!”
“为什么你不替我想想?”爸爸的脸比蒸熟的大闸蟹还红。
持续。冷战。
……
以上都是我十六岁以前的事。
高二那年,我趁着爸爸出差,约了几个朋友去草原上骑马。我不想告诉那个女人我要去哪里。原野大得无边,自由给我插上翅膀,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管我我就和谁急。没想到的是,胯下那匹马和我一样淘气,它对着白云昂头吟诗,后蹄一扬,把我从背上生生撂下来,摔断我三根肋骨。爸爸把我从医院接回家。“挽住我胳膊走!”他瓮声瓮气地说,脸上没有一丝儿笑。
家里没有那个人。爸爸给我保证,以后也不会有。他给我煮面,有点驼的背影映在厨房的玻璃上。我就喜欢他围着我转。一直这样的话,我宁肯再断几根胁骨……我需要条毛毯,进入爸爸的卧室。衣柜里藏的东西发出令人眩晕的香气,爽身粉、乳液、化妆水。事实并不像爸爸给我承诺的那样。在激烈的争吵中,我把那些粉色、紫色、黄色的瓶罐一个接一个地砸在地板上。碎片划伤我的脚,血淋淋的。当我把手伸向那些裙子和内衣,打算再剪个天女散花的时候,爸爸冲我扑过来,黑云压顶。我没躲开,他用手扭住我胳膊。我边哭边用脚踩他的脚背。他用几个很响的巴掌制服了我,凶狠异常。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大吼,“为什么要生我?”血和泪一齐从我身上涌出来,我鱼入网一样蹦起来。
想起那可怕的一幕,我忍不住摇摇头,好像那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幸好,现在再不是从前。我恨恨地想。我的两条胳膊青了一大片。拖着皮箱离开家时,我分明感到全身的痛。他,如果胆敢拦我,我必从六楼跳下去!他被我吓着了,他没有。我去了南方。这些年,我卖化妆品、做美甲师。认识卫伟后,我上了文秘培训班,后来以给网络平台写软文为业。我的事,佳佳知道一些。
佳佳短发,白衬衫藕粉西装,两条鹭鸶腿看见我直奔过来。拥抱我后她转身拉着服务员交代:“今天我买单,必须把我认准了!别人都不行!”她又嗲又尖的小细嗓子,配一口嘎嘣脆的普通话满大厅飘忽:“我去接寿星,堵车,来晚了。”走入包厢座位后,她左手伸向小姨父,摩挲他的背。右手递给小姨。小姨眯着眼看她,笑从眼里溢出来。姥姥抚着她笋尖样的白嫩手,嘴里直嗬嗬。我沉默。那情形倒像是佳佳从外地回来。
“吃点水果吧!”小姨和姥姥招呼我说,“为什么老不吭声?”
“仁顺坐了一整晚硬座,累了。”佳佳替我说。她加重强调“硬座”两个字,我不搭理她。我从来都这样,她也从来都这样,从小到大。让她优越去吧。一年前,我收到爸爸的简短来信,信上说他自去年起一直梦见我妈妈。希望我能多回来看看姥姥。至于他自己的事,一点没提。我没回复他,用打印机打了四个字:尚平安,忙。我想,他爱梦谁谁,那是他的事。
我的眼睛望向门外,疑惑他为什么还不出现——可能,张阿姨会挽着爸爸的胳膊走进来。这些年,她该养尊处优了吧。我重新低下头玩手机,其实是想找张我和卫伟的合影。万一爸爸问我个人问题,我得给他看看我们曾经亲密的样子。我绝不能告诉他我和一个赌徒结婚了,又因为他戒赌成功我和他分手的事。这是不是很奇怪?或许爸爸并不想见我,要不为什么迟迟不见他身影?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是有点想他。这个发现让我吃了一惊,我为我有这个想法而感到懊恼。似乎还不是懊恼,是泄气。难道就因为张阿姨的存在吗?当年你真的只是想让他只爱你一个吗?我相当忐忑不安。
身体被人轻拽一下。
转过脸,有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在我身后。他坐在轮椅上,眼袋浮肿,青黄的皮肤裹在高颧骨上。好奇怪哦,他用一双混浊的眼珠子定定地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我跳起来,犹如包厢里窜出条蛇。他摘下帽子,用手挠了挠光滑的头皮,又戴上,臉上的表情羞涩而不自信。我脑中闪过他和我妈妈的合影,全家三口人的合影。他在极力控制手的颤抖,嘴巴黑洞似的向着我,“啊——啊——呦——呜——”没有完整的音,涎水顺着右嘴角流下来。看来,他想对我说许多话,很激动,很艰难。
显然,女儿已经认出了他。丁雍庆幸她还认得出他。这些年,他一直很思念她。他希望她也一样。但他从她的回信中了解到她并不打算原谅他。或者说,她一点都不牵恋他。他感到做父亲的失败和无力,尤其身边没个能和他说话的人时。他为过去的行为流泪,唯有酒精和烟能让他重拾一点平静。的确,他严重伤害了一颗心。而仁顺,又是那么敏感。现在,这些对不起的话都卡在嗓子眼,堵得他直哽咽。他想用笔表达。但过去在他手中极灵活的笔现在都在调戏他,他压根儿连它们的身体都捏不住,更别指望它能替他吐露一丝半点的心声了。他盼着见面这天,尤其在她失联那段时间,许多次他都想开着电轮椅冲下古建公园的湖泊里,一口气,真痛快。还好,她在。至少现在看起来完全健康、平安、美丽。
“他,怎么了?”我转身抓住佳佳,她的手和我一样冰凉。127C867D-384F-4170-A0EB-028539BCF1A0
“脑梗,”佳佳说,“差点救不过来。”
“她呢?”佳佳当然知道我问的是谁。
“出国给她姐姐做伴去了。他俩一直没办结婚证,姨父不同意。”
“为什么我知道得这么迟?”
“你说呢?
是啊,春天那阵子,我换了手机号。我不主动联系,没人找得到我。
“就算知道,你该怎样?”佳佳说。她扭过头,不再搭理我。
他还在盯着我,眼睛都不愿眨一下,大约我太像一个人:我烫了头发,牛仔裤,小白鞋,梨形脸。他向我伸了伸双臂,试图站起来。但显然右腿是个叛徒,它不支撑他。佳佳扶住他,用手轻拍他的背。他的左手瘫放在扶手上,手背干瘪,青筋暴起。我闻到他身上有股腐烂的梨子味混杂着鱼腥味。握握他的手?或者主动给他个拥抱?我,我迈不动腿。他的眼神黯然移向某个地方,右手不停地戴帽子,脱帽子。脱帽子,戴帽子。
“姨父现在住康养中心。”佳佳说。
“老房子呢?”
“锁着。”佳佳想说什么,又停下。
外面的天空暗下来,水晶吊灯的莲花瓣透出乳白。它把柔和的光洒下来,笼罩住所有人,温情无限。我站在那里,感到光渐渐向我聚拢。
“为团聚干杯!”佳佳把爸爸推到中心位置,换上金边纸质寿星帽。我的周围一圈笑脸,没人对我说别的。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生日歌,拍手、举杯祝福爸爸长寿。我被众多声音裹挟着,向前走,向前走,潮涌一般,直到站到寿星的身后。鸭舌帽男人表情虔诚,他把右手蜷在额前,像在敬礼,又晃了几下头。小时候,他曾教过我怎样许愿:双手合十,心中默念,虔诚,点头。我庆幸我还懂得他,不需要语言。佳佳替他围上口水巾,我该干些什么?
“吹,用力!快!”他们催促我。我俯下身体,和爸爸一起鼓起腮帮子。
“好了好了!”几缕青烟萦绕在蜡烛的顶端,倏忽消失在笑声中。其实,根本不是姥姥要过寿诞,而是爸爸过生日。我不糊涂。不过,我承认我一直在装糊涂。我坐下来,在他旁边。我放弃了拥抱他的念头,我觉得我还需要积蓄些力量。
“他的左腿通过康复锻炼會恢复,”佳佳说,“但这需要时间。”
“会的,”我沉思一刻,说,“一定会的。”
我拿出手机,给卫伟发去爸爸的样子。我想,即使我已原谅他,我们也无法再在一起。可能永远也不行。我的手摸向裤兜,那里有叠纸。我一点一点地掐碎它。那些白色的、可恶的化验单,它证明我和妈妈一样,不太走运。我把幽怨的目光投向轮椅上的人。他的手颤颤地伸过来,紧紧抓住我。
突然,一切清晰起来。127C867D-384F-4170-A0EB-028539BCF1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