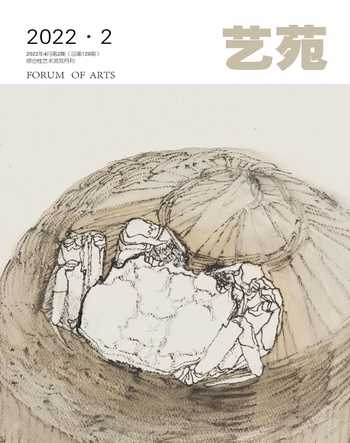关于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及其伦理性的思考
王丽
摘 要: 人工智能介入藝术创作,是当前艺术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与传统艺术创作不同,人工智能是作为理智工具介入艺术创作之中的。在艺术创作主体发生更替的人工智能“造物”中,从功能性定义上来说,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而在程式性定义上解释,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作为人工制品被授予了向公众展示的资格。人工智能介入艺术的程度愈深,艺术就愈发边界不明,产生了诸如创作主体模糊、原创性争议、公众接受程度不同、艺术是否终结、传统艺术家是否消亡等艺术伦理性问题。
关键词:介入艺术;人工智能产物;艺术伦理性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新文科背景下,传统人文学科与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交叉、融合日益密切。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开始参与写诗、作画、创作剧本等行为,人工智能既赋能艺术,让艺术作品重新焕发人文性,同时也引发了它与艺术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即便是在当前弱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造物”到底是“以假乱真”的高仿赝品?还是别具魅力的艺术新分支呢?能否作为艺术殿堂的新成员被接纳?传统艺术标准是否也适用于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思考,并尝试给出解答。
一、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
人工智能现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时代性名词,教育、法律、治安等领域都有它的身影,像指纹识别、无人驾驶、语音翻译等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技术更是直接受惠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通过模仿人类艺术创作经验,力图生成有创造力的作品,希冀在艺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目前人工智能已介入诗歌、绘画、音乐、编剧等艺术创作之中,并在艺术界引发了诸多如艺术定义、艺术标准、艺术主体等问题。
人工智能介入诗歌。微软人工智能小冰在2017年出版了《阳光失了玻璃窗》。小冰通过深度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学习了1920年以来的519位诗人的现代诗,其创作过程以人类艺术家为基准,在庞大数据集样本中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训练了10000次之后,作出混淆人类感知的诗句。“人人都是徐志摩”是由艾耕AI人工智能团队开发的写诗小程序,于2018年上线,用户上传图片后,人工智能机器人“MO”根据图片所传达的信息,就能为用户写一首现代诗。201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系统生成日本俳句,他们从诗歌网站上搜集了8000个开源俳句集,在给出俳句的第一行后,该系统能生成最后两行。笔者将安迪·沃霍尔的视觉作品《金宝汤罐头》上传至“人人都是徐志摩”小程序,一分钟内得到了一首现代诗(图1)。这首现代诗语句基本通顺,但是诗句中出现的“长江”“白雪公主”“学校”等意象,与视觉作品《金宝汤罐头》并没有任何联系。现阶段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在效率方面是人类无法匹敌的,但无法触发用户审美感知与想象的深层结构,只能将意象留存于表面形式技巧上,而无法与内容产生整体关联。

人工智能介入绘画。Google在2015年公布了Deep Dream项目,该项目只需略微修改参数就能生成以背景图像作为起点的奇幻图像。2019年微软小冰的个人画展“或然世界”(Alternative Worlds)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成功举办,依旧通过数据集对四百年艺术史上的236位著名人类画家画作进行系统学习,在构图、用色、表现力等细节方面显示了与人类创作相匹敌的水准。
人工智能介入音乐。在音乐创作、音乐演奏、数字声音处理等领域中也出现了人工智能的身影,例如交互式作曲技术的应用,音乐新媒体联盟装置展系列一“波凌”在2018年展出。王新宇的《波凌I》就是一部利用人机交互环境打造的多媒体声音装置,观众借助全息投影媒介参与到作品中来,体会作者对升腾和水这一传统文化意象的感悟。AIVA是由音乐制作初创公司AIVA Technologies打造的一款人工智能产品,通过对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人所创作的近3万首音乐作品的学习来作曲,并在2018年发布了首张中国音乐专辑“I am AI”。
人工智能介入编剧创作。首部由人工智能编写剧本的影片《Sunspring》在2019年6月的伦敦科幻电影节48小时挑战单元上亮相,“编剧”是递归神经网络“Benjamin”,它学习了《2001 太空漫游》《第五元素》等上千部科幻电影后,利用机器学习创作出包含科幻要素的剧本,实现了语言文本的输出。故事开头是男主角H和女主角H2在吵架,后另一位男主角C参与进来,三人的对话跳跃性很大,故事情节被忽略,逻辑上的不通顺增加了影片的乏味。曾执导过多部电影的凯文·麦克唐纳,也在2019年尝试拍摄了一部60秒的雷克萨斯轿车商业广告片:《直觉驱动》,剧本来自科技巨头IBM的Watson人工智能平台,在分析了品牌汽车的15年商业广告后,人工智能编写出展示雷克萨斯性能与曲线美的广告剧本。上述两个例子都实现了人工智能编写剧本的视觉化,并被带到观众面前,人工智能学习剧本的结构,并找到单词、句子、段落上的关联和语义特性,虽然人物塑造、逻辑关系上还处在襁褓中的婴儿阶段,但人工智能介入剧本的写作,并输出独立作品的现象是不容忽视的。
人工智能已介入多个艺术领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与传统艺术作品的高度相似性也使艺术的边界愈发模糊。比如在2016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有59%的作品令观众无法判断背后的创作者是机器还是人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Art Basel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展上, 把人类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和AICAN(人工智能创造对抗网络)的作品并置在同一空间,观众将两者相混淆的概率高达75%。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在种类的广度上和质量的深度上都有所成就,已成为当前艺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那么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的产物能走进艺术的殿堂吗?
二、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的产物是艺术作品吗
人工智能广泛介入艺术创作,并生产出了大量与传统艺术作品高度相似的产品。那么,这些产物能否看作是艺术作品?人工智能的介入迫使人们重返艺术本体论的思辨中。斯蒂芬·戴维斯在《艺术诸定义》中分别阐释了功能主义阵营和程式主义阵营两种定义艺术的方法:“体制理论艺术定义的辩护者坚持认为:不管总体上它是否与艺术的意义相配,一个作品是不是艺术作品,得具有艺术身份授予资格的某个人授予它艺术身份。功能性观点定义艺术的拥护者则坚信:一个作品只有满足艺术的意义要素,才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不管它遵从何种程式,也不管艺术的权威怎么追捧它。”[1]78人工智能介入到艺术中来,能否将其产物划分到功能性定义或程式性定义的艺术阵营中去呢?
从功能定义上来看,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的产物不是艺术作品。在艺术端赖的独创性那里,艺术作品需要有某种或某些特质才能配得上艺術殿堂所授予的荣誉,在艺术馆的厅廊里,它们不仅作为艺术,而且是作为好的艺术被展示。按照这种观点,人工智能虽然介入艺术创作,但其产物并不能称为艺术作品。人工智能利用智能化的方式对“尊”为艺术的作品进行描摹,仅仅完成了模仿,而远没有达到艺术的功能性呈现,或者说它们并不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2]13。公众在无限接近人工智能创造物的同时,愈发体会不到传统艺术所带来的审美快感,此时此地的光晕消散殆尽,作为正统艺术中充分条件的时间连贯性和空间一致性被列在缺席名单上。人工智能不能将艺术家在生活中得来的体验物化,也不能随便将其划分到某一时代,因为背景和所要传达的意蕴无从考据,这成为人工智能“造物”被圈内人士诟病的主要方面。有人曾尝试通过人工智能重新构造出青铜器,但青铜器的出现是当时宗教、政治、行礼时无法或缺的东西,不仅代表人物身份地位,更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时代文明的角色。将众多青铜器的图片输入给人工智能,得来的仅仅是没有温度的合成物,尚且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再比如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在这些诗中不难看出人类诗作本身的技巧和手法,但是还不够成熟,某些诗作在意象的选取上是重复的,缺乏逻辑性,更重要的是读者很难再感受到杜甫诗作中饱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了。此类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参与到艺术中来,它依旧只是作为工具为人类艺术作品增色,其背后缺乏审美感受、传达意蕴等独特艺术价值的支撑,公众作为拥有肉体的人类无从获得普遍性的共识。从功能定义上来说,人工智能本身所生成的产物不能称为艺术作品,至少不能算是人类艺术作品。
按照程式性定义,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的产物是艺术作品。在程式性定义的框架下,要想成为艺术,那些被创造之物需要经过博物馆或美术馆等艺术界中权威人士认可的程序。艺术体制论早期对艺术的定义是:“(1)一件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 (艺术界) 起作用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3]34迪基的艺术体制论为艺术程式性定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成为艺术在特定语境中可被授予地位的可行性契约。以《爱德蒙·贝拉米肖像》为例,这幅在2018年10月佳士得拍卖会上成功出售的人工智能画作,像杜尚的《泉》一样,对艺术史造成了文化冲击。这幅作品是署名是一串算法公式,同时参与竞拍的还有20多幅毕加索的画作,在与大众所熟悉的传统艺术家相媲美的过程中,仅就这幅人工智能产物的拍卖价格和大众接受程度来讲,它无疑跻身进了艺术作品行列。人工智能被输入了15000张14到20世纪的肖像画,学习了人类画法的规则程序,判别出属于人类画法结构之后,生成了《爱德蒙·贝拉米肖像》。如果说人工智能是“人造物”,那么《爱德蒙·贝拉米肖像》就是“人造物的造物”,颇具抽象主义的风格使它作为可供理解的对象面向大众公开传播,在既定语境中被展览和解读,有人类意图性的创作力的参与——Obvious团体中的成员选择将哪些画输入给人工智能,并将这幅获得艺术身份的画作带到了获得入场券资格的佳士得拍卖会上,最终以43.25万美元 (约300万人民币)获得公众的鉴赏与理解,成为与人类艺术作品相媲美的艺术作品。正是基于上述特点,从程式性定义上来说,有人将人工智能创作的绘画、诗歌、剧本视为艺术作品。
笔者认为,AI+艺术在被按下开启键之后,即使偶尔被艺术家和大众所恐惧,但目前来看还没有要结束的势头。像传统艺术一样,人工智能在艺术作品创作中也需遵循某种既定的法则,随意妄为带来的后果只能是终止在艺术市场中的流通,更得不到被公众鉴赏的机会。《速度与激情7》采用数字技术完成对逝世主演保罗·沃克的“换头术”,在受制于现实的情况下,既保证了影片原先的立意构思,也满足了观众对影片的期待。诸如此类的技术运用在影视作品中不在少数,这并不代表创作者极端痴迷于技术,放弃了对艺术的向往,而是在受制于现实条件的情形中,借助技术成就艺术作品的完整表达,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艺术品位。技术赋能协助艺术传达意蕴,同时也要避免技术的滥用,医学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为艺术界中技术的使用提供了一个范例,技术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应积极对待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人工智能在艺术作品中扮演的角色是赋能,而不是“恐怖谷”。因此在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开幕式上,作为中国本土原创的虚拟偶像泠鸢参与主持,呈现了“智联世界、众智成城”的人工智能数字新未来前景。事已至此,不妨借助特里·巴雷特的观点对什么是好的艺术加以研究,不啻排解忧愁的良药。“你不必一定要喜欢它,但作为一名观众,负责的做法就是暂时性地接受该件作品是一件艺术品,然后再决定它是否是一件好作品,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它被认为是一件好作品。”[4]18
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探索只是初期,技术的不成熟,以致和艺术的兼容出现了偏差,难免受到质疑,人工智能作品能不能被艺术界所认可还需要不断地在现实中实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艺术品的边界会越来越宽泛,而由人工智能引发的艺术伦理性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三、人工智能引发的艺术伦理性问题
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迅速发展并没有遮蔽艺术伦理性问题,像某些人类艺术作品一样,人工智能“造物”也同样面临着道德性争议。在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中,其创作主体是谁、是否涉嫌抄袭、公众能否接受、艺术是否终结、传统艺术家是否消亡等质疑是备受关注的议题。
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中,其创作主体是谁?传统艺术为创作者所属,创作主体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有鲜明的情感。而狭义人工智能时期的人工智能是有理智无情感的智能工具,其介入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不易界定,是AI程序员?还是使用AI的人?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结合逼迫着以往的人类艺术创作者驱新,艺术的边界被无限延伸,在艺术创作中人类艺术家的烙印被模糊化,人工智能正在挑战作者权的地位,在艺术领域中塑造独树一帜的带有作者风格的作品显然要困难得多。与人工智能相比,同样是借鉴优秀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经验,同样是面向观众的特定需求,人类艺术家的作品能打上原创标签,而人工智能“造物”的作者還有待商榷。
在传统艺术领域中,艺术家的个体主导地位是艺术之为艺术的光环,是艺术家体验生活,借助特定工具,在完成从生活中得来的艺术构思之后,将心中所想物态化的过程,有时还会伴随着突如其来又稍纵即逝的灵感。作为创作主体的是人,艺术家在流动的艺术创作中处于固定的主导地位。艺术家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在政治背景、个人阅历等条件的影响下,创作出具有个人印记的艺术作品,即便是偶发艺术也难以避免看似不可思议实则真实存在的现实土壤,又或者是作为反抗“优质传统”的法国新浪潮电影作者们,他们用摄影机自来水笔书写属于个人又逃离以“等价”手法为原则的剧本电影的“明天的电影”,赋予日常事件以神奇性,例如特吕弗的电影带有浓烈的个人传记色彩,戈达尔则不厌其烦地在电影中插入对事件的看法,他们在影片中践行着对生活的独特经验。
而在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后,人的绝对权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中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计算机作为终端无需获取生活经验,依托将非理性排除在外的算法,对从人类那里习得的艺术结构、形式等加以深度学习,在总结出规律后作出最优决策,获得一种新形式的艺术成果。《爱德蒙·贝拉米肖像》署名是被Obvious团体附加上去的算法公式,这幅作品是Obvious团体操作,借用AI程序员罗比·巴莱特提供的开源代码实现的,在暗箱中学习了1.5万张人类艺术家的画作后制作的,所以其创作主体拥有四个备选项,即算法公式、Obvious团体、罗比·巴莱特和人类艺术家。法国2009年修改的知识产权法典规定“保护一切智力作品的著作权”[5]64,其前提是基于自然人之上的,算法公式就被排除在创作主体之外了。英国1988年版权法案第九条第三点规定:“对于由计算机生成的文学、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作者应被视为对作品创作进行必要安排的人。”“必要安排”指的是难以替代的安排,照此说法,《爱德蒙·贝拉米肖像》的作者应该是在作品创作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衡量四者在作品生成中的占比分量成为决定作者的关键因素,在完全由计算机环境生成且不受人类干预的作品中,作者甚至不必须是自然人。
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是否涉嫌抄袭?与最初给定程序就能生成作品的“计算机艺术”不同,人工智能“造物”的输出是有人类艺术作品数据支撑的,大多数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是对人类艺术作品的风格迁移,它的创造力是人类艺术创作特征的相对性状态,并不具备自主变革性的创造力。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真正实现了“数据自由”吗?《爱德蒙·贝拉米肖像》最终受惠的是Obvious团体,拍卖交易成功的43.25万美元既不归输出成品的人工智能算法所拥有,也没有与提供代码的罗比·巴莱特分享,即便他在社区已开放源代码。作品的生成逃过了鉴别的火眼金睛,但风格上还是人类艺术品的风格迁移,只不过在迁移程度上更进了一步,目前各国法律对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的不完善和差异并不代表新表达方式的“数据自由”。例如在美国,版权局则宣布“注册原创作品,前提是该作品是由人类创作的”,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恐怕不能归入完全原创的作品之列。Adobe公司开发了Photoshop计算机程序,但并不拥有使用该软件制作的每件作品,版权属于使用该程序创作其作品的作者,即用户,在其他人借鉴此作品时,需打上原作者水印,而不是使用Photoshop软件就拥有借此生成的作品的权利。人类可以理解人工智能生成此类艺术作品的缘由,但无法解释机器是如何学习来输出此个艺术作品的,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脱离人类把控的过程涉及对创造“来源论”的质疑,法律还需进一步明确抄袭和原创的界限,以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和人类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益。
公众能否接受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众的认可,在公众完成对其在艺术史语境中的意义读解时,这件艺术作品才算是真正获得被授予地位的身份。尽管人工智能输入进去的是不断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但是为什么偏偏是《爱德蒙·贝拉米肖像》这幅作品被拿到了佳士得的拍卖会上呢,这里面还是蕴藏了大量人为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能在艺术界掀起轩然大波的原因。例如Obvious团体成员的“前策展”环节,即“创作的开始,艺术家会选择一组图像来喂给算法”,“后策展”环节,即“艺术家要在这些输出图像里面筛选、品味、找出他或她想要用的绘画”[6]22-26,意味着他们要在众多人工智能艺术作品中选择符合鉴赏主体观看心理和欣赏趣味的作品,同时也是符合主流社会价值取向的作品,公众现阶段的接受心理使得《爱德蒙·贝拉米肖像》得以被选择与世人见面。《爱德蒙·贝拉米肖像》被神秘电话买家以高价买走,先决条件是人工智能在形式、内容、意蕴等方面与鉴赏主体有共享的意义空间,使得它得以面向公众,而不是艺术家的孤芳自赏。人类艺术家在面对人工智能的介入时思考艺术何为,对于后台的公众来说则涉及艺术鉴赏的能力和可接受度。授予人工智能介入的艺术作品被观看、被展示的鉴赏主体或鉴赏机构在评判一件艺术作品时,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作品能不能在心理上与公众产生共鸣。《爱德蒙·贝拉米肖像》之所以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不亚于毕加索等人类艺术作品,其原因之一是这幅较少人类干预的作品将本属于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时刻补偿给公众,公众被艺术作品此时此刻述说的存在性同化,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再次一跃成为众人期盼的追求,并将公众带回艺术荣耀场域。
第四,人工智能赋能艺术是艺术的终结吗?对于《爱德蒙·贝拉米肖像》来说,没有固定的创作背景可供鉴赏主体深究,从创作到传达充满了多义性和模糊性,鉴赏主体找不到与之同行的入口,鉴赏主体所熟悉的色彩、线条拼凑在一起,恰巧没有逾越认知鸿沟,就像在意识流作品中寻找并不陌生的残垣断壁一样,不从总体上观照艺术作品,强行解释作品延展的意义恐怕并不能将其称之为艺术作品。与之相悖的观点是,人工智能暂时没有意识是否就完全失去成为艺术作品的资格呢?恐怕也未必如此,在深度学习过特定领域艺术家的作品之后,人工智能掌握的创作思维可能并不亚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艺术家,运用现成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进行大批量的作品生成,将艺术家从繁复冗杂的创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无事可做或者回归到艺术创作自由中去。阿里AI鲁班每秒钟可以制作8000张海报,这是人类设计师无法企及的速度,鲁班依托从用户搜索、浏览、点击中获取的大数据,可以更加精准地为用户画像、做个性化推荐,满足用户的交互性需求,在电商平台购物时,用户在人工智能智能交互设计面向自身的推荐中,产生购买欲望。相对于人类艺术家来说,艺术也许会在人类的恐慌中终结,艺术不再沉迷于模仿或再现,更是摆脱了情感表现的束缚,变得可数字化、可编码化,艺术主体的场域被彻底撼动,人类艺术终结在了他们所创造的“人造物”手中。“所谓艺术终结于主体并非指主体的消亡或消失,而指艺术主体的更迭或替换,即艺术主体由人类转向人工智能”[7]130-142,按照这个说法,艺术并不是终结了,而是新的开始,只是艺术的行为主体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了人类艺术家,这当然是最极端的结果。人类艺术家与其深深陷入被接替的末世情结,不如运用好人工智能这一为公众更易接受的创作媒介,在艺术作品中积蓄力量,创作更符合时代潮流的传世佳作。
第五,传统艺术家消亡了吗?艺术界存在“勒德谬误”吗?19世纪初期,英国失业纺织工人在勒德的带领下,砸毁了被视为失去工作机会原罪的织机,但此举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推演为一场谬误式的实践,即机器带来的并非只是社会威胁,人类也从中获益。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可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人类艺术作品除情感以外的精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艺术作品鉴定上,人工智能识别毕加索赝品的准确度达到了100%。那能否将鉴定师的工作全权交给人工智能呢?由于人工智能主要是通过在信源中输入的画家的笔触和笔画来鉴别画作的真伪,对于某些笔触笔画模糊的画作或者需要考虑作家在彼时彼地的心境时,人工智能就派不上用场了,所以在狭义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鉴别艺术作品依旧只是人工鉴赏的辅助性的工具,而不能独当一面,取消人工鉴别。同样的道理,在艺术创作的阶段,人类艺术家暂时也不会被夺走最后的领土。摄影初现时对写实画家的冲击最大,某些画家为了追求对象内容的真实性,甚至转行去做摄影师,不仅如此,“摄影的简单易操作使‘再现自然’的神力不再是画家独有的法宝,一个没有经过绘画训练的人也可以轻松地拍下眼前的事物”[8]70。面对摄影带来的威胁,绘画界的自救也在进行,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印象派对以往绘画功利性表现主题的反拨,印象派画家冲破既定规则的牢笼,将随处可见的光作为绘画主题,改写了绘画艺术的历史。摄影不仅没有消灭绘画这个行业,而是促使画家思考绘画的本体意义是否仅限于“再现自然”,从而开启了绘画史的新征程。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同摄影一样将传统艺术家放在相似的处境上,技术让人类突破现有阶段的认知极限,技术的介入不会消灭艺术,更不会消灭艺术家,艺术界的“勒德谬误”在技术赋能艺术的时代不证自明。在科技引领潮流的环境时代下,艺术不会终结,人类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依旧富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人工智能的介入为“艺术共和国”注入了新生的力量,不少艺术家愿意尝试与人工智能合作,让艺术成为更好的艺术。
四、结语
人工智能对介入艺术活动、重新定义艺术、引发的艺术伦理性等问题只具有相对存在的意义,至于实现状况还是要看“奇点”能不能来临,“强人工智能”能不能实现。人工智能和艺术一样,也是人类社会在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人工智能赋能艺术,让艺术重新审视自身,缔造不可能。人工智能介入到艺术中来,使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信息茧房,解除了回声室效应的艺术家应以扛鼎之势,与人工智能一道再次创造新时代。AI+艺术未来如何发展,还是要看艺术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吸引更多的受众。
参考文献:
[1]斯蒂芬·戴维斯.艺术诸定义[M].韩振华,赵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瓦爾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3]George Dickie.Art and the Aesthetic: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M].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
[4]特里·巴雷特.为什么那是艺术 当代艺术的美学和批评[M].徐文涛,邓峻,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
[5]《十二国著作权法》翻译组.十二国著作权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6]韩真,艾哈迈德·埃尔加码勒.人工智能正在模糊艺术家的定义[J].世界科学,2019(03).
[7]马草.人工智能与艺术终结[J].艺术评论,2019(10).
[8]秦剑.绘画与摄影在互动中的流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林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