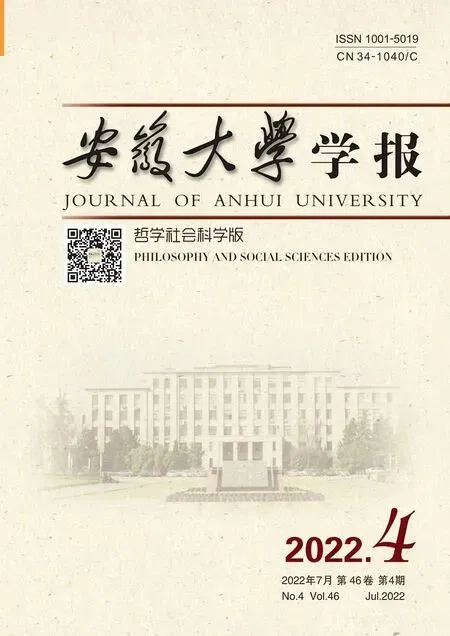笔记与南宋阅读转型
——以陆游《老学庵笔记》为中心的讨论
胡 鹏
一、引 言
笔记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肇始,中经唐、五代的潜滋暗长,作者与作品逐渐增多,至宋而呈井喷之势,遂由附庸而蔚为大观,成为两宋重要的文章体裁(1)关于笔记含义的界定,学界目前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笔记一般分属史部的别史、杂史、传记类,子部的小说家、杂家类等,而往往统摄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中。但由于现代西方学科划分体系视阈下的“小说”概念与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术语使用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淆乱不清、治丝益棼的情况。关于宋代笔记辨体情况,颇为烦冗,不赘述,可参胡鹏《宋代笔记辨体评述》,载《斯文》(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49~357页。笔者参考前贤时彦的相关争鸣,将本文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著述体式上分条记录、丛脞成书;内容上篇幅短小,以纪实性为主、间涉虚幻的文言随笔。凡因引述、行文需要而使用的“笔记”“笔记小说”“小说”等概念,皆指此文体。本文中凡《老学庵笔记》引文,皆出自(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为免辞费,行文中简称《笔记》并仅列卷次,不再一一出注。。宋代笔记内容丰富多样、不拘一格,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之类宏观社会生活领域,又涉及文人衣食住行、休闲逸乐、异闻轶事等日常生活诸层面。宋人不仅资书为诗,也资书为文。笔记文本中存有大量能够反映当代人阅读情况的内容,譬如黄伯思《东观馀论》,除辑入《法帖刊误》外,还收入讨论文艺作品得失的序跋、简论二百余条。又如王观国《学林》三百五十八则,皆为王氏读书心得,专以考辨字音、字义为主,与王应麟《困学纪闻》同为南宋颇为知名的学术笔记。魏了翁的《经外杂钞》《读书杂钞》,叶寘《爱日斋丛抄》,周密《志雅堂杂钞》、黄震《黄氏日抄》等,“望文生义”,即可得知其能反映各家的读书课程。欧阳修撰著《诗话》,开辟所谓“诗话”文体以后,记录诗歌本事、品评艺术章法、讨论写作技巧等的诗话作品,都可以透露出读者(批评者)对诗歌文本的阅读情况,而诗话便是从笔记中脱胎衍生而来。词话亦然。要之,如欲考察宋人阅读的历史现场,诗、词、零散的各类骈、散文不如宋代笔记专书来得直观、便利。
不过,上述列举的诸种笔记因论题集中专门,反而不易见出南宋一般士人的社会阅读情况。南宋前中期,士人主要分两大类:南渡士人与南方士人。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使华北地区兵燹相寻、生灵涂炭。中原衣冠士族纷纷仓皇南渡,在逃离战地、窜伏草莱之中,尠有人能够保全其家赀货贿,更遑论所收藏的图籍文物。这在脍炙人口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有生动反映,无须赘言。与之相反,长江以南的土著士人则因较少受到干戈俶扰,家藏书物得以大量保存。两宋时代的江南地区早已成为人文渊薮,在地士人藏书丰富;行在所临安(今浙江杭州)、建阳(今属福建)都是当时的出版印刷中心,一旦南宋国势底定,书籍市场便再度繁荣。南渡士人虽不保其图书,安定下来以后仍可以通过向南方土著士人借阅、在文化商品市场购入等方式获得书籍以观览,成为社会阅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地士人更是得地利人和之助,承平之下,读书无虚日。陆游作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土著士人,虽古往今来声名藉甚,但一生历官不过中下层职位,且去官较速、一度游幕边徼,又数十年退居乡里,与普通知识分子并无大异,其阅读情况,实可以作为南宋一般士人阅读史的典型代表。
长期以来,对陆游的受容一直局限于“爱国诗人”的刻板印象,虽亦有研究者关注其词、南唐史撰作,而放翁作为笔记作家的身份,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陆氏所撰笔记,虽属随手漫录,其实别有意味,有些还“臻于极高的艺术境界”(2)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洵为两宋笔记中的精品。陆氏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多元,但其中之一必然与其淹博的阅读量有关。陆游曾说过:“两眼欲读天下书,力虽不迨志有余。”(3)(宋)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35,钱仲联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09页。后文仅括注卷次。翻开《剑南诗稿》(后文简称《诗稿》),触目皆是与读书相关的诗句。《渭南文集》(简称《文集》)收录的题跋,也可以管窥个人阅读史之一斑。鉴于《笔记》关涉各种知识门类,颇为烦冗,本文仅考察其中所反映的放翁笔记阅读史的部分,条分缕析出作为普通士大夫的陆放翁,究竟阅读过哪些前人、当代的笔记,对其本人的笔记创作有何影响,冀可借此窥探南宋社会阅读的诸多面相,从而更新对当时一般知识、精神世界笼统的刻板印象。
二、物质载体、文本性质与身心状态对笔记阅读的规制
读者阅读一本书前,首先进入关注视野的并非纸上之文本,而是书本的“物质实体”(4)[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58页。。书本的不同形制——稿本、抄本、印本、搨(拓)本乃至当下的电子本——对于读者而言,其意义迥然不同。陆游时代的读者,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书籍的重视程度有着显著差别。由于种种原因辗转流传的前辈作者手稿,必然备受珍视,自不待言。如陆游《跋陵阳先生〈诗草〉》,记录自己得到韩驹(陵阳先生)诗作稿本之事,认为其作诗态度端正,“可以为后辈法矣”(5)(宋)陆游:《渭南文集校注》卷27,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2页。后文仅注卷次。。对于精心誊录的手抄本,读者也是推崇备至。《渭南文集》卷二六《跋尹耘师书〈刘随州集〉》云陆游看到抄书匠用来充作小憩枕头的尹耘师手抄《刘随州集》,“乃以百钱易之,手加装褫”。自然尠见对其文本有所苛责酷评。印本书易得,阅读固然更加便利,但物以稀为贵,“书籍实现批量印刷后,旋即丧失了其独一无二的品质,成为可即时更换的物品”(6)[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0页。,读者对于书籍的珍视态度定会大为削弱,且印刷术使得文本内容成为公有领域,读者对印本缺少毕恭毕敬的心理,由此进一步,便对印本所载的文本,也不再奉若圭臬,或疑之,或驳之,甚者或毁之。印本时代文本权威性的界定权,由作者一方转移到了读者一方。一卷印本笔记在手,作为读者的放翁首先从心理上就不会对之顶礼膜拜,阅读过程中时时审视、评判其文本,也就在情理之中。两宋之交的叶梦得恰处在中国书籍史从写本时代向印本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节点,他从自己的切身观察出发,认为唐代以前因写本文献难得,故藏者、读者会认真对待其文本,而自宋代开始,书籍付印寖多,写本藏书不复被人重视:“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7)(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陆游对此说法也颇为赞同。他在《跋唐〈卢肇集〉》中说:“前辈谓印本之害,一误之后,遂无别本可证,真知言哉。”(《文集》卷二八)明是叶氏观点的拥趸。由于印本书的传播速率大大超过稿钞本,一旦出现错误,很难在读者群中进行校正,反而以误为是,流害无穷。对于该《集》印本中《病马诗》的拙劣异文,放翁就愤怒地指称:“坏尽一篇语意,未必非妄校之罪也。可胜叹哉!”(《文集》卷二八) 北宋笔记作者主要是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等等第文坛第一流作家,他们的作品甫一问世,立刻就会哄传都下,被雕版售卖,或者广泛传抄。到了南宋初期,还出现了专事笔记出版的书商,如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铺,王国维即考证出其除刻有集部的《箧中集》一卷外,先后出版了《北户录》三卷、《却扫编》三卷、《钓矶立谈》一卷、《渑水燕谈录》十卷、《曲洧旧闻》十卷、《述异记》二卷、《续幽怪录》四卷、《茅亭客话》十卷(8)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黄爱梅点校、崔文印复校,载《王国维全集》(第7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此种易得的实物书籍,并不会得到陆游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特殊对待。
不仅物质载体对读者阅读行为有潜在的影响,文本的性质也会牵涉到阅读时的身心状态。阅读正经、正史时,陆游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相较而言,一般属史部杂史类、子部小说家类、杂家类的笔记作品,传统上被视为稗官野史、荒诞不经,阅读这类作品时便非常随意。陆游对笔记小说的轻视不时溢于言表:在《除修史上殿劄子》中,他就表示野史小说“谬妄”(《文集》卷四);谈及皮日休投靠黄巢任伪翰林学士的谤言,陆游复叹道:“《新唐书》喜取小说,亦载之。岂有是哉!”(《文集》卷三○)放翁是真心实意认为此类小说家言乃“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更何况先圣有教导:“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陆游在读此类书籍时往往怀着消遣放松的心情,如唐人陆羽(自号竟陵子、桑苎翁)的《茶经》。《崇文总目》将其著录于“小说类下”(9)(宋)王尧臣:《崇文总目(附补遗)》,钱东垣等辑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2页。,《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也著录在“小说家类”(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3页。,可见到放翁之时,宋人皆以该书为子部小说家类。 放翁不仅平时对这位先祖的著作爱不释手,矜夸:“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稿》卷七一);阅读时也是身心俱闲,毫无精神压力:“闲客逍遥无吏责,茂阴清润胜花时。茶经每向僧窗读,菰米仍于野艇炊”(《诗稿》卷七);甚至亲自动手续写起《茶经》来:“续得茶经新绝笔,补成僧史可藏山。”(《诗稿》卷三七)“遥遥桑苎家风在,重补茶经又一编。”(《诗稿》卷四四)
除此之外,陆游还经常与儿子一起读书,这是一个十分温馨幸福的阅读场景。途经黄州的行旅之中,读书稍倦,儿子就会主动接着朗读下去:“琅然诵经史,少倦儿为续”(《诗稿》卷一○);退居乡里时,也以亲子共读为乐:“旧书日伴吾儿读”(《诗稿》卷二一)“独取残书伴儿读”(《诗稿》卷三五);父子大部分时间共处一室,同用一枝灯盏:“读书父子共昏灯”(《诗稿》卷三○)、“短檠相对十年余”(《诗稿》卷四六)。每当二人相对亲子阅读的时刻,即使食且不继,他仍然感到满心欢喜。这里我们还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尽管陆游的时代已经可谓之“知识大爆炸”,大量书籍充斥寻常家庭,但并未出现欧洲向近世社会转型过程中阅读形式由“高声朗读”到“现代读法仅仅是用眼默看”(11)[法]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2页。的变化。从前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至少在阅读经部、史部著作时,此期读书人仍是放声朗读的,加上在欣赏诗文集时,一般需要摇头晃脑地“吟哦”——另一种有节奏韵律的朗读,似乎只有在阅读子部尤其是小说家类的笔记时,才会采用默读的方式。阅读时口耳并用能够直接感受诗文的气韵格调、作者的感情态度,明显加深记忆;而默读因“口腔喉舌绝不运动,只用眼睛在纸面上巡行”(12)叶圣陶:《中学国文学习法》,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91~92页。,虽然大大提高了阅读速度,但记忆效果则打了折扣。陆放翁以及其他笔记作者创作的笔记文本中存在不少疏失,致误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因默读原材料而记忆不深,以致误记的可能性是不可忽视的一种。
三、《笔记》中所见放翁笔记阅读史考原
在梳理了读者目之所及的书籍形制、阅读时的身心状态等准备程序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真正打开陆放翁手中正在阅读的笔记,看一看他究竟读的是哪些文本了。虽然忽略了经部、史部的经典之作以及几乎所有的别集、总集,此期陆游的阅读史仍可以“繁多”二字来形容。兹就《笔记》中明确提及的笔记作品略按时代先后顺序表列如下:

序号书名朝代责任者出处卷次1《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卷六2《隋唐嘉话》唐刘餗卷四3《酉阳杂俎》唐段成式卷二、卷六、卷八4《河东记》唐薛渔思卷十5《北户录》唐段公路卷二、卷六6《唐逸史》唐卢肇卷十7《南楚新闻》唐尉迟枢卷十8《稽神录》宋徐铉卷十9《太平广记》宋李昉等卷八10《该闻录》宋李畋卷十11《砚录》宋唐询卷八12《嘉祐杂志》宋江休复卷六13《杂识》宋曾巩卷四14《燕魏录》宋吕颐浩卷十
除上表中所列诸书外,还有一些并未明载材料来源的条目需要探讨。《笔记》卷四“隋唐嘉话”条:
《隋唐嘉话》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号“崔公望省楼”。又小说载:御史久次不得为郎者,道过南宫,辄回首望之,俗号“拗项桥”。如此之类,犹是谤语。予读郑畋作学士时《金鸾坡上南望》诗云:“玉晨钟韵上空虚,画戟祥烟拥帝居。极目向南无限地,绿烟深处认中书。”则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前半段所引文本,与《隋唐嘉话》卷下“崔潞府日知”(13)(唐)刘餗:《隋唐嘉话》(与《朝野佥载》合订),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1页。条、《太平广记》(下文省称《广记》)卷一八七“崔日知”(14)(宋)李昉:《太平广记》,汪绍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03页。条引《国史异纂》(《隋唐嘉话》异名)文字大同小异。后半段则但云“小说”所载。此“小说”,实为唐赵璘所撰《因话录》。《因话录》卷五曰:“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承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15)(唐)赵璘:《因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页。《因话录》较为常见的明商濬《稗海》本及此后以此为祖本进行点校的六卷本诸如《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等,此条“殿中”后均有“诸郎”二字。鲁明认为殿中即殿中侍御史,诸郎则是尚书省郎官,与文意不协,其据《太平广记》《南部新书》《近事会元》《长安志》《类说》《锦绣万花谷》《翰苑新书》等所引文本进行对校,考定“诸郎”二字为衍文,予以删去。见鲁明《〈因话录〉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4页。今采其说。这并非《笔记》唯一一次不具名地引用《因话录》,卷九“唐小说载”条:“唐小说载:有人路逢奔马入都者,问何急如此。其人答曰:‘应不求闻达科。’”此条记事实出自《因话录》卷四“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16)(唐)赵璘:《因话录》,第25页。条。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建国伊始即开制举,后时设时废,至仁宗天圣七年(1029)始固定为“天圣九科”。宋承唐制,制举确实允许士人自荐。庆历六年(1046),在监察御史唐询的抨击下,宋仁宗方下诏叫停举子自应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等后三科,要求“仍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六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35页。。据陆游《家世旧闻》卷下“彦猷侍读(询)言”(18)(宋)陆游:《家世旧闻》(与《西溪丛语》合订),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25页。条可知,唐询是陆游外曾祖父唐介的从兄,属陆氏外家。《笔记》卷八“唐彦猷《砚录》”条还曾记录唐询重视红丝砚之事。此处载士人奔竞应制科的笑谈,正是向姻亲先辈奏罢陋习的致敬之举。
《笔记》卷十“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条,“唐小说”同样指《因话录》,出自后书卷四“李纾侍郎好谐戏”(19)(唐)赵璘:《因话录》,第28页。条,王谠《唐语林》、曾慥《类说》均辗转稗贩此事。
《笔记》暗引《因话录》却处处以“唐小说”指称,更重要的疑问是,陆游阅读的究竟是单行本《因话录》,还是笔记总集、类书中引录的部分条目?《因话录》六卷流传有序,未曾亡佚。前引“拗项桥”的故事,在六卷本《因话录》中是有衍文“诸郎”的。陆游所引却没有衍文,由此可知,其并非在单行本《因话录》中看到这则轶事。陆游生前能够看到引录此事者,有《广记》卷一八七《职官》“省桥”条、《南部新书》卷一、《近事会元》卷二“拗项桥”条、《长安志》卷七、《类说》卷一四“拗项桥”条,或许还包括《锦绣万花谷》卷一○(20)据今人考证,《笔记》“一书应作于绍熙三年冬至绍熙五年之间,即1192年冬至1194年”。见阮怡《〈老学庵笔记〉研究》(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页。《太平广记》500卷目录10卷,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奉敕编纂,次年完成。《南部新书》10卷为钱易所撰,又经过其子钱明逸的整理,至迟在钱明逸嘉祐元年(1056)自序时已经形成定本,后被收入曾慥的《类说》中。《近事会元》5卷,作者李上交行实俱不详,自序称书成于嘉祐元年;该书直至清代收入《四库全书》,尚无梓本,均以手抄流传,似乎布传不广。《长安志》20卷,宋敏求撰,书前有熙宁九年(1076)赵彦若序。《类说》60卷定稿成于宋高宗绍兴六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重刊本序云《类说》问世后即有绍兴庚辰麻沙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各40卷,佚名编,书前有淳熙十五年(1188)序。不知放翁完成《笔记》前是否已见过该本。。诸书皆无“诸郎”二字。“应不求闻达科”事,则可从《广记》卷二六二“昭应书生”(21)(宋)李昉:《太平广记》,第2054页。条、《类说》卷一四征引《因话录》“应不求闻达科”(22)(宋)曾慥:《类说校注》,王汝涛等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7页。条获知。《唐语林》则未见陆游诗文中引证。另外,曾慥在靖康之变中有投敌嫌疑,因此免官;又被秦桧起用,前半生为叛臣,后半生属秦党。陆游与之道不同,不大可能阅读或者即使读过也不大可能引用这种身处对立阵营“小人”编纂的杂著;何况《类说》于绍兴十年(1140)由麻沙书坊始刊,此种麻沙本恐入不得曾在《笔记》中讥讽建本误人的放翁法眼。遍查陆氏著述,亦未见一语提及曾慥者。综上,陆游应是并未见到《因话录》原书,而是透过《广记》中收录的条目来获悉逸闻轶事。尚有旁证可参。《笔记》卷八“陈师锡家享仪”条有“予读《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卷,有《卢顼传》……”一语,此处明言已读至《广记》第三百四十卷,则卷一八七、卷二六二征引《因话录》内容,自然是早就寓目了的。
另外疑为通过类书、总集得见的笔记作品还有段成式《酉阳杂俎》与徐铉《稽神录》。《酉阳杂俎》自晚唐成书后直至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方有永康周登刊本,其间流传方式无非小范围传布的手抄本与类书、总集选录两种。周登本《后叙》中就说:“余旧不识此书,唯见诸家诗词多引据其说。”(2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校笺》,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83页。即便到南宋中期,一般读书人还很难见到《酉阳杂俎》。其在宋代的流传,主要依靠类书引述。《广记》《绀珠集》《类说》《海录碎事》(绍兴十九年纂成),《锦绣万花谷》《事物纪原》(庆元三年建安刊刻,1197),《记纂渊海》(嘉定二年刊,1209)等等都载录有大量条目,尤以《广记》为甚。《稽神录》情况更加特殊。徐铉积数十年笔力撰此书,时方修《广记》,经徐铉请求,“此录遂得见收”(24)(宋)袁褧:《枫窗小牍》(与《清波杂志》合订),袁颐续、尚成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页。。《稽神录》并未单行,因此放翁所读,实为收入《广记》的本子。
以上所述,皆唐五代笔记。《稽神录》虽稍晚至宋初,但主体部分完成于徐铉仕宦南唐时期。陆游阅读的文本,大部分很可能是载录于《广记》等笔记小说类书、总集之中的,单行本极少。
四、《笔记》所反映的社会阅读史现场
通过上述较为细密的复原,我们发现晚年陆游除却经、史、文集的阅读外,还博览了大量前人笔记。但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对这些向来为人所轻视的“小说”津津有味地阅读,于陆游个人乃至当时的知识界而言,究竟反映出怎样的历史图景?
首先是昭示着儒家博物观念在阅读活动中的潜归。自孔子提倡读《诗》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以来,“耻一物之不知”(《法言·君子》)的博物观或曰博物传统便成为古代中国知识人学问传习的重要内容。余欣甚至认为“方术之外,博物之学亦为中国学术本源之一端,同为构建古代中国的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25)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页。尽管确如部分学者所言,自中古时期开始,博物逐渐成为“被压抑的传统”(26)葛兆光:《序》,载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7页。,但从晋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五代徐铉《稽神录》、宋刘斧《青琐高议》、章炳文《搜神秘览》、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夷坚志》、李石《续博物志》等笔记,博物传统一直一脉相承,在经史知识的主流话语之外,不绝如缕地顽强延续。陆游对博物知识素来颇感兴趣,他曾希冀能与同道共同探究“自六经、百氏、历代史记,与夫文词议论、礼乐耕战、钟律星历、官名地志、姓族物类之学”(《文集》卷一三);其《采药有感》云:“蒹葭记霜露,蟋蟀谨岁月。古人于物理,琐细不敢忽。我少读苍雅,衰眊今白发……”(《诗稿》卷六七)“蒹葭”“蟋蟀”二句,指《诗经》中的《秦风·蒹葭》和《唐风·蟋蟀》;一起即引《诗》并说自己自少至衰探研“三苍”“二雅”等名物辞书,可见终身浸淫于博物之学。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例,《笔记》卷四提到读过的《小桃》诗:
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耳。及游成都,始识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着花,状如垂丝海棠。曾子固《杂识》云:“正月二十间,天章阁赏小桃。”正谓此也。
常态下,桃花于孟春方始盛开。陆游偶读《小桃》诗,初以为是某种早开的品种,耳食之言而已;及至成都,见到真正的初春即盛放的小桃,方将之前炫奇记异的文本转化为日常的、地方的、实用的知识。这一转化,所凸显的是陆游不仅仅注重书面记载,更强调在现实实践中对知识的验证,与中晚唐段公路、房千里、刘恂等博物笔记作者一样“在对‘博’的追求同时,又坚持着‘信’的标准”(27)余欣、钟无末:《博物学的中晚唐图景:以〈北户录〉的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可谓承袭了传统博物学“博而且信”的传统。作为“博物君子”(《左传·昭公元年》),放翁对于人文方面知识的传扬、考证、品评、反馈,在所多见,如《笔记》卷二“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条,对北宋士大夫头巾的戴法、背子须系腰、袴与裹肚的颜色等服制情况详细的介绍,表现出对前辈生活风尚的怀想。时世妆变动不居,过往的衣着搭配无法再成为当下的潮流。这样的追忆,相当程度上只能是一种“死”的知识。对它的掌握,并无当下实用的意义,而纯然出自博学多闻的需要。似此之处甚多,不备举。要之,陆游的笔记创作,氤氲着浓郁的博物传统。与中古时代中国博物学主要求“物”之“奇”“异”不同,“宋代博物学则将‘物’作为认识的对象”(28)温志拔:《宋代类书中的博物学世界》,《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1期。,陆游之“博物”,并非简单的复述已有的知识,而是有所品评、辩证、乃至驳斥,这体现了从“博物”到“格物”的价值取向,也是与宋代新儒学发展若合符契的。陆游虽未必是道学中人,但与道学诸老过从甚密,对朱子之学推崇备至。彼时新儒学“格物致知”的考论精神已经成为有宋士人圈层的普遍追求。陆游的脑海中,同样激荡着求真务实的浪潮。
其次是刺激了笔记的创作与回应。有些读者在阅读过大量笔记过后,一时技痒,产生了自己也进行创作的想法并付诸实践。《云斋广录》的作者李献民在自序中就声称自己受国朝杨亿、欧阳修、沈括及师聃都著有笔记以及唐代《甘泽谣》《松窗录》《云溪友议》《戎幕闲谈》等的影响,将曾听闻的“士大夫绪余之论”“清新奇异之事”“编而成集,用广其传,以资谈讌”(29)(宋)李献民:《云斋广录》,储玲玲整理,《全宋笔记》第9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282页。。上官融也说:“余读古今小说洎志怪之书多矣,常有跂纂述之意。”(30)(宋)上官融:《友会谈丛》,黄宝华整理,《全宋笔记》第8编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5页。尽管陆游并没有留下像李献民、上官融这样的自白可以直观地了解其创作动机,但大量阅读的事实与自撰笔记的结果之间,很难说绝无关联。陆游作为南宋第一流文学家,其所撰笔记的影响很大,后人的回应很多。有趣的是,后来者固然有引证放翁之文以自重者,但纠谬之处似乎更多。仅以《笔记》为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煎糖始于汉不始于唐”条云:
《老学庵笔记》,其中一条云:闻人茂德,博学士也,言“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凡唐以前书传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闻人固不足责,老学庵何至信其说而笔之?(31)(宋)史绳祖:《学斋占毕》,汤勤福整理,《全宋笔记》第8编第3册,第128~129页。
其后洋洋洒洒,引经传注疏驳斥中国砂糖始于唐代的传闻。然而史绳祖并不对此论的始作俑者闻人茂德有所腹诽,却对传述其论的陆游非常不满,尽管陆游毕竟只是诗人,闻人茂德才是“尤邃于小学”(《笔记》卷一)的学者,本不该犯此错误。这一来可以看出《笔记》的影响远远大过专业学者的学术讨论;二来可见后人对陆游的期待值甚高,以至于脱离实际,对其学术水平寄寓了过分的幻想。相似的例子还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揭露陆游所记中书、门下班次迁改之误(32)(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注》(第6册),翁元圻辑注,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41页。;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也批驳陆游因未详览《江表传》而弄错了“帕头”所指(33)(宋)韦居安:《梅磵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1页。。以上事例清晰地表明,不少宋代笔记是在阅读了前辈作品之后受到刺激而产生,此种情况一般是中小作家撰写笔记的缘起之一。一流作家的笔记,成了后人严格审视的对象,不管是引述典故,还是纠谬指瑕,均是学习型阅读的结果,其本身也成为后世笔记中知识生产的渊薮。阅读—回应—自撰,乃是宋人笔记生成的重要进路之一。
然事不止此。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形,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印刷出版愈加便利、科举制度定型导致的受教育人口急遽增长等多方合力,促发了文化消费市场的蓬勃兴旺。处于宋元明转型(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34)“宋元明转型”是近年来国际史学界兴起的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以期在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基础上进一步反思过往未足够重视南宋至明中叶(12~15世纪)约四百年历史、甚至视之为近世时代停滞期的历史认知,并将之继续向前推进,认为宋元明时期并非停滞阶段,应在整个近世化进程中对其予以重新定位。可参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历史大潮之初的知识生产,除因应进入仕途所需的经史讲章外,更多的是着眼于日渐崛起的包括地方化士大夫阶层和城市居民在内的新兴读者群。该读者群的阅读消费呈现趋俗的态势:一是俗文化的流衍,包括虽日渐雅化但仍能应歌的词、以口语白话为主的话本小说和勾栏瓦肆搬演的杂剧、南戏。二则是雅文学的下移,除愈来愈多知识人特别是下层文人对“诗人”身份不再避忌而开始在生前刊刻诗文别集以外,能够满足消费者猎奇心理的短篇文言笔记小说集也成为重要的文化商品。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促进生产。在出版发行一端和消费者一端的互动之下,两宋从收集刻印前代笔记始,逐渐出现了业余乃至专业笔记作家,如陆游前辈王铚家族、与其同时的洪迈家族等等。宋人自撰笔记大量流通于市场。据顾宏义的“不完全统计,宋代笔记多达1000余种,5000余卷”(35)顾宏义:《两宋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20年,第3页。,可说是异常繁荣。黄镇伟认为宋人笔记小说的勃兴,具有“自述读书经历”“劝勉读书,追求博学”“弘扬阅读精神”“考辨书籍讹误,指导阅读”“传播阅读的方法与理念”(36)黄镇伟:《中国阅读通史·隋唐五代两宋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302~313页。五个方面重要的意义,在古代阅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诚哉斯言。
如此繁多的笔记文本出现在文化消费市场上,导致了宋人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的重大变化。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曾表示:“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37)(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1,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苏轼所见老儒之“少时”至少在北宋初年。然情况很快就发生了转变:“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38)(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1,第360页。——对于《史记》《汉书》等经史名著束书不观——除了科举应考必读以外,宋人大量阅读的其实是非经、非史的子书尤其是笔记作品。大型笔记类书的编纂及其被阅读,对该文体的传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前文已几乎可以推定,陆游是通过《广记》等大型类书而非单行本来完成对大量唐、五代笔记的阅读的。尽管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突飞猛进,还出现了便捷低廉的活字印刷术,但实际上,书籍出版仍有一定困难。常见经史之书因科举需要,自然不断有官刻、坊刻的各种版本问世。子部与集部书籍,非有大力者或因缘际会,则很难上梓;即便刷印,印数也很小。经过一段时间市面流通后,大量子书、诗文别集就很难寻觅了。其文本只有进入选本、类书,方能够实现较大范围与较长时段的传布。《广记》卷帙浩繁,合计引录了自汉至宋四百七十余种笔记作品,集历代笔记之大成,尤其是将一些珍秘罕见、流传不广的著作收入其中,不仅有助于宋前笔记的保存与校勘,也更加便利了它们的传播受容。陆放翁经由《广记》阅读众多唐人笔记小说,转述与改写进《笔记》等作品中,正反映出宋代大型笔记类书“使唐代小说成为许多话本、戏曲故事题材的渊薮”(39)[马来西亚]陈依雯:《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84页。的文体功能。除大型类书外,宋人自撰笔记在放翁阅读史中也占据较大比重。这些笔记或因抄录、或因本地新近印刷、或因他人持赠等途径而进入放翁的书房。尽管时人常常对笔记嗤之以鼻——陈振孙就评价洪迈撰写《夷坚志》的行为“不亦谬用其心也哉!”(40)(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但其实并不妨碍其如饥似渴地阅读,陈撰《直斋书录解题》中就大量著录了笔记。甚至深闺之中的女性,也在常见女德书籍之外泛览笔记小说。晁补之《李氏墓志铭》就说道:“闻之夫人于书无不读,读能言其义,至百家方技小说皆知之。”(41)(宋)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66,明诗瘦阁仿宋刊本。虽不无谀墓之嫌,然“小说”厕其间,亦可见宋代普通官宦人家女子的阅读范围。隋唐之世,社会阅读仍集中于精英化的经典文本,这一点从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中可以清楚看到。宋人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社会阅读更趋向求新求异,传统经典已经无法满足阅读需求。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登第的张淏在所著《云谷杂记》卷末曰:
予自幼无他好,独嗜书之癖,根着胶固,与日加益。每获一异书,则津津喜见眉宇,意世间所谓乐事,无以易此。虽阴阳方伎、种植医卜之法,輶轩稗官、黄老浮图之书,可以娱闲暇而资见闻者,悉读而不厌。(42)(宋)张淏:《云谷杂记》,李国强整理,《全宋笔记》第7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80页。
这里令张淏“津津喜见眉宇”的“异书”,自然不是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这些常见书目,其自叙的阅读范围,就包括了“輶轩稗官”——笔记小说在内。叶廷珪在《海录碎事》自序中说:“每闻士大夫家有异书无不借,借无不读,读无不终篇而后止。”(43)(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首,明万历卓显卿刻本。可以见出南宋初年士大夫对异于经史常谈的新奇知识的特殊嗜好。绍兴二十九年,时年三十五的陆游曾记载“三二十年来”士人不乐经典之学的鄙陋风气:“诋穷经者,则曰传注已尽矣;诋博学者,则曰不知无害为君子。”(《文集》卷一三)逆向推理,读书人所乐于翻阅者,当是非经非史之作了。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宋人的知识结构已经由中古时代以儒家典籍为主的较为狭隘的经史精读向博读诸种知识演化;子部尤其是说部书,已经成为宋人积极追求、津津“悦”读的新贵对象。随着笔记数量的剧增和笔记作家的规模化出现,其文学市场的繁荣大大拓宽了宋人的阅读面,整个社会阅读迈入非经非史的平民化、亦即近世化进程。到了明代,笔记小说又以小品文的面貌出现在文学史长河中,“以生活化、个性化、审美化为主要特征”(44)吴承学:《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与长篇小说一起进一步呈现出社会阅读的近世化徵象。“笔记构成了宋人阅读世界的一块大陆,是建构其知识结构的生力军”(45)胡鹏:《略论北宋笔记的传播及其意义》,《师大学报》(台北)2020年第1期。。
五、结 语
陆游作为南宋时期的典型士人,考察其笔记阅读与创作情况,有助于揭示士人圈层普遍的阅读史与其知识结构、思想转型的隐秘关联。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读者热衷于阅读笔记,但因对笔记文体根深蒂固的轻视,仍会在诸多场合表达对“稗官野史”的不屑与不满。正因为这种轻视,导致了默读笔记时记忆的不深刻甚至变异,一定程度上形成不同笔记载录相关人事时的“传闻异辞”。由于记忆不深刻,在提及某些逸闻轶事的出处时,陆游便只好以笼统的“(唐)小说载”来敷衍成文。这从侧面也表明陆游对前代笔记的阅读并非检索式的,而是日常按部就班的学习型阅读,一旦创作需要,仅凭记忆调用知识储备。倘若为了创作而从类书、总集中检索相关文本,断不会以模糊的书名示人了。上文还曾引述陆游自承“予读《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卷”的话,读《广记》而能至三百余卷,更加证实了笔者“学习型阅读”的论断。以《广记》为代表的笔记类书、总集,成为南宋士人案头日常读物,其在建构士人知识构成方面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这提示我们,即使书籍刻印出现了长足发展,南宋士人广博的知识,仍然需要倚重于类书、总集、选本等的间接获取。间接获取二次编纂文献的代价之一便是原书文本、富文本部分信息的丢失,同时产生新的文本、富文本,因此加剧了知识的变异。多种知识并存以及在此基础上层出不穷的考异、疏解、笺证、评注,都更加促进了知识生成的进程,造成宋代文艺、学术的繁荣之势。两宋以文立国、以文名世,除了长期奉行右文之策的政治原因、社会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的经济原因之外,知识生产的内在演进理路,也应当纳入考量范围。
笔记以其广博溥被的知识覆盖面,改变了中古文人社会阅读局促于正经正史、儒家典籍狭窄天地的传统样态。它召唤虽不绝如缕却一度草蛇灰线的儒家博物观念在阅读活动中大规模复归,读书人热情记录、探讨日常生活与文本阅读中遭逢的种种自然、人文现象,并以格物致知的态度审视面前的材料。广大中小笔记作家在前贤时彦的刺激下,或出于回应的目的,或出于扬名的需要,纷纷开始撰作笔记,甚至出现了父子兄弟皆有笔记传世的家族式写作现象。作者大量增加,作品充斥书籍市场。陆游本人固然是四部并重,无书不读,但其他普通读者则往往除科考所需之外——一般读书应举大多也仅以诵习时文范本为尚——束经典不观,痴迷于此类道听途说者流。相较于士大夫群体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精英分子,这些占士人绝大部分的普通读者,其思想世界可谓之日渐趋向于世俗化、非经典化的小传统,直至达成“市民立场的确立”(46)沈松勤:《宋元之际士阶层分化与文学转型》,《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这种新动向,与宋代经学领域中盛行突破汉唐注疏的疑经思潮、史学领域中不断更新史书编纂观念和史料去取标准、诗文创作中对唐代文艺审美倾向的反动以及书写场域的拓殖等等桴鼓相应,都可视为思想世界向近世转型的表现。
我们对陆游及其《老学庵笔记》为中心的考察,试图从一个较小的切口来蠡测当时社会阅读出现的新变化。当然,“我们不能倚借当代学术的海量文献及严谨态度,去想象与规范一位古代诗人的文学阅读经历”(47)叶晔:《〈牡丹亭〉集句与汤显祖的唐诗阅读——基于文本文献的阅读史研究》,《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本文着重探讨放翁笔记阅读的书籍实物与知识构成,及其反映的南宋时代知识人的阅读史图景,当然无法完全重构彼时的文学现场;个别讨论,可能还有较大的疏误。笔者不拟作知识考古式的重建陆游经眼书录的工作——这必定是挂一漏万以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正的用意不仅在尽力搞清楚作为笔记作家的陆游阅读哪些笔记文本这样细微之处的历史真实,而更看重此中反映出南宋知识界阅读史概貌的艺术真实。对陆游笔记阅读史个案的追溯,可以借机管窥地方化士人圈层的知识构成与精神世界,进而对宋元明转型的历史脉动有更真切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