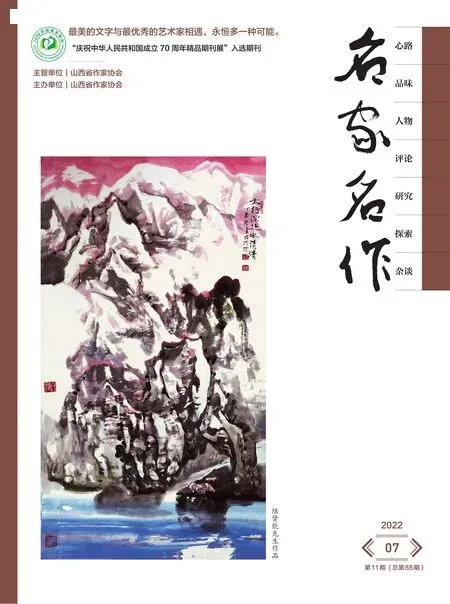震撼人心的堕落—马洛与库尔兹之间“看与被看”关系
刘鑫慧
“看/被看”这对二元对立统一的关系中,“看者”是以自己所在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评判“被看对象”,“看 /被看”是《黑暗的心》这部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情节、结构模式。《黑暗的心》中最为重要的是叙述者马洛与库尔兹“看与被看”的关系。康拉德没有着重表现情节,而是通过马洛的主观感受和主观叙事,对社会环境和思潮赤裸裸地表现,在“看与被看”关系中表现形形色色在非洲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勾勒出他们或撕裂而挣扎的灵魂,或卑鄙而平庸的人格。
一、马洛的眼睛
“马洛”既是作者设置的故事主人公,又是故事的叙述者。“马洛”在故事设定的世界里有自己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身份地位和主观感受。不同于《呼啸山庄》中采用的多层叙述者视角流转的方式进行有限叙事,虽然每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局限,但是丁柰莉、洛克伍德等叙述者视角互为补充,且尽量保持客观,《黑暗的心》是马洛一人进行叙事,完完全全表现的是马洛对非洲、对库尔兹等人的主观感受。因此,马洛的眼睛并不是客观的,它是“可以骗人的”,马洛有他自己无法摆脱的局限性。马洛这种“欺骗性”也是康拉德想要呈献给读者的重要内容,马洛只是一个看客。
生在欧洲,长在欧洲的马洛,欧洲是他的出发点,是他无法回避的根,这对他来说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他许多无意识的选择、想法以及衡量的依据,深受欧洲影响,不自觉地用欧洲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明衡量非洲文明。他形容非洲人“像蚂蚁一样窜来窜去”,他们是“黑骨头”“黑家伙”,呆滞而又麻木。受过“教化”的黑人,提着一支来复枪压迫同类。当然,这些黑人也没有被那些“带来光明”的殖民者当作“人”来看待:在高强度的工作下,他们生了病,扭曲着苟延残喘。这些“东西”的生死无足轻重,必要时可以毫不犹豫地炸死他们。马洛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他深受人道主义的影响,看到非洲人受到非人的对待,当传教者温情高尚的面纱被揭开,露出狰狞的面孔,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落差,看到母文化的虚伪性,他又不得不以母文化的标准去衡量这些非洲人,他们麻木,不懂得抗争,这一切似乎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母文化是马洛的原罪和隐痛之处,他痛恨这种虚伪,但却处处充斥着这种虚伪,殖民者们在大陆人心中是“帮助数百万无知土人戒除陋习”的光明天使,但其实他们是在这片不受惩罚的土地上日渐堕落。另外,这些底层殖民者也是资本积累上的一环,历史进程中的垫脚石,以及母文化的弃子,游荡的孤儿,他同情他们,也为他们扼腕叹息。非洲恶劣的气候损耗着他们的身体,消磨着他们的意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浑浑噩噩地凑合活着,少数人用浆得雪白的领子,顽固地与整个环境对抗着,掩饰着自己灵魂的肮脏,还有一部分人和新来的欧洲人套各种各样的关系以表现自己的欧洲优越感。暴躁、易怒、草菅人命已经成为习惯,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和生命漠不关心,也对他人的未来和生命漠不关心,如同一具具活着的麻木尸体。
二、马洛眼中的库尔兹
基于马洛的视角,他在“看”库尔兹的时候难免会带上时代“原罪”的观点,对库尔兹有天然的同情。马洛眼中的库尔兹,最大的特点是“挣扎”。初来非洲,库尔兹曾经画过一幅画,是一位妇人,披着衣服,蒙着眼睛,举着一把点燃的火炬。但背景是昏暗的,几乎是一片漆黑,像极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他挣扎着摆脱在欧洲大陆“贫穷”所带来的耻感,却不慎在非洲这片不受惩罚的大陆上落入自己欲望的深渊,他想拼命从人性黑暗的洞穴中爬出来,通过来到非洲来摆脱欧洲,却最终被非洲湮灭。
“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贸易站,我的河流,我的——”什么都是他的,他想拥有欧洲纯洁的理想,天真而纯洁的未婚妻,同时象牙、贸易站、河流这些也都是他接触过的,这些满足过他疯狂的欲望,他永远也回不到以前了。他拥有慈悲广博的气度,雄辩华丽的辞藻,受欧洲文明熏陶,同时他用这一切掩盖着在人性深处最原始的欲望。正如康拉德本人所说“没必要将邪恶归结于超自然因素,人类自身就足以犯下每一种恶”。
文明是人性黑暗的一块遮羞布,它形成于人们认识到彼此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达成某种契约。在非洲的荒野面前,欧洲的一切文明价值都丧失了意义,只有弱肉强食这一生存法则。没有一个民族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其他民族,除非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库尔兹带着传播文明的骑士梦想,现实却告诉他只能凭借最野蛮、极端的个人主义才能活下去。要么屈服,要么征服。但是,当库尔兹征服非洲之时,也被这种野蛮的极端个人主义反噬,非洲的野蛮也征服了他。他在文明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不公,被社会契约压抑的一切欲望,在这里全部爆发出来。脱去文明的外衣,他渐渐成为一个“野蛮人”。一方面他在这里打造了一个王国,享受着权力的快感与被别人崇拜的征服感,另一方面他用屠城等手段疯狂掠夺象牙,制造巨大经济利益,精心维护着自己在公司里的形象,享受成功的认同感。他通过雄辩掩饰着自己的行为,制造出神奇的“谋反者”,用屠杀、掠夺、控制他人填补自己在文明社会压抑的欲望,在不自知的过程中走向灭亡。
“吓人啊,吓人!”库尔兹临死前回顾自己的灵魂,发出可怕的呐喊。堕落似乎是他不可摆脱的宿命,他审视自己的灵魂,欧洲精神在他的身上星星点点回光返照——这一切是那么令人感到荒诞、惊讶与困惑。“人必须求助于某种天生的力量,必须求助于自己坚持某种信念的能力”,环境是使他堕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不小心“迟钝到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那些黑暗的力量攻击”。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能够吞噬自己的欲望黑洞,库尔兹长时间沉溺于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中,开始是欲望满足之后的快感,往复几次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空虚,自己为之奋斗的东西根本就是海市蜃楼。正如本书开头所说“我们无法将生命最真实的意义,一生中微妙而贯穿一切的本质传达出来”,只有到死,每个人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每个选择,人生的本质,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按照自己设定的剧本,活成自己想要活成的样子,一切总是相差甚远。他再也回不去欧洲了,不是外界的环境不允许,而是他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存方式桎梏了他自己。在库尔兹身上,马洛看到的是完全崩溃的欧洲精神,他离开家乡太久,已经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将库尔兹泛化来看,何尝又不是一个个在欲望中走到极致的人所面临的困境。欲望压倒了人性,人最终变成了兽。所有人包括读者,都忘记了库尔兹也曾经是一个人,有他温情细腻的一面。小说的最后康拉德让马洛去探望库尔兹的未婚妻,那位善良、苍白而美好的女子,她是库尔兹甘愿冒着巨大风险离开旧大陆赚钱的原因,他想守护她,守护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但这在等级森严的旧大陆何其艰难。库尔兹,这位曾经善良的青年,如今的怪胎,也曾拥有这样美好的愿望,这是他梦想的起点,但是在这广袤而野性的非洲,文明携带的善意于生存无益,甚至是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方。非洲,这片未开化的土地,更像是黑暗森林,每个人都在黑暗中行走,默默积蓄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唯有自己的力量能够拯救自己。
如果说欧洲大陆的无力感来自制度的规训,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全方位的入侵,每个人都按照自己阶层的“成规”生活,那么非洲大陆就是另一个极端:这里没有任何“成规”,相生相伴的是没有任何温情的“底线”,能为在这里的人们架起喘息的“屏障”,这里看似处处都是机遇,但却是一个巨大的修罗场。这一切都把人推向求生意志和财富、权力欲望的极致,并为之放弃底线,或者说不得不放弃为人的底线。“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非洲这片未开化的处女地,生存和财富、权力是相伴相生的,不存在“体面生存”的可能性,身处其中的人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
三、马洛存在的意义
库尔兹和马洛是《黑暗的心》中的双主人公,通过数十年之后马洛的回忆来讲述库尔兹惊心动魄的堕落。讲述故事的马洛,已不在那郁热而广袤的非洲荒野,他回到了宁静祥和的泰晤士河。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让马洛的叙事产生了欣赏的距离,将故事本身蕴含的扭曲、绝望消解殆尽,从而达到宗教的效果。马洛仿佛在悲悯中俯视故事中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人的人生困境,包括故事中的叙述者“我”,这也是他自我忏悔的过程。
悲悯是一种极为高级的审美情感,它将故事中的激情净化、升华,最终超越这种激情。在讲述故事的马洛,已经不是那个深处故事之中惊魂未定的马洛,这时候的马洛对故事有了很多深层次的思考,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也有一定反思和剖析,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更远距离理性审视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也是更高意义上的清醒。
马洛的“欺骗性”一方面在于他无法改变的身份(欧洲白人视角所带来的原罪感),另一方面就在于他的“悲悯”。无论是库尔兹,还是故事中的“我”,以及形形色色的殖民者和非洲“黑东西”,都是在尘世中煎熬而找不到出路的可怜虫。他在故事的叙述中不自觉地加了很多这样的内容。在他的叙述里,库尔兹不再是堕落与邪恶的化身,“他是如此形单影只,执意要走入荒野深处,走向那荒凉的贸易站”。他走的是一条凄荒死寂的路,“在巨大的孤独中,在太初时代的鬼地方,慢慢迟钝到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那些黑暗的力量攻击”。他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行,荒野蛊惑了他不安分的灵魂,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兽性本能,点燃了他扭曲的欲望与畸形的热情,但他也是一位先驱者,独自探索与荒野的相处模式,不幸的是,他失败了。他曾与灵魂苦苦搏斗过,与自己的灵魂搏斗到疲惫不堪,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马洛看到了库尔兹灵魂中难以想象的奥秘,所以说“没有比他更崇高的事物,也没有比他更下流的事物”。
康拉德借助马洛通过时间和地点产生距离沉淀下来的“悲悯”和“反思”,用一种主观臆测的方式勾勒出库尔兹灵魂的全貌。同时,他在揭露欧洲殖民者戕害非洲人的时候,也反思殖民主义对欧洲人本身的异化。这样“库尔兹”这个形象不再仅仅象征着殖民主义的拓荒者,他有了某种先驱者的意味,也是时代和环境的受害者。先驱者独自面对一个全新未知的世界,尽管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在其他人已经愚蠢到失去了犯错误的能力时,他还保持着自己灵魂的独立性,但是他本人也在猛烈地动摇着,不知所措,只能借助信念的力量不断前行。他们来自旧世界,带着旧世界最为崇高的理想,却长期受新世界生存规则的浸染,他们独自品尝着新旧两种世界的文化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冲突,饱受这种异质文化隔膜所带来的孤独感折磨。康拉德所关注的其实都是基于事物、事件和人的“理想”价值。借助“库尔兹”,他表现出了先行者的茫然无措、为了生存的心狠手辣,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在旧世界“理想”和新世界“现实”之间产生的灵魂撕裂。在这种挣扎中陷入不自知的盲目,处于被玩弄的地位。他们为了理想剑走偏锋,搭上一切,最后却像一颗榨干了的柠檬被抛弃在大街上。“他们抛弃了库尔兹,他们抛弃了贸易站”,正如经理所说“库尔兹先生对公司而言已然弊大于利,我们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人的灵魂和理想在利益面前如此廉价。“他估计错误,现在动武,时机还不成熟”“他使用了龌龊的手段”“那个制砖商,会帮你把那份报告写得精彩绝伦的”,在库尔兹挣扎,付出了失去灵魂的巨大代价之后,其他殖民者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更显荒谬可笑,只剩下经理们的愚蠢与猥琐。
马洛和库尔兹也是一种互文关系。“把人放在女人的环境中,他就会是一个女人”,同样,把人放在非洲的环境中,他就会是一个非洲人,库尔兹被迫不得不成为一个非洲人,或许他的内心也有类似于马洛的挣扎与困惑、痛苦与徘徊,他和马洛是互相映射的两个人。库尔兹刚来非洲时,可能也看见过另一个和非洲“库尔兹”一样的人,他对这个人充满了悲悯的情怀,告诫自己要坚守本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毕竟,还有远在欧洲的梦幻——他的未婚妻,温馨的家庭召唤和指引着他。然而,当生存的压力扑面而来,梦想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求生力量,指引他走过最艰难的时光,熟悉了非洲的种种生存方式,他也逐渐被这种生活的惯性侵蚀异化,成为一个真正的非洲人,在这个无秩序的地方角斗着财富、权力,忘记了自己来时的初衷。
库尔兹终其一生想回到欧洲,想回到自己的梦境中,可他忘记,他已经是一个非洲人了,故土的一切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库尔兹不是没有机会回去,而是主动放弃回欧洲,他产生了严重的逆文化休克,甚至无法再适应“规则”。
四、结语
通过马洛的“欺骗性”叙事,康拉德向读者展现了马洛自我忏悔的心路历程。马洛是不可靠的,但并非是不真实的,他所表达的都是他自己的独特感受,通过“观看”库尔兹的一生,认识到自己的内心,乃至认识到整个人类的过程,他的叙述目的就达到了。“看客”马洛对库尔兹人生的“观看”,也为库尔兹凄寒彻骨的人生注入了一丝丝温情。这颗浓雾遮蔽着的黑暗的心,就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他看到了库尔兹灵魂的挣扎与绝望,周遭的冷漠与势利,冷酷而强势的荒野和弱小孤独的良知,脆弱的文明悲悯地抚慰着这一切。时间流转,沧海桑田,历史的巨轮下又有多少库尔兹这样的牺牲品,无人知晓,哈德良长城是否也见证了类似的事件?马洛的故事,不自觉地为库尔兹们唱了一首长长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