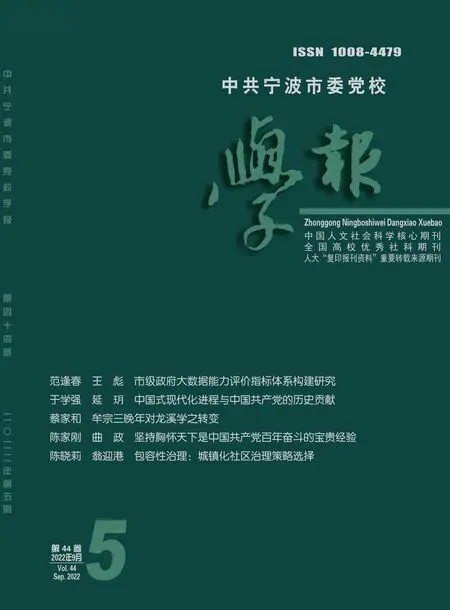牟宗三晚年对龙溪学之转变——论龙溪学对康德“三大批判”之补缺
蔡家和
牟宗三晚年对龙溪学之转变——论龙溪学对康德“三大批判”之补缺
蔡家和
(台湾东海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中 40704)
牟宗三先生之哲学建构中,主要以康德作为中、西学之交接点,尤其是道德实践这部分。牟先生晚年对王龙溪特别青睐,此是欲藉龙溪学而解决康德哲学之不足。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别对应着真、善、美,牟先生亦逐一消化、吸收,并做出颇具份量之回应。牟先生深入剖析中西文化之优缺点,如提出“良知坎陷”以补中哲之不重知识,亦认为西哲于人生神妙之境有所缺乏,遂有藉龙溪学以为灵感之汲取。其所提点到的龙溪学,包括:无相(向)、无执、圆教等心学义理。就此而论,牟先生可称为“当代新心学”,为当代中西会通、建构之学的成功典范。
王龙溪;康德;牟宗三;圆而神;方以智
一、前言
(一)牟先生的会通、建构之学
牟宗三先生(1909—1995)以“中西会通”见长,因而偏向建构之学,并以康德(1724—1804)作为中西学之交接点。此如朱子之以孔孟接佛老、接理学,又摄荀、庄以言心,并且融入汉代阴阳学,而来建构学问体系。
牟先生回应康德之“三个批判”,分别有如下重要著作:面对“第一批判”,回应以《现象与物自身》;面对“第二批判”,写下《圆善论》;面对“第三批判”,发表《以合目的性之原则为审美判断力之超越的原则之疑窦与商榷》(后文简称《商榷》)一文。
牟先生以康德作为中西疏通,确实有一些优点,略举如下:(1)便于中西比较:将康德与孟子、朱子、阳明等人做比较。视康德介于阳明、朱子之间;朱子为他律,康德自律,而阳明则可呈现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在康德,则仅是设准,并不呈现。(2)比较西方美学与中国道家之艺术哲学。(3)为道德实践保留出路:康德论尽知识,而为信仰、实践理性保留余地。此近于中国之以儒家担纲,在知识之外还要以行动实践来落实,以为“穷知见德”。又康德“义务论”:只论动机,不问结果。此与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可为衔接。
(二)晚年以龙溪心学为担纲



(三)选择龙溪,而非五峰、明道

《圆善论》中关于三家之圆教:郭象是为道家之圆教、天台宗为佛教之圆教,而儒家之圆教代表,则有五峰(1105—1161)、明道(1032—1085)、龙溪等。牟先生圆教体系中亦特别看重此三儒。又圆教者:讲求诡谲之相即,任一点皆可契入逍遥、佛性、物自身;境之每一点,纵不如意,都可心转契入福。龙溪的“四无四有”之相即,即是圆教的一种:心、意、知三者皆为无善无恶。五峰虽曾提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但是到了真善美之分别说、合一说阶段,五峰此说便须退场,改以采取“无相(向)判断”。这时,龙溪的“四无”又再次得到发挥。至于明道虽也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此近于“无向”,但明道之学的重点不是“无”,而是“圆顿一本”,如云:“出西门,便可到长安”“尽心,知性、知天”等。故三儒之中,龙溪最能满足牟先生的设想。
牟先生所重视之儒者,其实包括了周、张、明道、五峰、陆、王、蕺山等,但由于此时最重“自由无限智心之心转”,故只留下陆、王与阳明后学。起初亦好近溪,但可能近溪被归于祖师禅之精者,多谈破光景而少谈“无”,故后来只谈龙溪,龙溪谈“无”便多于近溪。又陆、王与龙溪三人之中,尤以龙溪为圆,遂最受到牟先生之倚重。
(四)以龙溪学补足康德
龙溪学何以能补足康德呢?须从康德的“三个批判”谈起。牟先生所认为康德之不足,在“第一批判”,他回应以《现象与物自身》一书,其前导则是《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此中问题意识:人只是感性直觉之存有,而不及于如上帝之智的直觉,上帝可直觉于物自身,而人不能。牟先生则认为,中国哲学亦得有“智的直觉”,虽不如上帝的“直觉即创造”,然人可以透过道德修养,而为从无到有之创造与升起。故中哲是一种“无执的存有论”,康德则是“执的存有论”,此中关键是面对识心之执,可否化掉?在中哲里,人不需透过“三层综合”来看待知识与世界,而能直接“转识成智”,拥有智的直觉。
到了“第二批判”,康德所倡议之“德福一致”,设准于上帝存在、灵魂不灭、人有自由意志等。特就上帝存在一项,牟先生认为中国不谈上帝,三教皆然,如儒家是以心学为宗,而道家“超越的道”是一种主观境界的形上学,纵有道,亦不是人格神之上帝,故提出“自由无限心之心转”来取代上帝之说。
“第三批判”中,康德以“超越的合目的性原则”来谈美,至牟先生则改以“神慧妙智”,来面对气化多余光彩,以此为美。这是一种“无向判断”。康德则是“有向判断”,甚至包括普遍性、必然性皆由概念而来,虽只是类比之相关。且真、善、美三者可以分别说,亦可合一说,而康德只到分别说。
在上述相关之反省与辩论中,牟先生皆用到龙溪学,其中重要观点包括:智的直觉、自由无限智心、圆善、圆教、心转、无执的存有论、无分别说、无向判断、真善美合一说、诡谲之相即,等等。下文再做进一步讨论。
二、早期对龙溪之看法
(一)《王阳明致良知教》
此为牟先生四十五岁时作品。书中对龙溪有如下判断:
如是此四无之说必是工夫纯熟之结果,如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圣,其根器不可谓不上,然至七十方能至此,则可见是工夫之所致也。此四无之说只是宋儒所谓“天理流行”已达“何思何虑”境地。此不可谓为工夫上之教法,亦不可谓是上根人顿悟之学,一悟至此,并不算数,悟至此境,并不即是终身有之,亦不可视四有之说为非究竟话头。若论工夫教法,则四有之说即是究竟话头矣,外此并无更高之教法也,四无之说非教法也。如此,则阳明之和会有不恰矣。[1](p76)
指出龙溪“四无说”不是工夫,只是境界之结果,既不可为上根人立法,亦非一悟全悟。工夫之扎实基础仍在“四句教”,而阳明竟合会龙溪与绪山,以为上等工夫与下等工夫之相合,实为不恰!纵使以孔子之资质,亦是至七十岁始可道出,而龙溪受用太早,不够务实,流为虚悬之荡越。此时牟先生对龙溪之见解,大致顺蕺山而来,视其虚悬、不实,不能算是工夫,只是境界之说。

(二)《陆王一系之心性之学》
此时牟先生四十七岁,与四十五岁时说法已稍有异,虽大致仍持批评态度。主要差异在于不再反对“四无说”,而是反对其他主张。如以龙溪之弊,即在只有虚灵明觉而无天理;若如阳明之良知说,便有天理以为基石。不过到了晚年,牟先生便不再谈论此弊。

那么,何以为圆?首先,无意之意则应圆;再次,如“藏通别圆”之历别扫除,而为圆;龙溪则是历四有,而进至四无,是为圆。牟先生言:
而龙溪专喜讲“形上之说明”,义理规模既不广大,亦不曲尽,故照顾有所不及,亦未能善予融通。且其专喜讲“形上之说明”,与阳明讲“致良知”亦有歧异处。[2](p51)
这里“形上之说明”,与“证悟”不同。证悟者,是真实工夫之体证结果,而说明者,则只是语言上之承接、倚傍与凑泊。又义理之所以不广,是因为只接引上根人,中、下根人则无份。
牟先生此时虽视龙溪“四无说”并无妨害,但仍接续不了阳明的“致良知教”。这大致同于黄宗羲之判,即在阳明与龙溪之间划出一道分水岭。
(三)《〈比较中日阳明学〉校后记》
《比较中日阳明学》乃张君劢(1887—1969)作品,而《校后记》一文,则写于牟先生五十九岁,文中大致赞同张氏之说,并未抬高龙溪地位。其曰:
王龙溪为阳明门下之直接弟子,颖悟过人,辩才过人,俨若以王学正宗自居,然于阳明言良知之肯要处,彼实未能握得住。彼所得于良知者,只是其虚灵义、明觉义。然阳明总言“良知之天理”或“吾心良知之天理”。虚灵明觉中有仁义礼智之天理存焉,有是非好恶之天理存焉。此“天理”二字决不可漏掉,而王龙溪则于此甚不能郑重认识,常轻忽而不道。故其言“心”遂混于佛、老而不自觉,故有为佛、老辩护之辞。盖佛、老所言之心正只是虚灵明觉之心,而并无仁义礼智之性或是非好恶之天理存其中。龙溪于此几微毫忽之间不能辨,故以为世人斥二氏为异端为不通也。[3](pp99-100)
这里看起来甚至是在贬斥龙溪近于佛、老,视其只有虚灵,而没有天理。牟先生对于佛、老之批评,如《生命的学问》提到,五代之乱概与禅学之兴有关;亦谓儒家可“纵贯纵讲”,而佛、老则是“纵贯横讲”。纵贯者,凡能论及于道者,都可属之,如儒家之“天道、性命直贯相通”;横讲者,佛、老不直从天道、天理之道德感通处下贯,而于作用上的不执定以为发言,此为“横讲”。
三、晚期对龙溪之见解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反省康德所谓“唯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认为人亦具备“智的直觉”,能及于现象,亦能及于物自身,能化范畴识心之执,从而解决“第一批判”之问题。《佛性与般若》亦谈到“智的直觉”,并且确立了圆教系统。而儒家龙溪学亦是圆教,圆教存有论视“福”具有经验之独立性,并非唯心的,此可解决康德之德福如何一致。顺道一提,在他六十五岁书写的《才性与玄理·三版序言》中,亦特别提到龙溪乃是“自本自根为儒家”,且“四无说”亦是依儒家而发,并非来自佛、老;又言道家是“无执的存有论”。此中期之说,对龙溪已有好感。

(一)《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关于宋明理学之客观理解,牟先生在五十八岁时只写至宋代,甚至陆象山处亦尚未诠释,为补足这部分,于是写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其中提到:
至王龙溪言“四无”,更言之而肆。至罗近溪破光景,更喜说此境,不待言。要说禅或类乎禅,只有在此作用义之无心上始可说之。但象山尚未进至此义。故朱子说是禅根本是误想,而且是模糊仿佛的联想。且即使到言本心之如如地呈现时可函有此境,或甚至如明道、阳明等已说至此境,这亦是任何人任何家皆可自发地发之者,而不必是谁来自谁,亦不因此而即丧失或歪曲或背离其教义之本质。此亦可说是佛家所谓“共法”而不能同一于任何特定教义者。故既可通于道家之玄智,亦可通于佛家之般若。儒家岂不能独自发之,而必谓其来自禅耶?此岂是佛家之专利品乎?如必谓来自禅,则亦可说佛家来自道家,此可乎?[4](p11)
此指出“四无说”与老学相关,皆具备“作用之保存”这一义理。如牟先生以王弼老学“上德不德”乃是“崇本举末”,此非谈论仁义礼智之为何,而是说明如何保有仁义礼智;其“本”系无为、自然,以此能举仁义,且不执仁义而施德,方为上德。因此,以无为、不执而保有仁义礼智,乃是儒、道相通之法。此亦其“作用之保存”的意思,乃指作用层,非指实有层。
这一层虽近道家,却是三教共法,不必限定属于何教,亦不因此丧失自家义理。故龙溪“四无说”还是属于儒家、本于儒家,非关佛、老,亦无违反阳明“明觉感应”之说。又此之“化境”,便是一种作用层之不执,三教皆可谈。因此,黄宗羲以江右王学为正,不以浙中王门为正,并非妥当。牟先生又言:

这里用“圆顿”来形容龙溪学。顿者,一体全化,当下即是,与“四句教”“四有句”的渐教不同。圆者,即于九法界而不离于一法。在牟先生看来,“四无说”不该只是上根人可悟,而中、下根人无份;若然,则如小乘辈之如聋如哑、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权法不开,迹不达本。然佛之本怀则是人人皆可成佛,故他未将上根人与中下根人之间极端地区分,而是强调中下根人只是“私欲多,牵绕重”,若能痛下省察,则能进趋上根之辈。
牟先生又以“尧舜性之”来形容龙溪学,此可接续于孟子。“尧舜性之”一语,意指生而有之,近似“生知安行”。龙溪的“四无说”是先天正心之学,属于圆顿法门,并非如渐教一般还要透过后天之经验、工夫以复其心体。这里已称许龙溪学是为圆教,而此圆教已可与《圆善论》说法相接。
(二)《圆善论》


盖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浑是一事,而亦未知体用显微之果孰体孰用孰显孰微,心意知物之果孰心孰意孰知孰物也。圣人冥寂无相而迹本圆融即是地载,而亦即是天覆之即在地载中,地载之即在天覆中,而亦未知天覆地载之果孰为天覆孰为地载也。分别言之,心知之本创始万物,此曰天覆。在圣人之实践中,万物摄于圣人之迹而即在圣人之迹中呈现(圣人之心顺物正物最后遍润一切存在而使之生生不息即是圣人功化之迹),迹本圆融,此曰地载(地德博厚持载一切)。然既是冥寂无相而迹本圆,则天覆地载之分别亦化矣。此即程明道所谓“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离此个别有天地之化”。凡分别说者皆是权教,非圆实教。[5](p314)
这里透露了真善美之分别说与非分别说的不同。分别说者是为权教,只是权宜之过程,还未究竟,不足以开权显实、发迹显本。若如天台宗之圆教则能开权显实,一切恶法无非佛法。而包括天台、龙溪、郭象等,皆属圆实,能够即于迹之天刑而得解脱!至于非分别说或合一说者,如“心、意、知、物”之一体而化,而“体、用、显、微”亦不必分别,此为圆实教。如天台宗之为圆教,而唯识学则为别教——系以阿赖耶而缘起一切法,赖耶为本,其他为末,而有分别、高下之判。再如“四句教”亦有分别,亦属别教,如“有善有恶意之动”,尚未进到“无善无恶”。
牟先生谈论“圆善”,又何以涉及圆教呢?此在回应康德。康德视斯多噶系“从德析出福”、伊比鸠鲁则“从福析出德”,此分析做法令德与福的独立性、存有性消失,还须综合之方式始成。而牟先生找到圆教之德与福、心与物之谲轨相即的关系,则由德析不出福,反之亦然,如是可以保住存在之独立性。一如荆溪之十不二门、色心不二、性修不二等说,都是综合的,都是诡谲之相即。此乃牟先生藉由龙溪圆教,而作为解决圆善之法门,可以说,在《圆善论》写作期间,大约七十六岁,他是相当看重龙溪学的。
(三)《商榷》
康德“第三批判”之译文,成于牟先生八十四岁,书首除了《序言》,还有《商榷》一文;此如《现象与物自身》是对“第一批判”的消化、《圆善论》是对“第二批判”的消化,而《商榷》一文则是对“第三批判”的消化。
《商榷》一文的全名,是《以合目的性之原则为审美判断力之超越的原则之疑窦与商榷》。牟先生所不满康德“第三批判”者,大致如下:(1)以“超越的合目的性原则”谈美,显得斧凿斑斑,且“美”与“合目的性”之间关联不大。(2)依范畴而来“无概念”之普遍性与必然性,如第二相与第四相之机要,还是近似依于概念之比配而来。(3)“第三批判”之真、善、美,仍属分别说阶段,还未真的合一,此如伊川执善,而东坡执美,所执不同,还互相否定。
牟先生于是藉“四无说”以为调适上遂,进趋于合一说。其曰:
圣心之无相不但无此善相,道德相,即连“现象之定相”,即“现象存在”之真相,亦无掉。盖现象之存在由于对人之感性而现,而为人之知性所决定。但圣心无相是知体明觉之神感神应,此神是“圆而神”之神,已超化了人之感触的直觉与辨解的知性。因此,在此神感神应中,物是无物之物(王龙溪云:无物之物其用神)。无物之物是无“物”相之物,既无“物”相,自亦无“对象”相。无物相,亦无对象相,即是物之如相,此即康德所谓“物之在其自己”也,故圣心无相中之物是“物之在其自己”(物如)之物之存在,而非现象之物之存在,此即是“真”之意义也。故圣心无相是“即善即美”同时亦是“即善即真”,因而亦即是“即真即美即善”也。[6](p82)
这里用“无相判断”来修正康德以“目的论”谈美的做法。“无相判断”乃三教共法,可化去现象之执,不必如康德还要用范畴之四相机要去判美学。龙溪的“四无说”是一种明觉感应,而神感神应,已超化感性直觉,进到了智的直觉。此直觉已不再限于现象界,还可进到物如、物自身、对象之在其自己,亦即是真善美之合一。又三教皆具备自由无限心与智的直觉,如佛教的如、道家的玄理玄智、儒家的四无说等。但牟先生自是以儒学为担纲。其曰:
惟释道两家不自道德心立教,虽其实践必函此境,然而终不若儒圣之“以道德心之纯亦不已导致此境”之为专当也。盖人之生命之振拔挺立其原初之根源惟在道德心之有“应当”之提得起也。此一“提得起”之“应当”亦合乎康德之“以实践理性居优位”之主张。[6](p81)

四、以龙溪学补足康德
(一)对康德“三个批判”之不满
牟先生对康德的“三个批判”皆有所反省。其中关于“第三批判”的不满,在前文《商榷》项下已做过说明,此不赘述,而只讨论他对第一批判、第二批判的质疑。
1.人皆有“智的直觉”,不限于上帝
首先,牟先生不满康德视域下人只有感性直觉而未及于物自身,故要求人同样要有“智的直觉”。依牟先生,上帝、儒、道、释都有“智的直觉”,但各家方式不同。康德之上帝能“直觉即创造”,由无到有之创造。而儒家则不如前述万物之创生,而是道德之创生,道德能从无到有地破空而出。牟先生对龙溪学之转变关键,当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与《现象与物自身》二者,特就后者来做讨论。牟先生言:
此中重要的关键即在智的直觉之有无。依康德智的直觉只属于上帝,吾人不能有之。我以为这影响太大。我反观中国的哲学,若以康德的词语衡之,我乃见出无论儒、释或道,似乎都已肯定了吾人可有智的直觉,否则成圣成佛,乃至成真人,俱不可能。因此,智的直觉不能单划给上帝;人虽有限而可无限。有限是有限,无限是无限,这是西方人的传统。在此传统下,人不可能有智的直觉。但中国的传统不如此。[7](p5)
在西方,人与上帝殊绝,人不能成上帝。而在东方则是众生皆可成佛、成尧舜、修道成真人。此要有“智的直觉”以为成圣根据。又言:
在此识心之执所成的“执的存有论”之下,我们确定“现象”之意义:现象是识心之执所挑起或触起的东西,是有而能无,无而能有的。依此,我们只有两层存有论:对物自身而言本体界的存有论;对现象而言现象界的存有论。前者亦曰无执的存有论,“无执”是相应“自由的无限心”(依阳明曰知体明觉)而言。[7](p40)
康德“执之存有论”系依范畴而建立时空之感性直觉,人系现象之存有,要依此三层综合而存在;然此三层综合,若依儒、道、释,则是皆可化掉、转识成智,故言“有而能无、无而能有”,而在《商榷》则谓“提得起,放得下”。若依明觉感觉、四无而言,则能相应于自由无限心而为无执,此现象之执虽可有,却可化去,由直觉升起自由无限心以为感通,不致陷于现象之执。

2.对康德“德福一致”之反省
康德的“第二批判”提到,关于“德福一致”需有三个设准: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首先,关于自由意志。牟先生依其师熊十力先生(1885—1968)认为,良知之真实呈现,而非只是设准却不呈现。牟先生认为冯友兰与康德都以假设视之。第二,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灭。如孔子提出了“践仁知天”,不去谈灵魂之灭或不灭,而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未知生,焉知死”。先不管有无来生,只先当前践德不怠。中国儒、释、道三家本就不谈西方基督教意义之上帝,而能具备“自由无限心”“智的直觉”等以为转识成智,人人皆可成圣、成佛、成真人,与西方的人与上帝之间有一跨越不过的鸿沟不同。
在中国哲学下关于“德福一致”的解决,牟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儒家心学,其中又以龙溪学最能符合他对于圆教、圆善的要求。此可参考前述《圆善论》项下之讨论,下文亦将做说明。
(二)龙溪学如何补足康德?
1.龙溪学何以为圆教?
圆教近于泛神说,每一点皆即于物如,九法界皆可成佛、小大皆逍遥。然龙溪学若如阳明所判,只为上根人立法,岂是圆教?对此,牟先生晚年乃视其为一普遍教法,只因中、下根人私欲较重,难以抉发,此为人病,而非“四无说”之病。
又龙溪《天泉证道记》曾曰:“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这里提到了“应圆”“用神”,既圆且神,此正可补充西方偏重主客对立、缺于圆而神之思想模式,而龙溪学遂为圆教的一种。此外,圆教之特征在于能诡谲相即地保住一切法,包括善法、恶法,而龙溪亦言:“大修行人,于尘劳烦恼中作道场。”[8](p11)一般修行人总想远离繁华喧嚣、诸多杂染,然真正修行人却能即于烦恼而修菩提,如佛家语:“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亦近于方以智的“圆伊三点”,有言:“谁倾轧我?谁剚刃我?……非我之恩人乎?人生不觏忧患,不遇疾病,则一隙蜗涎皆安乐椁也。”[9](p128)此亦属圆教,仇敌亦当有所惠于我也!又如方以智之师觉浪道盛禅师:“若喫老婆饭,抱不哭孩子,说不能说大话,将欺阎闾哉。”[10](p756)生活过于安逸恐将缺乏智慧,而只会说大话来欺骗人。
龙溪亦有“佛魔相即”之语,是为诡谲相即之意,曰:“魔佛相争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于见处能忘见,三界纵横奈尔何?”[8](p558)一念执着,佛即成魔;见处忘见,便得自在。此如天台宗“一念无明法性心”,点石以成金,而非拿金以换石。
2.龙溪学何能补足康德?

龙溪既属儒家,可有道德心之担当,又有无的精神,由此通于无向判断、道家作用层之无执,等于是把儒、道的优点都结合于一身。此外,龙溪尚有非分别的合一说、体用显微、心意知物只是一机、一事等说,此如真善美之合一,即真即美即善。而这些皆能契合牟先生补充康德美学之要求。
五、对牟先生看法之反思
笔者对于牟先生晚年之消化康德、推举龙溪的做法,以下试图提出若干想法。
(一)“无”为三教共法?抑或龙溪杂有佛老?

然道家既已立法注册了“无”,儒家就该避免。老子言“复归于无极”,庄子言“犹河汉而无极”,朱子以老庄之“无极”乃谓无穷,而周子则是儒家意义下的“无极”,系为形容太极之无声无臭,两者不同。然庄子出现三次“无极”,固可视之为“无穷”,而老子“配天古之极”“致虚极”等,则未必意指“无穷”,亦可曰:以无为极、以无为本。故象山视周子“无极”有道家义。
三教思想相互影响,本是自然之事。虽儒家亦言“无意必固我”“无有作好”,却非自家本色。大方地承认龙溪学杂有佛、老,亦有何妨?文化本是互通,亦不须争论儒、道孰强,因皆已是无分别说阶段。
(二)“四无”为上根人而设,此非法病?
牟先生以为,龙溪“四无说”专为上根人所设,境界甚高,然这是中下根人的私欲太重,而非教法问题;是人病,而非法病。牟先生言:
阳明后,唯王龙溪与罗近溪是王学之调适而上遂者,此可说是真正属于王学者。顺王龙溪之风格,可误引至“虚玄而荡”,顺罗近溪之风格(严格言之,当说顺泰州派之风格),可误引至“情识而肆”。然这是人病,并非法病。欲对治此种人病,一须义理分际清楚,二须真切作无工夫的工夫。若是义理分际混乱(即不精熟于王学之义理),则虽不荡不肆,亦非真正的王学也。[4](p245)
这意思是,龙溪、近溪皆可承继王学,堪称王学真传。纵有荡越之嫌,亦是学者误引或本身实力不足;弊出于人,而非出于法。
然而,法既是为人而设,却唯有上根人适用,中下根人则如聋如哑,此岂非如天台宗所云:不能三根普被!只能算是别教,而非为“圆”。现实中亦大抵万中无一,能倏然地便由先天立根、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才动即觉、才觉即化。此已几近为神立法,而非为人立法。若于一般人无甚益处,当是法病!法为人设,人不能遵守,则法亦有病痛在。
(三)参考孔孟之悦乐思想、孔颜乐处


君子有此乐,则德得其偿,而可不待他人与天及鬼神之赏。天与鬼神之赏,即在君子之自赏其德之中也。有此自赏,亦无更能罚之者矣。若君子于此乐外,更希其外之赏,则未尝自知其德在己,而自享其德,自乐其德,则亦不得称为真有德之君子。故君子之学,必有其乐。未有此乐,即德不真在己,亦未真有其德之证。故孔子首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待人知之而赏,待天与鬼神之知之而赏之,即皆不能于不被知之时不愠,而自悦自乐其德者也。[11](pp176-177)
福与赏不从外来,而是自悦其德。唐先生依于孟子“无义无命”:义之所在,即命之所在,既命之所在,纵为凶亦承担;不论之以福,但论之以命,并于中加入悦乐思想。而牟先生“德之所在即福之所在”之心转,则较为悲壮。
孟子的“君子有三乐”,或如孔颜之乐,这当中有忧有乐,而君子能乐以忘忧,不须将所有事皆心转之而为福,还能知其非福而承担下来,并且悦之、乐之,使成德性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不从外来的悦乐,不同于康德。虽亦部分同于牟先生的“心转”,却也不是不知其凶(德性事业必“恒易以知险阻”),而是虽知其凶,但悦乐足以盈满吾心,而能完成德行之事业。此则不必事事心转,也不必经常担忧自己对于祸、福之判断,是否和他人有异?
(四)中哲可补充康德的两大要点
牟先生抬高龙溪,以其圆教理论来补缺康德,然这些解决在康德来看,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例如“智的直觉”,康德视之为神秘主义的一种,近似通灵者之梦。细究之,笔者以为可由两处来回复、补缺西方:
1.依三教开出主体自觉自证之门
牟先生尝言:
康德在轮廓上、扭转上,他已由“观解的”转到“实践的”,由外在的客体上转到内在的主体上,但尚未从功夫实践上实现此种主体。勿以为只要从原则上理论上这样分解出即足够,至于实际作功夫,则不必讲矣。因为这功夫实践中也正有一套理论过程与原理系统也,譬如佛教经论之所说,宋明儒者之所说。[1](pp2-3)
这也是牟先生所认为由康德学接轨于中国哲学之优点。但康德之不足,在于其自由意志只是设准而不呈现,又虽能进到实践理性,亦无工夫而为落实,因此仍是理论、知解地谈,不如中哲之实践地谈。如此牟先生提出:不妨采取西方之存在主义,如所言“存在先于本质”,而非以人的逻辑理性来把握本质。此存在主义近于生命的自得体证之学,开出主体之门。但西方之存在主义者,如齐克果,毕竟仍是基督徒,基督徒只证“所”而不证“能”,牟先生评曰:
契氏仍未能进入内部心性之骨干,以明道德一阶段如何可能,道德的意志,道德的心性,是如何样的意志,如何样的心性,奋斗胜利中的意志、心性,与超奋斗胜利中的意志、心性,有何不同,是否冲突,意志是否只是战斗中的意志,放弃意志是否即是无意,放弃意志时的意志心性,是如何样的意志心性。这一切,他都未能进入讲明。他只是就宗教情绪在外面说。人的存在之有限性、罪恶性、失望性,西方人能把握得清楚,但是正面的心性之骨干,则始终不能悟入。[1](p6)
齐克果的存在主义虽能实践地谈,由主体而为体证,但齐氏终究依于基督教发言,从人的负面诸如有限性、罪恶性、怖栗性等来谈起。至于吾人心性之四无依傍者,齐氏则无法越雷池一步。
至于康德虽有实践理性,终究仍是思辨性地谈,而非实践性地透过工夫来悟入心性。此康德、齐氏等,于心性说之不足,便要再进到东方儒、释、道之学,以为开启主体自觉、自证及工夫之门,而非只为龙溪学可为担纲。
2.唐君毅先生之穷智见德
唐先生言:
然而除先秦之少数名家,或专以善辩能言,以服人之口为事外,几无一思想家,不重语言界以外之行为或生活,过于语言文字本身;亦几无一思想家,不以求学问之贯通为事者。唯因中国思想家,太重知与行之相连,学问之贯通,于是使纯知的兴趣未能充量发展,各种不同学问之界域不显,致中国过去历史中,未开出如西方之分门别类之科学世界。此可说是中国文化之短。然此同时亦是中国哲学精神,更能贯注于中国之学术文化与中国人之人生的一证明。[12](pp20-21)
意思是,中国哲学之短亦是其长。所短者,在知、行相连太多,以致开不出纯智之思;然其长者,亦是知而能行,不特别专注知识概念,不使其知过于其行,偏好于“穷智见德”。而康德学仍是理性主义之传统,于实践方面仍是思辨性地谈。西方之长亦是其短,偏重知解,于德行实践方面,则不如中哲体系之完整。故中哲素来强调的“知行合一”、学问之贯通,便可作为西哲之补缺。
那么,为何不取“四无说”以补西学?因为纵使如牟先生或龙溪之四无呈现、“智的直觉”之呈现,人还是在时空之中,还是受着万有引力之影响,此悟只是道觉的觉醒,人还是在时空范畴之内。如龙溪的“四无说”,时间亦是记载在“丁亥九年天泉桥上的《证道记》”,近溪的神秘体验亦在时空之内,惠能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然。
牟先生所以为,包括时空、图式、范畴等之“有而能无”,能化去识心之执,然时空等是认识的根据条件与配备,不是执着,无法化去。上帝“智的直觉”可以不用时空,然人不可不用时空,儒、道、释的“智的直觉”只是借用西方上帝之说,而内容不同,上帝“智的直觉”可为由无到有地创造,而儒者只是道德之生起,不能创造万物。
(五)“四无”必带“四有”而为实
牟先生约五十岁时写《生命的学问》,提到“圆而神”既有优点亦有缺点;缺点方面,例如无体无力、拖泥带水等。然晚年又要以龙溪的“无体无力”而来反省康德?笔者以为,“四无”必带“四有”方为实,此亦是融合了中、西之优点于一身。“四无”若不带四有,将是无体无力而拖泥带水,好比只是“圆而神”而不“坎陷求知识”,此文化体质还是不够强健。此与康德之“实践理性”只是思辨性地谈,弊端相同。
(六)“四无”如何分辨儒释道之纵或横?
牟先生在谈论“四无”境界时,曾引庄子为喻。《庄子·齐物论》:“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意思是,面对“有生于无”无限经验之后返,而回到当下,不去区隔有或无。牟先生将此类比于“四无说”,表示不去特别区分心、意、知等。这说法在《圆善论》《商榷》二文中亦曾出现,乃是面对康德“第二批判”“第三批判”时,皆以“四无”、不分心意知物、不分有与无的“无分别说”为主。
然而,心与物二者近于主与客的关系,主、客皆不区分,则有无、善恶等亦不区分,若然,则又何必区分儒、道、释?前文提及,牟先生始终坚持要以儒家的道德意识、以儒家之“纵贯纵讲”为担纲:纵讲天道、性命,而直贯创生,至于佛、老则只是横讲,只是“作用不执之保存”。只是若依前述“无分别说”原则,则此“纵讲、横讲”孰纵、孰横?如何区别?如何纲举目张?
六、结语
上述对于牟先生晚年之高看龙溪心学,以为康德“三个批判”之会通与回应,从而回返自身文化之璀璨与优势,分别爬梳了其来龙去脉、问题意识、采取办法等。同时笔者亦提出自己之研究心得与若干反思。
想补充的是,中国哲学尚有许多待发掘之宝藏,可为西方文化冲击之回应,得以回应“德福一致”等问题。例如,纵使以宋明为主,心学之外,尚有理学、气学。又或在宋明之外,如孔子之前的《诗经》《书经》所载,亦有人格神之“天”,所谓“天讨有罪”“天命有德”等。《中庸》亦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此系在“天命之谓性”下所做之保证,而有别于心学。
其实,龙溪自己似乎亦不多谈德福一致、心转与否?龙溪家曾遭祝融,他的回应是自认德行不足,故福亦不足;然龙溪曾居官位,享有厚禄,又岂敢因此自言有德,或有所心转!再者,圆教心转之法,固能保住一切,亦须提防变得萎靡不振、容易妥协,而无所改革与实践之弊端。
牟先生所提点到的龙溪学,包括了:无相(向)、无执、圆教等心学义理,而为回应重点,就此而论,牟先生大致可称为“当代新心学”,有别于冯友兰之“当代新理学”。牟先生于中西会通之建构与努力,业已是当代成功典范之一,实足为吾辈之效法与学习。
[1] 王阳明致良知教//牟宗三先生全集(八)[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2] 陆王一系心性之学//牟宗三先生全集(三十)[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3] 《比较中日阳明学》校后记//牟宗三先生全集(二十七)[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4]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八)[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5] 圆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二十二)[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6] 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牟宗三先生全集(十六)[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7] 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二十一)[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8] 王畿集[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9] 方以智. 东西均·生死格[M]. 庞朴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0] 复王子京居士//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 第二十七卷//CBETA电子佛典集成《嘉兴藏》: 第三十四册(No. B311), 第27卷[M/OL]. (J34nB311_027).
[11] 中国哲学原论: 原道一//唐君毅全集(十九)[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15] 哲学概论(上)//唐君毅全集(二十三)[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B261
A
1008-4479(2022)05-0032-14
2022-03-24
蔡家和(1968-),男,台湾基隆人,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