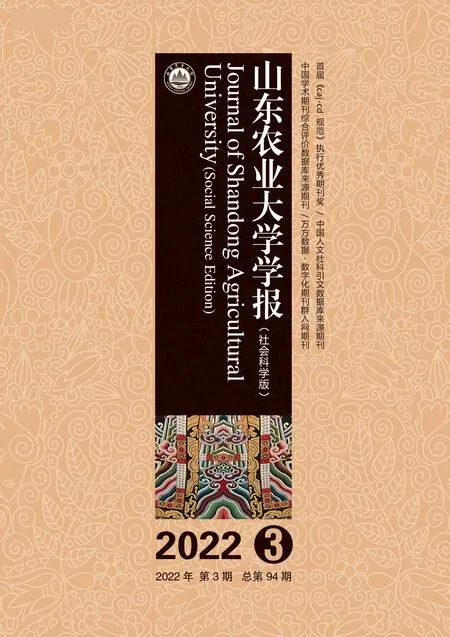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安置补助费在征地补偿中的现实运作
——以2019年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前后对比为视角
童 航
[内容提要]在目前的征地补偿费分配结构中,安置补助费具有特殊性,是土地保障价值的转化,承载着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双重功能。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立了统一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是立法对实践的现实回应。对比《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前后各地区的安置补助费在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的实践,发现除地区差异外,突出的问题是安置补助费的独立性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补偿标准仍依赖于地方,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在政府和农民的博弈结构中,政府在安置补偿方案的确定中居主导地位,农民凭借基本的道义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法官在审理涉及安置补助费纠纷的案件中对现行规范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与适用,但矫正正义功能的发挥依旧有所欠缺。
一、问题的提出
安置补助费是指征收主体(通常是政府)在征收土地时,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童航,2012)。安置补助费给付的初衷是“解决失地农民生存、生活问题而设立的补偿费用”(关保俊,2010),由此可知,安置补助费对失地农民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其也关系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关键环节之一,理应得到重视。
在实践中,对征地后所确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有关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不同地域的分配方案不尽相同,甚至有同一地域、同一辖区出现几种分配方式的情形。而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诉至法院的案件较多,审判实践中裁判结果也多有不同。在这些裁判中,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一般尊重村民自治原则,按照本村村民大会的决议进行土地补偿款分配①;安置补助费的分配则众说纷纭,裁判不一。本文拟从实务层面考察安置补助费的现实运作,以期规范安置补助费这一分配制度,实现该制度应然和实然的对接。
二、安置补助费现实运作的区域考察
安置补助费是一特殊的征地补偿费,具有鲜明的本土气息。对其类型的处理则应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对其功能的确定则应面向未来发展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考察安置补助费在各地区之间的现实运作,本文根据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政府征收利用土地公告中的内容,选取了吉林、四川、江苏、河南、广西、广东等省市作为考察对象(选取时间段为2012-2021年,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分析,在补偿标准部分本文统一换算为“万元/亩”)。为了更好地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比较,本文根据地区、地类、计算标准、安置方案制作了以下表格。
(一)区域考察的列表说明

地区时间/年地类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其他吉林长春2012建设用地区片综合地价:10.67万元/亩(土地补偿费30%,安置补助费70%)货币+社保安置一类区2020建设用地区片综合地价:3.33万元/亩,其中30%是土地补偿费,70%是安置补助费货币+社保安置七类区四川绵阳2012耕地(含园地)征地统一年产值的6倍,非耕地为3倍。货币+社保安置2020区片综合地价:区分I、Ⅱ、Ⅲ三类地,分别为5.04万元/亩、4.75万元/亩、4.48万元/亩(游仙区)。其中,30%是土地补偿费,70%是安置补助费。货币+社保安置江苏南京2012区片价补偿标准:8.21万元/亩货币+社保安置2020区片价补偿标准:8.21万元/亩货币+社保安置河南焦作2012征地补偿标准为2.1-3.7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货币安置等方法2020农用地5.8万元/亩货币补偿安置、留地安置、就业安置等其他安置方式+社保安置广西柳州2012农村宅基地统一年产值标准:5.53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货币安置安置补助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2020建设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7.05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广东广州2012耕地/园地/其他农用地年产值标准:16.8675万元/亩;17.0924万元/亩;11.245万元/亩。货币补偿、留用地和社会保险的形式安置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无安置补助费2021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征收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补偿标准均为30万元/亩(含土地补偿费15万元/亩,安置补助费15万元/亩)。货币补偿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也有安置补助费浙江绍兴2012耕地C(Ⅲ)类区片综合地价2.38万元/亩货币安置只有耕地有安置补助费2021耕地I类区片综合价6.8万元/亩,Ⅲ类区片综合价6.2万元/亩货币安置+社会养老保障安徽阜阳2013农用地/建设用地统一年产值(1730元/亩)的15倍,即2.595万元/亩;统一年产值(1730元/亩)的7倍,即1.211万元/亩采取货币补偿、产权调换等方式进行

地区时间/年地类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其他2020区片综合地价标准:1.Ⅰ类区域补偿费标准区片标准为5.593万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2.0974万元/亩,安置补助费3.4956万元/亩。2.Ⅱ类区域补偿费标准区片标准为5.3万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1.9875万元/亩,安置补助费3.3125万元/亩。采取货币补偿、产权调换等方式进行湖北黄石2012农用地三级综合片区地价2.431万元/亩货币安置、就业安置和社保安置2021区片综合地价标准:Ⅳ级,5.8万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占40%、安置补助费占60%。货币安置、就业安置和社保安置
(二)分析说明
根据2004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至50条的规定可知:(1)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其中,年产值的计算,与土地补偿费年产值的计算方法相同。被征用单位耕地的安置补助费,因人均耕地的数量和平均年产值多少而不等,人均耕地少,平均单位年产值高,支付的安置补助费就高,反之则低。(2)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规定。对征用有收益的非耕地的安置补助费,各地一般按该土地年产值乘以略低于邻近耕地的安置补助费倍数计算;对征用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地基以及无收益的非耕地,不支付安置补助费。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制定安置补助费标准时,一般是在《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范围内,结合当地的情况,对耕地和非耕地(如园地、鱼塘、藕塘、林地、牧地、草原等)的安置补助费作统一规定。在确定安置补助费时,被征地单位要有准确的应该享受安置补助费的人口数字。为此,《土地管理法》规定,人口数必须按农业人口计算,非农业人口不在计算之中,必须是拟议征地前居住的人口,开始拟议征地后迁入的户口不包括在内。(3)按照以上规定计算支付的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④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安置补助费应该用于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得挪作他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然而,在实践中,2020年之前有些地区的安置补助费的运作方式明显脱离了《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的规定。2020年以后,按照《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48条第3款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改变了之前《土地管理法》所确立的“年产值法”的征收补偿标准,而改为“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这也是对之前各地实践的立法回应,至少从规范层面提高了补偿标准,至于实践运行如何,我们通过对以上表格数据结合相关背景的分析可知:
第一,安置补助费的实践运行逻辑存在地区差异性。安置补助费的本意是让失地农民尽快实现就业转移,因此安置补助费的计算应以当地的劳动力平均转移成本为依据。但现行安置补助费的计算标准却过于注重各地区的资源察赋,缺乏与当地实际的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有机联系。上表中明显可以反映出:东部地区的安置补偿费高于西部地区。对此,是否应在制定各地区的“片区综合地价标准”时将国家土地总体规划因素考虑在内,值得思考。这就要求自然资源部应确立一个全国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影响下的地价标准。
第二,2020年之前,安置补偿费的计算标准多样化;2020年以后,统一为区片综合地价法。2004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计算标准是“统一年产值法”,实践中有些地方确实是如此操作的。但有些地区的安置补助费的计算,明显脱离了《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的规定,或者将之与土地补偿费进行捆绑性支付,称之为“综合价”,或者以被征收土地的数量为基础进行计算,而不以所受影响的农业人口为计算依据,或者对“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进行人为性夸大或缩小解释(钟水映、胡晓峰,2004)。由此可知,安置补助费目前的分配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我们不能否认,综合价法所计算出来的安置补偿费大于按年产值法所计算出来的数额。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标准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地方积极探索符合农民利益的补偿费用计算方式值得肯定(上文也提到2004年,原国土资源部在统一年产值标准外,又增加了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另一方面这些实践操作的标准由于缺乏地区间的协调性,极易在相邻地区,因补偿费的差异而激化矛盾。
此外,实践中有的地区的计算标准不区分土地的类型,如湖北黄石,吉林长春等地区;有的地方是区分土地类型的,如安徽阜阳、广东广州等地区。2020年之前,广东广州规定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无安置补偿费,这估计是考虑到了在这些土地上可能不存在需要安置的人口;2020年之后有安置补助费,这主要是受到区片综合地价的影响。
第三,2020年之前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低,不能明显改善生活水平;2020年之后,安置补助费标准有所提高,但各地存在差异,某些地方甚至依旧采用2010年的标准。《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之前规定的征地补偿费是按照土地原用途的年产值倍数来进行测算,这种测算办法,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按重庆市政府[2008]45号文件,土地补偿费最高每亩1.6万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8万元,这两项费用还要用于交纳养老保险,用完之后,其生活将面临困境②。欣喜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内容。
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在第48条确立了“片区综合地价标准”,提高了土地补偿标准(含安置补助费)。但在实践运行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地区根据《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的要求,颁布了最新的各地方“片区综合地价标准”,但仍有个别地区仍然适用之前的标准。如吉林长春,10年之间(2010年至2020年)没有任何变化。这明显是违背《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的规定的,该法要求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布周期,从原有的五年缩短为三年。
第四,安置补偿人员的认定标准不一致,有的按照农民户口认定,有的按照是否享有承包地认定,有的还考虑是否在本村居住。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成员权”问题,在现实中,农民成员权的实现和行使与集体经济组织常年纠缠不清,有待从立法上予以理清(陈小君,2014)。对此,本文认为需安置补偿人员的认定,对于确定集体土地征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落实有关基本生活保障意义重大。在认定被征地农民资格和名单时,应以村民户口为基本标准,但应考虑一些特殊情况。一是因在大中专以上院校就读、应征义务兵、劳改劳教等原因而迁出户口的人员,在征地报批前回到原籍,要求恢复集体经济组织身份并享有征地补偿安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是在土地承包期内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但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员,如其户口迁出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要求享有征地补偿安置的请求应予支持;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籍人员应视为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但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其村民待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③。
第五,实践突破了规范中单一“货币安置”的限制,发展出就业安置、留用地安置和社会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是对安置补助费功能的多方面体现。通过上表,我们发现,目前的征地安置实践已经很少仅仅进行货币补偿,而是多种安置方式的组合。其中,以“货币安置+社保安置”为多,但笔者认为还需要加上就业安置。如此,理想的安置方式应是“货币补偿+社保安置+就业安置”的组合,货币补偿着重失地农民的临时性救济,社保安置着眼于安置补助费的社会功能,就业安置是农民发展权的体现。关于社保安置又存在多种形式,实践中探索出“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被征地农民建立独立开放的养老保障和政府+商业保险三种主要养老保障模式”(陈正光、骆正清,2009),各地区应结合当地实际,并考虑失地农民的选择权来选择合适的社保安置模式。
三、司法实务层面:安置补助费分配纠纷的表现
本文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梳理,认为安置补助费在司法裁判层面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安置补偿方案不确定或者对安置补偿费等没有作出约定,法院能否不受理?
土地补偿款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这是201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予以明确的。但毕竟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其社会保障功能在现阶段是不容置疑的,如果集体经济组织迟迟不作出安置补偿方案或者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集体成员能否提起诉讼,这一问题同样至关重要,需要予以回应。
在“上诉人李永印因与被上诉人卫辉市后河镇大辛庄村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李永印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安置方案不确定(或者说安置补偿方案没有做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认为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理由是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定,即此类纠纷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人民法院不应干涉④。在“上诉人尉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南梨园村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南梨园经联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尉刚案”)中,二审法院依旧将其归为村民自治的范畴而不予受理⑤。
但是,安置补偿费是国家在征用土地时,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也就是说,安置补偿费就其性质来说,是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安置的补助费用,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将其简单地归为村民自治的范畴是不妥的。而且,《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48条对安置补偿费的补偿标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请求权基础是比较明确的。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安置补偿方案没有作出或者对某些补偿费用没有作出约定的情况下,一概将其划为村民自治的范围。也就是说,在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纠纷中,现行的司法裁判逻辑是以明确的安置方案为前提的。本文认为,这是对村民合法权益的漠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司法裁判方式,对此类案件应当区别对待。第一,安置补偿方案还没有作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安置补偿方案的作出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还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对于安置补偿方案有意见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信访途径寻求救济,司法救济有其自身的秉性。第二,安置补偿方案中没有对安置补偿费的分配作出规定,就救济方式的选择来说,村民的确也可以通过非司法途径寻求救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院对此类案件就不应受理?并非如此。理由是安置补偿费关系到失地村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土地管理法》对分配的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应当属于法释〔2005〕6号第一条规定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⑥。
(二)接受统一安置是否还享有安置补助费的分配资格?
根据201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即2021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条第4款)的规定,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法院在受理此类纠纷时,并未触及安置补助费的根源,只是对最终的数额如何分配进行裁判。如在“上诉人文昌益家庭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文昌益承包户)与被上诉人武隆县巷口镇柏杨村红坡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红坡村民小组)征地安置补助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文昌益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安置补助费的管理和使用,按照201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的规定,需要根据不同的安置方式来确定。二审则认为:只有在放弃统一安置时,其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方能予以支持⑦。该案所透露出的的信息是需要安置的集体成员在放弃同意安置的情形下,才能获得安置补助费的货币性补偿。其背后的法理是由安置补助费的性质所决定的,即社会保障功能和就业保障功能。换言之,接受统一安置,就不再享有安置补助费的分配资格。这对于固定安置补助费的分配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因此剥夺临时安置补助费的分配资格。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安置补助费类型,在征地补偿中所体现的功能是不同的。后者着眼于临时性,是过渡性救济,应以期限性的货币补偿予以体现和保障。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农户在接受调整土地和要求补偿之间是否具有选择权?我们还是先来看一则案例,在“费先久等六原告与被告梨树县梨树乡东平安村村民委员会土地征用补偿纠纷一案”中,法官肯定了农民在土地安置和货币补偿上,失地农民具有选择权,是对现行规范的严格解读⑧。这属于司法的进步。此外,应当明确的是,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广泛施行,为满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成员的主要生产资料及其生活来源的基本保障,土地作为该两种要素的必要载体,均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各成员以户为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承包集体土地的形式予以实现。因此,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只有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农户,才真正成为因丧失主要生产资料及其基本生活来源的多余劳动力,而因此获得统一安置或在放弃统一安置的前提下取得安置费用的权利。
四、结论
本文通过以上论述,得出以下结论:
1.安置补助费作为一特殊的征地补偿费,其具有双重功能——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是最主要的功能,但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发生变化,未来的安置补助费应仅具有就业保障功能。强调安置补助费的就业保障功能是重建“农村社会公共性”(武中哲、韩清怀,2016)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完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规范条文设计。此外,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制度有助于农村的稳定,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
2.在目前征地补偿费结构中,安置补助费不同于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着眼于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安置补助费着眼于土地所承载的保障价值的转化。故而,以技术手段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并确定为一综合价是不当的,这不仅违背法律精细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分配正义的宗旨。《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以后,各地在“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中明确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比例,说明了立法者认识到了两者在功能上的差异性。但本文仍建议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彻底分离(即明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中人均农业人口安置补助费数据),同一县(市、区)内采用相同的农业人口安置补助费标准,以真正实现“同地同价、同人同标准、地有级差,人无等级”(谢巧巧,2021)。
3.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存在地域性差异。这一地域性差异具有合理性,其实质是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在统一地区实行不同的标准则违反制度的内在正当性要求。为此,应在各地区实践基础上总结“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计算方式(屈茂辉、周志芳,2009),并通过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
4.安置补助方案的多元化是政府和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基于任期政绩的考虑,往往会以超出自身支付能力来透支土地资源;而农民在这现实背景之下,期望分享土地的增值价值(程雪阳,2014),而在于地方政府协商、谈判和争议中获得一定比例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5.司法实务层面并未在安置补助费纠纷裁判中很好的发挥矫正正义的作用,只是确立了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在接受安置和要求补偿上拥有选择权。也就是说,安置补助费的应然价值和实然价值之间存在断层,这是这一费用分配存在纠纷的根源之一。此外,在村民自治之下,安置补助费的分配在具体数额上与其他征地补偿费共同成为此类纠纷的诉讼标的。
注 释:
①可参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民一终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平民二终字第656号民事裁定书;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三亚民一终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等等。
②参见吴佳斌、杜利等:《规范土地征收行为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重庆北碚法院关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征地纠纷的调研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第08版。
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课题组:“积极寻求问题应对方案 促进土地资源公平分配——江苏高院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行政案件审理的调研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3月17日星期四第08版。
④参见洒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新中民四终字第409号民事裁定书。
⑤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15062号民事裁定书。
⑥最新的判例有所变化,参见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10民再25号二审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安由以及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本案系原告开荒地被征收后作为被告集体组织成员对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不服提起的诉讼,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且本案案由应定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⑦参见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07)渝三中民终字第367号民事判决书。
⑧参见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2000)梨经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