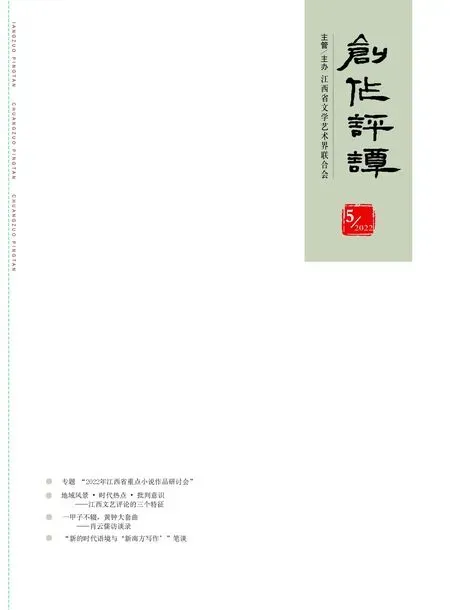农耕文明的颂歌和挽歌
——评萧亮的中篇小说《独角牛》
◎ 王 干
最初读到萧亮的中篇小说《独角牛》,我陷入了沉思:这是乡土小说吗?乡土小说到《独角牛》是不是可以终结了?
之所以提出这么多问题来,是因为我一直关注乡土小说。《独角牛》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发现作家除了写出了乡土作家惯有的土地情结、氏族情结和粮食情结外,还深化到对农耕文明的表现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困惑以及消失的主题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角牛》将成为乡土小说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它意味着乡土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结。这个终结与农耕文明的衰退乃至消失有关系。
在《独角牛》里,作家写了农耕文明的诸多方面。小说里小老是一个农事高手,这个朴实而勤快的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开拓了“十亩大丘”,成为村里人人眼红的“肥地”。与农事相关的是农具,因为牛的缘故写到木犁,作家笔端充满了深情,为那些已经消失的农具奏响了一曲深情的挽歌。同样写农活,作家在赞美劳动之美的时候,也哀叹这些劳动的消失。
但书中所展现的农耕文明的衰退和消亡,不像一般文学作品把它归结于工业文明的破坏,就形式上而言,没有毁于工业化的进程,也没有葬身于城市化的进程,它的格局依然还在。农耕文明慢慢消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的侵蚀。
小说通过塑造独角牛、笑笑、小老和母队长四个形象来展现这种消失的过程和必然。笑笑代表农耕文明的少年时代,她天真、无瑕和纯洁,凝聚着农耕文明时代人的美好情愫。而小老意味着农耕文明的壮年时期,年轻能干,堪称农耕文明的劳动典范。独角牛是小说最核心的形象中轴,它一方面连接了所有人物的命运,成为小说情节的发动机;另一方面,化身为农耕文明的晚年形象,隐忍、勤劳、无私而残缺,在暮年苦苦支撑,直到死去——它因为不能耕田而死于母队长的锤子。农耕文明的肉身在现代性的“锤子”敲打下,毫无抵抗之力。
《独角牛》塑造了一个叫母队长的女性,是农耕文明的掘墓人。她原是小老的妻子,后来因为小老是“富农”成分,而她思想上进,就和小老离婚了。她身上披挂的闹钟、背着的收音机,再后来是大喇叭,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她的形象是反农耕文明的,她追求的进步是一种现代性。现代性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是影响巨大的,但是现代性对农耕文明的摧毁也是无情而致命的。母队长作为“新的女性”,她摆脱家庭的羁绊,摆脱了传统文明的制约,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政治管理,追求男女平等,投身到现代性的时代大潮中,有某种反封建的精神。但她的行径对农耕文明的伤害却是令人震惊的。小说里反复写她对独角牛的虐待和暴行,正是对农耕文明的无情摧毁的象征。
《独角牛》在小说艺术上也独辟蹊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但小说里的“我”经常超越身处的时空限制,以一种全方位的视角来观察笔下的人物和事情,可以说是一种“套层叙述”:童年与成年交织,过去和现在交织……时空的自由转换,“我”时而是村里的小孩童,时而是俯瞰天下的大视角,文化、历史哲学、诗意交错在一起,吟唱了一曲农耕文明的挽歌。
《独角牛》取材于我们常见的乡土题材,但已经超越了乡土的母题,进入到农耕文明的反思和追思之中,既是对农耕文明的赞美,又是哀悼农耕文明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