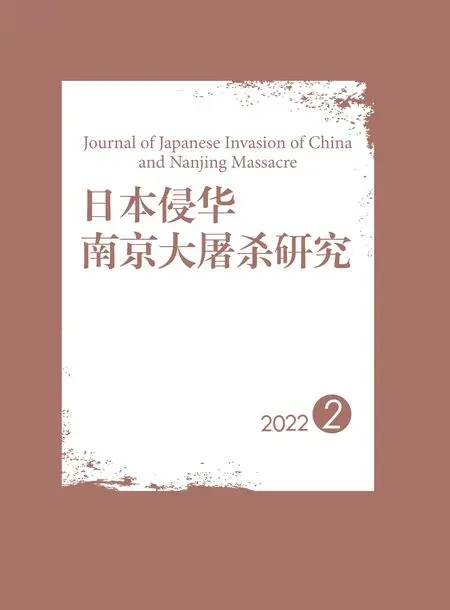皖南事变若干文电日期考订
程 毅 董国强
皖南事变自爆发以来,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相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绵延相继。检视既往研究,笔者发现,尽管此项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但较多论述似乎仍失之偏颇甚或存在对部分问题的严重误判,而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即是缺乏对所依据资料本身的考辨。从已出版的相关文献来看,因各种因素影响,其本身往往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对文电日期的误注即为显例,部分学者曾对此进行过有益探索,此处不赘。笔者拟对另外七份文电日期进行考订,尚祈方家指正。
一、《中共中央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的日期问题
1982年出版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收录了这份文件,标注的日期为1940年4月26日。笔者注意到,1988年出版的《新四军·文献》(1),在易题名刊出此份文电时,已将日期更正为“1940年5月26日”。然而,其后无论是史料汇编,还是学者征引,仍普遍采信“1940年4月26日”,甚至2013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亦持此议。
详析此电,其落款日期为“二十六日”,即表明月份由编者考订而来。文电中有“苏北部队……决定仍属项、陈指挥”,此时中共在苏北地区的作战力量为叶飞、张道庸、管文蔚、梁灵光等部,曾隶属陈毅的江南指挥部,4月20日,中共中央将其划归刘少奇指挥。如月份为4月,延安在4月26日就已将苏北部队指挥权重归陈部,何以5月4日延安会向刘少奇提出“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以及为何刘少奇迟至5月31日才电嘱张云逸“叶、陶部即归陈毅指挥”?于情于理,均不恰当。
查此文电中,中共中央对苏北部队“仍属项、陈指挥”给出的理由是“因胡服北上,电台未联络”,即因刘少奇赴皖东北根据地考察,与苏北部队未能进行电台联络。实际上,刘少奇自4月21日启程北上,6月12日才返回皖东驻地。在此期间,因皖东北局势动荡,刘虽未与苏北部队失去联系,但时有联络不通的状况,遂常以江北指挥部为中介来指挥苏北部队,这显然不利于应付苏北变局,故中央决定将苏北部队指挥权重归陈毅部。4月26日,刘少奇尽管仍在赴皖东北根据地的途中,但与江北指挥部联络基本是畅通的,叶、张两部尚在皖东休整(叶部于29日东返,张部稍后),此时提出将指挥权交与陈部,似乎略显过早。
此外,文电中指出,“苏北管、叶、张、梁四部中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既然4月26日延安已允许从苏北部队“酌抽一部加强苏南”,何以陈毅5月17日、19日两度要求中央批准从苏北叶、张两部调兵南下应急?如果是4月26日中共中央已允诺,苏北部队尚未调动,陈致电延安应系催促,而非要求批准。此外,中央既已将苏北部队指挥权交与陈部,并称“具体布置由项、陈决定”,陈毅在苏南遇到危局时调动叶、张两部,自然是直接电令叶、张抽兵南调,何须再电请中央批准?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此份文电日期应为“1940年5月26日”。如采信《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一书的说法,表明中共中央早在4月26日就已同意“苏北部队……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进而表明延安同意项英、袁国平就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问题向国民党作出让步,以及支持皖南新四军东移苏南。实际上,此时延安在南调问题上拒做任何让步,并试图以皖南主力北渡皖东,发展华中;后迟至5月5日,才因情势变迁,转而答应陈毅、项英提出的东移方案。如不顾前后史事,采信“4月26日”,极易得出项英违抗延安指示、株守皖南的错误论点,遮蔽了项英与延安、中原局就皖南部队转移问题存在的多维复杂互动。
二、《关于顾祝同要我做局部让步的情况反映》的时间问题
这份文件为《项英军事文选》收录,标注的时间为1940年5月29日。查此份文电落款为“二十九日”,即表明月份由编者考订得来。然而笔者详阅文电内容后,以为将其定为“五月”应系讹误。原因如下:
首先,文电中有“皖南、江南敌人已开始大规模的进攻。高淳之敌占东坝湾、之敌向青弋江、大通之敌向青阳进攻,使顾无法对我强硬”。考诸史实,此种情形应系4月下旬至5月初日伪军在江南地区发动的“扫荡”。因国民党军队几无抵抗便全线撤退,其防地相继失守,值此情势,顾祝同一方面有求于中共部队牵制日伪军,另一方面亦害怕其乘机占据国民党军队防区,即文电中所称的“恐怕我作怪”,故“不得不暂时让步,使情况缓和”,5月29日江南局势已趋稳定,故将其定为“5月”应属讹误。
其次,文电中提到,“管部南调决定五起增加经费三万元”,“五”显系“五月”。如果文电为“5月29日”,即5月已将近结束,作为顾祝同希望共方作出的让步条件之一“管部南调”尚未实行,部队调动尚需时日,即便答允对南调后的管部增加经费,按照抗战初期国民党对中共部队经费克扣的惯例,应是自“六月起”,而非“五月起”。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该文电日期应为“1940年4月29日”。实际上,早在4月22日,中共中央就已将新四军问题交涉权转与周恩来,因值日伪军“扫荡”皖南,故项英延至29日才将上饶谈判结果汇报中共中央及南方局。
三、《关于军部不能北移及对江南工作的意见》的时间问题
这份文件为《项英军事文选》收录,标注的时间为1940年8月17日。此电中有“据叶、袁回称”“据上饶谈判结果”等语,查叶挺自1939年10月离开新四军军部后,迄至次年8月1日才返回云岭,当日将上饶交涉详情报告军部,但项英何以迟至17日才电告中共中央?此显系违反中共组织纪律,更何况涉及皖南新四军转移事宜,影响到国共关系的全局,项英等军部领导自应立刻电告延安,延至17日,于情于理,均难以说通。
实际上,1940年新四军军部派代表就地与顾祝同或上官云相谈判,前期是由袁国平负责。叶挺重返军部后,通常是先请示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然后主要由叶挺负责交涉。此次之所以是叶、袁两人在上饶与顾祝同交涉,缘于袁国平6月11日赴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新四军工作,并受项英的委托接叶挺回军部。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40年6、7月份,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一起同叶挺、袁国平、饶漱石交谈时就曾指出,“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概移重庆,由周恩来负责进行”。叶、袁此次与顾祝同交涉,应系返回军部前,路经上饶,因叶挺与上官云相等国军将帅有私下交谊,故最初可能仅系叙旧,但终究还是将话题转到了新四军问题上来;虽系无意之举,但显系违背周恩来的交代。8月4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重申新四军“军部争取苏南,与国民党的谈判一概移重庆来解决”。因此,10月下旬,上官云相在泾县约见叶、项时,他们便先向中共中央及南方局请示,后遇到类似情况亦复如此;直到12月9日,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斐告知周恩来、叶剑英,“N4A北移问题,已电顾长官负责全责就地处理,就地解决”。如此一来,涉及皖南新四军北移的细目,就由军部与顾祝同(或上官云相)就地直接交涉。当然,因转移问题牵涉国共全局,故周恩来此后亦未厕身事外,始终发挥着重要枢纽作用。
综上所述,项英拍发文电的日期应系“1940年8月1—3日中的某一天”。延安收到电报后,4日周恩来再度强调新四军“与国民党的谈判一概移重庆来解决”,就成了顺理成章;故“8月17日”应系讹误。
四、《与顾祝同谈判所提的条件》的时间问题
这份文件为 《项英军事文选》收录,标注的时间为1940年8月16日。此文电提及,“过上饶,分别访晤顾祝同与张超”。由此可知,此系项英亲赴上饶与顾祝同进行谈判;但日期显系讹误。如前所述,周恩来曾在六七月间、八月四日两次强调,涉及新四军问题的交涉,“一概移重庆来解决”。项英作为历经考验的老党员,此一基本纪律应不会故意违犯;故时间应在8月4日以前。
文电还提及,“彻查苏南事件,并依法惩办祸首,抚恤新四军伤亡官兵”。此处的“苏南事件”,即1940年6月国民党部队开抵溧阳,迅即形成对苏南新四军的包围,并贸然进入新四军防区,围攻医院、截断兵站,使陈毅部主力被迫北移。项英此电应是将此情况电知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博古和尚在重庆的叶挺、袁国平,尽管此情况并非电文主体。笔者阅档偶得,6月17日,叶挺将“苏南事件”电告蒋介石,从内容来看,叶的消息源为陈毅。据《陈毅年谱》反映,6月10日,陈毅曾向延安电告此事,但其显示资料来源为《新四军征途纪事》与《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所载《苏北事件真相》一文。前者并未标明原始文献出处,故其可信度待考,后者陈述的是《六月十九日陈毅致巫兰溪等书》,但未披露陈毅向延安电告此事及其文电日期。笔者未曾见到陈毅向延安报告此事的文电,但1940年4月下旬后,陈部就与中共中央接通了无线电联系,直接向延安报告亦属正常。然而,既已向中共中央报告,延安通常是委托周恩来等南方局人员与蒋直接交涉,何以让叶挺与蒋交涉?似显蹊跷,暂作存疑。
此外,文电提到,顾祝同“希望苏北管、梅二部南调”,项英对此“拒绝不执行”,“顾亦未坚持”。实际上,7月16日“中央提示案”即已规定八路军、新四军要北移至黄河以北,顾祝同不可能在8月中旬向项英重弹“江北新四军南调”的老调。
综上所述,笔者推断此文电日期应为“1940年6月16日”。此时,顾祝同“亦未坚持”,可能也在等蒋介石的指示,将此文电定为6月16日,次日叶挺收到此电报后向蒋交涉就显得顺理成章,尽管文中称其消息源为陈毅,但亦有一种可能,即陈部是该事件直接承受者,称来自陈毅而非新四军军部或许效果更佳;此外,亦可表明6月中旬,苏南陈毅部决定移师北上后,尽管项英表示暂停转移,“目前只有待机移动”,但并未立即选择株守皖南,仍在通过与顾祝同的交涉,争取将部队从皖南转移出去。
五、《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之部署致叶挺等》的时间问题
这份文件为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收录,标注的时间为1940年9月22日。文电中称,“桂军五个师,李仙洲三个师,周岩三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一个师已越过淮南路东,汤恩伯九个师连日由鄂开豫,已在南阳集中,不日东进”,而这显系蒋介石为将中共部队逐出华中、迫至华北(甚或就地消灭)而作的军事部署,但引文所述局面大致形成于1940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曾试图通过叶挺在上饶谈判,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停滞汤恩伯等部东进的交换筹码,21日还电告新四军军部“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部队进攻)”。但上饶交涉无果,华中局势渐趋严峻。刘少奇多次致电延安希望尽快解决韩德勤,然后西援皖东、皖北,11月19日,中央终于同意在淮安、宝应间发动一个局部战役,以实现“拉韩拒汤、李”的意图,并将时间定在胡宗南进攻关中后,但这势必会影响到皖南部队北移,故中央电询军部“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显系催促其尽快转移完毕。
1940年9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表示“对新四军北开,蒋既坚持,我应坚拒”,迄至次月8日,因鉴于苏北战局对皖南新四军处境将造成的影响,中央才改变让皖南新四军固守原地的想法,转而要求军部率部分部队转移; 11月3日又进一步作出放弃皖南的指示,故此文电时间应系11月3日以后。将其标注为“9月22日”显系讹误;“12月22日”亦不可能,因曹甸战役业已结束,苏北已成僵局,延安对此处部队倾向于暂作整顿,而非立即动手解决韩德勤。
考诸前后史实,笔者以为,该文电日期应为“1940年11月22日”,恰与同日军部致中共中央的文电,在内容上,即“马、养两电同时收到”,“皖南部队开动尚需相当时间……亦非数日所能改变”形成呼应。
六、《关于皖南军部北渡问题报中央并致胡陈电》的时间问题
1987年出版的《叶挺研究史料》收录了这份文件,标注的时间为1940年11月13日。详析文电内容,应系中共中央要求皖南部队尽快北移。然而,1940年11月13日前后,对延安而言,急需制止汤恩伯等国军部队东进,以巩固华中局面,故电嘱赴上饶谈判的叶挺,“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中共中央此时实有以皖南部队北移与制止国军东进做交换,并以为此筹码对国民党极具吸引力,故倾向于让皖南部队展缓北移,故“11月13日”显系错讹。
笔者注意到,《新四军·文献》(2)在收录此份文电时,将日期更正为“1940年11月3日”。实际上,11月3日,当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皖南,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当日即复电同意,数日后再电详述对中央时局分析的赞同。笔者虽未看到项英等人11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赞同皖南新四军全部北移的明确电报,但从《同意中央对时局分析与总方针(1940年11月)》一文提及,“对于皖南北移,全体意见已详见江日电”,即在11月3日,皖南方面应收到中央的这一指示,或者即便没有收到,应该也是支持北移;但此份文电提到,“军部如全移走,留皖南部队即无适当统率人员指挥,又会影响坚持游击战争之信心”,“决心坚持皖南阵地”,即持“固守皖南”观点。如果其整体基调是“固守皖南”,显然是与数日后《项英关于同意对时局分析与总方针致毛泽东、周恩来电》的意见是相左的,这自无提及的必要,若提及岂不是引发延安方面不悦?故笔者认为,11月3日,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领导即已持放弃皖南、实行北移的想法,虽然未见“江电”(即3日电)的具体内容,笔者以为其内容应系新四军内部就转移相关事宜的讨论,只不过数日后的电文是详述北移合理性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皖南军部不可能在放弃皖南、决定北移时,又自相矛盾式向延安提出“决心坚持皖南”的主张。《新四军·文献(2)》或许是因为《同意中央对时局分析与总方针》一文中提到“我们经过讨论(参加者叶、曾、饶、袁、周、傅等)”“对于皖南北移,全体意见已详见江日电”,加上此处所提文电落款处有“叶、项、袁、周、曾、姚(即饶漱石——引者注)”,故未经详析两份文电的正文内容,就移花接木式地将二者联系起来,从其编排顺序似可推知,颇显草率。
文电还提到,“我们提议陈毅同志的两电,韩德勤尽可能包围于兴化地区”,但早在10月30日,叶挺、项英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到,上官云相已向叶挺表达了苏北中共部队应保留兴化、不打韩部的意愿,以及顾祝同之所以对进攻皖南新四军有顾虑,主要是害怕苏北中共部队消灭韩德勤,故无论是11月3日还是11月13日,项英都不可能提出“包围兴化”的提议,此提议只可能是10月28日叶挺与上官云相会谈前提出。
因此,“11月13日”和“11月3日”均不正确,《新四军·文献(2)》提到“档案馆所存此电落款处注有13日”,此处应无问题。笔者以为,该文电日期应为“10月13日”。原因有二:
首先,中共中央即在10月8日致电,让叶、项能够考虑转移,或移第三支队附近,或移苏南(条件允许下),11日项英接电后并未接受此项建议,而坚持固守原地即可应付危局,但仍表示“希夷尚在泾县,明日回部,讨论后再作详报”;中央显然无法接受项英的意见,加上此时刘少奇数电中央要求皖南军部尽快北移,故次日复电,要求“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延迟。皖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即表明中共中央此时并未有放弃皖南的想法,故仅指示军部及部分部队北移,皖南地区以部分部队游击坚持,以保持一个重要的南方战略据点。同日,叶挺返回军部后,随即就延安指示组织商讨,13日即将讨论结果电告中央,虽表“赞同北渡方针”,但整体上仍持“固守皖南”的意见,认为如无军部在皖南坐镇,该地便缺乏坚持的条件,而且此时北渡仍不够安全。笔者以为,此种商讨方式应系召开军部和东南局的联席会议,而非仅限于叶、项二人或者军部内部,毕竟部队转移对地方党的工作影响匪浅。如此一来,前文所述落款问题即可得以明了。
其次,该文中提到,“敌人‘扫荡’结果,友军布置错乱,伤亡更大”;“部队胜利信心进攻此次反‘扫荡’已更提高”;即日伪军在皖南发动该年度的第二次“扫荡”,时间为10月4日—11日;而此不仅打乱了顾祝同在皖南对新四军形成的既有布置,同时亦因新四军的有力作战,广受当地民众拥护,“众誉军部驻地为铁打的云岭”,凡此均使项英等军部领导相信坚持原地即可应付危局。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该文电日期应为“10月13日”。经此考证,亦可看出,项英等军部领导在中共中央与中原局一再电催转移的情况下,却因对周边形势判断过分乐观,对转移指示贯彻不力,故对后来造成的损失应负较大责任。当然,随着时局益趋严峻,军部亦转而动摇于坚守皖南而不转移兵力,或放弃皖南东移苏南或北渡皖东之间,已然不是10月初固守皖南即可应付的心理了。因此,当中央作出放弃皖南、坚决北移时,项英等军部领导立即复电同意,随后双方的分歧,更多是北移时机和路线等方面,而非转移与否的原则性问题。
七、《周恩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在无为以东北渡为宜致叶挺、项英电》的时间问题
1994年出版的《新四军·文献》(2)收录了这份文件,标注的时间为1940年10月20日。笔者发现,稍后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在收入此文电时,基本照录了1994年出版的《新四军·文献(2)》内容,即在日期判定上仍为“10月20日”,略有更易的是,对《新四军·文献(2)》中“另一方向顾,说明如相逼过甚竟出事端”之中的判识为“威胁”;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7册)基本上是将《周恩来军事文选》所载此文照录,均认定时间为10月20日。但周恩来的落款实仅有“二十日 渝”,即表明月份是由编者研判得来。笔者阅读后,甚觉不妥:
其一,《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给出的注释1,表明编者是根据“皓电”是19日来推论而来,似未明白该文件实际向周恩来等人传达时间为21日;虽然周恩来通过地下战线提前获悉此电内容,随即密电告知延安。但问题是,周在电告中共中央此一情报后,如对皖南新四军转移等重要问题有想法,应先与延安进行协商,再由后者对新四军军部作指示。转移问题影响到国共关系的全局,在皖南危局尚未彻底明朗前,周恩来应不可能先贸然向军部提出建议,24日才向中央汇报想法;而且24日的建议,即“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又与20日文电意见存在较大差异,似不合理。
其次,电文中有“江南在日人‘扫荡’及韩德勤被围攻状态下,可能一时和缓”等语。陈毅部于10月上旬黄桥战役中重创韩德勤部,尽管刘少奇有乘势解决韩部的想法,但中共中央主张对韩采取缓和态度,并数电刘、陈慎重行事,周恩来亦于10月15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刘、陈“必须拿稳逼韩攻势”,采取自卫,而非“彻底灭韩”,经毛获允并转达刘、陈。为实行“逼韩攻势”,中共苏北各部对韩部逐渐呈现出合围的态势,但更多是“围而不攻”,通过“逼韩”谋取华中及江南局势的转圜。即便此种态势被周恩来理解为“围攻”,但周在获知“皓电”内容后,对国民党反共态度的估计是非常严重的,即“反共高潮是着着上升”,周感觉事态严重,如违反常规就皖南部队移动向叶、项献策,完全可以建议通过苏北问题来迫使顾祝同让步,而非称“向顾威胁,说明如相逼过甚竟出事端,背水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或可使顾在执行蒋、何密令时有所顾虑”。文电亦提到日军在江南地区的“扫荡”,查1940年日伪军在江南地区活动概况,10月4—11日,日伪军在皖南地区“扫荡”,12月份日伪军在茅山地区“扫荡”;显然如将月份定为“10月”,日伪军在江南“扫荡”和“韩德勤被围攻”在时间上无法重合。
其三,10月27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及南方局时提到,“上官云相约我冬日在泾县会见,我们拟均不见”,如果周恩来早在20日就已密电授意叶、项与顾祝同交涉,而且周此份文电显系催促其尽快转移。面对上官云相的约见,应是叶、项在周恩来已部分让渡新四军问题交涉权的情况下,交涉转移问题的良机,何以叶、项“拟均不见”?该电提到叶挺认为自己有去的必要,给出的理由却是“以免使彼借口而影响与上官的关系(目前我受上官指挥)”,丝毫未涉及转移问题。此外,10月30日,叶、项致电延安时提到,“解决上官提出皖南部队北移皖北的方案,希夷答复去皖北实行困难而重提四月间与顾的移苏南的方案,唯均未做决定,只算初步商谈”,上官与叶的此次商谈,仅为“皓电”发布后的初步接洽。其商谈目的,笔者以为,是顾祝同让上官借敦促新四军执行“皓电”要求之机,来摸清苏北中共军队的态度。从此次汇报来看,顾祝同倾向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皖北”,而这恰与周恩来提议北渡“无为以东”有部分契合,既有周恩来的指示,叶挺自应是就走北线问题争取国民党方在无为等沿江渡口方面提供安全保障,而非“重提四月间与顾的移苏南的方案”。
如将月份定为“11月”,顾祝同于11月18日已允许皖南新四军经苏南过江,实无“威胁”顾的必要,故11月亦不符合。经过对史料的比勘,笔者以为,该文电日期似为“1940年12月20日”。原因如下:
其一,周恩来并未及时获悉苏北停战的消息。尽管刘少奇在12月15日就向中共中央表达停战的想法,次日获允,但部队回撤休整尚需时日,故有20日延安致电刘少奇、陈毅,“我军应停止于兴、高以外地区,苏北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22日刘、陈才电告中央及军部和南方局,称“苏北各部自本月十九日起已停止冲突,返回原防”,即12月20日,周恩来尚未明了苏北已停战,故其文电中有“韩德勤被围攻”的表述。
其次,周的提议似乎与时下皖南新四军面临的局势相契合。曹甸战役爆发后,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嘱咐顾祝同,为防江南新四军直接参与对韩德勤的攻击,不准新四军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顾收电报后,并未立即对叶挺下达指示,而是先将蒋电密告将参与12月底进攻皖南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称“勿谈(新四军)再过苏南”,并散布共军北移的消息,引发敌伪注意,“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14日顾祝同对皖南新四军提出“经过苏南不免展缓,应以主力就近北渡皖北”。这样,新四军军部“明走苏南,暗渡皖东”的方案便缺乏了隐蔽性,桂系在江北似亦呈现出加强防堵的态势;原定12月15或16日北渡皖东将就暂难执行,故周恩来提议“急应抢渡一部”。21日,军部电告中央及周恩来等,桂系157师“一个团到牛埠(无为西南),准备攻无为东乡我军,后续仍有一个师跟进”,即否定了周“宜在无为以东渡江”的建议。22日周恩来提议皖南部队宜移苏南,并继续与张冲等国民党要员继续交涉。
其三,电报中提到“蒋、何逼我新四军渡江之决定决不会取消的”,这一点如果放在12月20日,亦能更好地理解,即“皓电”的第一个截止期已过,后来蒋又允诺展期至12月底。尽管当时周恩来等人交涉再展期一个月,但他们亦明白,蒋介石即便会再度同意展期,但决不会取消北移的命令。此时局势已经显明,即国民党方面要求新四军部队北移势在必行,中共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争取充裕的北移准备时间。实际上,12月中旬,当叶、项得知北移消息已遭泄露时,在电告中共中央时已转告了周恩来,而此时周在重庆与国民党高层的谈判亦陷入僵局,故接到叶、项的电报后,仍为争取展缓皖南新四军北移而努力;18日又收到延安要求缓和顾祝同对江南新四军攻势的文电后,情势似将急转直下,周恩来直接急电叶、项亦是情理中事。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文电日期应为“12月20日”。此时,国共重庆交涉和苏北战局均成僵局,故无法以苏北围歼韩德勤来迫顾祝同让步,而周亦只能向叶、项提出“向顾威胁,说明如相逼过甚竟出事端,背水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的建议,而这亦是中共高层普遍所持的蒋介石怕皖南新四军“扰其后方”思想的体现;同时似亦表明,皖南事变爆发前的较长时间里,针对皖南部队转移方向,中共中央更倾向其北移皖东,以壮大其发展华中的力量。
通过对七份文电日期的考证,似在表明,就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而言,在事变前的较长时间里,项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更多体现在转移路线与时机上。项英更倾向于“东移苏南”,而中共中央倾向于“北移皖东”,但双方亦因外部情势影响而作出调适,并不存在根本对立。但因对时局判断的乐观,项英等人在1940年10月中旬转而倾向固守皖南,对中央指示贯彻不力;但当11月初延安决定放弃皖南、坚持北移后,项英等人亦随之作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