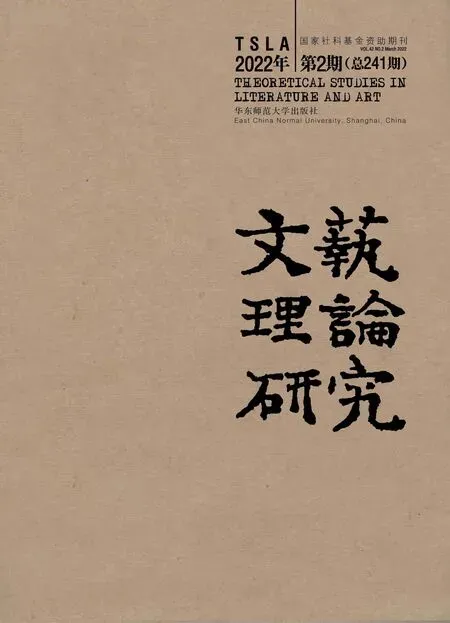从符号化的意向性通向艺术符号学的哲学向度: 归纳认知视域下的赝品问题再探
安 静
一、 引入:“以假乱真”和“以假代真”背后的归纳逻辑悖论
众所周知,赝品一般是指那些与真迹相对,能够在外观上混同于真迹的作品。赝品虽是收藏家的噩梦,但在很多时候,我们明知是假而依然代以为真。此处所探讨的赝品不仅是指与真迹难以辨别的完美赝品,也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真迹代替品。赝品在艺术哲学中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域——赝品关乎艺术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古德曼“艺术的语言”,79—100),它到底有没有价值(章辉47—55),能不能被称为艺术品等(Carter1),这些问题让赝品与艺术体制(李素军210—216)、艺术家、艺术史等话题都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比较有定论性的观点是,赝品具有审美价值,但并没有艺术史价值。在关于赝品问题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赝品所引发的广义的认知价值问题,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两类赝品的不同情况——“以假乱真”和“以假代真”。前者是我们试图避免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我们的主动选择。在学术历史上,关于“以假乱真”的赝品最为著名的例证莫过于梵·梅格伦模仿维梅尔的画作了,这就是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所说的“完美的赝品”——特指那些不标明仿作而带有欺骗性目的的赝品,这类赝品制作手法非常高明,足够以假乱真,对原作构成极大的挑战。上世纪30年代,汉·梵·梅格伦(Han van Meegeren)仿造17世纪荷兰大师级画家杨·维米尔(Jan Vermeer)制作了一些油画。由于使用了非常狡猾的绘画手段,这些作品使很多艺术鉴赏专家信以为真,认为那是维米尔一些罕见的作品,甚至当伪造者本人对某些伪作供认不讳时,很多号称专家的人依然不肯相信那是赝品。1967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科学家们进行了这项研究,小组利用X光透视画件、碳的同位素放射方法以判断这些画作是否系伪造。在这次伪作事件中,古德曼在符号学的层面解决了哪类作品能够被复制的问题,古德曼说,“音乐中没有已知作品的赝品这种事情”(《艺术的语言》91)。古德曼对“亲笔艺术”(autographic)和“代笔艺术”(allographic)(92)进行了区分;借鉴记谱理论,引申出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符号学解读,给出五个审美征候。毫无疑问,古德曼从符号学层面给予赝品问题以重要的启示,《艺术的语言》成为与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并置的经典文献地位就是明证。耐人寻味的是,古德曼在这里同样提出了关于赝品的认知问题: 当我们排除技术手段介入的界定过程后,我——观看者——能否直接感知出两幅作品的差异?答案是肯定的,“现在的观看在训练我在这两幅图像之间以及在其他图像之间做出区分的感知力”(86)。其中关窍在于对鉴赏者不断的训练和实践,而不仅仅是自然的敏锐视觉。观察和训练的最终目标,是确立某一位艺术家的惯例类型(precedent-classes)。一旦这种惯例类型确立起来,曾经需要建立在各种技术手段的严密监测才能判定真伪的作品,现在也可以一眼就识别出来,从而完成现象学所谓的“本质直观”,实现对具体符号构成的本质超越。
当我们探讨赝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艺术体制问题时,这些讨论的范围基本无法离开专业的艺术领域;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赝品所面对的对象是范围更加广泛的普通人群,因此,赝品所产生的价值,从更加普适的角度来看,是赝品的认知价值,也就是“以假代真”的赝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各种儿童艺术读物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印刷版《蒙娜丽莎》《向日葵》,但几乎所有图书都不会标出“这些是印刷赝品”的字样,而是会有板有眼地告诉孩子,这是某国艺术家的某部作品,它的布局与色彩是如何精妙,它在艺术史上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等;或者,会写一句,它的原作收藏于某著名的博物馆,但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告诉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这是“赝品”,而是把印刷品作为真迹的一个替代品来培养儿童对艺术品初步的认知能力。然而,仅仅是对孩子如此吗?就连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印刷精美的《神圣艺术》这一系列恢弘的艺术史著作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在细节放大的铜版纸印刷品上,我们的认知极力要告诉我们,这种精美的印刷所表征的艺术特征,就是真迹的艺术特征,我们所向往的真迹已经近在咫尺,甚至我们在真迹上也不可能这样凑近观看如此细微的“艺术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认知层面是有意地进行了“以假代真”的替换。
上述两类赝品问题,无论是“以假乱真”的鉴别还是“以假代真”的替换都存在一个归纳逻辑的问题。在“以假乱真”的鉴别过程中,鉴赏者需要不断从真迹与赝品的比较过程中提炼分别属于梅格伦和维米尔的审美类型,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来进行,但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依靠人的鉴赏力可以独自完成鉴定的审美惯例类型,技术只是确立这种审美类型的一种辅助条件。如果技术已经鉴定出来孰真孰伪,那么鉴赏者的任务就是通过不断学习来确定自己对不同审美类型构成要件的归纳途径和归纳方法。在“以假代真”的学习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归纳的过程。通过对赝品的反复观看,鉴赏者最终要学习真迹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以便在面对真迹的那一刻,可以确证自己曾经学习的各种细节都是真实有效的。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不同,天然地包含或然性结论,这虽然与追求唯一确定答案的演绎逻辑相反,但归纳逻辑却更加符合认知的实际发展过程,因为无论是“以假乱真”还是“以假代真”,作为鉴赏者都会存在真伪不确定或者说真伪混同的状况。这两种状况都蕴含着归纳的逻辑过程,都属于归纳逻辑中的认知概率问题。认知概率适合于命题或陈述句,而不适用于推理。在上述“以假乱真”和“以假代真”的认知过程中,鉴赏者都要进行相关的知识储备,认知概率就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关于命题的认知概率不是由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归纳概率的变化而引起,而是在于无论是借助技术手段还是借助不断的学习,鉴赏者的认知过程都会增加新的信息,这些新增信息又是在不断强化关于该作品是真是伪的认知概率。最终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休谟所说的归纳认知中的“习惯”,即不经过任何推理和思量,仅根据对类似现象的反复观察而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作出关于真伪的判断。由于知识背景、鉴赏者的学习水平乃至技术的手段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关于真伪判断不断反复的过程,因此在鉴定者对以假乱真提出最后判断之前,在以假代真的学习者面对真迹之前,都会产生一种真伪混同的情况;而且,所有的归纳问题都面临着休谟所说的归纳悖论: 即从特殊现象出发归纳而出的结论,为何能够跨越到一般的结论?休谟主要关注归纳的规则性。后来,古德曼对此有新的发展,这就是新的归纳难题——对古德曼而言,问题不在于保证归纳在未来仍然有效,而是试图以不太随意且不太含糊的方式刻画归纳是什么,也就是揭示出归纳的过程,进而将这个过程的投射性进行质疑,这就是古德曼提出的“绿蓝悖论”。绿蓝悖论恰恰符合赝品认知过程中的真伪混同的情况。
古德曼在1946年提出著名的“绿蓝悖论”,被誉为继休谟提出“旧归纳之谜”的新归纳之谜,在哲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然而,绿蓝悖论和赝品之间的联系还未曾有人注意到。归纳推理的基本形式是: 如果S_1是P, S_2是P,……一直到S_n也是P,那么可以归纳为S都是P。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是确定归纳结论成立的依据,归纳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但因果链条的确立只能借助于经验;这就造成了从个别经验出发的知识最终要得出超越经验的一般结论。在休谟问题背后,是知识归纳所建构的知识是否可信。古德曼认为:“归纳难题不是关于解证(demonstration)的难题,而是界定有效预测与无效预测之间差别的难题。”(古德曼,《事实、虚构和预测》83)为此,古德曼提出了他的“绿蓝悖论”。假定在一给定时刻t之前被检验的所有宝石都是绿色的,t表示未来的某个时刻。于是,在t时刻,我们的观察支持假说“所有翡翠都是绿色的”;当引入另外一个谓词“格路”(grue),它适用于在时间t以前检验为绿色的所有事物,以及对于其他情况为蓝色的其他事物。假设一块宝石是绿蓝的,当且仅当,它在t时刻之前被观察且是绿的,或者它在t之前未被观察且是蓝的。由于现在观察的一个翡翠满足绿蓝的定义,所以这个结论与之前的结论是相悖的。(89—97)这意味着,相同的观察证据以同等的程度认证了两个互不相容的假说(陈晓平23—24)。对赝品的判断,古德曼提出,如果某人x不能在某个时间t仅仅通过观看就将它们分辨开来,那么对于在时间t的x来说,这两幅图像之间是否存在审美上的差异(《艺术的语言》85)?古德曼不否认赝品问题的审美价值,但是在这种提问方式下,可以说绿蓝悖论投射到了赝品问题的判断。对于未来判定的某个t时刻之前,完美的赝品符合绿蓝悖论的基本内容,真假是无从定论的,的确存在一个“绿蓝悖论”的时刻。所以,假设一件作品是真或是伪的,当且仅当,它在t时刻之前被观察且是伪作,或者它在t之前未被观察且是真的。t表示未来的某个时刻。
赝品问题存在鲜明的意向行为过程,而且由于鉴定时刻的存在,赝品的鉴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过程。在“以假乱真”的判断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个真伪混同的时刻,无论技术手段是否介入。即使是在技术手段介入之后,依然有专家确信这是真迹,这些专家并没有将维米尔和梅格伦的审美惯例类型确立起来。在“以假代真”的接受过程中,其实鉴赏者并没有看到真迹,但他的任务是要把二者逐渐对接起来,直到他真的面对真迹那一刻,赝品才算退出了他的归纳系统。由于审美鉴赏是将客体转变为审美对象的过程,存在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的意向性过程。为了把这个过程清晰地展现出来,结合学术发展的历史,本文尝试提出“符号化的意向性”这一概念。
二、 符号化的意向性: 符号学、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再次相遇
“符号化的意向性”旨在用符号学的认知推理过程阐释意向性问题。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关注语言的意义问题以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成为20世纪哲学的主要话题——分析哲学从对语言的批判入手,发展出从语句意义来判定命题真伪的研究方法,即命题分析真。现象学以“意向性”作为基点概念,主张调和主客二元对立立场,体现出深刻的层次性,这些层面分别是相当于意识感受性的心理意向性、相当于意识关联性的关系意向性以及相当于意识构造性的构成意向性(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484)。现象学虽然聚焦于意识研究,但关于意向性的解读也离不开意义,而意义和思想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从学理上说,意向性问题甚至可以起到统摄语言-心灵-世界这个分析哲学中著名的语义三角关系的作用。”(张志林51)所以,意向性问题在分析哲学中也有广泛的讨论,其展开模式主要依据语言逻辑分析,也就是将心灵的意向性状态转换成思想语言的表征状态,这里已经触及到符号学的内容。所以说,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发源相当近,并一度沿着大致并列的河道流动,只是最终分出完全不同的方向,流入不同的海洋”(达米特26)。由于意义的载体不仅限于语言,“符号”成为更广义的切入点。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构成意义的学问,但意义的建立过程离不开意识的不断参与,可以说,在符号学的学术理路中,分析哲学与现象学都是天然存在的,“[……]它们[符号学与现象学]的论域重叠如此之多,可以说,无法找到不讨论意识诸问题的符号学,也无法找到不讨论意义诸问题的现象学”(赵毅衡,《意义理论》4)。
“意向性”在布伦塔诺这里第一次成为具有哲学色彩的专有名词,他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独有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可以通过意向性或者意向内存在(Inexistenze)的指明,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倪梁康47)。“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为解决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这一美学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方法。在意向性理论视野中,审美对象就不再是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意向性、关系性价值性的存在。”(张永清,《意向性理论》80)在胡塞尔看来,意识的本质在于意识的意向性,所谓意向性就是艺术对某物的指向性。意向性的基本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意向行为(Noesis)与意向对象(Noema)。所谓意向行为,是指意识投向对象的行为。胡塞尔将其分为“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是指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而非客体化的行为并不构造对象,但需要指向对象。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而意向对象,国内外对这一概念的阐述也是见仁见智。就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而言,胡塞尔本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前后并不一致,因此哲学家对此的解释和分析也分为多个层次(贝耐特150—170)。胡塞尔自己的举例是,观看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向观察同一个盒子,每次都看到不同的东西,现象学不关心盒子本身,而每次增加的新东西就是现象学所关注的意向部分(胡塞尔,《逻辑研究》449)。皮尔斯在现象学视野下,以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为支撑,并对这种观察进行概括,提出几种极为广泛的现象类型,然后描述每一种类型的特性(皮尔斯,《论符号》9)。
在皮尔斯符号体系下,存在(being)有三种模式: 我们直接面对的是事物的“第二性”(secondness),即一个事件的实际存在状况(actuality),如某种事实;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两种模式——第一性(first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第一性这种存在实在地存在于主体的存在之中,它只能是一种可能性(possiblity)。比如某种品质,红、苦、高贵等。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存在,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观念的抽象之中。第三性是一种倾向性,它存在于这些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是第二性的未来事实所具有的一种确定的一般品格。它既非品质,也非事实,而是一种在品质和事实之间的间性。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过程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刚刚接触时的可能性,中间过程的实在性以及最后主客一体的融合性。艺术赝品的存在,使艺术符号诸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审美鉴赏的意向性过程更为复杂,这种实在性的过程存在真假混同的“绿蓝”状态,让我们从符号学和现象学的多层次探讨成为可能。
相比于最后的结论,赝品问题的中间过程是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从物理现象来说,“以假乱真”的赝品当然不会是一个似是而非、亦真亦假的审美的客体。但是,在心理意识层面,赝品的识别却并不一定是确定无疑的赝品,特别是在技术手段介入之前;在技术手段介入之后,反复观摩赝品的意义在于修正之前的认知经验,从而在下一次遇到完美的赝品时,可以达到“本质直观”而不需要技术。只有在鉴赏者全部掌握真迹的审美特征之后,鉴别“以假代真”的赝品这一任务才算真正完成,否则便一直存在一种以赝品艺术符号替代真迹认知的状态,其间主体在观念中的意向性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赝品的发现处在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状态中。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实体性的研究,以清晰阐释和逻辑自洽为追求,是在共时层面的研究,但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却是一种相互培养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充满动态和变化的。相比于真迹的审美过程而言,对赝品的鉴定和鉴赏过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意向性过程。由于真伪之别,对于赝品的观看过程不能仅停留在“感受直观”的层面,而更应该走向“本质直观”。审美对象不等于审美客体,“某物是赝品”的判断仅是对审美客体的感受直观,但又因赝品的“完美”对审美主体所形成的影响最终应该是一种“本质直观”,那么,对于赝品的观看过程,经历了怎样的符号学和现象学过程?
首先是“感受直观”(feeling intuition),这是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发生关联的第一步,这个过程与符号的第一性相对应。“感受”用皮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指某种意识的一个实例(instance),而这种意识既不包含分析、比较或者任何过程,也不存在于任何可以使一段意识区别于另一段意识的行为之中”(《论符号》15)。皮尔斯认为,符号的意义活动应该包括三个阶段,符号的第一性就是符号的“显现性”,是首先的和短暂的,它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是整体的和瞬时的。在这里,皮尔斯并不是指意识主体真正地经历过某种感觉,而是指事物本身性质的诸种“可能”(may-bes)(14)。这种可能性的根源是知觉的意向对象并不确定是哪种性质最先被感知到。所以,在人的知觉在确定意向对象之前,它首先是一个事物,只有在意向行为产生之后,这个事物的某一方面才成为符号,才能体现出符号性来。而在感觉直观的阶段,事物只是整体性地成为知觉中的事物,并没有成为一个狭义的意向对象,即产生意向内容的对象。就赝品问题而言,在感受直观的过程中,赝品与真迹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因为主体并不知道这是赝品还是真迹,主体在这个阶段只是对物品的接受,是一种整体的接受,至于那一部分会成为产生意义的“意向对象”,还是一种可能性。
其次是“形式直观”(formal intuition)。形式直观是“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产生意义的无限衍义(赵毅衡,《形式直观》18—26)。在形式直观这一步,符号学和现象学实现了彻底的融合。符号的第二性是意识主体获得意义的初始阶段,即对象由“事物”转变为“符号”的过程。皮尔斯在论述第二性时,特别提到了一种“关系状态”,即“关于某时和某地具体说明包含所有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事件的现实性似乎存在于与存在物的宇宙的关系之中”(《皮尔斯文选》169)。由于这种关系相关性的存在,意向行为产生,物转变为意向对象,主客之间的现实性建立了起来,也就是产生意义的阶段。这一点与现象学的看法是一致的。杜夫海纳说:“形式与其说是对象的形状,不如说是主体同客体构成的这种体系的形状,是不倦地在我们身上表示的并构成主体和客体的这种‘与世界之关系’的形状。”(杜夫海纳267)在此前提下,意义的产生过程,就成为意向行为向意向对象投射的关系结果。形式直观与符号的第二性相对应,这里是产生意义的起始点,对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而言,赝品问题所产生的形式直观也是各自相异的。如果说,被确定的真迹都是由人工符号构成,意向行为从一开始就体现出符号性那么,赝品却并不全然如此,而是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识别的前后。在被识别出来之前,赝品的形式直观与其他艺术作品一样,都属于符号对象的初级解读阶段,是艺术作品第二符号性的产生阶段,它本来就是作为意义的载体而被创造出来。所有的人都会将其作为真迹而进入第三个阶段——本质直观,也就是对它的审美价值进行判定。在被识别之后,对赝品的形式直观就会产生很多层次的意向行为,不同的意向对象会与主体产生不同的关系类型。以梅格伦的仿作为例,有明确指向性后,鉴赏者就会修正自己的经验类型,在观念中产生真伪鉴别不同的判断结果,争取在下一次见到类似的完美赝品时可以直接进行本质直观。但是,也有很多鉴赏者或者说鉴定者依然不肯相信这是伪作,依然认为这就是维米尔本人的真迹。在后一种情况中,形式直观成为一种固定的见解,他们恪守着自己的意向对象而不肯改变自己的意向行为,“形式就是审美对象的真实性,它具有真实性所专有的那种无时间性的特质”(200)。这一类鉴赏者剔除了对象鉴定中的时间要素,而仅以语义要素来确定其真伪。
第三个阶段是本质直观,它与符号的第三性相对应。对于所观对象,我们终究要走向第三个阶段,即形成判断。用皮尔斯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思想中具有三个要素: 第一,表象的功能,它使思想成为表象;第二,纯粹指示性应用或者真实的联系,它使一种思想和另一种思想联系起来;第三,物质的品质,或者它是如何感觉的,它把自己的品质赋予思想。”(《皮尔斯文选》135)就赝品问题而言,我们在第三个阶段要形成观者对事物最终的判断。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的根本方法,它“不只是感性的、经验的看,而是(Sehen überhaupt),是一切合理论断的最终合法根源”(《纯粹现象学通论》77)。在胡塞尔看来,本质直观首先意味着直接把握对象的意识行为,并且不会受到客观对象的限制。也就是说,就赝品问题而言,我们在这个阶段的直观过程中,要达到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判断结果,而不仅是真与伪的问题;这种判断必然是要以判断者背后所依据的艺术史知识和艺术鉴赏经验作为背书。胡塞尔说,本质直观是“一种给与的直观,这个直观在其‘机体的’自性中把握着本质”(52)。这个过程不需要中介,它并不是肉眼之看,而是精神之看。对于完美的赝品而言,达到本质直观这一步其实是经过一个反复观审的过程的。最开始,即使是通过仪器检测得出这是赝品的结论,也依然有很多业内专家固执地认为,这些“作品”就是维米尔的真迹。显然,这些固执己见的专家在这个阶段并没有达到胡塞尔所说的“本质直观”,他们还没有形成对这些作品的本质认识。进一步,两幅图像之间的差异会教会观看者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不同,用古德曼的话说来说:“这种知识现在就指导我观看和分辨那两幅图像,即使我所看见的东西完全一样。除了确证我可以学会去看出差异来之外,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指出了现在可以适用的那种审查、在想象中进行的比较和对照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联想。”(古德曼,《艺术的语言》,86)需要注意的是,古德曼在这里同样提到了想象,而想象正是本质直观最重要的方法:“它[本质直观]需要通过知觉与想象尤其是想象的自由变更才能达到。”(张永清,《现象学的本质》110)由于想象的心理特征是在精神世界的自由展开,是知性和理性的和谐融合,所以,本质直观成为无需中介的活动,而恰恰是它的无所依傍成就了这份“自由”。这是本质直观最终的理想状态。对于赝品的判断,本质直观具有最终的和最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个过程需要符号参与吗?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本质直观不需要中介;但是,问题并不止于此。观者首先需要“知识”,然后才是想象。所以,本质直观的前提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这个阶段不能离开符号;只有知识基础足够牢固,才有能力超越符号这个桥梁和中介,进而对眼前的对象进行意向投射,通过自由想象得出本质结论。所以,本质直观的过程虽然不需要中介,但是意向行为的准确投射所建立的基础是离不开符号过程的。
可以说,对于赝品的价值判断经由感受直观、形式直观,再到本质直观,符号在整个过程中是基础,是桥梁,但也是认识飞跃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离开符号不能进入本质直观,也就是说,本质直观是不能凭空产生的。所以,“符号化的意向性”是阐释从感性直观到本质直观的必要过程。这一点,几乎是我们面对所有物品进行判断它究竟是不是艺术品,或者一件艺术品真伪时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意向与视域融合性,我们对赝品问题的认知都要经历一个“借名”的过程,既然是“借”,意味着最终我们就要摆脱开它。这种摆脱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像古德曼所说,即使是技术手段不能识别的赝品,但经过长期的训练和实践,主体可以一眼就看到它是赝品;二是像艺术读本中的精细化学习过程中,我们在句法层面用符号完成了赝品对真迹的替换。而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主体的最终目的是脱离开艺术文本的符号构成而进入“本质直观”,也就是一个从“器”入“道”的过程,从而产生由依据符号到脱离符号的哲学向度。
三、 借符与借名: 从赝品问题通向艺术符号学哲学向度的可能途径
综上所述,赝品的命名与定义最终走向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形式”成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标志,对形式的反思构成了“形而上学”。我们有关赝品问题的反思,首先的要点在于,“形式”在认识论的建构过程中的意义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自16世纪末起,西欧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18世纪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观念论标志着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这个过程中,“形式”研究成为连接事物属性和认知真理的桥梁,经验论以研究事物形式为己任,而观念论则以逻辑推理从深层助力形式研究,共同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在此前提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则以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和形式构成为主要目标。由于语言是符号的典型代表,语言学研究同时也成为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从深层学理联系来看,语言学、逻辑学成为绕不开的两个领域。在布隆菲尔德的《语言论》中,“形式(form)和意义(meaning)”属于符号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一种形式往往把它说成是表达意义的”(布隆菲尔德147)。但是,艺术的形式从来不单纯是一种物理结构,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建构,“形而上学”的必然结果是对形式的借用而非立足。在以假乱真的情形中,属于梅格伦的审美类型确立之后,就不存在模仿维米尔的赝品了;在以假代真的情形中,赝品其实充当真迹的替代品,在认识过程中,实际发挥的是真迹的认知作用。就语义学而言,如果每个形式元素被成功替换,也就不存在符号学意义上的赝品问题了,所以,“形式”研究可以构成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成为符号学的唯一理论基石。
就名称而言,对艺术作品的真伪的判断和命名,是认知主体对这一作品观念的符号呈现,是否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赝品,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仅以欺骗性的外观来定义赝品,也只是定义了这一类作品在人们认知观念上的暂时的欺骗性,当独立的审美类型的确立时,无论是以假乱真的赝品的审美类型的确立,还是以假代真的美学知识的学习,赝品都完成了它的认知使命。因此,无论在符号语义学层面的要素替换,还是在认知层面的观念建构,赝品的界定其实始终和时间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审美主体鲜明的意向性过程,对赝品的鉴别和鉴赏充满了思辨的趣味。绘画视觉艺术如此,更何况像音乐、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是基本无关乎赝品问题的,我们不会因为一部乐谱由不同的乐队演奏而称之为赝品。这也恰恰印证了索绪尔给符号的定义: 符号联系的是概念和声音结构,在本质上它是一种二元的心理实体(索绪尔101)。
既然符号是一种二元的心理实体,这就必然要求赝品问题研究去探寻经验论与观念论之间的辩证张力,打破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走向一种纵深的学问追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后逐渐走向一种融合的思路。经验论重在分析心理体验过程,认为知识的来源是感性的经验,但并没有将经验的基础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而是认为经验属于主观世界,将事物本身和所见经验同一化;观念论重在探讨观念与判断,符号学关注意义问题,其实也就是观念中对事物的判断。分析哲学注重语言的真值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逻辑推理。然而,审美判断的复杂性在于,艺术作品的意义从来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必然不能离开现象学对艺术意义的生成作用,也就是从经验到观念不断反复的过程。然而,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并不是一个天然的结果,而是认识主体在符号认知过程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是根据意识所指经的(direct through)抽象的内涵结构(语义的模拟)来说明意识的意向性”(霍尔46)。科学的归纳系统应该是一个规则的系统,它以不同层次的规则性对应于不同层次的论证方式,这个系统与科学实践非常一致。它必须在每个层次上进行预设,然后对未来进行判断。在实际的实践进行过程中,才能真正沟通经验论与观念论的二元对立,是主体走向审美认知自由的必然途径。实践真正确立了赝品鉴赏的认知依据。本质直观不是抽象的和先验的,而是在不断的符号认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对于赝品而言,最终形成的本质直观判断,进而达到现象学所追求的“先验还原”,是对符号规则深谙于心的结果,进而指导意识形成新的审美范型,才能在下一次面对同样的情况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符号同时包括了自然和文化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在总体上向着人类经验世界敞开,其总体性则同等地包括了处于共识性知识核心的‘常识’和具有现代发展特色的实践性知识”(迪利83),因此,在人这个主体的世界里,实践成为这种总体性实现的肯綮所在。
启蒙运动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真理,历史的任务主要聚焦于此岸世界的真理,艺术成为救赎人类精神的有效途径。语言的意义问题是探讨赝品问题的逻辑起点,这是分析美学、符号学和现象学共同关注的领域,它们共同受到语言学转向的深层影响。然而,语言也由于能指与所指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确定扭结而对人形成文化与规则的约束。超越语言的二元对立,对艺术本真性的关注,这一切的背后真正的关涉是人这个主体,是人的精神自由如何实现的哲学向度。所以,语言背后的主观才是真正的批判场域,“如果真有所谓的和‘语言学转向’,那也不是通过语言来否定主观,而应该是在语言的视差上发现主观。这才是批判的‘场域’”(柄谷行人43)。对艺术品而言,是人的存在使艺术实现了意义的增殖;对赝品而言,其终究的价值指向也是人这个主观。符号学被戏称为“文科中的数学”,毫无疑问它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用符号学分析某种现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符号学是否能够解决形而上的问题,借此去思考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符号学并非完美无缺。符号学的两位创始人分别是索绪尔和皮尔斯,索绪尔的二元对立思路在解构主义哲学中遭到猛烈抨击,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将符号降格为“中介”,当意义有效获得时,符号是可以不在场的。并且,皮尔斯将不能够同时在场的符号三元并置在同一个逻辑链条上,将历时问题作共时化处理,也是不恰当的。哲学符号学的建立,不能离开实践的维度,符号学研究应当超越方法论的层次。人不断面对赝品的过程,就是实践不断建立主客联系的过程,在一种关系思维的框架不断修正自己认知与赋予对象价值的过程。实践不仅能够弥补符号学视野下艺术无真伪所带来的价值缺失,而且能够在交往的理论立场中深刻地阐释价值问题。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在一件艺术品与其他艺术的交往对话中产生价值,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实践所产生的交往,艺术与人一样,都是“孤独的他自己”,这是判断艺术是否具有本真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根本基点,也是人作为主体真正成为人的最终标尺。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消解二元对立,更进一步整合人类的思想资源,才能真正走向哲学的境界,共同面对人类思想的终极追求。
① 关于胡塞尔这一组哲学概念的命名,国内学者的译法并不统一,“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主要体现了现象学意向性的研究意图,而赵毅衡命名为“获义活动”与“获义对象”更多体现了符号学对意义问题的追求,本文旨在体现现象学与符号学的融合,而在赝品问题中,不仅要解决符号第一性的意义问题,而且需要给予审美经验不断滋养,还要解决作为第三性意义的“本质直观”问题,更加偏重现象学对赝品的观照方式,因此选择“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的译法(《形式直观》18—26)。
② 原文译作“感觉”(皮尔斯15),鉴于feeling的本义,本文译作“感受”。
鲁道夫·贝耐特: 《胡塞尔的“Noema”概念》,倪梁康译,赵汀阳主编: 《论证》。沈阳: 辽海出版社,1999年。
[Bernet, Rudolf. “Husserl’s Concept of ‘Noema’”, trans. Ni Liangkang.. Ed. Zhao Tingyang. Shenyang: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1999.]
伦纳德·布隆菲尔德: 《语言论》。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Bloomfield, Leonar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Carter, L. Curtis.. Wisconsin: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陈晓平: 《关于绿蓝悖论的消解——答邓桂芳和徐敏的质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1(2015): 23—24。
[Chen, Xiaoping. “On Elimination of the Grue Paradox — A Reply to Deng Guifang and Xu Min.”() 18.1(2015): 23-24.]
约翰·迪利: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周劲松译。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
[Deely, John.. Trans. Zhou Jinsong.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米·杜夫海纳: 《审美经验现象学》(上),韩树站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Dufrenne, Mikel.. Vol.1. Trans. Han Shuzhan.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
迈克尔·达米特: 《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Dummett, Michael.. Trans. Wang L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纳尔逊·古德曼: 《事实、虚构和预测》,刘华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年。
[Goodman, Nelson.,,. Trans. Liu Hua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 《艺术的语言》,彭锋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 -.. Trans. Peng F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哈里森·霍尔: 《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哲学意义》,《哲学译丛》6(1983): 46—49。
[Hall, Harrison.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Husserl’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6(1983): 46-49.]
埃德蒙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Husserl, Edmund.:.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逻辑研究》(修订本)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 - -.Vol.2. Trans. Ni Liangk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柄谷行人: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Karatani, Kojin.:Trans. Zhao Jinghu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1.]
李素军: 《艺术体制视域下的赝品问题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2016): 201—16。
[Li, Sujun. “Reflections on Forgery in the Context of Art Institutions.”2(2016): 210-16.]
倪梁康: 《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学术月刊》38.6(2006): 47—50。
[Ni, Liangkang.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ality in Phenomenological Context.”38.6(2006): 47-50.]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Peirce, Charles Sanders.Trans. Zhao Xingzhi.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 -.Trans. Tu Jiliang and Zhou Zhaop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
弗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年。
[Saussure, Ferdinand de.Trans. Gao Mingk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章辉: 《赝品: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问题》,《山东社会科学》4(2014): 47—55。
[Zhang, Hui. “Forgery: A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4(2014): 47-55.]
张永清: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对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人文杂志》2(2003): 108—12。
[Zhang, Yongqing.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ssential Intuition Theory of Phenomenology in Aesthetic Research.”2(2003): 108-12.]
——: 《意向性理论与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江苏社会科学》3(2001): 80—85。
[- - -. “The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and the Way of Aesthetic Object Existence.”3(2001): 80-85.]
张志林: 《分析哲学中的意向性问题》,《学术月刊》38.6(2006): 50—53。
[Zhang, Zhilin. “Intentionality in Analytic Philosophy.”38.6(2006): 50-53.]
赵毅衡: 《形式直观: 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文艺研究》1(2015): 18—26。
[Zhao, Yiheng. “Formal Intuiti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Symbolic Phenomenology.”1(2015): 18-26.]
——: 《意义理论,符号现象学,哲学符号学》,《符号与传媒》2(2017): 1—9。
[- - -. “Meaning Theory, Semiotic Phenomenology, Philosophical Semiotics.”2(2017):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