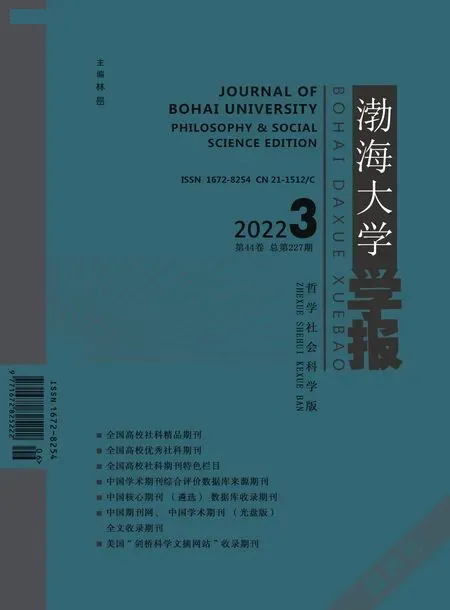格外艰难的写作
——新工人诗歌发表困境研究
李圆玲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000;.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北京 000)
新工人诗歌①是自发形成的。由于生活在困苦之中,难以排遣心中五味杂陈的情感,一些新工人便以诗歌为载体,抒发情志,舒缓情绪,以重新获得生活的力量。而后,由于报纸杂志,特别是地方报纸杂志,如《特区文学》《花城》《广州文艺》《珠海》《佛山文艺》等介入、引导,逐渐汇聚成一股力量,形成打工文学潮流,经过十多年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被命名为新工人诗歌,并在一定时期引发关注。但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文学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文学被网络文学、消费主义文学冲击,处境艰难。诗歌是受冲击最大的文学形式,逐渐被边缘化、圈层化,加之传统期刊面临转型,发表门槛提高,诗歌出版困难。这一系列变化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新工人诗歌的发表困境,阻碍其发展。
一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文学在互联网加持下繁荣发展;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成为大众文艺的生力军,促使大众文艺势力不断壮大,占领了主流消费市场。
但在消费主义时代,网络文艺空间瞬息万变,娱乐化属性使得网络文学成为海量信息中的一个小分支,其影响力很难持久。正如雅思贝斯所说:“公共生活变成单纯的娱乐;私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1]范雨素借助网络,凭借自传体作品《我叫范雨素》火遍全网,然而在遭媒体围堵后一个月便喧哗不再,两个月后已少有人谈起,现在基本上陷入沉寂之中。确如《撕开时代的沉默》一文所说:“相信过不了多久,范雨素就会变成别的名字,《我是范雨素》也会被别的话题取代,就像那几天她抢了《人民的名义》和‘达康书记’的戏一样。”[2]
但消费主义文学能够强有力地占据当下大众文化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消费主义文学煞费苦心地钻研大众心理,在依附、谄媚的同时,利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消费者,最终实现长久胜利,延续了消费主义文学的生命力。但消费主义文学生命力最初并不是源于意识控制,消费主义文学是在物质消费基础上产生的,而物质消费源自生产。马克思曾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是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3]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消费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消费主义文学源自最初的物质生产。但吊诡的是,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新工人群体,在这场消费主义主导的文化盛宴中却没有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新工人是这场盛宴的“黑暗面”,是消费主义生产背景下的“牺牲品”。在长期的辛劳中,他们创造出了消费世界的必需品,但在社会结构中这个群体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极少或几乎没有自我言说的能力,常常处于无尽的沉默之中,或处于被代言的状态之中。作为消费主义操控消费者的工具,大众媒介无疑成为第一个代言者。2000年前后,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的形象经常是负面的。然而,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新工人群体一旦浮出历史地表,便会打破消费主义粉饰的华丽世界,展示出现实粗粝的一面。新工人诗歌作为自我言说的媒介,就是新工人打破自身沉默的工具,无疑会对消费主义产生冲击。于是,在其打造、把控的世界中,消费主义对新工人群体进行文化遮蔽,通过操纵意识形态、同化大众认知等方式,让新工人诗歌背离大众审美,背离社会关注,从而让其消音②。比如,新工人诗歌的主阵地《大鹏湾》所发表的诗歌是站在消费主义对立面的,是为新工人群体摇旗呐喊的,但这样专门为新工人文学而创办的杂志,却因为市场的冲击而停办。除此之外,消费主义还借助其意识形态的强大威力对新工人诗歌进行“招安”,其首要目标就是新工人诗人。武善增在《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一文中指出:“许多作家在名利的驱赶下,以市场的要求为自己创作的目标,他们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并拼命炒作自己以使自己成为市场的新宠。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有的打工文学作家已经转向了以迎合市场、争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写作。如缪永与影视公司签约,批量化编写电视剧本,周崇贤后期转向传奇文学的写作,都是明证。”[4]
在消费主义的强大压力面前,新工人诗人坚守自我、不受诱惑相当困难;即使如此,仍有一些新工人诗人在坚持,甚至拓展自我。刘东在《贱民的歌唱》中谈及新工人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时说:“同样的道理:越是沦落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底部,选择文学生涯这种原本就风险很大的人生游戏,便越是表现为最无机会者的最大机会,即使由此而向上流动的概率微乎其微。”[5]郑小琼、谢湘南、曾文广、陈年喜、许立志就是在新工人诗歌被发掘后为人熟知,甚至获得一些诗歌奖项。2009年,广东作协破格提拔王十月、郑小琼担任《作品》杂志社副总编辑和副社长,他们完成了从打工作家到文学编辑再到文学期刊行政领导的身份转变,可以说,实现了逆袭。但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突破既往生活经验,拓展写作空间,另一方面也坚守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之“根”。比如,“自2005年起,郑小琼花了不少精力阅读先秦文与南北朝辞赋”[6],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作为突破自我的方式,为新工人诗歌写作寻找新的出路;同时这也是郑小琼向当代主流文学靠拢,为当代主流文学输送营养的积极尝试。
然而,像他们这种相对成功的范例少之又少。对于力图摆脱自身困境的新工人群体来说,他们的路径值得学习,即使无比艰难。退一步看,对于身负重压的新工人群体来说,资本的“招安”也可谓摆脱困境的契机。因此,部分新工人诗人转向,追随消费主义步伐,追寻生存空间,甚至彻底走上消费主义文学道路。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理解,而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新工人处境之艰难。实际上,即使算上成功转向消费主义写作的新工人诗人,成功者也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遑论众多尚在沉默中写作的新工人诗人。
二
新工人诗歌不仅在消费主义文化氛围中举步维艰,在传统文学领域相对圈层化、固化的情况下,想在主流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也并不容易。概括来看,成名作家由于积累了相当的名望资本,易于引发读者、社会关注,因而发表、出版作品相对顺风顺水,作品发表、出版逐渐形成内部循环消化的流通机制,产生一定的封闭性。有研究者指出,主流文学界“作家写给编辑看,编辑办给批评家看,批评家说给研讨会听,背后支撑的是作协期刊体制和学院体制”[7]。
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下,新工人诗人可谓脱离体制外、不在圈子中,不仅难以为自己谋得文坛的一隅之地,更难通过成为名家获得文学圈内人的认可。曾经多次发表过诗歌集的郑小琼,是新工人诗人中的成功案例,但也是仅有的个例,其他新工人诗人也在新工人诗歌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04年,在底层文学大讨论中,新工人诗歌作为其中一部分受到关注;第二次是2014年,许立志之死及《我的诗篇》上映,再次引起大众关注)落潮之后,再次沉入巨量的网络信息中,隐匿于主流文学界之外。一个直接的证据便是新工人诗人在《诗刊》《星星》等知名诗歌期刊发表诗歌数量的鲜明变化。2004年,新工人诗歌借助“底层文学”讨论之势浮出水面,当年《诗刊》全年发表了1278 首诗歌③,其中只发表了郁金1 首新工人诗歌。到2005年,“底层文学”研究热度不减,新工人诗歌也趁势而上,伴随着2005年《文艺争鸣》第3 期连续推出的多篇新工人诗歌研究文章,新工人诗歌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诗刊》当年便发表了4 首新工人诗歌,且除郁金之外,谢湘南、罗德远也有诗歌被《诗刊》发表。2006年,《诗刊》发表诗歌数量由上一年度的1352 首下降至714 首,仍然发表了5 首新工人诗歌,且在第21 期单独做了“打工诗选”作品选集,其中有20 位新工人诗人的23 首诗歌被选入。随着2007年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新潮奖”,《诗刊》与《星星》中也出现了郑小琼的作品,且《诗刊》与《星星》中出现的新工人诗人范围继续扩大,由郁金、罗德远、郑小琼到池沫树、柳冬妩、陈有才、程鹏、李明亮、张守刚等。这一热度持续到2010年后逐渐消退。2010年,《诗刊》全年共发表1480 首诗歌,其中有11 首是新工人诗歌;《星星》全年发表了724 首诗歌,其中有11 首是新工人诗歌。但是,越过高峰之后,新工人诗歌在《诗刊》《星星》中的发表数量急速锐减。2011年,《诗刊》全年发表1489 首诗歌,其中新工人诗歌仅有6首;《星星》同年发表543 首诗歌,仅有两首是新工人诗歌。此后3年,均未再超越2010年的发表数量。10年的数据对比,把新工人诗歌随着热度而起又随着热度消退的发表困境,以令人醒目的方式呈现出来。
不仅在知名诗刊上的热度不断降低,在知名诗歌公众号上,新工人诗歌也随着媒体热度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创办于2013年3月11日的诗歌公众号“读首诗再睡觉”,共发布了476篇原创内容,阅读量高的可达七八万,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其中,只发布了5 首新工人诗歌,其中有1 首郑小琼的诗,两首许立志的诗和两首陈年喜的诗④。在另一个具有广大读者群的诗歌公众号“为你读诗”中,新工人诗歌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为你读诗”创办于2013年6月1日,据统计已拥有1000 多万垂直优质用户,覆盖并影响了3000 万大众群体,但在这样的大V 诗歌公众号中,只发布了1 首新工人诗歌,即郑小琼的《他们》,发布时间是2021年5月1日,显然是因为劳动节,《他们》才有了这样的机会。
除了发表、出版难,作为文学界另一重要推动力量的评论家也未能真正重视新工人诗歌独特的美学价值。关于新工人诗歌的研究颇具争议,评论界以社会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分成两派,以张清华、张未民、蒋述卓、柳冬妩、吴敬思、王光明为主要代表,肯定新工人诗歌的社会价值,认为新工人诗歌的出现既是一个接近3 亿人的沉默群体的自我发声,同时也为当下诗歌发展迎来新的转机;以钱文亮、老刀、罗梅花、傅元峰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评论家则认为,新工人诗歌缺乏美学价值、贩卖苦难、视野狭窄、缺乏主体性等。对于注重其社会价值的评论家来说,新工人诗歌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现象,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社会现象,肯定其社会价值的同时,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又是对新工人诗歌的一种忽略。“‘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8],“无论是现实还是诗歌都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伦理问题的浮现而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确信它给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也因此给当代的诗人的社会良知与‘知识分子性’的幸存提供了一丝佐证”[8](52)。在肯定新工人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忽略了其文学价值、美学价值。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但从文学角度而言,新工人诗歌显然并非仅仅具有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或者说,如果缺乏独立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也无法得到更好的彰显,因而其文学方面的价值更值得关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褒贬,即使从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出发,研究、评论新工人诗歌也是昙花一现,随着2005年前后“底层文学”讨论热潮过去后,也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在断然否定新工人诗歌美学价值的评论话语里,则弥漫着浓烈的知识分子精英气息。20 世纪80年代,伴随着朦胧诗崛起而形成的诗歌评价体系,在评论家们不断阐释及反复演练中,形成一种审美无意识。利用这一精英化、现代化的美学标准来评价发端于灼热现实的诗歌,其结果自然是新工人诗歌文本空洞、视野狭窄、缺乏技巧。然而,在我们看来,与精英诗歌圈相比,新工人诗歌是来自“别一世界”的诗歌,就如鲁迅评价白莽的诗歌时所说的,“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9]也就是说,新工人诗歌正是那冬末的萌芽,属于“别一世界”,更是一个曾经处于沉默状态下无言者发出的生命呐喊,他们凭借自己微弱的力量,撕开了这个时代的沉默,贡献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范式,一种独特的有别于精英文学的诗歌美学。对于新工人诗歌的研究、评论,固然需要借鉴既有的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但我们更需要面对这一新的诗歌现象,创造、发展新的诗歌理论;至少,我们应该放宽理论的视野,避免用高度精英化了的现代主义美学这一把尺子去衡量新工人诗歌。当然,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而新工人诗歌徘徊在消费主义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夹缝中左右为难的境况,提醒我们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提醒我们打破这一困境的迫切性。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否认新工人诗歌内在美学上存在的缺憾。受生活环境、生存处境影响,新工人诗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质化的问题,比如,主题主要集中在思乡之情和工厂生活苦闷上。写思乡之情的代表作有陈向炜的《三千里外的乡愁》、唐以洪的《退着回到故乡》、程鹏的《乡愁》、吉克阿尤的《诗十首》之一《打工》、张俊的《七月,太阳是辽阔的火焰》等;写工厂生活苦闷的代表作有唐欣的《工厂记忆》《我的工厂》、田力的《一粒灰尘伏在你的肩上哭泣》《一闪而过的工厂》《卡通片:小人儿工厂》《深秋夜,工厂日记》《炼钢,炼钢》、蓝蓝的《铸造车间》《酒厂女工》《我的工友们》、绳子的《阶级兄弟》《穿工装的兄弟》《闲置的机器》《被铁消灭的铁》《主控室的梦魇》《钢铁是结束生活的地方》《狗日的工厂》、唐以洪的《搅拌机》、杏黄天的《在工业森林里》、谢湘南的《站在铜管切割机面前》等。相似的生存境遇导致相似的创作主题,这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感受的具身性与表达的多样性——这是美学创造的出发点,可细读这些诗歌,就会发现表达与诗意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类同化、单一化的问题,而未呈现出多元的精神与情感内涵,更未创作出展示新感受、新体悟的作品。我们列举的还是新工人诗歌中的好作品,如果把大量一般化的作品容纳进来,则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不仅如此,新工人诗歌在剖析现实问题上,也存在对其生存处境认知的简单化、道德化倾向,即使是新工人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郑小琼,也未能避免这一问题,她的《给某些诗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新工人诗歌美学上的不足成为其打破自身困境的最大障碍,新工人诗歌的未来,更在于美学突围。
三
新工人诗歌被消费主义文化掩埋在时代的角落里,又被精英文学封闭的世界所排斥,备尝艰辛;但又在诗歌式微的年代渴望用诗歌唤起社会对新工人群体的关注,这注定是一条格外艰难、坎坷的路。
进入20 世纪90年代,新工人诗歌逐渐远离“中心”,呈现边缘化状态,已成为学界广泛接受的一个判断;当然,做出这个判断,是以20 世纪80年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作为参照。20 世纪90年代是个人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诗人普遍意识到个体生命的体验高于任何集体精神和社会认同的抒情,个体生命的书写成为诗歌的主调,个人化写作态势呈现一种新的倾向。这种个人化的诗歌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打开了诗人、读者被束缚和禁锢的感受性,释放出了诗歌创作的能量;但毋庸讳言,也在相当程度上不断窄化个人经验,使诗歌逐渐走向封闭,甚至僵化,远离社会现实,远离读者大众。个人主义写作阻断了诗歌与读者间的交流通道,加之消费主义大潮冲击,新工人诗歌缺乏稳定的读者,逐步陷入困境。“专业化”诗人在缺乏写作市场的状况下,面临生存、精神双重压力,一部分转而投入市场化大潮中,成为书商或其他商业贸易领域从业者;一部分则转而开始小说创作。在生存压力下主动转型,既可保障个人生存,又可延伸创作领域,同时还可保持与诗歌的联系。但正是这一批钟情于诗歌创作且具有一定实力的诗人的流失,对20 世纪90年代甚至21 世纪诗坛带来了巨大损失,进一步加剧了诗歌边缘化处境。
新工人诗人不同于上述“专业化”诗人,他们从未将写诗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只是自我情感纾解的一种方式,这是他们之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将诗歌作为其发声的媒介,却又是他们的不幸。在一个诗歌没有读者的时代里,企图利用诗歌传递声音,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良策;即使如张德明所说,“网络拯救了处于颓废之中的中国新诗,网络无限敞开空间、自由自在的发表方式和交流方式以及迅速便利的传播特性,都给中国新诗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增长素”[10]。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网络并未为新工人诗歌提供另一个生存空间,至于未来能否提供这样的空间,依然值得探讨。借助网络、多媒体力量扩大新诗传播、流通的经验早已有之。“舞台演出,由专业演员担纲,通过电视转播的诗歌朗诵会,诗人朗诵自己作品的朗诵会,各地大大小小的诗歌节,各种诗歌联谊会、诗会、酒会,各种诗歌评奖活动,发布各种诗歌排行榜,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各种样式,形成在诗歌‘边缘化’中的异乎寻常的‘诗歌热’景象”[11],新工人诗人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尝试。2015年陈年喜应邀参加四川卫视主办的文化类节目“诗歌之王”,与歌手罗中旭搭档,“‘诗歌之王’官方微博位居‘微博热搜话题榜’第六,‘疯狂综艺季’第一,话题阅读量高达6.9 亿。在互联网播放平台上,新浪、搜狐、腾讯、优酷、爱奇艺等知名网站均对该节目做了宣传,网络点击量突破2 亿”[12]。“诗歌之王”以其独具创意的形式传播诗歌文化,在当时获得了极大的关注。2017年,由秦晓宇、吴飞跃共同执导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全国200多个城市放映,并获得纪录片金爵奖,受到各方好评。但无论是“诗歌之王”,还是《我的诗篇》,在轰动一时之后,终究难免寂寥落幕的命运。陈年喜在参加完“诗歌之王”与《我的诗篇》拍摄之后,生活再度陷入窘境,后来经朋友介绍,去了贵州景区给人写文案。而曾经的高热度、高流量,与其说是关注诗歌,倒不如说是关注写诗人的身份,其中不无将新工人诗人奇观化的意味,新工人身份经由媒体渲染所获得的关注度要远超诗歌本身。这样的境遇同样适用于当代诗歌,正如洪子诚在《当代诗歌“边缘化”问题》中所说的,“有的热闹喧哗的诗歌活动,‘只能被称为一幕幕热闹的诗歌嘉年华。不仅暗中取悦嘉年华的主办方与观赏者,也同时取悦并深深满足着其自身的怀旧需求’;‘除了酒精衡量的诗人真性情之外,探讨诗歌和展示诗歌都成了走过场’”[11](24)。
当代新诗“边缘化”致使诗歌出版也遭受重创。进入21 世纪,出版业展开了全方位的转企改制和集团化运作的产业转型。文学出版的市场化运作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文学生产的精英化观念,读者与市场地位不断凸显。而诗歌作为极具精英化色彩的文学体裁,在市场化浪潮所形成的消费主义文学冲击下,其“边缘化”的处境进一步加剧了出版困境,出版社普遍不愿出版诗集,诗歌刊物数量也极为有限。新工人诗歌于2004年及2014年前后成为社会文化热点,吸引了出版社与新闻媒体的关注,一批新工人诗歌集在此期间出版面世,如郑小琼的《黄麻岭》《女工记》《人行天桥》等诗集,于2006年前后出版;《我的诗篇》纪录片上映之后,2019年《我的诗篇》系列丛书出版。在诗歌“边缘化”的处境下,新工人诗歌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似乎预示着诗歌的再次复活,重新脱离“边缘化”,逐渐走向“中心”的过程;但其背后仍是资本的力量、消费的力量,而非诗歌本身的力量。资本靠热度、流量而生,也会因热度、流量消退而另谋他路。新工人诗歌不会永远站在浪潮顶端,始终保持热度,消费者视线的转移也意味着新工人诗歌将再度沉寂,以诗歌为媒介发出呐喊的期望也将再次落空。依靠热度不是长久、根本之策,但我们仍可将新工人诗歌的火爆,看作当代诗歌摆脱“边缘化”、摆脱生存困境的一个契机,但怎样利用这一契机,使其维持长久的活力与热度,是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新工人诗歌面临多重困境,特别是发表困境。突破这一困境,使新工人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得到相对宽容的发展空间,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探索。
注释:
①新工人诗歌是打工诗歌的升级版。随着20 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加剧,大批农村人口到发达地区城市打工,其中一些人为了抒发离乡之情与现实苦闷,开始写作,并逐渐形成潮流,引发关注,有研究者称其为打工诗歌。进入21 世纪之后,一些研究者认为打工者这一说法遮蔽了这一群体的经济、文化诉求,将其命名为新工人,打工诗歌也相应地被命名为新工人诗歌。就目前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来看,主要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上说,凡是写新工人群体生活的诗歌以及新工人群体所写的诗歌,皆为新工人诗歌;狭义上来说,新工人诗歌即为新工人群体在描述新工人生活状况、抒发个人情感、争取自身权益时创作的诗歌作品。本文在论述中采取的是新工人诗歌的狭义概念。
②消费主义并不必然是新工人诗歌的对立面,有时,特别是新工人诗歌与其利益并行时,甚至还会帮助新工人诗歌发展。但消费主义以营利为第一目的,新工人诗歌以生存为第一目标,二者核心诉求不同,甚至存在根本冲突,这是消费主义遮蔽新工人诗歌的深层次原因。
③本文中的诗歌发表数据是笔者统计的。这里,诗歌数量按照刊物目录计算,组诗作为一首诗来统计。
④“读首诗再睡觉”公众号:2017年9月2日,郑小琼《这些中年妓女的眼神,有如国家的面孔》;2021年5月5日,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2015年11月27日,许立志《忽如一夜春风来》;2016年,陈年喜《儿子》;2018年3月31日,陈年喜《皮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