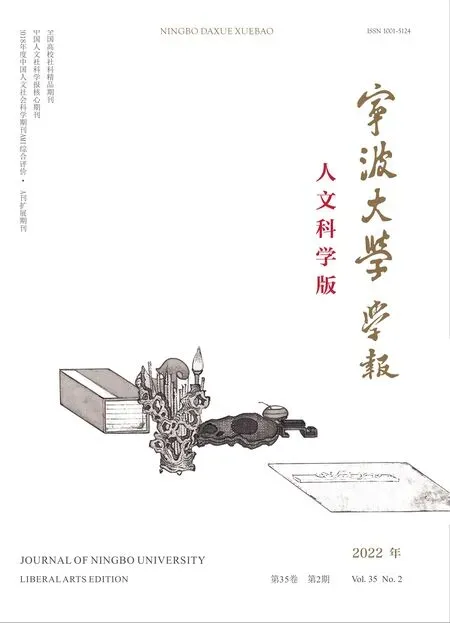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空间化转向
林 琳
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空间化转向
林 琳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20世纪30年代后,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转向”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化特征:从前期此在在世的时间性境域,转向后期本有时—空的源始整体结构;从前期此在在“时间性到时”中积极主动的生存筹划,转向后期终有一死者对本真栖居空间的被动承受与接纳;从前期思想方法的单向进行,转向后期二重运作对生境域的空间化方法。此转向的内在思想动力是后期“区—分”方法对“存在论差异”方法容易陷入表象及线性思维的内在缺陷的克服,由此产生的“之间”的对生境域对后现代空间转向产生重要影响,并与中国古代“间性”思想遥相呼应。
空间;本有;时—空结构;栖居;间性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存在思想发生了“转向”(Kehre),此转向是海德格尔存在之思内在的自我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是海德格尔思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转向”作了阐释①。对比前后期思想,可发现其后期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化特征,尤其是“之间”的对生境域方法,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形而上的线性时间思维的框架,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空间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间性”思想形成了对话。本文试从前期“存在与时间”向后期“时间与存在”的转向思路,探究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空间化转向的逻辑必然及其所具有的深层意蕴。
一、前期基础存在论的时间性境域
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理论起点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认为它以存在者取代存在,对存在者主体性、实体性的探讨替代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遮蔽了更为基础的生存论层面的问题,遗忘了存在本身。传统本体论的“本质主义”或“在场中心主义”,以某种最高的存在者的神/上帝作为解释存在者的根源,存在本身即存在性的自行显现却并未得到呈现。海德格尔由此提出“存在者的”(ontisch)与“存在的”(ontologisch)之间的“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问题,指出存在对于存在者而言是“超越性”(transcendens)的,“只有先把存在与存在者,而非一存在者与另一存在者区分开,我们才能进入哲学的问题域”[1]19并重新追问存在本身。前期海德格尔要从存在者中逼问出它的存在来,这种能对存在发问并领会存在的存在者为“此在”(Da-sein),它较其他存在者具有优先地位,海德格尔要从此在在世的日常生存(EK-sistenz)活动来追问存在的意义。为了让此在的存在自行显现,《存在与时间》回到二元对立尚未分化“前科学”的实际生活经验之流,运用存在论现象学方法,让此在在世的存在性自行显现出来,并以解释学(Hrmeneutik)方法对其生存论结构进行分析、整理与阐释,构成基础存在论(Fundameutal-ontologie)。
时间被理解为此在在世存在的根本境域,《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探讨‘存在’的意义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2]10。此在本身是作为“时间性”(Zeitlichkeit)绽放着的,“时间性到时”(Zeitlichkeit zeitigt)使此在在世的种种存在样式成为可能。此在的时间性是曾在、将来以及当前的源始统一,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2]203,作为自身筹划着的能在,“将来”是此在最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此在总是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时间性是存在作为此在的发生境域,在其中此在的自身筹划成为可能,“此在整体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根据于时间性。因此,必定是绽出的时间性本身的一种源始到时方式使对一般存在的绽出的筹划成为可能”[2]91。
前期基础存在论运用“此在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方法,在此在的“在世界中存在”与“时间性到时”中,揭示出存在的意义。但是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只是准备性与过渡性的,并未完全解决“存在论的差异”问题,因为此在虽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但并非源始的存在本身,只不过是以“存在的人”取代了传统认识论上的“知识的人”,还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结果则是“不但没有反掉这个主体,倒是从存在学的根基上把这个主体巩固起来了”[3]494。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发生转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的一种思想上的“根本性的倒转”[4]372。转向后的海德格尔自觉摒弃了此在在存在者整体中的优先地位,思想进一步突进源始的存在本身,并称之为“本有”(Ereignis)②,不再从此在在世去追问存在的意义,而是去思考存在的真理。
二、后期本有存在论的“时—空”源始结构
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存在是本有的赠礼(die Gabe)与给出(Geben),而此在的在世生存乃是从本有而来的绽开,此在作为存在的“被抛者”,被取入生存之“烦”中而成其本质,出窍地立于存在的真理中,并成为存在的看护者,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是关系着此在的基础来被理解的,因为它只有从此在出发才是可通达的,而如今颠倒过来,人的本质只在其“从存在的真理的来源”中被思考,在死面前个别化于自身的人的生存成为“绽出地栖居于存在的切近”[5]190。前期的此在存在论此时已发展为本有存在论,此在与其他存在者一样都归属于本有,聆听存在真理的召唤。本有成为了规定存在、时间入于其本己之中的那个更为根本的东西,它根植于存在敞开(das Offene)的澄明领域,这种敞开源于本有源始的“时—空结构”(Zeit-Raum)。与《存在与时间》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对时间与存在的思考已经出现了很大转变,不再强调此在的时间性,而是转向本有源始的时空整体结构,强调源始时空的整体性与共时性。本有的时—空整体结构是“四维”的,是在将来、曾在和当前三维相互达到中的自行澄明的在场的切近,这种相互达到本身是前空间的,它能够安置并给出空间,在其中时间到时且空间空间化,并为天、地、神、人世界四重整体的栖居空间开辟道路,这就是“时间—游戏—空间”(Zeit-Spiel-Raum)。栖居(Wohnen)乃是作为终有一死者所依据的存在的基本特征,只要是人,就已经随其栖居本质而来寓于四重整体中逗留而承受着空间。
前期的基础存在论仍然强调此在的时间性与主体性,死亡赋予此在在世以积极筹划性,此在以自身的主体力量在其时间性中不断去超越,实现存在的超越意义。此在在世作为“能在”,被强调其“将来”的时间纬度,因而呈现出线性发展趋势,“此在作为向死而生的‘能在’在有限的‘世间’经验到的时间与其说是一种‘整体性’时间,不如说是一种朝向将来的无限展开的过程,还不免具有一些线性的特征”[6]229。后期的本有存在论则转向存在本身的永恒空间性,此在作为终有一死者被存在的“天命”(Geschick von Sein)所遣送与呼唤,在死亡面前不是更加主动地去超越与筹划,而是对存在天命欣然“应答”,成为存在真理的守护者与聆听者,“海德格尔不再从此在急不可迫地逼向存在,而是着眼于存在本身,着眼于存在之真理的‘自行发生’来运思,要听命于存在之真理的邀请,期待‘存在的召唤’”[3]94。栖居并非此在在时间性境域中主动积极筹划的事情,而是终有一死者对本有天地人神四重域位置安然的接纳、承受与应答。此在不再急迫地去改造、征服世界,在宇宙空间呈现作为主体的强力,而是作为四重整体源始纯一之一元与其他三元共同游戏,和平地共处于四重域的“居有之圆环”(der Reigen des Ereignens)的共舞之中,受到存在整体的纯粹牵引,被动地承受着四重域互动游戏的位置,“唯如此安息,才有泰然和美的栖居”,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化转向。
前期海德格尔提出“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的方法试图解决传统形而上学以存在者取代存在本身的问题。这种方法虽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是从一个具体存在者的存在来寻找存在的根据,因此很容易陷入表象思维与线性思维,这个方法论上的阴影可以说笼罩了海德格尔前期的运思。基础存在论的基本思路仍然是从此在到存在的单线推进,并未构成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双向运动。前期思想虽已提出存在本身“无”的问题,但此时“无”只有依凭此在在世“畏”的情绪体验才能达到,仍然被拘束在此在的生存论层面,而未能触及无本身,存在的超越问题仍然只有在此在“向死而生”的时间性整体中达成。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一个必须要突破的困境即是如何克服“存在论差异”总是容易陷入从存在者到存在的表象思维以及线性思维的方法论缺陷,“‘存在论差异’之所以需要被克服与转化,并非因为它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但由于它易于缠陷在线性格局(存在者——存在)中,终究难以摆脱先验因素的局限”[7]13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转向后的海德格尔以“区—分”(Unter-Schied)来取代并深化“差异”。
三、从“差异”转向“区—分”显隐一体的运作
“区—分”即存在本身“显—隐”一体的运作,是本有的“二重性”(Zwiefalt)运作。这种“区—分”的方法与后期海德格尔对存在真理的思考密切相关。前期海德格尔认为“现象”意味着“显示自身、显现”,将遮蔽状态作为现象的对立概念,认为真理的源始意义是去除掩蔽的展开状态,而且它是必须不断从掩蔽之中争得的,“我们必须穿越占据统治地位的掩蔽状态才能通达本源的现象”[2]25,遮蔽状态此时显然是要被不断克服的,以确保此在真理的被揭示状态。而转向后的《论真理的本质》中,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真理本质上即是非真理(Un-Wahrheit),真理的本质中既已包含着非真理的遮蔽与伪装,遮蔽与迷误一道归属于真理的原初本质,遮蔽甚至比揭弊更为根本与古老,“存在者整体之遮蔽状态,即根本性的非真理,比此一或彼一存在者的任何一种可敞开状态更为古老。它也比让存在本身更为古老,这种让存在在解蔽之际已然保持遮蔽了,并且向遮蔽过程有所动作了”[4]228。存在的真理不再是单纯的自身显现,而是澄明与遮蔽、真与非真、在场与不在场、有与无之间的原始争执,它们共属一体且相互生成,这就是显—隐一体的“区—分”,存在一方面显现为存在者之存在(显),而同时作为存在自身又隐而不显,隐蔽入无,而且遮蔽状态、非真理对真理之本质来说是最根本与本己的,“显”乃源出于“隐”。遮蔽与澄明之间的相互牵引—争执形成“区—分”的“中间”,存在的真理就在这一对生境域中敞开。从此“区—分”方法出发,海德格尔后期思想都是以相对概念的双重运作出现的,如世界与大地,时间与空间,此在与存在,人性与神性,深渊与苍穹,“从单向递进的方式转变为‘相互牵引’的策略,即总要为一个主题找到它的相对者,以便让两者在相交相映中进入缘构成的境域,从而引发出超形而上学的纯思想意义”[8]155。在“区—分”中世界与物并非相互并存,而是相互贯通(durchgehen),两者横贯一个“中间”(Mitte),在这个“中间”中两者才是一体的。“区—分”不是事后从世界和物那里抽取出来的联系,区分居有(ereignet)物进入世界之实现,居有世界进入物之赐予,区分使物归隐于四重整体之宁静中。区—分的“中间”境域乃是本有运作之处,是存在的澄明之处,只有在这样的区—分的“中间”维度,才有本质的存在。“区—分”的对生境域方法克服了前期“存在论差异”容易陷入表象思维与线性思维的方法论缺陷,是以非形而上学的空间化方法进一步对传统形而上学线性逻辑主义传统的彻底突破。这一运思方法成为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关键,而且对整个西方思想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空间转向”产生重要影响。
四、后期“之间”的对生境域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指出,整个西方哲学是一种“在场形而上学”,它只关注在场的现成存在者,强调事物的现实本质,即事物是怎么在场、怎么存在的。这种在场状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现在时间”③的流俗时间理解上,因为“现在”乃是一种在场状态,是显现的当下,一切都成为当下可把握的存在者,它强调“是”,而遗忘了“是”是以“不是”为前提的,只关注在场、可见,忽视了“缺席”“隐匿”。康德进一步认为时间是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通过“时间”形成的“图型”(Schema)能给感性的表象提供一个想象的统一性,范畴通过“图型”而与经验对象结合起来,因而时间给知识提供了统一性,这就为数学等自然科学奠定了哲学基础[9]174。德里达认为这种强调“现在”在场性的流俗时间观中,时间被构想为“相继性”“连续性”,要素只能相继呈现,形成一个链条。传统的线性言语观、文字观、逻辑主义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之上,它“内在于整个西方的历史将其形而上学与其技术统一起来的一切”[10]71-72。主体在可把握的现在的时间中建立起一个可以计算与控制的可规范世界,而这正是现代性的根源,“从时间角度来看,主体的统治可以说就是主体化时间的统治,主体对世界的数学筹划活动,就是要以‘现在’为中心,在无穷的‘现在’中‘永远’保持对对象的计算和控制”[11]103。因此要克服现代性就必须打破这种线性时间观,关注到“有”着的“无”,“显示”着的“隐蔽”,而海德格尔后期显隐一体运作的域性思想正呈现出这样的方法论意义。
这一“有—无”“显—隐”一体运作的域性方法在转向后的重要作品《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最早表现出来。海德格尔在“世界”的基础上提出“大地”(Erde)。如果说“世界”是自行敞开的历史性此在的道路与筹划,具有历史性与有限性,是“有”与“显”,那么“大地”则是作为与世界相互争执的力量被海德格尔强调出来,它是此在的根基,但不允许被穿透,不被此在的操劳所改变,它自行锁闭、返身隐匿,是“无”与“隐”,是具有无时间性的空间性,“同《存在与时间》比较起来,占据《艺术作品的本源》之中心位置的是空间概念。在这里,真理的生成不是依据世界中的时间性或历史性,而是转向扬弃时间的无时间性的深层空间领域——大地”[12]156。存在的真理就在“世界”与“大地”相互牵引、争执所撕裂出来的“裂隙”(Riss)中产生,此“裂隙”即是一个“之间”的对生境域,存在就在世界与大地之间的本质性争执所形成的回旋空间(Spielraum)中。这种域性的空间化思维方法基本上贯彻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所有作品中。《如当节日的时候》中,存在的真理就在“天穹”(Ather)之激活一切的光明之父与“深渊”(Abgrund)之孕育锁闭的大地之母间的澄明领域中,“敞开域‘从天穹高处直抵幽幽深渊’澄明自身”[13]75。《人诗意地栖居》中,人的栖居之所在天空与大地“之间”(das Zwischen),人“仰望天空”同时“持留大地”,“这种仰望向上直抵天空,而根基还留在大地上。这种仰望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4]471。天空和大地的“之间”敞开维度(die Dimension),只有从此维度,人才根本上成为人。《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人诗意的栖居乃是出于这个“之间”的中间领域的居住,技术时代的人出离于“之间”的中间领域而无家可归,因为“唯有并首先在这个‘之间’中才能决定,人是谁和人在何处定居其此在”[4]324。《物》中,天地神人四方之间对生运作、相互敞开又相互映射,共同构成一个“居有之圆舞”(der Reigen des Ereignens)。
受到海德格尔“之间”的域性思想影响,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块茎”的“之间”理论,块茎始终居于存在者之间,并将连词“与……与……”作为织物,运行于“之间”,“建立了一种‘与’的逻辑,颠覆了本体论,废黜了基础,取消了开端和终结”[14]37。块茎理论颠覆了形而上学静态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块茎世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空间化转向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空间化思想遥相呼应,这种呼应乃是思想的平等对话与自然契合,而不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上的“以西释中”。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种“之间”的对生境域思想早已存在。《孟子》中浩然之气本存乎天地之间,“元与天地相流通”,人的生命乃存在于“天地之间”。中国古代艺术推崇“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作为最高审美范畴的意境正是在实境与虚境之间生发出来,“大象无形”“大音稀少”的至高艺术境界均存在于有无、虚实之间,艺术作品的灵气与神韵都从此“之间”而出。法国当代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艺术中的“之间”“间距”作了非常充分而深入的研究,“‘之间’不是一个‘实体’(substantiel)的存在,它没有‘己身’(ensoi),无法依靠自己(parsoi)存在,其功能在于气韵流动、畅通无阻,正如庖丁解牛之刀游弋在关节之间不受任何阻碍,如此便可以彼此沟通、互相激励”[15]34。美国当代哲学家商戈令建立了“间性”本体论,“以间性为基础的间性论,为什么不可以替代本体论而成为解释人与世界的哲学基础呢?中国古代先贤不正是这样做的吗?间性思维和由此发展出来的间性论模式,是中国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本体论模式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就是以间性研究或间性论为基础的哲学”[16]55。这些学者都努力在中西方文化中寻找深层对话的切入点,尝试以中国古代的间性思想来打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五、结语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空间化转向是基于思想的事情本身,它标志着西方思想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演进,且对20世纪6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Space turn)产生重要影响。空间转向并不仅仅是从时间到空间的理论侧重的改变而已,更突出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对以线性时间为基础的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现代性思想以线条时间为基础的话,那么,后现代思想则是以空间化思维为基础,“‘空间转向’是一种对现代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危机进行反思的理论动态。如果将现代性从理论上理解为时间压倒空间的优先结构及其思想动态,那么整个后现代思潮可视为一种‘空间转向’。它的主旨乃是一种以空间优于时间的空间化思维方式。”[17]27后现代空间转向实质上正是在对建立在线性时间方法上的现代性的批判中产生的,海德格尔思想后期的空间化转向即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批判基础上,对源始存在的追问所实行的“返回”步伐。
注释:
① 关于海德格尔20世纪30年代思想道路上的“转向”问题,研究者持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些重要议题如真理、语言,在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出现了,所以不存在所谓“转向”;而多数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这个“转向”是存在的,并且以此将海德格尔的思想分为前、后期。然而对于这个转向具体是何时发生的,转向是否是思想的截然的转折,在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仍然是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
② 此概念国内学者有很多的译法,本文使用孙周兴教授的译法。
③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章中所提出的现在时间观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人对时间的看法,他指出:“当我们感觉到‘现在’有前和后时,我们就说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时间;时间也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译本,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5-127页。
[1] 海德格尔.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 丁耘,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9.
[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0.
[3] 孙周兴. 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91.
[4] 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372.
[5] 卡尔·洛维特.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M]. 彭超,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190.
[6] 赵奎英. 语言、空间与艺术[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29.
[7] 张柯. 论海德格尔“四重一体”思想的起源——基于《黑皮笔记》(GA97)的文本分析[J]. 社会科学, 2017(6):126-136.
[8] 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55.
[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5.
[10] DERRIDA J, SPIVAK G C. Of grammatology[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71-72.
[11] 赵卫国. 海德格尔视野中现代性的时间根源[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101-105.
[12] 张志扬. 门: 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56.
[13]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75.
[14] DELEUZE G, GUATARRI F. Mille plateau[M]. Paris: Miniut, 1980: 37.
[15] 吴攸. “间距”即对话——从弗朗索瓦·于连的多元文化观谈去[J]. 中国比较文学, 2019(2): 30-34.
[16] 商戈令. 间性论撮要[J]. 哲学分析, 2015(6): 54-65.
[17] 胡大平. 哲学与“空间转向”——通往地方生产的知识[J].哲学研究, 2018(10): 24-34.
The Spatial Turn of Heidegger’s Later Period Thought
LIN Lin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fter the 1930s, Heidegger’s thought of existence took a “turn”. This “turn” presents three distinc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 change from the temporal realm in the early stage to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time and space in the later stage; a change from the active planning of survival in the time of time in the early stage to the passive acceptance of the real living space by the deceased in the later stage and a change from the unidirectional method of thought in the early stage to the spatial method of the biological domain in the late stage. The intrinsic motive force of this turn is the overcoming of the inherent defect of the “dividing-differentiation” method in the later period, which is easy to fall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and linear thinking of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 method, and the resulting “between” the biological realm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ostmodern spatial turn, and echoes the thought of “inter-ness” in ancient China.
space, Ereignis, Zeit-Raum, dwelling, inter-ness
B83-02
A
1001 - 5124(2022)02 - 0081 – 06
2020-12-1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空间批评研究”(17BZW057);浙江省教育厅规划课题“海德格尔技术时代的空间美学思想研究”(Y202043843)
林琳(1982-),女,浙江江山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现代文论。E-mail: 2207610358@qq.com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