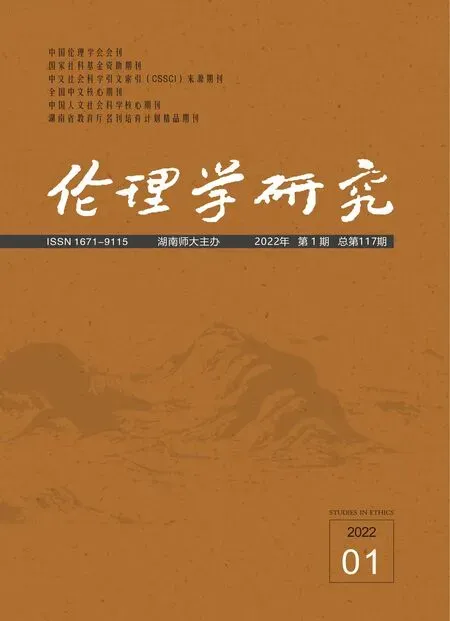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张培高
胡瑗所创的“明体达用”之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培养了大批人才,宋神宗有“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1](29)之赞誉。而且其所培养的学生在气质与品行上具有相当的趋同性,如欧阳修曰:“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2](389),又如二程曰:“安定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3](72)。“稽古爱民”实是胡瑗“体用之学”教育下的硕果。其“用”为农田、水利等实用技术,其“体”乃为儒家“道德仁义”①刘彝曾对宋神宗说:“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参见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5 页。之核心价值。从“仁学史”上看,胡瑗对儒家“仁义”的阐释,既有对汉唐思想的继承,更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其特色之处在于:(1)在宋初,率先主张“性善论”,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仁义”;(2)其论述存在抵牾之处,如“天地不仁”之说与“天地生成之仁”之论便有矛盾的嫌疑。因此,其理论的建构明显呈现出宋初开创的特征。学界研究胡瑗思想的成果虽然不少,但主要集中在胡瑗经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上,而较为专门研究其仁学的成果,通过各种数据库的检索后发现,只有张树俊教授的《胡瑗的安民之道与仁治之术》一文[4](36-39)。该文尽管对胡瑗的“仁义治国”和“仁义教化”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遗憾的是,作者并未注意到其“仁学”的特色。因为以“仁义”治国或教化是儒者的共同主张,所以若不讲其特色,既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出其仁学的面貌,又不能准确把握他在仁学史上的地位。
一、夫人禀天地之善性
人为何是道德的及为何具有道德能力,这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仅以儒学来说,“仁义”是其核心概念,而在先秦时,儒者对“仁义”的来源及其被推行的可能之问题的解答有两路线:一是《易传》的路线,从宇宙生成论上对此进行论证;一是《孟子》的路线,从性善论上对此进行论证。这两条路线其实很不一样:前者是由外至内的思路,后者是由内至外的思路。但他们对胡瑗皆有影响,然相对而言,胡瑗对前者继承多于创新,而对后者则创新多于继承,这也是其仁学特色的理论基础。
关于人性论,先秦儒家的内部就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不同的理论主张。这些理论在后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如性三品论便把这三种理论融合在一起,而且是汉唐时人性论中的主流。相对来说,性善论则是边缘化了的。李翱为了回应佛教的挑战,才真正扛起“性善论”的大旗,曰:“人之性皆善。”[5](107)此论在唐代虽有“知音稀”之伤感,但在宋代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成了主导理论,而胡瑗恰是宋代主张此论的先驱①可参看郭晓东:《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湖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 期;张培高:《论胡瑗对〈中庸〉的诠释》,《中国哲学史》2015 年第1 期。。
首先,胡瑗认为人性皆善,他说:“性之善,非独圣贤有之也,天下至愚之人皆有之”[6](2557),并认为“性善”之具体内容在于“五常之性”[6](2802)。此说开辟了宋代“性善论”的先河,对后来的理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胡瑗对“善性”进行了宇宙生成论上的证论,并提出了“天地之性”的概念。他说:“性者,天所禀之性也。天地之性,寂然不动。”[7](372)在性质上,“天地之性”是纯善无恶的,正所谓“夫人禀天地之善性”[7](379)。进一步地,胡瑗认为性善之依据在于“元善之气”:“元善之气受之于人,皆有善性。”[7](372)此“善气”与“阴阳之气”的关系,胡瑗未明确讲。若按其言“夫人既禀五行之气而生……所谓性者……为仁、为义”[8](454)和“太极既分阴阳之气,轻而清者为天,重而浊者为地”[7](408),此“气”极可能是“清气”。然胡瑗并未直言,而后来的张载则明确从太虚之清气上论证“善性”。同时,据此也可知,胡瑗之“性论”与孔颖达、李翱的不同。李翱只是照着《中庸》讲的,认为善性是天赋的;胡瑗则不同,吸收了汉唐元气论的成果,上升到宇宙生成论层面加以探讨。相对于孔颖达来说,孔颖达虽从元气论上论证了“善性”的依据,但同时也证明了人性的不平等,而胡瑗则完全否定了其中的等级性。孔颖达说:“唯人独禀秀气……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但感五行,在人为五常,得其清气备者为圣人,得其浊气简者则为愚人……孔子云:‘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9](1989)如此,不仅导致了理论上的互相矛盾(与其“凡人皆有善性”[10](308)之论矛盾),而且剥夺了普通民众“向善”的权利,实际上也剥夺了普通民众成为圣贤的可能和成为“仁人”的资格。而胡瑗则不仅从“元气论”上论证了人性之善,而且其言“天下至愚之人皆有之”更是断然否定了“下愚无善”之论的不合理性。
最后,胡瑗在论述“性善”的同时,对“恶”之产生的原因也进行了探讨。其根本原因在于:“惟圣人得天性之全,故凡思虑之间未有一不善……贤人而下,则性偏于五常之道,有厚有薄,情欲之发有邪有正,故于心术之间,思虑之际,不能无所汩。”[7](159)虽然人性皆善,但与圣人相比,众人所禀有的“善”在量上存在着厚与薄、偏与全的差别。因此圣人不会受情欲的影响而产生恶,而众人(包括贤人)则受容易受到情欲的影响,在邪情的影响下,从而产生恶。在此,实际上蕴含了后来“性二元论”的雏形②可参看张培高、张爱萍:《胡瑗经学的核心思想》,《中州学刊》2021 年第7 期。。因为恶之产生,虽然直接原因是后天情欲的影响,但间接原因或根本原因实在于所禀善性的量不足。恶一旦产生,必然就背离了“性”,自然也就远离了“仁义”,最终的结果是无法推行“仁政”,正所谓“以情而乱其性,以至流恶之深,则一身不保,况欲天下之利正乎!”[7](34)
人性论是胡瑗仁学的基础,胡瑗认为正由于人人皆禀有“五常之性”,所以任何人皆有成为“仁人”及实施“仁义”的可能。他说:“天地既立,则人生于其间。人既生于其间,则立仁义之道以本于人……又因其人而立仁义之道,以生成于天下也。”[7](466)但如上所述,“人”有圣人、贤人和普通人之分,他们虽然皆禀有善性,但在量上有区别,所以他们禀有“仁义”的量及其推行能力也有区别。对于圣人,胡瑗说:“元善之气受之于人,皆有善性,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圣人得天地之全性,纯而不杂,刚而不暴……以仁爱天下之人,以义宜天下之物。”[7](372)这其中蕴含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既然“善性”内容为“五常”,那么人先天必然就具有“至明”“至正”和“至公”的特点,而圣人禀得气之全性,自然能够自觉地“仁爱”他人。
对于贤人,胡瑗说:“贤人得天性之偏,故五常之道多所不备,或厚仁而薄于义,或厚于礼而薄于信,是五常之性故不能如圣人之兼也。”[7](372)虽然胡瑗在此没有提及贤人推行“仁爱”的问题,但由上述可知,圣人所禀为全性,而贤人则有偏,因此贤人当然就没有与圣人同等的能力和自觉的程度了。对于普通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本来人性之善恶与才智能力之高低并无必然的关系,但总有儒者(如孔颖达)常常把两者混淆在一起,胡瑗受其影响也认为众人(包括贤人)与圣人相比,在才智上也有所不足,他说:“至于天下百姓、常常之人,得天性之少者,故不可以明圣人所行之事。”[7](373)常人不仅在禀有“五常”的量上而且在才能上,皆与圣贤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推行“仁爱”的能力必然也最低。因此,若要有效推行“仁爱”,对于众人来说,如何通过后天的修养成为圣贤,是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而众人能成为圣贤的关键在于:众人所禀善性的量虽比圣贤少,但他们之间只有量的差异,并无质的不同。
二、圣贤之人皆以仁义为先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胡瑗说:“圣人虽富有天下,必须仁义道德遍及于天下,使无一民一物不被其泽、不被其烛,如此可以勿忧恤也。”[7](301)在理论上,圣人虽禀有“全性”,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把潜能转化为现实,而其“必须”之语则突出强调了圣人须把潜能变成现实的责任与义务。
对于“必须仁义道德遍及于天下”的圣人来说,能否真正履行职责与担当和方法的得当与否有密切关系。好的方法,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关于为“仁”的方法,孔子提出了“能近取譬”[11](92)之说,而孟子对此则从“性善论”上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推恩”之说[11](119)。胡瑗在他们的基础上,融合了子思与王弼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其一,综合了《中庸》的“尽性”说和孟子的“性善”“推恩”说。他说:“夫圣人禀天地之全性,五常之道皆出于中,天下有一物不被其赐者,若己内于沟壑。由是推己之性以观天下之性,推己之仁以安天下之物。”[7](370)“若己”源自孟子“若己推而内之沟中”[11](316),其依据在于“不忍之心”。胡瑗赞同性善论,当然也赞同“四心”,故也说“推仁义不忍之心……如此可以救天下之衰弱,立天下之事业也”。按此,“推己之仁以安天下之物”是必然的结论,问题是如何理解“由是推己之性以观天下之性”。从表面上看,似乎可按理学家所讲的“泛性善论”来解释,即人性与物性统一于“善”。然胡瑗并不认为物之性是善的,他认为之所以由“己性”可至“物性”,不仅在于人具有认识能力,更主要在于人与物之间有以下共同性:“万物之性,虽异于人,然生育之道,爱子之心,至深至切,与人不殊”,所以“圣人将尽物之性,设为制度,定为禁令,不使失其生育”[6](2802)。郑玄、孔颖达对此从人的认识能力和诚信上讲,并未有效解释“己性”何以能自然过渡到“物性”,胡瑗却大不同,以“生生”“仁爱”作为“己性”“物性”统合的依据。
其二,融合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王弼的“圣人有情”论。在《论语》中,曾子以“忠恕之道”概括孔子的思想,但并未解释“忠恕”之义,而孔子认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俗地说,“恕”即为“视人如己”,后人的解释也是如此,如王弼释曰:“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12](277)所谓“反情”即指人与人之间因有共同的情感,故可以己之情推之于彼之情。王弼在高度肯定人的真实情感(“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12](346)的同时,认为在情感上,圣人与人是共同的,正所谓“同于人者,五情也”[12](346)。胡瑗赞同此说,并与“仁爱”合在一起讲。他说:“圣人得天地之全性,纯而不杂,刚而不暴,喜则与天下共喜,怒则与天下共怒,以仁爱天下之人,以义宜天下之物”[7](372),又说:“内尽其心谓之忠,如己之心谓之恕。人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己爱其子必思人亦爱其子……夫忠恕以博爱言之,仁也”[6](2671-2672)。在胡瑗看来,“情”不仅是指“喜怒哀乐”等七情,还指“好逸恶劳”之情(“夫人之情,莫不欲安逸,而恶节制之为禁”)[7](328)。此情,在唐代的李翱看来,是“邪恶”的(“情本邪也、妄也”)[5](110),会严重影响以及干扰“善性”的弘扬与落实,故提出了“灭情复性”之说。胡瑗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并不认为“情”皆是恶的,而是主张“情欲之发有邪有正”[7](158);另一方面认为圣人与常人有一样的情感,而且这是圣人推行“仁爱”的一个出发点。客观地说,这一实施“仁爱”之方,通俗易懂且操作性强。表面上看,胡瑗此论似乎无甚新意,只是对孔子、王弼思想的继承,但若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看,实有重大意义。因为李氏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情灭”说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严重背离,所以胡瑗的圣人以同情来实施“仁爱”之论便在批评李翱的同时恢复了儒家重情的正统。
“仁爱天下”的“圣人”最早是指尧、舜、禹等“圣王”,周公以后,“圣人”就成了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然在现实生活中,实由“圣上”(君主)代替了圣人承担“仁爱天下”的责任。所以先秦的儒者皆认为关爱万民是君主的义务与使命。如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3](504)胡瑗也说:“夫君者,天之所以命也,故代天理物,以仁义之道生成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皆受其赐而会聚于时。”[7](253)孟子具体论述了君主仁爱天下的举措,如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实行轻税制等。胡瑗受其影响也说:“盖以仁义之道,务农重本,轻徭薄赋,天下之人衣食充足,财用丰实而又安其所居,使各得其所。”[7](152)“务农重本”非指君主亲自耕种,而是“劝之教之通商惠工而已”,此是“王者惠心(仁义之心)”[7](241)之体现。“轻徭薄赋”不仅是君主仁心仁政的体现,也是“务农重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役”少“赋”轻,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赋”上,胡瑗高度赞同先儒所主张的“什一税制”,有“什一法而得天下之中”[7](326)之语。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轻税极可能导致朝廷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严重不足,也会影响君主的个人生活,故哀公叹曰:“二,吾犹不足。”[11](132)然胡瑗认为实行“轻税”是朝廷应有的本分,他说:“益者,损上以益下,损君以益民,明圣人之志在于民也。”[7](236)从易学史上或从仁学史上看,此解特色极为鲜明。相对于前人而言,如孔颖达或随王弼从卦意本身上言“损阳益阴”或随向秀以“明王之道,志在惠下”[14](400)笼统言之,胡瑗则明言“损君益民”。胡瑗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把此念直接向君主传达,陈右司曰:“胡先生在迩英,专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为说。”[1](29)这是其仁学与易学思想的独到与精彩之处。
虽然“仁爱”天下是圣人的职责,但天下之大,并非一人可以担当,“贤人”是首选的依靠对象。孟子云:“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11](370)胡瑗也说:“四海之广,一人不可以独治……择天下之贤于众人者……代君之仁政……所以养天下之民也。”[7](171)贤人为何可以依靠呢?在胡瑗看来,有以下理由:其一,贤人所禀有的量仅次于圣人,可理解圣人之用意(“贤人得天地之偏,又可以仰及于圣人之行事”),故“圣贤”可以并提。其二,贤人与圣人一样也有推行“仁爱”的义务。他说:“圣贤之人皆以仁义为先……使天下罔有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圣贤之所用心。”[7](319)其三,贤人往往有其位,故有推行“仁爱”的平台。在现实中,“贤”往往是指贤臣能士,正所谓“有是君,必须有是臣,然后万物可举,天民可治”[7](18)。若无其位,即便是圣人,在实施“仁爱”上也有巧妇之憾,胡瑗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有圣人之德,有仁义之道,苟不得其时,不得其位,则无兴天下之势,无居天下之资。是则虽有仁义之道,安能有所为哉?”[7](300)其四,“贤人”通过学习,可以具有“仁爱”天下的才能。他说:“虽有五常之性,苟不该博古道,亦不能成之,是必多闻博识,然后道业可以成也。”[7](166)
三、“天地不仁”“天地生成之仁”
对“仁义”的来源及其被实施的能力,古人或从人的内在性上论证,或从外在的天道生生上寻找依据。胡瑗的仁学特色除了上述的特点外,还在于以“性善论”为基础对以“生生”论“仁”之思路进行改造。阴阳五行之说是汉人解释世界的基础理论。以仁学来说,汉人常把“五常”与“阴阳五行”合在一起论述,其中,春对应的是“阳”“木”“仁”。如《白虎通》曰:“木者阳,阳者施生……藏于木者,依于仁也……木王即谓之春。”[15](191,193-194)阳主生,春天又是万物生长之季,必然也是“仁”。汉人的这一思路对后世影响甚大。胡瑗亦受其影响。他说:“天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圣人法之,以仁而生成天下之民物,故于四时为春,于五常为仁。”[7](14)“天地”生“五常”,其中“仁”则来自“木”与“春”。问题的关键在于:天地本身是否具有价值属性?天地生万物属于古人的基本经验认知,也是先秦诸家的共同主张。然而,对这一现象之道德价值,儒道两家有不同的认识。《系辞》在肯定“生生”是“天地”之“大德”的同时,也认为“仁”是圣人“守位”的保证[14](664-665)。汉代的董仲舒更进一步认为“生”即是“仁”,他说:“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16](329)如此,“天”就不仅仅是“自然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统一了。道家则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无任何的道德属性。
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他说:“天地以生成为心,未尝有忧之之心,但任其自然而已……若圣贤有天地生成之心,又有忧万物之意,是以其功或过于天地。”[7](157)从仁学上说,性善论、善恶混论或与之相关理论的共同之处便是从人的内在性或先天的必然性上揭示了人何以能“仁爱”;而性无善恶论或性恶论的主张者则是从后天的学习或效仿上解释了“仁爱”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性恶论的主张者荀子便是从学习上解释的,“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13](443)。这里说的“质”“具”并非说先天就具有“仁义”,而是说人与圣人一样具有能知能学的资质。所谓的“效仿”主要是指从自然天地之生物中推出“仁爱”。不过,不同于性恶论或无善无恶论者,胡瑗认为圣贤之所以不同于天地,乃能忧虑万物,其原因在于先天禀有“五常之性”。
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他说:“夫天地之道,乾刚坤柔,日临月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使万物绵绵而不绝者,天地生成之仁也……夫圣人之道,恩涵泽浸,政渐仁煦,薄赋轻役,恤孤轸贫,使百姓安其土而不迁,劝其功而乐事者,圣人生成之仁也。”[7](373)在此,虽然“圣人生成之仁”与“天地生成之仁”仍有不同的内容,但天地生物已不再仅仅是“自然”之行为了,而是已经具有“仁义”之道德性质了。在同一部著作中,为何有两种矛盾的说法呢?或许有人会想,是否有可能像后来的张载那样,胡瑗的观点前后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张载在《横渠易说》中受老子影响,主张“天地不仁”,后来则放弃了此论,故在《语录》中有“虚则生仁”[17](325)之说,而在《正蒙》中甚至有“天,亦仁也”[17](236)之论。胡瑗亦可能是如此。因为“天地不仁”之说是对《易经》的解释,而“天地生成之仁”则是对《易传》的阐释。遗憾的是,这种类推并不能成立。因为在其对《易传》的解释中,虽然看不到“天地不仁”之主张,但仍有“天地自然”之说。他说:“道者,自然而生也,此言乾坤之道也……乾自然而为男……坤自然而为女。”[7](355)既然是“自然而生”,那么“不仁”当然是必然的结论了。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不过,胡瑗之天地“仁”与“不仁”的不同实际上也蕴含了共同点。其一,无论是“天地生成之仁”还是“天地不仁”,共同表明了胡瑗从易之“生生”上寻找“仁义”的思路,正所谓“圣人法之”“天地之心在于生成而已。犹圣贤之心以生成天下为心”[7](157)。其二,无论天地是“仁”还是“不仁”,从中体贴出“仁义之心”的主体首先是“圣贤”,正所谓“犹圣贤有天地生成之心”也。其因当然在于“圣贤”禀有完满或相对完满的“善性”。总之,虽然胡瑗继承了前人以“生生”论“仁”的思想,但仍有所不同,即他是在“性善论”视域下进行论证的。
四、其志在于佐君以泽天下之民物
“推行仁义”虽首先是圣贤的责任,但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若套用顾炎武的话便是“仁义天下,匹夫有责”。具体地说,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他说:“夫君子有仁义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为忧,所忧者天下;不以一己为乐,所乐者天下。”[7](105)这既是对孔子“修己以安人”思想的弘扬,更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念的推阐。这一思想在当时有重要的意义。
范仲淹对胡瑗不仅有举荐教授太学的知遇之恩,还有思想上的重要启迪。到范仲淹中举(1015年)时,宋建国已近六十年,然在这近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宋朝廷的价值观建设仍是筚路蓝缕。范仲淹就曾批评说:“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18](23)“回此天地力”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儒家的“仁义”之道①可参看张培高:《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哲学研究》2018 年第6 期。。范仲淹不仅高扬母校睢阳书院“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咸底于道”[18](192)的校风,而且以“乐道忘忧”[18](387)“进退惟道”[18](388)作为自己和要求士人的行事准则。胡瑗曾游其门下[19](10282),故能了解其思想并受之影响。胡瑗说:“(君子之人)推仁义不忍之心,独立特行,挺然而无所惧惮……如此可以救天下之衰弱,立天下之事业也……苟不得已而不可为,当韬光遁迹,养晦仁义,以道自乐,不与世俗混于衰弊之中而无所忧闷也。”[7](175)因有“仁义”作为精神的支撑,所以面对任何困境皆可“无所惧惮”,且也不会改变“仁义”救济天下的初心。在人生低谷,没有报国、济民之机时,也只是韬光养晦、以仁义养心,以此保持初衷不变和内心的自由安宁,耐心等待时机,机遇一旦萌现,便可及时“施仁义之术生成天下,以益天下之民”[7](236)。如此,天下之士便与“隐身于山林”的佛老划清了界限。之所以要如此强调儒与佛老价值观的不同,乃基于这一原理:不同的思想观念决定或影响着不同的行为,士人只有先信儒才可能自觉地行儒。据此,胡瑗说:“君子之人,先求仁义以益于身。身既益,则其仁义之道可以推及于天下。”[7](451)“求仁义”为儒家价值观的培育,而“推及于天下”则是把观念化为实践。
因为“圣贤”有先天的优势,所以胡瑗首先强调了他们“仁义天下”的责任。此意的通俗表达便为本事越大,责任就越大。但这也是普通士人的责任,而且与圣贤一样皆禀有善性,因此成为圣贤也就成了士人的追求。而这既是胡瑗自己的目标(“即以圣贤自期许”)[1](24),又是普通士人的追求。他说:“君子立身处世,则必内畜其德,外洁其行,而存心于圣贤自任,以天下生灵之重。”[7](53)既然“存心于圣贤自任”是士人的目标及其“仁义天下”的基础,那么如何成为“圣贤”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关于成贤之方,胡瑗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节情抑邪。胡瑗认为贤人以下“善性”之失的直接原因在于受到外物的诱惑而使“情”流为邪情。因此,若能像圣人那样对情进行控制,“善性”自然不会损失。他说:“夫人之情……必得礼以节制之,然后所为适中,动作合度而放僻之心无自入矣。”[7](90)通过持之以恒的修养,士人“善性”的完满程度在培育中自然能够逐渐接近贤圣。
其二,明心复性。“复性”之说始自李翱,其方为“灭情”。但胡瑗认为“情”有邪有正,“情”不可灭,故李氏之方不可行。他同时认为有邪有正的人情,必然会影响人的思考,进而产生邪念。对此,胡瑗认为既然“邪念”产生于“情欲之发”之时,那么就可把其扼杀于萌芽之中。他说:“贤人君子,凡思虑之间一有不善,则能早辨之,使过恶不形于外,而复其性于善道”[7](158),“嗜欲未形,未为外物之所迁而其心未动之前,先正其心而不陷于邪恶”[7](286)。“早辨之”与“先正其心”含义是一致的,即把恶念消灭于未形之中,目的为“复性”。“善性”恢复了,仁义自然就在其中了,正所谓“君子之人,始能治其心,明其性……至此可以为仁,可以为义”[7](150)。
其三,积善成贤。“节情”“明心”的方法适用于未发之时或已发之际,而已发之后(即邪念产生后),应采用后天培育“善性”的方法。胡瑗说:“积小善以至大善,由小贤以至大贤,由大贤以至于圣。”[7](259)由此可知,此法的关键在于“积”,积少成多,当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对此之方,胡瑗认为是有效的,而且未来可期,他说:“小善至于大善,以至愚者必贤,贤者必圣。”[7](145)
其四,明体达用。“仁义天下”只靠德行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本领。孔子就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论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1](94)“道、德、仁”属于德行的范畴,而“艺”则属于知识与技艺的范畴。此“艺”既指学习《礼》《易》《春秋》等经典文献,又指掌握乐、射、御等实用本领。尽管孔子有“君子不器”之语,但其实他所讲的实用本领之外延是较窄的。到了唐代,虽然教育制度规定要学的内容较多,如除了四门学外,还有算学、律学,但仍然是比较狭窄的。因为人类的生活涉及许多方面,除了算、律外,还包括建筑、水利等。而胡瑗的教育方法与以往相比,有较明显的不同:一是所学习的内容较为宽泛,具有类似现代分科治学的特点;二是此举措形成了制度,并在朝廷的支持下推向了全国。具体内容是:“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1](24)此教法,后人以“明体达用”括之。这一归纳是很恰当的,如宋神宗就曾云:“经义治事,以适士用。”[1](29)其中“经义”是指学习与掌握儒家的经典文献及其义理,尤其要通晓经典文献中所蕴含的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价值观,并把它内化为意识和信仰,此为“体”也;而“讲武”“水利”“算历”属于专攻之学,其目的要掌握实用的济世技能,此系“用”也。在“明体达用”教育观念的指引下,胡瑗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仁义之心和实用本领的贤人能士,仁爱天下、造福百姓。此正是二程所言“安定之门往往知稽古爱民”之表征。
结语
“仁”所指的对象是“泛爱众”[1](49),那么此“爱”必然是普遍之爱。“普遍之爱”自然也是广爱、兼爱或博爱。这便蕴含了以之释仁的可能。如在先秦,《庄子》便以“兼爱无私”[20](118)概括孔子的仁。后《荀子》亦曰:“泛利兼爱德施均。”[13](462)不过,或许是墨子也讲“兼爱”的缘故,汉宋士人更多使用的是“博爱”。如唐代的韩愈提出了“博爱之谓仁”[21](145)的说法。胡瑗受此影响,也如是言[7](466)。此外,他还有“广爱无私谓之仁”[6](2743)之说,这与欧阳修“大仁博爱而无私”[2](1364)之论是一致的。其实从含义上说,“兼爱”“博爱”“广爱”实无根本区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不过,胡、欧阳两人对人何以能“仁爱”之探讨的深度有较大的区别。胡瑗由心性论上升到宇宙生成论的层面加以探讨,故在宋初率先提出了“性善论”,并提出了“天地之性”一词和以“明心复性”“节情抑邪”为代表的修养工夫,这皆对理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修与之根本不同,对心性论大为不满,故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2](669)所以若以此来看,朱熹对胡瑗学术的评价(“教以安定之传,盖不出于章句诵说,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1](29-30)显然是不准确的。一是因为对照其著(《周易口义》《中庸义》《洪范口义》)可知,其解主要是义理阐释,不然四库馆臣不会以“义理之宗”[22](10)评价《周易口义》,故“盖不出于章句诵说”是不符合事实的。二是因为其所说的“其效远不相逮”也要辩证地看,若与唐代的李翱及同时期的欧阳修比较的话,胡瑗的“心性论”已较为系统了。然,若以后来理学家的体系作为比较对象,其不足之处当然是明显的。仅以其仁学来说,如他所主张的“人性论”,尽管对理学家有直接的影响,但实有不融洽处,“善性人皆有之”与“禀赋有厚薄”之间是有张力的,后来的张载、二程正式提出“性二元论”才使之圆融。又如,“天地不仁”与“天地生成之仁”之说也是相互抵牾的,后来的张载、二程直接就说“天,仁”或“天者理也”,消除了其中的矛盾。正因其学术思想(包括仁学)呈现宋学初创的特点,故清人黄百家以“开伊洛之先”[1](30)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