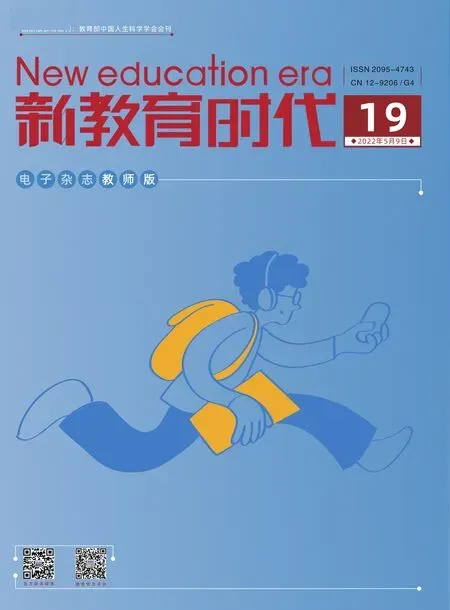“大设计”广融合背景下的新工科设计教育模型探讨
贾 振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 江苏徐州 221116)
改革开放以来,设计教育的发展紧随产业布局、市场开拓形成了并行发展模式,一方面为社会、市场源源不断输出人才,另一方面也在设计教育体系内部的自身架构中探索着设计教育的认知边界,为设计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内涵。回溯设计教育的发展历史,始终与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啮合在一起,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几十年,西方发展近百年的成果在我国被压缩到一个数十年的时空中。这种近乎极致的压缩给设计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养料,同时也促使设计教育在不断转型过程中探讨着新的认知框架。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认知框架的边界随着数字时代、虚实结合的新经济范式的扑面而来,将会进一步爆炸式拓展,人才需求将在产业链更为细分的领域形成增长诉求。设计教育在“大设计”广融合的背景下对人才培养知识架构的需求将会有所不同,因此,设计教育需要再次探讨在新时代、新背景、新要素、新经济模式下的认知定位,塑造更加柔性的人才培养框架,为人才的多元化、细分化、专业化发展提供沃土与养料[1]。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原理在互联网技术框架的赋能下,原本静默隐匿的生产要素之间的联系被催化和进一步激发显化了。至今,随着个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人们也逐渐被绑定成了互联网中具有实名IP的节点。如果对未来设计做一个简化的描述,无论它所包含的设计灵感多么独特、设计技术多么高端、设计内容多么复杂,它必然绕不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对设计过程的节点调用记录。设计过程所调用的节点(对应设计资源、能耗)与设计成果转化衍生的新的节点(关注度、流通度、交易量、应用拓展)之比可称之为设计所产生的效能,也是设计智慧的能量显化衡量标准之一。未来设计框架下,随着区块链物联网技术的应用,物联信息节点不断衍生,拓展为新的数字衍生边界,这种物质能量信息的调用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将会更加透明,以便于科学归因追根溯源。借助新技术和新的科学理念,我们对设计的创生过程会有不一样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数据与节点的视角。
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知识暴涨的时代,设计教育如何立足本源,在无限拓展的设计节点中寻找元认知,深耕元体系,找到数字时代创造力培养的01阀门?首先,我们需要对设计思维本身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设计思维并不仅仅是职业设计师的专属思考范式,而是人类从自然界动物生态链中走出人类文明独立发展路径的最普遍,最广泛的创造性思维范式,从第一把石斧、第一根骨针、第一幅岩画、第一个炊具的构思设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文明的制度设计都广泛存在着设计思维的运作。从设计思维的创生角度来看,设计思维很多时候是由哪些活跃的个体认知在把握所属时空的局限属性特征下,寻求一种解决当下问题的适合解,而无数的个体智能在寻求适和解、最优解的算法涌现联动协同过程形成了文明发展的宏观设计进程。可见,设计思维是人类思考问题、构想模型、解决问题的普遍思维范式,广义的设计思维过程包含了发现问题、描述问题、研究问题、抽象问题、构想模型、解决问题、优化方案的一系列设计、探索、观察、试验、优化过程。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设计思维正在回归它的原始定义,从前分门别类的职业设计范畴,如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交互设计、服务设计,正在信息时代互联互通的要素重组构建下相互融合,寻求系统最优解,因此,设计师的定位更加模糊了,从以往聚焦于视觉包装造型问题到参与到系统问题中利用自己某一专业维度的知识模型去辅助解决系统问题的角色。设计师所设计内容的外延扩展了,变得更加因地制宜,因事而异。
设计可能遇见的问题边界随着数字时代信息节点的无限衍生而无限拓展,给予了设计师更广泛的自由度和参照系。设计所涉及的维度越来越广,一所设计学院所能涵盖的知识资源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当下这个知识、科学技术指数级暴涨的时代,设计教育需进一步凝练设计需求定位,探讨设计思维的本质和边界,塑造新的设计教育认知模型,为未来设计行业的发展打开更多通道,赋能更多可能性[2]。
从设计教育适应新时代需求的角度思考,探讨设计教育模型的演化趋势。
一、从感知边界构建认知边界的设计教育认知模型重塑
设计思维从设计赋能的“产品”结果来看,是设计师自上而下的一种设计认知赋能活动,但从设计思维的建构过程来看,它又包含着设计师个体、团队的相互感知,基于设计目标的知识建构、知识耦合,认知聚焦过程。在设计思维的初期,感知先行于认知,有了感知的素材,在头脑中形成符号意象的感性质料,是进一步形成设计创作的基础。此外,在设计创作过程中的探索、试验、模型优化过程,都包含着对新构想模型的感知,这些阶段性方案都是刺激大脑进行设计优化形成最终方案的感知素材。
在目前的新工科设计教育模型中,感知端的输入还不够丰富,学生对于可用于设计构建的材料、力学性能、结构属性的理解从教育输入端层面多处于理论推演阶段,对于工业工程应用的材料应变磨合、设计优化分析对策不足。
传统教育范式的特征是理论先于实践,虚题多于真题,动脑多于动手,模拟多于试验。因此,学生在感知端信息的受限表现为理论与应用的认知桥梁构建不够充分,就导致理论教学对未来可预期的实践转化和应用场景缺乏联想,以及基于现实目标问题的设计构想力、探索试验能力欠缺。在迈向未来的设计教育进化过程中,感知端的输入需要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在新工科设计专业实验室可提供可观、可触、可用的材料工艺可视化融合创意平台,使这种基于材料、工艺、新工科知识技能的相关要素能够在学生大脑中通过试验、探索激活充分的神经元链接,培养具备针对目标工程问题进行分解探讨,协同设计,试验验证的新工科人才。
二、从继承构成式创新到构造模型式创新
如果对大学本科学生的部分设计作品做一个概括式的特征抽象,不难发现,一些作品如果追根溯源,都会发现主导其内在构成特征的“设计原型”,这些“设计原型”部分是来自著名设计师的作品,还有一些来自设计公司、优秀设计院校的概念原型。也许这些“设计原型”作品过于优秀,它给初学设计的同学带来了头脑印刻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榜样作品,学生以它们为蓝本进行模仿,作品不会显得过于稚嫩。但是,长期进行这种继承模仿式创新就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型设计思维,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出现在设计作品中,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很多需要设计思维进行创新的事项中。虽然这种模仿、继承式微创新是创新设计中的常态,但我们应该观察到有一些同学或学者在试图寻求更根本的,更具创造性的设计思维突破,这些作品虽然看起来并不成熟,但在设计思维上却是另辟蹊径的,存在着更为底层的突破,也需要整合更多维度认知,以更系统的认知储备去建构新模型,这种构造新型设计原型的创新是更值得鼓励和探索的,也是未来创造中国设计话语“根系统”应该去赋能的创造力[3]。
作为设计系教师,正如企业家对所在企业微观经济学的运行观察,教师对一个课程设计班的创新设计思维过程也是明察秋毫的,设计教师所具备的视角是能够平行地看到不同的学生在创新过程中的思维发展路径,从而对微观的个体设计思维进行批判、抽象、归纳、导引,在设计教学积累中形成一套系统性的临场指挥经验,这使得学生的灵感在这些富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得以助产成型。
新工科设计教育的赋能框架下,不仅要关注和赋能那些试图寻求从0到1在新维度、新理念微观突破的设计思维,也要赋能新工科设计教师形成产、学、研、教、验的全栈式课堂目标引导力、实验现场组织力;设计灵感助产力。在设计学院的内部建立起一套平行于企业研发的课堂研发、实验研发、创意研发流水线,使学生在进入职业就业之前就能够积累充分的产品开发感知经验。
三、疫情背景下的新工科设计教育模型探索
新冠疫情的传播给各行各业的运行都带来了影响,甚至重塑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和作息模式。高校设计教育也从以往高人员流动性的课堂教育、校企联动实践教育转为在线教育和低人员聚合度的实验实践教育。新冠病毒作为一种难以预知、快速传播的病毒在人类演化历史上重塑了时空走向,它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大自然在微观物种上演化的力量。自然宇宙中包含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人类正是这些知识的解码工程师。正如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影响一样,那些还未被感知、理解的新的维度蕴藏着未知的知识,当我们无法明白它的运行原理前,它会对人们造成威胁,甚至是一种不可抗力的存在。当人们逐渐解码了这些事物的运行原理,它的运行模式能够被人们掌控,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又会惠及人类在各行各业的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将人与自然可持续共处的理念融入设计教育,通过博物学、人类学、地球生态学、自然科学、设计科学的有机融合,培养敬畏自然、自觉维护地球生态健康、保护物种多样演化的地球公民和生态设计师。
四、数字智能涌现背景下的设计教育模型探讨
在这个学科交叉智能涌现的新时代,信息的获取和知识的传播更加扁平化了,人们的知识获取途径不仅限于学校,而是广泛地弥散在工作、生活、新媒体、互联网中。因此,新时代的设计教育也需要建立一种长期的、柔性的、弹性边界的可持续学习理念,减少现存教育中有限维度下的过度竞争,缓解认知负荷,与数字智能错位发展,提倡自觉地基于兴趣和天赋塑造的可持续学习。
基于未来设计的多维、复杂、系统、高融合特征,培养“多焦段”的复合型设计人才。其一为“广视野,多维视角”的扁平T型人才,其知识特征为对设计学科相关的多个学术领域有所关注,但不必追求底层原理的精通,善于将多个学术领域的前沿成果融合赋能于设计应用领域,也更适合从全局角度看待设计行业的宏观战略和发展趋势。其二为“围绕某一设计领域具备设计相关知识丛、技能丛特征”的设计人才或设计教育人才。其知识特征为围绕某一行业领域或特殊领域,在纵深维度和跨界维度上都有延展,在知识理论和技能生态上具备交错互补自我更新的知识模型。其三为围绕某一维度设计问题具备纵深认知的“长焦型”人才,其知识特征善于在设计学科某一领域跟踪前沿发展,拓展某一维度的知识边界。
通过构建多个焦段的人才储备,在专业教育体系内部形成针对某一领域的全息感知人才网络,构建知识管理点线面立体化框架,形成知识开拓、知识耦合、知识溢出、知识辐射、知识转化系统输出的师资架构[4]。
五、构建新工科设计教育多维成果评价机制,赋能设计认知边界拓展
设计行业具有鲜明的跨界属性,设计认知的发展也总是随着各个学科的纵向发展而得到交叉赋能,因此,设计学科作为各个学科认知赋能的交叉结点,它的发展也必然会不断地反向启发其他学科的纵横发展。设计教育也同样如此。近年来,随着产业分工逐渐细化,高校设计教育的定位也在逐渐向着职业教育与设计科研相结合的方向演化。教师作为距离教学场景最近的角色,对于设计教育理念的自我改进最能直接地体会到它的反馈闭环—学生认知效能和实际能力的提升。因此,即便没有形式上的改革,教师自身理念的改进和教师自身对专业知识技能的精进也在不间断地赋能着设计教育的微观变化,其整体表现为群体涌现式的自动化认知优化。
对于一项设计科研成果,其编码的信息节点越多,学科背景维度越丰富,它所蕴含的认知能量密度就越高,所带来的影响力就越大,知识溢出价值就越高。对于设计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评价,已经过了数数阶段,不应总是强调体量、数量、级别、书面形式那些资源禀赋型成果,而应该多关注那些设计初心、教育初心内驱力驱动下的个体的设计理念、教育理念、内容生态、设计方法变化所带来的认知模式变化,关注小趋势的力量、关注个体知识触角的拓展所带来的宏观认知边界拓展,关注专业认知的增长、融合带来的系统内生态变化。当教师在某个领域或交叉领域的认知边界上有所突破时,其知识溢出效应是自动显化传播输出的,学生的知识也会随着教师知识边界的拓展而扩展出更广阔的边界。混沌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涌现的系统中,微小的改进经过不断累积放大就会带来系统变化。目前,新工科设计教育正处在探索和转型升级过程中,我们需要用时空拓边界,建立弹性框架下的多维成果评价机制,保护教师自然精进发展所形成的知识生态体系,在微观视角寻求知识节点的衍生和知识边界的突破,构建与新工科设计教育相适应的基础研究生态体系。
结语
大设计理念下的设计教育,突破了学科之间的分水岭,为广泛的融合多维认知,形成基于设计目标的系统解提供了新的模型范式。从事设计教育、基础研究、应用科学、实践教学的师生,恰逢迎来了知识在基础研究应用科学领域无限交叉、无限涌现的饕餮盛宴,未来的设计创造者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持久扎根,找到属于自身知识生态系统的元认知,衍生出设计领域新的边界,以期为未来中国设计的话语权和设计生态根系统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