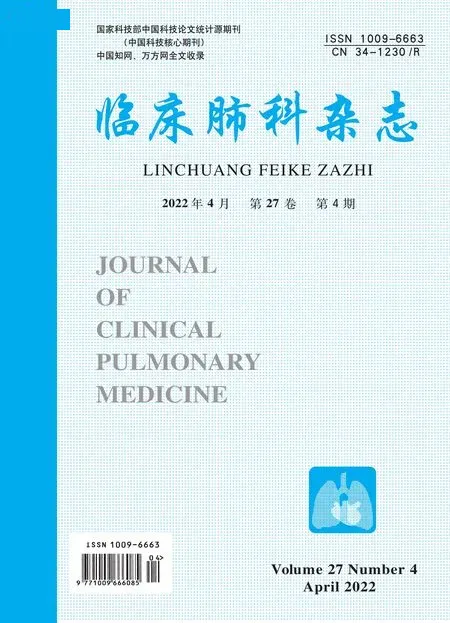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在肺部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李雅静 柴燕玲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也称为生长抑素C,是一种主要由生长激素刺激肝脏产生的一种调节机体新陈代谢及细胞增殖、分化、迁移的重要物质。与生长激素及下丘脑释放的促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形成反馈调节通路。IGF-1的本质是一种70kDa的多肽,由12号染色体上的基因调控,IGF-1信号通路包括配体、受体及6种结合蛋白(IGFBP1-6),IGF-1主要与受体IGF-1R结合,而结合蛋白起着延长IGF-1半衰期及携带转运IGF-1的作用,其中最常见的结合蛋白为IGFBP3。目前IGF-1被广泛认可的调控机制为:IGF-1与IGF-1R结合后激活胰岛素受体底物IRS及SHC,IRS1/IRS2进一步激活PI3k-Akt-mToR信号通路,SHC可激活RAS/RAI和EPK/MAPK通路[1],从而进一步调节机体的物质代谢及细胞增殖、凋亡及迁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在全身广泛分布,在肺组织中也有广泛表达(包括气道上皮细胞、肺实质细胞、平滑肌细胞、肺成 纤维细胞及肺泡巨噬细胞等)。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明IGF-1与肺部疾病(肺癌、肺纤维化、急性肺损伤、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等)存在关联,但在不同疾病中,IGF-1起到的作用及相应的变化不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IGF-1在肺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以期对IGF-1与肺部疾病的关系有一个系统全面认知。
IGF-1与肺癌
在许多人类恶性肿瘤如肺癌、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和黑色素瘤中,IGF-IR和/或其配体的高表达已被证实,并且IGF-1的高表达与转移、生存期短和预后不良有关[2],而肺癌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人类恶性肿瘤之一,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大约80%~85%,IGF-1与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认为IGF-1可通过PI3K/Akt信号通路影响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凋亡和肿瘤血管生成的能力[3],另外,IGF-I信号通路还被发现可通过上调GPER和DDR1而促进肿瘤的转移[4]。且其升高程度与肺癌的分期相关,在晚期肺癌的患者中IGF-1水平较高[5]。现许多研究还认为肺癌患者IGF-1的高表达提示预后不良,在 Tang Hexiao等人的一项纳入127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显示,IGF-1R高表达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6],Kotsantis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同时他们还发现在对一线治疗有效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体内IGF-1/ IGF-BP3比值降低,IGF-1或许可以用来预测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效果[7]。还有研究发现,血清IGF-1升高,发生第二原发癌的风险(SPC)也随之增加,血清IGF-1的测定可能是评估SPC风险的一个标志物[8]。
IGF-1信号通路与肺癌的关系已得到广泛认可,因此,目前以IGF-1/IGF-1R为靶点的抗肿瘤药物也陆续面世,这些药物在动物实验或小范围的临床实践中均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但由于其具有进一步诱导高血糖的发生等副作用,目前尚未进行大规模临床药物实验[9]。此外,还有大量研究发现部分非传统的抗肿瘤药物也可通过影响IGF-1通路影响肺癌的发生发展,如Kheirandish M.等人认为二甲双胍可以通过降低IGF-1的水平起到间接抗癌的作用[10],Sun L.等人的研究发现具菊内酯(Parthenolide,PTL)可以通过阻断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 1R)来抑制肺癌生长[11],这些研究均证明IGF-1或许可成为治疗肺癌的新靶点,虽然目前这些药物尚未成熟,还缺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但这为我们抗肺癌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思路。
同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诱导的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转移和耐药性中起关键作用, Yi Yanmei等人发现肿瘤相关纤维细胞(CAF)可通过HGF/IGF-1/ANXA2/EMT信号通路促进EGFR-TKIs耐药,ANXA2是肿瘤耐药的关键基因,抑制IGF-1/IGF-1R通路后可显著抑制ANXA2,并可显著降低由CAF诱导的TKI耐药性,这表示IGF-1可能成为解决肺癌EGFR突变的重要靶点[12]。Li Lei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在肿瘤患者复发的过程中,IGF1诱导肿瘤干细胞的扩增,是肿瘤复发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关卡,IGF1靶向治疗可能是预防肺癌患者复发的一种有前景的治疗方法[13]。
IGF-1与肺间质纤维化
肺间质纤维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纤维性间质性肺炎,以呼吸困难加重和肺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为特征,源于肺泡上皮损伤的异常修复,其发生发展与成纤维细胞的过度增殖,凋亡障碍有关。IGF-1作为一种调节细胞增殖、凋亡及组织损伤修复的因子,与肺间质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它能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迁移和胶原的产生,增强成纤维细胞合成纤维连接蛋白、α-平滑肌肌动蛋白、Ⅰ型和Ⅲ型胶原的能力, 从而增加细胞外基质的沉积[14], Xiao Huijuan等人通过往小鼠气管内注射博来霉素诱导小鼠肺纤维化,博莱霉素组大鼠血浆和BALF中IGF-1水平及肺组织中PI3K水平均显著升高[15],Chung Eun Joo等人的研究显示,肺泡上皮细胞Ⅱ型( AECII)衰老与肺纤维化的进展有关,而在IGF-1R缺陷小鼠中,AECII衰老减少,也从侧面证实了IGF-1在肺纤维化中,起到重要作用[16],这些研究证明了IGF-1在肺间质纤维化中起到促进疾病发生发展的作用,虽然目前肺间质纤维化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IGF-1作为肺纤维化形成的下游通路是可以确定的。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在肺纤维化患者组织内表现为IGF-1水平下调[17],在Danielle M.等人的研究中提出,肺纤维化IGF-1局限于受损的肺泡上皮和炎症细胞[18],肺组织的取材影响IGF-1的测定水平,这或许能解释为何部分研究结果表现为IGF-1下调。鉴于IGF-1在肺间质纤维化中的作用,目前有研究提出或许可将IGF-1作为治疗肺间质纤维化的靶点,在动物实验研究中,对肺纤维化小鼠使用IGF-1R抑制剂OSI-906,能有效减缓小鼠肺纤维化的进展[18]。在 Xiao Huijuan等人的研究中,通过使用二甲双胍抑制IGF-1途径,可进一步抑制大鼠肺纤维化[15]。这些发现提升了我们对IGF-1在肺纤维化中的认识,进一步证明阻断IGF-1/IGF-1R通路可能成为治疗肺间质纤维化的新方法。
IGF-1与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是一种急性低氧性呼吸功能不全,其发展至严重阶段(氧合指数<200)被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可以由不同原因 (如肺炎、脓毒症、创伤、多次输血、胃内容物吸入或肺挫伤)引起。Kim Tae-Hyung等人发现在博来霉素导致的肺损伤小鼠中,给予IGF-1受体阻断剂可提高肺损伤小鼠的存活率,他们还建立了高氧性肺损伤小鼠模型,发现在高氧性肺损伤小鼠中,IGF-1对肺损伤同样存在促进作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和肺组织裂解物中IGF-1水平显著升高,他们认为IGF-1趋化中性粒细胞聚集,从而加重了小鼠的肺部炎症[19],另外还有研究提出,在脂多糖(LPS)诱导的小鼠肺损伤模型中,肺损伤小鼠肺泡灌洗液内IGF-1水平同样出现了升高,且用IGF-1受体单克隆抗体治疗组BALF中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明显低于未治疗组[20]。但与之相反的是,在Munoz K.等人的研究中,使用IGF-1治疗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小鼠,小鼠肺损伤程度较对照组减轻[21],He M.等人的研究也证明,在由于肺缺血/再灌注导致的肺损伤大鼠中,用IGF-I治疗可增加Akt磷酸化,从而改善肺功能和组织形态[22]。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引起的肺损伤及ARDS中,又有新的观点提出,IGF-1水平的变化被观察到与疾病的进展有关,Bryan J. Winn的研究提出,在新冠肺炎早期,患者血清中IGF-1水平升高,而疾病进展加重出现ARDS后,IGF-1水平出现下降。与血清中的变化相反,急性肺损伤早期肺泡灌洗液中IGF-1水平下降,而肺损伤进展到ARDS后,IGF-1水平升高,肺组织中高浓度的IGF-1是严重ARDS发生的关键[23]。因此,目前关于IGF-1水平与肺损伤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这或许与肺损伤的进展时期不同及所测定的标本不同相关,还需要进一步动物研究或临床研究的探索。
IGF-1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是一种常见于新生早产儿的慢性肺疾病,其特征是出生后肺泡发育中断,呼吸道感染发病率增加,由于IGF-1具有促进细胞增殖分化,减少细胞凋亡的生理作用,其在胎儿的生长发育和各器官的成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BPD患儿中,IGF1浓度降低,极早产儿血清IGF-1水平降低与BPD和其他疾病(如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风险增加独立相关[24]。Yilmaz Cansu等人的研究中共纳入了40例早产儿,检查了插管病例的血清和气管抽吸液样本中IGF-1水平,发现在发生BPD的患儿中,IGF-1水平较低[25],持续监测早产儿IGF-1水平对预见BPD的发生具有一定意义。IGF-1在BPD的发生发展中起着保护作用,体外研究表明,rhIGF-1/BP3处理可增加肺内皮细胞和2型肺泡细胞的增殖,在产后损伤BPD模型中,rhIGF-1/IGFBP-3治疗可保存肺结构并预防右心室肥厚。这可能为预防早产儿的BPD提供新的策略[26],因此,IGF-1是一种用于治疗BPD的有前景的新方法。
IGF-1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以呼吸道症状和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常见疾病,死亡率高且在逐年上升,IGF1和IGF1R在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中的基础作用已被充分证明[27],在COPD大鼠肺组织中IGF-1水平升高,且其水平与细支气管管壁厚度呈正相关,其机制可能是IGF-1特异性激活PI3K信号通路,促进细胞增殖和细胞周期进程,从而促进COPD气道重塑[28],且Lin L.等人进一步发现熊果酸可通过抑制IGF-1通路从而实现抑制COPD小气道血管重塑及上皮间质转化[29],进一步证明了IGF-1可促进COPD患者的气道重塑。但Ye M.等人的研究发现在COPD患者的血清中IGF-1水平表现为下降,且AECOPD患者的IGF-1水平显著低于稳定期COPD患者[30]。IGF-1水平变化的差异是否是由于COPD患者体内血清及肺组织中IGF-1水平不同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IGF-1在慢阻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或许可作为未来治疗慢阻肺的靶点之一。
IGF-1与其他
一、IGF-1与哮喘
哮喘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及气道高反应为生理学特征,伴有可逆的呼吸气流受限,常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呼吸道症状的一种疾病,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呼吸系统疾病。目前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卵清蛋白诱导哮喘小鼠肺组织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IGF-1水平升高,IGF-1会抑制肺泡上皮细胞对凋亡细胞的吞噬,使凋亡细胞的炎性成分再次释放,从而加重哮喘[31]。但在Han Yueh Ying等人的研究中,血清IGF-1高水平患者患哮喘的概率更低[32]。与慢阻肺的相关研究一样,两个研究用于测定IGF-1的样本部位不同,这可能是造成这种相反结论出现的原因。
二、IGF-1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常出现慢性间歇性缺氧、交感神经激活、炎症、氧化应激和内皮功能障碍,影响到心脑血管、内分泌和胃肠系统等系统。目前有研究发现OSAS患者血清IGF-1水平显著降低,且使用呼吸机治疗有效的OSAS患者IGF-1水平随之升高[33],这提示我们IGF-1可能对OSAS患者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且IGF-1可作为观察呼吸机治疗OSAS疗效的指标之一。
三、IGF-1与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PH)是指肺动脉压力异常升高超过一定界值的血流动力学和病理生理状态,主要表现为远端肺动脉的收缩和血管重塑,由PH导致的右心室肥厚更是患者预后不良的原因之一,在 Miranda Sun等人的研究中,将IGF-1R抑制剂OSI-906用于新生小鼠及成年小鼠,发现在使用IGF-1R抑制剂特异性阻断IGF-1通路的新生小鼠中,小动脉血管重塑、右心室肥厚等均减少,但在成年小鼠中未观察到这种现象[34],同样,在Shi Lei、Martin Connolly等人的研究中也证明了在PH所致的右心室肥厚大鼠中,右心室内IGF-1水平明显升高[35-36],目前可以肯定的是IGF-1参与了未发育成熟肺的肺动脉高压以及右心室肥厚的形成,但在成熟肺中的IGF-1与PH之间的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IGF-1通路在肺部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目前有关于IGF-1在肺部疾病的治疗的研究比较局限,主要集中于肺癌的治疗,现以IGF-1轴为靶点的抗肿瘤药物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1)单克隆抗体cixutumab(IMC-A12),figitumumab(CP-751,871),Dalotuzumab(MK-0646),ganitumab(AMG479),Teprotomumab(R1507),Robatumab(SCH 717454,19D12)等。2)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如Masoprool(INSM-18,NDGA)、Linsitinib(OSI-906OSI)、BMS-754807、AXL1717等。3)降低配体生物利用度的药物,如Dusigtomab(Medi-573)、Xentuzumab(BI-836845)等[9]。其中针对IGF-1R的单克隆抗体因在前期临床试验中治疗疗效欠佳,且其导致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和轻度高血糖的作用明显,目前暂无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而IGF-1R的小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如利息替尼,在Wang R,等人的动物实验研究中发现,针对EGFR突变的NSCLC,利西替尼单药对于肿瘤无明显抑制作用,但在奥西替尼治疗的基础上,短暂联合利西替尼可使小鼠体内的肿瘤细胞消失[37]。该研究结果证明利息替尼可能成为耐药NSCLC的治疗药物之一,但由于小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相比于单克隆抗体更强的副作用,目前也暂无小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进入到临床试验。研究显示降低配体生物利用度的药物是以上三种药物中较为安全有效的药物,在一项Xentuzumab治疗体外和大鼠人肿瘤异种移植的模型中,结果显示其降低了来自不同类型癌症的人细胞系的增殖,并可以增强雷帕霉素的抗肿瘤疗效[38],另外在中国(台湾)和英国已有Xentuzumab的I期临床试验进行,结果显示了Xentuzumab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且较为安全有效,其主要副作用少,主要包括胃肠道反应和血糖升高,但其升高血糖的作用较弱[39]。另一项针对MEDI-573(Dusigtomab)的一期临床试验也在日本展开,同样显示出了较高的安全性及耐受性,在接受Dusigtomab 治疗的10例患者中有4例病情稳定。但现有的临床研究规模均较小,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Xentuzumab及Dusigtomab对于肺癌的治疗效果[40]。
另外,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治疗上,IGF-1治疗也取得了不错的临床疗效,在David Ley,等人开展的一项多中心二期临床试验中,对实验组23周至27周早产儿,使用250 μg/kg/24 h剂量的rhIGF-1/rhIGFBP-3,使用至296/7周,结果显示相比于未用药组,使用rhIGF-1/rhIGFBP-3的患儿严重BPD的比例明显下降,有向轻度BPD转化的趋势,且安全性好,虽然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似乎发生动脉导管未闭、贫血、阻塞性肺病的比例稍高,但总的来说,未观察到明显的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41]。
相对于肺癌及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其他肺部疾病,如肺间质纤维化、肺损伤、COPD、哮喘、OSAS、肺动脉高压等,针对IGF-1通路的治疗研究尚少,虽然已有动物实验中证明抑制IGF-1通路可抑制大鼠肺纤维化[15,18]、改善PH大鼠的小血管重塑[34],但尚无相关的药物临床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于机制以及探索IGF-1与肺部疾病的相关关系,靶向IGF-1通路以治疗相关的肺部疾病或许将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
综上所述,IGF-1与肺部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不同的疾病中IGF-1的反应及作用不同,但IGF-1在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被广泛认可的,其对肺部疾病的评估及治疗具有重要价值,首先,IGF-1已被证明在癌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IGF-1可作为评估肺癌及疾病进展程度的生物学标志物之一,其对肺癌的耐药及复发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以IGF-1通路为靶点的肺癌治疗药物也在不断的研究中,以IGF-1R为靶点抗肿瘤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及小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虽然小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被证明可以增加奥西替尼对EGFR耐药NSCLC的抗肿瘤活性,但由于二者对糖代谢影响较大而导致了较强的副作用,目前尚未进入临床试验。而以IGF-1为靶点的药物已被证明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及较小的副作用,已在日本、中国(台湾)、英国等地开展了小样本的I期临床试验,为目前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方向。其次,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肺局部IGF-1水平上升可以促进肺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且研究表明在对大鼠使用IGF-1抑制剂后可抑制肺纤维化形成,这证明或许IGF-1轴可以成为肺纤维化治疗的新靶点,但目前尚无相关的临床研究展开。另外,IGF-1还可促进肺的发育,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者中具有保护作用,目前已有相关的Ⅱ期临床试验开展,证明IGF-1可明显降低早产儿发生BPD的风险,是治疗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新方法之一。IGF-1在肺动脉高压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目前研究主要与肺动脉高压所致的右心室肥厚相关,与肺动脉高压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准确结论。而现有关于IGF-1水平与COPD、哮喘及OSAS的关系的各研究存在矛盾结果,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还观察到,在研究同一种疾病的不同研究中,所测得的血清IGF-1与肺泡灌洗液及肺组织内的IGF-1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循环水平与局部水平之间的差异产生机制还未完全明确,或许与IGF-1的全身多器官表达有关,这需要我们的进一步探索。总的来说,IGF-1对于肺部疾病是一种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评估疾病及作为治疗靶点,但要将其广泛应用于临床还欠缺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