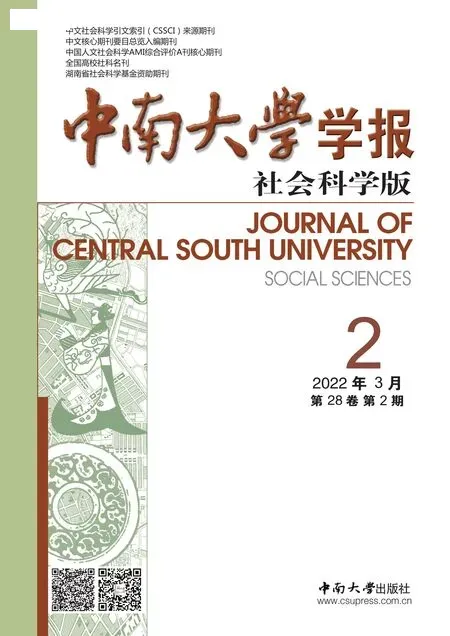“事件”:理解利奥塔思想的锁钥
曹晖,杜立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是法国20世纪下半叶极具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他写下了大量著作,显示出其在文化、政治、艺术领域的广泛兴趣。利奥塔的思想历程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虽然三个时期的关注点不同,但绝对差异作为反复出现的概念贯穿其思想始终,而绝对差异的思想核心主要来源于一个标志性用语——“事件”①。对利奥塔而言,所有的批评性作品都始于对事件的分析,因此可以说,利奥塔的一生都在书写事件。
利奥塔称事件为“突如其来者”(unexpected person),即重点强调事件的偶然性、发生性和不可预测性特征。事件超越于人的意识之外,是人的意识无法赋义的材料。在利奥塔看来,一直以来,西方哲学家的任务是寻找普遍的共相和确定性,从而寻找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而这又主要是通过追求结构规则和形式概念来实现的。但是,这种形式隶属于精神或者一种智性,受精神(意识)的统治,而在此过程中,意识之外的不确定性因素被过滤掉了,不可重复的此刻以及在此刻发生的“事件”也被系统忽略。作为当代法国最具反叛意识的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致力于逆转这一传统思维范式。利奥塔认为,事件是一种消除意识之物,不应该承担所谓的救赎任务。人们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内容,更不是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影响,而应该关注事件的发生本身,因为只有事件的发生性才能让人们感受未被意识统治的东西。概言之,利奥塔所说的事件是指事情的直接发生,这种直接发生超过了人们的描述能力和描述范围,充满了极强的不可把捉的神秘色彩。应该说,对事件的分析贯穿了利奥塔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事件是利奥塔理解一切后现代思想产生的根本。
一、“事件”与利奥塔的时间观
在重写现代性的过程中,利奥塔首先打破的是线性时间秩序。他将被遗忘的事件重新纳入后现代哲学体系中,以一种非线性时间观来强调时间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以一种绝对异质的瞬间概念取消了传统时间观中的“现在”。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非线性时间,才使得事件具有了一种不可重复的特征。利奥塔的这种非线性时间观,主要是借鉴了亚里士多德、胡塞尔的时间观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而在借鉴的过程中,又基本是借助了对事件的分析。
第一,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借鉴。利奥塔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有过两次分析,第一次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Physics)一书中对时间的划分方式。在书中,亚里士多德从物理运动这种实体性运动来考察时间,将“早”和“晚”纳入时间定义中,提出“现在”是与“早”和“晚”既联系又区分的东西,“区分在于,‘现在’是一个原点,一个基点,先于它为‘早’,后于它为‘晚’;联系则在于,‘早’不过就是尚不是现在,‘晚’是已不再是现在。这番考察通常被视为亚里士多德建构‘现在’时间序列的证据,当下瞬间似乎被授予了时间化的功能”[1]。亚里士多德这种意义上的时间被称为流俗时间观,即时间被划分为“回忆、呈现、期待”,它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这种时间观也被利奥塔称为线性时间观,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时间。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时间划分方式,三者是互相影响的,时间(早/晚)被“现在”确定、“现在”又受时间(早/晚)的影响,即“现在总不是现在,它不是尚未,就是不再,我们总无法在现在来言说现在:不是太早,就是太晚……‘现在’恰是那无法维持的东西”[1]。因此,亚里士多德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反而遮蔽了当下的“现在”,使得“现在”无法作为一种原初生发之物来分配时间。利奥塔对这种流俗时间观进行批判,他反对这种用前后顺序来划分的时间。由此,他转向了亚里士多德的另一时间理论,即“两个现在”,这是利奥塔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第二次分析。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在”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就这一次或每一次的‘现在’而言,它是同一的;就言说‘现在’将其置于一个短语中,或者将其视为一个实体而言,它不是它自身。”[1]第一个意义上的“现在”是此刻发生的“现在”(now),具有绝对的独一无二性,而第二个“现在”(the now)是处于既定环境中的经历一种历时变异的时间,从而被境遇化和相对化。利奥塔推崇的是第一种“现在”,即“这一次或每一次的现在”,并且将其吸收到他的短语理论的框架内,将这种意义上的“现在”作为事件发生的现在。这种意义上的事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绝对,在利奥塔看来,不断发生的瞬间就是独一无二,并且这种独一无二性需要建立在时间的前提之上。与此同时,这种绝对“现在”的发生也成为利奥塔异质思想的起点。
第二,对胡塞尔时间观的借鉴。利奥塔借鉴了胡塞尔将时间与人的感觉记忆相结合的方法。将时间和人的记忆相结合最早要追溯到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西方思想史上,奥古斯丁第一次把时间与人的记忆、感觉相结合,不仅完成了时间的心灵化,而且塑造了一种具有广延性的时间结构。胡塞尔将自己的时间观与奥古斯丁相联系,并且在其著作《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Lecture on phenomenology of inner time consciousness)的开篇就提出要沿着奥古斯丁的时间之思继续探索。之后,利奥塔在一篇文章中将奥古斯丁和胡塞尔并列在一起作为其时间观的思想奠基。胡塞尔将“现在”看成是一个在场域,这个在场域的核心为原印象②,在这个原印象周围存在一个晕结构,这个晕结构是刚刚过去之物(“滞留”)和即刻到来之物(“前摄”)的晕。胡塞尔的这种过去与未来都是处于意识的滞留的或前摄的意义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不仅是‘滞留-原印象-前摄’或‘曾在-当下-将来’之类的绽出性结构,更是主体性在各个源始层面的表征”[2](194)。正是借助主体意识的这种“滞留”或记忆功能,“‘瞬间’这样一个离散的、转瞬即逝、根本不可把握的时间点被我们把握住了”[3](66)。基于这种瞬间,利奥塔打破了传统的流俗时间观,提倡用一种非线性时间来强调时间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寻求高度自由和不可预测的瞬间。对于利奥塔来说,不存在线状的程式化、系统化的时间,有的只是点状的无中心、零散的瞬间(即胡塞尔的原印象)。这种瞬间不可表达,代表了一种不可预期的偶然性的存在。他认为,只有这种非线性的、当下的时间观念,才能突出“此刻”,避免“永恒”的和指向“未来”的时间概念对当下的遮蔽。因此,在事件的瞬间性特征基础之上,利奥塔始终提倡这种非线性时间观,表面上看是对线性时间的解构,实际上是对西方传统理性的反叛。由此,按照胡塞尔的原印象,利奥塔挖掘出主体,从时间的发生根源寻找原因。
第三,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借鉴。当代法国思想着力凸显事件的独特性,将不为“我思”所掌控的“事件”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这也意味着将不可表象的感觉经验重新纳入哲学的框架中并思考它的伦理、政治和审美意义。这一思想离不开利奥塔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借鉴。在《迥异》这部著作中,利奥塔将他的事件论题扩展到关于存在的研究。他主要借用了海德格尔的“ereignis”(相当于英文中的“events”)一词进行说明。这个词是海德格尔在1930年思想转向时的原初概念。在德语的日常用法中,“ereignis”主要指发生的不寻常的重大事件之义。海德格尔将“ereignis”解释为“发生”,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发生。“它是进行奠基的那个瞬间的瞬间性,这个瞬间性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发生。独一无二者就是开端的瞬间,并且是不断开始的开端或瞬间。”[4](92-93)利奥塔吸取了“ereignis”一词的核心思想,从海德格尔那里借鉴了事件的当下性和瞬间性特征,将时间看作一个存在。在利奥塔看来,事件在此刻的发生不是一个序列的时间问题,而是一个存在问题。由此,利奥塔将事件提升到一种本体论的高度,并试图通过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来揭示理性的限度。所以,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成为利奥塔后现代研究的敲门砖,不难看出,通过“ereignis”一词,海德格尔留给利奥塔的思想遗产就在于去努力追忆那种在记忆中被遗忘的并且不可被复原的不可言说之物。
海德格尔曾对流俗时间观做了一个时间哲学史的叙述,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包括胡塞尔的内在时间,都属于流俗时间观的范围,只是时间本质意义各有不同。首先,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这种流俗时间传统,开启了流俗时间观的进程。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确立的时间继承于传统形而上学,即通过现在确定和塑造了时间。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对这种继承进行了批判,他对这种序列时间的疑难又为脱离形而上学传统提供了资源。沿着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奥古斯丁为了维护上帝的意志,他提出时间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并且将时间与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指出这种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间是一种思想的延展,存在于人的心里。应该说奥古斯丁是首次将人的思想与时间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胡塞尔进一步将人与时间关联,挖掘出人与时间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提出时间是一种纯粹意识时间,时间与人的意识不可分割,这种本真性时间为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打下了基础。海德格尔将时间内化为此在的生命,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此在与时间共存亡。
虽然以上哲学家对时间的阐述不同,但是在事件的时间性来源分析上有着内在关联。利奥塔就是分别从各位思想家那里提取出关键要素,使之成为非线性时间观发展的有力证据。从利奥塔对亚里士多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三者时间观的借鉴可以看出,利奥塔强烈反对的是对时间进行阶段性划分,重点强调的是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特别着力的是消除任何综合的可能。
二、“事件”与利奥塔的哲学观
为了消除任何综合的可能,利奥塔以这种当下不可把捉的时间为核心,试图在异质性中、在事件的特性中,去寻求人类社会的公正性。利奥塔反对对时间进行阶段性划分,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去挖掘某种偶然发生的、不可预料的存在——事件。事件既然不可捉摸,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利奥塔在其力比多哲学和差异哲学中,重点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力比多哲学中的事件
利奥塔的力比多哲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他的前期思想阶段。处于思想漂流期的利奥塔刚从马克思主义战线中脱离出来,并极力反抗传统哲学话语。在寻找新出路的过程中,利奥塔走向了弗洛伊德,以求寻找到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理论话语来作为反抗传统理论话语的支撑,为自己的“另类”哲学寻找思想基础。在早期的欲望哲学中,利奥塔反抗传统理性的方式还未涉及社会公正问题,他借用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能量反抗传统符号结构学,用流动敞开的欲望对抗凝固的符号、用僭越性的欲望打破严整的理论格局。在他看来,“事件作为动荡总是蔑视知识,它能够蔑视得到清晰表达的作为话语的知识,而且它也能够扰乱处于半理性(quasi-understanding)状态的身体”[5](22)。利奥塔提出,在力比多系统中,力比多能量(情感和欲望)就是事件,但是在力比多系统内发生的事件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多个特殊的事件。其原因与力比多哲学中的几个关键词有关,即力比多带③(空间)、形象与构造④、双重性⑤。
由于欲望的流动性,力比多系统不是必然稳定的系统,它没有单一固定的边界和得以辨别的特征。但是能量(事件)的发生会产生一个力比多带(空间),它是事件得以发生的空间,也是情感和欲望呈现的场所。一旦情感和欲望呈现在这个场所中,且必须在这个特定的场所中,力比多带就具有了能够被辨识的形状,利奥塔称这种形状为形象(figures)和构造(dispositions)。但是,由于力比多系统始终是一个不稳定状态,所有已经形成的东西都是临时的,新的能量会不断挑战已经形成的力比多带,新能量的产生会挑战并且改变已经形成的具体构造。这意味着虽然这个空间或构造可以短时间内控制情感和欲望,但是它总是处于不稳定的冲突状态中,并且在这个构造内部如何利用能量也不可预测。由于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力比多系统中会出现多个不同且相互冲突的构造,并且它们之间无法进行比较和衡量。由此,能量与事件之间存在一种结构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只是一种虚假对立,真正的对立是能量所面对的一种双重性关系。这种双重性体现在两种符号中,即张量(tensor)与掩饰(dissimulation)机制。张量标志着不同构造和形象的汇集,意味着不能相容的紧张感的共存,并且可以逾越一个力比多空间,接纳不可限定的能量流。更重要的是,张量意味着一种双重力量之间的那种张力。利奥塔利用弗洛伊德的内驱力对此进行例证。弗洛伊德提出,在死本能存在的地方必然存在一种生存本能,生本能是欲望的产生、释放与平衡,是有回返的形成欲望的循环运动,而死本能则要突破这种循环活动,以一种过于强大的力量抛弃自我,形成对自我的否决与毁灭。这两种不同的内驱力相混合才能产生一种新的欲望,共同推动生命走向新生。但是,在力比多哲学中,“在希望释放能量,希望促进情感和欲望的增长时,力比多学家试图在体系内将张量掩饰起来”[6](133)。提出掩饰机制就是为了确保能量(事件)能够在这个力比多系统的内部发生,同时通过掩饰来促进所有的能量,防止一种能量高于其他能量。利奥塔的目的就是通过掩饰机制和张量,将构造和非构造的内容融合并置到一起,从而在原来的构造内也能识别出其他潜在的构造。所以利奥塔提出:“让我们满足于在掩饰中识辨出所有我们试图寻找的东西,在同一中识辨出差别,在结构的预见中识辨出偶然事件,在理性中识辨出激情——在要素之间,它们是绝对相互外在的,但是又处于最严格意义的同一之中:这就是掩饰。”[7](115)由此可见,利奥塔欲望哲学中颠覆理性的任务只能在这个力比多哲学系统的内部进行,利奥塔也称其为一种阴谋政治学(conspiration politics)。在这个时期,利奥塔的主要工作是对力比多系统中的事件展开论述,还未将其与语言哲学进行结合。到了迥异哲学中,利奥塔将事件与语言哲学进一步连接,使语言游戏所确立的差异的语用学来表明事件的独特性。
(二)差异哲学中的事件
在认识到欲望哲学的弊端后,利奥塔在差异哲学中将事件与语言游戏进一步结合,证明在差异哲学中事件的发生是语言之不可公度性的前提条件,故利奥塔将差异哲学中的事件称为“语句-事件”。严格来讲,“语句-事件”和“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略有不同。事件是利奥塔一切后现代思想的根源,事件的本质就是始终去挑战既定的话语类型,从而在这种颠覆中重新思考由事件所产生的所有问题。在利奥塔力比多哲学系统中,能量就是事件;而在他的差异哲学中,语句就是事件,“语句-事件”是利奥塔差异哲学中事件存在论的一种表现。何谓“语句-事件”呢?利奥塔的短语是一种包含着双重性的短语:一方面,由于每一个短语都是一个体制内的短语,在这个体制内部,短语会获得一种规定性。这时它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是在连接时它也伴随诸多可能性,由此短语之间的连接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时利奥塔称其为是一种可见的事例性,即“短语-事例”。另一方面,即使是“短语-事例”的短语,它的出现或发生这个动作本身又使它成为一个“短语-事件”。这种发生或这种存在本身是“短语-事例”自身所无法呈现的,此时“短语-事件”拥有了一种更大的不确定性,并且也无法为后续与其连接的短语所表达,是一种不可呈现之物。正是这种可见的事例性与不可见的事件性,共同构成了短语的“深度”。对于这种深度,利奥塔在其著作《迥异》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书中,利奥塔提到一个核心词汇:“différend”(异识)。它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即每一种语言游戏都有自己的风格,不同的语位体系(régime de phrase)有不同的规则,这意味着语言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具有诸多差异性和多样性。对此利奥塔得出关于语言游戏的三个结论:“第一,语言游戏的规则本身并没有合法化,它仅是游戏参与者之间明确或不明确的‘契约’;第二,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即使稍微改变一条规则也将改变游戏的性质,一个不符合规则的‘招数’不属于由这些规则定义的游戏;第三,语言中的任何表达或陈述都应被看作是游戏中使用的‘招数’。”[8](23)这三个结论也是利奥塔语用学的三条基本规定。“différend”的第二层含义为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也可称为语位的特殊性。语位是一种特例(token),而不是类型(type)。如果说在力比多哲学中能量就是事件的话,那么在差异哲学中,语句就是事件,事件是任何差异存在的条件。这种“语句-事件”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语句的发生是无法预测的独一无二的发生;正是由于这种不可预测、不确定发生的语句使得事件无法被完全理解。利奥塔不断地诉诸事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能够把握所有类型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信仰。由此,在语位政治学中,利奥塔把任何事件都定义为一个语句,每一个语句都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事件,语句无法被完全地理解,我们也无法知道其他语句如何同它相连接,任何一种连接都对最初的句子构成一种特殊的理解和与众不同的描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后现代状况才包含了规则不同的不可公度的语言游戏。
尽管利奥塔在其两个哲学系统中都对事件做出详细的阐述,但作为完全不同的哲学系统,事件也存在一定的同与不同。二者的相同之处表现在:两个系统中的事件都反映出一种对既定话语类型的反抗与挑战,不断地表达出新的话语类型和判断方式的诉求。利奥塔将其界定为飞逝政治学(fleeting politics)。飞逝意味着快速的变化与流动,即一种处于不断流动状态而又不拥有任何明确纲领或价值观的政治学”[6](162)。二者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事件的发生环境不同:力比多系统为事件的产生提供一种内部空间,而差异哲学系统则从外部边界为事件的产生提供场所。从两个系统中事件的产生来看,事件作为利奥塔后现代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标志着利奥塔反抗传统的坚定决心。事件就是通过打破以往的解释方式,去寻找一种新的判断方式和经验模式,去挖掘那些既定概念之外的内涵。
三、“事件”与利奥塔的语用观
如前所述,在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描述中,语句被形容为事件,语句的连接需要依赖规则,这个最初的语句事件存在着多种可能会发生的连接方式,并且这些连接方式之间是彼此冲突的。也就是说,由于事件的不可预测性,使得语句之间的连接必须按照语句之间的联系来加以思考。实际上,每一个语句的发生都打乱了我们关于时间前后相继的观念。利奥塔认为,事件总是处于时间之中,所以事件具有一种不可重复性,这种不可重复性和瞬间性特征注定了语句并不包含在具体的连接模式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根据既定的语言游戏去确定某种适当的连接。
第一,差异的“衔接法则”。既然语句就是事件,且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那么语句在进行连接时便会出现不同的连接法则,利奥塔称之为“衔接法则”。“衔接法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一个完整的语句系统中,一个句子要紧跟另外一个句子,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事件发生后,在此事件之后的每一种行为都是对它的反应。这一点表明,事件需要得到回应和判断。但是,事件的单一性和独特性又表明,事件拒绝简单地被放进一个预先设定的框架之中。一个事件是我们在瞬间觉察到某些事物正在发生,并且这个事件呼唤我们对此作出反应,但并不知道我们回应时使用什么话语类型。换句话说,任何预先确立好的类型并不能准确且适当地回应事件的独一性。所以利奥塔明确总结出:语句之间的连接是必然的,但如何连接以及具体的连接法则则不是既定的。有多少个事件发生,就可能存在多少种“衔接法则”。因此,不存在任何一种普遍必然的总体性方法能够决定语句连接的正确规则。既然存在无数个可能的连接法则,又不存在一种必然法则,语言又如何成体系呢?利奥塔指出,虽然不存在一种必然正确的连接,但是存在一种适当的连接。也就是说,一个句子与另外一个句子之间的连接并不存在一种必然公正的连接方式,连接方式要受到具体的语言游戏及其风格的影响,因此,仅限于某一种特定风格内的连接方式才是一种适当的连接方式,利奥塔将这种相关性称为“适当性”。所以利奥塔的语言链条中存在这样的状况:一方面,语句连接是必然的,这适用于所有可能出现的语言游戏;另一方面,语句连接只能是适当的,这只能适用于任何一种具体风格的语言游戏。
第二,多样的语言“指标”。基于不确定的“衔接法则”,利奥塔引出他的另外一个概念,即“指标”:“话语的风格不仅使我们能够确定某种连接的适当性,而且也能引入指标的概念。关于这些指标的一种简单理解可以是这样的,即它们是通过某种特殊连接而达到的东西。”[6](118)“指标”的出现依然与语句的连接密切相关,“指标”蕴涵在话语的风格之中,不同的风格包含不同的“指标”。“指标的多样性,等同于风格的多样性,它使每一种连接成为一种‘成功’,而其他的连接却没有。这些其他的连接仍处于某种被忽略、遗忘或压制的状态。”[9](136)最初的语句进行连接时,不同的语言风格会发生冲突,如果一种风格企图决定某个语句的连接,这种风格的“指标”就会强加在其他话语风格的“指标”上。这样的语句连接被视为一种非适当连接。在某种意义上,“指标”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利奥塔“衔接法则”的一种代名词,但“指标”比衔接法则更能体现语句连接的非必然性。利奥塔的“指标”不仅是为不同的语言游戏作证,也是为主体性的权威作证。在利奥塔的语位政治学链条上,主体既是说话者,又是倾听者。一方面,主体作为一个说话者首先超越了传统语言系统(如海德格尔的“语言说人”预设),个体并不只是在被动地等待事件的降临和发生。作为自由能动的人,主体无需遵从某种普遍性和规则性,可以逾越这种有限性和既定的秩序来回应已经发生的“语句-事件”,去创造新的事件来批判和重建传统。另一方面,每个主体作为倾听者,都是主宰历史进程和裁决真理的权威,没有什么规则规定他必须要按照某种合法性屈服于一种理性传统,在语用链条上,没有人可以占据意义诠释的中心位置。利奥塔多样的“指标”表明:因为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固定的“指标”,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元叙事,那么总体性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相对的表达“处境”。“différend”作为一种“异识”代表了语位,是一种特例而不是类型,这意味着新的“语用-事件”不断发生。“语位”在发生时由四项要素构成,即一个语句的发布者(addressor)、一个接受者(addressee)、一个所指物(所指称的事物)、一个含义。在一个事件发生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有某种事件发生了,但不明确它的具体内容,利奥塔称之为“表象”(presentation)。但是下一个语位的出现可以将前一个语用事件放到具体的语境之中,以此来确定它的含义和内容,利奥塔称之为“处境”(situation)。对于“处境”,利奥塔给出解释:任何一个语句都代表一个事件,这个最初的语句拥有一个事件的身份无法被完全理解。同时,由于没有任何一种指令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只能随着下一个语句的产生而出现,所以只有当另外一个句子紧跟最初语句出现的时候,“处境”才会发生。进一步讲,只有当后来的一个语句连接上了最初的语句,能用一种固定的方式将彼此联系时,这些实例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够被确定。所以,在不同的体系中将最初的表达置于某种处境的方式是不同的,并且各个体系之间无法比较,这些体系都包含着这个最初表达的异质的处境。“处境”的另外一面在于,处境永远无法把握最初语句表达的全部含义,它只是把表达限制在更为具体的“处境”之中,从而对前面的语位进行综合和进一步解释,并且消除在最初语句表达中产生的众多可能性。
四、“事件”与利奥塔的艺术观
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在利奥塔的艺术观中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利奥塔指出,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见证事件的发生,艺术创造保存了事件的震撼力量,成为事件发生的见证。在利奥塔看来,艺术有自己存在的使命与原则,艺术所追求的不是传统哲学中那种稳定的总体性,因此艺术不可能成为综合的工具。作品的事件性质拒绝将艺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艺术的目的是干扰已经约定俗成的共识和总体性,从而推崇一种新的声音。正是艺术,为利奥塔提供了思考分歧的方式。在艺术领域,利奥塔极力推崇先锋艺术,先锋派所试验的艺术就是在瞬间表现不可表现的事物,他们试图把这种不能表现却又要表现的精神在瞬间呈现出来。在他看来,先锋派真正体现了这种实验的精神,所以他呼吁艺术实验,呼吁突破艺术的边界。按照利奥塔的观点,先锋派的真正使命就是在作品中表现不可表现的东西。利奥塔将先锋艺术作为工具去证明一种不可表现性,先锋艺术的实验精神不仅体现在绘画艺术中,也体现在利奥塔独特的电影艺术中。
(一)不可表现的绘画艺术
在利奥塔那里,艺术的主要力量是见证事件的发生。“通常,它(事件)的反复出现是将艺术作为一个事件的可能性,把艺术看成是我们际遇的,或发生的事情,难以理解或言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不确定的,或者出于我们能感知或言表和理解的范围之外,甚至是一种让我们的时间感和自我感错位和断裂的东西。”[10](17)这种艺术打破传统的艺术呈现规则,去见证一种无人之地,从而寻求新的表达方式和话语类型。在绘画艺术中,利奥塔主要推崇的是画家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纽曼是典型的先锋画家,也是色域绘画的先驱。色域绘画的特征就是画面不会出现任何具体的物象,取而代之的是大块色面或用抽象的几何图案去表达某种意象。利奥塔认为,纽曼画作中的线条与韵律往往使人看不懂画的是何物,但它就在那里,它就是一切,观看者无法从中找到一种确定且清晰的含义,从而不得不去猜想画作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种回应方式中,观赏者体验到的是一种事件的发生性和瞬间性。事实上,这种方式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经验意识,它仅意味着“某些事情发生了……或者,更简单地说,它发生了……并不是媒体意义上的重大事件,也不是一个小事件,只是一个发生……一个事件,一个发生……是无限的简单,但对于这种简单,仅仅只能用一种知识贫困的状态去走近它,这时,我们所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必须停止运作”[3](90)。所以,在纽曼的作品中,一个绘画作品就是发生的一个瞬间,纽曼自己也提到过,艺术创作不是对形象的组合,而是致力于对时间的感知。除了纽曼,利奥塔还推崇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认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刻体现了对于传统的解构,表现为“怪诞”“无形式”。杜尚的目的就是使艺术脱离那些固定的形式,从而在纯粹自由的无形式中呈现“此刻-瞬间”的当下性特征。虽然杜尚的创作思维符合利奥塔所秉承的反叛本质,但是杜尚与纽曼的作品存在不同。在利奥塔看来,杜尚的作品虽然反叛,但是作品与观者之间依然存在一种传递信息的过程,杜尚作为画家也是信息发送者,观者作为信息接收者要极力猜测作品的意义,此时依然存在一种叙事和主题。但是纽曼的作品并不存在这些环节,画家不再担任发送信息的职责,“信息(画)就是信息员,它说:‘我在这里’,也就是说:‘我是你的’,或‘到我这儿来吧’。我、你,二者不可替代,仅存在于这里与现在的急迫之中”[3](81)。在纽曼那里,此刻就是主题,它不会向观者阐释某种叙事和意义,而仅仅象征事件的发生。利奥塔将这种感觉用一个现代美学传统中的词汇代替,即崇高(sublime)。崇高情感是对利奥塔事件本质的见证,表现不可表现性就是利奥塔通过崇高美学为后现代艺术寻找到的一种精神,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同时,基于这种不可表现性,利奥塔所推崇的这种绘画艺术也是对传统视觉效果的反叛,“原先画家实践中的那些小前提逐个受到检验与争辩,各种先锋派对色调、直线透视、价值表现……以及许多其他先决条件提出创造性诘问。……视野不但与眼睛而且还与灵魂有关,这些画家着手改革假定的视觉已知事物”[11](22)。这种改革不仅隐藏了传统叙事的再现性,还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视觉认知。这种颠覆在利奥塔的“异电影”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二)反视觉的电影艺术
在电影艺术中,利奥塔提出了一种基于事件特征的“异电影”⑥理论。在利奥塔看来,传统叙事电影遵循再现叙事的原则,通过胶片拍摄并按照一定的投影速度与比例使观众去感知这种有序运动,观众看到的叙事电影的剧本和场景是导演提前设定的,并以此引导人们坚信电影中所展示的被再现之物与无限的外部世界是完全相同的。利奥塔的“异电影”则突破了电影视觉的边界,他认为,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一些混乱和模糊的东西,这些都会打乱剧本节奏或电影拍摄秩序,是没有价值的必须要删除的内容。但是,利奥塔所追求的是事件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他极力推崇的不是那种被提前编排好的电影内容,而是在偶然性中出现的东西。在利奥塔看来,电影的本质并非仅仅去捕捉和复制运动,不是按照已有的运动去建构与综合,而是在组建这些镜头时的不断删除和纠错。并且,这种形式的电影不再是用来纯粹讲故事的消费品,而是彰显电影形式本身激发出来的快乐。
利奥塔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与弗洛伊德的两种内驱力有关。力比多有两种类型,即生本能与死本能。弗洛伊德晚期的一篇文章《超越快感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曾对这两种本能作出论述。在利奥塔看来,根据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原则,人的本能储存到一定程度后要进行释放,并且在不断释放之后再度达到能量的平衡,使欲望的流动在力比多装置⑦中完成循环。利奥塔把再现性叙事电影(如好莱坞电影)理解为一种对应生本能的力比多装置,电影在组合多个镜头时会实现欲望能量的传递和释放,所以,当电影拍摄过程中突然发生一些偶然或取景不佳等意外镜头时,导演往往会进行删除,防止这些跳脱的镜头违反力比多装置的规则、破坏能量平衡。但是利奥塔的“异电影”则是对应死本能的“反力比多装置”,在这个意义上,“异电影”作为一种新的电影形式与死亡冲动和自我否定的本能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恰恰是那些在摄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和反常的瞬间可以为电影艺术带来新的生机。应该说,利奥塔“异电影”的终极旨归是超越和颠覆,表面来看是对电影形式的反抗,实则是承继其后现代思想,通过新的电影形式去颠覆传统叙事电影的语言和形态,倡导一种逆向且具有破坏性的电影形式。利奥塔的“异电影”突破了电影视觉装置的边界,重视那些场外调度的内容,即那些在调度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不可预测也无法构想的内容,这种对瞬间的推崇在根本上体现出利奥塔事件存在论的本质。
如果说传统叙事电影追求一种能量生产与运转使人感到舒适平衡的话,那么利奥塔的“异电影”则要破坏这种平衡。他选取了两种极端的类型来打破这种视觉平衡,即活动绘画⑧和抒情抽象⑨,这两者分别代表极度静止和极速躁动。活动绘画主要提倡一种极度的静止,从而将一种无限的静止作为一幅画展示给观众,最具代表性的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安迪·沃霍尔的电影通常都是非叙事性的,较为典型的有两部,即《沉睡》(Sleep,1963)和《帝国大厦》(Empire,1965)。《沉睡》拍摄了诗人约翰·吉奥诺(John Giorno)的睡眠状态。一般来说,在普通的电影中,这个镜头最多也就几秒钟,但是安迪·沃霍尔的这部电影,整整5 个小时21 分钟都在拍摄这个诗人的睡觉状态。《帝国大厦》片长为8 小时51 分钟,而在这将近九个小时的时间里,该片以单一固定的镜头拍摄了帝国大厦从天黑到清晨八个多小时的变化,而观看这场电影的观众几乎无人能从头看到尾。由此可见,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其实是将电影叙事压缩成一种感受,一种像摩天大楼一样能让人觉得静止的感受,观者在影片中没有找到叙事而仅仅体验这种发生性本身。除了会冲击人们视觉感受的极度静止之外,利奥塔倡导的另外一种极速躁动的“抒情抽象”更加破坏人类的视觉认知。以他推重的杜尚的电影为例。杜尚《贫血的电影》(Anémic cinéma,1926)中,在圆形硬纸板上绘制出一种几何螺线,一旦转动圆盘,静止状态下的几何螺纹会形成一种三维立体式的形式,一个螺旋一个圆盘,这两者在完美的交替中持续到最后。平时传统叙事展示出来的电影影像模式与人的视觉感知相似,会尽可能符合人类直立行走时稳定的视觉感受,比如传统叙事电影在剧场的第一空间放映电影时会与观众保持一种距离,从而形成一种与地面平行的长方形的画框,画面中的视觉会极力还原现实情况的模拟。《贫血的电影》中的这种旋转会改变人们的视觉认知,在极速的旋转之后,人往往会感到幻觉和眩晕。极度静止和极速躁动这两种极端类型的电影模式改变了人们正常的视觉认知,在两极极端的融合下造成一种反视觉的视觉效果。由此不难看出,利奥塔的“异电影”使观众逃离了主流叙事的观赏模式,使观赏者可以在观影过程中真实的叙述自己的体验。
五、结语
“事件”贯穿利奥塔的整个思想历程,他试图通过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无法描述性来揭开后现代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哲学主要是以话语与图像、推论与感觉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其中,前者总是被赋予特权来压制后者。因此,利奥塔以事件的瞬间性和不确定性来打破传统理性中的确定性因素,将受到压制的感性从精神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在他看来,只有在某些前提下,如在无序的规则中、失常的意识中、开放的欲望中事件才会发生。因此,事件的产生必须以颠覆人的正常意识为前提,而解构意识的控制恰恰是利奥塔后现代思想的核心,“事件”其实是利奥塔用来反抗理性绝对统治的工具。基于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特征,利奥塔每个阶段的思想中都带有事件的色彩:在社会公正问题上,利奥塔反抗总体性,反对以一种宏大叙事压制统合所有的知识;在现代性问题上,利奥塔提出要重写现代性,尤其以事件的异识反抗哈贝马斯的共识,提出共识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地平线;在崇高美学问题上,利奥塔提倡一种无法呈现的物,崇高感代表某种无形的东西对经验的超越。所以,“事件”概念的使用表明了利奥塔反抗西方理性传统的强烈愿望,他就是要利用事件的不可把捉性来提倡一种异识,为反叛的后现代发声、为敞开的纷争作证。
注释:
① 在法语中,“phrase”意为“句子”或“短语”,但是作为语用学的基本单位,“phrase”既不是“句子”,也不是“短语”,而是“事件”之义。
② 原印象作为核心坐落到在场域的一种生发性的位置上,作为绝对开端,它是所有其他东西从中持续生产出来的源泉,从这一源泉流出来的是作为原印象的变异的滞留。
③ 力比多带是情感、形象和构造的交汇点。力比多带类似于一个身体,但又不同于身体,它没有一整套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由情感和欲望流动的后果拼凑而成的,是事件发生后的产物。同时,这个力比多带不具有身体的界限和边界。
④ 形象和构造是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能量在力比多带上产生出形状,形象和构造解释并控制能量。
⑤ 这里的双重性指利奥塔力比多哲学系统中的两个符号,即张量与掩饰机制。
⑥ 1973年利奥塔在《美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反电影》(“L’acinéma”)的文章,这里的“反电影”既不是“anti-cinema”,也不是传统英文的“against cinema”(反对电影),而是借鉴了阿多诺的反艺术。
⑦ 利奥塔在著作《作为力比多装置的绘画》(La peinture comme dispositif libidinal,1973)中将这个理论模型概括为“力比多装置”(dispositif libidinal)。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使用了“装置”(dispositif)这个词,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装置,并且利奥塔将再现性艺术,如绘画、戏剧和电影等都理解为一种力比多装置。
⑧ 活动绘画是欧洲一种有趣的传统,由真人来扮演绘画,许多人在精心绘制的虚拟场景中尽可能静止不动,伪装成一幅绘画。
⑨ 抒情抽象是欧洲二战后兴起的抽象派绘画,抒情抽象与“冷抽象”“几何抽象”相对,它的核心是极速运动,是一种热烈的、强烈释放的抽象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