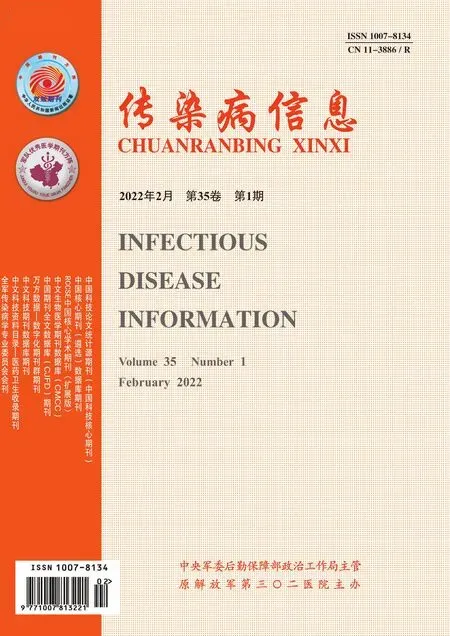肠道微生态与肝细胞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刘哲睿,贾晓东,陆荫英
1 概 述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世界上第六大常见癌症类型和第四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约占原发性肝癌的75%~85%[1]。HCC通常继发于慢性肝病和肝硬化,乙型肝炎(乙肝)、HCV感染、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黄曲霉素和马兜铃酸等都是诱发HCC的危险因素[2]。由于HCC早期诊断困难、起病隐匿和易复发转移等特点,大部分患者确诊时病情已经进展至中晚期,迄今为止,HCC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低于20%[3]。目前,索拉菲尼仍是中晚期HCC患者治疗的首要选择。虽然临床治疗HCC逐渐使用如阿特珠单抗联合贝伐单抗等新兴治疗手段,但效果仍不理想,因此亟需对HCC潜在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开发出针对HCC患者更有效的治疗方式。
肠道微生物群是人体中最大的微生物系统,目前认为肠道中的微生物数量超过1014个,其中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古生菌[4]。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间的共生关系在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机体免疫系统异常、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及环境改变等因素的影响下,肠道微生物群与机体间的共生关系发生改变并可能诱发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5]。由于肠道和肝脏间存在的天然解剖结构,即“肝-肠轴”的存在,肠道菌群在HCC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因此深入了解肠道菌群与HCC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未来HCC诊断标准的制定及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就目前肠道菌群影响HCC的机制和包括抗生素、益生菌、粪菌移植及免疫治疗在内的肠道微生物相关HCC治疗方式展开综述,旨在深入阐述肠道菌群及HCC发生、发展间的关系,为HCC的预防及临床诊治等方面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2 肠道微生态影响HCC的机制
目前认为,绝大多数的HCC患者继发于慢性肝病,肠道菌群紊乱及菌群易位能够促进肝脏炎症、纤维化及肝硬化的进展[7]。研究已证实,在肝硬化患者中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和肠屏障破坏会导致HCC的发生[8],因此,目前针对肠道微生态在影响HCC的发生、发展中的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肠屏障破坏导致肠道微生物的肝脏易位和肠道微生物群紊乱两方面。
2.1 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与HCC 目前认为慢性肝病导致的肠屏障破坏使得多种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microbiota-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MAMPs)易位,通过循环进入肝脏从而促进HCC的发生[1]。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是革兰阴性菌细胞壁的组成成分,有研究报道在HCC小鼠模型和HCC患者的血液循环中均发现高水平的LPS[9]。高水平的LPS可能导致细菌易位并促进肝脏炎症反应,此外,慢性肝病患者肠通透性升高导致LPS的高循环水平,也被证实可以促进慢性肝病的进展并导致HCC的发生[10]。据报道,LPS是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4的一种重要配体[11]。作为一种模式识别受体,TLR4可以识别MAMPs,从而调节机体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免疫应答[12]。研究发现,TLR4在HCC患者的肿瘤组织中过表达[13],同时动物模型也揭示了LPS/TLR4在促进HCC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低剂量LPS刺激的野生型化学诱导HCC的小鼠模型比无菌小鼠表现出更为严重的肿瘤表型[14],Naugler等[15]发现TLR4-/-小鼠在化学诱导所致的HCC中肿瘤发生率、肿瘤大小及数量与化学诱导的野生型小鼠组相比均显著降低。对其机制的深入探索阐明,活化的TLR4可以通过肝细胞、肝星形细胞和库普弗细胞激活NF-κB和STAT-3,产生促炎细胞因子IL-7、IL-1β、IL-6以及TNF-α,从而促进HCC的发生[1]。此外,TLR4还可以通过肝星形细胞上调促癌蛋白表皮调节素、肝细胞生长因子以及双向调节蛋白的表达,从而诱导HCC细胞的增殖[14]。
此外,革兰阳性菌的主要成分脂磷壁酸(lipoteichoic acid, LTA)也参与HCC的发生。LTA是TLR2的重要配体之一,TLR2被证实在机体应对革兰阳性菌的先天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16]。研究发现TLR2在与LTA结合并激活后,可以激活肝星形细胞表达衰老相关表型,Loo等[17]发现肥胖导致机体肠道LTA含量的上升,可以活化肝星形细胞上的TLR2,使肝星形细胞表达衰老相关表型并通过调节COX-2信号、前列腺素E2的活性与水平从而抑制其抗肿瘤免疫作用,形成促进肿瘤进展的肿瘤微环境,并最终导致HCC发展。综上,肠道微生物可以通过其自身的MAMPs作为配体激活肝脏中的TLRs,从而通过免疫应答或表达产物进而影响HCC的发生、发展。
2.2 微生物代谢物与HCC 除了肠屏障损伤导致的MAMPs通过“肝-肠轴”促进HCC的发生、发展外,肠道微生物紊乱同样在HCC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胆汁酸作为一种重要的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其在HCC发生、发展机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Kitazawa等[12]发现由于饮食或遗传因素导致的肥胖,会使机体肠道微生物群发生紊乱,革兰阳性菌含量升高,并最终导致其介导的脱氧胆酸(deoxycholic acid, DCA)含量上升。与LTA作用机制相似,DCA同样可以激活肝星形细胞TLR2,表达衰老相关表型进而导致促炎因子释放并促进HCC进展[17]。DCA还可以通过调节肝窦内皮细胞CXCL16的表达从而介导NK细胞的募集。Ma等[18]通过对HCC小鼠模型进行抗生素或胆碱胺处理,抑制肠道菌群对初级胆汁酸的代谢能力或抑制胆汁酸的生理功能,发现初级胆汁酸可以上调肝窦内皮细胞CXCL16的表达,从而使其对NKT细胞的募集能力增强,后者通过CD1d依赖途径发挥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而作为次级胆汁酸的DCA通过抑制肝窦内皮细胞对NKT细胞的募集从而促进HCC的进展。此外,Yamada等[19]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导致的HCC小鼠模型中发现,DCA可以通过激活肝细胞中mTOR信号通路介导HCC的发展。总之,DCA可以在衰老相关表型的调控、NKT细胞募集以及mTOR通路的激活等方面发挥促进HCC发展的作用。
另一种细菌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也被证实与HC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在SCFAs中,丁酸和丙二酸可以通过表观遗传机制诱导调节性T细胞,调节肝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抑制肝脏炎症[20]。然而,Singh等[21]发现富含丁酸饮食虽然能够减轻小鼠的炎症反应,但同时也会导致小鼠肝内胆汁淤积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并促进HCC进展。虽然现有研究证实SCFAs在HCC的发生、发展中确实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作用机制还未被明确阐述,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3 肠道微生态治疗与HCC
目前,针对肠道微生物群与HCC发生、发展的机制探索主要集中在动物水平,仍须在临床患者中对其进行验证并深入探索其下游效应机制。但现有研究提示了肠道微生物群的紊乱以及肠屏障的破坏与HCC的发生、发展间密切相关。因此,在维持机体正常的肠道微生物群以及防止出现微生物群的失调等方面,对HCC的治疗方式进行探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随着对肠道微生物群、“立肝-肠轴”以及HCC间关系的研究逐步增多,以肠道菌群为导向的抗生素疗法、益生菌治疗、粪菌移植疗法以及联合免疫疗法等已在HCC的临床治疗方面显示出了独特优势。
3.1 抗生素治疗与HCC 目前,有研究者在探索肠道微生态失调与HCC间关系的动物模型中发现,联合使用广谱抗生素可以减轻小鼠的肿瘤耐受并减缓HCC的发展[22]。对化学诱导HCC的小鼠模型联合使用氨苄霉素、新霉素、甲硝唑和万古霉素的四联抗生素,可以显著预防小鼠HCC的发生[14],提示抗生素具有对HCC的预防作用。Yoshimoto等[23]也发现,在对高脂饮食诱导HCC的小鼠进行四联抗生素干预同样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此外,对小鼠进行革兰阳性菌特异性清除的万古霉素干预,也会显著减轻高脂饮食诱导的HCC的进展,提示抗生素疗法具有治疗HCC的潜力。抗生素利福昔明也已被证实可以促进肠道有益微生物如双歧杆菌、粪杆菌和乳酸杆菌丰度的增加,同时不会过度改变肠道微生物特征[24]。此外,Dapito等[14]发现利福昔明可以减缓DEN/CCL4诱导的小鼠HCC肿瘤数目,提示其作为抗生素在通过肠道菌群干预HCC方面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然而,虽然抗生素在HCC的治疗方面已展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但临床上长期使用抗生素同样存在多种潜在的风险,如肠屏障损伤、肾脏毒性、抗菌素耐药及多药耐药感染等[25-26]。因此,具有HCC临床治疗潜力的低风险抗生素仍需进一步的探索及研发。
3.2 益生菌治疗与HCC 益生菌是一类定植于人体肠道,改善宿主微生物生态平衡并对宿主有益的活性微生物[27]。机体的益生菌主要包括丁酸梭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放线菌和酵母等,通过促进有益菌的生长并抑制有害菌来维持肠道菌群平衡,减少肠道炎症,改善肠屏障功能并抑制HCC的发展[28]。除了传统的益生菌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外,目前对于包括梭状芽孢杆菌Ⅳ、梭状芽孢杆菌ⅩⅣa以及艾克曼菌在内的“二代益生菌”的研究正逐渐兴起[29]。
益生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降低HCC发病风险。首先,益生菌能够促进具有抗肿瘤作用的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如Li等[30]发现使用一种混合了鼠李糖乳杆菌、大肠埃希菌Nissle 1917以及VSL#3的混合抗生素,能够促进小鼠肠道中具有生成抗炎代谢物作用的菌属如普雷沃菌属和颤螺旋菌属的生长,促进肠道内抗炎Treg/Tr1细胞分化,并通过下调肝脏TLR诱导的炎症反应来抑制HCC的发生。此外,Elshaer等[31]在硫代乙酰胺诱导肝硬化的Wistar大鼠模型中发现,早期给予植物乳杆菌干预,可以显著抑制肝细胞TLR4、CXCL9和PREX-2表达,从而抑制肝硬化向HCC的进展。
其次,益生菌能够通过表观遗传调控宿主基因表达水平,从而抑制HCC的发生、发展。Heydari等[32]对氧化偶氮甲烷诱导的小鼠癌症模型进行嗜酸性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干预后发现,小鼠血液中RNA-155、miR-221、肝脏中的Bcl-w和KRAS等致癌基因的表达显著降低,同时miR-122和抑癌基因转录因子PU.1表达显著上调,提示益生菌能够通过激活特定基因和microRNA表达在小鼠HCC的发生中发挥积极作用。有研究发现嗜酸性乳杆菌与酿酒酵母形成的一种益生菌混合物,可以通过激活肝细胞中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的表达,协同防止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33],此外,类植物乳杆菌可以减少Wistar大鼠肝脏中由于糖尿病导致的DNA损伤[34]。上述研究均提示益生菌通过减缓肝脏疾病进展从而在预防HCC的发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 益生菌可以通过预防慢性HBV和HCV感染来帮助减轻HCC的发生风险。Lee等[35]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用青春双岐杆菌提取物处理HepG2细胞可减少HBV载量和细胞变性。此外,在HCV感染者中粪肠球菌可以降低血清肝损伤标志物ALT和AST水平,虽然其对HCV载量的影响并未出现显著趋势[36],但已表明益生菌可以通过预防HBV和HCV感染促进肝功能的恢复,并有助于减轻HCC的发生风险。未来,仍需进一步对相关益生菌及其深入机制进行探索。
最后,益生菌能够通过改善肥胖来预防肝脏的脂质毒性。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中,补充嗜酸乳杆菌和乳酸乳杆菌可以改善肝损伤[37]。有研究表明,使用益生菌可显著降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体质量和总脂含量,并能够通过下调促炎细胞因子TNF-α来减少肝脏炎症[37],从而预防HCC的发生。
此外,益生菌疗法还具有安全、便宜及个体差异化等优势,因此,进一步探索新型益生菌疗法和机制在HCC的预防及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3.3 粪菌移植疗法与HCC 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al transplantation, FMT)是一种将健康人类粪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特定患者的胃肠道中,从而重塑有益于机体的肠道菌群的一种新技术,已受到广泛关注[38]。FMT具有操作简单,疗效高等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肠易激综合征、胰岛素抵抗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治疗[39]。在肝脏中的初步研究表明,FMT在代谢综合征、重症酒精性肝炎以及肝性脑病中也具有一定疗效[40-42],同时,FMT还可能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减少某些细胞毒性代谢物或炎症介质的产生,恢复失调的肠道菌群并可能影响HCC的进展[43]。但到目前为止,关于FMT与HCC间的确切机制及治疗方式仍在探索当中。FMT疗法还存在供、受体间疾病传播,患者耐受以及无法预知的免疫反应等相关问题[43],亟需更多的研究来确保其在HCC治疗中的实用性及安全性。
3.4 肠道微生态与HCC免疫治疗 近年来,通过肠道菌群改善免疫治疗中患者的免疫应答受到广泛关注[44]。如在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和尿路上皮癌治疗中,已有大量研究证实肠道菌群能够显著改善癌症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应答情况[45-46]。有研究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有无应答的黑色素瘤患者的肠道菌群进行比较,发现梭状芽孢杆菌、瘤胃球菌属和粪杆菌属在应答组患者肠道中丰度升高,拟杆菌属丰度则在无应答组患者肠道中显著富集[47]。还有研究发现,有着更高丰度的粪杆菌和其他厚壁菌门的黑色素瘤患者,能够更好的应答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 (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 CTLA-4)的免疫治疗[48]。黑色素瘤患者单独口服双歧杆菌的疗效与PD-L1抗体治疗效果相似,但当两者联合治疗时几乎能够完全控制肿瘤生长[49]。
以具有调节免疫系统发挥抗肿瘤活性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主的免疫疗法,在HCC的临床治疗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50]。其中,CTLA-4和PD-1/PD-L1抗体在HCC的治疗方面同样起到关键作用[1]。Zheng等[44]对PD-1治疗表现出不同应答水平的HCC患者肠道菌群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应答组患者肠道中变形菌门丰度逐渐增加,而应答组患者肠道中则呈现出艾克曼菌和瘤胃球菌属的大量富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能够影响癌症免疫治疗的效果[44-46,49]。肠道菌群的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早期接受PD-1抗体治疗的HCC患者的药物疗效及预后水平[44]。关于调控肠道菌群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多项实验也在逐渐开展[1],有望阐明肠道微生物与HCC免疫治疗间的关系从而推进开展更为有效的临床HCC治疗方式。
总之,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调节癌症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反应,在癌症的免疫治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能够改变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答情况。然而肠道微生物群与HCC患者免疫治疗间的关系仍未被完全阐明,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探索。
4 展 望
随着微生物技术的进步,肠道微生物群和HCC之间的关系逐渐被阐明。目前大多数关于肠道微生物群与HCC发生、发展间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动物模型中。由于人体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受到诸如抗生素、疾病以及饮食等因素影响,动物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人体肠道微生物的动态变化,因此人体肠道微生物群与HCC之间的关系仍需在人体内进一步探索及验证。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动物模型和其他肿瘤患者中肠道微生物群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效果是否同样适用于HCC的治疗,但肠道微生物群逐渐显示出其成为HCC辅助治疗策略的潜力。重塑肠道微生物群是否能够逆转肠道稳态失调HCC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应答效果仍需进一步阐释和研究。此外,对于肠道微生物群在HCC治疗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粪菌移植疗法及益生菌疗法的研究,有助于推动HCC的防治及个体化精确治疗,有望在未来成为治疗HCC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