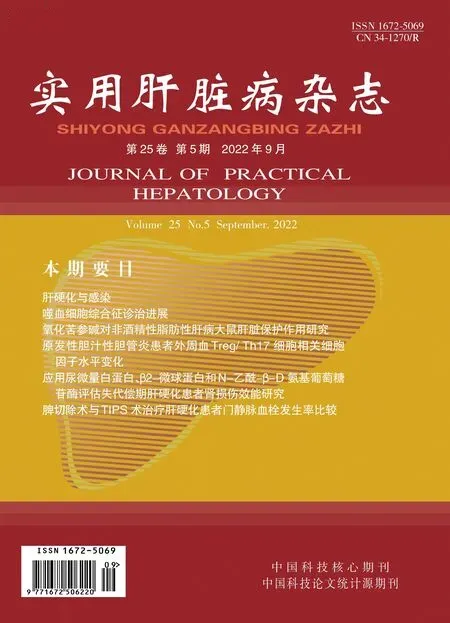肝硬化并发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诊治现状
罗楠,李荣宽
细菌感染是肝硬化的主要并发症[1],占肝硬化患者急性失代偿事件住院率的25%~46%[2]。细菌感染使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病死率增加4倍,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慢加急性肝衰竭引发的多脏器功能衰竭[3]。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SBP)是肝硬化患者最常见的细菌感染之一,其次是尿路感染、肺炎、皮肤软组织感染和自发性菌血症[4]。SBP是指在没有明显腹腔感染因素的情况下发生于肝硬化和腹水患者的腹水细菌感染,约占肝硬化住院患者的10%~30%[5]。因此,早期诊断及合理化治疗对于改善该部分患者预后至关重要。
1 肝硬化并发SBP的发病机制
SBP的发生涉及多种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肝硬化患者易感染的因素有很多,肝功能障碍引起的体液和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肠道菌群失调和细菌移位,尤其是门静脉高压症情况下加剧,以及遗传因素也是该人群感染的病理生理学的决定因素。
1.1 肠道黏膜屏障功能下降与细菌移位细菌移位是指一些肠道细菌穿过消化道黏膜屏障,侵入肠系膜淋巴结或肠外器官,是肝硬化患者发生SBP的重要原因。其发生机制首先是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发生质和量的变化。对肝硬化患者粪便分析发现肠道菌群多样性降低,有益菌减少、而有害菌增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6];其次,由于肠道蠕动降低和肠道胆汁酸减少,致使小肠细菌过度生长[7, 8];在肝硬化患者门静脉高压导致肠黏膜淤血,肠壁通透性增加、屏障功能随之降低,促进细菌移位[9]。
1.2 病原体及耐药菌属由于肠道细菌移位为主要致病机制,SBP常见的致病菌株是革兰氏阴性杆菌,以大肠杆菌和克雷伯氏菌为最常见的致病因子[10, 11]。但近年来,随着介入治疗和预防性抗生素使用的增多,出现了向革兰氏阳性菌、喹诺酮类耐药菌和多重耐药菌的转变。目前最常见的革兰氏阳性菌是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和葡萄球菌属[12, 13]。多重耐药菌感染占肝硬化患者总感染的35%[14],导致对推荐的初始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应答降低[15]。近期,对全球耐药菌的研究发现,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肠杆菌属仍是近年来最常见的多重耐药菌。在亚洲范围,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和鲍曼氏菌相对常见[16]。此外,也有少数真菌感染。
1.3 免疫功能紊乱及遗传因素肝硬化患者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均降低,同时伴随持续的促炎状态造成免疫功能紊乱,表现为肝脏吞噬细胞活性降低、补体产生减少、中性粒细胞功能缺陷、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功能受损,致使细菌或细菌产物无法通过门体分流被肝脏免疫系统所清除而进入体循环[17, 18]。此外, Toll样受体-2、法尼醇X、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2基因突变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高水平表达可能与SBP 发生有关[19-22]。肝硬化患者腹水总蛋白降低、低钠血症、高胆红素血症、胃肠道出血和质子泵抑制剂过度应用等可能增加细菌移位,使SBP的发生机率明显增加[23, 24]。
2 SBP的诊断
2.1 SBP的诊断国内外肝硬化腹水管理指南或共识均指出,SBP的诊断主要基于诊断性腹腔穿刺术,而延迟穿刺与死亡风险增加有关。与晚期腹腔穿刺术患者比,早期腹腔穿刺术患者病死率有降低的趋势(5.5%对7.5%)[3]。SBP的诊断标准为:肝硬化患者腹水多形核细胞(PMN)计数>250×106/L,即使无明显的伴随症状,也需考虑为SBP。该诊断标准于1977年由Jones首次提出,此后陆续类似研究发现在腹水培养阳性的SBP患者中腹水细胞学均出现多核细胞数大于250/μL[25]。2009年AASLD腹水管理指南正式提出SBP诊断标准亦引用了上述文献,此后该标准被沿用至今。由于腹水培养阳性率较低(20%~40%左右)[26-33],既往国内外指南均推荐腹穿后立即于床旁留取10 mL以上腹水培养,可以提高腹水培养的阳性率[3,33]。以腹水细菌培养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及启用抗感染的时机极易出现漏诊、错失早期治疗机会,影响预后,故腹水培养仅用于指导抗生素的选择,不能作为诊断的必需条件。临床上,SBP可被分为三种类型:即①腹水培养阳性的SBP:PMN≥250 mm3且细菌培养阳性;②腹水培养阴性的SBP:PMN≥250 mm3但细菌培养阴性;③细菌性腹水:PMN<250 mm3而细菌培养阳性[3, 27]。同时,还需注意鉴别继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虽然在肝硬化患者中并不常见,但确会增加死亡风险。 因此,我们可通过腹水常规及生化pH值、蛋白质、葡萄糖、LDH、癌胚抗原、碱性磷酸酶等成分及影像学检查进行鉴别、区分。
2.2 病原体或炎症标志物钙卫蛋白、腹水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脂多糖结合蛋白、乳铁蛋白等可作为诊断SBP的生物标志物,可客观反映患者炎症及肠黏膜屏障受损程度,作为早期干预SBP的指标[3, 28-30,35]。降钙素原(PCT)是目前临床常用的炎症指标,在感染后反应迅速,人体实质组织均可分泌,4 h开始升高,半衰期长达25~30 h,在健康人检测不到,用于细菌感染的早期诊断有较强的临床应用价值[31, 32]。在2018年我国发布的《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南》更是将腹水PCT>0.5 ng/ml纳入SBP实验室诊断标准之一[33]。超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炎症标志物比CRP更敏感。SBP患者血清和腹水hsCRP均较非SBP患者明显升高[34]。但是,PCT和hsCRP诊断SBP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存在较多争议,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持。
细菌内毒素是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L-6)等的主要刺激物。SBP患者腹水TNF-α和IL-6水平显著高于无菌腹水患者,对SBP的进展及预后评估有重要的价值[27,35]。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β(MIP-1β)属于趋化因子,具有趋化和促炎作用。SBP患者血清MIP-1β水平与非SBP患者无显著差异,但腹水MIP-1β水平明显升高。其他早期诊断的标志物还包括干扰素γ 诱导蛋白-10、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同型半胱氨酸和淀粉样蛋白A等,但这些生物学标志物均还缺乏大量研究数据的支持。
2.3 SBP分子生物学诊断细菌DNA检测和测序已被广泛应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腹水细菌DNA水平可能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同时检测腹水细菌DNA相较于普通腹水细菌培养,更省时、简便。对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腹水细菌DNA提取和PCR扩增, 同时行腹水细菌培养,结果提示细菌DNA检测技术诊断疑似SBP的敏感性显著高于细菌培养。采用定量PCR和16S rRNA基因测序方法证实细菌DNA水平与腹水中性粒细胞数量及短期不良临床结局呈正相关。病原体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已广泛应用于诊断感染性疾病,可检测多种体液样本并可较准确识别细菌、真菌、病毒等感染病原体,但在肝硬化并发SBP的诊断应用方面尚无充分的研究证据。我国的一项在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的mNGS检测的多中心研究发现mNGS 可提高病原体的检出率并提供具体的病原学类型,用于指导抗感染方案的选择。因此,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早期诊断SBP具有巨大的潜能。
2.4 白细胞酯酶同工酶试剂带(leukocyte esterasereagent strip,LERS)LERS试纸条测试基于白细胞酯酶活性,是一种非常廉价、简洁、快速的检测方法,是将LERS试纸条浸入腹水中, 白细胞酯酶作用于试剂中的吲哚酚酯产生吲哚酚与重氮盐反应形成的紫色缩合物, 通过判断其颜色深浅评估白细胞数量(呈正相关),最后对比试剂条或分光光度分析得出结果作为初步筛查SBP的诊断依据。由于试剂条带对PMN没有特异性,视觉判断较为主观,且敏感性低,存在假阴性可能,故不推荐直接使用试纸条的检测方法作为SBP的诊断方法。改良的采用分光光度计法在准确性方面明显优于视觉判断,甚至可达到与直接细胞计数相似的准确性,且在SBP低风险和高风险人群中均具有100%的阴性预测值,可作为排除性诊断手段,不必等待腹水培养结果,可能会降低患者检查费用和时间成本,避免抗生素滥用。
3 SBP治疗进展
3.1 抗生素治疗EASL和AASLD指南均强调了感染严重程度、病原菌和当地的细菌耐药性在指导SBP 经验性治疗的重要性,认为诊断SBP后必须立即开始经验性抗生素治疗,以减少并发症、提高生存率,建议在治疗48 h后复行诊断性腹腔穿刺,以验证经验性治疗的有效性。应答较差意为PMN计数较基线减少<25%,应扩大抗生素谱并调查是否存在继发性腹膜炎的可能[3]。对于疑似SBP患者,经验性抗生素的选择应考虑细菌感染史及用药史,仍支持第三代头孢菌素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作为社区获得性SBP的一线策略选择,因为与其它抗生素相比,它们具有肾毒性最小的优势[3],但需要注意该建议并不适用所有地区,每个地域,甚至单个医疗机构都应根据其细菌学谱变化调整经验用药。针对医院获得性SBP或多重耐药菌严重感染者,推荐碳青霉烯类,如美罗培南联合糖肽类或达托霉素;对于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生率较低的地区,可以考虑单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替代药物[3]。目前,临床面临着革兰氏阳性菌和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病原学变化,可能是与肝硬化患者反复住院治疗或ICU住院有关。如果存在革兰氏阳性菌感染或败血症患者,建议使用碳青霉烯类或与达托霉素、万古霉素或利奈唑胺合用[3, 10]。合理的抗生素治疗方案可使SBP消退率达80%~90%,疗程一般建议为5~7 d。研究表明,更长疗程对预后无显著提高[3]。此外,目前关于肝硬化患者感染管理指南不包括治疗自发性真菌性腹膜炎的建议,在大多数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中,棘白菌素被建议作为这些患者的一线治疗用药。
3.2 白蛋白的补充肝硬化患者并发细菌感染是导致肝功能失代偿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急剧恶化的常见诱因,其中肾脏是最常受影响的器官。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发生是 SBP 患者住院病死的主要预测因素。EASL指南推荐白蛋白与抗生素治疗相结合方案,即在诊断的第一天以抗生素联合白蛋白1.5 g.kg-1,在诊断的第3天给予1.0 g.kg-1。这种联合治疗相较于抗生素单一疗法显著降低肝肾综合征和死亡的风险。白蛋白输注可预防所有SBP患者肾功能损害并降低病死率。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出现肾功能不全(血尿素氮>30 mg/dL 或肌酐>1.0 mg/dL)或严重肝功能失代偿(胆红素>5 mg/dL)患者补充白蛋白,对预防AKI的进展起到重要作用,可能改善长期预后。
3.3 微生态治疗肠道菌群失调和细菌移位是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主要感染源。目前,欧美指南推荐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作为一级预防,但长期应用导致耐药菌增加和革兰氏阳性球菌感染[3]。因此,预防仅限于少数具有高感染风险的患者。我国最新发布的《终末期肝病并发感染诊治专家共识(2021年版)》推荐对感染高危患者短期预防性采用肠道选择性净化治疗即应用利福昔明等窄谱抗菌药物去除肠道革兰阴性杆菌,抑制肠道杂菌多度生长、降低肠道内毒素,提高肠道正常厌氧菌属定值力,可显著降低SBP的发生风险。益生菌的应用通过竞争性抑制与上皮细胞的粘附,降低肠道pH值,分泌抑菌复合物抑制有害病原微生物的生长,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降低肠道细菌移位。双歧杆菌被证明可以降低肝硬化小鼠淋巴细胞促炎趋化因子受体表达,减轻炎症反应、腹水形成和氧化损伤。合理的微生态制剂应用可使肝硬化患者血液内毒素水平显著降低,肠道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A显著增加,提高肠道局部免疫功能、促进病原菌排出。因此,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维持肠道菌群稳态也是治疗SBP的关键之一。
3.4 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常用于肝硬化并发静脉曲张出血的一、二级预防,但对于并发SBP患者应避免过量使用利尿剂和其他潜在肾毒性药物。在SBP患者应用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会增加肝肾综合征和急性肾损伤发生的风险、延长住院时间,并降低无移植生存率。因此,对于肝硬化并发SBP患者应谨慎应用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目前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均建议停用。
3.5 其他治疗包括免疫调节治疗、营养支持、有效控制和纠正危险因素、血液净化治疗、终末期肝移植等治疗,但其疗效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4 小结
SBP是肝硬化患者的常见并发症,死亡风险显著增加,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对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至关重要。首先,肝硬化并发腹水或临床特征高度怀疑SBP的患者都应尽早行诊断性腹腔穿刺术。尽管大量研究提出多种用于早期诊断的腹水或血液生物学诊断标志物,但尚未得到充分验证,仍需更多研究结果证实及临床应用的可能性。目前,明确诊断仍以腹水中性粒细胞多形核细胞>250 mm3为诊断标准。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早期、合理的治疗方案必须考虑感染地点、严重程度和当地抗生素耐药性、个人用药史及细菌感染史等情况,是指导正确选择抗生素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