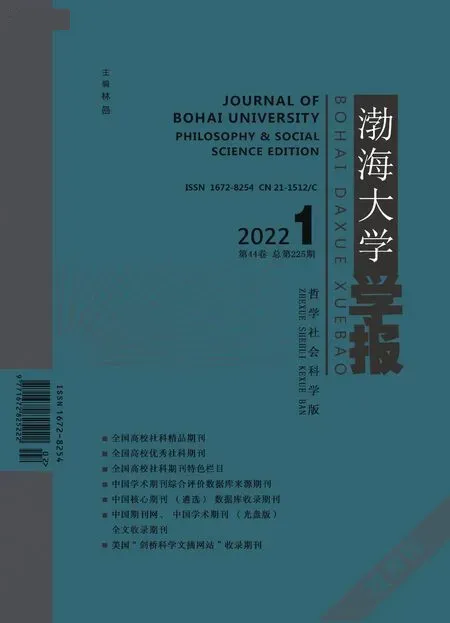论柯莱对斯宾诺莎实体和样态因果解释的困境
王 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作为深受笛卡尔影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同样追求确定无疑的知识,以求达到“清楚明白”的理解。正是出于对确定性的追求,在《伦理学》的写作和论证方式上,斯宾诺莎走得比笛卡尔更远、更极端。这里的极端并不是贬义词,因为《伦理学》一书是更为严格地按照几何学的形式写作。由一些确定的定义和公理出发,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论证进而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因此在对几何学方式的运用上,斯宾诺莎比笛卡尔更加彻底。由于几何学论证所具有的严谨性,我们很难从证明的方法和过程中找出矛盾和漏洞。但是,这并不代表《伦理学》中的内容都是“清楚明白”的。
一、“寓于”和“因果”
纵观《伦理学》全书,第一部分无疑是最为基础性的。其阐发的实体、属性和样态等概念为后面四个部分的论述奠定了基础。但是,其中一个看似再清楚不过的命题,却引发了后世长期的争论。在第一部分命题十五中,斯宾诺莎提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之内,没有神就不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东西被认识。”[1]这一命题看似解释了样态和实体之间的关系,即样态在实体之中(be in)。但是斯宾诺莎没有澄清的是,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在……之中”这一表达。换言之,实体和样态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由这一问题出发,后世的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以法国哲学家倍尔(Pierre Bayle)为代表的“寓于”(inherence) 模式,另一种是以柯莱(Edwin Curley)为代表的“因果”(causation)模式。两种思路在《伦理学》中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又不能完全地融贯于斯宾诺莎的体系。
首先来看“寓于”模式,其基本观点样态作为实体的某种性质是依附于实体的,从而样态离开实体无法存在。这种观点具有高度的笛卡尔甚至是亚里士多德色彩。当然,作为笛卡尔的继承者,这一理解方式似乎是合理的。在笛卡尔那里,实体的基本含义是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自存”,并且是各种属性和样态所依附的主体。亚里士多德也持类似观点。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似乎更强调其作为“存在之为存在”的被述谓(predication)的一面,即“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在主体当中”[2]的东西,比如一些具体的事物和存在者;而笛卡尔规定的实体则更侧重其存在或因果关系上的独立性。一方面,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将实体规定为“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3],即独立自存。另一方面,以实体为基础的存在论图景与因果序列等级相一致。即是说,绝对意义上的实体不需要任何他物作为其原因就可以独立存在,其自身就可以作为自身的原因,并且是被造物的终极因,即上帝;而思维实体和广延实体则需要上帝的加持、因果力的创造才能存在。但是相对于具体的事物和样态来说,二者也可被视为独立自存的。根据柯莱的观点,笛卡尔是实体由独立存在(亚氏)到因果关系中独立存在这一含义转变的过渡者。也就是说,由于其隐含的因果关系预设,笛卡尔已经开启了实体含义的转变,而斯宾诺莎则是这一转变的完成者。从哲学史的角度,尤其是从对笛卡尔的继承来看,这种解释体现了斯宾诺莎与传统哲学之间的连续性。但是,传统的“寓于”解释遮蔽了斯宾诺莎哲学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及其与传统哲学划清界限的决心。除此之外,倍尔的“寓于”性解释存在着比较多的困难,例如,在这种解释下,神会具有相反的性质、是可变的,需要为世界上的恶负责并且不能获得幸福,等等。
正是上述解释存在的困难和矛盾,柯莱认为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理解方式。首先,他认为,斯宾诺莎和亚氏的实体学说只具有表面的相似性,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的断裂。因此,为避免“寓于”模式所产生的错误,柯莱认为我们应当对斯宾诺莎的实体和样态采取全新的理解方式,根据样态对实体的“非对称的依赖性”而构建一种新的解释。在这种新的解释中,命题十五所提出的“在其中”(be in)不再意味着将样态视为内在于或寓于实体中,而是要以实体作为样态存在的原因。例如“样态A 是神的一个样态”或“样态A 在神之中”就意味着神是样态A 存在的原因,而样态则是无限的上帝通过因果法则创造的结果,这就是柯莱因果解释的基本思路。其次,柯莱的理解不仅在实体样态关系问题上与传统解释不同,而且在实体和属性的关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命题三和命题五出发,结合《伦理学》第一部分中的三处描述,即命题四证明部分:“在知性外……除了实体的属性和分殊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区别众多事物的异同。”[1](5)以及命题十九和命题二十绎理提到的,上帝及其属性都是永恒的、不变的。柯莱认为,属性所体现的正是实体的本质,并且二者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们发现斯宾诺莎以与定义实体相同的方式来定义属性”[4],构成神或实体本质的属性与实体其实是同一的,而样态则是最低等级的一些具体的思维或广延事物。换句话说,实体或神即属性,样态是神通过因果产生的结果。再次,在澄清了实体和属性间的同一关系后,我们还应考察柯莱那里实体或神的具体内涵。在这种三者等同的解释中,神的含义或内涵与传统解释也有着较大的区别。柯莱提到,“斯宾诺莎反对将神的概念理解为个人化的创造者(personal creator),而是将神视作万物提供最终解释的自然的法则。他将神与自然等同,不是考虑为事物的全体,而是理解为由事物展示出的秩序的最普遍的法则”[5]。将神或实体视为自然的法则,这一观点无疑是颠覆性的。柯莱本人也承认这一观点很难在《伦理学》第一部分中找到依据,但是在第三部分的序言中,他为这一观点找到了文本上的支持。在那里斯宾诺莎提到,“自然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自然的力量和作用,亦即万物按照它们取得存在,并从一些形态变化到另一些形态的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也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因此也应该运用同一的方法去理解一切事物的性质,这就是说,应该运用普遍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去理解一切事物的性质”[1](97)。这表明在斯宾诺莎那里,神不仅与自然等同,而且具体表现为支配自然的法则和秩序。总体来看,根据柯莱的解释,斯宾诺莎的实体不再表现为一个包含着所有属性和样态的“球体”,而是一个由无限因果法则支配的、层级分明的网状结构。
毫无疑问,全新的因果理解更加凸显了斯宾诺莎和亚里士多德在实体学说上的断裂。首先,亚氏所阐发的存在图景被斯宾诺莎完全颠覆了。同时,传统解释中作为偶性或性质的属性在斯宾诺莎这里则与最高的实体完全等同。因果解释一方面可以弥合传统解释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斯宾诺莎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改造,甚至是颠覆。但是,这种解释与斯宾诺莎的文本是完全融贯的吗?
二、因果解释的困难
第一,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二十九中,斯宾诺莎区分了“产生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和“被产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根据这种描述,柯莱认为,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神与自然并不是严格对应的,而只是对应包括实体和属性在其中的自然的主动部分,即产生自然的自然。对于自然的被动部分,即被产生的自然,则是以神作为其原因,而并不能等同于神,这是根据因果解释可以推出的合理结果。言下之意,神只是实体和属性,而样态并不是神,只是以神作为原因。这不仅与斯宾诺莎“神即自然”(Deus sive Natura)的表述直接矛盾,而且也不符合《伦理学》中提到的“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存在于神之内”“神之外没有其他事物”等观点。柯莱认为,这一结论正是来源于斯宾诺莎区分两种自然的段落。在那里,斯宾诺莎将产生自然的自然描述为“作为自由因的神”[1](30),这构成了柯莱做出上述判断的文本依据。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再来审察这段文本,就可能无法赞同柯莱做出的分析。斯宾诺莎的表述是,“主动的自然……换言之,就是指作为自由因的神而言”[1](30)。如果产生自然的自然只有在神作为自由因时才与其等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完全意义上的神与产生自然的自然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柯莱仅仅抓住了自然的一个方面,还缺少对于被动自然的分析。自然不仅有实体和属性的一面,还有着作为样态的一面。在命题二十九的证明部分,斯宾诺莎就样态必然来自神这一点做出了区分,“至于神的样式也是从神的本性必然而出,无论就神的本性被认作绝对的而言,或者就神的本性被认作表现为某种方式的分殊而言”[1](29)。绝对的神的本性是比较好理解的,在命题二十一中,斯宾诺莎将直接无限样态定义为“由神的属性的绝对本质而出”,就神是绝对的实体而言,直接无限样态乃是神创造的直接结果。它直接来自神的属性,属于神之下的“第二等”。但是,就神被认作表现为某种分殊而言,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有限样态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命题二十八集中地阐述了这一关系。在这个因果关系的网状结构中,每个样态存在和运动的原因是不能越级的,有限样态并不能像直接无限样态那样直接以神作为原因,而只能以另一个有限样态作为原因。因此,这里就需要神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作为原因的样态,也就是“就神的本性被认作表现为某种方式的分殊而言”。很明显,作为有限样态原因的“神”或自然并不是“产生自然的自然”,因为这时的“神”已经具象化为有限的样态,其存在和运动都是被决定的,应当被理解为“被产生的自然”。因此,即使在因果解释的框架下,斯宾诺莎的分析和柯莱的理解也是存在偏差的。神不仅是直接无限样态的直接原因,还需要具象化为有限样态去发挥因果性作用,决定其存在和运动,等等。一方面,柯莱将神单纯地定义为“产生自然的自然”与斯宾诺莎“神即自然”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矛盾;另一方面,这种等同并不能完全穷尽神既作为实体属性又作为样态的完整内涵。
第二,正是由于对神的片面理解,导致我们在因果解释下很难理清样态的含义和地位。在《伦理学》第一部分的界说三中,斯宾诺莎将样态定义如下:“样式,我理解为实体的分殊(affectiones),亦即在他物内(in alio est)通过他物而被认知的东西。”[1](1)在定义的前半部分,样态被直接定义为实体的分殊。一些国外学者如伯尼特(Jonathan Bennett)就曾指出,样态一词的拉丁原文(affection) 含义应理解为性质或状态,而并非由某些原因产生的结果,这就构成了对样态做出因果性理解的第一道障碍。另外,根据柯莱的分析,这一定义尤其是“通过他物而被认知”表明样态在因果关系上是依赖于其他事物,而无法独立自存的。但是,需要柯莱做出解释的是前一句话,即“在他物内(in alio est)”应该怎样与因果解释相融贯?仅仅根据斯宾诺莎的定义,我们很难从中分析出因果解释的色彩。并且在定义中并没有出现原因、结果、依赖等这样的词语。如果斯宾诺莎对样态真的做出因果性上的理解,那么在定义中这些相关词语的缺失无疑是十分奇怪的。
在定义五和命题十五中,斯宾诺莎将样态描述为在他物中和在上帝中,我们可以依照柯莱的思路对“在……之中”进行一些推理。根据因果解释,在……之中(be in)意味着以……作为原因(be caused by),我们可以得出,(1)对于所有的x 和所有的y 来说x 在y 之中,当且仅当y 是x 的原因。根据第一部分公理四(认识结果有赖于认识原因),我们可以推出,(2)对于x 和y 来说,y 是x 的原因,当且仅当x 通过y 而被构想和认识。再结合(1),最终推得,(3)对于x 和y来说,x 在y 之中,当且仅当x 通过y 被构想和认识。这是由柯莱的观点出发做出的合理的推论。但是这样的结论与斯宾诺莎的观点是有偏差的,只要稍加分析就能找出其反例。例如,作为有限样态的身体和外界的事物处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和互相作用中,认识我们的身体有赖于对其他物体或身体的认识,但是我们的身体并不处在其他物体和身体之中。
第三个可能的困难是对神的全知全能的威胁。在第二部分命题七的证明中,斯宾诺莎提出,“任何有原因的事物的观念,要依靠对于它原因的认识,而这一有原因的事物就是它的原因的结果。”[1](49)这样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对第一部分公理四(认识结果有赖于认识原因)的翻版。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说法涉及观念对于知识的替换。并且在其他几个地方,斯宾诺莎对观念和知识也做出了等同的使用。例如第二部分命题十九的证明部分,“人心就是人身的观念或知识,而这种观念或知识是在神内的……神具有人的身体的观念或人的身体的知识”[1](66),命题二十的证明部分,“况且人心这种观念或知识之存在于神内”[1](67),以及命题二十三的证明,“心灵的观念或知识是出自神并与神相关联,其情形正与身体的观念或知识相同。”[1](68)另外,根据斯宾诺莎关于思维的分析,所有我们的观念都是思维的样态。因此,根据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1)我们说具有关于某物的知识,其实就相当于具有关于某物的观念;(2)所有的观念都是思维的样态;以及(3)如果神具有关于某物的知识,那么神一定会有思维的样态。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如何理解神有样态?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传统观点会认为是观念或思维的样态寓于或内在于上帝之中,柯莱的观点会认为神是这些观念或样态的原因,在神那里并没有寓于其中的观念或知识,神所具有的功能只是引起或产生这些观念或知识。作为具体样态的观念或知识并不是神所具有的,而只是神的产物。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倍尔的思路更加符合哲学史上对斯宾诺莎的主流理解,即将属性和样态解释为寓于实体之中,“寓于”解释更多地展现了斯宾诺莎对哲学史传统的继承和接受,甚至将后者塑造成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我们同样看到,“寓于”思路与斯宾诺莎对神的定义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这种解释大大地抹杀了斯宾诺莎哲学理应具有的创新性。
因此,关于这一问题,柯莱的因果解释是极具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性不仅是对由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传统实体观的反叛,也意味着斯宾诺莎与传统形而上学图景的彻底决裂。一方面,必须承认的是,斯宾诺莎与亚里士多德仍存在着一些根本上的共识。例如,二者都认为有终极的或最高的存在,作为其他存在的根据或依托;并且,我们可以借助自身的认识能力达到对这一最高存在者的认识或把握[6]。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基于全新的因果理解,作为深受笛卡尔影响的笛卡尔主义者,斯宾诺莎肯定并继承了笛卡尔批评前者的努力方向。但是,他并没有继承前者主张的实体作为属性的基底的定义,并据此批评前者仍保留了较多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残余。同时,斯宾诺莎也没有接受笛卡尔形而上学中无限上帝实体—有限思维实体、有限广延实体—具体的样态的三分图景,而是将其创造性地理解为因果关系间的作用,并借此构造出一幅以因果关系和力量为基础的网状图景。但是,在处理与神的关系中,因果解释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例如对神的全知全能的威胁,样态和神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不难看出,一旦我们将神纳入问题中,“寓于”和“因果”都陷入了无法避免的困境。斯宾诺莎将神定义唯一实体的做法使得两种解释殊途同归。因此,一个合理的思路是两种解释模式的结合。事实上,一些国外的学者已经在做这种尝试。加勒特(Don Garrett)和洛卡(Michael Della Rocca)都表达过类似的思路,洛卡甚至明确认为我们应当接受一种双态的寓于—因果模式(Inherence-Causation Biconditional)[7]。当然,斯宾诺莎可能很难接受这种结合,但至少它是忠实于斯宾诺莎哲学的主要原则和轮廓的,也是解决这一疑难的一种思路。
在实体和样态之间,斯宾诺莎到底做出了怎样的设定?他的真实意图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上文提到的倍尔和柯莱的两种解释也只是基于文本进行的阐发和重构,我们也很难评估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斯宾诺莎本人的想法。这种情况不只体现在这一个问题上,每一位后世哲学家在对前人思想进行解释和建构时,都或多或少有些猜想的色彩在其中,并且很少有能与文本完全融贯没有矛盾的个例。但可以确定的是,经过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改造,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描绘的图景开始渐渐消退。随着哲学思考的不断推进,作为基底或基础的实体含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拒斥和否定。经由康德、尼采直到海德格尔批评和改造,实体概念淹没在各种批评之中濒临消失,时至今日,诸如实体这样传统的形而上学概念早就不是哲学讨论的中心话题。但是,不论是批评还是重构,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哲学思考仍然未脱离传统哲学的范围和影响。因此,反思和重释实体等概念仍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具有“形而上学冲动”的理性思维者的根本关切,对我们理解那些古老且永恒的哲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