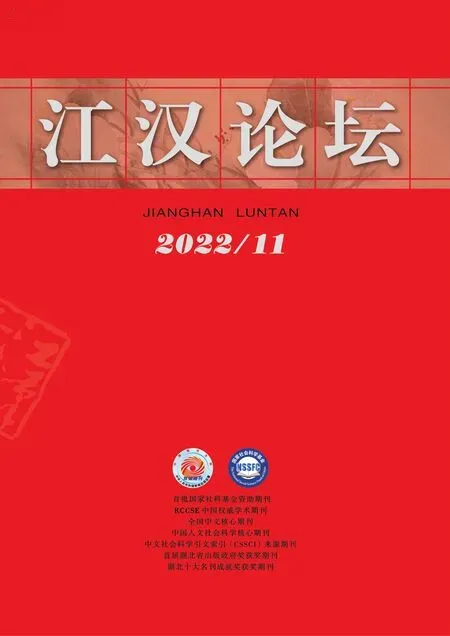操心的时间性:晋卦的存在论诠释
梅珍生
在存在论中,至少在海德格尔那里,对于存在的分析就是为了把此在的存在作为操心所具有的潜在的存在论意义揭示出来。而“意义意味着首要的筹划之何所向”①,从这何所向方面,某某事物作为它所是的东西在其可能性中得以把握。同样,在揭示此在是其所是的可能性方面,作为弥纶天地之道的大易,更能展现存在的本性。 《易》之为书,“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②六爻在六十四卦的不同场域中,“六位时成”正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时间性体现。本文拟以“此在的世界性奠基在时间性的时间化之上”③的视角,揭示晋卦的存在论意蕴,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日出于地:此在的时间性是定期的
晋卦开篇即提出此在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坤下离上。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④按照存在论的分析,“人的世界性以操心结构为基础,操心结构本身以时间化的时间性为基础”⑤。在这里,此在的时间性具有多重意蕴。“晋”的时间性首先表现为时间的定期。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使它的心须取得的时间定期;这一定期借助的是在世内照面的东西,……烦忙活动利用放送着光和热的太阳的‘上手存在’。太阳使在烦忙活动中得到解释的时间定期。从这一定期中生长出‘最自然的’时间尺度——日。而因为必须为自己获取时间的此在的时间性是有终的,所以它的日子也已是有数的。”⑥从卦的结构来说,离卦在上,坤卦在下,光明从地上发出。太阳从地面出来,升起后逐渐光明。卦名晋,有前进且光明盛大的含义。这说明晋卦既有时间定期的要素,同时,又具有此在的时间紧迫性的特征。此在日常的操心结构的时间性不仅仅是此在内在的感受,更具有公共性:“同样的生气、运行和下落并不只针对任何的个体或工具世界。”⑦在周易诠释学中,“晋”所反映的标识此在的时间性不仅仅是时间周期中黑暗与光明的交替,更代表着此在的绽出即是此在以时间性为奠基的存在。在传统的时间序列中,我们看到作为绽出的“晋”是以时间的延展为基础的,正如《程氏易传》所揭示的,晋卦的卦体为:“离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故为晋。进而光盛大之意也。凡物渐盛为进,故《彖》 曰:‘晋,进也。’”⑧“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所包含的时间性是以空间性的定位为奠基的,“日”由“地”而“升空”,时间的延展也由“晦”而“明”,此在的时间性结构表现为“进而光盛大”。在《周易正义》中,孔颖达认为:“‘晋’之为义,进长之名。此卦明臣之升进,故谓之‘晋’。‘康’者,美之名也。‘侯’谓升进之臣也。”⑨由此此在的时间性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绽出中呈现。晋,既可以是晋级加薪,也可以是人生际遇有新的跃迁。个体在与世界照面中发生重大向好的变化,再现了此在绽出的时间性。
从时间性解释此在的存在,既可以是绽出的“此在存在的意义”的时间性,也可能是使此在生存诸环节统一于“烦”的时间性。⑩《周易学说》引李士珍钅的说法,认为“晋,诸侯朝王象”,即是觐见、晋见之礼。觐见之臣是康侯;被觐见的主体是王,但“王”在卦辞中并没有出现。“锡马,侯享王之礼也。锡,犹锡贡锡纳之锡。享礼,匹马卓立,九马随之,故曰蕃庶。三接,王接侯之礼也。”⑪此在之“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意义,正是可以感受到在“王接侯之礼”中被重视,被世俗所倾慕,这种可领会性借助于“昼日三接”所含蕴的荣耀开展出此在生存论的意义。孔颖达认为,人臣遇明主,“非惟蒙赐蕃多,又被亲宠频数,一昼之间,三度接见也”。⑫反复被大人物亲宠,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此在绽出的时间性的标识。其实,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与时间性(Zeitlichkeit) 是有区别的。前者应用于自然科学,后者应用于历史科学。时间是单一同质而可度量的,时间性则否⑬。时间性带有领会的特征,此在存在的意义即是时间性,这也是存在论所强调的“我们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悟的境域”。⑭由此将存在论的时间概念与流俗对于时间的领悟区分开来。
《周易正义》认为:“‘晋,进也’者,以今释古,古之‘晋’字,即以进长为义,恐后世不晓,故以‘进’释之。”⑮也即是以现在的时间将已逝的时间连接起来,强调此在之“晋”在当前所具有的时间性。“进”的主体是谁呢?从“晋”字本身看,是“日”。年、月、日是标识时间的工具,但以日之“晋进”为基础。太阳作为此在最原始的时钟,它标识的时间必然是公共的、可度量的时间,也使得此在的筹划与时间性之间关联起来。所以,晋卦《彖传》的诠释从此在的时间性“明出地上”转移到此在的筹划,“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明、丽、大明,其实都是指“晋”字下的这个“日”。离上坤下,故言“明出地上”,就是具有大明特性的太阳跃出地面。人们对于太阳的思考必然指向时间,也即是此在所思考的时间内在地就是世界性的时间,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意义结构。“顺而丽乎大明”,既可以是对卦象的解说,“坤”,顺也;“离”,丽也;又在客观时间上揭示了太阳普照而大地一片光明的可预期性。此在因领悟而带有筹划性质的“柔进而上行”更具有主观的时间性意义。此在的“操心结构奠定了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生存的基础——奠定了它的总是已经在世界中存在的基础,在世界中,此在能够把存在者作为如其所是的存在者来遭遇”。⑯在“坤下离上”的生存场域中,人与人所构筑的意义是由此在的操心表现为对于六爻所构成的网络中的关系如何自处的操心。此在要能够如其所是地存在着,就要遵循社会日常时间的可定期性、时段性和公共性来生活的时间化要求,在“明出地上”之后,坤下与离上之间的关系就要遵循“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的为臣之道。“‘坤’,顺也;‘离’,丽也。又为明坤能顺从而丽著于大明,六五以柔而进,上行贵位,顺而著明臣之美道也。‘柔进而上行’,君上所与也,故得厚赐而被亲宠也。”⑰晋卦所昭示的此在生存法则明显由双重结构显示,一是坤与离的卦体关系以坤的顺从而依附于“离”为正途,一是以具体的六五爻与上九爻之间的“柔进而上行”为“美道”,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此在得以“是其所是”的上下秩序。处下位者不咄咄逼人地以下犯上,在上者自然嘉许这种“明臣之美道”。这样,君上厚赐明臣、亲宠明臣,正体现为此在绽出的时间性的意义。“锡马蕃庶”是对于此在过去行为的回响,“昼日三接”正是此在当下绽出的意义。在存在论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指同样重要的东西或维度,而是指绽出的模式——时间性的自我构成自我超越的模式:‘时间性的本质是在绽出的统一性当中发生的一个时间化过程’”。⑱因而,《彖传》衡定了“柔进而上行”在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中的意义,指出这是明臣得以“结君之宠”的原因。但此在若欲“自我超越”时间性的限制,就不可能是无原则的“顺”,顺必以正。以此结君上之欢心,就可以“昼日三接”,成为君上离不开的“康侯”。相反,此在当下若不以“柔进而上行”,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其未来必然会受到当下的制约,从而陷入“以柔进得宠”的反面,遭遇“讼受服”,更可能会“终朝三褫”⑲,被君上剥夺得一无所有。总之,对于此在来说,未来的意义以及过去还有无意义,都被此在当前所关心的事情所决定。⑳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㉑《象传》昭示了此在行为的德性特质。在存在论中,此在的行为更蕴涵着时间绽出的意义。“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此在’的行为拥有三重特征。首先是他称为‘调适’的东西:我们被抛入的情境自行显示出它或吸引人,或让人心生畏惧,或让人厌烦等等,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情绪来回应它。第二,‘此在’是言说的:就是说他生活在话语的世界当中,处在由我们与他人共享的语言和文化为我们言说和解释的实体当中。第三,‘此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领悟着’,就是说其行为指向(并非必然是有意识地) 某一目标,某种‘为了’将会使处于其文化语境当中的整体生命呈现出意义。‘此在’的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㉒“明出地上”,晋,恰恰是此在时间性的绽出,将时间的三重特征一并呈现。炽热的“大明”——太阳不会永久地为黑暗大地所淹没。君子要像“明出地上”一样,从困境中突围,发出光亮。“明”既是时间的开始,也是此在开始的时间性。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借《老子》的“自知者明”,将“自昭明德”诠释为此在“用明以自照为明德”㉓,“明德”自行显示出此在过去既成的德性,更具有当下与他人共同构建文化价值的能力,对于未来价值同样具有导向性。于是,王弼的《周易注》明明白白地将“君子以自昭明德”诠释为“以顺著明,自显之道”。㉔“自昭”是一种命令,“自显”是一种召唤,此在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因“君子以自昭明德”而统一为一个整体。此在作为人的任务就在于敢“自昭明德”、自显智慧,善用理智之光去照彻世界。
此在的时间性具有依存于此在的筹划性特征。“此在对存在者开放的基础就是它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性:对此在来说,把存在者揭示出来就是在当前表现出对它们的关注,这种关注着眼于此在已经开始的某项筹划,并被引向此在在未来的实际状况。”㉕“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㉖这里即有此在当下对于存在者的关注,毕竟此在的行为表现此在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奠基于操心之中。如果以觐见、晋见之礼来诠释晋之初六的爻辞,人作为操心的存在便跃然纸上。《周易正义》 引何氏云:“摧,退也。裕,宽也。如,辞也。”㉗“晋如、摧如”就是成语“进退自如”的语源。进退自如作为此在与世界的规则性关系,正反映了此在在筹划中适应世界的过程。在觐见之礼中,作为初六爻的此在行为,无非是康侯向天子进献礼物与之接欢的过程。“此在朝向一种具体的生存可能性筹划自己的能力要求它利用它当前的周围环境提供给它的资源来进行这种筹划。此在适应这种环境提供给它的机会和局限的能力本身就是它发现自己被抛入其中的情绪的一种产物。”㉘此在的筹划既可以是基于传统的指引,又可以是对自身限制的突破。此在遵守礼仪的周旋揖让,“晋如、摧如、贞吉”,但是,觐见的诸侯与天子的初次见面,即使明白无误地传递了顺从的信号,也不可能立即获得天子的信任,此在必然会处于“罔孚”的情绪中。突破“罔孚”的迷茫,此在利用周遭资源筹划,向朝觐的天子进献礼物(即“裕”,多衣多谷。) 此在在朝向未来的筹划中应该是可以结天子的欢心的,可以获致“无咎”的结果。
初六之位是指向未来的时间中的空间,它代表的是时间性关系的开始。王弼认为,初六爻无论是“处顺之初”,还是“处卦之始”,在这种有待深化的关系中,“故必‘裕’之,然后‘无咎’”㉙,它正揭示了此在的未来受制于当前的时间性约束。确实,在存在论中,“‘此在’就是操心(besorgen)。‘此在’不是‘我思’,而是‘我操心’:它不是一个思维的存在,而是一个会操心的东西。只有我有所操心,或者有利益所在,世界才愿意让我向它提出问题,并以知识—要求(knowledge—claims) 的形式为这些问题做答”。㉚既然此在的当下时间性是指向未来的,如果把晋卦初爻看作是此在以晋升、加官进爵而面对存在者,那此在的未来一定是超越周遭的。“晋如、摧如”,正是此在因操心而获致的回报,此在的势运来临,已然势不可挡,摧枯拉朽。但此在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从一开始,我们本身便是构成世界的因素,‘总是已在世界中存在’。我们是其他存在者中的一员,对之施加行为并与之产生反应”。㉛此在与其他存在者之间,重建了一个需要彼此校正的关系。作为此在的初六爻处在“罔孚”的不被信任状态,也就是孔颖达所疏解的,“‘罔孚’者,处卦之始,功业未著,未为人所信服”㉜,还得不到周围人的支持。此在的正确履职之道,是“裕,无咎”。此在对待周围人需要给予宽裕而不是严苛,也需要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以宽裕其德,使功业弘广,让他人信服,才可能站稳脚跟,此在以“裕”百姓的方式与世界照面,方能“无咎”。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㉝《象传》解释一个人的势运之可以到达“晋如摧如”之势,在于立身以正,修德不止,以德服人。孔颖达疏解“独犹专也,言进与退,专行其正也”。㉞在满是苟且的世界里,“独行正”必然会转化为此在德性所具有的澄明—明德。“‘裕无咎’,未受命也”,则是此在时刻准备着。“未受命”是指此在还处在“宽裕进德”的熟悉环境、摸清情况阶段,还没有行使君上所赋予的职权。这样,“‘此在’即‘能够是其所是的一种能力’,我的生活目标决定着我当下的处境与能力所具有的意义”。㉟按照程颐的看法,此在无论处在何种情况下,都有“行正道”的自主权利,这是他人无法剥夺的。“无进无抑,唯独行正道也。宽裕则无咎者,始欲进而未当位故也。君子之于进退,或迟或速,唯义所当,未尝不裕也。”㊱
二、久而必亨:在场的时间伸展到曾在和将来之中
此在被抛的筹划是一个向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的存在的生存模式。“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㊲六二爻的“晋如,愁如,贞吉”摹写了此在与世界照面时的心理。“晋如”,此在升级了、提拔了,固然是喜事,但也是愁事,忧喜相连,这是此在在世的常态。对于此在,海德格尔“所关心的操心结构的要素是:领会、现身情态、沉沦和话语”㊳,它们组成了一个可阐明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切领会都有其情绪。一切现身情态都是有所领会的。现身领会具有沉沦的性质。沉沦着而有情绪的领会就其可理解性而在言谈中勾连自己。”㊴此处与“晋如”相随的“愁如”正是此在操心的直观情绪。此在的领会之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愁此在的现身与周围人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新官“其德不昭”,王弼认为这会导致“进而无应”,独自凌乱于世内。二愁本领恐慌。面对全然陌生的新工作,新官不知道从何入手也是人生的常态。但是,知道自己不足的此在是有福的。“晋如,愁如”,说明此在是懂得反省的,尽管这表现为此在领会式的情绪,但其结果必然会比预期的好,“贞吉”是无疑的。王弼认为中位、正行、处晦修德,不改其志,即是“居中得位,履顺而正,不以无应而回其志,处晦能致其诚者也。修德以斯,闻乎幽昧,得正之吉也,故曰‘贞吉’”。㊵显然,王弼的诠释是以“中正”之德为此在对于未来时间性的预期的。“此在发现自己总是已经被抛入到情绪之中表明,它当前的生存是如何被它先前曾是的东西所决定并作为这种东西被决定。”㊶但是,此在在与世界照面的过程中,当前的时间性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基点,对于此在的整体性具有决定性作用。晋之六二爻辞提示的是“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就是此在当前时间在过往的基础上绽出自己。 《周易学说》引清人刘沅的诠释,认为王母是指六五爻。“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六二爻主要得益于六五爻的外援。所谓“离日象王,五亦王象。离中女,故象王母。凡二五以阴应阳,则象君臣。以阴应阴,故象王母。夫母子一气相亲,王母则亲而尊。二五柔中正同,一气相亲者也。王母之爱育其孙也,无异于子,而孙之亲王母也,尤甚于亲,然其尊益甚。以此明受介福之义,其意弥挚,而其荫弥远矣”。㊷“其荫弥远”正是过去时间性作用于此在当下的体现。此在的时间三维可以通过在场而一并呈现,毕竟“曾在也与我们有涉;它借它的不在场而在场。在场伸展到(reichen) 曾在和将来之中。将来伸达并供呈曾在,曾在伸展到将来,而‘两者的交互牵涉一齐伸达并供呈当前’”。㊸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是构成此在时间性的时间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回到此在本身。“在场与我们有涉,这叫作当前:与我们——人——相对着逗留。”㊹孔颖达揭示了作为此在的六二爻“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的时间性,他认为六二爻主要是靠自助,而非外援。“介者,大也。母者,处内而成德者也。初虽‘愁如’,但守正不改,终能受此大福于其所修。”㊺这种诠释就将时间内敛于此在的自我决断。当然,能获得“王母”的荫庇,与六二的反省、“愁如”与努力同样是分不开的。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孔颖达认为这是六二爻“履顺居于中正,不以无应而不修其德,正而获吉”。㊻时间性所揭示的此在“受福”的原因——秉持“中正”之道而自我超越。“受兹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㊼马其昶认为:“六二无应于上,守其中正之德,终能受福。此以诚自晋,达于鬼神者,其吉也,是积之久而自求多福也。”㊽“时间性不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系列从未来向当前再向过去不断流逝的自我充实的时刻,而且也不是某种东西的属性或特征,相反却类似于一种自我产生自我超越的过程。”㊾因而,“久而必亨”与积久多福,并非此在过去时间的叠加,而是此在绽出的时间性,也是“沉沦的此在把世内存在者领会为‘在时间中’来照面的”。㊿
“六三:众允,悔亡。”[51]日常此在在与世界照面时不是作为自己本身存在,此在消失在他人之中。但是,此在的自主性因“众允”而翻转为服从,“众允”便成为此在沉沦的某种变式。因为“我在本质上所是的东西,就是我自由地认定我所是的东西。这样一种选择的无根据性让人感到畏惧,于是我会逃避于不假思索的服从中”。[52]“虞翻曰:坤为众;允,信也。”[53]新晋之官处在六三之位,较之于初六不被周围人信任的“罔孚”,已是被众人信任的“众允”。不仅被信任,而且此在的希翼都能够得到众人支持。但爻辞中,为什么要强调“悔亡”呢?六三阴居阳位,力有所不逮,常情是动则有悔。所以,王弼认为“处非其位,悔也”。但是,能够做到“悔亡”,正在于六三的人生方向是“志在上行”[54],努力向上的。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此在应有的本真生存状态。“只要此在作为其所是的东西而存在,它就总是在抛掷状态中而且被卷入常人的非本真状态的旋涡中。可以藉此从现象上见出,实际性的这一被抛状态属于为存在本身而存在的此在。”[55]
在存在论中,海德格尔把“我”换成“此在”,并以与他人共在来对此在的本质加以规定。但是,此在先于他人和共在,无论此在如何沉沦于共在,此在“对他人来照面的情况的描述却又总是以自己的此在为准”[56]的。传统诠释学中,对于“《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的诠释,带有此在去蔽求明的特征。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曰:“居晋之时,众皆欲进,已应于上,志在上行,故能与众同信也。”[57]这“众允”正是天地人和的写照。离为大明,坤为地。六三正是天地相与之际,是此在“存在的疏明之地”,此在开放着,允许世内存在者和他人来照面。[58]《象传》这里的“志在上行”与初六的“独行正”的格局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是“与众同信”,大家都愿意一起“上行”,追求光明。“顺而丽明”正是卦象的特性,坤为顺,离为明,为太阳。丽,为附丽,“丽明”则为附丽于光明。此在的格局比彖辞中“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自然要更加开阔些,“晋”之此在展现的更可能是人生境界的跃迁。《周易学说》引“李士珍钅曰:三体坤顺之性。上与五同功而同德,下与初二同卦而同心,群阴允从,以晋于上,虽不中正,其悔亦亡。”[59]至此,此在一路通达,让存在者存在的那一此在把人向他自身解放出来,再现了“此在是存在的疏明之地”的存在论意蕴。此在“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操心结构的基础是时间性,那么此在对世界中的存在者的开放性——此在超越自己达到它所不是的存在者的能力——本身必定在本质上具有一种时间性基础”。[60]这时间性无疑是在筹划未来中绽出的。
三、晋如鼫鼠:此在的筹划总是指向未来的可能性
以存在论的视角来审视“九四:晋如鼫鼠,贞厉”[61],可以窥见此在无法摆脱“被在—世界—之中—存在所压制”[62]的命运。所以,在传统诠释学中,《周易学说》对九四爻象的分析,引刘沅的观点,认为“中爻艮,变爻亦艮,鼠象,昼伏夜动畏人者也。四窃位而居,上畏六五大君之明,下畏众人之逼,不能久安其位”。[63]这种基于此在之畏的分析,正恰当地揭示了此在操心的生存结构。“畏使此在认识到它已经被抛入世界之中——总是已经被引渡到对它非常重要而自己却不能完全选择或决定的选择和行动的处境中。它使此在遭遇到自己的世界性的生存是一个决定性的然而却是纯粹偶然性的事实。”[64]从爻象的象征意义看,晋之九四如鼫鼠,首鼠两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曰:“‘晋如鼫鼠’者,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虫也。九四履非其位,上承于五,下据三阴。上不许其承,下不许其据,以斯为进,无业可安,无据可守,事同鼫鼠,无所成功也。以斯为进,正之危也,故曰‘晋如鼫鼠,贞厉’也。”[65]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所意指的此在作为那种会操心的创造物,总是要受到生存条件的限制。人的生存是有条件性的,“这种有条件性从根本上讲就是自我的命运是被注定的”。[66]此在九四的命运既受制于世内照面的他人六五爻和其下三阴爻,更受制于“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的“此在这种向来我属性,在畏中都依赖自己如自己所是的样子显示自己”。[67]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68]九四何以“位不当”?此在和空间是何种关系?“此在由于其本身具有空间性,因此才能让世内存在者在空间中照面。而此在只要实际在世就必定给出空间。”[69]但是,此在的空间性源出于时间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世界、因缘、整体等都只有通过在时间性的地平线上才能得到理解。“时间性既然通过此在之此,通过此在的‘这里’到时,时间于是也就与此在所在的某个处所联系起来。”[70]如果说海德格尔的空间性源自时间还是颇为费解的,那么,《周易学说》引马其昶的诠释,则清晰地阐明了“此在特有的空间性也就必定奠基于时间性”[71]:“艮鼠居离坎之中。艮为止,离为日,止于昼也。坎为月,为行,为隐伏,潜行于夜也。小人贪进窃禄,鼫鼠之象斯为切矣!其厉也,是积之久而自成其厉也。”[72]离、坎的空间性正为日、月、昼、夜的时间性所确定。其实,按照马其昶的说法“艮鼠居离坎之中”,九四爻也可以是身处水火之中,就是此在身处水深火热的环境里。当然,因为“晋如鼫鼠”在与世界关系中多面操心,面面俱到,最终吃力不讨好,必然获致“贞厉”的结果。“时间在海德格尔对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分析中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表明”[73],此在的空间性从属于时间性。
“作为绽出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的生存必定建立在时间性的三重绽出过程的基础上。”[74]“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75],正包含着时间性的三重绽出。这里过去对于现在的决定性因素呈现为“悔亡。失得勿恤”,而“往,吉,无不利”,则构成此在朝向未来筹划的基础。孔颖达认为:六五是“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自用其明,以事委任于下,故得‘悔亡’。既以事任下,委物责成,失之与得,不须忧恤,故曰‘失得勿恤’也”。[76]六五的特性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尊位;二是处离之火的中心,三是阴虽为晋卦的尊位,但六五不自以为天下第一,能够做到不刚愎自用,主要依靠群众,将事情委任他人;同时,相信他人——无论办事的人把事情办得怎么样,都失得勿恤,无挂于怀。“失得勿恤”的失得,按照刘沅的观点,“离火无定形,倏起倏灭,故多以失得取象”。所以, 《周易学说》 引马其昶之言,认为“六五之悔亡,以其柔进上行而居中位。以是而往,吉无不利。得位失位,有应无应,皆不必计,故曰失得勿恤。”[77]此在“失得勿恤”的超越,不是着眼于当下,而是展开为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作为被抛的、沉沦的筹划,此在在总是要超出或不同于自己的实际状况和生活形式的意义上来说是超越的:它把自己和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联系起来——一旦此在把过去作为它现在所是的东西的决定因素据为己有,它当前的状态就成为朝向某种生存可能性筹划的基础。”[78]此在被抛在世无法选定自己所处的环境,但是作为被抛的此在的筹划总是指向未来的可能性,此在“领会的筹划本性——此在把它的生存可能性变成现实的能力——只有对朝向未来开放的存在者来说才是可能的”。[79]藉此,我们更可以理解李士珍钅的观点,六五爻在晋卦中的位置是“六五柔顺文明,贤侯之象。出奉天子,则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入治一国,则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无自私自利之见,一己之得失在所勿恤,惟不求利,是以无往不利”。[80]显然,“将来、曾在状态与当前这些境域格式的统一奠基在时间性的绽出统一性之中,整体时间性的境域规定着实际生存着的存在者本质上向何处展开”。[81]“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过,至于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则有蔽,尽天下之公,岂当复用私察也?”[82]此在与世内存在者的照面方式决定了此在的自由程度。“唯有此在当下揭示和开展什么,在何种方向上、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揭示和开展,才是此在自由之事,虽然仍始终在其被抛状态的限度之内。”[83]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84]在存在论中,此在的“生存是被抛的筹划——拥有某种领会,被情绪所控制;而且预先假定了操心结构的这些成分把时间性作为它们的可能性的条件”。[85]时间性从此在的情绪中绽出,传统的易学诠释更将这种情绪以生命的热度展现出来。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认为:此在即所谓“‘有庆’者,委任得人,非惟自得无忧,亦将人所庆说,故曰‘有庆’也”。[86]朱子的《周易本义》认为:真正乐于奉献社会的君子,就是那些“一切去其计功谋利之心”的人;那些以道自任的人,不介意人生的得失,他们恰恰可以收获“往吉无不利”的结果。
结语:存在本身就是澄明
“海德格尔的看法不是人必须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是人必须作为时间性而生存,人的生存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时间性。”[87]“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88]晋之上九的时间包含着公共性时间与绽出此在价值的内在时间两方面的含义。《周易正义》阐发了上九的时间性生存特征。孔颖达认为:“‘晋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处晋之极,过明之中,其犹日过于中,已在于角而犹进之,故曰‘进其角’也。”[89]从客观的世界时间来看,上九的时间标识为西南隅,日已过午;从此在主观的内在时间看,这是逐渐滑落的时间,此在的存在更具焦灼与操心的迫切感。毕竟“生存、实际性与沉沦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奠基于时间性当下完整到时的绽出统一性之中。”属于此在的时间性,“将来并不晚于曾在状态,而曾在状态并不早于当前。时间性作为曾在的当前化的将来到时”。[90]这样,此在最容易使自己在时间中绽出,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存在。此在越是快要在客观的时间中滑落,越希望绽出存在的焰火,满世界地推销自己的一孔之见。“在角犹进,过亢不已,不能端拱无为,使物自服,必须攻伐其邑,然后服之。”[91]“维用伐邑”不是因为作为照面的他人该被“攻伐”,而是为了问那自己掌控的“邑”中之人到底臣服与否?!至于“厉吉无咎贞吝”,则现身为此在的情绪在烦中奠定此在的整个展开状态。孔颖达认为:“兵者凶器,伐而服之,是危乃得吉,吉乃无咎,故曰‘厉吉无咎’。以此为正,亦以贱矣,故曰‘贞吝’也。”[92]当此在的情绪被厉、咎、吝的阴影所笼罩的时候,“才使得一切光亮照明成为可能,才使得一切知觉某事、‘看’某事与有某事成为可能”。[9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氏易传》就有限地肯定了此在的“维用伐邑”之举。“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谓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极则迁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则虽伤于厉,而吉且无咎也。严厉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94]
存在者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表明,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澄明的,不是由于其它存在者的澄照,而是:它本身就是澄明”。[95]“《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这说明在传统易学诠释中,恰恰借助的是他者的澄照,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认为:“‘道未光也’者,用伐乃服,虽得之,其道未光大也。”[96]此在作为“伐”的操心主体,对应的澄照对象是“邑”中之人,但以“伐”求“服”的过程,恰恰是存在未曾澄明的证明。程颐也认为“以正理言之,犹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则无不中正,安有过也?今以过刚,自治虽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97]程颐的诠释同样暗合了存在的澄明本性,并将此在的澄明与其咎吝得失联系在一起。尽管他是以“如果……如果……”的假言判断揭示此在的生存方式的。
总之,海德格尔的“三种时间绽出过程每一种都拥有一个‘视域图式’——一个此在被带到或拖往的‘目的地(whither)’。就未来而言,它就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就过去而言,它就是‘曾是的东西’;就当前而言,它就是‘何所用’”。[98]《晋》卦六爻揭示了此在三种时间绽出的途径。 《彖传》的“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以“柔”“顺”的方式,点明了此在时间性绽出的要旨。晋卦在肯定此在以“柔顺”与世内存在者照面的同时,强调此在的澄明本性。此在的时间性绽出必须以“明”为前提,即此在处下时,需要附着于“明”以求进;此在居上位时,则需要以“明”施治,六五尊居“离明”之中,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 《象传》称“君子以自昭明德”,正是此在以“自昭”而澄明。晋之此在的绽出必以澄明为前提,上九爻的“道未光”恰恰可能导致世内出现“君昏臣佞”、天下“明夷”(陷入黑暗) 的转换。因而,“人对世界的开放性取决于人对时间的开放性——取决于人作为时间性而生存,人的存在方式是绽出的时间化这个事实”。[99]
注释:
①⑥⑭㊴[55][56][71][81][83][90][93][95]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384、484、 23、398、 217、146、433、430、431、414、415、163 页。
②④⑨⑫⑮⑰⑲㉑㉓㉔㉖㉗㉙㉜㉝㉞㊲㊵㊺㊻[51][54][57][61][65][68][75][76][84][86][88][89][91][92][96] [魏] 王弼注、 [唐] 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15、151、151、151、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3、153、153、153、153、153、153、153、153、153、154、154、154、154、154、154、154、155、155、155、155 页。
③⑤⑦⑯⑱⑳㉕㉘㊳㊶㊾[60][62][64][66][67][73][74][78][79][85][87][98][99] [英]S·马尔霍尔:《海德格尔与〈存在与时间〉》,亓校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3、239、238—239、202、191、241、203、195、193、194、191、202、129、129、132、130、209、202、206、194、203、191、207、214 页。
⑧㊱㊼[82][94][97] 孙劲松等: 《周易程氏传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590、594、596、598、599、600页。
⑩⑬㊸㊹㊿[58][69][70]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版,第119、117、125、124、140、81、151、152 页。
⑪㊷㊽[53][59][63][72][77][80] 马振彪: 《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2、345、345、346、346、347、347、347—348、347 页。
㉒㉚㉛㉟[52] [英] 安东尼·肯尼: 《牛津西方哲学史》第4 卷,梁展译,吉林出版集团2016 年版,第96、95、95—96、95、9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