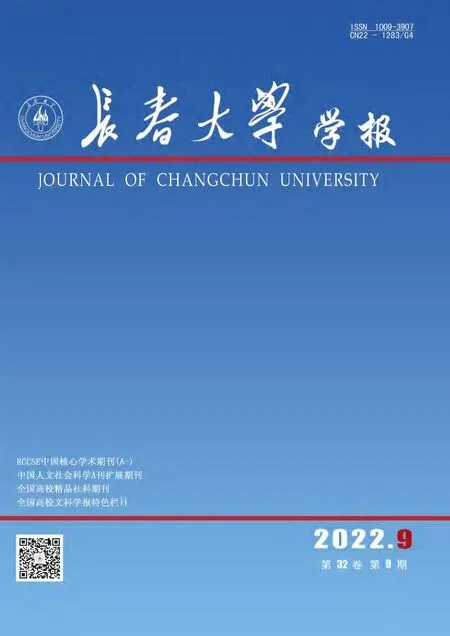论梁启超的欧西学理诗
宁夏江
(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0)
在清季诗坛,梁启超算不上大家,但他是个有创新精神和创作个性的诗人。然而学界太多注意的是他的“诗界革命”理论,他贯彻“诗界革命”理论的诗歌创作反而被忽略或忽视了。他沉痛指出诗界革命曾经走入的误区——“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1]374,认为“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1]376。为推动诗界革命派“举革命之实”,他创作了许多欧西学理诗——以西方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入诗,从思想内容(“精神”)上对诗歌进行革新,克服了维新派新学诗在字面上“挦扯新名词”的弊端。
一、梁启超诗歌思想内容的欧西学理特征
梁启超的诗歌中固然有抒怀、酬酢、品题、应景等旧体诗常见的内容(他晚年的诗歌这方面的内容尤多),但最有特色的是他所创作的欧西学理诗,即抒写西方政治历史、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思想学说的诗歌。这类诗歌题材的范围跳出了中国传统旧体诗的藩篱,同诗界革命派其他诗人作品中的“新意境”相比,具有明显的欧西文化的学理性特征,较少关注形而下层面的西方异域之景与风土人情,更多的是抒写形而上层面的西方社会科学、西方政治制度、西方历史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启蒙先行的新民思想
梁启超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国民道德缺陷和国民性衰弱的罪魁祸首,它使国人沦于奴隶的境地,养成了“奴性”的道德。他因此提出新民思想,通过打破传统旧思想的束缚,使民智大开,从根源上来医治国民被腐蚀的灵魂。他认为,一场政治(革命)运动先要有感奋人心的新思想作指导,先行者振臂一呼,民众广泛响应,才能取得成功:“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2]5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获实虽今日,播种良远繇……益信树人学,收效远且遒”[2]113,“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2]117。这样的革命运动当然需要卓越的领导者,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做思想启蒙工作,把民众培育成具有新型人格的国民,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谓是某英雄,只手回横流。岂识潜势力,乃在丘民丘。千里河出伏,奔海不能休”[2]113。他高度赞扬了美国独立运动中民众所体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寻思百廿年前事,穆穆神山不可望。拼死军前化猿鹤,岂闻闾左有蜩螗”[2]117。他希望通过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唤醒和激励国人向欧美和日本学习,“誓起民权移旧俗”[2]91,“欲向文殊叩法门”[2]63。
(二)舍身变革的志士思想
梁启超是维新派,但维新变法失败后,他的思想曾发生转变,甚至趋向于革命思潮。有论者认为,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便和孙中山来往日密,“渐有赞成革命的趋向”[3]119,甚至“与革命党携手,共图大事”[4],并鼓吹欲成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3]136。1902年,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月刊, “专叙俄罗斯民党之事实”的《东欧女豪杰》,“将民权大义发挥殆无余蕴”,时人谓:“读此不啻读一部《民约论》也。”[5]
梁启超许多诗篇赞颂了欧美和日本等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革命家,以及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如《去国行》歌颂了日本倒幕运动中僧月照、南洲翁、高山、蒲生、象山、松荫等仁人志士:“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2]14《奔勾山战场怀古》歌颂了北美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生命固所爱,不以易自由。国殇鬼亦雄,奴颜生逾羞。当其奋起时,磊落宁他求?公义之所在,赴之无夷犹”。他多次赞扬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思想启蒙在先,华盛顿、拿破仑等人革命在后,“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意大利的革命杰士玛志尼“变名怜玛志,亡邸想藤寅”[2]26。此外,他还颂扬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庾死兮”)[2]92、莎士比亚(“合与莎米为鲽鹣”)[2]92、哥仑布(“蛮长阁龙洲”)[2]27等哲人杰士。他极力抨击与志士精神相悖逆的奴性:“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6]421,“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6]5931。
(三)优胜劣汰的社会思想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引发了近代中国思想学术上极大的震撼,激发了有识之士强烈的危机意识。梁启超高度赞扬严复“远贩欧铅搀亚椠”[2]71,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中说:“因为物竞天择的公理,必要顺应著那时势的,才能够生存。”在《从军乐》中,梁启超描述了世纪之交世界诸国竞相并起,强盛弱衰的演变趋势,“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弱之肉,强食之,岁靡宁”[2]133。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他从生物界的进化谈起,“此虫他虫相阋天演界中复几劫,优胜劣败吾莫强。主宰造物役物物,庄严地土无尽藏”[2]42,再过渡到人类社会,指出人类文明发祥于四大文明古国,后由于“群族内力逾扩张”,地中海文明崛起,取代了四大文明古国;此后“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大西洋文明取代地中海文明而处于人类文明的领先地位。眼下世界格局是“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馀口无馀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西县古巴东菲岛,中有夏威八点烟微茫,太平洋变里湖水,遂取武库廉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容商量”[2]43。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和它们之间的战争就是弱肉强食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体现。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2]43,“弱肉宜强食,谁尤只自嗟”[2]247,从而唤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民族危机感。
(四)经世务实的学术思想
梁启超认识到学术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学术风气是紧密相关的。他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6]561他说:“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6]562近世史中华学术之所以相形见绌,主要是不讲经世务实之学,空疏务虚学风泛滥,他在《游日本京都岛津制作所,赠所主岛津源藏》赞扬中国上古学术“生饬化敛材用昌”,“百物效灵民乐康”,以经世务实为本,便于生民的生产与生活,国力也随之昌盛。然汉唐以后,学术渐染虚浮空谈之风,摈除艺事,空谈性理,“后不师古斫大横,学非所用汉汔唐。俞精俞虚竞南宋,及今风气空言张”。近代西方列强重器物之学,精研入微,“挟技百幻劖造物,一一铢寸基学堂”,国力日益强大,于是中西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我以拙胜与之遇,彼譬则车吾臂螳”。日本学习西方,重器物之学,国力日益强大,“当世若数善述巧,此邦无与抗颜行。日琢群楮乱真叶,尽羿之道孔穿杨。德成而上吾未知,形下惟器信所长”。最后,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封闭守旧是导致中国百工技艺落后的根本原因,“目力耳力今犹古,原绕原鲜固有常。力不出身货弃地,厥咎皆坐无纪纲。下伤新步后四国,上悲绝业坠百王”[2]199-200。
二、梁启超诗歌体制上的欧西特征
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非革其形式”,他的欧西学理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用旧的诗歌体式来表现近代西方历史文化、社会科学思想、自然科学理论,也就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旧瓶装新酒”,思想先进但在形式上“文体寄于古”。他诗集中标注甚明的“次原韵”“仍用前韵”“次韵”等诗歌,显示出梁启超在诗歌创作中对于传统诗歌格律声韵的严格遵守。但并不是说他对传统诗歌的旧形式、旧风格一味地继承。事实上,他主张对旧体诗在继承中求新变,对“旧风格”作适当的变通。他说:
彼西人之诗不一样,吾侪译其名词,则皆曰诗而已。若吾中国之骚、之乐、之词、之曲皆诗属也,而寻常不名曰诗,于是乎诗之技乃有所限。吾以为若取最狭义,则惟三百篇可谓之诗;若取其最广义,则凡词曲之类,皆应谓之诗。数诗才而至词曲,则古代之屈、宋,岂让荷马、但丁?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数家,若汤临川、孔东塘、蒋藏其人者,何尝不一诗累数万言也?其才又岂在摆伦、弥儿敦下邪?[7]
这段话精练地体现出他的主张:(1)借鉴西方诗学,以有韵作为诗歌最重要文体特征,“凡有韵的皆是”诗,诗歌不应局限于古体、律体和绝句,骚、乐府、词、曲、山歌、弹词等有韵之文,都应属于诗歌的大家庭;(2)借鉴西方诗学,诗歌的体式可以“不一样”;(3)借鉴西方诗学,“不受格律的束缚”,解放诗歌体制,诗句可以长短不一,反对传统诗歌格律严苛的限制;(4)借鉴西方诗学,扩大诗歌篇幅,可写出“数万言”“十几万字”长篇巨制。他把自己的诗学主张贯彻于诗歌创作之中,如《去国行》:
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州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2]14-15
这首诗抒写日本明治维新时,僧月照、西乡隆盛、高山正之等仁人志士为国图强奋起拼搏,不惧牺牲,最终使日本国“驾欧凌美气葱茏”,激励戊戌变法失败的维新志士,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像日本一样变法成功。诗歌没有固定的体式,也就没有受到格律限制。全诗以押韵句子组成,句子长短不一,自由灵活,颇有骚体赋和抒情散文的特色。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是作者有意创作的长篇歌行:
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水银钻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虫焉藏?尔来环球九万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强权强。惟余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肃肃天雨霜,鼾声如雷卧榻傍。诗灵罢歌鬼罢哭,问天不语徒苍苍。(节选)[2]43-44
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调写诗,尽力扩大诗歌容量,表达作者弱肉强食的忧患思想。诗体自由,没有固定体式,姑且以“歌”标其题;“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惟余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等不仅内容上是新语句,句式上也是新语句。
梁启超受近代西方军歌的影响。他认为,军歌可传唱全新的时代内容,以军歌来激发人心,达到启蒙新民的目的。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类似西方军歌的诗歌作品,如《爱国歌四章》《黄帝歌四章》《结业式四章》《从军乐十二章》,这些诗歌“格式属自创,几乎与整齐押韵的白话诗差不多”[8],“不屑拘拘绳尺间耳”[9]116。如《从军乐十二章》(选二):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况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其一)
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爷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平生,今日慰平生。(其二)[2]133
这些诗歌句式上松散自由,每句长短不一,韵律灵活多变,节奏明快,文字浅近,可以看作是白话诗的滥觞。诗歌沉郁雄壮,常常以一种重复叠唱的方式来增加情感,强化主题,给读者造成一种音韵上循环往复的视听感,起到教育国民的目的[10]78-79。
梁启超反对维新派新体诗一味“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他并不反对为表达需要而使用新名词、新语句。在他看来,诗歌要表达“新意境”,如果古典诗歌传统的语言库中找不到相应的语词来表达,就只能自造新语,甚至借用来自欧西、日本的外译词,突破古典诗歌语言表达上的桎梏。
梁启超对新语句、新名词的使用是很有节制的。他认为新语句必须服从于“新意境”,能少用则尽量少用,刻意使用必反受其害。他在比较黄遵宪与夏曾佑、谭嗣同的诗时曾说:“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6]1219他赞赏黄遵宪的诗歌“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用“新名词”不多;婉批夏曾佑、谭嗣同的诗歌滥用令人费解的新语句、新名词,“已不备诗家之资格”。
梁启超诗歌中所用的新词汇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一是国外人名,如拿破仑、华盛顿、伋顿曲、麦塞郞;二是国外地名,如波罗的、西伯利亚、火奴奴等;三是新事物名词,如轮船、铁路、电线,海电;四是自然科学名词,如以太、无机、微生等;五是与进化论相关的名词,如竞争存、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六是政治文化术语,如共和、政体、自由、平等、民权、文明等。前两类新词汇由于无法意译,只能音译,由其组合成的诗句稍有点生硬。后四类基本上以意译为主,运用于诗歌中很是得体和巧妙,意境与语句俱新。
三、梁启超诗歌欧西化的诗学史意义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列梁启超为“专造一应大小号炮”的地辅星,并评之曰:“新会(笔者注:指梁启超)向不能诗,惟尝与谭浏阳、黄公度鼓吹诗界革命,著为论说,颇足易一时观听。返国以来,从赵尧生、陈石遗问诗法,乃窥唐宋门径。游台一集,颇多可采。惟才气横厉,不屑拘拘绳尺间耳。”[9]116汪辟疆从传统诗论家的角度来评价梁启超的诗歌,着眼点还是1910年前后梁启超曾向赵尧生、陈石遗询问诗法而创作的旧体诗。从他旧体诗的成就来看,在诗人林立的清季诗坛排座次,梁启超确实只能属地辅星之位。然而如果从他所创作的欧西学理诗对清季诗坛产生的新变和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其诗歌具有一种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10]73。
“诗界革命”派从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喜摭拾西籍名词,入诸韵语”[9]43,到黄遵宪、康有为等人以西方异国风光、民俗人情、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新事物、新现象入诗,“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11]。梁启超认为“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6]1219有些“新体诗”虽“驱役(欧西)教典”,却掩盖不了“欧学皮与毛”的浅率(《广诗中八贤歌》)。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钱钟书评价黄遵宪就说他“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12]24。又说严复“号西学巨子”,他的诗除少数几首,“其他偶欲就旧解出新意者……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12]347。
梁启超强调“诗界革命”重在“革其精神”,他深刻地意识到“当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这样才能提高“诗界革命”的水平,才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欧西学理诗主要以“真精神,真思想”见长。他的诗歌在“新意境”方面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引“西学”入诗更多的不是从器物层面上,而是从“精神思想”上入手,即“用新理入诗”,达到“洞见政本”的目的。他的诗歌描写国外自然景物、名胜古迹以及新事物、新现象,比黄遵宪少,比康有为更少。即使是写欧西新事物、新现象,他也是概述几句后,马上转入感想和议论。如《游日本京都岛津制作所,赠所主岛津源藏》本来是可花大笔墨描写制作所器械的新奇精妙,但诗人只轻描淡写几句后马上转向对欧西之学务实而国强、中国之学务虚而国弱的思考。所以,梁启超的欧西学理诗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围绕欧西政治文化上下议论,阐述借鉴效法西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的诗歌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蕴蓄着他的学术思想,体现出“新版”学人之诗(1)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是指晚清以来受海外异质文化影响的一批“新式”学人创作的诗歌。严迪昌先生说他们的诗读起来“有种以‘新学’入诗,是学人诗新版本的感觉”。见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0页。的特征,归旨于救国强国之路的探寻[13]。
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初,新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诗人不仅摆脱了挦扯西典西物、琐碎务奇的诗风,而且诗歌创作的视野扩展到哲学、美学和文学等领域。如受梁启超《时务报》影响而放弃举业、趋向新学的王国维“以西方义理入诗”[12]347,“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12]24,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14]大道。其后,陈寅恪、马一浮,萧公权、胡先骕、吴宓、朱光潜等,“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笔者注:指梁启超)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15],“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16]。他们自觉“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17],“体现出对中西文化的历史、现状、未来的感性体悟与学理思考”[18],诗歌的“新意境”更加委婉深沉,“新版”学人之诗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