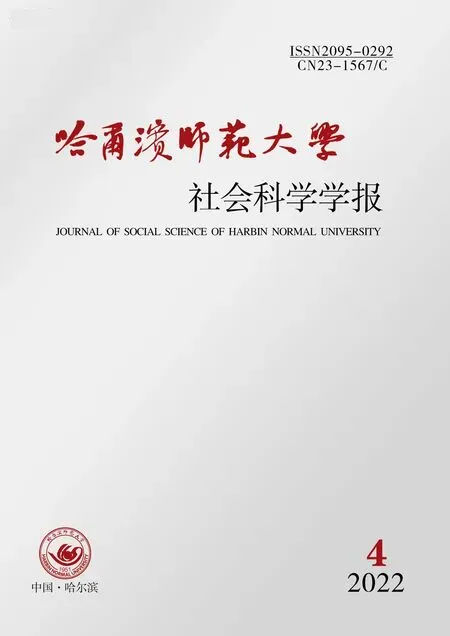荀子的“礼”是否有超时代性?
李成彬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荀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礼,但不全对,准确地说,应该是礼义。因为,礼与礼义之间是有差别的。清楚这一点,对于理解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关系,理解荀子思想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依《荀子》(1)本文所引《荀子》皆据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以下只引篇名。文本解读“礼义”是本文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荀子》中所说的“礼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荀子·王制》云: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
这里,荀子把礼义与天地并称。比照天地是万物之根本,礼义乃是人类之根本,并进一步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即,从个人而言,人是天生的,但从群体而言,人是礼生的。他在《天论》中还说: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
再度申明礼义于人之重要意义。总之,说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义。那么,什么是礼义呢?下面我们先说礼。荀子说:
“礼者,断长结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礼论》)
“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儒效》)
对此,梁启超解释说,“荀子有感于人类物质欲望之不能无限制也,于是应用孔门所谓礼者以立其度量分界”[1](P116),“荀子所谓度量分界(一)贵贱,(二)贫富,(三)长幼,(四)知愚,(五)能不能。以为人类身分境遇年龄材质上享用之差等,是谓‘各得其宜’,是谓义。将此义演为公认共循之制度,是谓礼。”“荀子言礼专主‘分’。”[1](P118)荀子说:
“人何以为人?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
既然礼就是度量分界,其功能就是分,那么义是什么?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对此,荀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則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
据此可知,义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其实质是“分”,所以荀子把礼义并称。(2)一种观点认为,荀子“礼义”并称的原因是礼与义的功用相同。详见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页。一般来说,荀子的礼义有三层含义:一是礼义(不是血缘出身)能够提高人的社会地位。他说: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於礼义,則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二是礼义能够使社会安定。他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义》)
三是礼义能够实现王者之政。他说: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
“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王霸》)
荀子的理想是实现王政,而实现王政就必须要实行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就是礼义。但是,荀子所生活的年代并无他所说的“义立而王”,有的只是“信立而霸”,对此,荀子顺应时代,予以接受。
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其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瓦解,周天子权威不断衰落,礼乐征伐则开始自诸侯出,而到了战国后期,封建制度开始确立,七雄争霸已近尾声,统一局面就要形成。此时的荀子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变革旧制度,缔造新社会。但是,他又不想与秦统治者所推崇的法家合流,而是希望以儒家思想来主导这一历史进程。这是有难度的。因为,就当时而言,法家思想因其应时性,符合当政者的需求。而儒家思想反映的则是春秋早期的历史要求,其历史条件大体说来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氏族血亲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开始瓦解,以地域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开始萌芽并不断发展,地域关系占主导地位;二是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中还具有强大力量。恩格斯说:“我们已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2](P461)同样,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生是有它的确定的前提和条件的。它的前提无疑是奴隶社会,它的条件应当说就是周王制下的分封诸侯国。奴隶社会是以氏族血亲为基础的。周公当年分封诸侯国的目的是为了拱卫周天子所居住的国都,而且,71个诸侯国中,53个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姬姓贵族。“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2](P200)这样,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基本上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阶级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其二是血缘关系已经降至次要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正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就是这样的,所以荀子的思想才以礼义为核心。
这样看来,荀子的礼反映了血亲关系;荀子的义则反映了阶级关系。前面说过,荀子的礼是“度量分界”,梁启超认为是荀子对于法家挑战的一种回应,所以说它是法也不为过,但准确地说,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荀子说: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
其实,荀子是用法的形式来表现礼,典型的新瓶装旧酒,而礼的实质没有改变,还是“道德之极”,属伦理范畴,仍以血缘为基础。但从结果看,礼则有双重属性,既是政治的,又是伦理的;前者与法家的法对应,后者与儒家的仁对应。荀子的礼、法关系与孔子的德、刑关系相似,但有区别。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孔子讲的礼着眼于个人修身,属伦理范畴,但荀子的礼则着眼于社会群体秩序,还有政治考量,这是荀子向法家的靠拢,同时又是对于儒家的坚持,是对仁的呼应。这种关系,在荀子的思想中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说: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处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大略》)
“礼以顺人心为本。”(《大略》)
这里,“礼、节也”,是说礼有法的标准之义。“制礼反本成末”、“礼以顺人心为本”表明礼的根本是“人心”,即仁。另外,“贵贵、尊尊、贤贤”,反映了当时存在的等级社会关系。“行义以礼,然后义也”是说义的价值只有通过礼的来实现。不仅如此,荀子还说: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子道》)
这段话能够证明,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确是阶级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因为,伦理(仁)低于政治(义),义则更近于道(人道,即仁与法的结合,是礼)。显然仁、义、礼就是一组正、反、合。即,荀子的礼要为政治服务,但其根本又在仁。所以,对于荀子的礼来说,地域的封建社会的兴起是其历史条件,而血缘的分封诸侯制是其前提。荀子之所以要礼义并称,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对传承的坚守,具体说来,是对法家崛起的抗争。从中不难看出,荀子所讲的礼义有时代性,在它的上面有阶级的烙印。但是,它们有没有超时代意义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本文认为有,理由如下:
实践证明,历史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超时代性,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没有时代性,历史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没有超时代性,历史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历史通过时代性不断地表现自己,又通过超时代性不断地扬弃自己,以新陈代谢的方式推向前进。但是如果在旧的当中,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则新一代势必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好比熊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最后剩下的还是一个,这样的历史是不会持续发展的。
由于忽略了这个道理,有很多人混淆了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他们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否定旧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封建思想),把新与旧看成是绝对对立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实,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在传统文化中,固然有封建的因素,但也有非封建的因素,它正是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统一。
下面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荀子思想为例来说明。荀子思想以礼义为核心,强调“从道不从君”。这可看作是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坚持。同样的意思,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由于荀子基本思想还是儒家传统,因此,其思想并没有在国家层面得以实施。如在《议兵》篇中,其思想没有受到秦、赵君主的采纳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并且在思想界,他也一样特立独行,这在《非十二子》、《正论》中都有体现。还有,听说李斯在秦国为相,荀子为此三日不食,更能反映其思想与当时政治环境之间的格格不入。这说明,荀子的礼义思想的根柢在氏族血亲的分封时代,不在以地域为界限的封建时代,所以才不被统治者所接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能因此就说礼义思想没有超时代意义。
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P30)据此可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劳动亦即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始终存在的;家庭亦即人类自身的生产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断言,荀子所讲的礼义,不仅有时代性,也应有超时代性。因为阶级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阶级是要消灭的。而作为两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则不能消灭,而是要长期存在的。
《礼记·礼运》说: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孟子·告子上》说:
“食色,性也。”
虽然我们并不能因这两句话而想当然地认为古人已经懂得两种生产的理论,但是,如果说他们的说法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一致或不相违背,还是可以的。总之,这是一种真理,即人总是要吃饭的,否则就要死;人还要生小孩,否则就会绝种;还要吃饭、劳动。而只要有家庭,有劳动,就会如恩格斯所说在不同的阶段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人们生活在这不同的社会制度中,遇到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除了措施、方法之外,有没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呢?应该是有的。大体上说有两种主张,且互相对立。有的主张利己,有的主张利他;有的重利,有的重义;所以,有争,也有让。其实,二者是对立的统一,绝对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是不对的。但在历史上,特别强调某一方的事实,却是存在的。例如,荀子思想,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崇尚礼义(群分),而西方就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好呢?应该说,各有所长。正确做法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而不非此即彼,互相对立。因为,中西两种文化,都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即以中国论,不仅在崇尚礼义这一点上,其它如文字、历法、建筑乃至音乐、绘画等等,都与西方不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正是有赖于此,才能在历史上保持领先。至于说,落后于西方,只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我们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勇于向对手学习。而不应该一味地否定祖先或者坚持与西方对抗。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经过长期发展才最后形成的。从各自的历史来看,都有过兴盛与衰落、顺境和曲折,都有长处和短处。因此,只根据一时的得失,就作出全称肯定或否定的判断,难免出错。
现在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荀子所讲的礼义。因其儒家身份,荀子并没有像韩非、李斯那样受到秦王的重视,在随后的秦帝国,甚至还发生了“坑儒”的事件,但是这并不能说荀子的礼义思想就完全没有适应时代的合理之处。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有超越时代之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说明。《大略》云: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親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處处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荀子的礼义思想,必须从仁说起,因为他是儒家,仁是其根本,即“亲亲”。然后是义,即“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理性判断,既可以仁来断,也可以法来断,前者是儒家,后者是法家。但两家其实都是礼、法结合。儒家主张大夫以上,用礼,以下用法;法家主张,君主一人用礼,其他皆用法。荀子则主张,士以上用礼,以下用法,显然扩大了礼的应用范围,缩小了法的范围,(3)由于时代的不同,孔丘所要复的“礼”与荀况所要隆的“礼”,基阶级内容是有区别的。孔丘所要复的“礼”是奴隶主阶级的“礼”;荀况所要隆的“礼”是地主阶级的“礼”。所以孔丘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荀况则主张“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在礼的适用范围上,荀况为了满足新兴的地主阶级的需要把它由大夫扩大到士,这是他与孔丘不同的地方;至于对众庶百姓必须以法与刑来统治,这又是他与孔丘相同的地方。见乔木青:《荀况“法后王”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第39页。但其实是公开承认了法治的价值。最后是礼,节也。说荀子的礼具有超时代性,就是因为它既是伦理规范也是政治法度;前者是对于儒家传统的坚持,后者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这样,荀子的礼就跨越了产生它的血亲时代,从而进入了地域政治时代,这当然是一种超时代性。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不离根本的超越。“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就是说,人要依照仁的等级标准来判断是非,内在的仁被外在化,礼也就获得了法的形式。这样的话,当人从家庭进入社会,必须从“仁”开始,处仁以义,以亲亲来行贵贵之事。仁是就个体而言,对于个体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的冲突问题,孔子想用自觉的恕道来解决。但荀子认为这样不行,就以来礼来解决,而礼是客观的标准,是圣人为群体制定的,是强制的,类似于法,但它的目的又是“和”。“行义以礼,然后义也”,义者宜也,按照礼来做,大家都能接受,这就是和而不同,所以荀子说,“制礼反本成末”。客观的礼最后又与主观的仁呼应,这是荀子礼义思想设计上最精妙之处。既体现了时代性,又体现了超时代性。其中的关键,是儒法两家的对立统一。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诸侯争霸的封建时代,它的出现,就是对儒家的否定。司马谈撰《论六家之要指》说: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法儒两家的思想主张是针锋相对的。而礼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梁启超说:“荀子生于战国末,时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为影响者不少,故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荀子曰:‘礼岂不至矣哉。产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礼者人道这极也。’法家之言曰:‘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不法度者不可诬以诈伪。’两文语意若合符节,不过其功用一归诸礼一归诸法而已。”[1](P120)梁启超认为,荀子生活的年代与法家兴起的时间相当,所以思想相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儒家传统来说,这确实是转变。对于这种转变的合理性,李泽厚给出了解释。他说:“战国末期,氏族政治经济制度早已彻底瓦解,地域性的后期奴隶制国家已经确立。因之,荀子在遵循孔门传统中,也就作了许多变通。例如孔孟只讲仁义,不大讲兵(打仗);荀子却大谈其兵,而议兵中又仍不离仁义……孔孟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政’;荀则大讲‘刑政’,并称‘礼’、‘法’,成为区别于孔孟的基本特色。便是这种特色又仍然从属于上述儒家轨道。”“荀子是新时代条件下的儒家,他不是法家,也不再是像孔孟那样的儒家。这种‘不像’,也正表现为荀学中的原始相比民主和人道遗风毕竟大削减,从而更为明白地呈展出它的阶级统治面目。”[4]相比之下,前儒与法家都有些极端之嫌,而荀子则有折衷的二元倾向。(4)“荀子所谓法,不具备上述法家所谓法的绝对法制意义, 而是相对于礼的次一级规范或法则《正论》:“圣王以为法, 士大夫以为道, 官人以为守, 百姓以为成俗。”按法与道、守、俗等并言,不过应为诸种规范或法则之一。因而荀子实有礼法二元论的倾向。”见葛志毅:《荀子学辨》,《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总之,荀子礼义思想的产生,是对儒家作出的改变,这种改变,体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荀子的主要思想是礼治主义,这证明他的立场基本上是儒家的立场;但是他又相当重视法治的作用,这又证明他的思想正是儒家向法家过渡的桥梁。荀子思想的这一转化,正是当时贵族旧政权向封建新政权转化的思想反映,荀子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和反动性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估价。”见李德永:《荀子的思想》,《文史哲》1957年第1期,第38页。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如果说,法家的法是对孔孟的礼的否定,那么,荀子的礼就是对法的否定,它们是一种正反合的关系。可以说,孔孟的礼反映了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情况,法家的法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以后的情况,而荀子的礼,既反映了与法家相同的时代,也反映了之后的情况,具体来说,就是秦帝国之后的情况。这是由它的超时代性所决定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超越时代也意味着与“主流思想”的背离,并遭受当权势力的打压。所以,超越也需要巨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哪里?宋洪兵的研究可供参考。他认为儒法之间在历史观上有共识也有分歧,而分歧的原因“并不在于知识层面或认知层面的“不知道”,而在于各自观察问题的视角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意识不同”。所以,他说:“儒家之所以在历史观念最终选择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姿态,并非他们‘不知道’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性,而是出于改变正义缺失这一政治现实而产生的正义追求的政治信仰,宁愿以高调的理想主义对现实政治形成正义批判,也‘不愿意’与现实政治‘同流合污’”[5]荀子的礼义思想超越了时代,因此,他必须在现实中承受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对于时人的误解和政治上的失意,选择了默认。只有作此层面的分析,才能真切地体会当他知道李斯为相后的复杂性情,才能知道他何以三日不食的原因。
荀子对于李斯命运的判断,也就是对法家思想社会功用的判断,而且,秦帝国的速亡,和汉家天下的长久,也说明他的预判是正确的。荀子为什么能够做到?前面曾提到恩格斯论断,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荀子的类思想与恩格斯的论断暗合。恩格斯的论断可以按照纵横两条线索来理解,纵的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属于时间的历史范畴;横的是维持生命的物质生产,属于空间的逻辑范畴,人类无法摆脱这两种生产的制约。荀子的思想中也有这样两条线索,“先祖者,类之始”,是指纵向的历史,“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是指横向的社生产。荀子的思想体系就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建立起来的。儒法两家分别对应这两种生产,仁强调的是人类自身,法强调的是社会管理,其实,这两种思想都是我们需要的。这样,就有了一个问题:孔孟的主张始终不得重用,而法家思想在秦帝国的实践又以速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各执一方,不能兼顾。而荀子的礼义思想则是二者兼得,是对儒学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儒、法、荀就是正反合。
正反合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我们理解人类历史与现实的有效手段。在人类历史中,在某一个时期,总会有一正一反两事物产生,产生的时间一般会大致相同(若以逻辑来推断,必然是完全相同)。起初,正反双方要进行斗争,结果是其中一方否定另一方,但是接下来又必然是双方的和解,历史的大势就在这一过程之中。举个例子,希腊罗马文化大约与犹太教同时产生,先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发达,后有中世纪基督教的昌盛,最后是双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在西欧文明中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