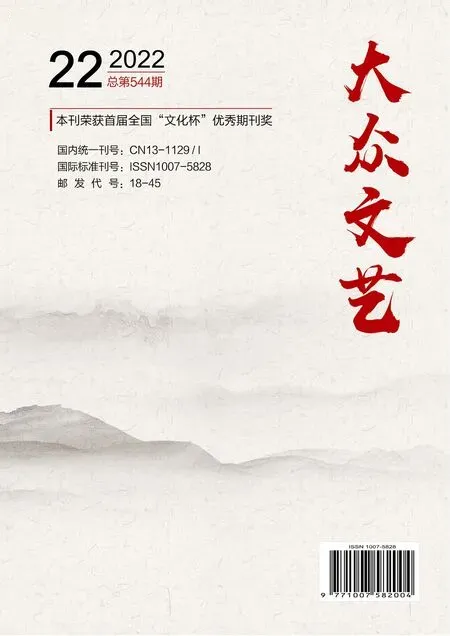论话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再现与表现
王婧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杭州 310053)
话剧是以演员的动作和对话为主干的戏剧形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中国。话剧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台对白展现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话剧人物造型主要指的是人物的外部形象,包含服装造型和化妆造型两部分。造型设计师根据文本中对人物的描述,利用各种造型手段将文本中描写的人物呈现于观众面前,即将一个二维的平面人物立体的外化。
再现与表现是艺术家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艺术语言中的“再现“与”表现“各自侧重的核心是客观的直呈和主观的情感表达。在写实主义的话剧中追求人物真实和形似的要求下,再现毋庸置疑人物造型是必须的设计手段,而具有“表现性”的话剧人物造型,则是在不同的话剧流派、多样的话剧题材和不同导演风格的背景下,创作者将自我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运用艺术手段表达出来。这两种艺术创作方法是在话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基本创作方法,两者各有侧重,相互依存。本文将通过理论阐述与作品例证分析,分别论述话剧人物造型的再现性与表现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再现性——从文本出发的典型形象
观众对人物的认识是从造型开始的,设计师必须给角色一个确定的外部形象[1],根据人物的身份、年龄、职业等信息,同时兼顾演员自身的特点进行外部形象设计。通过视觉传达出角色的外在信息和内在的性格、心境等精神状态,让观众在角色一出场就能就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进而随着剧情展开逐步深入其内心。尤其在现实主义的话剧中,设计师必须更加严谨的将文本中关于角色的信息再现于舞台。话剧人物造型的再现性主要体现在据史设计、性格化和典型性三方面。[1]
(一)据史设计
现实主义话剧的人物造型必须符合剧中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地域文化特点,服装样式、发型、装饰物件、妆容特点等多方面的细节都要能够再现戏剧环境中人物的真实感。同时,通过外部形象的塑造,还要能发映出角色当时的心境。特别是在一些表现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剧目中,人物的造型是必须是“像”的,除了衣着发型等必须完全吻合,面部的妆容造型也必须以“像”为标准贴近真实的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名人,更需要化妆师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拉近演员与塑造的角色的“形似”关系,这种情况下,化妆师塑造的人物就是高度还原再现的设计手法。
北京人艺版话剧《茶馆》第一幕,众茶客们长袍马褂、素衣短打,都拖着根大辫子,让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发生在清末京城的故事。王利发一出场是一袭蓝色袍子,带着瓜皮小帽,是当时民众典型的打扮,也是其意气风发的状态阶段,与50年后身着黑棉袄,步履蹒跚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人物身上的遭遇和心境的变化;同是北京人艺的话剧《日出》,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图景,不同阶层人群的穿着打扮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某大旅馆(惠中饭店)华丽的休息室里身着颜色极鲜艳极薄的晚礼服,烫着精致波浪发型,发际插着一朵红花的的交际花陈白露;三等妓院逼仄房间里的穿着酱红色棉袍套着绒坎肩,棉鞋棉裤,黑缎带扎住腿的廉价朴素装扮、却满脸涂着粉,一直晕染倒太阳穴的红紫胭脂的妓女翠喜构成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生活的对比画面。这些例子都是话剧再现真实人物造型的典型例子。
(二)性格化
话剧舞台上“再现”人物仅仅形似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外部形象的细节上看到人物鲜明的性格,性格化是现实主义话剧对人物造型基本的要求之一,只有贴上鲜明的的性格标签,才是真实生动的剧中人物。化妆师常常利用改变头型结构、五官比例、须发造型、装饰物件等方法从细节上塑造人物性格、将人物的性格外化。
人物的生理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物的性格。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就精准的表达出人物貌美心硬的性格特点;而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则将黛玉敏感多愁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不能以貌取人,但在舞台上,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则需要以貌取人。阿Q的八字眉和瘌痢头、葛朗台的尖细鹰钩鼻、虎妞的龅牙、张飞的络腮胡等,都是利用生理细节突出人物个性中最鲜明的部分。除了生理细节,人的心理现象细节、生活经历细节、风俗习惯和趣味爱好细节等都会影响观众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和判断。人的性格千差万别,他的生活经历、气质、修养、思想情感等都会以不同的程度反映在容貌上,造型师就是要敏锐的抓住其中的细节用于塑造鲜明性格的舞台形象。
(三)典型性
话剧人物造型的真实舞台再现都具有典型性。虽然侧重再现性的造型要求角色形象看起来真实和形似,但并非所有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的细节都要放在角色身上。人物的外部形象的视觉表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固定模式可套用,文本形象可以描述和比喻,舞台形象则必须直观的表现出人物。因此,就要求造型师必须在塑造人物的众多元素里筛选过滤出最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用在人物的外部形象塑造上,因而这个元素必须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大多数人理解中约定俗成的细节。热情奔放的女主角红色的长裙和波浪卷发、成功商人一丝不苟的背头和雪茄、知识分子的金丝边眼镜等等,都是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能够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关于角色的信息,进而进入剧情。
二、表现性——经过艺术加工的风格化形象
斐罗斯屈拉塔斯在他的著作《狄阿那的阿波洛尼阿斯的生平》中指出,文艺在摹仿之外,还有想象,想象是“用心来创造形象”。话剧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是由剧本创作、导演、表演、舞美、灯光、评论等共同构成的舞台艺术。一部话剧的执行决策者是导演,因此导演的决策结果直接影响了剧目最终成形的方方面面。同样的剧本,同样的演员,会因为导演风格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演出效果,人物造型的形式亦会受到导演选择和创造的影响和制约,成为表达主观审美情感的艺术“表现性”造型。
(一)艺术语言对客观对象的转化
艺术语言是审美形象的符号和载体。在话剧人物造型的创作中,角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创作者运用各类艺术语言,把构思形成的审美意象实现为舞台上的具有个人审美风格的角色形象。虽然艺术语言的使用是艺术家个人风格的集中体现,但其设计也必须是建立在对文本和角色的深刻理解和解读的基础上的,否则角色形象的舞台呈现将是不合逻辑的、没有支撑的。
2018年乌镇戏剧节首演的孟京辉导演版《茶馆》,是对经典进行解构主义、解读和充斥着各种后现代符号的全新版本,与前文提到的北京人艺版的《茶馆》大相径庭,在当时甚至引发舆论热潮。在这一版的《茶馆》里,通过对老舍的文本的改造和重述,叙事层面上的故事和情节已然消失。在这样的导演风格前提下,我们熟悉的原著中老北京市井茶馆文化中的人物形象自然翻天覆地。导演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给这部经典现实主义剧作披上了自己解读的艺术形式外衣。原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人”也被拆解为“常四爷代表头脑和脚、秦二爷是胃、王利发是心,他们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引自节目单)。所以我们看到的舞台上的一众人物本质上是一个个符号,是对人物重新解读和抽象后的结果,这部剧里的人物造型更注重对人物的精神层面的表现,在工业化巨轮的舞台设计背景下,人物黑白主色调下简洁的服装和几乎不加修饰的造型,正是对导演对人物艺术化的加工,渗透了艺术家的个人审美理想和情感表达。
(二)话剧人物造型的艺术表现手法
话剧人物造型创作主要的艺术表现方法有夸张、象征、隐喻等。艺术创作是对情感、生命和现实的某种探测、发现并进而表现的精神性活动,这个过程充分体现出创作者的性格、审美等个人化的影子。话剧人物造型的任务是将人物的年龄、身份等信息通过视觉传达的方式外化,而如何将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示于外在,是人物造型更深层次的创作内容,造型设计师一般通过运用符号、色彩、面具等手段对角色进行艺术性的表现,以达到展示人物的精神和心理世界,喻示人物的命运、表现人物的关系等作用。
2012年西安话剧院出品的布莱希特的经典剧作《四川好人》就中就运用了符号、色彩等喻示手法表现人物。剧中女主角一人分饰两角,白衣白裙的是单纯善良的沈黛,黑衣西装墨镜的是精明能干冷血无情的表哥隋达。这里的人物造型运用了典型符号的喻示方法,用以区别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身份,服装造型不仅区别的男女、职业、身份,更主要的是区别了人物的性格,黑白两色和服装样式的变化对比是最直观的将人物变换身份的信息传达给观众的方法,而更深层次的喻示则是正反同体、一人二身的“沈黛”与“隋达”所展现出的人性之复杂、矛盾与多变。而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出现的“众人”的造型,并不拘泥于特定的时代和样式,有人物甚至穿着中式民族花纹对襟服装却留着金色大波浪发型,服装的色彩更是高饱和度的红、绿、黄、蓝的搭配,让人眼花缭乱。导演似乎是想通过丰富抢眼的色彩来表现人性之复杂、对比出人内心的暗面,也是想衬托出沈黛与隋达无色彩的黑白造型,更为舞台营造出了几分荒诞与神话色彩。这部剧的人物造型创作充满了象征和喻示的意味,着力于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运用了夸张、象征、暗喻等艺术创作手法,凝结了创作者审美情趣,对角色的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就是具体呈现。
三、再现性与表现性的关系——相互呈现,辩证统一
艺术的表现性和再现性始终是相对存在的。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既有展示自己主观世界的本能,也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的各种因素对艺术创作的制约,因此,再现客观世界和表达主观情感变成为了艺术创作的动力。而再现与表现的关系绝不是对立和分割的,只是在哪些时候那种方式表现的更明显更清晰而已。在话剧人物造型设计中,再现与表现的关系也是相互呈现,辩证统一的。
首先,我们无法将话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再现性与表现性绝对化。虽然在通常情况,再现是再现现实与外部世界为主要特征的,表现是表现创作者情感为主要特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者之间是泾渭分明的。2016年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被认为是原汁原味西北风情舞台呈现的剧目,剧中的舞台美术及造型设计整体是写实风格,但仍然有巧妙的艺术表现处理。剧中人物的服装基本都是黯淡的灰黑色调,与整个舞台肃穆沧桑的氛围和冷色暗黑的灯光融合在一起,视觉上仿佛是一出黑白故事片。唯有田小娥穿着艳色色彩的人物,尤其在一群八卦,爱看杀头,爱看他人笑话的、身着统一黑底局部白色晕染服装的陕北农民组成的“歌队”的衬托下,形象更为突出;与之对应的是另一个“新女性”角色白灵,她的服装全程是白或粉色系,甚至在眼部妆容上都画上了相对较大面积的粉红色眼影,充满了象征意味。由此可见,即便是现实主义戏剧,对角色的外部形象的设计也绝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模仿历史现实,一定是经过艺术处理和加工的,不存在直接的、外在的、纯客观的客体。艺术形态不同于生活形态,舞台艺术的真实不等同于自然形态的真实。
其次,创作者所感知的情感并非完全抽象的情感,是他们过去审美经验的综合体[2],是无法脱离物质和社会的,没有所谓纯粹的表现个人感情的创作。话剧艺术表现的对象首先是文本和叙事,舞台上众多的角色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对话是推动剧情发展的手段,交代和呈现角色的各种信息并将其外化,是话剧人物造型的主要功能。这这个过程中,创作者可能有自己主观对人物的理解,运用各种手段和技法进行艺术加工,但仍然脱离不了对角色信息视觉传达的主旨。罗伯特.威尔逊被誉为是后现代艺术家,他戏剧作品中的人物造型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华丽怪诞,过目难忘。威尔逊给他剧中出现的动物形象赋予拟人化的造型方法,让每个动物的舞台形象都是有思想性格的独立个体,既有深度又有趣味性。如《郑和1433》中东方剪纸风格的忧郁猴子、《拉封丹寓言》中穿着西装绅士般的各种动物,造型固然是夸张神秘令人称奇的,但观众首先接受到的是通过动物面具传达给观众的身份信息——兔子、狐狸或者狼。由此可见,创作者所面对的对象既可以是主观情感,也可以是某种事物或事件,还可以是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体,所谓单纯的主观情感表达并不存在。不同的话剧剧目,再现与表现的人物造型设计的只是有所侧重,本质上还是辩证统一的。
结语
话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创作核心在于艺术性的将文本中的人物外化,将文字描述中的人物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真实的展现与观众面前。这个创作过程会受到文本和题材的限定、导演风格的制约,也要服从于整部剧的美术风格,但人物造型的创作依然是一项独特的艺术创作活动,它的创作围绕着对角色外部形象的塑造展开。角色作为话剧舞台上一个动态的符号最先进入观众视野,既是存在于舞台空间中整体的一部分,又是独立的个体,造型师使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会塑造出了不同风格的人物形象——可以是侧重真实再现历史环境中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是侧重表现创作者的审美和情感的风格化人物形象。但话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再现性与表现性绝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密不可分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教导画家和雕刻家,艺术家应该准确地观察“感情支配人体动态”的方式,从而表现出“心灵的活动”。[3]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为艺术的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话剧人物造型创作的再现性与表现性的关系亦是如此。再现与表现这两种创作手法相互作用、交替呈现,推动了话剧人物造型艺术创作的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