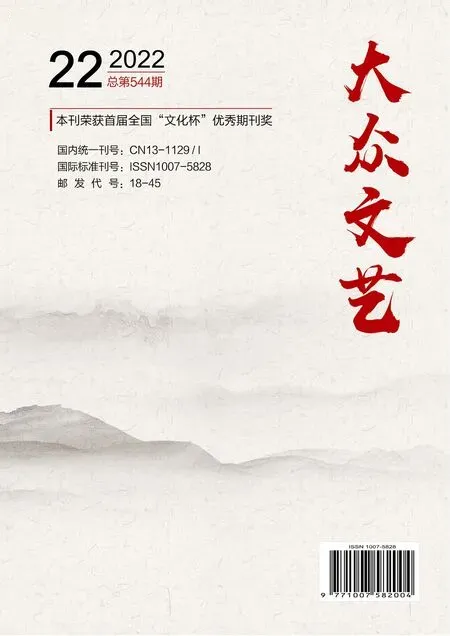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特征探析*
——以文牧野导演电影为例
葛胜男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800)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增长与日渐成熟,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在社会中的经济、文化、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于是电影自然地承担起对内凝聚民族精神、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社会责任,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华形象”就成为中国电影义不容辞的使命。“百年中国电影就是现代社会现实的影像折射天地,再现生活、表现现实、揭示人间苦难,描绘当下社会情状,成为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任务。”[1]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是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发展至今一以贯之的创作传统。中国电影开拓者——郑正秋在他的故事片《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影片中大力抨击以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性、传统道德的,大胆揭露社会问题,体现出极强的进步性和现代性;左翼电影之父夏衍拍摄的《狂流》,以豪绅和农民在长江流域大水灾中的不同表现来体现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创作者对于现实主义美学标准的孜孜以求流露于电影的主题题材和影像风格之中;建国之后社会主义电影的奠基者桑弧、谢铁骊、谢晋,他们的作品《祝福》《早春二月》《天云山传奇》等作品触及暴露旧中国和社会现实问题,表现中国人民自我批评的胸怀和勇气;改革开放以后伊明和陈凯歌执导的《城南旧事》《黄土地》,他们忠实地在银幕上再现客观世界,强烈地表现创作者对时代和命运的关注,展现中华民族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力量;新世纪以后还有王小帅、贾樟柯、娄烨……以“离经叛道”的电影之笔书写着着他们眼中的现实中国。
时下世界疫情未平、战争又起、经济衰退、大环境内卷等客观原因给人们带来诸多生存困境。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两部电影,以开拓性的社会现实题材为取向,塑造了两个面对困难永不放弃、不断完成救赎与自我救赎的草根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叙事为精神困顿的群众带来一缕阳光,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房。这些年除了温暖现实主义电影之外,网络上颇受欢迎的奇幻、科幻类型的影片其实也有着相近的社会机制。观众通过电影这扇“世界之窗”和“生活之镜”[2]和角色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因此,有情感、有温度、有现实穿透力的影像呈现不仅电影行业主管部门对创作者的要求,更是市场的现实需求与和观众的精神诉求。
一、温暖现实主义电影
现实本是客观的,很难说它有温度。但如何表现现实,由于创作者主体意识的介入,会赋予作品感情与温度。一直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争论不休,学者们在现实主义一词的前面加上不同的定语以明确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例如钟惦棐先生主张的“严格的现实主义”、丁亚平研究员提出的“感觉现实主义”、李道新教授提出的“参与式现实主义”,还有研究者提出过“建设性的现实主义”等等,不一而足。2011年,学者饶曙光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在“充分肯定个人奋斗、个人利益追求正当合理的同时,更应倡导一种超越自我的‘他者关怀’”[3]。今年3月,北京电影学院胡智锋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再次提出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胡智锋认为,“温暖现实主义就是‘在关注平民叙事、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求’”[4]。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从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两个层面来概括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范畴。就创作原则而言,它要求创作主体必须关注现实困顿和人性困惑,揭示社会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问题,含蓄或直接地表达创作者对所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批判,并且提出一个积极的、向上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就创作方法而论,温暖现实主义要求创作主体要尽量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但不能完全展示生活的阴暗面,通过运用观众更易于接受的视听语言将生活中的美呈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寓教于乐”。
二、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
(一)电影中的“作者性”表达
作者电影理论最早发端于1948年的法国,一篇名为《摄影机—自来水笔,新先锋派的诞生》的文章指出,“正如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电影导演用摄影机进行‘写作’”。随后,年轻的法国影评人弗朗索瓦·特吕弗在他的文章《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首次提出“作者电影”和“电影作者”的概念,后经电影评论家们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作者电影”逐渐演化为泛指带有明显导演个人创作特征的电影。众所周知,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产品,天然地带有作者属性。中国历代导演中,不乏“作者电影”的开拓者和继承者。以第六代导演为例,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所执导许多电影都带有很强的作者气质,如《三峡好人》《春风沉醉的晚上》《十七岁的单车》,这些作品所呈现的不确定的叙事策略、诗意的纪实美学、灰冷的电影色调、深刻的生命反思等美学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中重要一维。新生代导演文牧野则批判地继承了电影学院前辈们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电影中保留了对社会现实题材的取向,同时加入了他个人对待生活的诚意、表达现实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智慧,呈现出不一样的现实主义电影美学风貌。在取材上,文牧野将镜头对准社会边缘人物——卖“神油”的程勇和修手机的“景浩”,当然还有大量作为故事“背景”出现的社会底层群众,如买不起药的癌症病人、单亲妈妈、下岗职工、网瘾青年、养老院看护等等……文牧野通过大胆虚构和艺术创造,给观众描绘了一幅稍具设计感的底层群像图。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聚焦边缘人物、呈现社会的冰冷和人性丑陋、追求纪实美学风格的美学主张,勾勒出一幅独具特色的“作者电影”景观。文牧野导演结合当下时代需求,摒弃了前人阴鸷的、消极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用温暖的、积极的、向上的精神态度去塑造人物、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作为两部现实主义电影作品,体现出不同寻常的现代性与进步性。主人公程勇通过个人的努力与牺牲,为白血病患者争取到了永久的福音,推动了国内医保改革和社会变革。导演在影片中融入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索,他在尝试积极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创作者的艺术良知和现实主义电影的力量。《奇迹·笨小孩》中有一座手机堆成的“山”,整部影片讲述的就是当代社会“愚公移山”的故事:一个叫做景浩的年轻人带领他的“奇迹小队”一路风雨兼程,最终追求到人生幸福。这两部电影选取了芸芸众生中的两个小人物作为横切面,为观众展现了他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所传达出的达观向上的态度,以平凡人物为梦想奋斗的故事与银幕外的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两位主人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对幸福的“个人之争”构成了文牧野电影的个性化表达,透露着浓烈的“作者电影”气息。
(二)家庭叙事构建情感认同
《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思想,《孟子·尽心上》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修养准则,梁晓声先生说:“情感和责任是中国人刻在基因中难以抹去的。”可以看出,“家国天下”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家庭给了大部分中国人全部的爱与力量。“家”是中国人的“生命之源”,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元素。因此,中国人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特征集中体现在电影当中对于家庭元素的表达。在文牧野的两部电影当中,无论是血缘家庭还是社会家庭,故事的开始主人公总是陷入家庭困境,如何化解困境、解决危机构成了文牧野电影统一的叙事主题。《奇迹·笨小孩》中讲述了一个20岁的穷困青年,母亲去世,父亲抛妻弃子,独自抚养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妹妹。然而他不向命运低头,通过自己的坚持与努力,坚强地支撑起了一个蒸蒸日上,充满希望的“小家”。《我不是药神》中几乎每一个人物角色都在努力维护家庭的平衡。主人公程勇面对婚姻失败、照顾老父儿子分离,思慧与白血病女儿相依为命,只能在夜总会跳舞为女儿筹钱买药……保护家庭和家人成为了片中角色的共同情感推动力。作为电影叙事的深层情感逻辑,《我不是药神》还突破小家的概念,扩充了“家”的内涵。主人公程勇在最终落难之际得到了白血病友群体的爱与支持,给予他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近些年一些导演乐于使用家庭叙事策略创作电影,如尹力导演的《没有过不去的年》、薛晓路导演的《穿过寒冬拥抱你》、刘江江导演的《人生大事》等,都是把普通人所遭遇的困境放回家庭中解决,家庭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血缘,是导演用于表达温暖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叙事中不变的主题与归宿。
(三)镜头语言构筑温暖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文牧野的两部电影《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从镜头剪辑、影像风格、美术呈现上来看,与很多其他现实主义电影对生活场景的刻画所呈现出来的矫揉造作和虚空悬浮形成了美学上的鲜明分界。影片中的许多场景、细节都来自于导演对现实的观察,镜头、场面、美术、音乐都准确克制,演员对于人物的刻画也都富有魅力。从这层意义来说,它们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确定了一种美学风格。我们在影片当中可以捕捉到很多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典型元素:手持肩扛的镜头,昏黄的灯光、和低饱和的画面,这些手段的运用都为是为了营造现实的粗砺感。以《我不是药神》中的美术造型为例,摄影师和美术指导淼最初讨论了一套四幕的色彩分配法则,分别为黄、橙、蓝、白。色彩根据剧情的起承转合由浓烈转向冷峻又逐渐趋于清淡。影片开始以橙色、黄色为主色调,整部电影的调性比较温暖;影片的后半部分温暖的颜色逐渐抽离,冷峻的蓝色绿色逐渐凸显,表现现实的残酷和作者的冷静思考。色彩作为一种符号,让这个关于现实题材的故事充满了表意的张力,产生巨大的艺术冲击力。
《奇迹·笨小孩》在冷峻的内核之外为影片穿上了一层温暖的“外衣”。摄影师王博学使用了两款镜头来区分不同的故事线,一款偏锐利的镜头,拍主人公景浩的创业线;另一款偏柔和的镜头,拍景浩和妹妹的感情线。《奇迹·笨小孩》在表现景浩奋斗时,通过冷色调、大景别来表现正在发展的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庞大的力量感。片中多次出现俯瞰、航拍的大全景,上帝般的鸟瞰视角呈现了这座城市无法掌控的力量感、压迫感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当镜头俯瞰整个城市时,七巧板一样的城中村即刻产生“降维”效果,被压缩在地面上,与航拍视角中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形成繁华与没落、财富与贫穷的巨大对比。在美术造型方面,《奇迹·笨小孩》采用很强烈的色彩搭配来营造生机勃勃的生活现实感。例如:景浩和他的“奇迹小队”在通透的蓝绿色窗前夜以继日忙忙碌碌,人才市场里纷飞的红色、黄色、粉色广告纸和务工者五颜六色的服装交相辉映,养老院护工梁永诚工作时身上永远套着一件温暖的粉红色围裙,身着明黄色广告衫的景浩就像一道光穿梭在冷漠的城市丛林中......这些温暖明亮的视觉形象渲染了整部电影的叙事基调,迎合了观众心理期待,也表达了生活中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在沉郁的现实主义底色上,用明亮的色彩带领观众跳脱“悲剧”的情绪,点燃观众内心的希望,这也是以文牧野为代表的导演能把小众电影大众化的秘密。
三、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反思
随着世界电影市场和以高清技术、智能化、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电影技术的发展,中国电影确实面临着差异文化、利益诱导、舆论导向、意识形态管控等诸多文化因素影响,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中国电影创作者是否能够坚守本心,坚持电影艺术的进步性,始终不向客观社会因素屈服以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不论在任何时代,电影创作者都要自觉承担起文化责任担当——弘扬真善美,表达人间之爱。
《奇迹·笨小孩》表达了“爱拼才会赢”的人生哲学,传递了底层人民相互扶持的温暖火光,但故事结尾稍显牵强。它让所有人都成了“成功人士”,与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体现不相符,叙事逻辑与现实逻辑稍显违背。温暖现实主义的“温暖”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一旦陷入空想、虚浮、主观,就会变得“廉价”,就与艺术创作规律相违背,误入“悬空现实主义”“虚假现实主义”歧途。如文牧野所言,“我在电影中会表达失望,但不会绝望”,艺术创作可以煽情,但不能矫情。这需要电影创作者具有足够诚意、勇气和智慧去思考中国当代现实问题,寻找建设性的解决路径,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我不是药神》勇敢地触及了中国“看病贵、看病难”的现实问题,体现了中国年轻一代电影人责任担当。有医学专家对这部电影给予积极评价,“真心地希望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能够以《我不是药神》作为反思的起点,以老百姓的真实诉求为出发点,让广播电视的平台再干净一些,再安静一些。”[5]希望《我不是药神》是一道灯塔,照耀中国电影推动社会变革之路。
结语
当下世界环境复杂,关注社会底层、观众社会公平的思潮弥漫于全球电影界,为现实主义电影营造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一方面,观众不再热衷于“大”电影而回归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另一方面,观众审美的提高与细化,为真正可以生产出“经典”电影的导演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土壤。文牧野回应公众对社会公正性的焦虑和关切,接连创作出两部打动观众内心和顺应时代呼吸的电影作品。电影以其“作者性”表达、温暖的镜头语言、家庭叙事策略确立的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特征,为现实主义电影提供了一种美学范式和创作路径。但温暖现实主义并不是当下电影唯一的创作主张和理念方式,中国电影事业需要更多人去探索更多的创作维度,生产出更多元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如何让中国电影承载对社会问题既有原则又有高度的批判,需要长久的智慧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