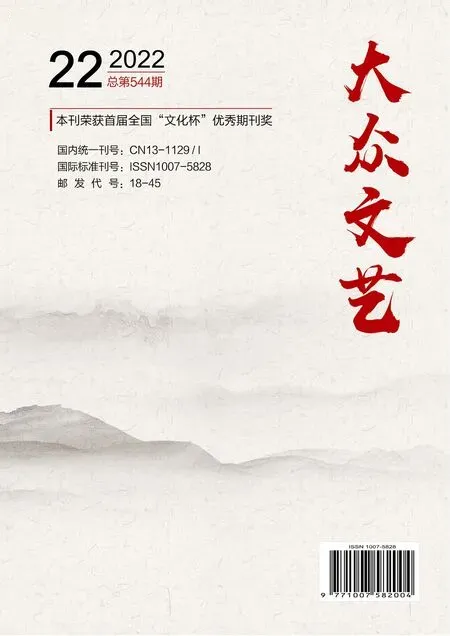纪录片《二十二》中的文化创伤教育书写
刘莹莹
(广东警官学院,广东广州 510440)
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名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在中国则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战后,“慰安妇”问题却逐渐被人们淡忘。直至20世纪90 年代初,才逐渐为公众所知。[1]
文化创伤理论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2],“慰安妇”史实之于“慰安妇”,之于中国,正是一种建构中的文化创伤。在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对待幸存的“慰安妇”,不仅关乎历史的真相,更是关乎人类生而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价值问题。而“文化创伤教育是一种以创伤事件为载体而开展的,以培养受教育者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责任感为目的的,集叙事、体验、反思为一体的,兼有生成性与过程性的教育活动。”[3]
2017年8月,郭柯导演的以“慰安妇”幸存者为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在内地上映。《二十二》以严肃态度面对历史,以深情凝视事件受害者,以镜头将历史事件转述为审美对象,记录历史与当下,并尝试实现由历史通往现实的创伤修复,从而赢得了公众的尊重与好评。本文试在文化创伤的理论视阈下,分析纪录片《二十二》对“慰安妇”问题的表现形式,以期对文化创伤教育的实现策略得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创伤记忆与现实经验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记忆的社会框架与当时的社会主导思想相一致,记忆在不同的社会框架之下将得到不同的建构和重修,在这个层面上,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构的。[4]《二十二》将目光投射到“慰安妇”幸存者群体,关注个体生存状态,以平实而朴素的语法将个体创伤记忆转换成叙事记忆,进而在叙事记忆的言说中即创伤话语中,为创伤事件的受害者搭建起由创伤回归现实的精神桥梁,表征当下的生存状况,把握记忆的当下性。
影片《二十二》是在与现实生活经验的建构中显示出创伤叙事的现代意义。《二十二》作为一部纪录片,可以说是一部关涉“慰安妇”问题的重要影像资料,因而很容易被大众期待为一次“历史教科书”式的说教。但细看影片,没有解说式的旁白,没有历史画面的切入,有的是见证真相的历史遗迹,是已经回归于日常生活的普通老人。《二十二》摄取了大量“慰安妇”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镜头,一日三餐、家长里短等现实因素的介入使得关注当下成为影片的一个突出特征。当镜头介绍到山西省盂县的慰安所遗址,志愿者充当叙述者,介绍慰安所的方位布局以及当年对“慰安妇”的关押情况,叙述中是历史的沉痛过往,镜头下是现实的满目疮痍,声与画勾连起历史与现实,观者借今天的历史遗骸,追溯当年的事件真相。当创伤事件已经发生,伤害也已不可逆转的造成,那么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除去怨恨,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尽快返回正常的普通的现实人生,也即如何回到当下,如何面对未来。
在“创伤受害者回到现实人生”这一进程中,身份认同危机是一大阻碍,影片直面这一现实问题,体现出影片的现实意义。对于曾经历创伤事件以及直接受到事件影响的受害者而言,心理创伤的产生不仅是在遭遇事件的过程中,更是在返回社会、回归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身份认同,“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5]。出生于韩国的毛银梅老人,将原姓氏“朴”,改成了和毛主席一样的姓氏;生长在广西的中日混血罗善学老人从小未能得到同龄伙伴的群体认同和接纳。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产生了困惑,而当他们决心选择追认一种民族身份时,却又遭到阻碍。由于面对身份认同危机,创伤事件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加深,而要想痊愈,就必须通过社会的帮助重新找回对民族和社会的认同,从而确认个人民族身份,重新融入社会群体之中,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叙述历史,表征当下,《二十二》准确地把握住创伤话语言说的这一原则,在讲述历史客观现实的同时,深情观照老人们的生活现状,搭建起由历史通往现实的桥梁,回归当下,关注并着手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彰显出影片的现代意义和教育价值。
二、景观疗愈与审美修复
纪录片,是基于镜头的影像表达。在镜头将创伤转变为一个审美对象的过程中,创伤即获得了一种基于镜头语言的审美修复。[6]纪录片《二十二》正是充分运用了镜头画面这一言说方式,在创伤事件转换成创伤话语的过程中,将创伤与景观、回忆与身份相结合,因而创伤在景观的疗愈功能下获得了一种审美修复的美感和慰藉,让观者在审美修复的蕴藉中接受文化创伤教育。
关于景观疗愈,学者李雪梅曾在论文中指出,后殖民语境下的景观在治疗印第安文化创伤方面具有特殊功效,认为景观是有生命的实体,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治愈性的地方意识,因而成为了主人公治疗创伤的关键因素。[7]在纪录片《二十二》中,尽管景观还没有彰显出其可以作为生命实体的本体性地位,没有成为治愈创伤受害者的关键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影片将创伤记忆与现实景观联袂,景观成为了过去创伤产生的地方,同时也是现在创伤获得治愈的地方。影片开始于陈林桃老人的葬礼,结束于张改香老人的葬礼,老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在这片土地上遭遇创伤事件,最终也在这入土为安。斯人虽已逝,但历史的真相是永远不能被埋葬的。正如老人坟头上冒出的青草芽,历经寒冬终有破土而出的一刻。
景观镜头,是影片创伤叙事的断裂带。文化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ssmannAleida)指出,创伤经历具有反记忆性,即创伤经历会妨碍人们的记忆行为,从而造成遗忘,并且遗忘的产生总是先于记忆的处理过程。[8]这解释了为什么当创伤个体试图讲述创伤事件时,会出现失语的现象。《二十二》中,当“慰安妇”老人无法有意识地处理创伤经历,落泪而失语时,导演即将镜头切换到天空、云朵、屋檐、雨水、田野等自然景观,景观镜头的及时切入就意味着此时叙事断裂的发生,但叙事的断裂并不阻碍影片的叙事进程,它是影片创伤叙事的策略之一。影片以叙事的断裂喻指老人创伤记忆的断裂和情绪的起伏,而创伤记忆及创伤叙事又事关个体的身份建构。叙事的断裂游移在记忆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人像与景象之间,映照出老人作为创伤事件亲历者在回忆事件时的时断时续的思想运动轨迹,也暗指老人个体身份建构的受挫进程。
与此同时,景观镜头也是创伤叙事的镇定剂、舒缓剂。景观镜头的切入减缓了影片的叙事节奏,使得每一次的情绪宣泄在即将到达爆发临界点的时候被中断,进而被无尽的延宕,这使得影片在情绪处理方面呈现出冷静克制而又余味悠长的特点。影片将镜头对准的是创伤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事件已经过去多年,但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重谈一段已长时间被自我防御机制封锁的回忆,也是再一次在心理层面上对创伤的重演,悲伤与痛苦的情绪极易被放大。但影片对情绪渲染节点的把握十分精当,避免了负面情绪的大肆宣泄,体现出明显的“分寸意识”。这在呈现形式上主要得益于影片中景观镜头的参与。影片中,毛银梅老人因情绪激动而记忆中断、一时失语,镜头随即由人物面部特写,切到自然景观及日常生活的远景镜头,叙述者也由老人自然过渡到老人家属。同样的处理方式还出现在45分林爱兰老人、66分李爱莲老人掩面落泪时,镜头由凝视老人面部切换到室外自然景观,随后再切回老人的叙述。艳阳,或是大雨;和风,或是雷鸣。自然景观充当着老人情绪的保护色,充当着影片创伤叙事的镇定剂、舒缓剂。悠悠不尽的情绪延宕在天空、在田野,消融在一日三餐、家长里短的生活中,进而为影片带来了余味不尽,令人回思无限的观感,从而达到一种审美修复的境界。
三、离散叙事与“共享创伤”[9]
学者陶家俊曾归纳西方创伤文化存在着三大疑难,再现危机为其中之一。再现危机具体体现为真切的创伤体验和心理感受与知识话语之间的矛盾。[10]为克服传统创伤叙事的再现危机,影片《二十二》采用创伤受害者自我叙述与他者叙述相阐发的离散型叙事方式,将多位叙述者的叙述线并行,以突破时间和历史、记忆与现实的界限。
《二十二》将“慰安妇”老人作为影片主角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通过叙事过程来重现、召回创伤经历和情景,并在现时的叙事中进行着自我重构。由于创伤事件对受害者带来的巨大冲击,可能使人改变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那么创伤受害者为了重新理解这一事件,为了完成自我重构,往往需要通过建构一种叙事,将心理碎片在回忆中整合,并通过讲述获得宣泄,从而得以从创伤中恢复。《二十二》时长99分钟,不汲汲于揭露历史真相,而将关注点聚集在二十二位老人身上,尝试从个体角度探寻历史创伤事件背后的个人命运和心理情感,为老人提供创伤后的宣泄、慰藉和勇气,帮助老人通过自我叙述完成创伤叙事的建构,重建自我。
以“慰安妇”老人的第一人称自我叙述进行叙事建构,在老人借此完成自我重构的同时,历史真相的碎片也得以不断的拼合,从而将个人记忆与历史事件相连接。相比传统的历史纪录片惯用的宏大叙事的手法,《二十二》选择在宏大历史事件背景下聚焦生命个体,使得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慰安妇”老人们因那段特殊经历而身份特殊,但回到现实生活中,她们又确确实实只是一名名普通老人。影片将历史的焦点“从‘那些拥有正式头衔和社会地位的演员身上’转移到了‘默默无闻的人们身上和日常的事件上’,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一段时期的‘转喻细节’。”[11]以已经回归于日常生活的“慰安妇”老人们为表现对象,使之成为那一段长时间被刻意隐瞒的历史的最有力注脚,导向一种比事件的真实更接近真实的文化创伤的实质。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慰安妇”老人作为创伤受害者其自我叙述存在的主观性。事实上,创伤见证的真实性历来受到创伤研究学者的质疑,创伤话语总是不可避免地囊括了创伤受害者的重新编辑和自我想象。“这种呈现并非是真实自我的表征,而是根据自我或外界的需求对自我身份的重构。”[6]基于此,《二十二》在“慰安妇”老人的自我叙述之外,穿插了他者叙述的线索,两者互为阐发,构成一种离散型叙事方式,以完成创伤话语的言说。
采用创伤受害者自我叙述与他者叙述相阐发、补充的创伤叙述方式,较好地搭建了创伤受害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得以引发公众对创伤事件的集体性回忆和反思,导向一种“共享创伤”。文化创伤的建构具有群体维度。这不仅是指直接遭受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具有群体性,更是指创伤记忆在建构成为文化创伤的过程中,应借创伤话语投射到社会中其他非直接遭受创伤的公众身上,使创伤的受众范围不断的扩大,因此那些没有直接经历创伤事件的人才能够自觉建立起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联系。影片中,出镜的除了“慰安妇”老人们,还有志愿协助“慰安妇”问题解决的各国志愿者及“慰安妇”老人的家属们。各国志愿者及家属作为事件的“他者性”存在,其叙述作为“自我叙述”的相对面,从第三角度观察事件,反思事件,将创伤事件建立起“由他及我”的关联,从而建立起群体认同。“创伤叙事是对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所经历的创伤历史予以见证,从而获得集体、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如果某群体成员能够认同某一文化创伤,这种群体的认同感有可能使该群体在未来重构他们的文化身份,重获该群体的凝聚力。”[6]在《二十二》中,创伤叙述所传递出的对待历史真相的严肃态度和人道责任,最终将导向一种集体认同的建构。在这里,“慰安妇”事件作为文化创伤,就不只是个别创伤受害者的事情,也不只是承受创伤事件影响的相关家属群体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民族或国家的事情。此时,创伤话语的言说,文化创伤的建构,就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事件,寻找创伤的根源,更是在对创伤事件给予文化上的提升和反思,扩宽创伤事件的“受众”,最终实现增强群体认同感、修复文化身份的文化创伤教育价值。
此外,“慰安妇”问题的创伤话语言说,并非孤立的创伤叙事,它是“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宏大叙事的一个侧面。今天的我们如何看待“慰安妇”幸存者,如何看待这一段创伤记忆,实则是我们如何看待抗日战争史的一个折射。“慰安妇”这一群体长期以来遭受非议,为社会忽视,“慰安妇”问题更没有被视为文化创伤事件予以建构和检视,令人遗憾。
综上,《二十二》作为一部以“慰安妇”幸存者为主题的影像作品,较为妥帖地处理了历史创伤事件与构建现代话语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创伤教育价值。无论是在故事内容对历史和现实的摄取,还是在镜头语言的对景观审美修复效果的运用,以及在叙事策略上由他者叙述导向“共享创伤”的建构等方面,《二十二》都对创伤话语的言说、文化创伤的建构及价值实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我们更应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将个体的创伤受害经验建构为全人类共同的受难经验,把创伤受害者的创伤建构为和每个人有关的“共享创伤”,探求该如何修复创伤后的人类精神世界以及物质世界,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