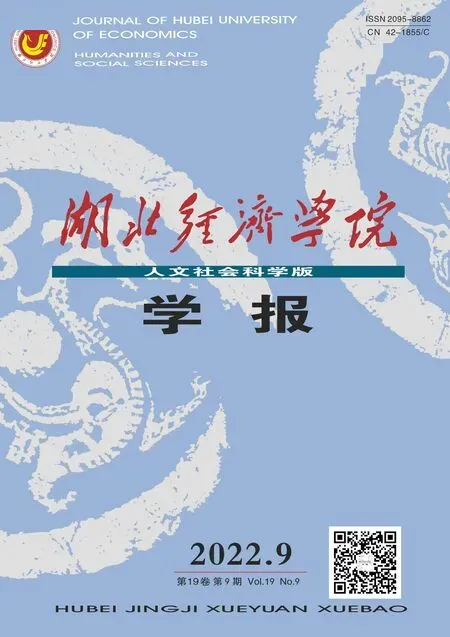浅析禅宗语篇翻译的语用学进路
——以铃木大拙为例
卢钰婷(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一、引言
在众多关于东方宗教典籍的语言研究中,对禅宗的重视尤为突出。有学者认为,禅宗语言研究的兴盛是多种偶然因素聚合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文献中禅宗作品的问世和中国白话文运动所带来的革新意义,也源于东方学界对考据方法的追捧以及对铃木大拙研究立场的反思(聂清,2019:107-108)。的确,自1897年始,铃木大拙以大量的英文禅宗翻译读物及深入浅出的通俗演讲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世界禅者”的美称后,“禅”——这个过去只为东方人熟知的概念已然走出寺院,从宗教学领域延伸至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范畴。而铃木在禅宗语篇翻译中基于语义层面的“反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立场则长期主导着西方读者对东方宗教思想的理解导向。而实际上,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翻译转向才是真正理解禅宗语篇的有效进路。
二、铃木大拙与禅宗语篇翻译
在亚洲研究和宗教研究领域尚且被白人,尤其是欧美男性主导的时期,铃木大拙(1870-1966)以其个人之力不知疲倦地将禅宗这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思想模态传播到亚洲以外的地方:他向世界各地的读者翻译、撰写并讲授禅宗思想,使其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而他本人也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正因如此,铃木在佛教,尤其是禅宗上的成就使其成了二十世纪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亚洲人之一。
纵观铃木一生,从年轻时代广泛阅读佛典、禅籍及西方哲学著作开始,他对禅宗思想的著述就再未停止。26岁时受访美经验的启发,《新宗教论》得以面世,其后的《大乘起信论》英译本(欧朋·柯特出版社)更引起学界注目。37岁时的英文著作《大乘佛教概论》在伦敦出版并在缅因州的古利恩诶卡第一次举行关于佛教的讲演。而《坛经》的英文译本则最早见于1960年由格罗夫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禅宗手册》(Manuals of Zen Buddhism)当中。除了大量著述之外,铃木还担当着佛教和宗教学的教学,先后讲授的课程包括:《禅宗学概论——关于中国禅宗的发生》《禅宗哲学》《楞伽经的研究》《惠能时代禅思想的诸方面》《念佛与禅》《禅宗思想史的初期》《禅宗思想史》《中国禅与净土的交涉》《禅与净土》《净土系思想》《禅》《般若的理论》《禅思想与神秘思想》。同时,对于中西宗教文化及观念的差异,铃木也十分关注。曾先后讲述《东西方神秘论——佛教特别是禅与普罗丁》《宗教概论》《神秘主义,东方和西方》(Rudolf Otto:Mysticism,East and West)、《佛教与基督教的宗教经验比较研究》《宗教经验之种种》(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等 课程。而最近由美国加州大学与佛教协会信托基金(Buddhist Society Trust)联合出版的《铃木大拙作品集》(2015)更是收录了他对禅宗作品的翻译及其思想探讨的大量文本。
然而,正是基于东方人的心性立场以及西方威廉·詹姆斯式的强调个人“宗教经验”的进路,使得铃木在禅宗思想的翻译传播中呈现出一种近乎独断的“反实证主义”立场和“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倾向,即驳斥了通过语言和逻辑对禅宗文本进行解读的有效性。
(一)铃木的“反实证主义”的立场
首先,鉴于铃木对西方哲学以及西方宗教的熟知,他始终坚持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进路对禅宗思想进行翻译解读。他一向反对用割裂的、对立的西式态度去看待主客体。因此,在1957年的英文禅学演讲《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中,铃木首先就这一古老议题展开探讨:他以东方诗人芭蕉和西方诗人丁尼生为对比展现中西思想的分殊①。铃木用一系列的对立词汇总结道:“西方(心灵)是分析的(analytical)、分辨的(discriminative)、分别的(differential)、归纳的(inductive)、个体化的((individualistic)、知性的(intellectual)…;而东方是综合的(synthetic)、合一的(integrative)、不 区 分 的(nondiscriminative)、演 绎 的(deductive)、独断的(dogmatic)、直观的(intuitive)…②不仅如此,当谈及禅宗核心“开悟”概念时,铃木指出“在宗教心理学中,与个人全副生命相关的这种精神上的强化,一般称之为‘皈依’(conversion)。但因此词通常被用于基督教的皈依者(converts)并含有太浓的感情意味,故无法取代以知性为主调的‘开悟’(awakening)一词”(铃木大拙,1975:211)。由此可见在铃木眼里,东方禅宗截然不同于西方宗教的得救之说,作为大乘各派之一的代表,大量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主知主义使西方逻辑二元论趋于无效。在铃木看来,西方式的重分析、重归纳、重演绎的“实证式”思维根本无法契入禅宗内核。还是以“开悟”为例,铃木竭尽一切力量在英文的禅学演讲《五步》(five steps)中给出了明确的步骤和路径,以求得对禅的生活和禅的教导做进一步的说明。它们分别是:(1)“正中偏”;(2)“偏中正”;(3)“正中来”;(4)“兼中至”以及(5)最后一步“兼中到”③。他指出,这五个步骤中的前三位是“认知的”(noetic),而后两位是“情感的”(affective)或“意志的”(conative),但是禅者要实现他的颖悟,以达到命定的终点则关键在于由“认知”转为“意志”。在“认知”向“意志”的转化中,重点不在于人们从理智上去理解或认知关于禅的字面含义,而在于人们从抽象的概念转变为“有意志的、有感受的活生生的人”(D.T.Suzuki,1960:73)。正如迦叶对佛祖拈花一笑,意味深长;维摩诘以沉默来表现自己的彻悟;慧可用无语的鞠躬来回答菩提达摩的诘问——这些著名的案例都说明,对于禅宗的核心概念如佛性或开悟的理解,理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当铃木面对大量的禅宗语篇中出现的语义晦涩,他的对应策略是要求人们抛弃理性和二元对立,打碎有限的“自我”概念的辖制,在最为基本的自身感受中去感觉“事物作为无限整体(infinite totality of things)时所拥有的体验”(D.T.Suzuki,1960:74)。换言之,强调宗教体验的“个体性”和“情感性”代替了理智中的分析性和理智性。因此,“反实证主义”已经成为铃木式禅宗立场的标志之一。
(二)铃木的“不可知论”立场
其次,禅宗语篇的“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的二律背反也深深困扰着铃木。因此,在面对语义的逻辑矛盾时,铃木所展现出的“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倾向也愈发明显。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言:“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思考;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1962:79)而禅宗语篇确实充斥着大量这种看似矛盾且无法思考的公案。无论是《五灯会元》中的德山禅师,在面对弟子发问时示众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有话可说三十棒,无话可说三十棒),还是《坛经》中的六祖慧能,在“风吹幡动”和“幡动而知风吹”的争执中道出“非风动,非幡动,是仁者的心在动”的感悟,抑或是百丈怀海禅师被马祖“扭鼻子”而大悟的体验,这些无法用理智求得的公案使得铃木无法给予读者们(尤其是西方读者)以确切无疑的答案。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铃木通常在翻译之后再添加注解:“禅的里面含有某种不容解说的东西无法运用理智的分析求得…禅师只是信手拈弄,或说一两句不为局外人所懂得话。”(铃木大拙,1975:211)可见,在面对语义层面的逻辑矛盾时,铃木除了进行语义层面的翻译也别无他法。实际上,任何文本,“只要是由词语构成的,就旨在传达观念或概念”(奥托,1995:2),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强调理智中的“理性”特征。而宗教体验中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已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理智范围。因此,试图通过表层的语义翻译是无法达到对禅宗真性的理解的。不仅如此,逻辑理解中的不一致还源于人们在自然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对“元语言”与“对象语言”混同使用④。具体而言,在自然语言系统中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元语言与对象语言层次间的混淆,这种混淆直接引起语形与语义、语义与语用层次间的混乱;同一层次中部分与整体之间跨层次的相互作用;以及显明意义与隐含意义、隐含意义与终极指的等层次间的混同。混同的结果导致了语义的结构纠缠和含混不清,于是必然引发逻辑上的矛盾。因此,单纯依赖靠语义层面的文本翻译来去描述禅宗真性,必然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为了避免语义悖论,要么放弃语义有效性,要么放弃逻辑有效性。如果放弃语义有效性,必然导致铃木式的“不可知论”倾向,结果是不可能用语言去翻译和阐释禅宗语篇背后的真性。反之,如果放弃逻辑有效性,那等于接受语义悖论,这又与“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确定性相抵牾。所以,与其说铃木在翻译和理解过程中专注于语义层面的有效性而不得其法,倒不如说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语用学与翻译过程的紧密关系。
总而言之,铃木在禅宗思想中的“独断性”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批评的声音。从第一本佛教经文和大乘佛教的英文译本开始,众多批评就集中在他对传统禅宗里的“真性”问题上。批评者们认为铃木的观点过多的受惠或受制于西方的宗教哲学或是日本禅宗,而并未展现出中国禅宗的真实意蕴。而这种批判最早可见于1908年,路易斯·普桑(Louis de LaValléePoussin)在对铃木的大乘佛教纲要的评论中写道:“铃木的大乘佛教超越了其实用的或可允许的范围,充满了吠陀主义和德国哲学的色彩”,其言下之意即是指责铃木用宗教激情掩盖对大乘佛教的客观性理解,这使得大乘佛教变为了“虚无的神秘主 义”(mysticism of sophistic nihilism)(S.Dicerto,2018:10)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如James Ketelaar,Bernard Faure,T.Griffi th Foulk,David McMahan,Elisabetta Porcu,Robert Sharf)都指出了铃木在禅宗思想阐释或翻译中的缺憾。他们认为,铃木对佛教禅宗的介绍(包括一系列的英文翻译以及英文演讲)实质上只是他本人所经历的社会的、政治的、理智的一种交互式再现。也正因如此,禅宗的语篇的分析及其翻译亟需某种方法的更新或者转向。
三、禅宗语篇与“多模态”
实际上,从狭义上看,禅宗语篇以《六祖坛经》和《五灯会元》等经文为首;以禅律《百丈清规》为辅:因为前者是对禅宗思想的框架性阐释,而后者则是百丈禅师根据风情地理,博采大小乘戒律制定出的适合我国风俗的修持制度。而从广义上看,本文所攫取的禅宗语篇不仅涵盖了禅宗原典,还涉及与禅宗思想传播相关的研究性或反思性文本(皆以铃木大拙的作品为例)。因此,首先厘清禅宗语篇的文本类型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西方翻译理论与语言学结合的不断深入,不同文本或语篇的翻译对应方法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重视。以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为例,虽然其对象为英汉翻译,但不可否认,语言转换中的“量体裁衣”已然成为高级阶段翻译的要求之一⑤。而纵观禅宗的语篇类型,其“不立文字”的难以言说性和“机锋对答”的日常对话性,似乎很难将其划归到任何一种对应的语篇类型之中。以《六祖坛经》为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慧能在大梵寺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第二部分为“无相戒”的传授;第三部分与弟子间的问答)各有侧重和异同:首部的自序生平和之后的弘法内容到最后的请益问答层层递进且不拘风格,尤其在与弟子的“机锋问答”中,句法结构的简短性、语义结构的跳跃性以及逻辑结构的矛盾性层出不穷。不仅如此,在禅宗语篇的相关性研究中还经常会出现一两幅禅师说道的画像或相关禅法的题字⑥,这些都使得禅宗语篇和其他类型的文字语篇产生了某些分殊。
首先,作为翻译“目的论”的前身,语言学家赖斯曾针对“文本类型”(text type)明确提到过多模态意义的翻译模型(Katharina Reiss,1977/1989)。赖斯认为:在多模态文本中,言语内容(verbal content)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文本资源的支持。同时她还声称存在四种不同的文本类型:即信息性(informative)、有效性(operative)、表达性(expressive)以及多媒体性(multimedial)。但她随后又改变了最初的立场并表示“多媒体文本”(multimedial texts)实际上是一种“超类型”,是“针对其他三种基本类型”的一种“超结构”且“具有自身规范性”的东西(1981/2004:164)。而斯内尔·霍恩比则同样出于整合语言学和翻译方法的目的,她将文本的语言学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Snell-Hornby,1995)并继而提出了一种基于“非语言元素”的文本分类,用其术语表示即是“多模态”(multimodal)、“多符号”(multisemiotic)和 “声频媒体”(audiomedial)(2006:84-90)。顺着这样的思路,越来越多的关于多模态的研究应运而生(Lemke,1998;Marsh,2003;Baldry,2005;Martinec,2005;Salway,2005;Hughes etal.,2007;Pastra,2008;Liu,2009;Bateman,2014)),但这些理论往往集中关注视觉和言语内容建立关联的方式,而并未提及翻译本身。因此绝大多数多模态翻译研究都局限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屏幕翻译研究(screen translation)(Gambier,2001;Chaume,2004;PérezGonzález,2014)或是漫画研究(studies on comics)(Kaindl,2004;Zanettin,2004)。然而这些案例却不足以涵盖多模态翻译本身,因为它们与源文本的类型无关。正因如此,建立起书面文本(written-text)与多模态翻译的关联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只有采取“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方法,才能更好地阐释多模态翻译的整体图景(Cattrysse,2001;Remael,2001),尽管他们就“多学科”需要涉及哪些学科且如何建构它们间的关联还未达成共识。但也正因如此,禅宗语篇在“不可言说”和“机锋对答”的语义表层下,众多学科符号的交融才更容易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以铃木大拙为例,他在禅宗思想及其相关语篇的翻译中,展现了各种与现代性思想的对话,其中就“包括了存在主义、十九世纪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神秘主义、神学、哲学以及先验论等。”(Richard M.Jaffe,2015:6)可以说,禅宗语篇背后的“多学科性”是其他任何一种单一模态的语篇文本所无法比拟的。
而在2009年,由穆本伽所提出“多模态语用学分析”(Multimodal Pragmatics Analysis)研究更表明了对新的多模态翻译观点的需求。如她所言:“多模态语用学分析是语用学和多模态的融合。”(Mubenga,2009:467)尽管这个模型的语用学成分有限,且看上去更像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的延展,但首次明确地将语用学应用在源文本中仍不失为一种创新。由此可见,不论是除书面文本之外的图像、声音、动作还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多重符号资源,都应该被视为“多模态语篇”的类型,尽管“多种模态的语篇翻译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在相关领域还尚无定论。”(胡永近,2014:124)因此,本文将禅宗语篇划归为“多模态语篇”的类型不可谓一种新颖的尝试,其目的就是为了更深入地挖掘出禅宗语篇语义表层下的内在语用学逻辑和有效的翻译方法。
四、禅宗语篇翻译的语用学转向
实际上,在禅宗语言的研究方面,“集中于词义诠释、句法分析、语法归纳、文献整理等语义学层面,其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而关注文本关联的具体环境,则是语用学不同于语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聂清,2019:107-108)。而语用学,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从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的创刊距今也不过五十年左右。毫无疑问,语篇的交际行为需要系统化的语用学理论为支撑,因为无论是在话语实践还是在话语阐释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语言家们都倾向专注于语言运用本身而非仅仅将自然语言视为一种逻辑形式的模型。“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Mey,2001:4)的提出,实质上标志着由皮尔士(Peirce)、莫里斯(Morris)以及卡纳普(Carnap)最初提出的从“句子结构”到“句子使用”理论转型渐渐地与维特根斯坦的 《哲学研究》思想(Investigation)(1953)融合在了一起(Keith Allen,2012:2)。
近几年,出于认知语用学方法中“跨学科性”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将语义学由关注“言语”扩展到“交际的非言语方面”(non-verbal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S.Dicerto,2018:37)。奥 莱 巴(Orlebar,2009)指出,构成多模态文本的符号通常具有多义性,文本的接收者根据自身对符号和文化背景的阐释而消除歧义。换言之,文本的接收者本身即是我们所谓的“语境”。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出于翻译的目的,语用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于理解禅宗语篇的多模态性?
(一)语用学与双方共同的认知环境
首先,从禅宗语篇的源文本来看,最为显著的特征即为“对话性”。以《六祖坛经》为例,其主要记载的是六祖慧能毕生的弘法事迹以及启导门徒的丰富言教,且内容丰富、文字通俗。而对话中的“话语交换”(talk exchange)则刚好为语用学提供了“理想的工作材料”(ideal work material),因为与其他语篇类型相比,“话语交换”中的语义结构清晰且内容集中。不仅如此,话语交换更易搭建起交流双方的共同认知环境,即 “展现在官方面前的事实集合”(the set of facts that are manifest to them)(Sperber and Wilson,1995:39),而这对于语境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参与者在交流中所具备的知识是语用学得以应用的基础”(S.Dicerto,2018:38-39)。
事实上,在源文本的翻译过程中,陈述性文字和话语交际隶属于不同的语言表达体系。克里斯特尔指出:“(这两者)在结构和使用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因为它们根本就是不同的交际情境的产物。陈述性语言的空间是有限的、静态的、永恒的。通常情况下,交流双方的距离很远,甚至通常不知道对象是谁(如文献);而对话是有时间限制的、动态的、短暂的、互动的。通常情况下,参与双方都必须在场,讲话者的心中有特定的对象”(Crystal,2010:187)。
的确,在文本的理解过程中,由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容易出现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匹配,因此很难找出双方共享的认知环境。例如,当读者面对陌生的文本,很可能作者已经辞世;或是读者和作者虽处于相同时代,却属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搭建作者和读者间共享的认知环境是语用学对文本分析的助益。而禅宗语篇之所以历久弥新,禅师及弟子间的对话“往返性”则恰恰是搭建作者和读者共同认知环境的桥梁。因为从语言认知映射的角度来看,意义的获取实际上经过了心灵的双重投射,即世界投射到心灵,心灵产生的思想再投射到语言。禅宗语篇中的“机锋对答”以已有的某种理解为前提,以得到一种新的理解,而理解和解释过程涉及某种循环;解释需要的表达模式往往不止一种,其有效性又与解释者的主观心灵映射密切相关。因此,译者在源文本向目标文本的转换中,实际上也经历了自身的心理投射。对铃木而言,虽然他付诸毕生精力翻译传播禅宗思想,但对中西文化分殊的“预设”以及对“实证主义”思潮的批驳,使得他本人表现出的恰恰是对文本接收者(尤其是西方读者)理解力和感受力的不信赖或不信任。面对这样的情况,同时也为了让语用学契入语篇翻译的内核,库任颇有争议地提出了“文本代理”(textual agency)的概念。他解释道,“文本实体”(text entities)具有独立于人类行为者进行言语行为的能力。因此,它们应被视为代理人,且能够影响周遭世界。通过文本代理,语用学被用以分析基于享有共同认知环境的“文本—读者”(text-reader)的双向关系,而非“作者—读者”(writer-reader)的双向关系(Cooren,2008)。只有这样,才可以将文本的发出者和接受者聚集在相同的认知情境之下,以消除他们时间与空间的错位问题。因此,在禅宗语篇的翻译中,尤其是面对禅师和其弟子的对话语篇,铃木所需要做的恰恰不是处处强调禅宗文本的历史久远性和东方异域性,而应该以一种“无分别”的心理趋向引导读者采取某种基于文本本身的理解或行动,以求得读者对自身语言环境、文化处境、交流原则以及思想连贯性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解。
(二)语用学与语篇的隐义
其次,禅宗的话语体系在生成过程中,还凸显出了一种由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如禅师经常会用间接的指称、双遣双非的否定手段去阻断求法之人的语义诉求。在《坛经》以及《五元灯会》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菏泽神会见慧能禅师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慧能则以拄仗打三下,答曰:“吾打汝是痛不痛?”同样地,南岳怀让见慧能,慧能问曰:“汝从何来?”怀让答曰:从嵩山来。慧能继而问道是什么物?怎么来?使怀让哑口无以作答。还有曹洞宗的创始人曹山本寂,因抛弃尘缘投入洞山良价门下。洞山问:“汝何名?”答曰“本寂”,洞山继而问道“哪个呀!”曹山又曰“不叫本寂”。可见,“将语言玄化,禅寓于言”是禅宗语篇背后隐性含义的集中体现。
而在文本的翻译理论中,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and Wilson,1986/1995)的 “相关理论”(theory of relevance)以及格莱斯(Grice,1989)的语用学框架最初就是为解释语言交流而设计的。斯珀伯和威尔逊坚持认为,从亚里斯多德到格莱斯,语言只是根据其代码(code)实现,而话语交流则被看作编码和解码的过程(Sperber and Wilson 1995:2)。但是,所有的语言行为都要遵从推论原则,即文本接受者通过理智分析去理解说话者的意图(1995:27)。而针对禅宗的多模态文本,因其包含众多模式符号且每个模式都有其特殊代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多模式文本中,每种不同的隐形含义在其他模式中都可以找到其最直接的可供参考的语境,而这会恰恰影响符号系统的交互使用。由于可以从不同的来源获取信息,因此在多模态语篇中,通过单一模态传达的消息是不完整的:一种模态可以依靠另一种模态来表达其无法表达的内容或增强其语用学的隐义。故,语境(也就是语用角度)成为多模态较之“单模态”更具优势的关键所在。
(三)语用学与语义的悖论
最后,禅宗语篇里的公案还处处充满着言语悖论的困扰。从表面上看,禅师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答非所问。实际上,惠洪早在《临济宗旨》中就指出:“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源,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杜继文,1993:399)因而真性等终极问题,不是靠一致性的概念分别的语言所能描述,而是需要运用悖论性的语言来显现悖论的真性。禅师们无论是使用间接的指称还是双遣双非的否定手段,隐喻性才是禅宗语篇中语用学维度的核心。正是这种暗示性的、诗意的、指向性的,而非定义性的语言,才能使话语的接受者不再囿限于语义表层的描述能力,而在于语言使用者在心灵背景中的投射作用。斯珀波和威尔逊提出的以认知语境为基础的关联理论来解读错综复杂的禅宗语言,实际上表达的是,尽管这些刺激讯号在外行看起来完全不可理喻,但依然和禅宗教义之间有某种既定的关联(Sperber and Wilson,1986/1995)。因此,为了打断求法之人的语义诉求,禅师们要求人们对禅法的理解并非要执着于语言本身,而是要不断努力探析语言所指向的对象。而这种体验必须建立在某种超验的信念之上,或者说是建立在某种特定的宗教环境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文本的接受者只有在心智以及推论行为的参与下,对言语过程中语言所传达的表层含义以及深层含义进行不断的区分、选择以及评估,才能真正达到千丝万缕的整个语言活动中的中枢。
因此,语言的玄化、语义的跳跃乃至悖论要求译者不能照字面去理解禅师的话语,而是要在公案中别求禅师意旨、体悟言不可及旨之妙。实际上,如果将“语”字的“言”字旁去掉换成“心”字旁,就会得到“开悟”的“悟”(周昌乐,2006:198),这正是禅宗所强调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因此,铃木式的“不可知论”立场会使读者囿限于语义的迷宫不可自拔,而语用学中的隐性含义或语言中的隐喻却有助于文本的接受者破除对文字的执着。禅法、开悟或是公案之不可说,并非否定的是语言,而旨在用最彻底的办法则是要破除逻辑思维的执着。毫不夸张地说,文字禅是逻辑禅,逻辑上破疑则一切文字上破疑。逻辑禅不仅可以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更是“不可知论”的有力反驳。
五、结语
由于禅宗语篇的“多模态性”和“跨学科性”,加之语言学者们对禅宗语篇具体的宗教实践尚不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语篇研究以及语篇翻译的“语用学转向”还远未完成(聂清,2019:107-108)。虽然铃木大拙反对“实证主义”并坚持逻辑在语义上的“不可知论”,但他孜孜不倦地倾尽毕生精力著述有关禅学的著作,不正是用语言文字在解释禅学吗?如果语言仅仅是语义的牢笼,是翻译的异化,那么他毕生的结晶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因此,为了能够重现目标受众的对源文本的理解,译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熟知语用学概念。并在翻译过程搭建双方的共同认识环境以催生读者对目标文本的个人阐释。如此一来,禅宗语用学研究可以为禅宗理论翻译提供更契合禅宗语言使用情境的解说;而禅宗宗教理论的学理可以通过语用学得以引导,最终在理论预设和实际话语间生成建设性的语用学循环。这样,语用学的翻译转向才能为禅宗的语篇翻译提供新的机遇。
注 释:
①两位著名诗人曾都以花作为对象作诗,但前者只是默默注视着小花,使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而后者却摘下小花,放在手中观察把玩。
②实际上,铃木大拙分别用了将近20组对比词汇去阐释中西思想差异。参见《Zen Buddism and Psychoanalysis》第5页。
③所谓的“五步”,就是“五个步骤”或是“五种情境”,“五种级别”。
④“元语言”与“对象语言”是由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Tarski)在1933年提出的。他认为,当我们讨论一件事物时,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对象语言”,因为它是对象的表现;而当我们谈论一种语言时,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则被称为“元语言”。
⑤参阅刘宓庆,《文体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年版。其中,刘将文体或语篇类型分为了“新闻”、“论述”、“公关”、“叙述”、“科技”和“应用文”六种。
⑥可参见由美国加州大学与佛教协会信托基金(Buddhist Society Trust)联合出版的2015年《铃木大拙作品集》的封面以及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