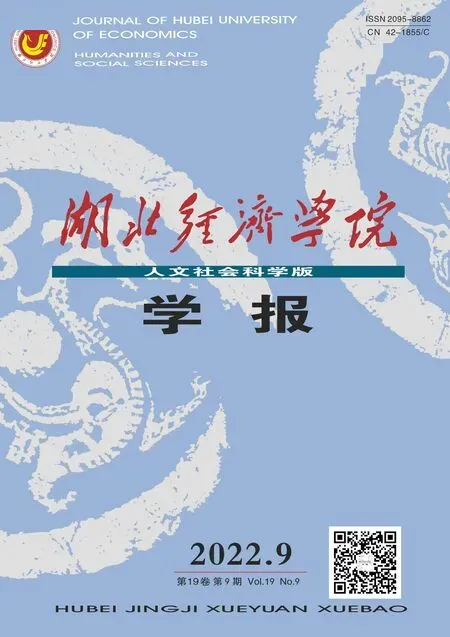论《雪松后的房子》中的美国黑人女性教育困境
王亚萍(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 《雪松后的房子》(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1900)出版30年后,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nutt,1858—1932)称这部小说为其“最喜欢的孩子”[1]。究其原因,主人公瑞娜·瓦尔登与切斯纳特的经历相仿,皆为“白种黑人”[2]127且从事黑人的教育事业。切斯纳特自幼就读于一所自由民局创办的学校,1872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开始了教书生涯,1880年成为费耶特维尔州立黑人师范学校校长,随后攻读英国古典文学和速记,皆有所成。教育是普通大众实现上升迁移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教育则意味着自由与反抗,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阐述,“如果一个民族希望既无知又自由,那么它这个希望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3]但殖民地时期以来,反对黑人受教育是南方白人的一贯立场,白人种族主义者唯一能够容忍的黑人教育仅限于教授简单手艺和劳动技巧的职业教育,以培养农业劳动力和家仆等[4]。南北战争前,美国女性教育并不包括黑人女性,给予黑人妇女的有限教育也只属于黑人教育的范围[5]112。奴隶制被废止后,黑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仍持续偏低,文盲率较高:1880年为70%,1890年为56%,1900年为44.5%[6]286,303,329。
期间,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的妥协主义大行其道,他提出黑人的职业技术教育计划并呼吁黑人暂时放弃对包括选举权在内的一切权利的要求[7]72,使黑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切斯纳特则认为,“无知、贫穷和不道德存在于所有国家”[2]120,不应过于乐观而放弃争取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他也曾发文探讨教育方法,提倡“完善的教育体系必须建立在完善的人类学基础上”[2]51。他尤其关注女性的教育问题,强调女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2]384。及至19世纪中期,美国黑人认为教育对男女同样重要。但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黑人女性教育很早就被打上了传统的性别烙印。主流观点表示,女性受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她们的女性角色。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将这种对女性的潜在歧视描述为“和根一样深,却像海上烟雾般难以触及”[8]。长期以来,女性主要接受家庭的非正式教育,那些有幸在学校就读的年轻女性,大多数只念一至两个学期,然后重返家庭学习持家技能,为今后顺利进入自己的家庭角色做准备[9]。生物学的谬论也让人们误认为女性在智力和心理上都弱于男性,不能承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压力[10]。这种教育的不公平最终导致黑人女性职业选择上的弱势处境,1900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96%的黑人妇女从事家务劳动或农业劳作[5]115。
基于此,切斯纳特在小说《雪松后的房子》中刻画了以瑞娜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从接受白人教育到从事黑人教育的独特体验,将其对美国黑人女性教育的关注隐匿在“种族装扮”的表层之下,展现了黑人女性教育面临困厄的严酷现实,隐喻性地表达了教育才是黑人女性取得进步的关键。
一、“成为他家里的女主人”:“家庭天使”的教育
小说开篇提到,成功越界的约翰·沃里克回到故乡帕特斯维尔说服妹妹瑞娜一起摆脱黑人身份。约翰表示,“在查尔斯顿的一所寄宿学校待上一年之后,她就成为他家里的女主人”[11]43,帮他照顾自己的孩子艾伯特。瑞娜的黑人身份被曝,约翰再次提出送她去北方学校以便“嫁一个比特里恩更好的男人”[11]181。此外,其母莫利·瓦尔登夫人也认为瑞娜成为教师“不仅仅意味着就业”[11]196,更是觅得佳婿的绝佳机会。这些事实集中揭示部分黑人在追求白人生活的同时,被白人社会的价值观所同化,认为妇女接受教育是为了有一个好归宿,最后成为模范妻子与母亲,即“家庭天使”。显而易见,当时的女性教育是培养女性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女人,以巩固其从属地位,印证了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经典论断:“女人是逐渐形成的”[12]。
小说有几处细节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诠释。第一处围绕白人男性进行的骑士比武,胜利者有权挑选在场的任意女士成为“爱与美的女王”[11]55。女性成为男性的战利品,这种比赛规则本身就将父权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然,多数女性把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内化为自己的意识与行为指南,对“爱与美的女王”这个头衔趋之若鹜、“表达敬意”[11]57。第二处是莉莎·特里恩夫人为儿子特里恩挑选“端庄、漂亮、性情和蔼”[11]191的白人布兰奇·莉瑞小姐为伴侣,而“莉瑞小姐用尽力气吸引和取悦”[11]234特里恩。这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分不开的,杰斐逊总统的顾问吉恩·鲁索(Jean Rousseau)曾发表言论:“对妇女教育的计划必须和男性关联。妇女一辈子的责任是使男人赏心悦目、赢得男人的尊重和爱、培养自己的儿子、照顾自己的丈夫、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咨询、使他们生活快乐。”[13]
此时,瑞娜凭借生理优势装扮为白人女性进入查尔斯顿寄宿学校学习。回溯美国历史,南北战争的第一枪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Fort Sumter)打响,查尔斯顿象征黑人反抗的开端,而瑞娜由此越界并接受教育也是对传统的反击。但此时,瑞娜并未厘清自我认知,她改变种族身份及接受教育的理由简洁了当,即“她想去某个地方”[11]26。小说虽对白人女性教育着墨不多,却也足见端倪。白人学校配备仆人,瑞娜“是许多被服侍的人中的一员”[11]64;瑞娜渴望进步以“取悦她哥哥、给他荣誉”[11]60;除了学习仪态标准,一些小说使她相信“爱是一个征服者,无论生与死,无论信仰与种姓”[11]73。事实证明,这种天真的想法与小说的种族悲剧相抵牾,暴露了女性教育的虚伪性。
即便如此,象牙塔似的女性教育也并不包含美国的黑人女性。早期的女子学院将黑人女性拒之门外,大多数白人妇女在追求平等待遇的同时,往往否认黑人妇女在这些方面的要求。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E.B.Du Bois)于1900年开展的一项有关美国黑人大学生的研究表明:黑人男性进入白人男子院校比黑人女性进入白人女子学院容易得多[14]。实际上,南北战争前,白人女性和所有的黑人一样受到社会歧视,被认为智力低于白人男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不甚相同,却皆是为了使其更服从于白人男性的统治。战后,父权制仍然占据主导。各教派为了实现对黑人的教化,定期组织黑人学习,“黑人男性学习读写,而女性除了学习读写之外还要学习缝纫和编织技能”[15],为其以后做家政服务工作做准备。是故,莫利夫人为了“品尝知识果实的味道”,“养成了去教堂的习惯”[11]159。
小说对幼年瑞娜接受的教育零星提供了一些线索。当少儿约翰从黑人教师那里学会读写后,“把那些简单的故事读给他妹妹听”[11]162;莫利夫人有时带女儿一起出现在圣公会教堂;瑞娜“读过母亲大厅书柜里的一些小说”[11]75等。比起哥哥约翰,瑞娜“没有读过那么多书”[11]26。原因在于,在黑人社团内部,女性教育机会的增加被视为造成男子教育机会减少的原因[5]115。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批准给予黑人男性选举权,使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白人社会造成的性别差异;第二,主流社会价值观和标准同化的结果。美国历史学家乔尔·威廉森(Joel Williamson)曾就黑人男子对妇女的态度评论道:“大多数黑人男人骨子里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男人的特质”[16]76-77,显然,“女性——作为妻子、母亲——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守护者”[17]139。纵观瑞娜在不同阶段接受的教育,反映出美国的女性教育包括黑人女性教育都毫无例外地迎合了主流社会对女性成为“家庭天使”的角色期待。
二、“弯腰才能举起别人”:“种族提升”的使命
南北战争前期,“种族提升”(race uplift)是所有黑人共同的目标,但战争过后,黑人妇女更多地坚持这一理想。她们的着眼点是整个黑人种族:通过提高种族的地位,使黑人摆脱种族歧视和隔离,最终走向平等和自由[5]128。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很多黑人女性选择教师职业,也导致当时的黑人女性教育倾向于培养教师。小说中瑞娜之所以想成为一名教师,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19世纪50年代,小学教师被普遍认为是专属女性的工作。19世纪末,美国黑人女教育家露西·莱尼(Lucy Laney)提出,黑人知识女性不仅可以教小学,还能够胜任其他各级各类的教学,包括中学和大学[16]81-82。教师成为当时人们广泛接受的女性职业,除了因为师资短缺,还包括其他原因:首先,年轻的女教师借此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其次,教学的微薄收入帮助改善她们的经济状况;其次,避免了与白人接触所受到的羞辱。在这一代美国黑人女性的脑海里,深深烙有黑人享受不平等待遇的痛苦回忆,从小说瑞娜的经历中可窥见一二。
当瑞娜的黑人身份被意外发现,特里恩果断放弃这段关系,而瑞娜痛苦地说道,“他看着我,仿佛我不是一个人”[11]180,反映出当时仍然紧张的种族关系。对此,切斯纳特坦言:“种族偏见变得更加强烈和毫不妥协。”[18]从“爱与美的女王”[11]55到“可怕的黑巫婆”[11]147,“美丽的头发变成粗羊毛,用肮脏的棉线裹着;清澈的眼睛布满血丝;象牙般的牙齿变成了令人不快的獠牙”[11]147,这种强烈的反差源于特里恩的主观臆想。按照胡克斯(Bell Hooks)的说法,“观看是一种权力。”[19]自殖民时期起,白人始终占据“观看”的主动权,黑人作为被看的对象,既没有主动看的权力,也无权决定自己如何被看,种族隔离将这种刻板想象化作公开的展览。在教师考试中,瑞娜因黑人身份被迫退出候考室,直至所有的白人教师考试结束,才被允许接受面试。这些经历使瑞娜对种族关系的认识逐渐清晰,她表示,“我会和我的人民待在一起”[11]181,也萌生了“为她重新发现的人民服务”[11]194的想法,将自我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直至投身黑人教育,瑞娜才真正地厘正这一使命。
黑人学校最初由黑人和白人共同建立,但学校的管理及发展主要掌握在白人手中,为此一部分黑人致力于建立完全由黑人掌控的学校,任用自己的教师并支付他们薪水。小说中黑人韦恩·怀恩就是桑普森县黑人学校的校长。为了吸引瑞娜,他表示:“有她的教育经历加上我的推荐,她就能拿到满级证书,一个月领40美元薪水。”[11]200他几乎完全是用最高级对“这所优雅的校舍、聪明的学生和邻里的友好社会做了最生动的描述”[11]200,甚至主动提出协助她的管理。然而,韦恩却说黑人土语且“对文字知之甚少”[11]201。显然,当时很多黑人接受的教育良莠不齐,投身教育更是不乏现实因素的考量。譬如聘用瑞娜,一方面,“浅肤色的老师比深肤色的老师更能留住小黑鬼们”[11]200;另一方面,韦恩殷勤体贴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占有瑞娜的不正当目的。
那么,学校条件并不优渥也属情理之中。事实上,校舍是一间简陋的木屋,号称“一间房”学校,即一间房子,一个老师和十几个学生,与当时大批黑人学校的情况并无二致。学校实现男女同校制,黑人女性与男性接受同样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瘦小的黑人孩子柏拉图仍然称呼特里恩为“主人”。在他看来,白人的地位堪比上帝,“去上学”以及“学习读书和写字”[11]237只是模仿白人的行为,正如他的名字柏拉图取自古希腊智者之名一样。虽读来可笑,却引人深思,这种对白人的盲目崇拜正是作者所极力鞭挞的。相比较而言,大一些的黄孩子(a yellow boy)提醒柏拉图,“你是自由的”[11]237,反映出教育对黑人观念带来的实质性改变。然而,特里恩却以金钱为奖励打压这种进步行为,他“把一枚小硬币扔给柏拉图,手里拿着另一枚,朝高个子的黄孩子微笑”[11]237。对此,黄孩子的拒绝是需要勇气的。
就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黑人史学家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指出,“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初叶是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最低点”[20]62。1880年,75%以上的美国黑人仍在前南部联邦各州从事农业劳动[21]。其中,3/4的农村黑人没有土地,只能作为雇农和佃农出卖劳力[20]125,131-133。种族歧视的持续存在使许多白人雇主招收欧洲移民代替黑人劳力。内战后的机械化和技术革新也使很多黑人失去了传统的工作,且遭受来自白人工人和工会的仇视和排斥,唯有从事粗重的劳动和家庭服务等。即使与白人做同样的工作,他们的收入也远低于白人[22]。以黑人教师为例,小说的混血男老师“免费教一群黑人孩子,只获得极少的报酬维持生计”[11]162,而黑人女教师的待遇更加糟糕。这就直接导致金钱对于贫困的黑人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瑞娜面临骚扰,因无法承担失去工资的风险只能选择留下;小柏拉图被金钱收买。
小说还提到,对南部黑人教育的帮助主要来源于北方,“北方佬到处为白人和黑鬼开办了学校”[11]26。据统计,1869年在南方任教的白人教师共计9503人,其中5千人是北方人[23]。同时,北方还建立了50个以上的团体救济南方黑人,除了向他们输送优秀教师外还向他们送去大量的衣物、课本及资金[24],瑞娜使用的教材正是由北方带来的《韦伯斯特蓝背拼写手册》。很多黑人父母为了使子女接受教育,做出了无法估量的牺牲,莫利夫人正是其中之一,但她仍感叹,“我很高兴我的孩子能上学”[11]123。瑞娜也坦言,“我宁愿为知识而死,也不愿生活在无知之中。”[11]179这种信念使她相信“能在学校发挥用处”[11]200,并深信“弯腰才能举起别人”[11]213,即“种族提升”的理想。
三、“传统是暴政”:黑人女性教育的困境
瑞娜将自己比作为信仰而死的基督徒,期望“把仍陷在奴隶制的泥泞中挣扎的黑人群众举起来”[11]246。但她逐渐发觉,“各个种族必须提升自己,而其他人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机会和公平竞争。”[11]246对于这群黑人孩子,她只能教会他们读写,为他们“打开机会之门”[11]246。约翰得到了这个机会,成为“所有人的主人”[11]165;瑞娜也曾抓住这个机会,“当上女主人,尝到权力的甜头”[11]64。正当她致力于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却发现早已陷入重重困厄。察觉到韦恩“浅薄、自私的内心”[11]247后,瑞娜的躲闪行为被视为“一种羞怯的表现”,逃跑被当成“只不过是为了引诱他”[11]250。莉莎夫人说过,韦恩的妻子曾被虐待且一年前离家。那么,韦恩编织妻子离世的谎言及对瑞娜展开的公开追求显得愈发可笑。同样,特里恩也将瑞娜在此任教视为追随他。虽然怀有强烈的种族偏见,甚至表示“把这个女孩从附近赶走”[11]253,他却收买小柏拉图传递信息并掌握瑞娜的行踪。毋庸置疑,特里恩也并非心怀善意。韦恩利用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束缚即“一个女人的软弱和对丑闻的厌恶”[11]261,在公开场合肆无忌惮地接近瑞娜;而瑞娜的拒绝损害了特里恩的种族优越感与男性权威,他表示,“决不能娶她,但他必须去看她”[11]265,以此攫取被服从的心理补偿。小说将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展露无遗,极尽讽刺。
长期的教学工作使瑞娜有勇气以一种得体的方式向曾经的爱人告别。她表示,“我找到了一份可以为之服务的工作,为那些机会比我少的人”[11]259,不仅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更是承担种族责任的显露。不幸的是,“被捕的恐惧”[11]268加上黑人教育的现状,加剧了她的自我怀疑。“每年的学期为两个月,她觉得自己在300万人的教育中所能发挥的任何作用都是微不足道的。”[11]268例如小说中的黑人孩子柏拉图,虽然接受了黑人教育却收效甚微。从他出场“用手走路,双脚在空中保持平衡”[11]236,到后来“偶尔转一个手翻”[11]253、“头朝下地垂在树枝上”[11]269,柏拉图始终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不仅如此,他始终称呼特里恩为主人。由此看来,萨莉安·弗格森(Sally Ann Ferguson)对切斯纳特的指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他寻求给浅肤色黑人带来种族和平和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深肤色黑人的利益。”[25]118很显然,小说对柏拉图的描写映射了白人对黑人动物性以及不可靠、易于控制的种族偏见。
但这种分析也并非完全可靠,“传统是暴政”[11]292,浅肤色的瑞娜久居其中,同样付出了惨痛代价。当瑞娜走到交叉路口时,白人特里恩与黑人韦恩分别站在两条路上。这两条路可谓分别隐喻白人社会与黑人社会,也代表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共同定义。考虑到女性的名声,也为了避免误会,瑞娜选择“转身逃走”[11]272,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反抗。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报告(1966)曾显示,种族歧视与隔离的存在,导致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民族后裔相比于白人中产阶级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叙述者也提到,“一种更聪明的直觉会引导她前进……但她只看到了事情的阴暗面。”[11]272遗憾的是,瑞娜迷失的位置恰巧“离一条清晰的小路只有几步远”[11]275。
正如小说出现的多处巧合,“包括令人难以置信的相遇、未读的信件、被风吹走的信封、导致绕道的倒下的树,以及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时间”[26],杰伊·德尔马(P.Jay Delmar)分析道,“切斯纳特运用巧合的手法,强调人物自身垮台过程中外部力量所发挥的作用”[27]97。无论对于瑞娜、韦恩,或是特里恩,这个结局都是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肇因于社会的种族歧视与父权传统。也正因此,当弗兰克偶遇白皮肤的疯女人(即陷入疯癫的瑞娜),“苗条的身躯伸直了躺在几码远的一块小空地上,……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上缠着树枝、树叶和苍耳”[11]287,对是否提供帮助犹豫不决,甚至试图与这个受害者保持距离。因为长期以来,黑人男性经常因观看白人女性而被谋杀或处以私刑。传统不但影响了黑人女性的价值判断,也在男性的行为中发挥作用。
作者深知“疯女人”暴露出的非理性和动物性不容于传统的道德伦理,加上美国传统对“跨种族的婚姻关系有所忌讳”[28],因而只能将黑人女性面临的道德困境隐匿在这种精心编排的疯癫与死亡中,以建立一种平衡——白人读者的心理平衡。换言之,通过刻意将瑞娜描述成一名衣衫褴褛、神志不清的疯女人形象,借助这个父权社会中经典的文学隐喻表达黑人女性的愤怒与反抗。福柯在其扛鼎之作《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也曾说过,“胜利属于疯癫”[29]。作为理性的对立面,疯癫不仅是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也象征着对规范的逾越和对理性的抗争。进一步来看,瑞娜的疯癫促使小说的情节逆转,在错觉的迷雾与虚假的混乱中,她摆脱了黑人女性的不自信,直呼:“别碰我!我恨你,鄙视你!”[11]288同时,也有勇气直面失去的爱人,“你不爱我!”[11]288然而,这种“无知与自由”的结合与杰斐逊传达的意思恰好背道而驰,讽刺之余也发人深省。
四、结语
切斯纳特呕心沥血近十年时间创作名为《瑞娜·瓦尔登》的小说,几经易稿,终以《雪松后的房子》付梓,他期待这部小说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30]。虽然小说微妙地触及“种族装扮”、种族融合等主题,但其落脚点在黑人女性教育的问题上。透视瑞娜的个人经历,从她接受的白人女性教育到从事黑人教育事业,不难发现小说映射整个美国女性教育的通病——种族与父权社会的歧视性对待。切斯纳特鼓励黑人女性接受教育,以期“为黑人种族取得更多的进步扫清路障”[2]381。因为相较于白人女性,一旦结婚就不再外出工作,黑人妇女即便结了婚仍需工作谋生,她们的成功对于黑人种族来说影响卓著。然而,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与“种族提升”的使命使黑人女性教育一味地以家政服务和黑人教师等职业教育为目标,忽略她们进一步的发展。对于瑞娜等黑人女性来说,虽得以接受教育并陆续进入学校、医院、工厂等场所发挥作用,却无法摆脱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对待,从成为“家庭天使”到沦为男性猎物,她们甚至无法得到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作为黑人女性的典型代表,瑞娜的悲剧为19世纪美国黑人女性教育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