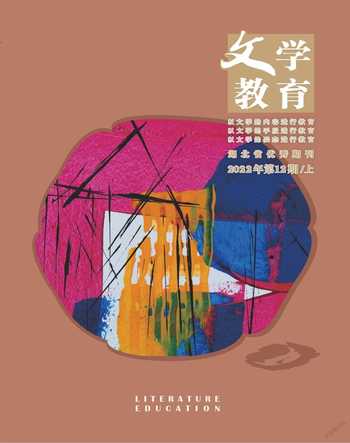穆旦诗歌中的“我”:一个不能完成的自己
王艳春
内容摘要:穆旦诗歌中一个现代的“我”在个体生命的认知上是一个“不能完成”的自己。它体现在对“我”的诞生经验、“我”的成长经验(爱的历程)及“我”的肉体经验的表述中,从而叙述一个现代的“我”存在于世界的荒诞感受。穆旦诗歌中这个内省的“我”,确立了现代生命意识,其叙述的是形而上的哲学观照下一个现代的“我”的精神历程。
关键词:穆旦 穆旦诗歌 “子宫”意象 爱的历程 时间意识 肉体经验
穆旦诗歌对现代性的诉求及其卓越的艺术表达确立了其诗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梁秉钧在《穆旦与现代的“我”》这篇评论文章中,将穆旦诗歌中的“我”与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我”及中国早期新诗中的“我”区别开来,赋予了现代的品质。穆旦诗歌中的“我”不再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含蓄”的自我,甚至“消失”的自我,也不再是中国早期新诗中“直接”的自我。穆旦诗歌中一个现代的“我”是“不完整、不稳定、甚至带有争论性的”。[1]本文试从“我”的诞生经验、成长经验(爱的历程)、肉体经验等三个方面探寻穆旦诗歌中“我”的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历程。
一.“我”的诞生与“子宫”意象
在穆旦的诗歌中,对一个现代的“我”的叙述及其“我”在现实处境中的精神受难是与“子宫”意象密不可分的。“子宫”一词在穆旦诗歌中多次出现。王佐良说“子宫”二字“在英文诗里虽然常见,在中文诗里却不大有人用过。在一个诗人探问着子宫秘密的时候,他实在是问着事物黑暗的神秘”。[2]
“子宫”是生命的孕育之所,是人类生命起源的发祥地。实际上,不止是英文诗里,西方许多现代主义诗篇都有对“子宫”的叙述。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3]
而在穆旦的诗歌里,“子宫”不仅指向与人类生命源起的隐秘联系,它还有另外的隐喻。也就是说,“子宫”不仅孕育生命,还暗示着人类命运的一个缘由,从而探知人的孤独与残缺的存在现状。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居所“即是母亲的子宫即第一个住所的替代物,在子宫里他是安全的,且感到满足,他可能此后一直渴望着它”。[4]穆旦的《我》(1940年11月):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5]
穆旦在《诗八首》(1942年2月)中也有对“子宫”的叙述: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穆旦的诗歌中,“我”与“子宫”构成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家园的关系。作者用“割裂”一词形容“我”与“子宫”的分离,实质上就是“我”的诞生与母体的分离形成的一种残缺的状态。因而才会有: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7]
日本学者秋吉纪久夫说,“在《我》这篇诗中流露出的‘焦躁感和‘危机感象征着一种痛苦。这是人类自有史以来永远无法解脱的痛苦。正因为如此,世间的每一个人只能从彻底的孤独和绝望的深渊中,伸出两只手,紧紧抱住‘自己幻化的形象”。[8]王佐良说,《我》这首诗“所涉及到的有性,母亲的‘母题,爱上一个女郎,自己的‘一部分,而她是像母亲的。”[9]王佐良说这使他想起1936年与穆旦在北平城外的一个校园里读的柏拉图的对话。《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的《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谈到爱神时说“我们每人只是人的一半,一种合起来才见全体的符,……每个人都常在希求自己的另一半,那块可以和他吻合的符”。[10]正如英国玄学诗人赫伯特在诗歌中作这样的描述:
于是当我们将要离开世间,
你和我都将再不存在,
作为相互的不解之谜,
每个人将是两个人,但两个人又仅仅是一个人。[11]
实际上《圣经》中也是这样描述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亚当与夏娃合成一个整体,才形成一个完整的“我”。诗中的“我”,是亚当在寻找自身的肋骨——他的另一部分生命,然而终究是虚妄: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12]
因而才会有: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13]
也就是说,我的“孤独”与“残缺”的状态最终还是肇始于“我”与母体的分离。这是人的“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由于和起保护作用的母亲相分离”。[14]“我”与母体的分离,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残缺”的“我”,另一方面形成了这个残缺的“我”的被放逐。对于人的被放逐的命运,一如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穆旦是用“锁”这个词来表现人于“子宫”的家園进入永远的“荒野”;“死底子宫”也正是人对家园的失去,而被放逐于甚或囚禁于“荒野”的描述,正如艾略特所描述的人类在荒原中的迷失的命运。
因而,在现代诗人穆旦看来,“我”的诞生,同时就是一个残缺的“我”开始精神的流浪。
二.《诗八首》中的成长经验
穆旦对一个“不能完成”的自己的叙述,不仅来自于“我”的“诞生”经验,还来自于“我”对爱情的体认,亦即“我”的成长经验。在“我”的“诞生”经验中,“我”与母体的分离,形成“我”的孤独与残缺的存在状态。而在“我”的成长经验中,“我”对爱情的追寻,实际上则是一个不断地想要重新完成自我的过程。本节将通过对穆旦重要作品《诗八首》的解读,来阐述在现代时间意识的观照下,穆旦诗歌中一个“不能完成”的自己在爱情中的历程和成长中的经验。
《诗八首》的第一首: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15]
在“你”、“我”的成长经验中,面对“成熟的年代”,男女主人公对爱的体验却截然不同。“我”(男性)体验到的是爱的燃烧——激情,而“你”(女性)体验到的却是爱的“火灾”——恐惧。诗的开篇,就否定了“你”“我”爱情的和谐与圆融,而将之置于一种对立的张力中。袁可嘉说穆旦的《诗八首》“用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来对待多少世纪以来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其冷静的、自嘲的口吻在新诗史上是少见的”。穆旦的情诗“是现代派的,它冷酷尖锐,使人感到刺疼。”[16]
虽然对于爱情的审美体验从来都是与“永恒”“天长地久”的时间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穆旦却使诗歌接受者期待受挫。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17]
穆旦揭示了“永恒”背后的真实,那就是时间的永续性带来的无数变化的可能。此时“你”“我”的爱情是确定的,然而却是“暂时”的,而彼时“你”“我”的爱情需要不断地更新来应对时间的变化。
《诗八首》的第二首: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18]
“水流山石”有很多的隐喻和暗示,水流山石本是自然之物,如天地万物的自然运行,而人的生命的孕育与诞生,本也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水流山石”又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好似流动的时间,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里“沉淀”下的“你”“我”——相爱的两个人。
“你”“我”的诞生与成长都充满无数的可能。而“变形的生命”一方面对应于“死的子宫”,一方面又对应于“无数的可能”。而“无数的可能”正来自于时间的无穷变化。在时间的巨流里,“我”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自己。因为“完美就其定义来说只能无限地重复自己,它否定了作为整个西方文明基础的不可逆时间概念”。[19]因此,人永远无法做到与“永恒的结合”。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20]
唐湜说,“这是一章生命的历史,没有起点,也无从终结,‘水流山石是自然的现象,而我们却由之从‘死的神秘里出生,生命永远在变形,却没有终结任务,完成自我的理想……我们简直无法确定自己的爱与信任,因为自然不断使我们新陈代谢,‘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21]而只有“我的主”却得意于自己的创造,因此又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我”,使爱情不具有永恒的性质,爱情一方面变得更为丰富,一方面又更加“危险”。当“我”为爱情而痛苦与困惑,不断地寻求,又不断地背离,而对于“我的主”来说,这不过是他所操纵的一场可爱的游戏罢了。
《诗八首》的第五首[22],相较于前几首对时间变化的敏感,在这一首中,仿佛心理时间被无限延长了。“积累”一词呼应了第一首的“沉淀”,使得爱情在时间中的不确定性获得了一种延续与肯定。爱情如自然万物一样顺应时间的缓慢流淌。“时间”本无始无终,而“我”的爱情却始于时间的“开端”,使爱情在现实中的境遇获得了心理时间的肯定,从而也使爱情获得一种形而上的超越。
一切在它底过程中流露的美
教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23]
因为这一切在自然中都是“过程”。而爱的过程中“流露的美”,使“我”不断地需要超越时间的羁绊,在时间中成长、成熟,爱的“美丽”教“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因而《诗八首》的第五首从时间上的暂时舒缓,进入第六首时间变化的紧张状态:
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24]
因为“我”与“你”都在不断地变化与生成中,因此“我”不仅要应对自己在时间中的变化,还要应对“你”在时间中的不断变化,因此相同则“溶为怠倦”,而差别又“凝固着陌生”,不仅爱情经验无法获得圆满,而且是在“危险的窄路”上旅行。“我”与“你”都不断地分裂、添加无数的“他”。“部分”与“部分”的融合已不是原来的“整体”,因而“你”“我”的爱情无法“永恒”,而是在不断地“寻求”又不断地“背离”中忍受痛苦与孤独。
如穆旦的《隐现》[25],对于爱情的“谎言”,一直在人类的历史中,在“你”“我”“他(她)”中不断地重复。“这是一种冠冕堂皇地把自己理想化的狂热,一种巧妙地编造自己谎言的醉态……而当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他一定善于向自己撒谎,撒关于自己的谎:他似乎面目一新了,更强壮、更丰富、更完美了,他是更完美了……”[26]而穆旦却揭穿这个谎言,告诉人们爱情痛苦与孤独的真相:因为人无法做到与“永恒”的结合,因而爱情其实是被限制在“永变的事物里”,也就是说,被限制在变化的时间里。而诗中对“她”的“宽恕”就是对人类的谅解,就是对人类的渺小与时间的永恒之间的矛盾的悲剧性体认。
《诗八首》的第七首:
那里,我看見你孤独的爱情
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27]
爱情原是相爱的两个人所共同拥有的生命体验,它原是将“你”与“我”融为一个整体的“符”,也就是说,应由部分归于整体。在读者的审美视域中,所接受的常常是像当代诗人舒婷在《致橡树》中对爱情的言说方式: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28]
在舒婷这里,爱情是“求同存异”的。而在穆旦的诗歌里,它竟是“孤独”的,是“求异存同”的,它更多地正视“异”的存在。它是“你”的爱情与“我”的爱情,而不是“我们”的爱情。它“笔立”着,和我的“平行”着生长。“笔立”与“平行”仿佛说出“你”与“我”在此时拥有了相同的“爱情”,而实质上却暗示了即便是爱情也不能使人脱离孤独的生命真相。
由于有一个不断变化的“你”“我”,爱情的永恒就如生命的永恒一样,在经验的世界里只是一个神话。
《诗八首》的第八首:
再没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29]
“接近”,说出了残酷的爱的真相。这个“接近”,其实是对应了第七首的“孤独”“笔立”“平行”。虽然“再没有更近的”了,但恰恰暗示了爱的悲剧:无论“我”与“你”多么“接近”,但实际上都是无法真正融为一体。此时的“接近”已是爱的最大近似值了,生命中的所有的“偶然”定型为“我”与“你”此时的爱情。使爱情完满的可能不是爱情本身,使两片“情愿的心”相同的,不是“我”与“你”,而是自然的“阳光”。因而我们就可以理解爱的悲剧与生命的悲剧一样,它无法自我超越,它甚至被自我禁锢在生命的有限里。
等生命的“季候”一到,“你”“我”就要各自飘零,而“赐生”我们又收回我们的生命的“巨树”——永青。而我们不能完成的爱情,在造物主的“不仁”的“嘲弄”和“我们”的“哭泣”中化为了永远的“平静”。有论者认为《诗八首》缺少“刻骨铭心”的爱的体验,或认为《诗八首》过于“理性”,甚至偏于“冷漠”。这可能是没有真正理解穆旦诗歌的精神内质与现代性诉求,“摸到的恰恰是暖水瓶的外壳”。[30]穆旦诗歌里的“我”,是将爱的对象看作自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是一个“不能完成”的自己。而在正视“你”“我”的有限性的同时,则对“爱情”有着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追求。因而对于《诗八首》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诗八首》是将爱情的体验上升为生命的体验,并希求在自然的怀抱中获得永恒意义的杰作,是试图在对造物主的“不仁”的“嘲弄”中对人的悲剧命运所作的“抵抗”与升华。
三.肉体纳入“我”的历史
艾略特“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总是嫌弃世俗的、物质的、肉体的因素的。他从来不用美好的诗句来歌颂它们”。[31]不同的是,穆旦在自己的诗歌中确立了肉体的地位与价值,并将在文明社会中被忽视和压抑的肉体重新纳入“我”的历史。在穆旦的诗歌中,“我”是时间巨流里的细沙,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自己。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肉体”。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
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32]
经验世界是不被肯定也无法肯定的。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唯一被真实感知的是自我的肉体。因而自我的肉体是我们在虚幻、变化的经验世界中坚定的“岩石”和心灵的“岛屿”。穆旦认为是肉体(而不是思想)决定了“我”的存在,从而将肉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
摇吧,缤纷的枝叶,这里是你稳固的根基。[33]
穆旦否定笛卡尔哲学的“我思故我在”。认为“思想”是压制肉体的“敌人”。
但什么是思想它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
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
自由而活泼的,是那肉体。[34]
肉体不仅是被真实感知的,更应该是自由的:
是在这块岩石上,成立我们和世界的距离,
是在这块岩石上,自然寄托了它一点东西,
风雨和太阳,时间和空间,都由于它的大胆的
网罗而投在我们怀里。[35]
穆旦对肉体的发现和对肉体的赞美融入他的诗歌中,即“我”的历史叙述中。穆旦的诗歌“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 王佐良说,“这感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36]。
穆旦写于1937年的《野兽》: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37]
在民族灾难的整体背景下,穆旦用“身体思想”刻画“野兽”——也就是“我”的民族的血性与“复仇”的勇力。唐湜说穆旦的基本精神是“自然主义”的。“他的自然主义是溶入了自己的血肉与意识,特别是潜意识的,自然主义只是他的自觉的强烈表现。他把自我分裂为二:自然的生理的自我,也就是‘恶毒地澎湃着的血肉,与‘永不能完成的‘我自己,心理的自我,使二者展开辩证地追求与抗争”。[38]
穆旦的《春》(1942年2月):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39]
在经验的世界中,肉体的历史是被压抑的歷史。而穆旦却拥有自觉反抗的意识,努力使自然的“我”(“本我”)与现实中的我(也就是“自我”或“超我”)统一,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形成悖论的力量。“我”肯定“欲望”的美丽:在草上摇曳的“绿色的火焰”与反抗土地的“花朵”,渴望“被点燃”。这就是二十岁的“肉体”,然而是“紧闭”的。虽然“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自然的肉体已经成熟,但却是“无处归依”,只能“痛苦着”,等待“新的组合”。“我”对肉体的自觉意识,不可避免地遭受现实原则的压制。然而“我”的肉体的欲望“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却是自然的歌吟与抒写。
穆旦《诗八首》的第三首: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40]
上一节分析了穆旦《诗八首》。王佐良说,“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感官的形象里”。[41]唐湜也说,“八章情诗就是这爱的燃烧,这里,自我分裂与自然主义的恋爱观仍然贯穿了诗句。”[42]穆旦诗歌里的爱情,并不排斥肉体欲望的自由抒写,因而写出真实自然的人性。“小小野兽”“春草一样的呼吸”,说出肉体的欲望也与自然万物一般,是生命的自然而美丽的过程。因此“它”要“你”规避现实原则的束缚,“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爱欲不断被压抑的历史。因此,所谓“自我分裂与自然主义的恋爱观”,也是由于本我要不断地与自我、超我作斗争。“大理石的理智殿堂”“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它底固执,我底惊喜”,都是本我对自我、超我的超越与妥协。
穆旦的《发现》(1947年10月):
你把我轻轻打开,一如春天
一瓣又一瓣的打开花朵,
你把我打开像幽暗的甬道
直达死的面前:在虚伪的日子下面
解开那被一切纠缠着的生命的根;[43]
李瑛这样评价穆旦的诗:“读穆旦的诗,比一个大的快乐还要丰富,它给我们蕴蓄着的爱情,快乐和荣耀以适当的表现;我们不成熟的思想,我们隐蔽的心情,我们被压抑的欲望和需要,将一齐从他的作品中,启示出来,赋予和谐和完整,这种给我们过重的情感,给我们高度的激情以解放的,就是我们欠给一切伟大抒情诗的债务”。[44]这或许也是穆旦的爱情诗能够超越中国诗歌史上大多数的爱情诗的缘由吧。在这里,“我”原先是“沙粒”,是“你”把“我轻轻打开”,使“我”发现并感知肉体。于是肉体的发现以及“我”对肉体的奇异而细微的感知,化入生命感知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直达死的面前”,使自我对肉体的确认上升到生命意识的高度。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肉体的历史是被压抑的历史。穆旦在《我歌颂肉体》中说:
但是我们害怕它,歪曲它,幽禁它;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的生命认为我们的生命,
还没有把它的发展纳入我们的历史,
因为它的秘密远在我们所有的语言之外。
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
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我的上帝。[45]
穆旦将肉体纳入“我”的历史,并置于“美的真实,我的上帝”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湜说,“他所追求的正是这个在语言之外的美的上帝,沉默而丰富的自然,与其说要把它的发展纳入我们的历史,不如说要把历史‘还原为自然”[46]。但是“我”在经验世界中肉体的被感知,并不能够真正“‘还原为自然”。肉体的“发现”并不代表肉体的“实现”,它的秘密还“远在我们所有的语言之外”。因为我们“害怕它,歪曲它,幽禁它”,“把个体从……各种压制中解放出来的现实可能性越大,想维持这些压制并使之合理化,以免现存的统治秩序被瓦解的要求也就越强。文明不得不抵御自由世界的幽灵。”[47]
穆旦非常清楚,在经验的世界里,“我”还并没有能够真正触摸肉体所有的“秘密”。也就是说,肉体在“我”的历史中并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肉体“受制于现有的‘思想”,“在现实规则失效之前……不可能在经验中使肉体(被围者)重获自由。”[48]“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光明”代表的是超验于现存世界的理想,而“黑暗”正是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穆旦将肉体的“美的真实”看做“我的上帝”,而上帝只存在超验的世界里,实质上也就是指出肉体的美的真实并不存在于经验世界中。“沉默而丰富的刹那”是肉体在经验世界被超越的一刹那所见的丰富。但另一方面,“我”对肉体的感知依然停留于经验世界之中,而无法认识超越于经验世界之外的“真实”的肉体。“由于事实上存在着抑制,人们经验到的世界是有限经验的结果”。[4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穆旦将肉体纳入“我”的历史,并不能够使“我”真正“完成自己”。
参考文献
[1]梁秉钧:《穆旦与现代的“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9][36][41]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原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引自: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3]里尔克:《里尔克诗选》,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4]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弗洛伊德文集》第8卷,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
[5][6][7][12][13][15][17][18][20][22][23][24][25][27][29][32][33][34][35][37][39][40][43][45]穆旦:《穆旦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8]秋吉纪久夫:《祈求智慧的诗人——穆旦》,《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杜运燮等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11]转引自: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14]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文集》第6卷,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
[16][31]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引自作者论文集:《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9]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1][38][42][46]唐湜:《穆旦论》,《中国新诗》,1948年第3、4集,引自: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26]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8]舒婷:《舒婷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30]刘兆吉:《穆旦其人其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杜运燮等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44]李瑛:《读穆旦诗集》,《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9月27日,引自: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47]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48]李荣明:《穆旦诗歌中的价值语言分析》,《现代中国(第3辑)》,陈平原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9]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
基金项目:2020年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2020WTSCX298);广东省教育厅2020年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JGGZKZ2020130);2020年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研科研重点项目(2020JY06);2021年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质量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类项目(2021SWZLGC20)。
(作者单位: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