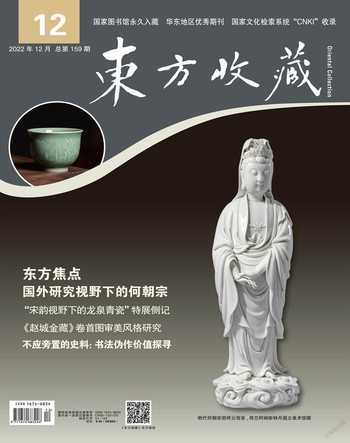敦煌写经影响下的西夏文写经书法风格
摘要:写经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相对独立的书体,西夏佛教文化的活跃,带动其写经书法的兴盛。西夏与敦煌同处“河西走廊”,时空的差异与统一为这两种文化带来区别与联系。本文着眼于西夏写经书法,通过比较西夏与敦煌写经在笔法、结构与书法风格中的异同,进而探寻西夏文写经书法中的敦煌遗风。这是根植传统,立足创新的过程,揭示了西夏文写经书法对于多民族文化的汇聚与趋同。
关键词:写经书法;笔法;结构;书法风格
“河西走廊自凉、魏经隋、唐,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有很大影响,对迁到这一地区来的党项族,有着潜移默化和直接继承的关系。”[1]西夏书法是中国书法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地处河西走廊的敦煌文化与北宋年间迁至此处的党项族所形成的西夏文化,在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其书法风格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二者写经书法的笔法、结构进行比较,探寻相距数百年的敦煌与西夏写经书法在笔法、结构上有何联系?西夏较之敦煌写经书法是否有创新之处?二者在书法风格间有何内在关系?未尝见有人将二者进行深入比较,进而管窥西夏写经中的敦煌遗风。笔者愿陈刍荛之言,体悟西夏写经的书法特征与其蕴含的独特魅力。
一、写经书法的时代背景
“文字在书写中具有某一共同特点或具有某一种风格,并能自成体统者,称为一种书体。”[2]在书录经卷或经折时所用书体,风格统一,蔚然成风,称为“写经体”。敦煌写经书法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秦始皇八年(前239)以前[3]。写经字体也经历了从古隶到楷体的演变,这个过程是写经体的楷化,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写经作品,如晋代《增一阿含经第廿七卷》、北朝《金光明经卷舍身品》、唐代《三阶佛法卷第三》等,形成了灿烂恢宏的“敦煌体”,是写经书法的瑰宝。北宋宝元元年(1038),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新王朝[4],后世称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形成具有党项族特色的西夏文化。“春正月癸卯,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从之。”[5]由于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常向宋求赐佛经,使得佛教在西夏广泛传播,西夏文字创制不久,大规模翻译佛经的行为就已经开始,与之伴随的是大批量写经本的诞生,写经书法也因此繁荣。据《国藏黑水城文献》收录可知,西夏文佛经多为刻本与活字本,仅《大般若波多蜜多经》(亦称《般若经》)为手写本。其经卷数量多、书写技艺纯熟、风格面貌多样、墨迹手写等特点,也使得研究笔法、结构与书法风格上更为直观。现从笔法开始,试较二者的联系。
二、敦煌写经与西夏写经笔法的“异同”
“书势自定时代”[6],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有不同的书法风格与用笔习惯,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决定着其书法发展的方向。如今我们常通过“点横竖撇捺折钩”,对书法作品中单字的笔画与运动轨迹进行拆解、分析,其实也是对整个时代笔法的剖析。
在西夏文《般若经》写本卷第九十三、一百一十三中,横画尖峰落笔,在线条中段略提笔,至末尾处回锋收笔,略作向下弯势,形成两端重、中间轻的线形特征。横画在晋代敦煌写经作品中,如《法本斋经》《诸佛要集经》等,逆锋起笔,圆笔方笔兼用,逆入平铺,线条圆厚,头粗尾细,饶有隶意,但未见西夏文用笔根源。至北朝敦煌写经《金光明经卷舍身品》,这种两端明顯、中段挺拔的趯笔衄锋楷书笔法,才初具形貌。此卷为隶书楷化较为完备的作品,虽楷书笔法运用仍未娴熟,但对楷书笔法的从何而来,西夏书法用笔根植何处指明了方向。
撇画写法在西夏书法中则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起笔处侧锋铺毫,行笔至笔画尽处,将笔锋完全送出,呈上粗下细的形态。撇画的第二种写法,在卷第二百九十三中是侧锋起笔,行笔至结尾处向左上方送出笔尖形成一种勾挑的态势。这种写法可视为西夏书家在笔法上的创造,但这种创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晋代《增一阿含经第廿七卷》写本中,撇画锋毫尽处往往回笔收,且回锋后留下一个肉眼可见的上行弯弧[7]。这是较为早期的敦煌写经作品,当时字体还未完全楷化,其间夹杂隶意。
捺画也是西夏写经体在笔法上颇有创新的地方。欧阳询在《八诀》中对捺画写法有明确的记载:“一波常三过笔”[8]。在西夏写本《般若经》卷第二百八十三中,捺画至笔画尽处顿驻,略提笔二次出尖,笔势向下弯呈蟹爪状。这是在“三过笔”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再创作,流露出一种奇诡、俏皮的书法风格。在西夏写经体中,反捺则用向左的“翻笔”代替,“翻笔”是笔尖运动至笔画尽处,向上翻转后至下出锋的用笔方法。“翻笔”常见于行草书,起贯气作用,西夏写经将其运用于楷书书写,这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翻笔能够传递笔势中蕴藏的动能,是连接上下字的桥梁,极大增强了楷书的流动性,为端正谨严的写经体注入了活力。“不见古人”的笔法选择,打破书法用笔的思想桎梏,体现了西夏人民颇具创新、勇于变革的精神。
通过比较敦煌写经与西夏写经笔法的异同可知,西夏写经体笔法并非凭空臆造,其根植于不同时期敦煌写经作品当中。西夏王朝与敦煌位处同一“空”,但并非同一“时”,时空的交错使西夏民族在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上有了更多的选择。由于西夏境内党项、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混同杂居,通行番、汉、吐蕃、回鹘等多种文字,尤与中原汉族文化往来密切[9]。所以在用笔风格上既有敦煌遗风,同时也有宋代时人的笔法风格。西夏文字笔画繁多,笔法的运用难度增大,恰当的笔法选择需要西夏书家具备过硬的书法素养,加之时风的杂糅,西夏写经书法风格洒脱纵逸,独具一格。
三、西夏写经结构的“出新”
“六书”是传统汉字的造字方法,汉字结构最初源于自然,讲求“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因为以自然界做参考诞生的字体需要有漫长的演变进程,而西夏王朝历史较为短暂,不足以使西夏文字经历完整的字体演进。党项人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基础上,按汉字的造字规律,形成“单体字”和“合体字”的造字方法[10]。所以西夏写经书法在结构面貌的呈现上,也体现出与敦煌写经的不同之处。
通观西夏《心经卷》第一百一十三、第二百九十三等,单字结构大抵都是近似正方体的结字。而在敦煌写经体中,如《阿含经卷》《诸佛要集经》等晋代的写经作品,字距紧密,笔画较多却不显得拥挤,有三点原因:一是结构紧密,中宫收紧;二是方正与纵长字交替间杂,打破了单字字势的单调;三是笔画多与笔画少的字所据空间不一,左高右低式结字居多,字周围就留有一些空间,显得疏密有致[11]。这是隶楷过渡时期的写经作品,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结体上都中宫紧收,结体方正。二者在结体上的不谋而合,说明西夏书法并非仅受时代书风的影响,在取法上也没有脱离书法风格演进的主流。
但二者也并非完全相同,如卷第一百一十三中,采取收右放左的结体方式以达字势平衡,以左边舒展的笔画将字的重心拉向左侧,打破因笔画密集重心端正所产生的呆板势态。整体也因这种结体上“因字适宜”的改变,左低右高,在字周多出空间,故密中有疏,轻重节奏鲜明。另一种则是在端正结体中,拉长右下方所占整个字的比例,这种结体与晋代敦煌隶楷时期结体较为相似,它是对隶楷结体的延伸。用更为夸张的表现形式,突出了捺画的延展程度,打破结构中过于平衡的部分,在遵守楷书法度的同时,又在工整中谋求欹侧。这是一种根据字体需要产生的结构变革,因笔画数量成倍增长的西夏文字,原有的结体方式已不再完全适用。经文需章法统一、排列有序,正是这种既具严格标准又要表现书家书写性情的时候,往往会带来无限的创造力,这种充满创新性的结体方法应运而生。
据记载,西夏字,“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八分”是东汉出现的新体隶书,“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12],特点是结体方正且伴有波磔。而西夏文字结构整状若“八分”,结体方正的笔画却已是成熟的楷体。近年来对于西夏书法的考证中,一直未发现西夏隶书,卢桐在《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中认为西夏未有隶书[13]。究竟是未发现还是西夏书法未创制隶体,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就上文对笔法结构的分析,我们可根据楷体上溯西夏文隶楷乃至隶书风貌。在结体上,我们取“八分”的方正。用笔则以敦煌晋代写经隶楷书中逆锋圆笔取代西夏书法以完全楷化的起笔,将瘦硬的转折变为圆滑流畅的弧线,最后把字结构右半部最长的笔画渐加波磔,以增华饰,便是对西夏隶书面貌的初步还原。王羲之云:“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14],西夏书法虽不像敦煌写经那般有隶楷化进程,但在西夏楷书中试融入隶意,进行这种逆推式还原,为西夏隶书面貌的追溯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新思路,同时也是对西夏结构出新的更深层次的诠释。
四、西夏写经的“法”与“意”
书法风格研究是研究书体绕不开的问题,“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15]每个时期都有明显的历史特征与审美意趣,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时不能脱离文化背景,也不能仅对技法展开论述。书法风格形成的原因有外在与内在两方面因素,外在因素是笔法结构形成的直观面貌;内在因素则是在文化大背景与人文情怀中形成的,往往能反映出时代的风气与书家的性情。因党项族常年征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在风俗还是在文化中都表现出奔放豪迈的情感,当这种情感作用于书法中,西夏书法便形成一种率意劲健的风格特征。
“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敦煌与西夏同为写经体,而抄经则为这门字体赋予了严格的秩序。这是一种章法上的限制,经卷的书写者要秉持恭敬的态度以及规矩的章法排列书写。在书法艺术中,其秩序性表现在字的法度中。“上有所好,下必随之”,统治者的喜好,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在唐代楷书多用于官方文书,所以楷书在书写上要求严谨工整,一丝不苟。这种严苛的法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书家性情的表达,直至宋代才逐渐摆脱法度的束缚,以表达书家性情为书写的主要目的。苏轼说:“书出无意于佳乃佳”[16]“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17],在宋代形成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风,将书法作为表达书家性情的手段,意图在法度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自由——精神自由。西夏体以敦煌体为源头,身处宋代,与中原交流频繁,时代书风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然渗透。这种文化性约束与书法自身的法度,并没有打消西夏书家挥毫泼墨,表情达意的热情。在西夏体中,其用笔如同长枪战戟,沉着痛快、爽利挺拔,给人以俊朗劲健的感受。排列整齐、方正的结体,与排布有序的笔画共同营造出一种沉稳大气、井然有序的风格。这种秩序性是党项民族思想与社会背景统一的结果,是西夏书家在尚武社会熏陶下的情感表达,是对人们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敦煌写经在隋朝经南北书风的融合,在北凉体与晋代隶楷体中融入南方秀美清逸的书风。这种从北凉体转化而成,带有简牍风味的楷书一直沿用至唐以后。经朝代的更替,宋代书风也是对前朝书风的继承与吸收。那么身处宋代的西夏王国,在书法风格上虽未像敦煌体一样经历南北书风的融合,但二者在写经书法上的内在联系,使其在间接的书风碰撞中,让西夏有更大的空间发展自己的写经书风,使得它能够从历史悠久的书法文化中跳脱出来,没有完完全全当作汉字书法的延续,更像是一条河流在蜿蜒曲折下的不同分支,虽涓细,但动人。
五、结论
在西夏两百余年的历史文化中,能够迅速创制文字,并以纯熟精练的笔法书写经文,离不开对敦煌写经笔法的继承与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选择与创新。西夏书法并非仅是一种文化的孤芳自赏,它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广泛地吸收和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取其精华。多民族的智慧与经验被吸收采纳,最终形成与西夏文字高度匹配的书法风格。这是根植传统、立足创新的过程,也是西夏文写经体对多民族文化的汇聚与趋同。
参考文献:
[1]史金波.西夏风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329.
[2]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 [M].中国香港: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01.
[3]楚默.敦煌书法史·写经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03.
[4]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9-17.
[5]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一),仁宗宝元元年(1038)正月癸卯条[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翁方纲《跋汉朱君长题字》[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00:17.
[7]楚默.敦煌书法史·写经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44.
[8]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欧阳询《八诀》[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98.
[9]崔宁,姜欧.从中国藏西夏文献看西夏文写经书法风格及成因[J].西夏研究,2020(02):49-55.
[10]柴建方.古朴的石碑 奇异的文字——“西夏碑”及西夏书法简评[J].中国书法,2005(10):38-41.
[11]楚默.敦煌书法史·写经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51.
[12]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684.
[13]卢桐.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J].宁夏社会科学,1986(04):73-79.
[14]上海書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王羲之《书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28.
[15]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706.
[16][17]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苏轼《论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313-314.
作者简介:
刘智源(1997—),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