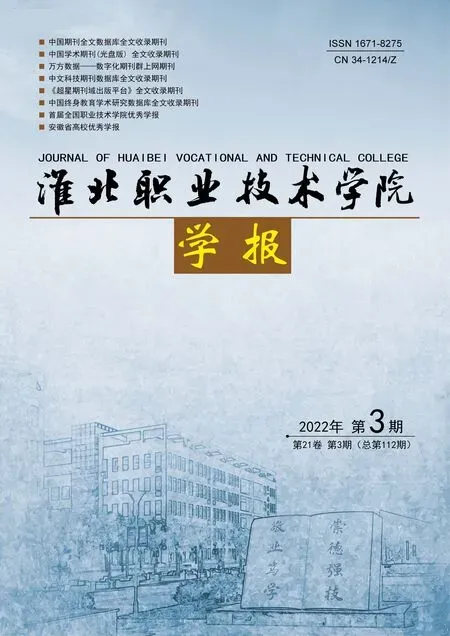诗与史的建构:论《空山》的古典文学传统
李晶晶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在追逐快感与速度的时代,阿来耐得住寂寞,用心写作精品。虽然《尘埃落定》取得巨大成功,但是,也没有打乱阿来的写作步调。伴随着读者期待的目光,阿来的又一长篇小说《空山》(三部曲)问世。小说《空山》描写一个普通藏式村落——机村在20世纪后50年经历一系列政治变革,是一部极具“史诗性”作品。
得益于独特的地域环境及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阿来写作受多种文学资源的浸润,其中:包括藏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欧美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以往研究多关注民间文化资源以及阿来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方面,而忽视了中国古典文学资源对阿来写作的影响。阿来直言“我非常喜欢诗经与汉乐府里那种情感与表达完全一致的东西”[1]23,这说明古典文学资源及审美品格是研究阿来及阿来作品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作为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阿来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自然而然的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传统。”[1]23追溯中国文学伟大传统:一是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抒情传统;二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传统”。诚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的材料。”[2]经过十年的酝酿与打磨,继《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一长篇力作《空山》,以其“有情”心灵的“诗性叙事”,以及为“机村”作史的实录精神显现出对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的追认,其中对普通人的关注,也对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起到示范性作用。这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以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有情”心灵的“诗意叙事”
与王德威的“幽暗的抒情”不同,陈世骧在1917年发表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主要从文本诗学的角度谈论“抒情诗”,认为诗是“歌之言”,“兼且个人化语调充盈其间,再加上内里普世的人情关怀和直接的感染力。”[3]换言之,抒情诗的定义在于“有调”与“有情”的结合。阿来的文学表达从诗歌开始,正如阿来所谈“如果不读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就不能形成对语言的真正认识”[4]。随着阿来思考的深入及诗歌抒情性质的局限,小说成为阿来传播“大声音”的重要物质载体。“虚实结合”的审美意象及“感时忧国”的家国情怀构成了阿来在《空山》中独特的“诗意叙事”。
1.1 “虚实结合”的审美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的范畴,也是架构抒情诗的重要因素。从《周易》“立象以尽意”[5]到《庄子》“得意而忘言”[6],再到刘勰《文心雕龙》“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7],“意”与“象”的关系由分开论述走向整体升华,“意象”作为存在客体表达作者主观之思。阿来以诗人般的气质在小说世界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审美意象,力图营造“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8]梦,是阿来小说常用的意象之一。从表意功能上讲,梦境在《空山》中兼具建构虚境和揭露现实的功用。
其一,建构虚境。《空山》的故事发生在机村,几代人的命运沉浮于历史的“太虚梦境”之中,可以说,机村就是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面对现实的残酷、人性的冷漠、欲望的无限扩张,机村人渴望逃脱“烂泥沼”,在梦境中想象陶渊明笔下“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因父亲的缺席,格拉饱受同伴欺凌;疯癫的母亲使格拉得不到正常的母爱;唯一的好朋友“兔子”也被鞭炮无意间致伤。朋友的离去,机村村民的冷漠、孤立,格拉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当悲伤得不到现实的回应,格拉无奈到梦境中寻找安慰。于是,格拉梦到了春暖花开,梦到了各种颜色的花朵竞相开放,梦到了仙女一般的母亲。然而,梦未醒,格拉就被机村村民赶出机村。“哀莫大于心死”,精神的沉沦是生命最大的悲哀。“觉尔郎峡谷”对协拉顿珠来说,就是理想的“桃花源”世界。在协拉顿珠玄而又玄的古歌和梦中,我们看见了祖先的容颜;看见了国王的城堡;更看见了幸福的姿态。当改革开放发展旅游业的时代到来时,这片美丽的“桃花源”自然就被发现,成了万千经济消费品之一。此时,协拉顿珠的“桃花源”世界也将暴露,最终也丧失其神秘虚幻性。
其二,揭露现实。如果说《尘埃落定》的梦境描写有预示未来的占卜作用,那么,《空山》十四处梦境书写就带有鲜明的揭露社会的功用。文中通过对达瑟与索波人物心理的透视,揭露出现代社会下人的孤独、迷茫。达瑟类似于卡尔维诺笔下的“树下男爵”形象,嗜书如命,终日在树上学习生活。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知识带给达瑟极大的满足。达瑟用梦幻般的神情向人们解释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但是,谁又会相信一位“疯癫”之人的话呢?就像百年前谁又相信“狂人”口中“吃人的历史”是真的呢?古往今来,“先知者”就是孤独的存在。果不其然,当昔日的好朋友达戈为爱而死后,达瑟变成酒鬼,整日在酒吧消极度日,成了机村的“孔乙己”。
阿来凭借高超的写作技艺,使得虚境(梦)与醒境(现实)紧密结合,既飘渺离奇,也不脱离生活。
1.2 “感时忧国”的家国情怀
儒家讲究“仁民爱物”,并将这种入世精神凝结为“感时忧国”的情怀,即关注现实,对社会、国家怀有使命感。作为极具天赋的小说家,阿来敏感且清醒地意识到:消费社会并非单向度的发展,而是在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尤其是生态的危机和人的危机。不可否认,这种“忧患意识”成为《空山》的主旋律。
首先,自然生态的危机。朱熹在《延平答问》中指出“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9]。也就是说,人与物的本性不无不同,皆来自天地,两者为平等关系。而在《空山》中,机村村民淡漠“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毫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究其原因是人们无尽的欲望在作祟。为了修建远方的“万岁宫”,机村人砍去一整面山坡的“神树”,这一举动昭示着几千年以来的人神关系终将断裂;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人们建立伐木场,用电锯将山坡变为荒地,导致下游需要“人工降雨”增加降水量;为了心目中的爱情,达戈撕破了古老村庄与猴子的千年契约,一次性杀死十余只猴子等。无尽的索取终究会迎来报复,自然发怒的后果也不堪设想。漫天遍野的大火导致了湖水的消失,“金鸭子”也随之消失;泥石流冲走了黑土,冲毁了房屋,淹没了公路,最终骆木匠葬身于洪水之中。达戈不堪忍受内心的谴责,丧失了“爱”的权力,机村最后一位“猎人”也遗憾消失。
其次,人的危机。“在机村,人与人的冷漠与猜忌构成了生活的主调。”[10]在《随风飘散》中,“至纯”形象化身的“兔子”被鞭炮无意间重伤,可是兔子是如何受伤的呢?无人能够回答,于是,机村人将罪行强加给格拉。因受到不合事实的猜忌,格拉选择出走。在冷漠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也呼之欲出,外来户与本地人之间的界限,孩子们之间的界限表现尤为明显。久而久之,界限转变为孤独,格拉最终死于谣言。权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造成机村人之间的隔阂。《天火》中森林里熊熊燃烧的大火也比不上政治舞台上的斗争来得猛烈。索波为了获得认可,为了摆脱“外来人”的身份,不断“向上”攀爬,不惜违逆自己的父亲。可惜“生不逢时”,个人的奋斗事业却以失败告终。“物是人非”的现实处境,也使他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机村了。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生态的危机和人的危机,阿来并没有任其无可控制地发展下去,而是采取“自救”的方式,在小说中给读者希望。在《空山》中,阿来不仅塑造了一位“智者形象”——崔巴噶瓦老人,而且还塑造了一位曾经的“伐木者”、如今的“植树人”形象——拉佳泽里。前者仍旧坚持古老的精神伦理,并试图将走向迷途的拉佳泽里拉回正道;后者在经历“国家的改造”与内心的升华后,改过自新,努力还“空山”一片绿色。
2 “轻”“重”之间的“实录”精神
无论是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以一位“傻子少爷”的视角描写土司制度的崩溃,还是新作《云中记》以“祭司招魂”的方式缅怀地震中的生与死,阿来善于将宏大题材简单化,展现出大智若愚的智慧。在《空山》中,阿来以“花瓣式”的结构表现一座普通藏族村落50年的乡村图景。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史记》之所以在文学或文学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就在于其“实录”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对“实录精神”进行概念界定,即“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1]。经过十年的沉寂,五年的非连续性写作,阿来秉持“实录精神”,记录全球化浪潮下新式乡村的重构,创作出“一部为普通人而歌的当代乡村编年史”[12]。
2.1 “其文直,其事核”的记录方式
所谓“其文直,其事核”,就是要真实地记录历史。阿来在《文学的叙写抒发与想象》中辨析在短篇小说写作中“叙述”与“叙写”写作手法区别,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是否真实细致地描写事件。[13]阿来运用“叙述”的手法将机村发生的“破碎”事件容纳在六篇“事物笔记”,以及六篇“人物素描”中。谈及这些小说的作用,冯庆华认为“‘事物笔记’与‘人物素描’是一系列理解时代和作品主题的关键词”[14]。也就是说,阿来将社会历史的巨变通过一系列的新事物、新现象表现出来,为读者真实展现出“大历史”中“机村”。在前现代文明时期,人们通过一张画满“横横竖竖的线条”的图纸结束了对汉语词汇“马车”的想象,当“拖拉机手”出现后,机村的第一位马车夫也成为最后一位马车夫。随着现代文明进入机村,机村经济、政治、社会及宗教的发生了极大转变。《报纸》体现出文革时期“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瘸子》展现了两个残疾人的生活;《水电站》与《脱粒机》写出了“现代的两面性”,即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人们也应该时刻警惕现代性的“反噬”;《秤砣》通过计量单位的改变影射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改革。除此之外,《番茄机村》通过番茄的种植体现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丹巴喇叭》则体现了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无感;《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与《电话》揭示出“机村”的存在像“围城”一样,呆在“机村”的人拼命想要逃离,而“机村”外的人则想要回到机村,躲避外界的艰辛。
2.2 “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取向
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说记录历史应秉持公正的价值取向,既不能盲目地赞颂,也不能一味地贬低。
独特的地域书写使阿来的写作面临两种意识形态的博弈:一种是显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另一种是达赖喇嘛的隐性意识形态。面对现实写作的困难,阿来认为:“作家要有这种准备、能力,甚至有勇气来表达。”[15]25但是,这种“勇气”并非是与意识形态作对,而是“在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时候也要有勇气表达”[15]25。机村是中国万千乡村中的一个普通乡村,机村的历史也统摄于中国的历史之中。相较于“颂歌”,以及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批判与揭露,阿来在《天火》中,歌颂与讽刺并存,既讽刺特殊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又歌颂机村百姓汇聚力量、共战洪流的集体主义精神。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在三个隐身人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隐身人是权力的“代言人”。他们隐藏在“幽暗之处”,但又好像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像影子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例如:在大火案件中,三个关键人物巫吉、格桑旺堆、江村贡布都不知不觉地被抓走了。这很难不让人心生隔膜,但是,没有人敢反抗权力。这可以说是那一代人心里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国家与人民共同抗灾感到欣喜,“人人都准备大赶一场”,则表现出机村村民与国家在灾难面前空前高涨的团结意识。在这场共同抵抗大火的救援活动中,人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惧艰险,坚韧不拔的精神,感染读者,使读者相信在正义的指引下人定会胜“天”。
对史实的记录,对历史文学的表述,阿来始终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兼具史识、史才、史德,秉持“实录”精神,在官方“大历史”的背景下演绎着普通村落的“小历史”。
3 示范性:对中国伟大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西藏作家也曾经用汉语写作对主流文学作出积极的尝试与回应,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主流文学的发展。以徐怀中、刘克、汪承栋为代表的“十八军战士”成为50-60年代西藏文学的主力军,他们以激越的情绪创作出众多控诉旧制度,歌唱新中国、新西藏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和政治抒情诗。20世纪80年代,以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为代表的作品在藏地表达对“根”的追寻,成为“寻根文学”有力的一极;马原敢为人先,引领先锋文学的大潮,创作出《冈底斯的诱惑》等先锋文学经典作品。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文学边缘化及作家的流失,西藏文学创作出现滑坡态势。基于此,也就不难解释西藏自治区文联为何在“纪念《西藏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的活动中将“藏族文学如何与中国主流文学接轨”作为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正如有关学者所认为:“这表现出当代藏族文学与西藏当代文学的焦虑与困惑。”[16]
当下,“文化自信与优秀传统”成为主流文学的“主旋律”。如何做到中国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是当代文学努力与发展的方向。正如王尧所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问题,即讨论当代文学如何传承和创造性转换‘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17]《空山》中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是阿来就这一问题交出的满意答卷。
唐宋之前的史传文学讲究以人物为中心,尤其是以非凡人物为中心,例如:《左传》中的郑庄公、楚庄公等人;《史记》中对帝王将相的记述等。《空山》中对史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则更多表现在对历史中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阿来深处藏地,深刻地感受藏地的发展与生活的变迁。他说:“在这五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那样始终处于时代舞台的中心。”[18]于是,阿来采用“花瓣式”的结构,将机村50年的历史变迁由六部故事时间不同的小说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也展现众多普通人在历史中的曲折命运。可以说,索波和拉佳泽里是小说中最重要的新人形象。抛开历史背景不谈,两个人“向上”的奋斗途径相似,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渴望出人头地。但是,造化弄人,去干部学校学习的机会被央金横空夺取,索波之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拉佳泽里则是奋斗的方向出现了偏差,他通过盗卖木材的“不义之道”发家致富,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显现出阿来常怀一颗同情心。这同情的背后,不仅是阿来对藏地人民的关注,更是对中国普遍现实的关注。可以说,阿来的写作是“行走的写作”。近年来,阿来走遍藏地各处,除了家乡的若尔盖草原,还北至河西走廊,南至茶马古,“在行走中,慢慢就把自己和土地、文化、族群的联系找到了。”[19]可以说,阿来通过行走的意义,紧密连接小说与现实,人与世界,继而进行“超越性”的写作。
李继凯认为:“中国的‘大古代’有其无法遮蔽的辉煌,而其优秀的传统文化恰恰可以为‘大现代’所继承发扬,这样也就被‘重构’和‘建构’成为‘大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也就是说,在文化自信的语境下,作为“后古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自觉地接连中国古典文学的脉络,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作为“现代文化人”的阿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继承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无论是成名作《尘埃落定》,还是如今再版后的《空山》,阿来将创新与弘扬相结合,独具天赋地用汉语写出“藏地中国”的故事,满足读者对“真实西藏”的想象。在“纯文学”复兴时代,阿来应该继续以汉语文学传承者的身份,肩负着“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以“灵动”的诗性撰写历史中的尘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来之于中国当代文学是独特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拥有阿来这样的作家感到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