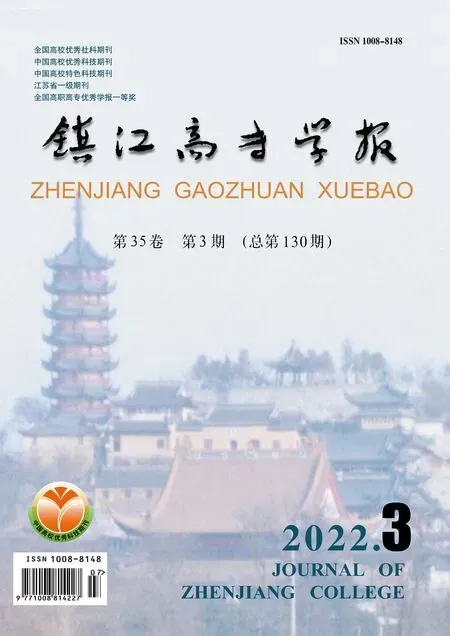论李煜词建筑意象书写
侯飞宇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从日常起居的栖所到登临游赏的名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庭院楼阁。诗词中建筑意象的书写由来已久,远溯《诗经》已能觅见其踪,如“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斯干》),极言门庭之宽、廊柱之高。“诗人多在‘心物交感’说的支撑下将建筑看作是诗词中具有寄情功能的意象符号”[1],诗词中的建筑意象往往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照。正如在“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中,诗人将登高望远油然而生的情感融入诗中的建筑意象,较好地抒发了汉代文人的苦闷与迷茫,激起了后世无数士人的共鸣。“在主观之意和客观之像作用下以直觉思维的形式瞬间形成”[2]121的意象构成了诸多承载着寄托与感慨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五代词人李煜虽存词不多但艺术成就卓越。其词中雨、月、梦等自然意象被诸多研究者关注,而较少被探讨的庭院、楼阁等建筑意象实则也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在36首词作中出现20余次)。个人遭际与创作心态影响了词人的意象选取。李煜于建隆二年(961年)即位,此时南唐已奉宋正朔,偏安一隅。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3]87,深院宫墙成为其创作素材并高频入词,仅以宫殿为例,即有“别殿”“春殿”“瑶殿”“画堂”等多种表述。李煜笃信佛教,史书称“国主与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4]45,诗词里出现的佛寺等建筑意象体现了将佛法视作慰藉的思想情感。建筑意象的选择还受社会美学传统的影响。南唐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大放异彩的文人圈层,隋唐时期登临高楼成为文人的群体行为与重要的创作母题。在此环境之下,李煜词的内容、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五代词人冯延巳词的建筑意象多作为“架构在词人心中的一道难以排解的精神屏障”[5]呈现。中主李璟现存4首词皆含有楼阁意象,词中无论幽怨深锁的高楼还是笙歌凄咽的小楼等意象都能在李煜词中窥见,中主词重慨叹感发、绝少修饰的特征也在后主李煜词中得到继承。
意象作为表情达意的媒介为诗词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着眼点,李煜词中丰富的建筑意象在不同的抒情视角下呈现多样的情感表达,既能从“男子作闺音”的角度倾吐相思闺愁,又能直抒生命体验,表达亡国之悲,呈现“眼界始大,感慨遂深”[3]82的开阔词境。探究李煜词中的建筑意象书写,能更好地观照其诗词创作的审美心理、思想内容、创作风格。
清代李渔曾言:“词内人我之分,切宜界得清楚。……或全述己意,或全代人言。”[6]557晚唐五代时期词多和乐而歌,以女性化的叙述方式表情达意的作品占据主流。李煜前期创作中有不少此类作品,后期创作在题材上有所开拓,其词由聊以遣兴的“伶工之词”向言抒己怀的“士大夫之词”发生转变。
1 对“男子作闺音”创作传统的承袭
在封建社会,女性被视作男性的附庸,生存空间常局限于深闺绣户。文人的文学创作时有涉及女性的生存环境,展现其生活状态,或揣度其心意,或借此表达作家个人的喜怒哀乐。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抒情传统从《楚辞》“香草美人”肇始,经历唐朝戍卒与闺怨题材的蜂起,直接影响了倚声而作的词的创作。李煜的创作也延续了这种抒情传统,相关词作约占四分之一的比重。相关建筑意象主要有庭院、画堂、阑干3种,各自关涉的主题思想呈现不同的面貌。
1.1 庭院:相思怀人
以相思怀人为意旨的词境里高频出现的是“庭院”意象,尤以《捣练子令·深院静》和《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两首为代表。
《捣练子令·深院静》起句“深院静,小庭空”渲染了幽闭冷清的氛围,如俞陛云所言“院静庭空,已写出幽悄之境”[7]45,此句较好地呈现了词中女性的外部生存环境,也深刻反映了女性的内心情感状态。接着一句“断续寒砧断续风”,以捣衣砧声的断断续续点明动作行为的反复停顿,进一步凸显了女子心绪不宁的心理状态。“无奈长夜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用听觉与视觉的联动刻画了因饱受思念之苦而辗转难眠的女性形象。深院和小庭的幽闭与狭窄映射了现实环境的闭塞与主人公身心受到的压抑。词中女性的相思之苦与其在禁锢中产生的无助之感相互交织,使得悱恻缠绵之情表现得更加真切。李白《子夜吴歌·秋歌》中“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一句同样以月夜捣衣砧声为描写对象,侧重远景式的阔大场面描写。《捣练子令·深院静》与之相较,对建筑意象作了更集中的焦点式选取,从一家一户的小庭深院着笔,运笔更为细腻,达到了通过极具艺术概括性的个别形象表现一般意义的效果。
《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中,“庭前春逐红英尽”突出了暮春时节庭前百花凋零的凄凉景象,红英乱落也隐喻了美人迟暮。院落冷清又逢阴雨连绵本就让人感伤,思念之人音信全无更添愁苦。词中的“舞态徘徊”与“香印成灰”暗示了女子的心境,女主人公在痛苦煎熬中陷入更深的幽怨与绝望。
《捣练子令·深院静》和《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两首词皆以相思怀人为意旨,却呈现同源殊途的表达效果。相较而言,前者侧重听觉的表现,后者侧重视觉的传达。在氛围营造方面,前者强调环境的闭锁与冷寂,凸显禁锢感;后者强调暮春残景的萧条与衰颓,凸显衰飒气。可见词人创作视域并未囿于同样的主题思想与相类的建筑意象,在细节处理上各有所侧重,使得其词的情感表达层次更为细腻。
1.2 阑干:孤寂落寞
李煜以女性视角抒发孤寂落寞情感的词中,主要的建筑意象是“阑干”。在《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中,上片描写女子沉溺于饮酒弹唱、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下片描摹其懒于妆扮、不顾仪容的颓废之态。由此可知起句“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中的“闲”非安闲舒适之意,而指长时间孤独带来的百无聊赖之感,起句即奠定了整首词的情感基调。词人以观赏夕阳斜照的“日衔山”起笔,以“黄昏独倚阑”作为照应收束,特意点明倚靠阑干的动作,赋予“阑干”这一意象特别的意味。
首先,阑干作为建筑的防护设施,给人带来可供依靠的安全感。“倚阑”表现了女主人公姿态的懒散与柔美,倚的动作“隐含着弱小事物向更强大的事物寻求帮助”[8],这一隐含意义与封建时代女性居于依附地位的状态相合,阑干象征女子孤独心境下寻找到的带来抚慰感的支撑力量。
其次,阑干具有分隔、阻挡作用,较好地表现了人物的诸多复杂情感。阑干隔开了厅堂内殿和室外的广阔天地,“向外界强调阑内空间的所有权,在内外之间建立明显的分割线”[9]。阑干以内的世界是繁弦急管、酣歌醉舞,阑干之外则是广阔空间下的风吹水皱、斜阳映山。这使得“倚阑”的动作体现了对笙歌醉梦生活的拒斥和背离、对阑外世界的向往与渴望,在本质上凸显为对寂寞无聊生存状态的反抗。同时,阑干具有阻挡的作用,暗示主人公无法从醉生梦死、孤寂落寞的生活状态中完全抽离。
1.3 画堂:热烈爱恋
李煜词中具有明媚色彩的建筑意象并不多见。《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中的画堂意象是不可多得的一抹亮色,展现了主人公对纯粹爱情的积极追求。
“画堂”即以彩绘装饰的厅堂,具有明艳亮丽的环境氛围。夜赴幽会的少女从花明月暗、薄雾笼罩的浪漫氛围中走向装饰精美的厅堂,生动的动作描写和细腻心灵剖白将其紧张与大胆、热情与娇媚展现得淋漓尽致,视觉上呈现的明暗交织也暗示了词中少女的心境起伏。对此词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沈雄《古今词话》引孙琮评:“正见词家本色,但嫌意态之不文也。”[7]33词中用语的确俚俗,涉及的情色因素在六朝宫体诗中也能找到痕迹。然而六朝宫体诗中女性的物化特征明显,作品意在描摹女性外貌体态,鲜少刻画性情,“把女性当成一种动态的美物来进行客观的审视”[10]。此首词中的女性形象更为鲜活灵动,画堂内的少女具有大胆热情的性格,拥有真切可感的强烈个性。可见其词在人物塑造上多有进步之处。
父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女性是相对男性而言的“他者”,男性文人对女性的书写难免掺杂了男性的主体欲求。五代时期词仍为“小道”,男性词家以女性视角抒发的情感大多集中于爱情的相思、幽怨等方面,女性日常生活中安闲愉悦、畅快适意等个性化情感几乎不被关注。从这一层面而言,李煜以男性身份“作闺音”,固然塑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女性形象,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视角的片面性。
2 自我生命体验的抒发
晚唐五代时期,词作表现情感的方式多以男子作闺音的形式呈现,充满香软浮艳的脂粉气。而李煜在“词为艳科”的审美规范里开辟了新路,真挚而深沉地直抒胸怀。这不仅摆脱了词“文抽丽锦”“拍案香檀”的传统风貌,也对后来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艺术创作产生影响。其词作中自我生命体验的抒发主要有欢宴之乐、思亲之念、危境之忧、亡国之恨4类,而亡国之恨这一类作品尤多。这4类词作在对建筑意象的选择运用上各具特点。
2.1 欢宴之乐
表现欢宴之乐的词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与《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两首,两者都选取了“殿”这一建筑意象。宫殿作为歌舞宴饮的欢乐场所,以华丽宽敞的特质为豪奢的纵情游乐创造了条件。《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中描写了华美绮丽的宫殿,但更注重殿内人物活动状态的描摹。“春殿嫔娥鱼贯列”呈现热闹繁华的人物群像,“晚妆初了明肌雪”聚焦人物肌容之美,视觉落点更为具体。《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一词在表现殿内人物和环境的互动上较前首更为细腻,以“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两句为例,发间滑落的金钗与脚下地毯的皱褶于细微处展现了夜宴的热闹繁华,“皱”“溜”两字的点染灵动有致,毫无堆砌斧凿之气。殿内群像的描摹与单一细节的刻画相结合,兼顾了阔大场面感与个体形象概括力,欢宴场面呼之欲出。另外,意象的排列组合也颇见巧思。宫殿与乐曲意象的叠合使用使得这类词作呈现鲜明的空间广阔性特点, “别殿遥闻箫鼓奏”“笙箫吹断水云间”两句可为例证。前者冲破了一室一殿束缚,将狂歌曼舞的欢畅传遍整座宫院,给读者带来视觉空间上的宏阔体验;后者对音乐的处理则在听觉空间上完成了天地间的延展,凸显夜宴人群欢乐纵情之盛。
2.2 思亲之哀
李煜抒发怀亲之情的作品常在伤感郁结之外平添几分愁苦悲慨。其词中的悲剧色彩不仅源于亡国北上引发的深沉凄厉的国仇家恨,还来自弱国苟安之君面对时局的挣扎与无奈。外受北宋威逼,内有亲族离散,妻儿过早离世、兄弟受羁于宋,诸般酸楚见于《却登高文》《昭惠皇后诔》《书灵筵手巾》等诗文中,其词作中也多有流露。直接抒发怀人之情的词作主要有《喜迁莺·晓月坠》《谢新恩·秦楼不见吹箫女》《清平乐·别来春半》3首。前两首怀念对象有明显的女性指向,第3首则较为模糊,有学者推断其为怀念入宋不归的七弟李从善而作。3首词中选取的建筑意象较多,画堂、上苑、栏杆、台阶皆有涉及。这些建筑尚留存生活的痕迹,而曾身处其中的故人却音信茫茫;宫室是眼中实景,故人却成了梦中幻象。值得注意的是3首词皆为梦词,词作构筑了真实与虚幻的两重情境,现实与梦境的落差更易激发感伤的情绪。与建筑意象同时出现的是落花、白梅、春草、垂杨这类具有细、柔质地的植物,词人既以落花、白梅的残与冷表现哀戚心境,又通过坚固的建筑、年年生长的花草等来衬托人类生命的脆弱、人与人之间离合聚散的无常。作为抒情主体的词人不仅无法避免这种思而不得的痛苦,更难以逃离感物伤怀的环境,这使得怀人之思因触景生情而陷入灭而犹生的闭环中,哀愁反复而绵长。
2.3 危境之忧
李煜对国势的忧思在词作中也有所体现,主要有《临江仙·庭空客散人归后》《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等。较之前期“作闺音”的幽怨伤感,这类作品呈现不同的情境。前期词作因闲愁无聊而悲春伤秋,后期词作字里行间充斥示山雨欲来的悲伤绝望。能使人短暂倚靠、带来安慰的阑干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空旷庭院、半掩画堂、幽暗小楼、寂寥别巷。空庭和别巷等共同营造了静寂冷清的环境氛围,而这种氛围明显有别于久无人居古宅中的死寂。空寂衔接于“客散人归后”,生发于一瞬之间,是歌舞欢宴后的陡然冷落。处于长久的寂寥中会因习惯而心境平和,热闹和冷寂的猛然转换更易激起人情绪的翻涌。乐能不避其真,哀则不掩其深,两相对比之下,“当年之繁盛,今日之孤凄,欣戚之怀,相形而益见”[11]137。画堂“半掩珠帘”的处理方式也颇为微妙,刻意营造似有人刚刚卷帘的状态,暗示对人去楼空、只余画堂这一现状的逃避与抗拒。词中的小楼见于“小楼新月”“子规啼月小楼西”两句,“月”的存在使得建筑被置于广阔天地间而更显渺小,新月的尖锐形态引起触感上的刺痛联想,声声啼血的杜鹃鸣啼在冷寒空寂之外平添几分凄厉,词中低迷的哀音中家国危亡之痛清晰可辨。
2.4 亡国之恨
如果说危亡之忧仅以感时伤怀的方式进行了克制的表达,那么亡国北上后的愁恨悲恸则以“如生马驹,不受控捉”[11]157之态奔涌放纵,达到了以浅显之语道深沉之意的表达效果。入宋后饱尝的辛酸侮辱使得李煜之词表意多悲恸凄绝、字字泣血。这类词中建筑意象高频密集出现,犹以“楼”为最多。无论“凤阁龙楼”“荫花楼阁”还是“玉楼瑶殿”,都凸显了建筑高大状美。注重从整体上描摹建筑的宏伟气势,整体词境更为开阔。
李煜前、后期词作中皆不乏对虚境幻象的构建,梦境包含丰富的情感意蕴,有“纱窗醉梦”“朦胧入梦”等常见的闺怨相思,也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等怀念故国的直白流露。相较而言,建筑在前期词中多处于梦境之外,多作为词中的客观环境而存在,抑或为产生幻梦的诱因之一。后期词中建筑直接且大量地构成了幻象的组成部分。虚化的处理方式给人以朦胧缥缈的不真实感,加之楼阁宫殿华美性的描摹,营造了“彩云易散”的悲剧意味。其词在表现旧日繁华逝去的空落感之余,还强调了现实处境的艰难。“秋风庭院”“小楼深院”等建筑意象展现了冰冷凄凉的现实际遇。此类词中“阑干”意象成为连通往昔与现实的媒介,词人通过“凭阑半日”来追思故国,或以“独自莫凭栏”打碎幻梦重回现实。今夕对照、虚实相映之间,巨大的心理落差生成直接而磅礴的情感张力,激起深厚绵长的苦痛愁绪。此外,描摹整体、规避细节的处理方式也为情感的表达让出更多空间,使得感情更加明白直露、不加掩饰地倾泻,词作风格发生明显转变。在压缩之后的有限文字空间里,李煜对建筑的描写从大处着笔、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落点,“凤阁龙楼连霄汉”之语将先前的柔婉绮丽转为清刚冷硬,开拓了词境、提升了词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