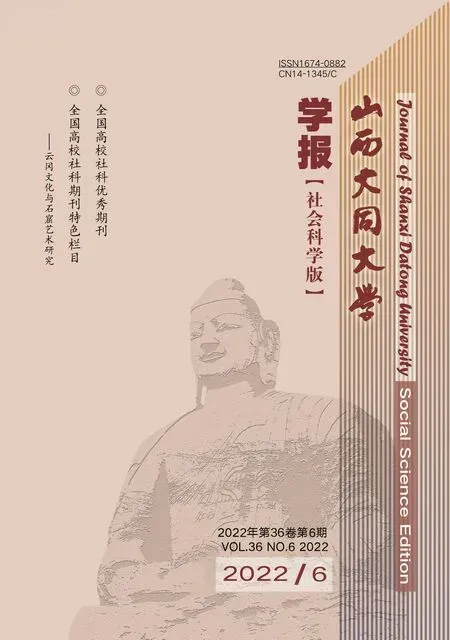古代诗歌的“悲愤”情感及其诗学价值
覃 才,董迎春
(1.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2.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诗作为抒情的艺术,其创作和审美显然与诗人的人生经历、审美情感及社会境遇相关。自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文论观点以来,愤怒、忧思、哀怨、穷饿等具有否定性、悲愤性的诗歌审美情感就成为历代文论家和诗人探讨诗歌创作生成和诗风转型的重要依据,并形成一种共识:古代诗歌中有精言、秀句、妙语特征的经典传世之作即出自诗人的“悲愤”情感与磨难(即悲愤成诗、悲愤出诗人)。对古代诗歌的这种创作与审美特征,白居易指出:“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方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1](P1479)显然,在封建等级社会当中,“学优而仕”的寒门仕子,他们波折起伏的仕途和穷困、寒饿的人生遭遇既造就了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愤”情感与生命意识,也生成了“悲愤”的诗歌创作与审美能力,更让他们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人生理想、社会更替及天下命运的思考与关怀。显然,从“诗言志”的认同中,我们明白了诗歌是“公卿列士与君王间‘言志’与‘观志’的重要方式”,[2]但我们还没有仔细审视与概观古代诗人的“悲愤”情感与他们的诗歌创作、传世及经典之作的生成关联。
一、“悲愤”作为古代诗歌的生成情感与审美传统
自“诗言志”[3](P18)的文论观点提出以来,诗人的情感、志向就成为文论家和诗人思考诗歌本体、诗歌生成及其诗学价值的重要参照维度。就中国诗歌的整体发展而言,“诗言志”确实可以作为诗歌创作、诗歌本质及其价值的总体性概观,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情感、志向都能生成诗歌,特别是那些经典传世之作。我们能够从诸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之类的传世名句当中,捕捉到忧思、哀怨这类情感与经典传世之作的直接关联。这就是说,诗歌作为抒情和有审美指向的文体,驱动诗人进行创作的应是一种相对强烈、稳定并且是不那么“正面”的情感。在“诗言志”这一前提下,纵观古代诗歌(特别是那些经典传世之作),其内部衍生出一种以“悲愤”情感为审美主线的文论思想与诗歌创作观。中国古代诗歌“悲愤”的文论思想与诗歌创作观的雏形,较早可追溯至《论语》当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4](P67)和“诗……可以怨”[4](P192)等论述。在孔子之后,屈原也在《九章·惜诵》当中提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5](P144)的观点。屈原作为古代“失志”的士大夫象征,明显地将个人失志、忧愤情感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以诗抒愤。在孔子与屈原之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当中总结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6](P546)司马迁关于《诗经》“发愤之所为作”的概观,既总结了孔子、屈原所强调的“悲愤”情感与诗歌创作的关联,也标志着“发愤著书”文论观的正式形成。哀伯诚指出:“在中国文学义上第一个把‘愤’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是屈原,……而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个把‘发愤著书’作为理论提出来的是司马迁。”[7]
作为一种古代文论思想,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整体上是以“悲愤”概括人的否定性、低落性情感与诗歌创作的本质关联。他所强调的这种“悲愤”情感不仅催生了封建等级社会中人性的觉醒,更对古人探讨诗歌创作动力及其本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司马迁“发愤说”之后,“悲愤”情感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被普遍认同并获得不同维度的释义与丰富。如桓谭在论述贾谊、扬雄的创作动力时指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8](P9)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当中亦也指出:“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9](P154)萧绎指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0](P727)王微认为“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11](P11)及韩愈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12](P20)和“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13](P892)都是关于“悲愤”情感与诗歌(文章)创作动力、审美指向价值的新思考。南朝文论家钟嵘在《诗品》当中评价《诗经》以来的古诗之时,也认为它们具有“托诗以怨”[14](P10)和“多哀怨”[14](P26)的“悲愤”特征。对这种新产生的“悲愤”创作标准与审美指向的思考,欧阳修总结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穷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5](P104)欧阳修将诗歌创作与诗人的穷困、忧思、怨刺、失志等经历与情感相联系的“诗穷而工”的文论观,既表征了自孔子、屈原、司马迁以来关于诗歌的一种“悲愤”情感流变,同时也结合古今时代诗歌创作的特征,对诗歌趣味与意义作出了再思考。
在诗人层面,哀怨、悲愤等情感与诗歌创作的直接性关联不仅被诗人所把握与应用,而且他们作为诗歌的创作者,在创作过程当中是“以诗论诗”的形式呈现了这种个人和历史维度的“悲愤”情感审美。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中指出:“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16](P1149)对他而言,《诗经》作为古诗正统虽然表现出“微茫”或衰弱的特征,但《诗经》当中具有的“哀怨”特征和审美情感依然是成为一个诗人的重要前提。在《和答诗十首·并序》当中,白居易认为元稹被贬之后写的诗“心甚贵重”,其诗风转变是“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时发愤”[1](P39)所致。在此基础上,白居易得出了古今诗歌十有八、九是“愤忧怨伤”而来的论断。苏轼在一系列的诗歌当中表达了穷困、贫寒经历对诗人创作的决定意义。在《次韵徐仲车》当中,苏轼指出:“恶衣恶食诗愈好,恰似霜松啭春鸟”;[17](P873)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一》当中指出:“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18](P323)及《僧惠勤初罢僧职》中认为“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18](P163)等。此外,同是南宋诗人的陈师道和王炎分别指出了“惟其穷愈甚,故其得愈多”[19](P1834)和“人穷愈甚诗方好,留取珠玑向后传”[20](P26)的相近诗观,以肯定穷困经历对诗人和诗心的磨炼。比陈、王稍晚的南宋诗人陆游在《澹斋居士诗序》当中则综合了《诗经》以来历代诗的“悲愤”情感与诗心,对古今诗歌作了“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21](P2110)的概观。
迨至明清时期,“悲愤”的文论观和创作情感不仅继续在诗歌当中产生影响,更成为小说家创作和思考的核心情感之一。在诗歌方面,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强调“性灵”,但也认同“诗能穷人穷者工”[22](P107)的观点;赵翼更是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3](P162)的本质观点,肯定国家的战乱、动荡等具有忧思、哀怨特征的时代语境对诗歌创作的推动作用。在小说方面,李贽在《焚书·忠义水浒传序》当中指出“古之圣贤,不愤不作矣”的观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志》以“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24](P332)的自述,向世人说明《聊斋志异》一书是“悲愤”的创造及其审美显现。可见,具有穷困、哀思、忧怨、失志及时代黑暗、皇帝昏庸等意蕴的“悲愤”情感与认识,作为推动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的情感,被不断重视与强调,并愈来愈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领域。
同时,《诗经》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端,它表达不同地域人民对社会不公、战乱等现实的否定,也体现着古代诗歌当中“悲愤”情感具有的民间传统特征。孔子、屈原、司马迁有关“愤”情感的发端论述,也表现了古代诗歌“悲愤”情感所具有的深远传统。显然,自从司马迁具有自身经历(受宫刑后写《史记》)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发愤著书”论,将“愤”的情感与创作对接起来以后,不同时代的文论家和诗人对其内涵与审美维度进行补充与完善,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证明:这种“悲愤”情感既引起文人的共鸣与认同,更成为诗歌创作的推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古代诗歌创作传统。
二、古代诗歌的“悲愤成诗”特征及其书写结构
诗歌作为抒发诗人情志的艺术,显然与诗人的经历和遭遇、国家和时代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诗心、诗艺有关。北宋诗人余靖指出:“世谓诗人必经穷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蕴、写凄辛之景象,盖以其孤愤郁结、触怀成感,其言必精,于理必诣也。”[25](P16-17)按照余靖所言,对于一个立志从事诗歌创作的人而言,穷困和哀愁的人生境遇能够使其触及到诗歌艺术的“幽蕴”而感知到“凄辛”的景象;而孤寂和悲愤则能够使他达到某种造诣,即做到能够写出精言、秀句、妙声。在穷困、哀愁、孤寂、悲愤的过程当中,诗人显现出优秀的品质与功力,也让他的诗歌显现出精妙的经典特征。显然,这种关于自我审视、自我批判及时代反思的“悲愤”情感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经典演化的本质性生成力与审美指向。纵观杜甫、李白、苏轼、陆游、陶渊明等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审美表现出明显的“悲愤”书写结构。
首先,由穷困、寒饿产生的怨与愤。“诗言志”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诗歌创作是一种人生经历和肺腑之言的抒发与呈现。作为一个诗人,其诗歌创作既切近真实的生命状态、境况,同时也是对这一状态、境况的所思所感。在古代社会,出自寒门仕子的创作显然也与其穷困、寒饿的经历和生命状态息息相关。陈子谦指出:“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忠介之士遭受统治者和谗佞之徒的残酷迫害,使得他们走投无路,只好用著书述志来发泄其愤懑,这就是所谓由‘穷’而‘怨’。”[26]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27](P229)我们在这首诗中,很明显地感觉到杜甫处于穷困、寒饿的生存处境当中,他的住所是只有“三重茅”的草堂,不仅一家人用的被子十分破旧,屋子更是多处漏雨。但就是这样的状态当中,杜甫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传世佳句。在这一过程当中,杜甫所处的穷困、寒饿状态发挥着直接的诗歌生成与建构作用,并且展现了他“敢于直面人生困境、心系天下苍生的生命精神”。[28]很显然,在“诗圣”杜甫身上,我们看到了穷困、寒饿的折磨、伤痛铸就了他关于自身、家人及天下寒士的替换性与等同性把握与感知,并以风骨与气节的诗性形式表现出来。
其次,由丧亡、哀思构成的悲与愤。贫寒的出身,造就了古代诗人有异于常人的哀思体验与感知能力。在诗歌创作当中,这种不同常人的哀思体验与感知能力即是一种诗性生成与转化能力。对诗人而言,诗歌创作即是将日常生活当中习以为常或一闪而过的哀思、敏感瞬间转化成诗,以呈现人与生活二者的瞬间诗意与直觉体验。如苏轼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29](P150)我们看到经历官场、仕途起伏的苏轼,他的“哀思”感受与感知能力将“梦”和过去的诸多人、事、物都变成一种直觉的“现实”、诗的“现实”。在这一过程当中,“哀思”作为一种诗性、诗意的生成能力笼罩着诗人的身心转换,建构并展示着诗人的所思所想。显然,在这首诗当中,对妻子生死相隔的哀思、怀念及对个人颜容衰老与生活颠簸流离的悲伤感叹,构成了苏轼的“悲愤”抒情,呈现了“哀思”这种情感结构对诗歌创作与诗性的生成作用。
再次,失志的忧与愤。对大都熟读圣贤之书且具备风雅传统的古代诗人而言,朝堂之中的功名利禄和家国天下情怀既是他们所向往与憧憬的,更是他们的理想。然而,随着仕途不如意或重大变故的接踵而来,一种“失志”的忧愤也随之萌生并滋长。在这种失志和忧愤的冲击当中,古代诗人的价值世界与创作审美也发生重大的转型,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写出经典性的佳作。如李白在《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30](P285)李白写作这首诗时,已经被贬出京,处于仕途失意的人生状态之中。“弃我去者”和“乱我心者”即是对帝王和朝廷疏离或排斥的暗指,这种失志、失意的遭遇使其产生了无法排遣的忧愁和愤懑之感。因而,对这种失志的忧愤之感的抒发与宣泄不仅构成李白写作的心理与精神动力,同时也建构了具有“悲愤”情感的豪放诗风,呈现了“忧愤”对诗歌创作的直接关联。
最后,回归孤寂本质与淡然。在理想与现实、失意与得意的不断变化、冲击之间,年龄渐长的诗人逐渐确立了关于生活、生命及人生价值的本质思考与认知。对艺术修养与风雅传统强烈的诗人而言,在经历了人生、官场的波澜起伏、勾心斗角、朝夕无常之后,他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人生与世事的虚无本质。对达到这一境界的诗人而言,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归生命与生活本身,以表现生命、生活及世事的孤寂本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31](P32)由于经历有违心性的官场起伏,向往自然山水的陶渊明最终选择“归园田居”的闲逸生活。在种豆、除杂草的朴素劳作当中,陶渊明既回归了生命的孤寂本质,更感受与把握到了这种孤寂本质给诗歌创作带来的灵性,他的诗歌价值也由这种孤寂与淡然显现而出。
显然,对古代诗人而言,他们的诗歌创作首先与个人或浅或深的“小我”感受、体验有关,其次才上升到家国忧思的“大我”层次,并最终在无数的波澜起伏和大起大落之后回归生命与生活的孤寂本质。古代诗人这种具有穷困磨炼、哀思感受、失志忧愤及回归淡然的“悲愤”情感写作特征,显然呈现了他们具有批判精神特征的风雅、风骨创作倾向。在这种《诗经》以来的风雅、风骨诗歌创作与追求当中,古代诗人对自身与时代的审视与把握不仅表现了古代诗歌精言、秀句、妙语的运演本质,更呈现了古代诗歌“悲愤”成诗的创作与审美特征。
三、“悲愤”情感的审美价值及诗学意义
作为一种诗歌创作观,“悲愤”或与其相关的情感在古代诗歌创作的作用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子谦、袁伯诚、顾易生、顾植、刘振东、陈莹、祁志祥等为代表的学者不仅对司马迁“发愤著书”文论思想进行时间维度的探幽梳理,更在空间维度上对其进行垂直性的解读与阐释,并将其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得出愤书是“古典情感美学观”[32]和“诗以悲怨为美”[33](P110)的论断,及对讽谕文学理论[34]和叛逆文学理论[35]的影响概观。显然,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引起了古今文论家、诗人对诗歌生成机制与审美结构的深入思考与探究,并形成了一种关于个人穷困、哀思、忧怨、失志、苦难、挫折及时代黑暗、皇帝昏庸等“悲愤”美学指认与诗学观,呈现了古代诗歌稳定的、核心的经典运演路径,进而使“悲愤”情感表现出重要的诗学价值与意义。
(一)呈现中国古代诗歌的批判传统《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具有民间性、民族性、地方性的叙事、抒怀、言志及劝恶扬善审美指向与创作特征,建构起中国古代诗歌抒情传统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中国古代诗歌整体上表现出的“发愤”特征,或者是一种对社会不公、战乱、压迫、恶丑的批判精神。我们看到,司马迁作为“发愤”论的提出者,通过考察《诗经》之后得出的“《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论断,一方面是认同了诗人怨愤、悲愤等情感与诗歌创作的直接性关联,另一方面也是整体性地把握了《诗经》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与传统。黄南珊指出“愤书闪耀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的光芒,并具有反传统的异端色彩”,[32]即体现着司马迁对《诗经》批判精神的认同与理解。而在司马迁之后,历代文论家和诗人不仅认同了《诗经》是发愤所作的论断,更将这种“发愤”与自身及时代相联系,衍生出穷困、寒饿、哀思、忧怨、失志、挫折及时代黑暗、皇帝昏庸等具体意蕴的“悲愤”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续了《诗经》以来中国古代诗歌的批判传统。
(二)形成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诗学观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精言、秀句、妙语、诗工不仅是历代文论家和诗人评判古代诗歌优劣的标准,更是他们认同的一种“经典”诗学观。这些文论家和诗人在诗歌审美、情感结构及创作本身的系列论断,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思考、探索古代诗歌精言、秀句、妙语、经典诗学观的产生缘由与关联因素。李冰燕说:“在封建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一些优秀的作品往往在历经千年之后仍然能够引起后人的共鸣,大都与作者在现实中遭受不幸或受到压抑联系在一起的。”[36]我们看到,在司马迁“发愤”说提出之后,不管是桓谭的失志文采发还是钟嵘的托怨以“感荡心灵”和“骋其情”,或是王微的怨思抑扬而文词有味、韩愈的愁思声妙和穷苦言好,抑或是欧阳修的诗穷后工和穷人之诗传世,及苏轼的秀句出寒饿和恶衣恶食诗愈好等思考与诊断,都是在“悲愤”的诗学情感基础上,将诗人自身具有艰难特征的人生遭遇及失志的时代境遇与诗歌创作相对接,由此呈现了“悲愤”情感对中国古代诗歌精言、秀句、妙语、诗工“经典”诗学观的生成与推动作用。
(三)让诗歌审美回归诗人主体的风骨“自觉”
诗歌作为一门与诗人身心情感、体验、气质相关的艺术,它的形成、发展及达到的高度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诗人诗心、诗艺的形成与变化一般与其人生遭遇、心性变化及精神的境界、格局息息相关。古代文人大多具有较高的风雅修养和诗词歌赋创作能力,但这种创作能力由于人生阅历较浅,大都处于较为粗浅的层面,具有附庸风雅或风花雪月的性质。纵观古代诗人人生遭遇与诗歌创作的转型,他们的诗风由附庸风雅的风花雪月到精言、秀句、妙语、诗工的转变,“是建立在个体与社会矛盾的基础之上,是个体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强烈对立与冲突的结果”。[37]可以说,古代诗人这种回归自我审视和社会探知的“悲愤”想象与创造,不仅让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审美回归诗人主体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建构起他们具有文学自觉性质的诗心、诗艺。
(四)建构古代诗歌“本体性否定”的情感结构与美学观 朱立元指出:“‘本体性否定’的否定内涵,不是将‘打倒、克服、取消’这类传统否定观‘取消’了,而且是其‘空虚’之‘局限’处,产生不满足于生存世界的否定冲动,通过创造一个独特的思想性世界来获得自己的‘心安感’的。”[38](序6)显然,对这种“本体性否定”而言,它显著的价值与意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具有物质性的“否定”,而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创造性、人文性的“否定”。对古代诗人而言,他们一方面饱读圣贤之书,也大都忧思天下,但又由于人生抱负无法实现,在这种矛盾中就产生了一种具有“本体性否定”的情感结构。关于人生理想、社会更替及天下命运的人生观、思想观,表现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当中。纵观古代优秀的诗歌,它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是诗人在寒饿、哀思、忧愁及伤情的状态或情感当中写出来的,这种具有“悲愤”审美特征的诗歌创作观与生成特性,表现着古代诗人具有的“人因意识到现实的问题和局限,才会有‘不满足于’的批判冲动,才会有创造性的行为与实践”[38](P96)的“本体性否定”美学观。
综上而述,与司马迁“发愤著书”文论一脉同源的“悲愤”情感,作为一种诗歌创作观或审视自我与时代的本质理念,对诗人的诗歌创作本身、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风雅传统及经典的诗学观都有重要的影响与建构作用。刘安指出:“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则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39](P123)诗歌作为由诗人创造的语言艺术,它的产生、生成及其审美显然也由诗人个体的忧、丧、悲、哀、愤、怒等状态和情感直接建构,我们看到,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悲愤”情感的价值与意义。这种让诗歌审美回归诗人主体本身的文论思想与创作对重塑古代诗歌审美体系及反思中国古代诗歌的当下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