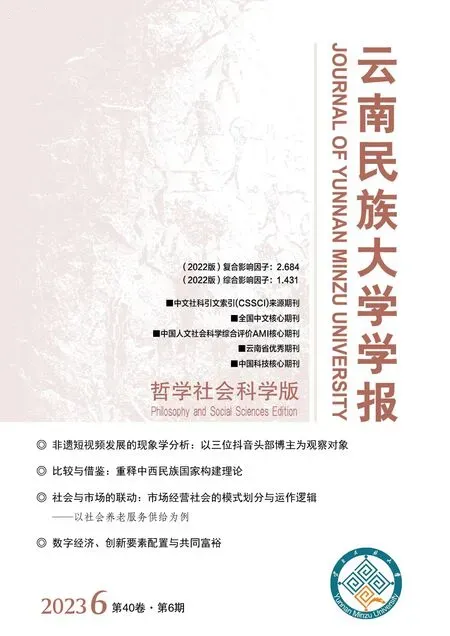比较与借鉴:重释中西民族国家构建理论
安北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101)
西方民族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初,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推进,最终发展成为一套较为成熟的体系。“冷战”结束后,世界多国掀起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有关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焦点。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民族问题复杂化,极端宗教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潮裹挟在一起,不仅导致区域间民族宗教冲突,甚至引发国家分裂等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
与西方民族理论相比,中国早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侧重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政策(包括民族识别、民族制度建设等),其中民族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中华民族源流及其历史演进方面,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对其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为代表的史学家撰写了《中国民族史》,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发展历程演变。抗战时期,因受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为使各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御敌,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把中国民族问题与当时的政治结合起来。建国之后,学界基本接受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进行民族识别工作。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翁独健、白寿彝、费孝通等一大批学者针对历史上民族的“多”与“一”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最后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理论等系列重大问题出现研究高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理论问题又成为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今历史文化认同、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成为当下民族问题研究的焦点。
中国的民族问题有着自身的复杂性,需要在借鉴西方民族理论的同时又要能跳出其理论陷阱,汲取多学科理论知识,重新审视民族主义思潮背后的理论逻辑。具体而言,即在西方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下,中国民族所表现出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中国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其历史进程如何,结局如何等系列问题。
一、中西方民族理论的本质区别
西方理论界认为“民族”是“某种人类或人们的共同体”,针对这个“共同体”,学界给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促使“共同体”形成的客观因素或表现出的一般特征;另一种是促使“共同体”形成的主观因素或表现出的心理特征。早期民族在中西方发展历程中,因受到不同客观因素影响,致使民族、民族-国家及民族意识等概念、内涵大相径庭。相比之下,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更注重血缘文化的传承性,与西方民族主义倡导的民族国家截然不同。
(一)共同体:西方民族概念及其理论核心要义
因时代背景和观察视角的差异,不同学者对种族、族群、民族、国民等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文化层面各有侧重。尽管如此,但各概念中却含有一个不变的客观实体,即在某一区域内所形成的“共同体”。今天在学理层面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完全是出于在民族理论体系下对历史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做出的社会性解释。
现代民族之概念,主要是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民族至少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4个特征。随后,斯大林又指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1)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也就是说,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民族的因素本身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因为社会发展条件的困窘未能凝结在一起。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整合在一起,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分裂公国”从此变成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借助资本主义市场来推动。
除斯大林所强调的民族客观要素外,有些学者也强调民族的主观因素。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成天生拥有边界和至高无上,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就是“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刀涛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尤其在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以国家共同体为单元的民族共同体也随之出现,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且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中不断上升的事实。如此,想象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共同体便凸显出自身的理论缺陷。故而,也有学者提出把目前对“民族”认识的主客观因素结合起来,得出民族就是“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体,它的成员享有一块历史性的领土,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适应的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4)[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在国内,有些学者受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影响,认为“民族是人类共同体依托于民族国家而形成的现代形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居民或全部享有该国家国籍的人的总称”(5)郝时远:《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论来源》,见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这一观点完全受马克斯·韦伯关于民族定义(6)马克斯·韦伯认为,“民族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联结,其适当的诉求是成立自己的国家,而这通常趋向于产生这样的国家”。参见Anthony D.Smith.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5.的影响,属于当代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范畴。
(二)政治体:“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
民族既不是国家,也不是族群,因为国家的概念与制度行为有关,而民族的概念则指的是某种类型的共同体。(7)[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那么,“民族”与“国家”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宏观层面讲,民族与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共同体形式,其组织方式却截然不同,民族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国家则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相结合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明确提出“一切主权在本质上均源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8)[德]格奥尔格·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李锦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0页。,最终打破地方壁垒,消除原地方制度隔阂,建立起与法兰西民族合为一体的具有统一经济、疆域和单一公共文化的民族国家。(9)叶江:《解读安东尼·D·史密斯相关著述中的几个关键性术语》,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5期。法国大革命也开创了新的民族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思潮波及到亚非拉等地,促使民族国家理念广泛流传。
“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是区别国家形态的主要概念,前者主要指单一民族国家,而后者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组成的国家。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国民-国家”一方面是对多民族帝国的背离;另一方面则是对多王国民族的整合。只有同时完成了这两个过程或实现了这两个目标,才可以说建成了“国民-国家”。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国民-国家”的本意与主观要求是国家的单一民族性。在欧洲人的语言和观念中,“国民”与“民族”有时通用,原因就在于“民族”与“国家”实现一体化以后,“民族”变成了“国民”。而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国民”与“民族”是不能通用的。(10)朱伦:《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载《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国民-国家”在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将同一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统一起来试图与其他民族分离,在民族独立运动思潮中起到重大作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单一性和完整性,但民族在社会发展中难免产生交流、迁移,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单一民族是很难实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以一种共同语言为基础的单一文化内部哲学的、宗教的和族类的多样性,而不承认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也不讨论多民族国家社会文化、语言和民族群体的多样性。事实上,自由主义理论家也知道现代国家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当代民主国家的多元性,但他们一致假设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只是人们对美好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已。(11)[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马莉,张昌耀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因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逻辑的推衍是紧紧围绕个人权利而展开,通常强调人的理性与自主,认为国家是个人为了保护自身权利和实现个人权利的一种创造物,当个人完成制造国家的授权之后,“个人”也就变成了“公民”。(12)黄其松:《多元文化、少数民族权利与多民族国家建设——以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当然,这套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悖论,避重就轻,无视民族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终究属于西方政治理论界的理想模式,面临种种挑战。
可以说,在社会发展演进中,以“国民-国家”的理想开始,却以“多民族国家”的现实而告终。西方“国民-国家”的理念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也不断凸显出自身的缺点,成为民族分裂的理由,或成为民族强制同化的借口,最终成为诸多民族问题的导火索。“民族-国家”的叙事标准,主要体现在政治法律及其公民权利上,反而在传统的民族因素上显得并不突出。
(三)民族体:中国“民族的国家”
相对西方以政治为导向原则的民族诠释,中国则凸显出其文化导向性原则。中国早期“民族”之意,并非所指西方国家民族或者政治民族之概念,主要是指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中国最早的民族思想,既不是种族,也不是地域划分的民族,而是以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等为基础所形成的以价值观为代表的文明方式,成为一种文明共同体,其内涵与前文所述安东尼·史密斯之民族定义类同,即强调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风俗习性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崇尚的单一民族主义国家前景黯淡,也无法得以实现,其理论体系也未免遭人诟病。反而在多元文化影响下,多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既然“国家”与“民族”不能完全重合,那么,“民族-国家”不妨被称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即“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合法性的国家,它的成员拥有很大程度民族的团结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质性)”(13)[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将民族团结和整合作为一个变量,避免民族边界与国家疆界不一致的问题。
纵观历史上的中国,无论哪个民族建立政权,无不包含各种民族(族群),呈现出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因此,西方自由主义所标榜的政治民主主义下的单一民族国家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究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中国历史上固有民族(或族群)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呈现出共存态势;其二,这些族体本身更侧向以血缘和文化为纽带的“族裔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虽然在民族意识及民族-国家意识方面比西方出现稍晚,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民族建构过程中原始的民族-国家形态不存在。同时,民族意识的表达也并非如西方民族理论所指是基于资本主义力量推动而产生,中国民族意识的流露反而恰恰是在历史时期各族群集团相互碰撞中产生。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形态和民族意识表达,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冲击下所表现出的民族自我反抗意识,此时由原先国内各族体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上升到“国族”意识与反抗侵略意识之间的斗争,中华民族便顺势成为各族体的“通称”。中华民族也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集体意志的指代,呈现出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政治民主主义国家共同体形态,即“国族”概念,中华民族即代表中国。
二、一元与多元:疆域变迁视域下的国家认同
“民族”与“民族-国家”理论内涵在中西方相差巨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同一历史空间内某一政权历史命运走向不同。中国在东亚既定疆域范围内走向一体,而西方虽然在其历史上也出现过地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但最终走向分裂,未能延续其统一的使命,这也成为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形成的客观缘由。
(一)疆域分裂到统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纵观整部中国史,秦汉以后族群统一逐渐制度化,“天下一统”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秦汉之后,无论在国家制度的成熟度上,还是在王朝实际控制疆域面积上都有所提升。历史上,尽管出现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宋西夏金等分裂期,但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无不想着一统天下,拓展疆土。范文澜指出,“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呢?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自北宋起,由于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的加强,这个共同体更趋于稳定。”(14)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换言之,汉民族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统一成为主流的根本原因。历史时期的汉民族无论在人口基数上,还是在文明程度上都远胜于周边民族,汉民族团体的形成是统一国家稳定的基础。
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其分裂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政权内部分裂;另一种是受中原以外的非汉民族冲击,最终导致中央王朝解体。前者属于汉民族政权内部个别野心家为谋取政治意图而做出的举动,一般时间较短,中央政权行政体系仍旧存续;后者则分裂时间较长,因为汉民族中央政权受到冲击,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与程序运行中需要时间磨合。在每次大分裂之后,后一代政权统一基础更加牢固,疆域更加广阔。但有一点要明确,汉民族不等于中华民族,中原政权对全国的统一主要是侧重于对汉地农耕区的统一,对边疆尤其非汉民族统治区则往往采取“羁縻”形式或设立专门机构来统治,如明清的土司制度等。汉民族形成强大稳定的共同体,并不能成为历史上非汉民族终结分裂而建立统一政权的理由,如元与清政权,并不以汉民族为共同体而一统天下。汉民族在国家统一进程中或在消除国家分裂因素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是因为汉民族群体在不断扩大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密切交往,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实体。这便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高于汉民族的新实体重新整合起来,同呼吸共命运,抵御外辱,建立新政权,求得各民族共同的利益。
纵观中国历代疆域,大统一政权所控疆域范围是在逐步扩大。“三代”时期,据考古发掘推知,夏朝疆域范围大致以今河南西部为中心,北抵黄河北岸,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商朝经过多次迁都,最终定都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其疆域范围大致东到大海,西达今陕西西部。西周时,范围继续向西扩展,一直到甘肃,南跨长江。战国时,赵国疆域北部扩展至河套及阴山地区,燕国北部抵达辽宁南部,秦国西部到甘肃临洮一带,楚国疆土拓至江浙。可以看出,华夏疆域由中原向四周扩展,南线从黄河中游到淮河流域再到长江流域,最后扩展到岭南;北线从中原到河北中部再到河套阴山;东北到辽宁南部,西北到甘肃东南部。
秦灭六国,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西汉初期,北方匈奴南下,占据“河南地”,汉匈分界于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一线)等一线。(16)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汉武帝时,打通河西走廊,设置西域都护府。其疆域向南推至今越南北部,东北推至朝鲜半岛中北部,东达日本海一带,“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1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疆域胜过秦朝。进入隋唐,疆域再次扩大,《隋书·地理志》载:其地“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18)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8页。至唐高宗时,“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9)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4页。。元代疆域空前广阔,“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0)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明朝时疆域缩小,漠北被北元占有,新疆大部分地区被察合台汗国占有。明朝有效控制的疆域即原来南宋、金、大理、西夏等政权所控制辖区,北边以“九边”为边界,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1616年,努尔哈赤雄心勃勃建立后金,先后统一漠南漠北。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最终实现全国大统一。清朝疆域面积远超明代,也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格局。
不难看出,历史上的非汉民族政权统一全国后的疆域不比汉民族政权疆域小,边疆内地化和王权在边疆的渗透力度明显加强。正是受到游牧民族政权的不断冲击,中国疆域的整合力度愈加牢固。中国疆域的形成也正是历史上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虽然历史上各民族在不同区域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最终走向了更大范围的统一,这是与同时代西方帝国解体后走向分裂结局的最大不同点。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形成强大的政治经济联合体,最终成为“一体化”格局。
(二)疆域整合到分裂:西方历史发展进程
众所周知,自国家政权建立以来,统治者便不断尝试着疆域的整合,但整合的结果却在东西方世界中形成显明的差异。如果说爱琴海、尼罗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促生了西方文明,那么,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波斯帝国便是完成了西方世界疆域史上的第一次大整合,其地跨亚、非、欧三大洲。随后经大流士一世改革,波斯帝国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但这套凭借武力构筑的政治体系因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础,后期加上波斯贵族与奴隶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导致奴隶频繁暴动,最终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击溃。至此,延续两百多年的波斯帝国解体,同时西亚及北非的古代文明也宣告结束。紧接着是亚历山大的东西扩张,在原波斯帝国基础上,其疆域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至印度河流域,南至尼罗河第一瀑布,占领埃及全境,西达色雷斯和古希腊,北抵黑海及阿姆河,这是欧洲疆域史上的第二次大整合,亚历山大帝国(马其顿帝国)成为西方史上第二个地跨亚欧非的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故,因继承人问题,政权内部发生王权争夺战,最终致使帝国一分为三:马其顿王国、塞琉西王国和埃及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虽然结束了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却把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火种带向东方,推及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及中亚世界,迎来“希腊化时代”。在亚历山大扩张的同时,罗马人也随之而起,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之后经过3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146年)的洗礼,实力渐增,遂即进入扩张时代。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称号。从此,古罗马共和国进入帝国时代。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达到极盛,其疆域地跨亚非欧,西起西班牙、不列颠、高卢,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抵莱茵河、多瑙河,南达非洲北部,地中海成为帝国内海,囊括黑海、爱琴海,这是欧洲疆域史上的第三次大整合。395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史称东、西罗马帝国,从此之后罗马帝国再未统一。其中,西罗马帝国于476年亡于日耳曼人,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6世纪中叶,日耳曼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法兰克王国。8世纪中后期至9世纪初,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欧洲大陆,这是欧洲疆域史上第四次大整合,但这次相比前三次,疆域小的多。查理去世后,帝国一分为三:东、中、西法兰克王国,即今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前身。进入近现代(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兴起,西方出现了民族国家,即从原来“统一”帝国疆域基础上分裂成系列单元型的“民族国家”,单一政权地跨亚非欧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在经济全球化下,欧洲许多国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自发性组成政治经济联盟,具有代表性的如欧盟(EU)这样的团体组织,如果按照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理想,这早已违背了他们所提倡的单一民族政治共同体夙愿,反而走向跨国跨地域的新“政治共同体”联盟。再者,这种联盟也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不同国家的简单联合体。
综上可见,历史上的中国与西欧历史演进模式结局不同,中国从文明诞生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共同的领土,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而西方却分裂成大小不一的四十多个“单一民族国家”,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裂国”时代,最终也未能走向统一,这是民族国家概念在中西方话语表达中最根本的不同。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意识就是一种“共同意识”,是在共同思想文化基础之上表现出的一种共同心理状态。汉族族源在先秦时期主要是指华夏族,夏商周三代政权更迭,但疆土范围内的夏、商、周族人始终聚集在一起,至春秋战国时代,除了原夏商周族后裔外,还吸纳了大量的南方族群成员,尤其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原和南方“民族”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文献中称之为“诸夏”或“华夏族”。进入汉代,随着国力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国家影响力不断提升,开始用王朝名称作为族名,“华夏族”逐渐被“汉族”称号所替代。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在王朝政权建立之前,与华夏族群并存的一些族群,因生活环境或生活方式的不同,一时未能并入华夏群体范围之内,一般称其为“异族”或“他者”。当“国家”政治体出现后,整个族群被一套完整的制度所束缚,为了群体成员或整体的发展,族群本能地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这种意识便是带有排他性的民族意识。从族群团体的财产物质利益保护到国家建立后的政治利益所需,都是民族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如历史上的尊王攘夷、华夷之辨、正闰之争等。
古代中国的民族意识,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下产生的。尽管各民族有着利益上的冲突,但各主体民族政权所隐含的“大一统”意识却是历史发展主流。与西方民族所表现的共同体意识相比,中国民族意识很明显侧重于共同信仰和文化基础,略淡化国家法律和政权疆域领土层面内的族群联合意识,这是“族裔”民族的表现特征,即以出身和原生文化二元素为根本。历史上的民族基本都是以此为准则来建立自己本族群或政权集体的“共同体意识”,当原始群体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之后,族员身上便打上本族的烙印,无论他族介入还是自己融入他族,自己永远抹不去原始地域和血缘的印记。当各群体面临新生政权重新整合时,便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这种抵触也是早期民族意识的表现。客观地讲,历史上的民族就是一个拥有血缘的共同体。事实也证明如此,历史上以某一民族为核心而建立的政权,其境内包含着与之并存的其他血缘族群,这些群体无论在何时何地,无不拥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正是以血缘和宗族谱系来维持的民族团体,才有了后代对祖先的认同和共同历史记忆的追溯。
步入近代,清政权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冲击,中国境内各民族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同仇敌忾,抵御外辱成为时代使命,各民族团体摒弃历史前嫌,团结一致,各民族间的矛盾转化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级,中华民族与其他侵略民族之间的抗争。在一批批民主人士的努力下,新生政治势力终究取代清封建余势,也拉开了中国“民主国家”的帷幕。当代表各“民族”的统一性中国政权诞生时,各民族团体便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抽象团体,即中华民族。那么,我们又是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华民族这个“单一民族团体”呢?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概念”被加以讨论,主要原因是中华民族的实体本来就已经存在,换言之,中华民族所包含的各民族实体在历史上本身就以血缘或宗族文化为纽带而传承延续至今,是不争的事实。自20世纪初“中华民族”作为术语概念被提出以来,(21)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一文,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1905年,其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文中,频繁使用“中华民族”,此时含义基本与“汉族”等同。其含义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22)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强调汉民族的主体性,主要从种族特性上解释“中华民族”,认为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经过不断整合吸收其他民族扩大而成的一个共同体。主张“五族共和”,是中华民族概念内涵转变的重要思想转折点,此时中华民族由汉族“一元观”转变为“五族共源观”。到三十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凝聚共识,民族大义至上,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术语逐渐成为中国境内全体民族的代称,即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时至今日,每当谈起自己成为中华民族一员时,首先想到的是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或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族源观。
中华民族概念不能用西方民族定义来解释。西方“民族”之意包含两种解释:一是民族,另一是国家。(2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反观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它“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2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部分学者对“中华民族”与“民族”概念相抵牾的原因,主要是受困于斯大林民族之定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某一区域内,资产阶级往往以国家政权形式来保护资本市场,而国家政权则常以本地区民众集体民义来建立,本地区的民众便是“民族”。相应地,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就变成了民族独立的革命,最后形成“公民-民族-国家”模式。西方“民族”也侧重于政治,往往强调“民族自决权”(25)“民族自决权”源于欧洲,其理念早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时就已经产生,在19世纪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理论的阐释主要是由一战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国“十月革命”时的列宁系统阐述,主张“民族自决权”除了政治自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之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参见《列宁全集》(卷10),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民族概念只有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才能被指称。这一理论正好适合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华民族”概念演变的诠释,“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表明“中华民族”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被定义过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作为自觉民族实体的形成,也表明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至上局面逐渐形成,被各民族承认的中华民族也成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
中华民族上升到国家层面,实质是民族从血缘和文化上升到国家意志的表现。中华民族被视为一个单行体民族,并被给予民族之定义,就是各民族利益最大化和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地位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近现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记忆,这是中华民族成为“公民-民族”和中国成为“民族的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此时的中华民族已经成为拥有公民意识、领土主权、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大型“民族”。于国际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体”;于历史而言,中华民族是“多元”,多元一体格局便是对中华民族最好的总结。中华民族也是中国各兄弟民族对最高共同利益的认同,这一总体认同,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民族意识中的反映,不是主观上规定出来的。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这不仅给“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定了调,也阐明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高于各民族的实体,正是体现出他的政治性原则,这是其他各民族无法展现出的。而中华民族的政治性,则首先表现在国家认同或政治认同上,其次表现在文化认同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其民族成分都是复杂多样的,本国民族难免与邻国民族有同根同源者,但不能因为两国边界之民族同源而挑战本属国家的政治权威,不认同自己国家反而认同他国。民族之定义,也仅仅是在统一政权体系或完整国家形态之下而产生的理论阐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6)《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四、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上的各民族都存在着本族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统一,形成一个高于本族群体的政治共同体,与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者所提倡的“民族-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西方民族理论体系成熟于中国,但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分析中国民族问题时,则务必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西方民族相比,中国的民族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历史上的民族不少是现在民族的前身,前后有着血缘与文化的传承,这些民族并非直接源于简单的政治构建,而是经过历史的洗礼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磨合”相继发展而来。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民族理论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时,则往往出现不对标的情形。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过于强调政治主导性,反而忽视“族群-民族”的历史传承以及各族体原始的“共同体”基因,这本身就是一种伪论。中华民族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各民族团体的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历史疆域版图上。
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上的中国,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历史上出现过政权林立的现象,但各民族主体政权始终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族人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凝聚成伟大的中华民族,最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和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团结御辱,共同抗敌,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共同的民族利益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共同镶嵌在中华民族之中,“共同性要求民族联合,差异性蕴含着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互补性”(27)宋月红:《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在今天中国政治实体中,中华民族是国人最根本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