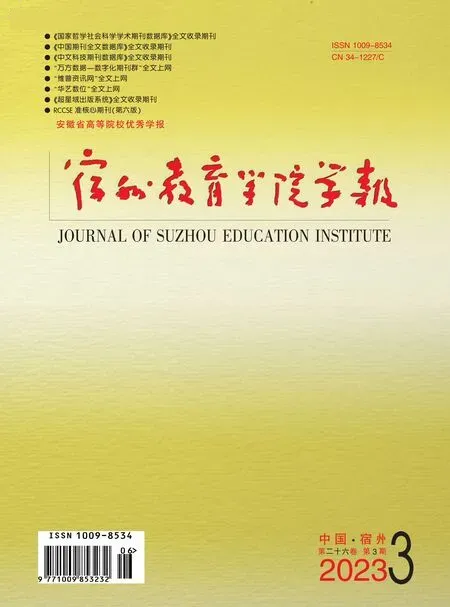缩期禁烟:清末新政后期浙江地区的禁烟运动(1908—1911)
李熠萧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清末浙江的鸦片种植远早于中国内地的其他地区,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有泛滥的趋势。 “台民以所获之利数倍稼穑,以子榨油,以叶肥田,以花包割浆煎卖,名曰台浆。 从前地方官因台民抗粮者多,种罂粟者完粮较易,遂之不禁。 ”[1]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金华、衢州、严州等府因战乱人口减损严重,多招温州、台州等地的客民移居,导致浙江土烟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2]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条约压力下开始将鸦片作为一种税收来源,开始施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 将进口鸦片称之为“洋药”,而本土产鸦片称为“土药”。 与鸦片合法化一并而来的是大量的厘税收入,从1887 年到1894 年每年洋药税厘共占同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中1888 年达到39.37%。[3]鸦片流通所带来的税收也成为浙江省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将禁绝鸦片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且伴随着1906 年的禁烟上谕的颁发, 中国再次掀起了席卷全国的禁烟运动。 而此时,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也紧跟中央步伐,进行了一场全面的禁烟运动。 1908 年,浙江在巡抚增韫的要求下, 为了贯彻清政府的禁烟方略,开始推进以“缩期禁烟”为指导方针的禁烟运动。当前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活动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 比如,潘崇[4]以锡良三次上书奏请缩期禁烟的举动及其结局反映出清末禁烟运动过程中中央决策、督抚政令、州县执行三方之间的矛盾博弈;马维熙[5]探究了全国范围内缩期禁烟政策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与利弊分析;钟声[2]探寻了晚清浙江沿海、山区鸦片种植的数量与地域变化, 以及对浙江农业的影响;卓辉立[6]以浙江为考察对象,探讨晚清来华传教士在禁烟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及意义;陈云樵[7]探讨了在清末禁烟运动中出现的以反禁烟为代表的社会失序与基层控制力下降等现象。 现基于《浙江禁烟官报》等材料,以浙江省为考察对象,探讨在增韫的领导下以“缩期禁烟”为方针所开展的禁烟运动在浙江地区的执行情况与所遇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烟禁与否及所用策略一直是朝野内外饱受争议的内容。 在清末时期,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烟禁无论是在国家政策还是社会舆论层面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在浙江省具体执行中却仍遭到了烟农们的强烈反对,长期的弛禁环境以及洋货税收反而让禁烟政策的执行在浙江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清末浙江禁烟运动的兴起
从一开始,浙江禁烟运动就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 为了避免因进口“洋药”而造成的白银外流与经济损失,清政府默许了本土鸦片的种植,试图以土烟来对抗洋烟。 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浙江的鸦片消费量和种植规模都开始迅速上升,1873 年到1889年,短短的十几年内,浙江省的鸦片产量从4500 担增长到12000 担。[8]269
但是, 土药的种植开放却并未有效遏制洋药的进口。1858 年鸦片进口开放之后,进口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861 年进口1514 担,1864 年就增长了一倍达3304 担,到1867 年则达5136 担。[8]106而洋土药并行流通甚至形成了不同的产品消费群体,温州的鸦片吸食者中有大概八成人只能吸食土烟,而洋烟和土洋混合烟土的吸食者加起来也才两成左右。[8]417在“寓禁于征”的方针之下,浙江鸦片的消费群体和生产规模都在不断上升,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虽然鸦片早在中国本土有所种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列强对中国的鸦片商贸输出才是导致鸦片在中国泛滥的元凶,两次鸦片战争更是明目张胆地迫使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 然而,到了20 世纪初期,与清政府下定决心禁烟的同时,国际社会关于鸦片贸易的局势也有了新的变化。
此时日本对清廷禁烟决策的影响较大,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使得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危机大大加深。 而当时的有识之士希望中国模仿日本,对鸦片贸易进行由政府垄断的专卖制度。 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初始国英国,在1906 年5 月30 日下议院的集会上,议员德雷称:鸦片的毒害已被各国公认,并且许多国家都立法禁止,英国继续维持这种毒品贸易会给英国人民带来耻辱。[9]但是,英国也不愿轻易放弃在华鸦片贸易的利润,担心如果清廷采用日本的方案, 那么英国的在华利益就会受损,从而迫使中国采用类似美国的方案, 并最终在1908年3 月与中国达成协议,签署《中英禁烟协定》。 该协议规定从1908 年开始, 每年来自印度的鸦片减少一成,也就是大约5100 箱。[10]251
1906 年9 月20 日,清政府明发上谕,决定在十年之内,将鸦片(无论洋药、土药)清除殆尽。 在禁烟诏书下达后的两年内,中国各地在禁烟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例如,为应对洋药的进口与鸦片的流通,浙江实行了强有力的禁运政策,宁波的浙海关报告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洋药……进口量由1905 年的1814 担下降为1906 年的1388 担。 在1911 年,只有412 担。”从数据上来看,从1907 年到1908 年的下降幅度还不算明显, 但是自1908 年之后,下降的趋势就变得尤为显著。 以浙江温州为例,1902 年温州洋药进口190 箱, 而到了1911 年则减到30 箱。[11]251但是,在针对土药流通的禁种方面遭到了较大的挫折,因反对禁种土烟而导致的官民对抗时有发生。 烟农与基层官员始终对于清政府能否长久贯彻禁烟政策持怀疑态度,时间一久便形成了上下拖曳,于是有官员提出应缩短禁烟期限。
为责令地方督抚全力禁烟,1908 年 《禁烟考成议叙议处条例》《禁烟稽核章程》接连颁布,自此在地方禁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层面, 也已日益严密。而后, 云南巡抚锡良在当年宣称云南已缩禁完成,其余各省呈请缩期禁烟的奏折便纷至沓来。 而清政府则采用了督办各省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的分年分省禁种之法, 其中浙江被规划1909 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全面禁种的策略。[11]6001于是更为激进的缩期禁烟策略在浙江地区快速推行。
二、官方禁烟政策与举措
1906 年,清政府禁烟令下达之后,浙江省即刻开始推行关于禁烟的各项措施,但浙江作为土烟的主要产地,其禁烟政策始终无法彻底贯彻。1908 年,增韫任浙江巡抚后,对浙江的鸦片问题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决定从烟土种植着手。 “浙省地近海滨,开通较早,四民之沾染烟癖亦较他省为多,欲禁其源必以严禁吸食、力惩私种为入手办法。”[12]并“查浙省著名产浆之区温台两府最盛,处州次之,宁绍又次之,其余府间有种者亦温台客民居多。 ”并在此之后又从禁吸、禁种、买卖管制等多方面推进禁烟。
(一)禁烟机构的增设
1908 年5 月,清政府在《禁烟稽核章程》中提出各省督抚应监督各府州县地方官设立官方戒烟局,而后规定了对断烟成效高的机构、人员进行嘉奖,并由各督抚奏明,嘉奖以虚衔、封典、奖札、匾额、功牌。[13]
清政府的态度引导地方各省都积极设立禁烟机构,而增韫在杭州由绅商设调查社、禁烟局各一处[14],后设立全浙禁烟公所,并“订立分所章程,饬各厅州县就地分设”[15], 由当地士绅担任禁烟公所正副董事,至此,浙江各厅州县的禁烟场所迅速设立。 各地士绅热心组织禁烟联合会,弥补清政府力所不及之处。
在台州,“黄岩县王大令志鹤具禀省宪谓黄产浆素盛吸烟之人较他处较为多……与地方再三酌拟先就城设立禁烟局一所,邀齐绅学商界共同议决投票举董规定章程酌收浆行膏店领照费及增收膏浆各价以充禁烟公费。 ”[16]
湖州长兴县当局“严禁并派管带亲兵稽查复于城中设立禁烟局,定职守,施给戒烟丸。 ”并规定“凡烟膏店……每两捐洋一角一分,请以四分解膏捐总局,七分留作禁烟开支。 ”[17]在衢州,“球川地方领得王县令照会并戒烟告示遂组织戒烟分局一所。”[18]严州分水县“提倡对于禁烟尤形严密,现已捐廉,首设官立戒烟局,规则办法既从实际……按浙江其实吧厅州县报告戒烟局成立者,实以该邑为首不可。 ”[19]嘉兴萧山县余大令“详报宪台略谓萧邑虽有戒烟集义社会……难以措手,兹经会绅议定,拟暂借工艺所余屋设立禁烟分所。 ”[20]
而除了由政令下达所公建的禁烟局等机构,各地士绅所自发创办的禁烟社等也不断出现,温州永嘉县各大小烟馆已经“严申禁令已一律闭歇。 ”[21]而后因县令更换有复起现象,但在当地士绅徐伯英等人在当地设置了调查禁烟社,并按照官方杭州禁烟社的章程办理。 绍兴嘉善县“仿照嘉秀办法添设禁烟调查会。 ”[22]
在成立诸多禁烟机构之后,浙江更是借助新式媒介,发行《浙江禁烟官报》,将关于禁烟事项的政令、措施、各地新闻汇编起来,希望借助这一举措刺激读报者进行自觉的禁烟行动,进一步促进烟毒禁绝。
(二)禁种措施的实行
增韫于1908 年7 月30 日就任,不出一月以白话文发布《浙抚禁种莺粟示谕》,其中提及“地方官绅予限劝禁而农民贪图厚利阳奉阴违,反而书差以生财之隙……从本年秋季起浙江全省一概不准再种莺粟了……莺粟不禁,鸦片的害断不能除,所以今年一定要把这莺粟禁绝了,你们绅商士庶也不论城镇乡村务须一体遵照,等到秋末冬初本部院还派官员四处查勘,一见烟苗立时拔弃,地亩充公,还要拿种烟的人按名治罪。 ”[23]
在增韫对浙江地区土烟泛滥的清晰认知下,浙江各地开明乡绅随即协助成立各类禁烟组织。 “各府热心人士同时组织禁烟联合会, 以辅官力之不及,劝惩互用,成绩大彰。 ”[24]在此指导方针下,浙江省根据《禁烟查验条例》中的要求:“分别此地举行严禁种烟,以绝来源。 并体察所属种植之多寡或分年减种,或全行禁种,均责成地方官遴选公正绅士,分投劝禁,不准假受胥吏,以期害除而民不扰”[25]而由于《中英禁烟协议》的签订,洋药的输入规模日益降低,浙江随后依照本省盛产土烟的特点,将重心放到了禁种方面。
自此,浙江各地掀起了禁种罂粟的风潮,宁波鄞县黄大令“日前照会鄞属禁烟局绅董亲赴各乡切实调查烟亩禁种莺粟兹据覆鄞属各乡只有咸祥、大嵩、 尖峙等三处地临海滨向植莺粟近已减少百余亩,自奉示禁以后已于十月起一律改种五谷。 ”[26]宁波市象山县邓大令“以象浆为著名土产利之所在难保乡愚不复踏故辙……爰于日前亲冒风雨会同凌委往历南乡按亩履勘。 ”[27]
在台州,黄岩县卢子鸣大令“划除烟苗甚为严厉……筹议勒令各地保每人招士兵八名各携锄头,由卢令亲率下乡到田划拨。 ”[28]并“许邓太守自设禁烟调查局,郡城烟间已一律封闭,兹又派员至六邑查禁种烟,饬令农民一律改种杂粮,责成绅董地保认真劝导,不许再行布种。 ”[29]
处州“有平垣之地种植罂粟要皆张叚畸零统计三十余亩当以分年减之法原施行于素产浆土之区。”[30]温州“吴太守日前电禀省宪略谓二月十九日督队回郡沿途拔烟数万亩,调查平乐泰三邑渐就肃清永玉二邑寥寥几惟瑞安地广民顽, 经此次痛拔大半,合属统计已减十之八九,知府拟于日内周历勘除,以期肃清。 ”[31]在禁烟令下达之后,因为各地执行从而成效卓越。 “原禁种之始,系于秋后,莺粟播植期间即分饬印委各员偏历查勘勒令改种杂粮,至来春复饬府督县再勘,遇有烟苗发现随时犁除,并将种户分别惩罚,历届办理无异,乃自去岁以来烟浆锐减,土价过昂。 ”[32]并且,这一政策一直坚持到辛亥革命前夕。“温台二府案奉抚宪本道详严禁烟亩改植杂粮并商由吴绅坐镇于明春专收菜籽小麦, 不论多寡一律销售, 一矣出产。 ”[33]到1911 年9 月,浙江温州、台州两地当年共铲除烟苗30 多万亩,杭州、嘉兴等地铲除烟苗共8800多亩,绍兴私种鸦片已被根绝。[34]
(三)销售管制与禁吸措施的推行
除了禁止鸦片种植, 为进一步减少鸦片规模,浙江开始针对鸦片的买卖资格进行管制。 1909 年,浙江巡抚增韫决定编定受官方统计的鸦片店铺,并发放牌照,以官方掌控代替私自贩卖,以期逐步减少鸦片直到禁绝。[35]更有甚者提出了“烟籍”管理的概念,试图将烟土的销售、购买者全员编籍管理。[36]而烟土牌照的涨价频率也相当快,嘉兴“剪土二钱者亦收小洋一角,四月二十七日……剪土每钱须缴照费一角。 ”[37]
浙江在禁烟期间曾经有咨议局议决后公布的《筹备禁绝鸦片和各稽察零卖章程》,其中规定烟膏店数目不准添设。 1909 年后,浙江对吸烟牌照发放也开始严格控制[38]而对于这些措施的弊端,浙江也进行了相当的整治。 “照会禁烟公所会同警局彻底查清,已将各店牌数积欠详细列表具报到州。 ”[39]并且执法更是严格到了仅2 角价格的鸦片买卖也会被巡查队查处。[40]并且对于烟土买卖也课以重税:“每膏一两捐洋一角一分,以三分留禁烟局作经费,八分解总局。 ”
而关于消费人员直接相关的禁吸政策也随着禁烟令的下达一并制定, 并且在1909 年前后的缩种政策下达之后也同样呈激进化。 1909 年12 月12日,浙江巡抚增韫颁布《禁烟条例》(共十二条),严禁鸦片的种、制、贩、售、吸,违者处以四等(一年未满二月以上)及五等(三年未满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以1000 元以下罚款。[41]并且迅速推进相关禁烟机构的设立,如禁烟公所:“尤以严行禁烟为第一要务……旧有禁烟局、调茶社各一处,均系绅商公立,未能遍及全省……参酌本省情形,设立全浙禁烟公所。 ”[42]同时,增韞严禁兵士的吸烟行为:“嘉防水陆各营队徐统领人骥禀陆师第五队勇丁吸烟,请惩办……吸食洋烟为军营大忌……惩办斥革私开烟室。 ”[43]
在增韫过激的禁吸与销售管制下,浙江鸦片泛滥的情形得到了控制。 根据宁波海关记录:“在许多地方, 反对鸦片吸食的文告得到了大众的热烈支持,许多近来才开始吸食的人已经戒掉了。 禁烟谕令的成效体现在烟馆关闭和罂粟种植面积的缩减上。 所取得的成果与地方官和绅士的努力成正比,各地罂粟种植成为固定产业的程度和大众吸食的普遍程度对于禁烟成果影响也很大。 ”这些描述充分肯定了在缩期禁烟政策所起到的作用。
三、禁烟政策的局限性与困局
浙江在清末禁烟运动中的表现可谓大动干戈,成效卓著,在禁烟策略由“渐禁”转为“缩期”之后,在一系列禁烟相关法规的约束下,从数据上看,浙江的禁烟效果堪称卓越。1910 年,杭州第四季度所发放给鸦片吸食者的许可牌照相比第一季度减少了八千多人,嘉兴登记的零销商由三位数降低至个位数。 鸦片的流通、售卖和消费得到了肉眼可见的约束。
但是, 这种情况只限制于政府可控制的范围内。 浙江鸦片的本土种植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初具规模,经过长时间的“寓禁于征”政策后,在清末禁烟运动时期,缩期禁烟对禁烟成果在短时间内要求成效违背了部分群体的利益,未能妥善处理类似矛盾,以及清末由于在各方面的革新导致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等原因,造成缩期禁烟极强的局限性。
(一)财政困难的加剧
晚清时期,在寓禁于征的政策指导下,鸦片的税厘抽成早已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 以1905 年为例, 清政府财政总收入至多不过15,000万两。[44]而当年洋土药的税值合计就高达22610478两。[45]占到当年财政收入的15%左右,在土烟产地较多的浙江,这个比例可能更高。 而在禁烟运动中,由于根除鸦片的时限相当紧迫,这就意味着在短短几年内,洋土药的税值会大幅下降。 这对同时期开启大量财政缺口以推行新政的清政府来说并非易事。
而在增韫主政浙江时期, 不但要广开税源,而且还要节减政府的财政支出。 但为了推行“缩期禁烟”的策略,就必须投入资金支持各地官办的禁烟机构。 在缩期禁烟的政策环境下,浙江各县都积极开办官立禁烟机构,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有关禁烟的财政支出也在持续增加。 绍兴“余姚办理禁烟经费不敷,拟请将石塘捐款分拨数百元以向民间收买种子劝令耕种有益植物。 ”[46]即使是一省之首的杭州,“于潜县戒烟局自光绪三十三年九月间开办以来颇著成效,唯开办年余局中医药薪水以及一切开支全赖土膏店捐款以资经费,兹因土商皆多歇业,上年局用经费不敷至四百四十元之多,均由局董李炳南设法借垫,今岁店少利微,情形更难,以致戒烟局经费无出,公议停办。”[47]也就是说,禁烟机构的经费来源就是其禁烟的目标,其运转的效率越高,财政供给就越是捉襟见肘。 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自然是当时财政困境的一种反映。
而在财政收入方面,瓯海关十年报告(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指出:“必须注意到,鸦片税厘减少致使平均水平下降,除非有大量出口地方产品以补偿减量, 税收走低将在预料之中。 ”[48]而由于1887 年之后土烟产量的增加,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将税收重心转移到了土药税厘上,并将其作为新军军饷的重要来源:“溢收之数,另储候解,专作练兵经费。 ”[11]5320-5321但是,由于禁烟运动的快速推行,作为练兵经费的土药税源自然大打折扣,清政府又认为“近来各省认解练兵经费之款,多未照解,尤恃此统税溢收之项源源接济。”[11]5320-5321也就是说,在禁绝此项税基的同时,也要求此项税收数目不得下降。并且为了弥补洋土药下降的税值,更是开征牌照捐,并言明各省因禁烟事项而税收锐减,最终只能“奏以盐斤加价抵补土税,如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六省应得加价钱文足敷额款且属有余。 ”[49]在这种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混乱管理中, 关于烟土的税收项目反而不断增加,一方面严禁种鸦片,奏请拨给禁烟经费, 另一方面却被要求将土产鸦片转卖所得的土药税厘转而用作其余持续的开支, 在禁烟成效明显之时却要求烟税收入不得下降,否则,就另开他捐,以维持其他项目的正常运行。
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开支,浙江地区各类税收都进行了加码,各项存银也不断降低。 以杭州关为例,1908 年时,第一九十结征收“洋药厘金二万八千一百七十六两,旧管存银七万五千七百四十一两。”[50]而仅仅一年之后,第一九四结征收“洋药厘金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四两,存银三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两。”[51]都呈现下降趋势。而移解数目则从“浙省添募水师购置船械经费银一万两”增加到“防饷银三万两”,收入下降但支出上升,如此持续下去,必将入不敷出,到了1910 年,杭州关的旧存已经仅余“八千六百九十四两”[52]。入不敷出,由此可见一斑。而浙江“兹查预算各款一千五百九十四万零,又据监理官电禀可增加税契及诉讼状费并膏捐牌照等款二十万计共一千六百十四万零。 已较元年收数增出百数十万以出款相抵,尚余银四十余万……所列各款为数已达四百八十余万, 驻防俸饷等项三十余万……仍不敷二百三十余万,如此巨款自应由浙省就地另筹,或将军政费切实核减,仍照清理财政局原编数目开列,别无弥补之策。 ”[53]
实际上,寄希望于当时的浙江政府能够根绝鸦片问题是不可能的,在上文中提到鸦片税收是浙江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当禁烟运动开始后,财政收入就会出现巨大空洞,鸦片税收主要用途有:解部、解拨项、偿还各项赔款、内外债等等。 此外,鸦片税也是各省举办各项新政的重要经费来源,包括偿还各省分摊的赔款部分以及军饷。
由上述可知,每年数量可观的鸦片税收成了清政府赖以维持的经济命脉。 尤其是在禁烟运动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各类缺饷的通告,就连禁烟局的成立都无法由财政转款调拨,而是“允绅富官商分半担任”[54]。而兵勇的战斗力并没有随着禁烟运动而大幅提高, 对之后辛亥年杭州的起义有直接的影响。 即使是在抗击禁烟的过程中,民众也有将禁烟与新政等同的表现。 1910 年4 月,浙江金华有农民为反对禁种鸦片,从而攻进县城,捣毁大量学堂和鸦片店。[55]禁烟作为清末新政一大重要内容,在这里竟成为新政推行的拦路虎。
(二)烟农对禁种的反抗
在清末浙江的禁烟运动期间,浙江的土烟生产土地面积急速下降, 土烟生产数量也随之降低,但是,本土鸦片的生产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早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来源之一,浙江严厉的禁烟政策造成了严重的中下层民众不满。 并且在1905 年科举废除之后, 地方士绅与清政府的利益绑定不再严密,需要乡绅们参与推进的地方政策在执行层面上往往被掺杂了水分,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烟农反抗案例。 1907 年8 月,黄岩县烟农集体冲击并捣毁了当地土捐分局;1908 年2 月,台州仙居、太平两县烟农集结万余人抗议禁种烟苗;1909 年4 月, 遂安县出现官吏借禁种烟苗为名实行敲诈勒索,烟农以此为由在县署“哄闹”;1910 年3 月,温州府瑞安县农民结众反对查禁烟苗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地方上,由于禁烟的成效则直接与官员的政绩与去留挂钩,而地方官员往往操之过急,故甚至直接与烟农发生冲突。 以1910 年温州瑞安事件为例,“瑞安县金令嗜好甚深,绅民啧有烦言,上峰亦颇知之,惟表面办理禁烟表面似尚认真,以故,上峰不肯邃易生手近温处道郭派委员查勘烟苗,查至该境,突被烟户戕毙。”[56]在禁烟过程中直接遭人杀死, 其冲突不可谓不惨烈,而这也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官员因禁烟与当地烟农起冲突是常有的情况。 如1908 年12 月,黄岩县潘澧泉鸣锣“煽惑”众人反抗禁烟。[57]1910 年3 月,温州各属办理禁烟印委人员勒罚苛扰, 激起乡民暴动,并波及劝导士绅惨遭焚劫,倾家荡产多至十余家。[58]为反对禁烟而形成的民愤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是收效最为卓越的禁种方面, 也会因为执行层面出现重大波动, 在清末禁烟运动末期出现反复的情况。 例如,嘉兴“地方肥沃,罂粟栽种所在多有冒充台浆……该县陈大令并不出示晓谕禁令减重,又不下乡清丈饬种他物,故种烟转倍于前云。”[59]台州“地广人稠,历来种浆易米,小民一闻此禁,约定仍种烟苗……每户愿出一人听官惩办。”[60]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种情况就是烟农为了应对缩期禁烟时的处理方式,所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缩期禁烟策略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了糟糕的影响。
为了增强禁烟力度, 必须要强化监督者的权力,而在湖州则出现了冒充委员进行私人报复的事件。 “去腊下旬有徐某者面诘武康县洪子靖大令……派警兵帮同将店主王某弟兄拘住, 王坚不承认。”[61]而在牌照方面执照更换者计凡三次其执照系由官纸局代印,每换一次照费加价一倍,只计销照之畅旺,不问吸户之多寡。[62]
尽管清末浙江地方当局采取禁吸、禁种、禁售相结合的办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不仅吸食人员数量和鸦片的销售量双双减少,并且罂粟的种植面积也大幅下降,其采用的牌照制度与严格的查勘方式也对民初的禁烟运动有所启发,可是在清末危机重重的局面下, 将禁烟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向下传达,在浙江这样被本土鸦片种植荼毒已久的地区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明面上的数据都有所下降,但是对于下层种植者来说,没有可靠的替代品来解决民生问题,始终无法根治浙江的鸦片问题。
结语
在如此环境之下,浙江的禁烟运动获得如此巨大的成果是让人怀疑的。 实际上,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土烟种植的重新统计中,鸦片种植面积却增长到四十二万九千零七十五亩七分。[63]75温州地区据统计仍共有近三十万亩;台州地区临海、黄岩、宁海等县仍有近三万亩;宁波下辖慈溪、奉化、象山等地都有数目不少的烟田。[63]77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弹,大概率是因为清政府在推行“缩期禁烟” 时脱离当时浙江实际的社会环境,盲目达成任务要求,在铲除烟苗种植时并没有有效推行替代农作物,并且也没有断绝烟农、烟民与烟馆的供应联系。 从而导致整个禁烟运动仍然浮于表面,并未彻底解决浙江的鸦片隐患,从而导致民初浙江鸦片问题的复起。
禁烟作为必行政策在浙江落地实行时,从省府到地方县级官吏乃至士绅都积极响应,进行各项禁烟举措,虽然从一时看来成效显著,但是作为一个流传已久的长期问题,鸦片种植的根绝反而造成了财政、民生等更严重的问题,而缩期禁烟作为指导方针,则要求短期内杜绝洋土烟患,武断式的杜绝为禁烟作为其余如财政等问题的诱发原因进行周密的备案,导致这一指导方针无法对当时日益严重的财政、政府公信等问题作出回应,诱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在执行过程中,一边削减鸦片税厘的税基,一边又要求其完成其对于其余新政开支的支持,阶段性的现实要求和“缩期禁烟”方针最终要求的自相矛盾最终导致了禁烟执行的武断与失序,在相关措施难以配套推进的情况下强行推进禁烟,致使清政府在浙江的公信力严重损害。
作为一个目的正确、成效优越的政策,“缩期禁烟”却并未形成合力与示范,而是造成了各级执行层、决策层与受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成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而这种矛盾并非仅仅存在于禁烟运动中,而是在清末各地的多项改革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呈现,把握其底层逻辑的共性和具体表现的个性是深化认识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