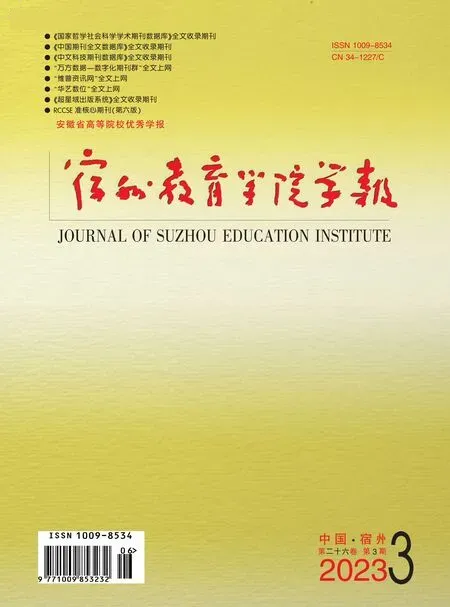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倾向的四重差异分析
李雯静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 安徽·宿州 234101)
20 年代的中国农村,农民艰难度日,手工业作坊纷纷破产,封建家庭加速分化,女性地位、封建伦理道德等各种问题日益凸显。 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乡土文学,即出现在20 年代初期。 乡土文学作家群成员多来自乡间而寓居大城市。 他们将笔触伸向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 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乡土文化,他们书写的内容主要是家乡的地域特色、 风土人情、关于国民性问题思考、带有乡愁悲剧色彩人物或事件等。
乡土文学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当是鲁迅和沈从文。 二人是典型的、不同叙述倾向的文学大家。 鲁迅的倾向是“揭丑”,而沈从文的倾向是“构美”。 以鲁迅为代表的“揭丑”倾向派,通过对乡村的旧习俗、旧道德、旧传统的深刻批判,揭示病态社会的丑与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构美”倾向派,则通过对乡村人情美、人性美、自然美勾勒,构建出健康、自然、诗意的生活状态。 “揭丑”倾向与“构美”两大倾向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四层差异: 崇真与尚美、国民性批判与健全人性重构、 真实刻画与诗性写作、无奈逃离与深情回归。
一、审美追求:崇真与尚美
文学创造首先是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认识活动。 真与美作为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体现着作家不同的美学趣味。 鲁迅的美学趣味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这里的“真”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反映, 更是对生活真实的超越,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真实的发掘与表现。 鲁迅作品里,乡土小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创作中,鲁迅一方面把底层农民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实关系中加以再现,展现了一个未经彻底革命、社会动荡的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 另一方面,从不对人物作表面描述,笔触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与灵魂。 《药》通过华老栓形象的刻画,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悲剧性;《孔乙己》中对于主人公孔乙己穿着的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1]458, 只一句便道尽了封建旧式文人的酸腐和可怜的虚荣心,也从侧面揭示了当时不同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差别。其女性形象多农家妇女,或苍白呆滞,或尖酸刻薄,或勤劳善良,她们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经济和精神等方面的多重压迫。 其中,祥林嫂的形象和命运最为典型,单四嫂子也一样,受尽折磨;杨二嫂稍强势,贪小便宜、泼辣刻薄、见风使舵,但骨子里的“奴才”本性是没有变的。 她们一个个生活单调,固守常规,相夫教子,等级观念分明。 偶尔出来一两个不甘于现实、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的人来掀起一点波澜,不是沦为看客们的谈资,就是在悲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对于现实农村中人生世相的逼真描绘,是基于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采用冷峻客观的笔调,把强烈的情感隐蔽于不动声色的描绘中,力透纸背。
其二,“个别”与“一般”的统一。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多具有典型的意义,他们既是性格各异的“这一个”,同时又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包容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 《阿Q 正传》中,那个努力想把圈画圆的阿Q,不仅仅是特殊个体,也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是底层麻木、不知所措、无力抗争又心怀希望的大多数人的缩影。 《离婚》中的爱姑泼辣而凌厉,但又卑弱而胆怯,外强中干、以强凌弱。 不可否认,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抗争意识的人,但由于势单力薄,最终不得不妥协。 因为离开了丈夫,她没有任何的出路和谋生手段。 她的委屈和担心就如她自己所说:“‘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有这么容易的? ‘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2]149,两个“不要我”道尽了那个时期女性的无奈与对未来的恐惧。 鲁迅并不只是揭示她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深刻反映了扭曲的社会形态和封建思想对人性的迫害、对女性的无情摧残。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则表现了对于 “美”的向往与追求。 这里的“美”与作家的审美追求有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性美。 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人性,且多为健康、有活力的人性。 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可爱、善良、明朗。 在他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里,住着这样三类人:一是青年,如龙朱、柏子和豹子,“威仪如神,温和如羊”;二是中老年人,如腰背微驼的翠翠爷爷和老水手,朴素善良,正直勤劳;三是美丽宁静的少女:翠翠“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3]64, 萧萧个高又勤劳——“一个夏天中,一面照料丈夫,一面还绩了细麻四斤”[3]256,跟妈妈一起生活的三三单纯率真,连妓女、娼妇也善解人意、充满人情味。 《边城》里写道:“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3]70他们一个个形象饱满,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与活力, 努力而认真地活着,散发着令人向往的气息,表现出作者对人类美好健康本性的追求。
其二,风情美。 沈从文小说的环境一般都是青山绿水、河边人家、船只往来、客栈林立,且水往往是那种清澈、纯净的山涧小溪,优美恬淡。 《边城》自不必说,风景宜人,如同桃花源般,徐志摩赞为“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在童养媳萧萧生活的村子里,夏日光景如梦,人们饭后歇凉:“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子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 远近声音繁密如落雨,禾花风悠悠吹到脸上……”[3]253。 《长河》中的秋是这样的:“秋成熟一切。 大河边触目所见,尽是一年来阳光雨露之力,影啊到万汇百物时用各种式样形成的象征。 野花多用比春天更美丽炫目的颜色,点缀地面各处。 沿河的高大白杨银杏树, 无不为自然装点以动人的色彩,到处是鲜艳与饱满。 ”[4]小说中的人物多活在大自然里,远离城市喧嚣,诚实热情、善良勤劳,在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楚地风情中自在生活,代代相续。
其三,民俗美。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5]沈从文小说里多次写到湘西独特的风俗,多民风淳朴。 比如:《月下小景》中小碧主摊佑与睡梦中的女孩夜晚对歌,柔美而甜蜜;《边城》里的端午节,喜庆且热闹;《萧萧》中的婚嫁、出生仪礼;还有一些独特的宗教习俗等也写得细腻生动。 每当节日到来时,人们总会放下农事,放下先前的不快,置办东西,走亲访友,肆意玩闹,心里充满了喜庆和欢乐。虽然一些民俗现象本即客观存在的,但体现在小说里则反映了沈从文先生独特的审美理想,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执着,对健康纯洁人性的向往,对淳朴民风的眷恋,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
由以上可以看出,鲁迅通过现实主义崇“真”的美学原则,通过想象、幻想、并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进行艺术加工,化“丑”为“美”成为审美对象以表达深刻的寓意。 而沈从文反对一切扭曲人类健康本性的东西,笔下的人物、风俗等很大程度上是他尚“美”理想的对象化体现,糅合了作家的深情与厚爱。
二、叙述立场:国民性批判与健全人性重构
鲁迅的小说里,“立人” 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也是其乡土小说叙述的基本立场。 然而,鲁迅的“立人”思想并不是从正面来体现,而是以对国民劣根性深刻批判的姿态来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探讨,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达到启蒙的目的。可以说,鲁迅的整个创作,基本上都是围绕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思考这一命题展开。
小说集《呐喊》《彷徨》对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礼教的揭露和批判极其深刻。 小说重在表现群众的愚昧麻木、冷漠自私,既揭露了封建势力造成的人民物质上的“病苦”,更着重暴露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苦”,以惊醒“不幸的人们”。 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闰土等,他们以自己被侮辱、被剥削的血泪人生,控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荒谬。 其中,贫困雇农阿Q,生活潦倒,精神上却时不时以“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麻痹,以便与他人发生矛盾时能获得一点可怜的自尊。 他既害怕革命又迎接革命,既自尊自大,又自卑自轻。 鲁迅以这一人物形象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底层劳动妇女祥林嫂,她丧夫,逃离,又再嫁,丧夫,丧子,她勤劳却命运坎坷,受尽人间冷暖,几次对这不公的命运进行了反抗,却在悲剧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在热热闹闹的“祝福”之夜孤零零死去。 鲁迅以祥林嫂的命运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对人的戕害。 孔乙己作为一个文人,酸腐又清高,好吃懒做,还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时常因为偷书被人打,身上偶有伤痕,但他却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1]458在他看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体面的,其他的生存手段多少有点不那么光彩,然而,最终他的生活难以为继,且改不了偷的习性,而被人打断了腿。鲁迅对以孔乙己为代表的旧式文人既有同情更有讽刺,并以此来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心灵的扭曲;作为《呐喊》集中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则直接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历史的“吃人”本质。 有学者认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7]。 可以说,整个鲁迅的乡土小说,都贯穿着“批判”这个链条。
在沈从文那里, 人性是其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湘西世界”,即是他在现实基础上以诗意之笔重新构筑的精神栖息地。 美学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持有这样的观点,“想象中的一切来自想象之外,这意味着想象不是自我生成的, 而需要外部的刺激”[8],也就是说,这种精神栖息地,绝非无中生有,而是有着现实的和经验的基础。 一方面,湘西作为他生长的地方,祖父曾是高官,小时候家境还算富裕,可以说,他在湘西这块土地度过了较为温馨的童年以及少年时期,因此,当他拿起笔来重新审视这片土地, 必然会在笔尖流露出对故乡的情感与爱;另一方面,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也是作者“湘西世界”产生的原因。 自1922 年来到北京,这个大都市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中, 滋生了一些享乐、浮躁、奢靡的不良风气,传统文化道德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瓦解,沈从文置身其间,却深感不适,与之格格不入,在对城市文化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体验之后, 故乡便作为一种参照, 通过对故乡美好、诗意、宁静、自在、淳朴的描绘与重构,对抗城市文化虚伪、浮华、冷漠、非人性的一面。
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他所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一个美丽而温馨的所在,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态,赞美这里的风俗美、人性美、人情美。 湘西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无不美好、淳朴、自然。 他所精心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亦凝结了自己对于人性美的所有美好品质。 翠翠如同自然的女儿:“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为人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3]64。 《三三》虽然没有专门描写女孩三三的外貌, 但通过阅读不难发现她“很聪明,很美”“很俏皮”,拥有“小小的美丽嘴唇”。由于湘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属性,在这片土地上还生活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反映在小说《月下小景》《雨后》《龙朱》《采薇》里,则充溢着一种雄健且舒展的力量,一种源自自然本身的原始野性,一种浓烈而真实的情欲。 一句话,在“湘西世界”里,他重构了美的自然、健全的人性,活泼泼的生命与力。
三、写作方式:真实刻画与诗性写作
在鲁迅的创作中, 采用较多的即是写实手法,包括人物、情节、细节的真实,以直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与思考。 而沈从文则追求一种恬淡宁静、温馨自在的审美意境,以写意的笔法赞美不曾被污染的自然以及健全的人性。
作为绍兴人的鲁迅,在其许多小说中,一些地点和人物故事发生的场景都可在其故乡找到具体对应,形成了鲁迅小说中较为独特的“文学地图”。有学者以周作人的回忆文为基础,探讨周氏兄弟文学空间与真实空间的重叠与交错,并指出:“所谓的‘文学地图’, 是指明确以绍兴为背景的12 篇鲁迅小说里的地点所构成的‘小说版图’,周作人不仅将小说地名还原到历史地图之中,并解析了小说地点与实际地点的各种关系。 ”[9]鲁迅的小说里,多次出现鲁镇、咸亨酒店、未庄等,都可找到现实对应。 小说中的许多地点和场景不仅仅只是故事发生的场地,也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这些“满熏着中国土气”[10]的大地上,人们日复一日地过着自己简单而平庸的生活,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风浪出现,他们会一直这样过下去,贫穷、单调、麻木也沉重。 由于鲁迅采用的是写实手法,这里的鲁镇等地可以说是当时广大中国土地上众多乡村的“这一个”,它萧条、落后、凝滞,没有色彩。
提到沈从文不能不说他所精心刻画的湘西世界,他自小在那里长大,熟悉那里的一切,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以一支生花妙笔抒写出来,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幅优美动人的湘西风情。 湘西世界里有水、有船、山洞、吊脚楼、码头、美丽的女子。 不可否认,沈从文小说里的地点、 故事场景也有故乡的影子,但这些地方已经夹杂了沈从文个人感情并经过了他的审美理想的沉淀,而更偏于写意。 他在《我的分析兼检讨》提到:“作品中不论改写佛经故事,或直接写农村人事, 通过头脑, 都一例成为抒情诗气氛。 ”[11]相较于鲁迅,沈从文笔下的风景描写篇幅更多也更优美,一些风俗及环境可以说是人物本身的外化,且有一种理想的意味。
另外,在语言运用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鲁迅的乡土小说数量不多,语言简洁,多采用白描手法,只写主要的几个人物便使作品节奏明快、 言短意深。在《狂人日记》中,看不到堆砌华丽的辞藻,看不到冗长的景物描写和心理刻画,用极少的语句便把狂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了。 小说《药》开头的景物描写, 短短38 个字, 便刻画出了古老中国乡村的沉闷、闭塞、压抑。 由于鲁迅所处的特殊时代和他的多疑反向思维,使其小说的语言、人物和内在肌理都呈现出一种隐喻性。 他善于借古喻今,从不刻画表面,不把话说完说尽,言未尽处留给读者自己体味。有些小说里还融汇着杂文写法, 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鲁迅艰深晦涩的文风,这也是鲁迅作品被一些人抱怨读不懂的原因之一。
沈从文则不同,用他那支生花妙笔,以诗意的笔调、浪漫的想象为我们建构了一幅幅桃源般的梦幻湘西。 他曾说:“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12]375。 “文白杂糅”的语言使其小说自带一种诗性。 他对茶峒人及生活描写:“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4]67质朴淡然、超凡脱俗,别具一种诗般的意境美。 “晚风中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 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 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 ”[3]279写景优美如画,写人也别具一格。 如写龙朱:“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 是人中模型。 是权威。是力。 是光。 ”[13]读来语速由缓而快,富有节奏感。
四、情感归属:无奈逃离与深情回归
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之所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述倾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与故乡之间的双向情感关系。 一方面,故乡养育了他们,此时的故乡具体且实在,具体到一棵树,一条河,一片麦田,一声声来自母亲的呼唤,这是主体在长期的生活与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习惯、方式、气息、记忆;另一方面,主体之于故乡,前提是主体离开故乡,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在传统乡土中国,以农为生的人们“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4], 不同的乡村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稳定且孤立,构成一个小的熟人社会,代代相续。 从某种程度上,只身远赴他乡多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鲁迅和沈从文都曾离开故乡,在经历了外面生活的风风雨雨之后,返乡之念则油然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故乡不只是那一方土地, 而更多的是一种集情绪、情感、思考、想象等多方面因素于一体的抽象性所在。准确来说,“故乡”是一种精神意象。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主体的经历、学识、修养、性格、视角、审美、情感归属等的不同,便呈现出不同的故乡风貌。 这一风貌当然也影响到文学作品,如果说鲁迅是以逃离的方式接近“故乡”,沈从文则是回归“故乡”。
1898 年,18 岁的鲁迅第一次离开故乡绍兴去南京求学,1902 年鲁迅官费留学日本,4 月初到达。留学生活长达7 年, 鲁迅学到了新的思想和文化,但日子过得并不愉快, 由于古老中国的贫困落后,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人便是弱国子民,他们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中国留学生。 这期间还曾发生过“找茬事件”,鲁迅曾因成绩在一百余人中名列中间而被日本学生怀疑是藤野先生向鲁迅泄题,甚至写匿名信骂他。 这件事对鲁迅打击很大,以至于他后来说:“中国是弱国, 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1]317在他乡的不愉快, 很容易在心里激起对于故乡的思念。在日本4 年后的一天(1906 年夏),鲁迅接到一封故乡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归”,原来是家里给他准备了一门婚事,对方是旧式女子且长他三岁的朱安。 作为长子,他默默接受了,但这不幸的婚姻后来却一直困扰着他。 不得不说,此时的故乡不但没有给予他温暖,反而多了一层难以言说的苦涩与无奈。 鲁迅最后一次回乡,触目所见为:“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1]501这即是小说《故乡》开篇的句子,萧瑟、苍凉、破败,没有活气。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返乡实则是为了告别故乡,并举家搬到了北京八道湾。 小说写道:“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1]510有学者对此说,《故乡》中的前后两幅画面展示了作者“背对故乡”[15]式的决绝姿态。 以后鲁迅便没有再回过故乡。 不可否认,这样的无奈选择与对故乡的决绝也影响了后来他的乡土小说写作底色。
回到沈从文,15 岁时,也就是1917 年,沈从文第一次离开故乡,1922 年到达北京,即“由一个苗区荒僻小县,跑到百万市民居住凡事陌生的北京城”[12]372。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和学历较低(仅受小学教育),在生活、求学各方面都面临困难,很难真正融入大城市的生活。 后来由于母亲病重,第一次返乡,他将自己的爱、欣喜、同情、期待融入笔端,详细记录了沿途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这就是后来的《湘行散记》。 正是这样浓烈的故乡之情,使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不诗意、美好、宁静、自在。直到1982 年5月,沈从文最后一次到故乡凤凰探亲。 他一生走过风雨无数,但故乡于他,一直牵挂在心,所谓“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乡一盏灯”。
面对故乡,一个沉重,一个温暖;一个失望,一个期待;一个彻底搬离故乡,一个几次在现实或者回忆中回归故乡。 当然如此简单对举并非要得出鲁迅于故乡的冷漠,离开故乡后他也曾给朋友透露过“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16]。 爱之深则恨之切,鲁迅对于故乡的逃离,与他的性格有关,与他沿途之观感有关,与他方向思维模式有关,更与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挖掘有关,他以一个孤独的远去背影诠释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决绝与彻底。 而沈从文的故乡或者说他的乡土小说里所呈现的也不只是温馨诗意和美好自在,在其田园牧歌式的叙述背后亦有悲伤、忧愁、不满、失望。 学者王德威说得好:“故乡之成为‘故乡’,亦必须透露出似近似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象魅力。 当作家津津乐道家乡可歌可记的大事时, 其所贯注的不只是念兹在兹的写实心愿,也更是一种偷天换日式的‘异乡’情调。”[17]只是沈从文的回归,是他以故乡为参照,构建“希腊小庙”的艺术努力,是他审美理想的艺术折射,是他骨子里的柔和与对理想人性的执着追求,亦是对自然自在生活状态的艺术呈现。
结 语
作为乡土文学大师,鲁迅以“真”为审美追求,以写实的笔触,意在“揭丑”,批判国民劣根性;而沈从文则以“美”为审美追求,以写意的笔触,意在“构美”, 重构健全的人性和理想的生命形态。 在这背后,亦凝结了作家对于故乡的复杂情感,鲁迅以决绝而彻底逃离的方式留给“故乡”一个孤独远去的背影,而沈从文则以田园牧歌的方式呼唤“故乡”之美。 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叙述倾向呼应互衬,共同构筑并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之塔。 尽管视角不同,风格存异,但其忧国之情,忧民之心,对人类永恒主题的关注与思考,如烛如炬,成为后世乡土小说创作的不竭动力和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