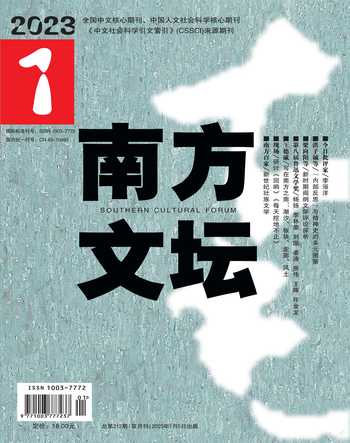“一片赤诚和捍卫文学纯洁的不屈精神”
王晨 刘继林

改革开放浪潮带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崭新局面,市场经济冲击着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崭新的文化浪潮。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内容上注重表现现实人生,形式上注重创新,是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审美享受。但是在90年代市场化经济浪潮体制的冲击下,文学创作开始转向对经济效应和市场效应的追求,因此回避现实矛盾与重大题材、追求“私人化”与“边缘化”的作品数量逐渐增多;而大众传媒和娱乐文化的兴盛也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选择①。在消费文学和娱乐文学大肆发展的背景下,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有1980年代的繁荣,人们阅读欣赏严肃的文学批评的耐心下降,“表扬式批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不良批评风气占据了上风。面对着丧失了传统批评精神的文学批评,世纪转型期,一批青年批评家凭着无所顾忌的锐气,以“保持反对精神和独立姿态”②的批评态度,不约而同地对当下文坛的某些不良现象和著名作家的“消极写作”发起冲击,他们的文章后来被结集为《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成为与不良批评风气斗争的珍贵记录和历史文献。本文将梳理《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以下簡称《十博士》)一书的出版概况、出版反响及对当代文坛的意义。
一、从《与魔鬼下棋》到
《十博士》
在《十博士》出版之前,文坛就已经对各种不利于文学健康发展的批评乱象感到不满。为了与风行文坛的批评乱象相抗衡,一些态度尖锐、风格严肃的批评文章逐渐在新世纪初的文坛上出现,如时代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以及中国工人出版社于同年出版的《与魔鬼下棋》等。在《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中,徐友渔思考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应该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在物质条件变化引起精神文化变化的当下,文学环境和文学自身的价值几何③。秉承着以优秀的文学批评来帮助公众掌握评价文学作品的尺度和方法的初心,形成有利于文学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氛围,《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编选了一批文字激进、态度直接的批评文章,以求与各式不良的批评乱象拉开距离。出于类似的目的,中国工人出版社于同年3月出版了《与魔鬼下棋》一书,对世纪初备受欢迎的五位作家——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二月河——毫不客气地开刀,呈现出与世纪初文坛的“表扬式批评”截然相反的批评态度。
《与魔鬼下棋》出版后,在苦于不良批评之风气的文坛内部大受好评。有评论认为,《与魔鬼下棋》一书,以及彼时已经在媒体上开展的“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运动,共同表现了激烈而理性的批评精神。而这种直抵世纪初文学批评痛处的理性批评精神是一次对已经堕落的中国文坛的拯救,对作家庸俗的审美情趣和奇缺的人文精神的揭露,以及敲响在所有人耳边的警钟,于是有人激动地宣称“终于出现了鲁迅的传人,终于有人不再沉默,终于有人愤怒了”④。
《与魔鬼下棋》大受好评,仅仅过了5个月的时间,那些对批评现状不满、渴望凭借一己之力扭转风气的青年评论家们乘胜追击,在文笔犀利、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李建军的号召和推动下,将王彬彬、王兆胜、赵勇、吴俊、傅谨、肖鹰、黄发有、邵燕君、刘川鄂包括李建军自己在内的十位青年博士富有真正批评态度的评论文章集结成书,编成评论著作《十博士》,以期能与不良的评论风气抗衡。
相对于《与魔鬼下棋》,《十博士》的批评态度更加端正,目标更加明确,批评姿态更加直接。端正的批评姿态,决定了其在纠正当代文学批评不良风气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图书市场上,《十博士》共有两个印刷版本,分别是2004年8月的初版,以及2007年5月的二次印刷版本,两个版本除封面设计以及价格的不同之外,并无内容上的差别。而其中初版版本的两个不同封面,也恰恰说明了刚出版时此书的热销程度。而《十博士》在三年后的再次印刷出版足以证明,尽管面向的多是专业读者,《十博士》一书仍以其勇敢、不妥协、直言不讳的批评态度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市场。这也是世纪初文坛对于不良批评风气的不满,以及对于真正批评态度的渴望的证明。
此外,在组织编辑《十博士》一书时,编者李建军所选文章大部分来自各位作者之前就已发表在各种杂志的文章。具体情况如下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十博士》编选文章的最早发表时间可以追溯至1992年,选择最多的杂志是《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这些杂志至今仍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前沿阵地。编选者在选择文章时注重以发表于新世纪前后、更能表现作者对世纪初文坛态度的文章为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论作入书,整本书以“拒绝随顺和盲从,拒绝服从市场的役使,拒绝依从权力的询唤”的勇敢态度,直面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些流弊,扭转市场化和经济浪潮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并作出校正的努力。《十博士》以集体亮相的姿态表明,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已无法继续忍受类似“表扬式批评”等不良风气,健康的批评迫在眉睫。
二、“直谏”与“直击”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线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消费主义,在物质层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文学、电影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开始强调文化产业的消遣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伴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文学中心话语权消失,文学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教化功能在市场作用下被消解,消遣娱乐功能在市场环境中大行其道。于是,为了迎合市场的趣味和市民们的口味,一大批只剩娱乐消遣而毫无精神内涵的作品在文学市场上横冲直撞。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和创作环境下,文学评论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平面化的市场价值和大众文化的冲刷下,文学批评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深度和锋芒,甚至为了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消费主义时代下的文学环境相一致,呈现出为迎合市场的需要而作、为左右市场发展而作、为批评自身需要而作的新特点。于是乎,文学批评的片面传媒化、泡沫化、粗暴化、表扬化等不良倾向随之呼之欲出,在文学评论场上横行霸道⑤。文学批评不再是直接击中文坛创作的利刃,而是成了装饰书籍的广告。在这样环境下,“文学批评已出现危机”一言,绝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刚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就曾经掀起过一场“博士‘直谏’陕西文坛”的文化事件。事件起因是《十博士》的编者李建军在《〈白鹿原〉评论集》研讨会上,对陈忠实的创作、目前评论界存在的问题以及贾平凹的《怀念狼》做了发言,语言尖锐,轰动陕西文坛,形成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文学事件。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直谏”的释义为“直言规谏”,《孔子家语》有云:“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时隔4年,由李建军领军,秉持真正批评态度精神的青年学者们,已经从对文坛的“直谏”变为“直击”。“直谏”的行为是自下而上对于位高者的劝谏,态度直接且言语尖锐,其目的是期望以此引起位高者的重视并做出改变;而“直击”则把自己和对象放在了同一层面,以更坚定的姿态进行“攻击”。由忠言逆耳的“谏”变为动作更为直接的“击”,隐藏在背后的批评态度更加坚决,也更富有攻击性。在面对笼罩着阴霾的文学批评,仅仅是言语上忠言逆耳的“谏”已无法继续推动改变的发生,而只有更富有攻击性的“直击”,才能从根本上激起文坛对僵化的批评现状的重视。茨维坦·托多洛夫的话常常被引用:“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兩种声音的相汇。”“文学与批评无所谓优越,都在寻找真理。”⑥直击,就是一种平等的、坦然的、不卑不亢的对话与寻找。
当代文学批评的危机暴露了当代文学的危机,而文学的危机也正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回到《十博士》一书,它的出版以犀利、理性的文字,正面宣告着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复苏,对打破如一潭死水的当代文学批评无疑是有所裨益的⑦;经历了二次印刷的《十博士》,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有需求才有再次印刷,也正是因为有阅读的必要才产生了需求。
在这篇跋文的最后,作者效仿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提出了新世纪文学改良的“八条”。暂不讨论这“八条”提出的权威性和合理性,但是作者与广大的文学批评者的愿望都是最朴素的:重振刚健的文学精神,将其从颓废和萎靡的泥潭中拉出。总的来说,《十博士》是当代文坛的一道灼目白光,引导着文学批评的前进方向。
三、对新世纪初文坛的意义
作为《与魔鬼下棋》的升华和延续,《十博士》进行的是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坛批评的残缺和畸形现象的批判工作。《十博士》一书的出版,不仅让人看到了新世纪文学批评新的希望,同样也是对批评界不良之风的一次有力的纠正。
在《十博士》问世之后,其秉承的真正批评态度给它带来了大量好评,不论是对整本书的编写态度,还是编写者的价值立场,其反响和评价均以正面为主。如在《十博士》刚上市之初,朱竞便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编者李建军的文学信念和批评态度,认为当代文坛缺少的正是李建军“容不得任何人对文学的亵渎”的精神,也正是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的执着,促成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和自信。对于此书的编纂,朱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集合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不甘良知泯灭的十位博士,内中的诚实的忧思、睿智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容忽略的一页。”⑧2005年,张治国在《文学批评的表扬化倾向——从〈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说起》一文中,从《十博士》出发,重新思考了当下文学批评的病象,尤其强调了“表扬化”的批评倾向对批评界、作家、批评家乃至文坛未来发展的恶劣影响;而《十博士》的出版,对于纠正文坛这股不良风气无疑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这本书的问世,不仅必将打破当下文学评论界令人艰于呼吸的沉闷局面,而且必然让人们从这些敢于用理性之针、批判之刺去戳穿‘表扬化’评论所包装粉饰的文学气球的勇士们身上,获得正视现实的力量,看到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希望。”⑨韩伟和杨晓燕则将李建军、王彬彬、刘川鄂等青年评论家与李健吾“实实在在为艺术服务”的批评精神进行比照,认为他们是一批和李健吾一样的批评家,他们对文学的“一片赤诚和捍卫文学纯洁的不屈精神”,和当下枯竭的文学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甚至起到了“症候分析、治病救人”的作用⑩。
《十博士》的批评态度和批评姿态直接影响了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书中的观点和结论也成为许多评论文章所引用的对象。张治国在《对“精英文学”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概念做了细致的区分,并把对“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进行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表现出真正批评态度的余杰、王彬彬、李建军、刘川鄂等十位青年学者列入精英文学之列11。
某种创作成功之后,必然少不了的是和同类型创作的对比,《十博士》一书也不例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出版《十作家批判书》,以尖刻凌厉的批评态度,对钱锺书、余秋雨等作家进行猛烈攻击,其狂风骤雨般的批评仿佛宣告着新的文学批评氛围的到来。但是这种为了批评而批评的态度不仅与理性的、温和的批评相去甚远,而且在“否定了表扬化批评的学术虚妄的同时,又以极端非理性的姿态制造了新的学术虚妄”12;而《十博士》却以理性、勇敢、正视文坛缺陷的态度,直面世纪初文学批评暧昧的不良风气。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有诸如《十诗人批判书》《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等态度尖锐、语词激烈的批评。诗人、评论家刘春观察到这种市场现象,认为这是精明的书商在“表扬化”批评遍地的畸形的文坛现象中发现的商机,而这些只不过是“伪批评家”们眼中的商品,是用作利益交换的筹码13。
尽管《十博士》以真正的批评姿态直击批评乱象的中国文坛,仍然有不少质疑《十博士》尖锐批评态度背后的目的的声音出现。邰科祥在《矫枉未必要过正——质疑李建军先生的“贾作四评”兼及文学批评的策略》一文中,对李建军的批评策略和尖锐的批评姿态提出质疑。邰科祥认为,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批评是冷嘲热讽式的“酷评”,是以完全的“唱反调”和“泼冷水”的攻击和作秀行为14。在邰科祥看来,李建军对于贾平凹的批评以及他拒绝温和的态度,并不是公正和客观的,而是带有攻击性的嘲笑和挖苦。但是,正如学者刘川鄂所说,严肃的、严厉的批评并不等于“不负责任地乱评”的“酷评”,“严肃的批评,是批评家基于良知、基于学理,对批评对象的客观评价”15。作家和评论家处于平等的地位,如果说作家从事的创作活动是审美价值的创造活动,那么评论家从事的批评活动则是对作家创作审美价值高低的判断。批评应是理性的,需要依据理论和方法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客观的评价。有时在作家眼里,批评家的批评也许是严苛的,是需要勇气面对的。如若一再逃避这样的批评,甚至冠之以“酷评”的名称,这样文坛风气绝不利于当代文学健康生长。而这也是《十博士》一书和拥有“真正批评姿态”的评论家们决心纠正之处。
综合来看,《十博士》的出版确是令世纪初文坛所欣喜的现象。此书的问世,不仅和畸形的批评风气划开界限,而且给了正常的文学批评生存和成长的空间。不仅如此,其批评精神也影响到了今天文坛。2017年11月,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秉承严肃的、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精神,试图营造更健康的批评生态和良好的批评环境。显而易见,这一套丛书的批评精神传承于《十博士》理性的、勇敢的、真实的批评态度,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态度,遮盖在当代文学评论场上的阴霾得以清扫,文学批评得到了新鲜空气的注入。
【注释】
①邱明正主编《新时期文学三十年:邓小平文艺思想与新时期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27页。
②李建军:《不从的精神与反对的自由》,《延河》2004年第7期。
③徐友渔:《关于文学的价值问题》,载朱竞主编《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第8页。
④余开伟主编《世纪末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第234-235页。
⑤张永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批评及其转型》,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⑥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175页。
⑦李建军编《十博士直擊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412-414页。
⑧朱竞:《“枭鸣丛书”编后(两则)》,《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5期。
⑨张治国:《文学批评的表扬化倾向——从〈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说起》,《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⑩韩伟、杨晓燕:《重识异彩:李健吾批评论》,《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11张治国:《对“精英文学”若干问题的探讨》,《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2张治国:《学术的虚妄:当下文学批评的表扬化倾向——从〈十作家批判书〉和〈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说起》,《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3刘春:《文坛边》,海豚出版社,2017,第176-181页。
14邰科祥:《矫枉未必要过正——质疑李建军先生的“贾作四评”兼及文学批评的策略》,《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15刘川鄂:《“狂妄”的作家与“坚守”的批评家》,《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王晨、刘继林,湖北大学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当代文艺创作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