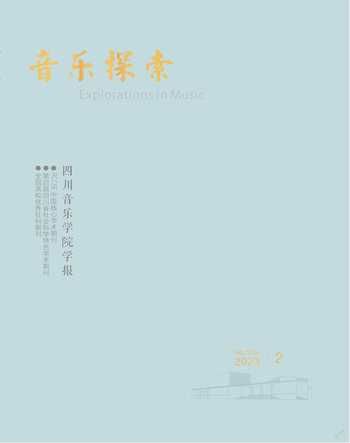北朝时期贵族阶层的乐舞生产与消费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USICAL DANCE AMONG ARISTOCRA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世家大族时代,门阀制度和坞壁经济决定了豪绅贵族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比肩帝王。雄踞北方的北朝社会总体具有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结构的复杂性、统治集团的地域民族性,以及丝绸之路的深刻影响,导致其音乐发展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北朝贵族阶层的乐舞经济发展状况,归纳在这一时期拥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贵族群体的乐舞生产与消费方式、成本与特点,以期探寻其总体音乐发展独特性的原因。
关键词:北朝;贵族阶层;音乐生产;音乐消费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3)02-0047-09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2.006
前 言
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时间跨度从公元386年(北魏登国元年)到公元581年(杨坚称帝,改国号隋),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5个相互更迭的政权,基本与南朝(宋、齐、梁、陈)对峙。
作为特殊的历史阶段,北朝的社会政治结构核心是鲜卑贵族统治下的门阀制度。虽然史学界常以魏晋南北朝的大历史时代为背景,讨论北朝社会政治结构的兴衰流变和文化属性;但从北朝政治和文化的特殊性来看,理应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做切片式的横向历史考察。故本文试图借鉴社会阶层学的理论,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音乐经济发展是否也具有典型性、特殊性。当然,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世家大族和官员豪绅为主体的贵族阶层。坞壁经济和政治特权导致其从生活饮食到娱乐消费都极尽奢华,竞相蓄妓之风弥漫,宴飨酣歌夜以继日;大量的文士官员对江南文化的追求和优美世族门风的建构,又促使其乐舞生产具有典型的江南文化品格。
因此,从经济学视域来看,北朝贵族阶层的音乐生产与消费是社会音乐经济发展的主要构成维度。其中,生产环节的核心范畴是生产者、生产方式和产品内容,消费环节的核心范畴是消费的方式与成本。在中古伎乐前期这一宏观背景之下,北朝贵族阶层的乐舞经济呈现何种特点?这是本文试图以梳理大量文献的方式返回历史语境去分析和描述的主要内容。
一、北朝贵族的自主性乐舞生产与消费
魏晋南朝名士风流,贵族文士、官员竞相参与乐舞生产,此种风气在北朝也极为盛行。一些贵族文士、权臣常常以歌舞创作、表演为风尚。从艺术经济学维度来看,这种生产方式具有典型的自主性,即贵族、文士自觉充当乐舞生产者,积极从事乐舞生产活动,其乐舞生产的目的是自娱、众娱或情感宣泄,并不是获取物质或经济上的回报,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特定场合的娱人行为存在一定的政治目的。因此,从生产的方式、内容和目的来看,北朝贵族的自主性乐舞生产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朝夕宴歌”的乐舞行为
门阀制度给予了北朝世族纵情声色的资本,无论是官宴还是私宴,酒酣之际,宾主双方或高歌,或弹琴,或即席而舞,或“以舞相属”①,形成一种其乐融融、把酒言欢的氛围。对此,文献记载颇丰,如北魏丞相尔朱宴饮酒酣之际“必自匡坐唱虏歌”,在家里也常常“与左右连手踏地,唱回波乐而出”②。宴飨之中,“以舞相属”成为当时贵族圈的风尚。如《魏书》卷五十四载,宴飨之际魏高祖亲自带头起舞,为太后上寿敬酒“群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③。《魏书》卷七十三载:
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杀缚之势。④
帝王宴飨如此乐于进行“以舞相属”,在文士贵族的宴飨之中,更是频繁。“以舞相属”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于贵族宴飨的一个交谊性乐舞活动。
这种宴飨之风在达官贵族之中形成了一种“朝夕宴歌”的乐舞生产消费现象。对此,《北齐书》有着详细描绘:
后除司州中从事。时将还邺,会霖雨,行旅拥于河桥。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时节,作此声也,固大痴。”游道应曰:“何时节而不作此声也?亦大痴。”⑤
(二)“颐养神性”的乐舞行为
所谓“颐养神性”,是指这一期的贵族文士深受魏晋南朝文士风流的影响,常常以掌握乐舞技艺为基本素养,内心向往隐居式的田园生活,藉乐舞生产自娱,实现修身养性之目的。如北魏大臣孙绍之兄孙世元善弹筝,常以筝自娱;相州刺史李安世之子李谧“惟以琴书为业” ⑥;平恩县候崔光“取乐琴书,颐养神性”⑦;著作郎宗钦“肃志琴书,恬心初素”⑧;秦州刺史赵煦“好音律,以善歌闻于世”⑨;光州刺史郑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悟而写得” ⑩;
北周时期高平檀翥,能鼓瑟;等等。据统计,北朝时期以善琴著称的官员繁多,除上述及记载外,还有世宗挽郎谷世恢、著作佐郎柳谐、尚书仆射崔亮、文士陈仲儒等。
(三)“乐以佐食”的应诏行为
接受帝王诏令,在宫廷宴飨为帝王及参与宴飨者进行即兴式的乐舞生产活动,这在北朝极为常见。如北齐时期,齐武成皇帝常在内廷宴飨让中书侍郎祖珽弹琵琶,齐郡太守和士开跳胡舞。①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时,命宗室大臣孝珩吹笛,孝珩举笛裁至口,泪下呜咽。②此种活动,一方面是当时的帝王、臣僚都普遍掌握一两门乐舞技艺,常常在宴飨中相互表演;另一方面是帝王诏令臣僚进行乐舞表演或臣僚主动在帝王宴飨中进行乐舞表演,大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乐舞生产就成为政治利益交换的重要媒介。
当然,娱乐帝王的乐舞行为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为了表达对帝王的谄媚之情而主动自觉地进行乐舞生产。如《魏书》所载,京都仕女为了献媚帝王(魏孝文帝),自发创作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后纳入乐府,合乐奏之。③
(四)“情思所感”的清商杂曲创作
相和歌和清商乐舞是个体自发性乐舞生产的主要产品类型,也是贵族文士为了追求情感抒发而进行的主动性乐舞生产行为。根据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记载,北朝贵族文士创作了大量的相和、清商作品,如北魏宰相高允创作有瑟调曲《罗敷行》;北周昌州刺史王褒创作有瑟调曲《日出东南隅行》,吟叹曲《明君词》,平调曲《燕歌行》《從军行》《远征人》,清调曲《长安有狭斜行》,瑟调曲《饮马长城窟行》《墙上难为趋》;西魏到北周时期的名臣萧捴创作有相和曲《日出行》;北魏到北周时期的贵族名臣庾信创作有吟叹曲《王昭君》《明君词》,平调曲《燕歌行》《从军行》,楚调曲《怨歌行》;北齐大臣魏收创作有楚调曲《棹歌行》;北周文士徐谦创作有平调曲《短歌行》;北周赵王创作有平调曲《从军行》;北周尚法师创作有瑟调曲《饮马长城窟行》等等。④
创作杂曲以抒发情感也是北朝文士自觉乐舞行为的一个典型现象。所谓杂曲,《乐府诗集》云:“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⑤
据统计,这一时期的文人贵族创作的杂曲很多,如祖叔辨《千里思》、温子昇《结袜子》《安定侯曲》、魏收《齐瑟行》《永世乐》《挟瑟歌》、邢劭《思公子》、王褒《轻举篇》《游侠篇》《陵云台》《古曲》《高句丽》、蕭捴《霜妇吟》《劳歌》、庾信《出自蓟北门行》《苦热行》《结客少年场行》等。《乐府诗集》还收录了庾信创作的10首《步虚词》,并在题解中曰:“《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 ⑥
显然,北朝文士官员、贵族豪绅竞相创作清商曲、相和曲和杂曲,一方面是由于北朝文士官员中有一批来自南方的士人,另一方面也是深受江南文人风骨影响。
(五)“寄之亲朋”的挽歌创作
汉魏南朝厚葬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挽歌在北朝也比较盛行。士大夫多在丧葬活动中进行创作,所谓“临死,作诗及挽歌词,寄之亲朋,以见怨痛”⑦。如北魏温子昇曾创作《相国清河王挽歌》以悼念清河王元怿,其辞曰:
高门讵改辙,曲沼尚余波。何言吹楼下,翻成薤露歌。①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二》记载了北齐名臣祖珽创作的挽歌:
昔日驱驷马,谒帝长杨宫。旌悬白云外,骑猎红尘中。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②
当然,如果在丧葬活动中从事其他自发的乐舞娱乐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伦理秩序,还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如神武第十一子高阳康穆王湜在文宣帝去世的时候,兼任司徒,导引梓宫,但其行为是吹笛,又击胡鼓为乐。结果被太后杖责百余而死。③此虽令人唏嘘,却有力地说明了北朝贵族阶层对丧葬活动乐舞生产消费具有严格的规定性。
(六)“曲水流觞”的乐舞行为
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迭频繁,战争时有发生,但宗室成员和官宦子弟却过着一种奢华的理想生活,竞相模仿和追求江南士人“曲水流觞”的诗意境界,游宴雅集之风盛行,所谓:
及勾芒御节,姑洗之首,散迟迟于丽日,发依依于弱柳。鸟间关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听乃越于笙簧,望有踰于新妇。袭成服以逍遥,愿良辰而聊厚。乃席垅而踞石,遂啸俦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宾奉万年之觞,主报千金之寿。……弋凫雁于清溪,钓鲂鲤于深泉。张广幕,布长筵。酌浊酒,割芳鲜。起白雪于促柱,奉绿水于危弦。赋湛露而不已,歌骊驹而未旋。跌荡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间。人生行乐,聊用永年。④
受此风影响,北齐著名诗人、左仆射祖珽不仅自己善弹琵琶,能为新曲,还常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并常与友人陈元康、穆子容、任冑、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⑤北周著名文人庾信创作的《对酒歌》也生动描绘了文人雅集歌舞娱乐的消费行为: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琴从绿珠借,酒就文君取。牵马向渭桥,日曝山头脯。山简接倒,王戎如意舞。筝鸣金谷园,笛韵平阳坞。人生一百年,欢笑唯三五。何处觅钱刀,求为洛阳贾。⑥
简而言之,上述音乐生产消费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为了抒情达意而进行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二是为了宴飨欢愉而进行乐舞表演。这类生产消费包括主动行为的乐舞表演和被动行为(被邀请、被帝王诏令)的乐舞献艺。从生产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相和、清商、杂曲、挽歌等创作,以及弹琵琶、操琴、吹笛、唱歌、击胡鼓等表演。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音乐形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贵族阶层的乐舞审美取向和文化品格。
二、北朝豪绅贵族“私家部伎”乐舞生产与消费
魏晋南朝是世家大族的时代,北朝社会依然具有此种属性。世代沿袭的世族、豪绅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他们拥有政治和经济特权,拥有大量的宅邸、良田。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坚实的政治资本导致他们竞相过着奢靡的生活,私家蓄妓和乐舞娱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主要方式。这就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文士、贵族个体自发性音乐生产的新方式,即以恩主所蓄妓乐人员为主体,以家族为单位的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别生产。但在家族内部,每一个私家部伎又天然形成了一种简单的、小规模的协作生产,形成了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闭环,其核心是以私家恩主的消费喜好为转移或改变,所以它的生产性质具有典型的娱他性。
从文献来看,北朝私家蓄妓现象不亚于魏晋南朝,如北魏光禄大夫高聪“有妓十余人”①;骁骑将军夏侯道迁“妓妾十余,常自娱兴”②;徐州刺史薛安都从弟薛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奏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③;河间王元琛“有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④;高阳王雍所蓄乐妓多达千人,其中技艺高超者有美人徐月华、修容和艳姿;⑤等等。
现今遗存的大量北朝贵族墓葬中的壁画、石刻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蓄妓之风盛行。如在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东北齐武安君王徐显秀的墓葬中,有壁画生动刻画了当时贵族拥有大量私家乐妓的情景:男女主人安坐于床榻之上,举杯饮酒,面前杯盘陈列,食物丰盛。两旁多位男女乐人手持琵琶、箜篌、笙管等,随时根据主人的指令进行乐舞表演。 (见图1)
《洛阳伽蓝记·城南》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贵族私家部伎乐舞生产方式和产品内容:
(高阳王雍)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美人徐月华善弹琵琶,能为《明妃出塞》之歌,……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火凤舞》。⑥
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上的乐舞图像,也描绘了这一时期贵族宴飨中私家乐妓进行乐舞生产的盛况。壁画中,主人端坐中央,或主人举杯或宾主双方举杯共饮,周边私家乐人林立,或演奏琵琶、箜篌、腰鼓,或吹奏竖笛、排箫,或朱唇轻启缓歌低音,或身着胡服,拍手、甩袖、扭腰、踢腿跳胡舞。⑦
贵族让私家乐妓从事乐舞生产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私家乐妓跟随恩主参与战争,并作为恩主攻城掠地的一种策略或工具,如《洛阳伽蓝记》卷第四载:
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每临阵令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镇戎竖。⑧
(河间王琛)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屢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①
乐舞在战争中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未曾可知,但恩主在战争中使用私家乐妓进行乐舞生产,扩大了私家乐舞的使用范围和功能,体现了私家蓄妓行为的音乐生产消费本质——一切以恩主的需要为宗旨。这些私家蓄妓没有独立地位,只是作为私有财产、私有工具属于恩主个人所有,是恩主的专属消费品。
三、北朝贵族乐舞生产消费的奢华成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音乐生产与消费行为。显然,北朝时期,以帝王为中心的皇室和世族、豪绅掌握着社会资源分配权力,包括音乐资源的分配权力。因此,贵族豪绅这一特定的阶层为满足个人娱乐需求所进行的乐舞生产与消费根本不计成本,其豪奢程度甚至连王室成员都自愧不如。如北魏时期,冀州刺史王椿“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妓自适,无乏于时” ②;骁骑将军夏侯道迁“于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园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伎妾十余,常自娱乐,国秩岁入三千余匹,专供酒馔,不营家产”,并以孔融诗“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为标榜。③ 但到其子夏侯夬的时候,其奢华的乐舞宴飨消费导致“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犹数千余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饥寒”④。齐州刺史李元护“妾妓十余,声色自纵”⑤。高官王超也“性豪华,能自奉养,每食必穷水陆之味”⑥。南安王余则“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日之间,帑藏空罄”⑦。高阳王 “给舆、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⑧。连陈留候李崇也自叹不如,说“高阳一日敌我千日”,所以被认为是“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⑨。但河间王琛却极力与高阳王争富,“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柰朱李,枝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⑩。
北齐奢侈之风依然盛行,如北齐东莱王韩晋明日常生活是“一席之费,动至万钱,尤恨俭率”;清河王岳“性华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陈鼎击钟,诸王皆不及也” ;元晖也是“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犊”。以此为据,这些豪绅贵族拥有庞大的乐舞生产群体,从事乐舞生产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所以,为了支撑这种享乐生活,豪绅官员倾其所有。
从文献来看,北朝贵族豪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食封、俸禄、赏赐和经商射利,尤其是利用手中特权进行经商射利,是支撑贵族乐舞消费的重要基础之一。史载北魏咸阳王元禧“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①。北魏大长秋卿刘腾利用私权进行贸易,“岁入利息以巨万计”②。即便是“牧守之官,颇为货利”,如果俸禄、良田、互市还不能支撑消费支出,部分贵族则选择“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的腐败行为。当然,这种奢靡乐舞消费核心基础是豪绅世族自身拥有的强大政治、经济特权和大量的良田宅邸。
四、北朝贵族乐舞生产消费的显著特点
(一)乐舞生产者对恩主的严重依附性
《魏晋南北朝史》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族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这种封建关系的形成,隶属性是极度强化的。”③因此,学界也把这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归纳为“庄园农奴制”。这充分说明北朝时期乐舞生产者(私家乐妓)是音乐资料上的无产者,音乐生产资料、音乐产品,连同乐人自身都归恩主所有,即豪绅贵族是音乐资料和音乐产品的占有者和使用者。张振涛先生亦说,这一时期的私家部伎属于最底层的贱民或奴婢阶级,没有独立地位,完全依附于贵族,这是具有奴隶制特征的隶属关系,恩主可以自由支配乐伎们的生命,尤其是女性乐伎与恩主的另一重依附关系——作为妓妾对主人的依附关系。④
因此,基于这种隶属关系,北朝的乐舞生产与消费对于乐人来说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深受权贵恩宠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如前文所说的乐人田僧超、朝云、徐月华、修容、艳姿等,或因美色,或因技艺而深受主人恩宠,其地位如同妻妾、好友,随身相携,亲密无间;一是被当成普通私产随意处置,命运极为悲惨,尤其是当恩主们一旦因某种原因不能再继续进行乐舞消费时,就逼迫这些乐妓烧指禁弹、吞炭哑声、出家为尼,抑或迫害致死等等。如北魏高阳王为宰相时,乐妓成群,生活极为奢华,但死后“诸妓悉令入道”,人数高达数百。⑤北齐尚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卢宗道曾在晋阳置酒,以私家伎乐招待宾客。席间,中书舍人马士达看到弹箜篌的女妓,夸赞曰“手甚织素”。卢宗道立即把此乐妓送与士达,士达固辞,但“宗道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⑥。因此,残酷的现实环境导致这些私家乐妓只能为自己的恩主服务,听从于恩主的指令,以专业化的乐舞生产谄媚于恩主,从而强化这种隶属关系,以获取生存保障。
(二)乐舞生产消费的封闭性
权贵阶层乐舞生产消费具有典型的封闭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特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它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政府限定了乐舞生产者的户籍属性,导致乐人社会阶层固化,不能自由地流动和交往。如北魏政府将从乐人员界定为乐户,配为贱民,强调“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①。显然,固化的社会身份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乐舞的传播。
其二,政府限定了樂舞生产消费的阶层性,所谓“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②。这显然是人为地固化了不同阶层的乐舞生产消费内容,阻断了乐舞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更是剥削了普通民众的乐舞消费权利。
其三,豪绅贵族在“庄园农奴制”基础上的“私家蓄妓”行为,天然阻碍了乐舞的流通。它表现在世家大族、豪绅官员等恩主将私家乐妓完全等同于私人器物,所蓄乐人与恩主之间是具有奴隶制特征的隶属关系,这导致其所蓄乐妓的音乐生产行为基本局限在豪绅官员的私家厅堂、庄园之内。即便是恩主年老生病或死亡,作为私有财产的乐舞生产者也常常被毁掉,以此来阻断私家蓄妓的乐舞生产外溢传播。这就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狭隘的音乐经济模式。
(三)乐舞生产消费的双主体性与江南品格
所谓“双主体性”是指北朝时期的音乐消费总体上与魏晋南朝一脉相承,兼具魏晋南朝的典型时代特征,即整个社会乐舞生产与消费活动存在两个基本并行的主体: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和以贵族豪绅为中心的庄园坞壁。社会音乐生产消费的主流由这两个主体共同构成。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贵族阶层基本把持着国家的政治资源,并拥有大量的土地、雄厚的经济基础;皇室权力则相对羸弱,以致部分世族豪绅在生活上的奢侈程度比肩皇室。如辅国将军乐逊曾云:“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皆尚奢靡。”③社会奢靡的风气导致豪绅、贵族竞相蓄妓,规模庞大。另外,北朝豪绅世族在坞壁之中竞相学习魏晋南朝的文化风尚,其音乐活动与江南社会的人文思潮、北方宗教文化紧密相连,与世家大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导致音乐产品、消费娱乐都深深带有江南世家大族的审美风尚和文化品格。在很多情况下,“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④已经成为北朝士族子弟娱乐审美和生命追求的至高境界。
因此,庄园坞壁之内,无论是私家蓄妓人员的规模还是乐舞产品的种类,总体上已经比肩帝王庭院,这实际上已经导致音乐生产消费的重心从宫廷转移到了世家大族的坞堡之中。
结 语
北朝贵族阶层的乐舞生产消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既保留了魏晋南朝的文化品格,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应该与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属性有关。前后5个政权的核心统治集团虽是少数民族,却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与魏晋南朝一样的社会属性——门阀世族统治,这说明北朝国家的选士制度如南朝一样重视门第。世家大族和地方豪绅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财富和政治特权,甚至被人为限制在一个独特的阶层范畴之内,卓然引领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帝王和贵族门则积极巩固和建构这一特殊阶层的文化品格和审美属性,正如魏孝文帝所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①亦如《魏书》云:“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②说明当时世族门阀制度深入人心,世族内部强调家风学养,阶层观念鲜明。
当然,经济的繁荣也为贵族阶层的奢侈乐舞生产消费提供了扎实的经济基础,《洛阳伽蓝记》中所描绘的“四方民众、天下商贾群集,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金银锦绣”的国际化大都市洛阳、平城、邺城等涌现,进一步增加了豪绅贵族的财富基础。豪绅地主的强权政治结构进一步推动了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坞壁经济——坞壁在坞壁主的统率下从事战斗和生产,坞壁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③
在文化层面上,北朝虽为鲜卑族统治,但各民族大融合是时代主流,社会文化多元发展,汉儒之学盛行。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帝王不遗余力地推行汉化运动,导致贵族阶层也非常重视学习汉族文化,尊奉孔子、礼遇儒者、振兴经学,江南士人的审美风尚、世家大族的家风学养也在北朝贵族阶层中得以传承。
综上,北朝贵族阶层的乐舞经济活动,虽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但总体依然与魏晋南朝相近,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本篇责任编辑钱芳
收稿日期: 2022-12-21
作者简介:韩启超(1977— )男, 博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11)。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usical Dance among Aristocra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N Qichao
Abstract: Wei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a period typical of kindred clan. The system of dominant family and fortified building based economy make the power of the aristocracy parallels to that of emperors. Having this general feature of the times, the Northern Dynasty has its peculia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due to cultural diversity,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system, regional nationality under different hierarchies 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ical dance economy among the Northern Dynasty aristocrats and summarizes the way of it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cost and characteristics to explore how this peculiarity in the music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come into been.
Key words: the Northern Dynasty,aristocrat,musical production,musical consumption
- 音乐探索的其它文章
- 川南合江汉画像石乐舞图像考A STYDY ON THE STONE CARVINGS OF MUSICAL DANCE OF THE HAN DYNASTY IN SOUTHERN SICHUAN HEJIANG COUNTY
- 文献记载与现实关照Documentation and Reality: The Stories of Performance in Ancient Chinese Music Documents
- 论清代湖北礼俗音乐文化的社会属性The Social Attribute of the Musical Culture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in Hubei in the Qing Dynasty
- 游于城:宋代成都城市音乐略考THE CITY MUSIC OF CHENGDU IN THE SONG DYNASTY
- 东北站人群体的文化嵌入与音乐遗存考The Cultural Embedding and Musical Remains of North-East China Zhan ren Group
- 铜磬考述A STUDY ON BRONZE CH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