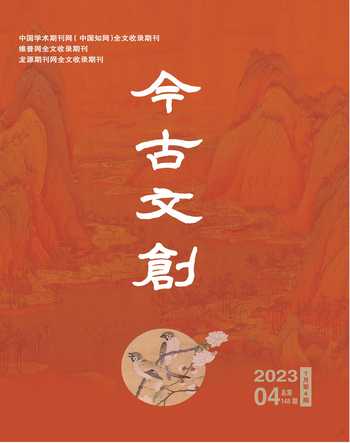平等、辩证、多元:张柏然先生译论观
董君 方嘉琪
【摘要】 如何看待中国译论传统、中国现代译论以及西方译论?中国当代译论该怎样发展?这些已成为亟需回答的难题。通过研读梳理张柏然先生发表的文献著作,尝试以张柏然先生宝贵观点进行回答。张柏然先生秉持平等、辩证、多元的态度看待各方译论,倡导以现代译学理论为基点,理性借鉴西方译论优势,继承更新我国传统精华,发展特色与普适并存的多元当代译论。张柏然思想为中国当代译学发展提供了参考方向。
【关键词】张柏然;当代译论;中西译论;辩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4-010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4.032
张柏然先生是我国资深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一生发表出版众多学术著作,仅知网收录文章就高达58篇。张柏然先生极具前瞻性,早在1997年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跳脱出传统的中西二元对立,张柏然在谈及中西译论时不仅关注中西整体译论批评对比外,更注重中国译论内部的古代译论传统与现代译论的古今对比。而其相关论述大多立足于当代译论建设,可概括为平等、辩证、多元等特点,每种特点中都蕴含了张柏然关于中国当代译论建设问题的前瞻性回答。
一、平等
新时期以来,众多西方译论引进国内,促进了译学研究的繁荣兴盛。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交际翻译等诸多西方译论,每一种译论的引进都成为了焦点,激发了国内学界的热议。我国长期引进西方译论,译论发展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而与此同时,西方却较少引进我国译论。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流模式,中西译学的关系也因此失衡。以建设发展我国当代译论为立场[1]2中西译学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与西方译论的对话模式应是平等沟通交流,这种“平等”是建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倡在中西对话交流中,客观看待中西译论。
张柏然多次探讨西方译论,在其学术期刊与著作中,张柏然先生的中西“平等”的主张显现为秉持对中西译论的批评与肯定并存的态度。翻译本体论是张柏然先生的研究重点之一,知网中收录的张柏然先生第一篇文章——《翻译本体论的断想》于1998年发表,早在那时张柏然先生便已重视翻译本体论。张柏然先生认为本体论的研究指的是“存在本身”,而“(作)译者、(作)译品和读者”只是“在者”并非“存在本身”。《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一文以翻译本体研究为着眼点,总体评价了西方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研究,肯定了语言学派的研究带领翻译研究由过去的经验模式,逐渐走向科学化;批评了结构语言学家诸如雅各布逊、韩礼德,“将翻译研究视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结论的补证”,在功利性前设下开展翻译研究,其研究结果偏向研究的工具性目的,结论的普适性因此受到影响[2]。针对奈达关于翻译过程的三阶段划分,即分析、转移和重组,张柏然肯定其中分析和转移两个阶段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层级性,但批评了其未从客观、经验角度描述翻译过程,导致“不具备可操作性。”
文化学派中的多元文化系统论主张“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于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3],并认为翻译研究应注重同人类社会中的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系统联系起来。但張柏然先生指出该理论“实质就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接受和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2]504,批评该研究从译学研究偏移到了比较文学研究范畴,“质言之,翻译的文化研究回避了翻译的本体研究”[4]。
要建设发展我国当代译论,这种“平等”不仅应存在于中西译论交流中,还应存在于古今译论交流之中。当我国部分学者对西方译学盲目崇拜逐渐消失时,却有部分学者走向另一极端,打着“复古”旗号盲目尊古,将古代译照搬过来盲目在现代语境里使用。不可否认,中国古代译论蕴含着中国独特的民族特征,拥有着中国传统意蕴价值。但并非所有古代译论都能取来今用,时代背景在发生变化,当今的翻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与古代翻译所面对的已然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正如张柏然所言,“在未来的理论体系中,虽说是一部分中国古代译论资源取得了话语权,但也不是局部的复古,而是古代译论某个命题或范畴在现代意义上的激活”[1]2。古为今用并非是简单照搬照抄的复古浪潮,而是使古今同样进行平等对话,肯定部分传统意蕴价值,批评已然不符当今时代发展的过时思想,将肯定的部分投入现代的意义中重新阐释进行激活。
二、辩证
张柏然先生明晰中西译论以及中国古今译论间的差异性,阐述其联系性,以辩证态度看待不同译论交流与发展。辩证态度是张柏然先生平等态度的进一步深化。
中西译论差异首要体现在二者的偏重不同,特点不同。中国译论从佛经翻译时期起便着眼于翻译实践过程中所遇困境以及译者难题,偏重实践。其中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讲述了佛经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五种失去了佛经原本面目的情况以及译者翻译的难点。中国译论拥有鲜明的美学特点,“表现在以中和为主、讲求和谐,尚化实为虚、讲求含蓄,重感性体悟、讲求综合”[5]。而西方则更注重译论的系统和条理性。例如法国翻译家多雷于1540年提出了翻译的五条基本原则。这五条原则依照重要程度排序,涵盖了译者的语言能力、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译文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翻译理论。其次,中国译论较为模糊,以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为典型;而西方译论则逻辑性较强,以奈达与纽马克的译论为典型。
从表象的中西译论差异向下挖掘,差异的根茎扎在文化以及思维认知上。着眼语言本身,各种语言之间的呈现方式以及内在的支撑结构就已展现出差异。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句子间的链接缺乏语法形态表现,以意串联,而英语则是形合语言。汉语以形写意,字形与意义有着某种理据性的连接,而英语以音表意,音与意义被强行连接在一起。从句子结构来看,“主语”体现了汉语与英语的差异。汉语中通常以“人”作为句子的主语,句子以“人”的角度进行展开。而英语中通常以“物”作为句子的主语。从语态来看,汉语常常采用主动语态叙述,而英语则多采用被动语态。语言密切联系思维,二者相互映照,语言的特性折射出思维特性。汉语与英语的主语差异体现了二者不同的思维模式。英语以“物”为主语,体现其物我两分的思维模式,清晰地将主体与客体分离看待,将客体作为研究对象,突出了客体意识,以客体作为发散的中心和立足点,表现为逻辑理性的认知方式。而汉语以“人”为主语,体现其“物我合一”的思维模式,突出了主体意识,表现为注重“人”的体验感知,直觉领悟性的认知方式。其次,英语叙述中,常常“开门见山”,首先提出句子的重点,体现其直线型思维。汉语叙述中,常常将句子重点“压轴出场”,体现其迂回思维。中式思维是“整体综合性”认知模式,人们倾向于以“援物比类”的方式,用比喻、拟人或者类比等说明“象”,以主观的感知体验概括描述事物。而西方则是“分析性”思维模式,倾向于理性地依照某种逻辑阐明事物。
明确认知差异性,正视中西译论、古今译论,才能使我们更全面更透彻地把握事物,辩证看待彼此关系。引进西方理论仍是丰富我国译论的途径之一,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中西对话只会愈加频繁。许多学者倡导对待西方译论应当秉持适当借鉴的态度。关于如何借鉴?借鉴什么?张柏然先生以辩证角度谈及了两点,指出了中西译论间的联系,一是借鉴“吸取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述”[1]20,二是借鉴西方译论的发展之路。中西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原语和译语社会语言、文化以及思维不同,但作为对于翻译活动这一实践活动的认知仍具有共性。中国译论或者西方译论都是围绕回答“翻译是什么?翻译什么?为什么翻译?为谁翻译?怎么翻译?翻译的重点是什么,是内容还是形式?”[6]等问题发展。而这些问题大多都是翻译实践活动的共性问题。提取出西方译论中关于翻译共性的思想精华,浇灌在中国的土地上,以期促长中国译论的藤蔓。其次,借鉴西方译论的发展之路。一是“对继承原有的体系和学术逻辑进行演绎”,二是“直接面对一些经典的文本,进行现代的阐释和重读”,西方译论的两条发展之路归根结底是对于“本土的翻译现象和翻译经验”的珍惜[1]4 。借鉴西方译论的发展之路是为了引起中国学者对中国本土翻译现象和翻译经验的重视,这二者是中国译论诞生的深厚力量所在。
当着眼中国译论内部时,在宣扬继承的呼声下,张柏然强调应“以史为鉴”,关注中国古今译论诞生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时代中,译者肩负着不同的时代任务,将自身体验经验总结升华为译学理论。古代译论传统中的“文质之争”的时代背景是东汉至唐宋时期,当时统治者引进佛经巩固皇权统治,译者的时代任务便是佛经翻译,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则是诞生于大量佛经翻译实践之中。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引进西学以求为当时社会带来新希望新气象,“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对当时民族救亡和启迪民蒙这一现代性的客观、积极响应”[1]26。而当代的时代任务,已从单方的引进,变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过去的百余年,不论是在作品,又或译界的理论方面,我们在“引进来”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当代我们更注重的是如何让中国优秀的作品以更好的姿态“走出去”。
事物间差异与联系并存,古今译论亦是如此。古今译论中都留着中华文化的印痕,蕴含着“中国特色”,其次有着翻译认知的共性。正是基于古今译论间的差异与联系,张柏然先生辩证地提出“激活”与“现代转换”的观点。以“激活”一词而言,其释义为刺激某物使之活跃起来。这其中有一层隐含之意,又或说几乎是学界的一个公认,中国古代译论在未来中国译论发展中必定发挥着活跃的作用。张柏然先生明确指出“激活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译论部分”[1]37。如何判定哪部分具有生命力呢?由于对于中国古代译论的种种争论皆是立足于当代译学的建设发展,因此能够助力解决当代翻译问题的古代译论便是仍具有生命力的。而激活的方式并非简单的拿来搬用,而是指完成对古代译论的“现代转换”。现代转换的实质是发掘古今译论的联系性,以现代视角重现阐释古代译论传统,助力当代译论建设。
当代译论建设要向何方发展?特色还是普适?张柏然先生多次发文呼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译论,但其对于“中国特色”的理解是辩证而非偏颇的。张柏然以辩证思想考量,认为强调中国本土传统哲学文化的“特色派”中国当代译论,与追求超越语言文化差异外的“普适”译论,实质上是矛盾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映照。普遍性依托于特殊性而存在,特殊性中必定包含普遍性,二者對立统一。追求中国特色译论还是纯翻译译论,其实质是追求个性还是追求共性的问题。中国特色为个性,纯翻译为共性,中国特色译论中必定存在普适的翻译译论,而普适译论从各种特色译论中提炼,二者从不同的研究点出发,但同样经过共性与个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任何事物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当代译论的建设不可缺少中国特色的个性,也不可缺少纯翻译的共性。张柏然所主张的“中国特色”兼具民族特色与真理普适。
三、多元
张柏然的多元译论观体现为立足于世界格局,思考中国当代译论建设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如何定位。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全球化进程,并非绝对的统一化,而是部分趋于同质化,部分趋于异质化。就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互补。文化因交流而焕发生机,因交流而保持紧跟时代潮流。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仍源远流长,其力量源泉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和而不同。民族文化的根深深根植于本土,早已处于稳定发展状态,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的结果只能是互相选择性的借鉴。多元共存才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化的追求目标。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置身于世界文化的格局之中,中国译论应呈现出积极姿态。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心,中国文化作为“他者”,本身便彰显着多元的光亮,应积极追求“对话”而非“对抗”,以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中西为例,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共存,使得中西文化彼此靠近,在交流中彼此汲取营养转化进自己的特色之中。
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当代译论建设应当发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发扬中国特色风格,这恰恰有助于中国译论与世界接轨。张柏然认为可以以矛盾体系中的共性与个性看待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世界性寓于民族个性之中,并通过民族个性体现出来,文化的民族个性则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人类共性。”[1]39 中国译论走出去,是在共性的基础上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平台,沟通民族文化的个性。若丧失了自身的民族特性,盲目地片面追求世界性,将陷入真正的“失语”境地。
四、总结
西方译论或中国译论传统,都并非完美无瑕,过度自卑或自傲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译论或中国译论传统都应以平等为基础进行交流。当代译论构建应以现代译学理论为基点,从西方译论对于翻译共性问题的描述以及发展路线中理性借鉴西方优势,激活更新中国译论传统,辩证看待中国特色理论与普适理论二者对立统一关系,发展特色与普适并存的多元当代译论,于世界文化格局中多元共存。
参考文献:
[1]张柏然,辛红娟.译学研究叩问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张柏然,辛红娟.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04):501-506.
[3]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04):21-27.
[4]陶李春,张柏然.对当前翻译研究的观察与思考——张柏然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7,38(02):66-71.
[5]张柏然,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J].现代外语,1997,(02):26-30.
[6]谭载喜.中西译论的相似性[J].中国翻译,1999,
(06):26-29.
作者简介:
董君,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方嘉琪,女,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