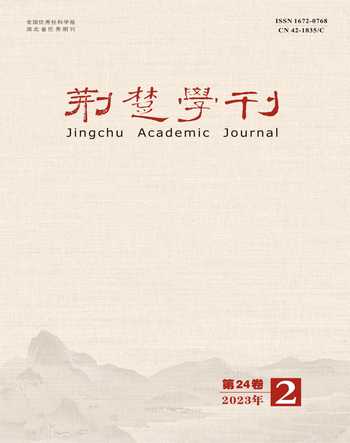对危险接受理论类型化的反思与重构
摘要:危险接受作为过失犯的违法阻却事由,如何类型化影响着行为人的出罪与入刑。既有的以故意犯中的行为支配要素为标准的方案存在着理论的根基不当与事实缺省问题,有必要从危险接受理论的“本土资源”出发,考察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是否结成了危险接受共同体,过失结果的归责在共同体层面得到消解,阻却对共同体内部的个人归责;反之,若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过失结果的出现意味着行为人没有正确掌控风险,违背了被害人反对结果发生的信赖,应当承担过失责任。
关键词:危险接受;行为支配;危险接受共同体;被害人信赖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2-0062-07
一、问题的提出
肇端于德国判例学说的危险接受理论,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产出了诸多教义学成果。例如,危险接受理论的适用领域是过失犯罪,只有结果的发生才具有刑法意义;被害人的接受对象仅限于行为的风险,而未接受此种风险的现实化;危险接受的体系定位是违法阻却事由,在与共犯理论关联的意义上,根据何者支配了危险行为,将危险接受案件类型化为自己危险化的参与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 1 ],前者因缺乏构成要件符合性而一律阻却违法,后者则原则上不阻却违法性,仅在被害人间接支配了危险行为时才例外地阻却违法。前两点教义学成果几乎获得了所有学者的认同,成为了学界探讨危险接受的理论基底,但是对于危险接受理论的类型化这一点,则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质疑。有的学者批判这种类型化立场的合理性,认为正犯与共犯的理论不适用于过失犯领域,所有对过失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都是过失正犯[ 2 ];有的学者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之争出发,认为我国刑法不是共犯从属性的立场,因而不能将之作为解决危险接受理论的前提,否则会造成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的局面[ 3 ];还有的学者认为“自我危险化的参与”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在规范上具有实质的相同性,这种区分仅仅具有将案件分类的作用,而不具有规范上的意义,应当放弃这种类型化,给予二者相同的(排除不法的)评价[ 4 ]。可见,批驳“自我危险化的参与”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类型化方案的观点主要集中于对将故意犯罪的正犯与共犯理论移植到解决阻却过失犯违法性的危险接受理论的反对。
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这种移植具有巧思之处,试图用行为支配这一要素贯通于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之间,进而达致体系的协调。但是,贸然移植难免产生“排异”,解决一个理论问题首要考虑的应是从问题本身的内涵与逻辑出发,寻找解决该问题的“本土资源”。因此,从“危险接受”这一自身要素出发,尝试从行为人与被害人是否构成危险接受共同体的角度,对危险接受理论进行再类型化,方能圆满化解以行为支配为标准进行类型化的理论难题。
二、“行为支配”类型化方案的理论检视
危险接受问题诞生于德意志帝国法院的梅梅尔河案,确立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海洛因注射器案,而最终类型化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加速试验案[ 4 ] 115-142。详言之,在加速试验案中,S和J为了拍摄下赛车的全过程,分别坐上了B和H的赛车。当两辆赛车在两车道公路上高速行驶时,为了超过前方正常行使的车辆,B和H同时作出了危险的超车行为,导致发生车祸,造成了J的死亡后果。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作出超车决定的是B和H,具体实施超车行为的也是二人,综合评判二人对整个事件起着完全的支配作用,因此B和H除构成危害道路交通罪外,还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否定了J的危险接受对其死亡结果的违法阻却。据此,行为支配将海洛因注射器案确立的危险接受理论进一步划分为被害人自己实施了危险行为的“自我危险化”和被害人参与他人实施的危险行为的“他人危险化”,并且认可了二者间在违法阻却上的不同功能。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也持相同的观点,主张在与正犯论相关联的意义上区分二者[ 1 ]。运用正犯理论来对危险接受案件进行类型化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疑问。
(一)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理论运用于危险接受的正当性存疑
危险接受属于过失犯领域的子问题,要确定正犯与共犯区分的理论能否适用于危险接受,首先要经过能否适用于过失犯的检验。而这一检验实际上确定的是正犯与共犯理论本身的辐射范围。在共犯的本质问题上,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着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争论。前者认为,共犯要求行为人之间只能就某一具体的犯罪成立犯罪;后者认为共犯是一种不法形态,只要行为人之间就行为就各自实施的行为具有意思联络即可,最终成立的犯罪与行为人各自的责任有关,因此可能成立不同的犯罪。如果采犯罪共同说,当被害人“自我危险化”时,其本人无论如何也不成立犯罪,只具有参与的他人成立单独犯罪的空间,因而不适用共犯论,这是当然的推论。问题在于如果采行为共同说,共犯论又能否适用于过失犯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即使是将共犯看作一种不法形态,也存在着故意的不法形态与过失的不法形态之分。行为无价值二元论为了发挥构成要件的类型化机能,将故意和过失作为主观的违法要素纳入了构成要件,因此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构成要件层面即可區分出来,而不必等到责任层面。相反,结果无价值论者则将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要素考察,认为故意犯和过失犯在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层面别无二致,区别仅在于责任要素的不同,进而得出不法形态无故意过失之分的结论,为共犯论适用于过失犯开辟出道路。笔者认为,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观点更具有合理性,符合物本逻辑,厘清了事实与认识的关系。行为人在实施某一犯罪行为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意志,例如,行为人在下出租车时顺手将上个乘客遗留的财物带走,即使不考察责任层面,仅从“取走他人财物”这一客观要素,也能得出行为人具有盗窃罪不法的结论,而不可能认为行为人是过失。故意和过失与行为、对象和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要素的关系远比于与责任年龄、责任能力等责任要素关系更为密切。此外,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是在事后立场对已定型犯罪进行的追问,但这种追问影响的是对犯罪的认识顺序,本质上并无不同。换言之,在结果无价值论尚未检讨责任要素时,某个犯罪是故意犯还是过失就早已确定了,将二者的差异归结于责任要素可能并不是事实的真实面貌,而是一种理论安排。相比之下,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理论安排更贴近现代心理学对于行为与意志的研究成果。所以,当不法形态具有故意和过失之分时,就不能认为共犯理论可以理所当然地适用于过失犯。
其次,共犯理论解决的是正犯与狭义共犯的关系问题,而狭义共犯只可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德国刑法第26、27条分别规定,故意教唆或帮助他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方可成立教唆犯和帮助犯[ 5 ] 13。换言之,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成立需要满足两个故意,即正犯实施违法性的故意和共犯实施教唆或帮助行为的故意。故德国刑法理论一般不承认过失的教唆犯和帮助犯[ 6 ] 10。我国刑法的立场与之相同,在第25条共同犯罪的概念中强调了“故意犯罪”,表明了共犯理论旨在解决故意犯罪领域的多人犯罪。究其原因,相比于单人犯罪,多人参与犯罪,法益侵害结果更容易发生,行为人躲避抓捕的可能性更大[ 7 ] 312。而这种相较于单人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共同犯罪行为人之间的谋划与协作,非多个过失行为竞合在一起所能实现。在危险接受类型的案件中,危害结果是在行为人和被害人共同不注意的情况下出现的,只不过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其自身的过失不具有刑法意义,仅追究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当二者成立共同过失( 1 )尚存疑问时,遑论成立共同故意。
最后,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过失犯领域适用的是单一正犯体系,而故意犯适用的是区分制正犯体系,不能将区分制下的共犯理论套用到过失犯上。虽然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但是达致法益侵害的路径有所不同,如罗克辛教授就曾建立支配犯、义务犯和亲手犯的三元正犯体系[ 8 ] 584。在这一体系下,身份犯和不作为犯均是通过对义务的违反而造成法益侵害成立犯罪的。而新过失论认为,过失的本体在于违反了结果回避义务[ 7 ] 164,并且学者亦认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与过失犯的结果回避义务实际上是相同的义务[ 9 ] 245。在这意义上而言,作为区分制正犯体系核心概念的行为支配理论就难以说明过失犯的正犯性,过失犯罪的正犯只能是每个违反注意义务、有助于实现构成要件之人[ 10 ] 887。换言之,对于过失犯的犯罪参与体系只能是单一的正犯体系,违反了注意义务,与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力的人都是正犯。因此过失的教唆犯和帮助犯符合上述条件也能被认定为过失正犯,而不再适用共犯从属性。与正犯理论相关联的意义上区分“自我危险化的参与”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正犯理论与故意犯罪具有高度适配性,导致套用到过失犯罪中反而根基不稳、疑窦丛生。
(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理论运用于危险接受的具有事实缺陷
理论的形成,存在着建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路径,前者强调人对理论的设计,后者强调人对事实的接受[ 11 ]。毫无疑问,危险接受理论的形成路径属于后者,其并非是理性建构的产物,而是来自德国判例实践的经验升华。其判例基础包括1923年德国帝国法院“梅梅尔河案”、1925年德國帝国法院“摩托车案”、195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赛车案”、1962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天花医生案”、1972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警察手枪案”、1997年杜塞尔上级法院的“车顶甩落案”和2008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加速试验案”。正是凭借法院和学者对上述案例进行阐明和评述,如今的危险接受理论的概念与类型才得以形成。从事实到理论的经验升华的过程中,研究者要以充分认识经验现象为前提,在梳理分析因果链条的基础上,阐释经验内涵的价值,从“经验”中“推出”理论[ 12 ]。因此,对危险接受理论既有类型化的事实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以行为支配为标准进行类型化的理论存在如下事实缺陷。
首先,与正犯论相关联的类型化观点将行为支配与危害结果之间进行了不适合的绑定,最终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偶然的结果。以梅梅尔河案为例,该观点认为,船夫实施了驾船行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行为支配,因此属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应当追究其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责。但是可以发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并非是一开始就能够确定的结果,换言之,渡河行为也可能发生船夫死亡,乘客幸存的局面。根据上述观点,此时案件的类型又变为了自我危险化的参与,乘客无责。似乎并非单是何者支配了行为起到了类型化案件,进而决定违法性阻却与否的作用,而是当结果没发生在行为支配者身上时,才能确定。这种绑定是不合理的。行为支配在结果发生前就能确定,而具体结果的发生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当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叠加后不难看出,实际上是不确定的结果主导了最终的归责。这个结论实际上推翻了上述类型化以“行为支配”的标准。
其次,正犯论相关联的类型化观点对危险接受案件事实的归纳不够全面,放弃了行为支配者可能同样具有危险接受以及行为人和被害人共同形成支配的事实情形。学界一般认为,危险接受阐述的是这样一种事实:“明知自己实施或参与他人某种行为存在风险,但仍然自愿实施或参与”[ 13 ],并最终导致结果发生。所以危险接受首先是一个个体接受法益侵害风险的事实概念,而非一开始就具有保护倾向的价值观念。在梅梅尔河案中,船夫在乘客的百般请求下最终决定驾船渡河,此时不仅是乘客接受了渡河的风险,船夫也同样作出了接受风险的决定,并且这种危险接受的决定是乘客推动形成的,不能因死亡结果仅发生在乘客身上就放弃这一事实。因为,如上所述,具体结果发生在谁身上具有偶然性,倘若最终发生的是船夫死亡、乘客幸存的结果,在学界普遍承认过失犯领域采用的是单一正犯体系的理论背景下,就可能存在着要求不具有行为支配的乘客为船夫的死亡承担过失正犯责任的空间。这种可能性彰显着法律对于公民的平等保护,尤其是在过失犯下行为人并不具有对社会的敌视态度时尤为重要。例如,在二人互相斗殴时,在杜绝死亡结果出现的意义上,斗殴的双方都是法律的保护对象。此外,以行为支配为标准的类型化方法正确解决危险接受案件的潜在条件是,只有其中一方具有行为支配,被害人一方只能接受这种行为支配的风险。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双方共同支配行为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甲和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共同采下了一丛毒蘑菇,共同烹饪然后进食,最终导致甲重伤和乙死亡的结果;又如,丙和丁为寻求刺激,在未充分检查降落伞装置时就进行双人跳伞,最终导致丙重伤和丁死亡的结果。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恐怕就不能根据行为支配将死亡结果完全归属于幸存者。
最后,强调行为支配对于危险接受类型化的意义,与危险接受理论的形成路径相违背,存在以规范框定事实,而非由事实上升到规范的逻辑颠倒之嫌。危险接受理论作为经验主义的产物,遵循的是一条由事实归纳到理论升华的生成道路。这条道路指向的是违法阻却的终点。正如张明楷教授曾对危险接受的案件进行归纳后指出,“上述介绍给人的印象是,凡是属于危险接受的案件,均阻却犯罪的成立。”[ 1 ]但稍后其反驳道“事实上并非如此”。张明楷教授的上述言论反映出基于经验主义生成的理论的共同困境,即在对已知的事实的歸纳仅是部分归纳,而不能穷尽所有情形,因此基于前者升华的理论就面临着例外的现象。要化解这个困境有两种方案:其一是坚守理论已有的内涵与外延,谨慎对待理论形成之后的相似事实的归结与纳入;其二是以“原则—例外”的模式扩张既有理论的内涵与外沿,修正既有理论。以“行为支配”为标准的类型化方法采取的就是第二种方案,在承认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属于危险接受的情形下,否定其违法阻却的功能。相比之下,笔者更支持第一种方案。原因在于,第一种方案有利于保持理论的本真,减少理论的“骑墙派”,也不至于在本就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上继续叠床架屋,进一步复杂化,同时也不会影响具体案件的正确处理。例如甲明知道乙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仍然决定坐上车兜风,后乙因驾驶失误,导致其车越过道路中线,与它车相撞,造成甲重伤的结果。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应当将本案归纳为危险接受的“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同时认为乙应当承担过失致人重伤的责任。这个结论在笔者看来,如果坚持这种情形仍属于危险接受,实际上就否定了危险接受阻却违法性的基本法理,否则就必须承认,不属于危险接受的类型。根据笔者的见解,本案并不属于危险接受的类型。被害人危险接受的对象是对于自身法益具有侵害风险的行为,风险附着于行为而存在,因此不能笼统地认为是接受风险。既然“侵犯公法益的犯罪,不存在危险接受问题”[ 1 ],那么对具有侵犯公法益危险的行为也不能进入危险接受的领域内。乙醉酒驾驶的行为是一个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甲并不具有接受的权限,因此此时并不存在危险接受,当乙驾车失误造成甲重伤,自然应当承担过失致人重伤的责任,这一责任已经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结果所包含。
除此之外,江溯教授根据对自我负责的同意和同意他人的危害的三个共通特征的归纳[ 4 ] 142,认为应当对这两种类型的危险接受给予相同的规范评价,即“应当承认两者均有排除行为人之不法的效力,并且在这一前提下探讨这种排除不法的正当化根据。”换言之,取消以“行为支配”为标准的类型化,肯定其违法阻却的功能。笔者赞同江溯教授的基本立场,进一步认为,可以根据行为人与被害人是否结成危险接受的共同体为核心标准,将部分案件排除出危险接受的范围,进而还原危险接受阻却违法的理论本色。
三、本文见解:以危险接受共同体作为核心标准进行类型化
在与正犯论相关联的意义上,根据是被害人还是行为人具有行为支配为标准,将危险接受类型化为“自我危险化的参与”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的观点,存在上述说理和事实上的缺陷,不能圆满地解决危险接受理论的难题。究其原因,行为支配在故意犯罪中属于核心要素,而对处于过失犯领域的危险接受问题则可能“橘生淮北”。因此,放弃行为支配转而从危险接受理论中发掘“本土资源”就显得具有合理性。传统的危险接受理论站在事后立场,将危险接受的主体锁定在了被害人身上,而把同样参与或实施了危险行为他者仅仅作为一个待追责的主体,缺乏对其全盘审视。如果以一个事前和事中的立场审视危险接受案件,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情形:被害人与他人共同接受风险和被害人独自接受风险的情形。下文将对此展开进行阐述。
(一)被害人与他人共同接受风险
被害人与行为人共同接受风险意味着,被害人和他人均认识到、接受了即将实施的行为可能对自身法益产生的风险,并且也彼此认识到对方法益面临的相同风险。在最终的结果因双方过失的共同作用下发生时,可以认为被害人与他人之间结成了一个危险接受的共同体,过失结果的归责在这一共同体层面因共同体的自我答责而被阻却,不再对共同体内的个体产生作用。原因在于,过失犯中行为支配并非确证正犯的标准,所有违反注意义务的人都应当被当作过失正犯,行为具体由谁实施对于结果归责的意义不再如在故意犯罪中重要。当被害人与行为人决意共同接受危险时,也意味着二人注意义务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并非是将一方的特殊义务强加于另一方,而是指应当对这种特殊义务违反造成的结果一并承担责任。从被害人自我答责上来说,由于行为人与被害人结成危险共同体时,二者都是潜在的共同危险行为的被害者,因此有必要基于同等保护的意义上对这一共同体人格化,适用自我答责理论。
例如在梅梅尓河案中,德意志帝国法院则是在认为乘客的危险接受阻却了船夫的注意义务的角度来否定船夫的过失罪责的[ 4 ] 118。笔者认为,在暴风雨中渡河的风险问题上,乘客与船夫之间达成了一致,结成了危险接受的共同体,危险行为的实施可以视作这一共同体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因为船夫在具体的事实层面操纵了行为就将该行为产生的所有结果都归责于船夫。因此最终无论发生的乘客死亡还是船夫死亡的结果归责应当在共同体层面被消解,而不再追究共同体内个体对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的承担。被害人与他人成立危险接受的共同体,必须考虑以下三种情形:
其中一方具有更优越认知时,否定危险接受共同体的成立。危险共同体的成立要求被害人与行为人对危险具有共同的认知,既不能是被害人具有更高的认知,也不能允许他人具有更高的认知。原因在于,如果其中一方具有更高的危险认知,就意味着,另一方以接受的是较低的危险,而非实际上存在的高度危险。当双方的认知不匹配时,不能成立共同体。例如,甲与乙均是同性恋者,甲明知自己曾与HIV患者进行过危险性行为,虽然自己尚未检测确诊,但仍隐瞒了这一事实,与乙发生了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在此案中,表面上看,甲与乙进行无套性行为是一种共同的危险接受,但是由于甲确诊HIV阳性的可能性极大,而乙对此并未认识到,双方对彼此面临的危险并无相同的认知,不能成立危险接受的共同体,如果最终造成乙感染的结果,甲至少应当承担过失的责任。又如,在日本千叶赛车案中,由于被害人作为经验丰富的赛车教练,对于危险的认知明显优越于初学赛车的被告人,因此二者不能成立危险接受的共同体而直接阻却死亡的结果的归责,必须实质考虑被害人与被告人何者对结果的因果力作用。在结合被害人对危险的态度和高度认知以及在结果发生过程中对被告人行为起到的事实控制的基础上,应当肯定被害人自我承担死亡结果。
危险接受共同体接受的只能是个人法益的危险,而不能是集体或社会法益的危险。虽然,被害人同意理论不能直接适用于危险接受案件,但阻却违法性的实质理论均在于危险行为符合被害人自我决定[ 14 ],因此可以在理论构造上对二者进行比较。被害人同意理论认为,被害人必须对被侵害的法益具有处分权限[ 15 ] 297,亦即只能对涉及自身的个体法益侵害进行承诺,而不能承诺对集体法益、社会法益的侵害。同理,危险接受的主体也只能接受可能对自身法益造成法益侵害风险的行为,而无权接受对集体法益、社会法益的危险行为。这就可以将醉酒同乘类型的案件排除出危险接受共同体的范围。具体而言,甲虽然明知乙陷入醉酒状态,仍然接受了其要求搭乘乙车兜风的邀请,最终由于乙因为醉酒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而致甲重伤。表面上看,甲与乙就醉酒驾驶的危险作出了共同的接受,但是不能承认二者结成了危险接受的共同体。风险附着于行为才能存在,接受风险,实际上是接受风险背后的行为。乙醉酒驾驶的行为已不再是一种仅针对甲个人安全法益的危险行为,而是威胁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作为社会个体的甲不能代表社会或集体接受这种危险行为。故甲重伤的结果应当归责于乙的醉酒驾驶行为,而不能阻却。
当任意一方脱离危险共同体时,先前共同的危险行为赋予了其救助另一方的义务,应当在不作为犯的框架下重新考量。危险接受共同体的结成,具有三个方面的共同意涵:其一是对于彼此面临危险的共同接受;其二是对于共同危险行为造成后果的共同承擔;其三是对于结果的共同反对以及基于这种反对产生的互相救助的义务。当危险行为现实化为结果过程中,这种救助义务因个体陷入危险而有所缓和,同时也会因个体脱离危险而加强。如果共同体任一方脱离危险后,在具有救助能力和救助可能性时,仍放弃救助他者造成结果的,仍应追究其过失犯罪的责任。后文的“冰上行车溺亡案”对被告人追究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根据即来源于此。
(二)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
当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时,无论该危险是由他人与被害人共同创设,还是仅由他人独自创设,都应当将过失结果归责于他人。理由在于,当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但并未接受危险现实化的结果,所以其接受危险的前提是足以信赖并未共同身处危险之中的他人,能够采取避免危险化的措施结果的出现,或者说是创设危险的他人提供了这种信赖。而在因发生结果从而进入刑法视野的案件中,他人恰恰是推翻了这种信赖。例如,被告人与被害人在小汽车内发生性关系时,被害人为了追求快感,请求被告人共同用手掐自己的颈部。后来被害人因颈部外力陷入机械性窒息,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本案中,被害人独自接受的危险虽然由被害人与被告人共同创设,但是被害人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危险行为,是因为有理由信赖处于安全处境中的被告人能够避免致其死亡的结果,事实上,被告人只要掌握适当的力度,密切关注被害人的状态即可避免悲剧的发生。但很明显被告人推翻了被害人的安全信赖与期待,应当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张明楷教授认为,倘若本案是被告人单独用手掐被害人的颈部,就属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应当将死亡结果归属于被告人,但由于本案是由被告人与被害人共同用手掐被害人的颈部,就不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 1 ]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由于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与濒死的求生本能存在,个人不可能通过自己掐自己颈部或者屏住呼吸的方式自杀,在被害人与被告人共同掐被害人颈部时,实际起到关键作用的仍是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告人单独掐被害人颈部的行为在致死的关键性上并无太大差别。分别考虑并不会造成难以确定结果是由谁造成的结论。相反这一结论的产生恰恰是过于看重谁具体实施了行为这一标准造成的。
可能产生的质疑是,当他人为吸毒者提供吸毒工具,尔后吸毒者自己吸毒过量死亡时( 2 ),按照本文观点似乎属于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的情形,最终可推导出提供吸毒工具者需承担过失致人死亡刑事责任的不合理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会影响本文观点的贯彻。具体而言,虽然笔者并不支持以行为支配的标准来说明危险接受违法阻却的根据,但是危险并非凭空而来,所以仍需要考虑危险的创设问题。当危险由他人和被害人共同创设或者仅由他人创设,同时陷入危险之中的只有被害人时,他人才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整体而言,单纯提供吸毒工具的行为或许可以被评价为参与创设被害人吸食毒品的危险,但离参与创设被害人过量吸食毒品死亡的危险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并不属于本文所认可的被害人独自陷入危险的危险接受类型。例外的情形是,当提供吸毒场所的人员同时提供吸毒工具导致吸毒者过量吸毒而死亡的情形,则属于本文所认可的不阻却违法的危险接受类型。这是因为场所的提供这一先行行为,对行为人产生了“基于对法益的危险发生领域的支配产生的阻止义务”,所以行为人应当承担容留他人吸毒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的刑事责任。此外,如果是在吸毒者群体之间相互借用或者提供吸毒工具,那么这种行为就像普通人借用日常用品一样平常,即使被害人使用该工具过量吸毒死亡,也不一定会进入刑法视野。因为违法性抑或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其必须能够还原为一定群体的价值观,一定群体的价值观又必须能够确证为构成群体的每一个人所大体具有的价值观[ 16 ] 31。这也正是行为支配理论下自我危险化的参与类型阻却违法的实质根据所在,只不过将之外化为了缺乏行为支配这一表象。因此如患有血友病的甲向邻居乙借用菜刀,结果自己不慎割伤手指导致血流不止而死亡的例子不可能要求甲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一样,吸毒者之间相互借用工具导致吸毒过量死亡的,同样不能仅根据发生死亡结果而要求提供工具者承担刑事责任。
四、具体案例的检验
案例一“相约游泳试水身亡案”:大学生周强、刘卿、刘敏相约到河边渡口游泳,刘敏提出到水最深处看看河水到底有多深,其余二人表示同意。由于害怕危险,三人以手牵手的方式向河中央走去,由于手未拉稳,一起掉入了河中。刘敏和刘卿因被冲到岸边被人救起幸免于难,而周强则溺水身亡[ 17 ]。
对于本案张明楷教授认识到“三人牵手试水的行为,对各自都是一种危险行为”[ 1 ] 180这一点,但没有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得出结论,而是最终以被害人周强的行为不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而否定刘敏和刘卿的责任。笔者认为,这不过是就事论事的循环论证[ 2 ],没有说明危险的接受阻却违法的特殊性。周强接受该种危险的前提是信赖三人拉手的协作行为能够有效地避免危险结果,故三人手拉手试水的行为不能简单分解为三人试水的行为,而应当作为一个危险接受共同体的整体冒险,进而应当肯定死亡结果的归责在共同体层面被消解,幸存的刘卿和刘敏不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
案例二“冰上行车溺亡案”:被告人钟平为了近距离观赏野鸭,在查看冰层厚度并试走后,邀请被害人龙丽娟与其一同乘车穿过冰面,龙丽娟表示同意。但当汽车行驶到河岔中心时,冰面破裂,二人落入水中,钟平爬上岸后既未采取抢救措施,亦未报案,悄然离开了现场。最终龙丽娟溺水身亡。张明楷教授认为,被告人钟平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原因在于其完全掌控了风险,龙丽娟的死亡属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笔者认为,虽然本案与案例一一样,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了危险接受的共同体,但在具体事实上有别,因此处理结果上也有所不同。案例一和案例二中,幸存者都脱离了危险接受的共同体,但是前者刘卿与刘敏是被冲到岸边被人救起,而非依靠自救行为脱离危险,并且周强也沉入水中被冲走,二人既无再实施救助行为的能力,也无救助的可能性,因此阻却了结果的归责。但是案例二则不同,钟平自行上岸后离开,既未尝试救助,也未报警。这才是导致龙丽娟死亡的最终原因,因此钟平应当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脱离了危险接受共同体的人,基于先前共同的危险行为以及团结义务,有必要对仍陷入危险中的他人提供救助,否则仍可能成立过失犯罪。
案例三“艾滋病人性交案”:女被害人明知男被告人患有艾滋病而同意在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之发生性行为,并因此感染艾滋病( 3 )。张明楷教授认为,在这样的场合,形式上是二人共同作用导致被害人感染艾滋病,但被告人并没有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也没有隐瞒患艾滋病的事实,是否发生性关系进而是否感染艾滋病完全由被害人支配,而不能认为被告人支配了实害结果的发生[ 1 ] 174。但事实明明是二人共同行为导致的结果,为了规范处理上的妥当却只承认一方起到了支配作用,难言合理。退一步讲,同样也可以说是被告人支配了实害结果的发生,因为如果被告人坚决拒绝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也能阻止结果的发生,故上述观点并未切中要害。笔者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应当承担过失犯的责任,原因如下:实际接受和面临感染艾滋病危险的只有女被害人一人,与被告人的危险接受共同体并不成立,因此属于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的情形。由于男被告人作为艾滋病感染者,本身属于危险源,其避免他人感染艾滋病的义务来源于对危险源的监管或者说对自身行为的控制,例如不能参加献血活动、不能与他人进行无保护的性接触等。这类注意义务涉及对公共安全的保护,不会因被害人的危险接受而缓和。因此当违反这种义务造成他人感染艾滋病时,应当承担过失犯的责任。
五、结论
对危险接受的类型化,应当立足于危险接受本身,根据被害人与他人是否结成危险接受的共同划分为危险接受共同体和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两种类型。就前者而言,危险行为具体由谁实施并不重要,因为基于共同的危险接受,过失结果的归责已在共同体层面被阻断,原则上阻却违法;对于后者,被害人独自接受危险时的前提是对他人对危险的掌控不至于危险现实化为结果,如果他人违背了被害人的这种期待,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应当承担过失的罪责。
注释:
(1)刑法理论即使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也要求二人以上具有相同的结果回避义务,并且都没有回避结果的发生。但是在危险接受中,被害人与行为人的结果回避义务不可能相同,例如在梅梅尔河案中,被害人的结果回避义务体现在不强行要求船夫渡河即可,而行为人(船夫)的结果回避义务则是安全地将乘客渡过河。
(2)此例不包括他人事先具有杀人故意或者被害人已经陷入意识不清等情形。
(3)Vgl.OLG Bayern,NJW 1990,S.131.转引自庄劲:《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之反思》,《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第60页。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中危险接受的法理[J].法学研究,2012,34(5):171-190.
[2]庄劲.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之反思[J].法商研究,2017,34(2):55-63.
[3]何立荣,陈晨.刑法中的危险接受理论之否定[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5):166-173.
[4]江溯.过失犯中被害人自陷风险的体系性位置——以德国刑法判例为线索的考察[J].北大法律评论,2013,14(1):115-142.
[5]徐久生.德国刑法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3.
[6]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犯罪行为的特别表现形式[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
[7]周光权.刑法总论[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64.
[8]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584.
[9]山口厚.刑法总论[M].3版.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45.
[10]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下)[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887.
[11]童德华.非法经营罪规制目的的预设与生成[J].政治与法律,2021(4):53-67.
[12]杨子潇.经验研究可能提炼法理吗?[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26(3):207-224.
[13]车浩.过失犯中的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J].政治与法律,2014(5):27-36.
[14]蔡颖.被害人同意與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统合——以刑法中被害人同意的对象为视角[J].法学评论,2021,39(5):47-57.
[15]张明楷.刑法学[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297.
[16]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1.
[17]程成.相约游泳试水身亡,甘愿冒险责任自负[N].检察日报,2008-11-01.
[责任编辑:马好义]
收稿日期:2022-04-18
作者简介:陈强(1995-),男,四川泸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