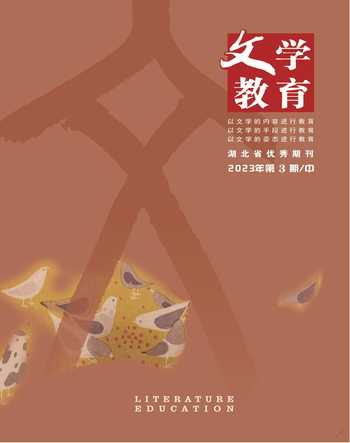我的同事徐纪明

在我的待人接物中,凡是只高我一个年级的,我都直呼其名,不喊为老师。对徐纪明,也是这样,从未在他的名字后面缀一个“老师”。窃以为,这样称呼是以平辈关系相处,没有客套,也不拘礼,随和,随意。
说起来,我是他的同乡。那年,我老家的小县被并到他的大县里去了。不过我从来没有以自己是他的老乡自居。原因有二:一是不愿攀高枝,免去沾光之嫌;二是当年要合并时,我们县有些干部很不情愿,说过一些领导不喜欢听的话,甚至组织一些人上访,据说一度还形成了相当的场面。最后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丢了官,降了级。在潜意识里我站在他们一边。当然这些和徐纪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我知道,他的家境不好。每每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拨出一部分钱赡养有病在身的母亲,还要资助境况不佳的弟弟。这从他日常的穿着可以看出。他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没有资本捯饬自己,总是朴朴实实的那般模样。我依稀记得夏天的傍晚他穿一条宽松的长裤,一件几乎可以透肉的背心,拖一双拖鞋在校园林荫道上一边散步一边和人交谈的情景。夕阳花花点点地洒落在他并不怎么高的身上。
我听过他一次课。那是中文系组织的公开课。他讲的是赵树理及其《三里湾》。他条分缕析,由浅入深,把《三里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烙印在听者的脑际。他的课堂语言干净流畅,词汇丰富,语调抑扬顿挫,该轻则轻该重则重,不拖泥,不带水,没有夹杂这个那个之类的口头禅。可以不夸张地说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依那时的惯例,课后进行了评课。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惟记得朱伯石老师在肯定的基础上,以商量的口吻轻言细语地说还是有一点瑕疵,把赵树理的《三里湾》的艺术手法说成“老一套”,不怎么妥。这个所谓“老一套”是赵树理自己对《三里湾》表现手法的一种谦逊的说法,徐纪明是暗引,而不是明引。换了别的老师,可能会说明一下。徐纪明没有。
有一阵,坊间传说他要到学校任党委副书记,这并没有成为事实。对徐纪明而言,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这样的愿。有,人之常情,没有,也是人之常态。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坊间传说至少表明他的德、才、能的某一方面或各个方面曾被有关领导或组织部门注意过看好过肯定过。不像我这样的平头百姓从来就没有进过领导的眼帘,即使中规中矩地站在领导眼前,领导也不曾拿眼睛的余辉瞟一眼。徐纪明到底不一样。
然而,他确实担任过中文系系主任。他担任系主任的功过是非,我无从评说,也没有资格评说。我只记得,每逢全系开会的时候,他手拿一个小本本,有条不紊地不紧不慢地传达着学校的有关精神,讲说着中文系的近期工作和下一段的安排,语言干干净净,利利落落,不枝不蔓,要言不烦。记得有一次,他说到台湾一个什么代表团来学校访问的事,当时有老师从坐位上站起来插话说明有关情况,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跟着又说了一些话。今天看来,他那时还没有练就宰相肚,还撑不了船。这也不足为怪,一个普通平民家庭出身的人,怎么可能像那些在干部大院军区大院长大的人那样,什么拿起,什么放下,先什么,后什么,亲谁,疏谁,远谁,近谁,怎么样不动声色地一枪不举一刀不挥地就把一切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任何人想动弹都动弹不得。
我与徐纪明没有多的交往,偶尔碰到也只聊几句,但都是片言只语,没有深谈。他总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显得有些苦不堪言,有些欲说还休,还有类似于一地鸡毛的叹息。最后总免不了反复嘱咐我不要对他人说起。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22年11月20日下午在大操场上参加离退休工作处和学校老协组织的老年人金秋健行。行完之后,他提着纪念品洗衣液,我也提着纪念品洗衣液。一起走到音乐厅侧住在华大家园的教职工候车的地方。他说他走不动了,要歇歇,我要帮他提,他不肯,叫我先走。于是,我先走了。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他是2022年12月27日离开这个世界的,与我见到他只隔了一个月零七天。
我写下如此不像样的文字,倒不是我怎么会写,也不是因为徐纪明有怎样了不得的功量。仅仅是因为我们毕竟相遇于昙华林共事于桂子山,多少有点交际。更何况,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是一个无害人之心的人,是一个值得我时时记起的人。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想法,希望文学院的领导能够启动一件事,为曾经在中文系或者文学院工作过的已经调离或者已经故去的老师建一张卡片,写下他們和她们的生平及在中文系或者文学院工作的起止时间。时间不论长短,字数几百即可。当我们闲暇无事时,可以去翻阅去抚摸那些卡片。一张卡片上的寥寥数语或许能够承载并表达我们对那些同事的怀想与惦念。这样才不枉相遇一场,共事一场。
刘安海,文艺理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